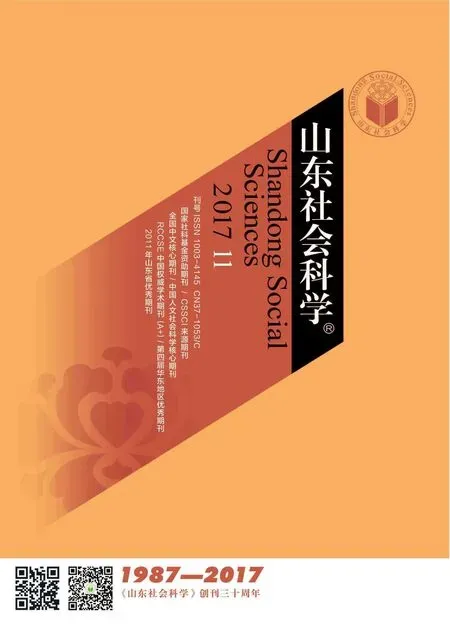叙事修辞与潜文本
——凌叔华小说创作的一种解读
2017-04-02赵文兰
赵文兰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聊城大学 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叙事修辞与潜文本
——凌叔华小说创作的一种解读
赵文兰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聊城大学 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素有“中国的曼殊斐尔”之称的“五四”女作家凌叔华,深受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影响,其小说创作明显地带有现代主义叙事风格的印记,表现在叙事修辞方面,则是反讽、隐喻、意象和重复等诸多手法的运用。在其小说中,凌叔华往往借助多种修辞手段,巧妙地表现出作品的深层主题寓意,使隐含在表层文本之下的潜文本得以浮现,既增强了审美效果,又实现了小说叙事与主题的完美统一。叙事手法的选择,在呈现作家精湛的现代短篇小说叙事艺术的同时,也使其多元思想和对世界人生的体认昭然若揭。
凌叔华;短篇小说;叙事修辞;潜文本
“五四”时期崛起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凌叔华,以其细腻的笔触、温婉的风格和敏锐的心理感知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鲁迅曾评价道,凌叔华所描写的是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①鲁迅:《鲁迅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1页。。沈从文也称其在中国女作家中,写了“另外一种创作”②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第2卷第5号,1931年4月15日。。夏志清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创造的才能上,其他“五四”女作家都比不上凌叔华,她的成就甚至高于冰心。③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 66页。孟悦和戴锦华则认为凌叔华“以一种女性方式接过了西方小说艺术并重建为一种适合女性表达的形式”④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5-96页。。作为一名现代短篇小说家,凌叔华的小说多涉及婚恋家庭题材,侧重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和中产阶级及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描摹。其作品主题多样,既揭示了旧式女子的生存悲剧和精神困境,又描绘了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格分裂,同时表现出异化世界中现代人的孤独和幻灭、疏离和隔阂。然而,与其深刻的主题意蕴相比,凌叔华小说创作的成就更大程度上却在于其形式特征的革新,表现为情节的淡化处理和散文诗的叙事笔调、内心独白和时空倒错等意识流技巧、客观而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以及隐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法等。凌叔华的小说是独特的,而其独特性也是有迹可循的。晚清以降,西学东渐,西方小说大量引入,包括凌叔华在内的“五四”作家从小说的形式层面对西方现代小说进行积极的摹仿。燕京大学外文系的教育背景、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交往,使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现代作家尤其是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影响。积极追求艺术技巧革新的她,甚至被徐志摩冠之以“中国的曼殊斐尔”的美称。正如陈平原所说,“五四”作家中真正掌握纯客观叙事技巧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凌叔华,前者受契诃夫的影响较大,而后者则直接师承曼殊斐尔。⑤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这无不是对凌叔华精湛的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极大肯定。
文学作品具有表层和深层双重结构,二者的区分在于形式性和生成性,作品的直接陈述与所要展示的深邃意蕴之间的关系常常是间接而隐蔽的。文学语言意在追求一种双重语境效果,语言符号除了其浅层语境中的字面意义外,还具有由深层语境所赋予的“言外之意”*参见狄其骢、王汶成、凌晨光:《文艺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文学语言通过暗示由表层文本指向蕴藉象征意义的潜藏文本。中西文学理论批评中,均可找到相似的言论。如亨利·詹姆斯曾说过,小说的主题不应显而易见,而应含蓄表达。*参见[英]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也意识到了文学语言的含蓄性,指出艺术的方法“永远是拐弯抹角的”*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而伊丽莎白·鲍温在谈到小说家的技巧时,同样认为“主题必须深蕴在故事中”*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中国文艺创作自古就有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力求创造一种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如庄子的“得意忘言”论、刘勰的“隐秀”说、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论、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境论、叶燮的“言在此而意在彼”说、王世禛“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以及王国维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说等。*参见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89、145、 184、246、279、345页。对于凌叔华的小说创作而言,其小说主题同样是内隐的,她往往借助叙事技法的选择,使蕴含其中的主题得以巧妙呈现,从而构筑起表层文本与深层结构即潜文本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虽然学界不乏对凌叔华小说的研究,但鲜有从叙事形式与主题意旨之关系的角度对其小说进行的诠释。本文拟弥补这一缺失,从叙事修辞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对日常语言的审美偏离,文学依赖于修辞,甚至可以说文学语言就是修辞。作为语言的基本结构,修辞意指对于普通用法的变换或反常,其中隐喻是最重要的修辞手法,此外,还包括转喻、提喻、反讽等其他多种方式,修辞构成话语的基础,并使其产生意义。文学语言的审美意义集中表现在它能创造出寓意或言外之意,而这一审美功能的发挥,得力于独特的修辞性表达方式。为了达到特定效果,包括凌叔华在内的现代小说家在创作中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在暗示人物复杂内心情感的同时,也使主题寓意得以呈现。本文旨在从微观层面实现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管窥,聚焦其小说的形式层面,选取叙事形式的一个维度——修辞的视角,采用整体细读的方法,从反讽、隐喻、意象和重复等方面,挖掘被表层文本遮蔽的潜文本,探究凌叔华是如何通过叙事修辞手段的选择,来揭示小说的深层涵义,从而达到其作品叙事与主题、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的。
一、反讽
反讽(irony)就是所言非所指,即语言的表层意思与它实际表达的意思相异,词语的意义被语境的压力所扭曲。布鲁克斯对此界定道:“反讽是由于语词受到语境的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的对立的语言现象。”*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戴维·洛奇则从读者接受层面强调了反讽效果的实现与读者的积极诠释之间的关系:“在修辞学里,反讽要表达的是与所说的话语相反的语意,或引导读者不按字面意思来理解……话语讥讽是通过诠释来领悟的……当读者清楚察觉故事所叙述的实情与故事角色对该事件的认识之间出现矛盾时,‘戏剧反讽’的效果便出来了。”*[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卢丽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而乔纳森·卡勒则对反讽进行了这番解读:“反讽把外表与实际相提并论,实际发生的与期待的正相反。”*[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作为深谙现代叙事技法的短篇小说家,凌叔华在其小说中也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反讽的修辞。借助这一手法,作家在小说的表层文本和潜文本之间、在表面语义和深层语义的冲突中构建了一种张力,往往使读者对故事的期待与叙事所揭示的真实之间产生冲撞,在营造戏剧性反讽效果的同时,其旨在表达的深层意旨也得以彰显和强化。代表性作品有《中秋晚》《有福气的人》《太太》《一件喜事》等。
在婚姻家庭题材小说《中秋晚》和《有福气的人》中,反讽的运用,揭示了人的异化主题,反映了作家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之本质的敏锐感知力。《中秋晚》的题目本身就具有反讽意义。中秋节本是和谐、幸福和美满的象征,中秋晚本应是家人团聚、共吃团圆饭的。但在敬仁夫妇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却因一个外人——敬仁的干姐姐而起争执,并最终导致关系破裂。得知干姐姐病重的消息后,敬仁连象征着团圆的团鸭也不吃就匆忙离去,这暗示着他们夫妻之间的疏离和隔阂。没见到干姐姐最后一面,他回来后大加埋怨,太太赌气回了娘家,没有吃团圆饭的中秋节以两人的不欢而散而结束。后来,敬仁太太虽被送了回来,但“夫妻之间……总觉得彼此心中新立了一块冰冷的石碑”。至此,读者臆想中的中秋晚的和谐温馨与故事所展示的冲突冷漠构成了强烈反差,女主人公对婚姻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现实生活中两人的疏离隔阂产生了巨大冲撞,而反讽意义也得以产生。可以说,反讽的运用,揭示了作品的潜在主旨,即现代婚姻中人的幻灭感和疏离感。《有福气的人》中的标题人物章老太在认识她的人眼中是最有福气的,一生衣食无忧,儿孙贤孝,样样心满意足,而她呢,对人慈和,无偏无相。全家上下,一片谐和。然而,在她六十九大寿后的第三天,她无意中听到了大儿子夫妇的谈话,才发现真相,明白了“她的有福”原来是虚无缥缈的,他们都是冲着她的钱来的,一直以来都是戴着一副假面具来哄着她,而所谓的“贤孝”,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章老太顿时产生了一种幻灭感。这样,令人惬意的表象与冷冰冰的现实之间构成的张力,产生了反讽效果,并凸显了作品的主题意旨:金钱驱使下物欲世界中人的疏离和冷漠。
而《太太》和《一件喜事》则通过反讽手段的选择,描绘了反叛和传统两种女性他者类型,使作家的女性主义意识得以流露。《太太》的标题人物是匿名的,暗示了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的失语状态: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的他者地位,自我缺失且没有话语权,只能作为某人的太太、孩子的母亲而存在。所谓的“太太”本应担负起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但故事中的这位太太却是以反叛他者的形象出现的,她摒弃了传统性别角色,只关心自己享乐,满脑子就是打牌,对丈夫、儿女毫不关心,为了筹钱,甚至把丈夫的狐皮袍子都给当了。当蔡妈跟她要钱给她儿女买生活用品时,她非但没给钱,反而说:“讨厌,早不要钱,晚不要钱,偏偏我出去打牌才要!今天先别买吧”,就坐上洋车打牌去了。结尾显然使读者的期待遭到逆转,他们会感受到题目预设的失语的传统女性他者和故事呈现的自我的反叛女性他者之间的张力,从而体会到反讽意义之所在。反讽的运用,使爱的缺失和人际的异化这一潜文本得到了彰显。《一件喜事》从孩童的视角讲述了凤儿父亲纳妾的事。题目本身也是反讽的。对于女人来说,结婚本是件高兴的事,但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作为他者的女性却没有自我,无力抗争,只能逆来顺受,在悲叹和啜泣中终其一生,可以说,只有死亡才是她们的归宿。凤儿的父亲娶六姨太太入门,五娘只是不作声地叹了口气,对凤儿说:“我只想死,死了什么都忘记了。”题目中的“喜”、凤儿父亲纳妾这一“喜”事与故事所透露的父权制婚姻中女性他者的“悲”剧命运之间形成了一种反讽性张力,作家的意图是用表面上的喜事来反衬故事的悲剧性潜在文本: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他者的生存悲剧,并对父权/夫权制度予以抨击。
二、隐喻
隐喻(metaphor),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打比方”,它涉及“感情、思想和行为的表达方式在不同但相关领域间的转换生成”*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版,第776页。。I. A. 理查兹认为,文学隐喻不是一种词的关联,而是“一种上下文的关系,一种事物之间的类比”*[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7页。。卡勒指出,“隐喻是最重要的修辞手法……是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我们通过把一种事物看做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而布鲁克斯则断言:“文学最终是隐喻的、象征的。”*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隐喻是象征的基础,象征是隐喻的提升。隐喻是艺术家对人类生存本质和境遇的领悟能力,现代小说中的深层结构基本上是隐喻结构。小说既有表层的情节结构,又有深层的隐喻结构,表层情节只是一种手段,小说家的目的是对人类生存深层模式的探究。*参见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4页。通过隐喻的中介作用,读者可体会到作品中被表层文本遮蔽的潜在内涵。追求语言的间接性表达和含蓄化效果的凌叔华在其小说创作中也自觉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格。她的小说里,一句话或者一个细微动作都能揭示人物本质或一个永不说出的主题。她往往借用多重隐喻和暗示,来展现人物矛盾复杂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揭示作品深层主题寓意。代表性作品包括《绮霞》《绣枕》《无聊》《病》等。
《绮霞》和《绣枕》描摹了两类不同的女性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礼教,并透露出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绮霞》指涉婚姻中知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主人公绮霞放弃了传统性别角色,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作出了艰难抉择,毅然抛弃家庭而投身事业,最终完成了从他者到自我的嬗变。绮霞喜欢音乐,但婚后的生活使她一度放弃了拉琴的爱好。在她心中,家庭胜于一切,“爱卓群就应当为了他牺牲一切”这句话暗示出传统思想对其影响之深,但最终自我占了上风,在丈夫和琴二者中,她毅然选择了后者,做了S女校的音乐教师。可以说,这一“中国娜拉”的出走,表明了其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决裂,隐喻着其对旧礼教的公然挑战以及对男性权威的彻底颠覆。另外,学生对绮霞的评论也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她一定没出过嫁,你看她多活泼多漂亮。”这句闲聊,却有着深刻的潜台词,喻指婚姻是女人的地狱,暗示出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的悲剧命运。《绣枕》中的女主人公是位深闺中的大小姐,匿名使其命运具有了普适意义。小说围绕着女主人公绣靠枕一事,揭露了封建制度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性。对于闺阁女子而言,婚姻是唯一的归宿,她们像待售商品,毫无自主权,无法把握命运,只能在幻想和幻灭中心灰意冷。绣枕这一行为被赋予了喻义,它规范了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暗示了女性生存悲剧的不可避免。为了找到一个好归宿,大小姐废寝忘食、倾注了全部感情和心血、精心绣的一对靠垫,却遭到了践踏、漠视和遗弃,而不知情的大小姐却还在梦想着自己嫁入高门并受到了其他女子的羡慕,直到真相揭露才从梦中惊醒。故事中靠枕的“不幸遭遇”一定程度上隐喻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受践踏、被蔑视的他者处境。可以说,隐喻的运用,在对女主人公施以同情的同时,也对封建旧礼教展开了无情的抨击。
《无聊》发出了作家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拷问。女主人公如璧是一个自我受到压抑的双重人格的女性他者形象。她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厌倦和失望、无聊和烦闷,得出“家即是枷”的论断。“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要给他带上一个枷?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要给人像养猪一样养着?”这句话揭示出传统婚姻对女性自我的压制,也表现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抗拒。但另一方面,她又是悲观而虚无的,常常发出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除了暗地里生气落泪,又会怎样?”“猪是该无聊的呵……还能有什么希望呢?猪,安安静静的在猪圈里歇歇吧!”*凌叔华:《绣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234页。这几句内心独白暗示出女主人公无力改变命运的妥协心态,表达出其对婚姻的幻灭。另外,标题本身即隐喻着主人公婚姻生活的不和谐,揭示出现代女性的精神困境。
《病》展示了凌叔华笔下两性关系的实质,表现出其消极的婚姻观。故事主要采用了男主人公的限知视角,叙事者对他的内心进行了透视。芷青是一个自私、冷酷、多疑而病态的人,这与他温柔、大度、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妻子玉如形成了鲜明对比。芷青得了重病,玉如为了挣够钱把家搬到山上去给他养病,瞒着他起早贪黑去朋友家画画出售,而他却怀疑她移情别恋,虽然最后真相大白,但他们已回不到当初了。小说标题即含有深层寓意,表层文本指涉男主人公生病的事实,潜文本却暗示其扭曲的人格和精神的病态,隐喻了他们婚姻关系的疏离、隔膜和不和谐。小说结尾是这样的:“她就势伏在他的肩上,过了一会儿他的肩膀上部有些暖和和的潮湿。”两人虽冰释前嫌,但他们之间将永远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结尾句暗示着他们关系的破裂。
三、意象
意象(imagery),用埃兹拉·庞德的话来说就是“在一刹那时间中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林骧华:《西方现代派文学综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休姆同样追求诗歌意象,主张通过形象来表达诗人细微复杂的思想感情。*参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新批评派关注语言的表层和修辞层面的意义,他们的细读法不可避免涉及对诗歌意象的解读。对他们来说,意象可以是一个物体或人物的具体形象,也可以是一个动作或一种感觉。韦勒克解释说,意象表示过去的感受或知觉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理查兹则表示,意象具有作为一个心理事件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参见[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另外,戴维·特罗特指出,“意象主义通过使文学更有文学性来使其获得现代主义的特征。”*David Trotter, “The Modernist Novel”, in Michael Levens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p.74.对于凌叔华的小说创作而言,意象手法的运用,是其精湛技巧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她的小说中,她往往不直接描述人物的潜意识或情感体验,而是借助一些暗示性的具体物象来传达。这种把平凡的事物置于意象主义框架之中、间接反映生活真谛的手法,使她的小说具有了一种诗的意境和新颖独特的艺术魅力。下面对凌叔华小说中“月亮”“花”“寒冷”和“镜子”等几种意象进行分析,挖掘出这些意象被赋予的深层意义。
凌叔华小说中最常见的要数“月亮”意象了,往往传递着其消极的婚恋观,如《中秋晚》。“月亮”象征着团圆与和谐,但故事中主人公婚后第一个中秋晚的月亮却被赋予了更多的反讽意义。此时的月光在太太眼中有一种“凄寂生感”;而敬仁看到的那轮圆月好像“正对他冷笑”。第四个中秋晚的月儿发出“微弱的光”,在院子里铺上“一层冷霜”。显然,月亮意象的运用,烘托了人物悲凄、孤独之情,暗示出夫妻关系的疏离和隔阂。而《他俩的一日》中的“月亮”意象则暗示着婚姻生活的缺憾、不美满。筱和因为照顾母亲而与丈夫棣生分离了一年,短聚两天后她又该走了,望着窗外的下弦月,棣生认为“还是满月可爱些。缺月终归是一种缺陷”;而筱和却不喜欢满月,觉得缺陷才是美。此处的缺月与满月,显然暗示着他们的分离与团聚,喻指他们和谐却不美满的婚姻。
“花”意象在凌叔华作品中比比皆是,其悲观的婚恋观同样随之流露。《茶会以后》涉及阿英和阿珠姐妹茶会归来的对话,反映出旧式闺阁女子的悲剧命运。故事弥漫着感伤和落寞的情调,而这通过“花”意象得以凸显。桌上的海棠花“已过盛开”,这是阿英昨天拿回家的,然而只一天,这些花“便已褪红零粉,蕊也不复鲜黄,叶也不复碧绿了……情景很是落漠”。显然,此处海棠花象征了两位老处女的一生,表达出她们对爱情和婚姻的幻灭感。岁月流逝,她们青春不再,只能在无望等待中孤独终老。《春天》讲述了女主人公霄音不满于沉闷、乏味的婚姻生活,向往婚外情而不可得的故事。全篇笼罩着一种阴郁、令人窒息的氛围,那株娇矜的海棠花连头都“一动不动”,这里“海棠花”意象映照了主人公烦闷的心情,暗示其婚姻生活的停滞。远处的琴声勾起了她对往日恋人的回忆,就在她给对方写信时,桌上的白玫瑰花却被猫碰倒了,水把信弄湿了,她试图摆脱生活的压抑、追求自我解放的努力也无果而终。此处被碰倒的“白玫瑰花”暗示了霄音对婚姻和爱情的幻灭。
凌叔华的小说中,“寒冷”意象也有着深层含义。如《再见》中,作家运用一系列 “寒冷”意象,衬托出女主人公偶遇昔日恋人后的情感变化,强化了她的失望和悲凉,从而揭示了“幻灭的爱情”这一主题。四年未见,西湖的邂逅使筱秋起初在见到骏仁时是惊喜的,但是他们的交谈使她意识到他变了,对他的好感荡然无存,她感到“冷气”阵阵回到心上。最后,她带着绝望的心毅然离去,虽然互道了再见,但相信她再也不会见他了。此时,“凉秋”的晚风散吹着她额前碎发,也同样吹着她早已冰冷的心。另外,《病》中,“寒冷”意象烘托了男主人公在怀疑妻子有外遇之后内心的痛苦,暗示了他对婚姻的幻灭感。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已是四月,到天黑时还有一些寒气,从玻璃缝隙中透进的一丝一缕的冷风,吹进烦恼悲观的人心上,简直想象到一个人到那天躺在棺木里的滋味。”*凌叔华:《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这里“寒气”“冷气”等意象符号,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主人公对婚姻的幻灭,并使人际的疏离和不和谐这一主题得以呈现。
“镜子”意象同样不容忽视。“镜子”世界是人类自我封闭性的镜像反映,整天对镜的人是自恋而孤独的。凌叔华的小说中不乏这种自恋的女性,如《吃茶》中的芳影。正值芳菲的她对爱情和婚姻有着美好幻想,经常对镜自照、顾影自怜。早晨,她对着“镜子”出神,感慨着年华的飞逝。和“理想青年”同游公园后,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却又不再惘然寡兴。她自信于自己的容貌,幻想着爱情;同时,未来的不确定又使她感到悲观。幻想和幻灭的交错,通过“镜子”意象表现出来。另外,《绮霞》中也运用了“镜子”意象。女主人公为了家庭牺牲了自我,放弃了钟爱的音乐事业,而她丈夫却连陪她去公园赏花的要求都婉然拒绝。绮霞闷闷地踱进卧房,“迎面放的衣橱上的镜子,照出一个苍白无血色的脸,像冥衣铺糊扎的纸人儿似的,有些瘆人。”*凌叔华:《绣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这里的镜像,暗示绮霞已然是行尸走肉,只是作为依附于丈夫的他者而存在。此处作家借用“镜子”意象,抨击了传统性别角色对女性的束缚,揭露了她们的孤独感和悲剧命运。
四、重复
重复(repetition)涉及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指语词、细节或事件的多重话语呈现。对于重复叙事的本质,热拉尔·热奈特如此界定:“重复是思想的构筑,它去除每次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而J.希利斯·米勒则从读者反应的角度对重复叙事的重要性作出阐释,指出对小说的解读多半要“通过对重复和由重复所产生的深层意义的认同来实现”*J. Hillis Miller, Fiction and Repetition: Seven English Nove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重复即强调,每一次反复叙事都不是无谓的重复,也不是简单雷同,而是意义的叠加和增殖,它使小说的主题得以不断复现。海明威深谙重复叙事手法,其小说往往通过浅显的词或句式的重复,“来刻画生命的惨淡”*[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卢丽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凌叔华的小说也不乏重复叙事的运用,主要包括语词、语式和场景三方面。重复性修辞手段的选择,不仅有助于推动情节进展、表现人物个性和内心感受,而且还强化了作品的主题含义,使读者透过表层文本领悟到潜藏的深层意义,从而使叙事修辞效果得以增强。
首先,说到语词的重复,不得不提及《资本家之圣诞》。这是个复调小说,叙事在圣诞前夜老爷在家里的活动和对往日的回顾之间穿插进行,而促使两条线索自如切换的主导动机就是礼拜堂的“钟声”。“钟声”在全文出现四次,每次都使资本家沉浸到往事的意识流中。第一次是他十四岁在上海看圣诞会的情景,暴露出其追求名利的野心;第二次是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表现出他爱慕虚荣的一面;第三次是他回国后做圣诞会以及撰稿攻击社会不良现象的事,暗示出其虚伪本质;第四次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暴露出他的专制。可以说,“钟声”的复现,使一个专制、伪善、冷酷、自私的资本家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腐败堕落的社会也得到了无情批判。在《无聊》中,“无聊”“烦闷”这样的词多次出现。一大早如璧便情绪不好,觉得一切都是“无聊”的,看到来访的白太太得意的神色,她愈发觉得“无聊”;后来发了一番“为什么要被人像猪一样养着”的感慨后,又自我解嘲地认为“猪该是无聊的呵”;在白日梦中度过了一上午,想到还要去买东西,觉得好“烦腻”;在商店逛着,她更加“烦腻”,说着“烦死人了”就打道回府了;坐在洋车上,想着绸缎庄伙计的话,她“更加烦闷”。显然,这些消极词汇的重复,强化了婚姻生活给主人公带来的窒息感,暗示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揭示出她渴望挣脱婚姻家庭的桎梏、追求自由解放的潜意识,而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在此也窥见一斑。
其次,至于语式的重复,《“我哪件事对不起他?”》较具代表性。胡少奶奶是典型的封建婚姻中的旧式女子:克尽妇道、柔顺贤德。然而,七年未见的丈夫归国后对其却冰冷异常、百般挑剔。后来她发现,原来他是想离婚娶王小姐的,悲愤绝望的她只能发出“我哪件事对不起他?”的哭诉,服毒自尽。标题话语在全文出现四次,前三次出自女主人公之口,最后一次是在跟妈的梦呓中出现:“我们姑奶奶哪一件事对不起姑爷?”可以说,句式的复现,强化了小说的潜在意义,即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毒害和摧残,展示了女性他者的失语状态和悲剧命运。另外,在《有福气的人》中,句式重复同样得到了完美体现。标题句式在全文复现三次。开篇是这样一句话:“平常谈起好命,有福气的人,凡认识章老太的谁不是一些不疑惑的说‘章老太要算第一名了’!”*凌叔华:《绣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在强调了儿孙满堂的章老太“真是福气”之后,叙事者又证明了“老太的福气是谁都赶不上的”,因为她从小衣食无忧。然而,文末真相的浮现,却揭示了章老太“福气”的虚幻性:儿贤孙孝都是假象。在此,叙事重复加强了反讽效果,凸显了人的异化和幻灭主题。
最后,叙事结构的重复表现为场景的重复。《女儿身世太凄凉》由两个相似的场景构成。第一个场景涉及待字闺中的婉兰和表姐就其包办婚姻所做的交流,身为新女性的表姐劝说婉兰拒绝旧式婚姻、寻找自己的幸福;第二个场景展示出嫁归宁的婉兰和三姨娘的谈话,此时追求个性自由的表姐因遭到诽谤而抑郁致死。场景的复现,凸显了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个囿于封建婚姻的桎梏生不如死,一个虽有新思想却不为社会所容。结构的重复,强化了作品的深层含义,即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自我的压制和摧残,并暗示出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中秋晚》中叙事结构的重复,在于对四个中秋场景的描绘。小说是个复调结构,即敬仁夫妻感情越加疏离和家道越加败落两条线索的并行。第一个中秋晚,指涉夫妻关系破裂的经过,敬仁成了一家妓院的常客;第二个中秋节,为了两个石头胡同的姑娘,他竟把杂货铺典给了人,太太动了肝火,小产了;第三个中秋晚,由于敬仁搬弄是非,他母亲把他太太骂了一顿,后来太太又小产了;第四个中秋晚,结满了蛛网的破败小屋已到期交割,敬仁太太连个住处都没有了。四个中秋场景的复现,强化了人际的疏离这一主题。这四个本应是团聚、和谐、温馨的场景,展现的却是分离、隔阂、悲凉。随着家道的衰败,他们夫妻的隔膜也渐深。至此,结构重复使作家消极的婚姻观走向极致。
关于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批评界曾从不同层面给予阐释。正如黑格尔所言,就好的艺术作品而言,“其内容自身隐含着外部实在的、甚至是感性形式的在场,并与这种形式达到完美融合”*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Fine Art”, in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Ⅲ). Hazard Adams (ed.) , Wadsworth Publishing, 2004, pp.519-520.。亨利·詹姆斯则把小说的形式和主题归结为“针”和“线”的关系。*参见[英]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珀西·卢伯克同样说过:“好的作品,主题和形式应和谐一致而又难以区分。”*[英]卢伯克、福斯特、缪尔:《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土人、罗婉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卡勒也强调,要思考小说隐含意义和阐明意义时的具体做法之间的关系*参见[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7页。,即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彼得·巴里更是明确指出:“形式和内容在文学中融合为有机整体,有其一,必得其二。”*[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杨建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特雷·伊格尔顿则认为,文学批评通常从非语义或形式方面来把握意义,在此意义上,“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英]特雷·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在中国古代则有孔子的“辞达”说,道家的“得意忘言”论,王充的“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说,以及陆机的“诗缘情”说等。*参见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7、57、75页。毋庸置疑,以上看法均不同程度地消解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二元对立性,肯定了它们的同一性和交融性。而这种同一性和交融性,在凌叔华的作品里已得到体现。上述分析表明,凌叔华在其小说创作中,通过对反讽、隐喻、意象和重复等叙事修辞特征的选择,巧妙地表达了其意图中的深层结构,使小说潜在的深层含义浮出表面,达到了作为“能指”的叙事与作为“所指”的主题的统一,并透露出作家的多元思想和对世界人生的体认。具体来说,就反讽而言,幻想与现实的冲撞、表象与实质的反差在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叙事真实之间产生一种张力,从而戏剧性地呈现了作品的主题寓意。至于隐喻,人物话语和行动等细节描写甚至是标题,均超越了文本表层意义,间接而含蓄地使隐含的深层意义得以去蔽。此外,意象的运用,在渲染主题情调、烘托人物瞬间情感体验的同时,更是凸显了人物的境遇、暗示了深层象征含义。而重复性叙事不仅使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逐层显现,而且使主题内涵得以强化。诚如伍尔夫所说,小说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他要写的东西”*[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吴晓雷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可以说,作为一个现代短篇小说家,凌叔华显然已经找到了得心应手地表达她的思想的方法了,那就是通过叙事手法的选择性运用,跨越故事的“显在”意义,而把某些在表面上隐而不彰的深层结构巧妙地揭示出来。对此,读者需充分施展想象力,进行积极阐释,在对小说深层精神寓意的追寻中,感受微妙隐秘的审美内蕴,以期获得更大的审美愉悦。可以说,凌叔华对表层和深层双重文本的驾驭,既达到了主题寓意的强化,又凸显了审美效果,最终实现了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而其现代小说叙事艺术也得以精彩呈现。
2017-04-28
赵文兰(1974—),女,山东冠县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现代文学和叙事学。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肖邦与曼斯菲尔德:他者身份研究”(项目编号:14CWXJ65)、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YBW15001)和聊城大学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321021412)的阶段性成果。
I206.6
A
1003-4145[2017]11-0047-07
(责任编辑:陆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