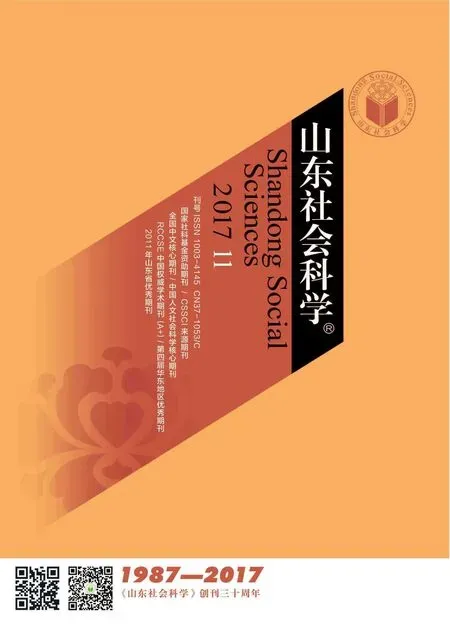世界历史视野下苏东巨变的反思
2017-04-02隽鸿飞
隽鸿飞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世界历史视野下苏东巨变的反思
隽鸿飞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苏东巨变无疑是20世纪末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21世纪世界历史的格局,而且对于理解20世纪人类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的反思,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东欧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必须在20世纪世界历史格局总体之中,通过深入分析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历史根源,才能真正阐明这一巨变得以产生的根源及性质。具体而言,苏东巨变并不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乃是一种尝试超越自由资本主义探索的失败,其本身对于21世纪的世界历史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苏东巨变;世界历史;自由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苏东巨变无疑是20世纪末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21世纪的世界历史格局,而且对于理解20世纪的人类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R.W.戴维斯指出的:“这个关于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前景黯淡的观点可能是对过去20年来趋势的一个表面的推断。仅仅在数百年的动荡之后,通过长时期的进步和衰退的过程,资本主义把自身建设成了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世界性经济体系。也许还要经历一两个世纪的时间,70年代和80年代才会仅仅被视为社会主义兴盛阶段之中的一个短短的阶段性退潮。”①R.W.Davies: Gorbacheev’s Soci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Left Review I-179,January-February 1990.
一、冷战与全球化的悖反
20世纪无疑是资本全球化的世纪。开始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世界性的扩张不仅为资本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同时以其创造的现代的交通运输、通讯手段将整个世界普遍地联系起来,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6页。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同样创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并在广大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引发了世界性的反抗运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前提下诞生的。因此,自苏维埃俄国的诞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就从没有停止过。特别是第二次世纪大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反殖民化浪潮,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于是,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扩张明确要求打破民族、国家、区域的界限,建立统一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冷战铁幕的拉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几乎处于绝对的隔绝和对立状态,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这一矛盾的世界历史格局对于20世纪人类的历史、特别是对苏东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进程影响是巨大的。
第一,冷战主导的东西方格局形成的强大的外部压力,严重压缩了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空间。一方面导致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扭曲。“二十世纪的准社会主义革命 ,都发生在战争破坏与资本主义失败的背景下,每次都不得不与社会经济落后的沉重负担和军队的围剿相抗争。到目前为止,在每次革命过程中,都存在着原始的民主元素,比如对宣称自身的基本利益阶层人口的压抑和镇压;但在第一种情况下,集权的政治和军事武装都为革命提供了稳定方向,阻碍了民主的发展。……当被饥荒、道德败坏的恐惧以及对反革命可能轻易卷土重来的信念包围时,后革命时代的领导人会以取缔对手的党派、颁布正式的执政党,并在党内压制各派的方式来应对。”*Robin Blackburn: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urary 1991.因此,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特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苏联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非正常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为苏联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形成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力,在东欧地区强制推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断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而造成了苏联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苏南冲突”、“波茨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就是这种冲突的重要体现,而上述冲突则为20世纪末东欧各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埋下了隐患。
第二,不断强化的东西方对抗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扭曲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使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成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一方面,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斯大林主导下的苏联沿袭了大部分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是在干部准军事动员驱动下推进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他们将斯大林的‘总路线’视为党的生存和国家的控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党的机构占据并控制了国家,并且通过将自上而下的军事化的计划和自下而上的干部动员相结合的方式,强制建立了计划经济结构。”*Robin Blackburn: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urary 1991.另一方面,这种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与资本所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原则相违背,更缺乏管理经济所需要的精准性。“苏联经济始终是一个社会经济混合体,往往找不到一种方法来利用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矛盾——它唯一的希望是破坏这种主导地位,并确保其自身的综合发展。”*Robin Blackburn: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urary 1991.但是,由于双重的封闭: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闭,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封闭,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无法消解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难以确保其自身的综合发展。因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状态。苏东巨变前的苏联一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另一方面却无力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品的供给。正是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品的匮乏,造成了对经济状况的普遍的不满,从而成为其内部矛盾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三,冷战割断了苏联与东欧各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使之无法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使之处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之外,这成为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失败的重要的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其一是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保留东方的土地公有制,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其二是必须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这又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才是可以的。尽管资本主义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合理性,但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其本身具有非常革命性的意义,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带来的个体的自由发展、还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为新世纪创造的物质基础,以及与上述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都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源。而冷战却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隔绝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严重制约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冷战政策——从巴黎统筹委员会到其它形式的经济和军事封锁——被成功用于切断苏联对西方技术的运用,而且还迫使苏联浪费巨大的军费开支。……而在1945年之后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上变得越发统一,因而几乎没有为苏联在外交上提供机会。……苏联认为马歇尔援助应该被新的‘人民民主’取代,这暗示了一个代价高昂且对资本主义入侵感到恐惧的危险。”*Robin Blackburn: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urary 1991.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入侵的恐惧则会进 一步强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封闭,由此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克服了其最新阶段的结构性危机,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新保守主义浪潮到达顶峰,并且里根政府并未隐瞒其意图利用美国对苏联的经济优势来改变军事—战略平衡,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外在的压力,使苏联陷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在进一步加剧了苏东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巨大冲击。
因此,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格局,对苏东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刻的。但从根本上来讲,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同样有其内在的根源。
二、苏东社会主义的内部困境
如果说冷战使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主导的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造成了其自身发展的外部困境,那么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则成为其最终失败的重要的根源。
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模式,苏东社会主义各国的无疑在形式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理论诉求,即以公有制为手段,以大众福利为目的,并在医疗、教育以及无产阶级出身人群社会地位的提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社会主义应发端于实际的运动,而不是被定义在思想家的研究中。一般地说,相较于特定的纲领性概念,马克思更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坚持。作为对这种推动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历史、社会、文化研究和经济学领域都衍生出了多样化的学派,它们都充满批判、怀疑和现实主义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阐明重要的判断原则,即‘真正的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指向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运动。”*Robin Blackburn:Fin de Siecle: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urary 1991.正是在这方面,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思想精神,而是简单地成为资本主义的绝对的对立面。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完成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政治解放一方面将分散、割裂、分流在封建社会各个死巷里的政治精神解放出来,构成了共同体——国家,另一方面则是人的全部的共同性被抽离之后只剩下市民社会的孤独的个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政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因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不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是要借助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逐步消解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重建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只有如此,人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个人的基础上的话,那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则真的走到了它的截然对立面,即将社会主义完全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将个体的人消融于共同体之中。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的前提下,国家就成了共同体的代名词。因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这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为个体的人的发展留下任何的空间,而是将个体的人完全融入国家、集体之中。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现代社会建构的基础——个体的人——的消失。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将现代社会的建构建立在孤独的市民社会的个人的基础之上是有问题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是由于个体的人的解放焕发出了人的巨大的创造力,才推动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苏东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面,对个体的人的消解同样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问题。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替代模式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而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作为一种非资本主义力量,苏联所取得的扭曲的、代价惨重的成就,以及对于遍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苏联体系核心特征的或多或少的忠实再现,都证明了一种观念,即它代表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完全不同的选择。但是,现在我们逐渐明白——而此前却是确信无疑的——这一替代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如若作为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的选择,尚缺乏动态的整合”*Robin Blackburn:Fin de Siecle: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urary 1991.正是由于苏东社会主义自身的僵化及改革的失败,成为苏东社会主义解体的根本原因。
第一,在经济层面表现为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失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企业的生产都是源于中央的指令性计划,企业要么是“奉命经营”,要么是“我行我素”。在第一种情况下,管理的社会化受到计划人员无法了解或控制大型复杂经济体的限制;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工厂自治主义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行为。企业的管理者关心的并不是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能够及时完成上级部门的计划,生产出来的产品及其社会效益则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在苏联经济改革的初期表现得非常明显。苏联“企业领导者只得调用了那些‘以备不时之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秘密储备物。很多经理人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效。1985年的经济指标明显优于前一年。一方面,部门主管已经论证了没有必要匆忙实施改革,因为采用旧的管理机制可能也会取得合理的成果,并且只需要给各位领导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各领导现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所取得的成果水平,避免造成严重的麻烦。”*Boris Kagarlitsky, Perestroika The Dialectic of Change, New Left Review I-169, May-June 1988.因此,在实践中并没有改变原有的体制机制,而仅仅是原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更不会形成新的经济管理模式。
另一方面,由于处于相对封闭的体系之中,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既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更无法融入世界市场。 “由于苏联型的经济体制不接受或否认市场价格,而且又没有任何与市场价格脱钩的理论依据,因而这种体制往往形成一个个与世界经济主流隔绝的死水塘。”*Robin Blackburn: 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urary 1991.而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以及苏东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都明确提出如何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要求,这就会进一步激化其内部经济的矛盾,从而加剧内部的分离意识。“其部分原因在于,国有化指令性经济体制都存在着自给自足的倾向,因而减少了不同国营集团之间的相互接触。另一个原因是,它鼓励公民用有形的零和态度来看待经济分配。实际上,很多商品需要通过一个关系网来获取,而这个网络太容易受到亲属和种族关系的影响。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的冷酷无情隐藏了太多的东西(包括社会成本和对人的剥削),但共产主义的指令性经济体制却有助于恶性个人主义的普遍滋生。……由于缺少其他的合法性依据,在国家权力机关知道自己遭受经济失败后,只好转而求助于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Robin Blackburn: 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urary 1991.
第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导致了“单一集体意志”的失败,即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和物质的高压手段强制模塑人性的过程来鼓动大众的热情,建构共产主义意识。“结果是它的教化工具和它的镇压工具都不能成功地对构成共产主义自由观念的‘盲目的’、自发的力量建立起全面的控制。一切以消除市场‘无序性’和现实意识形态强制统一性的方式试图达到这一乌托邦观念的尝试,导致了无心的后果,……对大众乃至他们所谓的‘先锋’的一如既往的意识形态动员在实践上已经不可能,被常规化的教化形式只形成了奥威尔式的‘双重意识’”。*Andrzei Walicki: From Stalinism to Post-Communist Pluralism: The Case of Poland.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ruary 1990.无可否认识的事实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基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应对强大的外部压力的需要,以及在进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过程中所实现的充分的社会动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建立了“单一的集体意志”,并对于推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社会生活的变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政治革命进程的完成、社会生活的常态化,人们关注的重心逐渐从政治领域回归到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从而使原来的政治动员失去了效用。“在‘稳定’岁月中长大的新一代需要更多的教育和需求。不一致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新要求,最终导致了新的不满。人们感觉他们自己更加独立,并要求他们的公民和人类尊严受到尊重。多年的‘稳定’已经传达了社会福利:社会关系被加强,并且人们也更加理解他们的集体利益。相反,官僚部门之间的矛盾加剧,很明显,‘好果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不仅是下层阶级,上层阶级中的重要部门对此也感到不满。”*Boris Kagarlitsky, Perestroika The Dialectic of Change, New Left Review I-169, May-June 1988.对这种普遍不满的改革要求恰恰又是却偏偏不合时宜地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创造了条件,从而加速了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
第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的过程中赋予了官僚化的和专业化的管理人员以极大的特权,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官僚化的和专业的党的骨干被极大地赋予了特权;然而,他们不允许‘成为一个具有其自己的社会政治身份的结实而清晰的人’。羽翼丰满的要职人员类似享有某种团体独立性并根据其团体利益(即根据自我复制,而不是根据不停地进行革命努力以实现共产主义观念)进行思考的一种‘新阶级’”。*Andrzei Walicki: From Stalinism to Post-Communist Pluralism: The Case of Poland.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ruary 1990.这些去意识形态化的“特殊利益集团”与完全受控、中央计划经济的极权主义观念相矛盾。因而,随着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的进行,各国内部的政治局势呈现出迅速地分化局面,各个不同的派别都执着于本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以社会的发展为根本目标,因而无论哪个派别都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改革方案。“一方面,社会变革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另一方面,却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改革运动。持不同政见者从来没有,甚至在他们比较吃香的几年中也从未提出社会变革的计划。在它存在的整个周期中,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提出了人权和保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口号,但它没有能力制定一个建设性的计划方式,这些口号变得太抽象并脱离了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结果,持不同政见者便越来越多的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来源于外界的外交压力上。”*Boris Kagarlitsky, Perestroika The Dialectic of Change, New Left Review I-169, May-June 1988.这种策略在1979—1982年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实际上完全就是自取灭亡。
最后,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历史上形成的不正常的关系,也成为东欧各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原因之一。从历史上来看,俄国与东欧各国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特别是在沙皇俄国时期,东欧各民族始终是沙皇俄国侵略、掠夺的对象。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苏联成为东欧各族人民的解放者,通过培养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帮助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中断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大都经历了一个人民民主建设时期,即各国根据反法西斯战争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而形成的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政治组织方式,由此也决定了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但是,冷战开始后苏联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于是与东欧各国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不但严重损害了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影响,而且也使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被视为苏联的代理人,无形中割裂了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东欧各国民主进程的深入,与共产主义相背离的意识不断地被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脱离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也许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整个波兰知识界经历了一个异常激烈的反共产主义的自我教化过程。购买、阅读和散布反共产主义或潜在地反共产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文献——从对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经典分析和一流的历史性专著,到完全不同的回忆录、小说和杂志连载的作品,甚至包括通俗的宣传册——被视为一个自觉的波兰爱国主义者的主要职责。因此,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现实的认知极度地意识形态化而由此被严重地扭曲了。”*Andrzei Walicki: From Stalinism to Post-Communist Pluralism: The Case of Poland.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ruary 1990.
三、苏东巨变的启示
苏东巨变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原苏东社会主义各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并没有获得所预期的发展结果,更没有实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解。可以说,苏东巨变的历史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同时也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深刻的启示。
第一,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道路的一种探索和努力的失败。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会也不能简单地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面获得成功,而是必须在真正理解马克思所阐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建立社会主义作为其终生奋斗的目标。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样给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以极高度的评价。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不彻底性的同时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使个体的人从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的巨大增长,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因此,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而是必须吸收其创造的肯定性成果,将实现个体的人与人的社会的统一、最终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社会主义的目标,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开创人类历史的新局面。为此,社会主义就必须通过开放,主动融入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才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果,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
第二,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更不能说明自由资本主义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特别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资本的全球化,整个世界已经资本化了,广大的发展中国无可奈何地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因此,“当我们提及前共产主义世界崩溃前的最后阶段,我们不应忘记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异,即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病。在当下,全球被牢牢地控制在资本主义积累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进程所造成的混乱和痛苦、破坏和忽视以及分裂和不负责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资本主义活动方式是与一种令人憎恶的进程相联系的,它从庞大的贫困国家人口数量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前景,并用债务将其与富裕国家隔绝,让他们与自身生产的产品相相分离。经济和政治权利在众多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情况,证明了普遍饥荒与可治愈疾病流行的相关性。在贫困人群中,为了挑战这种状态而进行的尝试性运动,经常会遭到残酷的镇压和军事武装的屠戮。事实上,毫无疑问,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给人们造成的流血牺牲和身体创伤,已经超过了人们在共产主义官僚主义统治下的国家所经历的痛苦。”*Robin Blackburn: 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January-Feburary 1991.
第三,在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不可能通过走向自由资本主义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解而融入现代世界进程的。回顾原苏东地区各国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俄罗斯并没有因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被西方国家所接纳,反而因自身实力的削弱遭遇西方的步步紧逼而日益陷入生存的困境;从苏联解体而分裂出来的各个小国及原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也并没有逃脱大国利益博弈的工具的命运。原因何在?究其根本就在于,当今的时代依然是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遵循的根本原则仍然是资本的原则——弱肉强食。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利益博弈,每一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决定自己的对内对外的政策。在这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作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只有立足于自身的现实社会历史条件,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需要的道路,使之始终处于世界历史的前列,才能够保证自身的发展,并在与资本主义家的世界历史性的博弈之中,逐步改变世界历史运行的规则,才有可能为自身及人类的历史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2017-09-30
隽鸿飞(1970—),男,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D81
A
1003-4145[2017]11-0011-06
(责任编辑:周文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