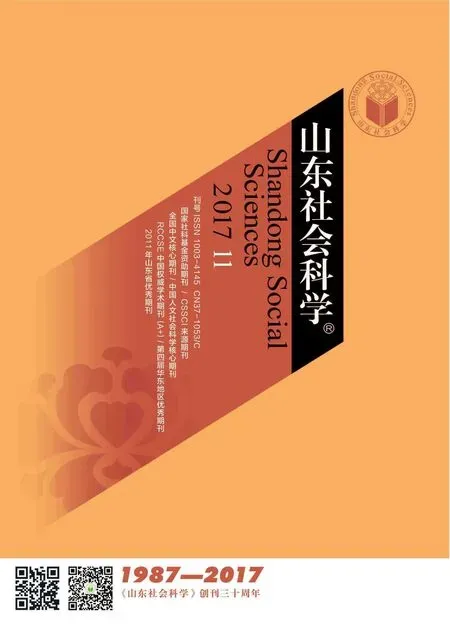从主体性衰落到非人崛起
——战后法国左翼批判思想的发展脉络
2017-04-02蓝江
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46)
·《新左派评论》视野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学术主持人:张亮)·
编者按:创办于1960年的《新左派评论》是当代西方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左派理论期刊: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期刊排名中,它常年保持在政治科学类期刊和跨学科综合性期刊的前30%,基本上体现了左派理论刊物在欧美学院体制中的最好水平。自创刊以来,《新左派评论》始终引领着左派政治批评和理论批判的方向,即便是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也是如此。为了更全面地追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潮流,南京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黑龙江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合作编译“《新左派评论》精粹译丛”,聚焦1990年以来《新左派评论》所刊发论文,集中展现了当代西方左派学者对中国道路的本质与模式、苏东剧变的历史及其后果、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与重建、当代法国激进批判思想的历史进程、新自由主义批判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本刊特将该译丛相关卷册(蓝江《从主体性衰落到非人崛起——战后法国左翼批判思想的发展脉》、隽鸿飞《世界历史视野下苏东巨变的反思》、黄晓武《危机与重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周嘉昕《“新自由主义”与西方新左派》)的译者导言荟萃提前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从主体性衰落到非人崛起
——战后法国左翼批判思想的发展脉络
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46)
二战之后的法国哲学被称为第三个辉煌年代。这个年代起始于萨特,不过萨特仍然使用了德国唯心主义的概念和范畴,并与后来的法国哲学的主要概念有较大的差距。然而,实际上萨特尽管使用了古老的概念,但他思考的问题确实是后来法国哲学的方向,他对自我主体的思考,他潜在的生命经历和装置的二分,奠定了后来法国左翼思想发展的两个不同的潮流,这两个潮流的汇聚的理论结果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生产着正常人的身体,而隔离着不正常的人。对于眼下法国思想家能够想到的超越生命政治学的方案在于非人化,或者说走向人的身体与技术的合成,让我们成为合成的赛博格,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走出生命政治的人类纪。
主体性;结构主义;生命政治;非人
法国哲学,尤其是法国左翼批判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为数众多的拥趸,我们看到了诸如萨特、梅洛-庞蒂、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德里达、巴迪欧这些群星闪耀的名字,在这个名字下面也有一条隐秘的法国哲学的逻辑,而如何去面对这个逻辑,是我们走进法国左翼批判思想的一条重要路径。
一、主体性的余晖
2012年,在巴迪欧为他的文集《法国哲学的历险》撰写的序言中,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辉煌的哲学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古希腊;第二个时代是从18—19世纪初期;最后一个时代,就是巴迪欧宣称的法国哲学的时代,按照巴迪欧的说法:
“20世纪下半叶是法国哲学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整个过程,完全可以媲美于古希腊和启蒙时期的德国。从1943年出版的萨特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到九十年代出版的德勒兹的《什么是哲学?》。法国哲学的时代在这两部著作之间风起云涌,包括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和拉康,当然还有萨特和德勒兹,或许还有我自己,如果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法国哲学时代的话,那么我的立场或许是法国哲学最后的代表 。”*Alain Badiou, L’Aventure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ois, Paris: Fabrique, 2012. p.9.
的确,战后的法国哲学和思想界风起云涌,诞生了新的一批极富创造力的批判思想家。萨特、列维-施特劳斯、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拉康、阿尔都塞、布尔迪厄、德勒兹、德里达、鲍德里亚、利奥塔、巴迪欧等一代又一代法国思想家,日益引导着世界思想发展的潮流,而且即便是在法国哲学圈子之外的学者,如齐泽克、阿甘本、奈格里等人也受惠于当代法国思想的影响。的确,这是一个法国思想拥有着巨大影响和魅力的时代,从欧洲到美国,从东亚到拉美,从中东到黑非洲,这些法国思想家为全世界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思想养料,并在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生根发芽。
不过,我们还需要注意,巴迪欧不仅强调新的法国哲学时代来临了,而且这个时代降临的标志是萨特。为什么萨特会构成一个转折性的标志?究竟是什么让萨特成为一个法国哲学时代的开端?
对于第一个哲学的回答,或许在不同人那里理解上判若云泥。不过,我们可以认为,萨特思想的根源恰恰在于德国,尤其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尽管不可否认,萨特是在法国抵抗运动和知识分子政治参与中成长为思想家的,但是,萨特的知识谱系恰恰是在德国思想的荫庇下滋养成长的。正如大卫·谢尔曼(David Sherman)指出的:“萨特对信仰及其随后的自为存在、为他存在、‘境况’、自由和责任的分析,以及生存性精神分析都全部依赖于他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和存在论的升华。”*David Sherman, Sartre and Adorno: The Dialectics of Subjectivity, New York: State Uin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2007.显然,1936年的《自我的超越性》以及1939年的《情感》都是在胡塞尔现象学影响下的作品,而《存在与虚无》中的许多概念也直接受惠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同时代人,萨特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都有不少的交集。尤其是在《存在与虚无》出版之后,萨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理论家之间进行了交流和互动,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萨特的哲学并不代表前进的潮流,而是倒退到古老的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当中。如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s)指出:“萨特哲学在其巅峰时期是依照一种古老的主体的自由行动的唯心主义范畴来架构的。他的存在主义仿佛是费希特的哲学,所有客观性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萨特哲学中的非理性让他成为最顽固的启蒙精神的使徒。绝对选择自由的概念就如同绝对自我概念一样虚无缥缈。”*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E.B. Ashton trans.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p.50.而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马尔库塞专门用一篇文章《存在主义: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评论》来清算萨特这种带有古老德国唯心主义色彩的存在主义:
“萨特脱离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孤立地谈主体的‘超越性’,将这种‘超越性’作为自由的前提条件,并假设定了主体的存在论形式,这种超验自由恰恰成为奴役的标志……人类自由恰恰是对萨特想要实现的超验自由的否定。在《存在与虚无》中,这种否定仅仅表现为‘欲望态度’(attitude désirante):它是‘自为’(pour-soi)的失却,是对‘真实血肉之躯’的物化,而这个‘血肉之躯’(corps vécu comme chair)意味着新自由和幸福的观念。”*Herbert Marcuse, Studies in Critique Philosophy, Jris De Bres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pp.183-184.
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萨特太过执着于一个过时观念:超验主体。这个超越性的自我或主体性实际上被萨特拔高到超越一切具体的历史背景。不过,萨特并不是对这些批判意见无动于衷,在萨特自己看来,晚期的《辩证理性批判》就是他本人试图对这些批判做出的回应。不过,萨特仍然坚持主体性的概念,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只不过用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体性,取代了《存在与虚无》中的个体主体性。萨特1961年在罗马的一次讲座就被萨特自己命名为《什么是主体性?》,而这个时期,萨特刚刚出版了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一卷,然而,他坚持他的主体性的立场,即“主体性仅仅是我们特有的存在,即我们必须成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被动地去存在”*Jean-Paul Sartre, What is Subjectivity? David Broder & Trista Selous trans. London: Verso, 2016, p.37.。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属于上一个时代,即巴迪欧所命名的十九世纪的德国唯心主义时代,他的主要范畴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甚至胡塞尔的哲学。以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萨特犹如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在一个并非骑士的年代里,和他的桑丘去挑战巨大的风车,主体性就是他手中的长枪,而这杆长枪刺向的是虚幻的客体性的魅影。随后的法国哲学时代,实际上是桑丘们的时代,他们不再执着于一个超越历史的概念,身体、肉体、欲望、力比多,这些概念成为了后来法国哲学主导性的概念。然而萨特坚持以主体性的长枪一骑绝尘,在与空气的搏斗中为后人留下千古绝唱。然而就在萨特施展他那屠龙绝技的时候,一帮年轻的知识分子却换上了新式的自动化武器,开辟了全新的战争,他们背后留下萨特一个人扮演独角戏的舞台,让他自己在舞台独白:“选择还是不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不过,萨特的确站在一个关键的分界点上,这或许也是巴迪欧为什么将“最后一个主体性哲学家”萨特放在新的哲学时代的起点处。在萨特的时代,爆发了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之后,流亡法国的科耶夫成功地举办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讲座,主奴辩证法受到萨特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追捧。此后在法国掀起的阿尔及利亚反战运动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都是萨特在二战之后面对的真实处境,尽管萨特非常喜欢用处境(situation)一词,但是他的主体性武器却被处境所抛弃,尽管萨特仍然积极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以宣示知识分子不妥协的姿态。但是萨特仍然被称为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虚无主义者,其根本原因恰恰是他在一个大量使用火器战斗的时代挥舞着早已过时的主体性的冷兵器,在穹宇中留下了寂寞的主体性的余晖。
二、断裂的症候:生命体验与装置
让我们回到前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如果说萨特代表着一个古典范式,那么为什么新的法国哲学的时代还必须以萨特为起点?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一个时代的开端是以一个连续性的起点为开端,还是一个无法继续行进下去的断裂为开端?在一定程度上,萨特的概念虽然属于观念论范式,但他同时以法国的政治和斗争实践为基底,在思想上,萨特并不是新航向的开拓者,他更像是上一个阶段的遗老,在那里静候着慢慢地被历史进程所取代。萨特的起点问题并不能在线性历史观的层面上来理解,而是需要从法国本土的思想酝酿来把握萨特的历史价值。
巴迪欧曾对萨特有如下评价:“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试图在理论上进行更新的政治性主体,从来就不是萨特所说的造反主体,即便在造反之前,萨特的主体也业已存在。……在政治性主体中,在新型政党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种连续性原则,但这个原则不是萨特的系列、融合、或制度。这是在萨特总体化的实践集合之外的不可还原为其他东西的原则。这个原则不再建基于个体实践。”*[法]阿兰·巴迪欧:《小万神殿》,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页。我们可以将巴迪欧的这个评价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1)萨特的主体是一种先于政治的主体,也就是说,萨特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构建了一种外在于政治活动的主体,同样,在哲学上,萨特的主体概念是外在于历史框架的。这意味着萨特的思维范式已经远离了法国具体的背景。(2)存在着一个不可化约的总体原则,这个原则是实在的,而萨特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原则的存在。不过,巴迪欧强调的是,尽管萨特利用的是一个古老的主体性的长矛,但实际上,萨特本身的话语确实是在一种新型的总体原则下进行的,而这个总体原则是无法还原为萨特自己的旧式概念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萨特的矛是旧的,但是他的立足的世界却是新的。萨特的概念和范畴还停留在德国观念论的阶段,但是萨特的问题式却是法国式的。尽管手执主体性的长矛,但他所立足的大地永远是法国式的,他与后来兴起的结构主义者进行了论战,但是萨特可能并没有注意到的是,他自己或许也处在结构主义勾画的地界之内。
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来理解,真正的断裂点从来不是表现为一种连续过渡的范畴,相反,它代表着一种症候(symptme),拉康说:“症候首先是一个假定言说的主体的沉默症。如果他开始说话,显然就治愈了其沉默症。但这并没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开始说话。”*Jacques Lacan,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Seuil, 1973, p.20.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具有症候特征的人来说,他想说的东西与他真实所依赖的背景存在着断裂,他真实所思与其再现性表述之间出现了裂痕,无法表现为一个连贯的统一体。萨特的地位正是如此。如果萨特如同胡塞尔一样,他的思想背景与其言说保持了严格的连贯的关系,那么萨特不过是现象学在法国发展的一个注脚而已。但是萨特的价值是,他所言说的主体性和他所基于的立场之间不是连贯的,他所处的时代,他所依赖的问题式,与他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之间存在着巨大断裂,萨特是被撕裂的形象,他将自己作为一个症候呈现在战后法国思想家的断裂点上。
尽管萨特和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施特劳斯之间发生了一场巨大的争论,但是这场争论的结果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崛起对最后的主体性哲学家萨特的彻底取代。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施特劳斯批评萨特说:“实际上,萨特成为了他的‘我思’的俘虏,笛卡尔的‘我思’能够达到普遍性,而始终以保持心理性和个体性为前提。萨特只不过通过‘我思’社会化,用一座牢狱替换另一座牢狱。”*[法]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萨特那种神话学的我思和自为的概念,实际上成为预先设定的概念牢笼,而强行将这个辔头套在现实社会的具体的人身上。然而,萨特对于这个批评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反驳,以十分温和的态度重新思考他的立场,在1969年的一次访谈中,萨特谈到某种不能言说的东西与自我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
“在我最新的一本谈福楼拜的书中,用我所谓亲身经历(vécu)来取代了之前的我意识观念(尽管我仍然会使用意识一词)。在这里,我要谈论的不是前意识的警觉,也不是无意识,更不是意识,而是个体本身及其财富和意识永恒流溢着(overflowed)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总是借助遗忘(forgetfulness)来玩弄自我决定把戏。”*Jean-Paul Sartre, ‘Itinerary of a Thought’, in New Left Review, 58(Nov.-Dec. 1969), p.48.
与早年那个坚持 “自由意志”的萨特相比,借助“亲身经历”反思了那种超越性自我的立场。在这个时期,萨特关注点毋宁是“个体本身及其财富和意识永恒充盈着的领域”,我们从中看到,萨特关注的是一种被多种关系架构出来的“自我”。在这段文字中,遗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汇。遗忘是对活生生体验的遗忘,也就是对那些在真实经历流溢的生命的遗忘。在萨特看来,由于遗忘,我们不得不将我们的生命经验还原为抽象的“自我决定”。萨特以这种方式回应了结构主义的攻击。自我是一种处于活生生亲身经历的自我,是带有生命丰富性的自我,但这个自我被遗忘了,被还原为一种基于整体架构的“自我决定”,一个鲜活生命被抽空之后的自我的干瘪躯壳。而列维-施特劳斯攻击的恰恰是这个躯壳,所谓的神话也只是话语和符号的虚假的自我躯壳,而在被再现出来的情境中,这个被人为塞入了虚假填充物的躯壳仿佛复苏了,实际上,这个躯壳不过是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僵尸,它没有充盈和活生生的灵魂。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福柯的影子。因为,在这次题为《思想的旅程》的访谈中,萨特明显具有了两种自我的区分,即再现式自我和生命性自我。
首先我们来看看再现式自我。它属于处于话语连续性的构造下生成的大写自我,这种大写自我的价值并不在于保存活生生的生命体验,而是走向一种与象征与话语的衔接和建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的主题,即存在一种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这种话语构型并不是在历史中通过累积的方式形成的,而是表现了共时性(synchronic)的结构:“它们连续出现的次序,它们的同时性中的对应关系,在共同空间中可被确定的位置,相互作用,被链接和计划的转换。”*[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页。这种散布性(dispersive)的话语结构后来被福柯命名为装置(dispositif)。也就是说,除了话语构型这种装置决定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言说什么,可以思考什么,也存在着其他的装置,如凝视的装置,决定了我们本身的能见度,以及我们自己的能看见什么。我们整个社会体现为一个巨大的装置,我们所有的自我决定的行为,都附着在这个装置之上。
其次是生命性的自我。阿甘本曾指出:“当装置越让自己的权力侵蚀和弥散在所有生活领域当中,治理就会发现自己越不得不面对那些逃逸的元素。”*Giorgio Agamben, What is an Apparatus? Divid Kishik & Stefan Pedatella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3.而这些逃逸的元素,就是游牧在规范化的装置之外的生命体验。德勒兹和迦塔利设想了在巨大的统治机制下的逃逸可能性,正如他们所说:“在这个意义上,游牧没有地点,没有路径,没有陆地,甚至它们只有表象。如果游牧可以被称之为脱域化的话,这正是因为之后它也不会再辖域化,也不会留下任何沉淀。”*Gilles Deleuze,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Brian Mussmi trans. London: Bloombury, 2014, pp.444-445.游牧是最纯粹的生命,这种生命符合萨特的亲身经历的命名,它是对遗忘之后的还原性的自身身份的逃逸。对此,迦塔利曾说:“要么我们,甚至我们最私密的存在都接受权力等级化,要么我们同意随着欲望的逃逸线运动,各处预先设定的装置,用于统治的赘余信息,以及限制性的意指关系……”*Felix Guattari, Lignes de fuite: Pour un autre monde de possibles, Paris: L’aube, 2014, p.101.
由此可见,在萨特的词语与位置的二分法下面,恰恰是当代法国思想发展的两条进路,一条是从结构主义语义学走向的实证性的装置研究,福柯将这一机制展现得淋漓精致,成为我们今天重新反思现代性的途径。而在另一边,对国家机器,话语装置,甚至物体系(鲍德里亚)的逃逸,是我们面对这个时间,避免遗忘,避免让自己成为巨大装置的僵尸傀儡,我们面对是德勒兹和迦塔利等人的游牧生命的路径。而这两条路径的断裂性症候全部起源于萨特,也正是在这个症候之下,在法国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以欲望和力比多为主题的生命体验的潮流,以及话语构型、实证性、物体系为核心的装置研究的分叉。
三、生命政治学与非人
作为思想症候的萨特裂变出来的两条法国哲学思想路径的一个结果是生命政治学研究。从早期的《规训与惩罚》开始,福柯已经开始思考一种新型政治学。相对于传统社会中的惩罚机制,生命政治学更多地依赖于福柯提出的“规训”机制。福柯谈到,从17世纪开始,各个国家都试图打造出“理想的士兵”,这些士兵最直接的符号就是强壮的体魄,而在18世纪的时候,各国政府显然通过规训的方式得出了这样理想化的士兵:
“到18世纪后期,士兵变成了可以创造出来的事物。用一堆不成形的泥、一个不合格的人体,就可以造出这种所需要的机器。体态可以逐步矫正。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成为习惯性动作。总之,人们‘改造了农民’,使之具有了‘军人气派’。新兵逐渐习惯了昂首挺胸,收腹垂臂,笔直站立。”*[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4-155页。
福柯这段文字的意义在于,现代军事中的士兵的身体并不是自然的素质,而是被体制生产的身体,而这种被生产的身体,正是生命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关键在于,为什么要生产出士兵的身体?同时又是什么让士兵可以主动接受身体的生产?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军事行动需要一种秩序,也就是说,当军令下达,士兵能够按照将军的命令来执行其任务。在这个方面,既需要士兵有足够的体能和身体条件来完成任务,也需要士兵顺从驯服,不至于在军事行动中违抗军令。而作为身体生产的规训可以同时完成这两个任务,即一方面通过演操和队列,让士兵可以遵守命令,服从纪律,成为“被驯服”的肉体,另一方面,这种肉体不仅是“驯服”的,也是有能力的身体。在福柯那里,纪律上的服从,身体素质上的胜任都始终服务于一个标准,即能够在军事行动中担当任务,保障整个军事战略的实施和完成。同样的程序也被应用到监狱之中。相对于古代社会的惩罚机制,现代社会的监狱已经不再是惩罚与肉体的比例关系。在福柯看来,现代人文主义的兴起,让惩罚的观念逐渐弱化,最终认为人的罪行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失范,可以通过改造的方式,让犯罪的人重归正轨。这就是现代监狱的诞生,监狱的目的不纯粹再是对罪行的惩罚,它还兼任着对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改造,而改造的方式,与军队上生产士兵的方式如出一辙。
不过,《规训与惩罚》一书最值得关注的是福柯在书的第四部分将军队和监狱中的这种规训模式拓展到整个现代社会范围内,在其中,由于规训体制的运作,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所有的人都是“过失犯”。这里的“过失犯”的概念,意味着每一个人需要生产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尽可能地服从于社会的规范。因为,决定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否生存的关键就在于规范,正如皮耶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在对福柯的规范概念解释的时候指出:“实际上,从规范的角度定义可能经验的范围,就是把它们定位成规范化社会中的主体,而规范化的社会为其提供了运作规范。这并不是指,主体严格服从于这些规范,或者主体根据先于自己而存在的天赋和自主原则,在规范作用下做出顺从或是反叛的姿态,而是相反地,在构成主体性的领域的同时,主体性自身就已经倾向于这些规范了。”*[法]皮耶尔·马舍雷:《从康吉莱姆到福柯:规范的力量》,刘冰菁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6-97页。马舍雷的解释进一步澄清了福柯意义上的规范实际上并不存在主体服不服从的问题,在规训的机制下,个体将自己生产为符合规范的身体,这样,由于符合规范,个体才成为主体性。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不断地从事着规范机制的生产,而在生产机制下面,所有人必须选择在规范之下成为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从来就不是自然权利的产物,“它”的出现在根本上依赖于微观权力的规范体制。现代个体实际上都是这种现代规范的产物,我们被天生地塑造为一个主体,在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的地方,实际上已经成为依附于当代正常规范体制的孤立个体。而我们彼此间的联系,只有在共同规范和尺度下才有意义,比如说价值、年龄、学历、收入、颜值等等,在我们看起来拥有自由选择的地方,实际上我们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模式,我们在一个现代性的气泡中不断生产着自己,让我们自己更正常,更符合标准,我们不断地锻炼身体、做瑜伽、购物、泡温泉、买房、做美容手术等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自我选择的行为,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规范力量在引导着我们,在自我生产的喜悦中沦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装置的同谋。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第二个问题。士兵在面对规训机制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可能选择不服从,拒绝接受规训,拒绝大写的强制性规范,也拒绝变成被统计数字化的“人口”?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现代规范机制下,也建立了对应的排斥机制,也就是说,一旦建立标准和规范,我们便可以将所有的对象分成符合规范的对象(这类对象被视为正常人),而另一部分被视为是病态的,或者被称为不正常的人。从康吉莱姆开始,就思考了正常与病态之间的规范区分,他指出:“人只有在感到不仅仅是正常的——即适应了环境及其要求——而且也是标准的,能够适应新的生命标准时候,才会感到处于健康之中——这就是健康本身。”*[法]乔治·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李春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150页。康吉莱姆显然是在适应环境和生命标准的双重标准意义上来定义健康和病态的,这个双重标准建立了现代的病理学。福柯显然将康吉莱姆的生理学上的结论演绎到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的规范体制下,我们有一个正常人与不正常人的区分体制。对于正常人,是那些适应于生活环境和政治体制,即正常人,他们已经被架构在巨大的“人口”概念之下。而对于不正常的人,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游牧在体制之外。福柯以黑色的笔调对疯癫、监狱犯人、不正常性态的人研究,所面对的就是这些被体制所隔离的不正常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不正常的人迎来的绝不是解放,而是隔离和监禁。福柯说,对于那些不正常的人的隔离制度“这里不是一种排斥,而是一种检疫隔离。他们不是要驱逐,相反是建立、固定、给定他一个位置,指定场所,确定在场、被区分控制的在场。”*[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被隔离的不正常的人,需要重新完成自我的生产,如果不能完成自我生产,就必须被永远隔离。换言之,成为不正常的人,拒绝规范的规训,并不是帮助我们实现超越生命政治学的途径,相反,现代规范或规训的生命权力,就是隔离和生产不正常的人为前提的。在上面的问题中,兵营的士兵之所以接受规训式的纪律和身体生产,前提是如果是不正常的人,命运会更为悲惨,为了避免成为被隔离的不正常的人,每一个士兵都必须接受纪律的规训。唯有如此,正常人不断的自我生产才能成为可能,所有的正常人为了避免自己的被生命政治的机制所淘汰,就不得不按照新的规范来不断地生产自己,这同时是两个方面的生产,既是身体生产,也是意识生产,生命政治学同时在身体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完成对现代社会的治理,正常与不正常的人都概莫能外。
我们是否还具有超越生命政治的可能性?对于这样问题的回答,在今天不会有太明确的答案。其原因是,我们并不能具体把握在正常和不正常的二元分割之下,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性。实际上,理论家们已经开始从事这些方面的思考。利奥塔是比较早对生命政治的未来可能性进行思考的法国思想家,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已经提出了非人的概念。简言之,在当代生命政治之下,我们的身体已经毫无例外地作为社会人工技术的产物,我们的选项不可能是退回到一个前现代的状态当中,去拥抱所谓纯粹自然的身体,这种纯自然的身体只能在乌托邦的语境中存在,一旦出现在现实中,它毫无例外地会被现有体制所规范化,如果不能被规范化,面对的是被消灭的命运。所以,我们唯一的可能性在于未来,也就是说,尽管现代数字技术、生命技术、医学促成了生命政治体制在当代的实现,但是我们不能像一些带有前现代乡愁的思想家那样(尤其是海德格尔)去拒斥科学技术在今天的广泛应用。实际上,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科技融合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锻造为一种更适合于治理的对象,但是,这实际上是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的表现,我们可以展望的是,科技本身创造的可能性,至少可以打破眼下社会中的藩篱,利奥塔说:“技术-科学问题可以表述为:保证为独立于地球生命状态之外的硬件提供这种软件。”*[法]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罗国强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页。利奥塔将这种思维称之为“无身体思维”或“非人思维”,也就是说,生命政治治理的着眼点是一种规范的身体,即便是排斥不正常的人,也必须以身体为根本,我们今后的路径正是走向这种身体-技术的合成状态,这或许是我们眼下能够设想的超越正常和不正常二元对立的唯一途径。
2017-09-30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研究”(项目编号:16BZX016)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项目编号:16ZDA101)的阶段性成果。
D091
A
1003-4145[2017]11-0005-06
(责任编辑:周文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