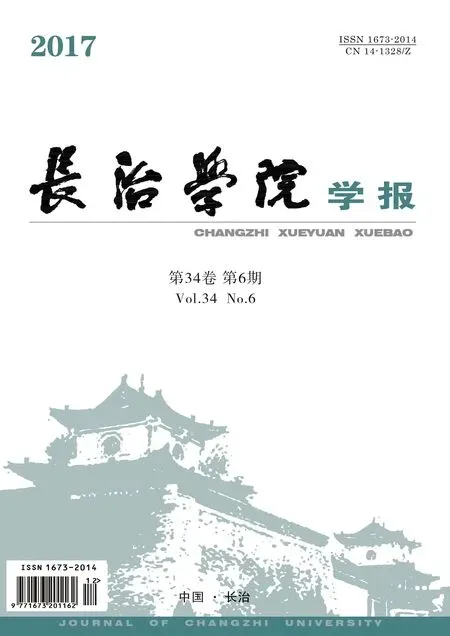康乾时期文言短篇小说中的宗教类儿童形象论述
2017-03-29李辰辰
李辰辰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一、宗教类儿童形象的具体类型及其作用
在儿童数量上,宗教类儿童形象并不在少数,可见当时社会中人们拥有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在艺术表现上,宗教类儿童形象往往在故事中作为陪衬性人物,伴随着道士、僧人等出现,或充当传达文章主旨的工具,或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完整发展的点缀作用;在思想成就上,作者借用宗教类儿童形象,揭示出世人生活中受宗教浸染的现象,并由此把宗教理念作为解释现实生活的思想依据,将宗教维护社会安定平稳的作用、对人们道德观念的禁锢作用展露无疑。
(一)道童形象
作者通过道童侧面辅助道士,用道教法术拯救自然灾害,救济社会灾难的故事,展现道教以“道生万物”为理论起点,发挥着驱灾避疫、劝善惩恶的作用。
1.驱灾避疫
《新齐谐·卷七·孛星女身》中塑造的道童形象可谓是典型道童形象的代表。道士为解救大旱,不得已登坛求雨,在道童手心上画三道符咒,嘱咐他寻找白衣妇女,找到后需按吩咐分三次往妇女身上丟掷符咒,将白衣妇女引来祭坛。后“童子往,果见白衣妇,如其言,掷一符。妇人怒,弃裙追童。童掷次符,妇人益怒。童掷三符,忽霹雳一声,赤身狂追。童急趋至坛,而妇人亦至”。[1]果不其然,恰如道士所料,道童按照道士的指示引来了白衣妇女,道士求得雨水,成功解救百姓于大旱之中。
作者将自己的笔墨重心放在了描绘道童掷符和奔跑的行为动作上,透过道童的行为和结果的正确性来验证道士判断的准确,表达了对道士的夸赞与景仰之情,赞扬了以道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中救世助人的社会功能。在那科技水平并不发达的时代,小到解救个人的疾痛灾疫,大至治理天地异象灾害,人类知识对很多真实生活中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都无法进行解释与处理应对,只能将自身人力所限、解决不了的事情寄托于道教神灵相助,请求消灾免祸,侧面展示了当时人们内心深处对道教的信仰与尊崇。
道教本身推崇清静无为的自然境界,这就决定了相对于追求世俗功名、利欲熏心的成人,会更倾向于选择自然、淳朴、单纯的儿童,放大儿童的自然纯真状态将它作为道童陪伴于道士身边,更能映衬出道士的仙风道骨,继而才能更好地揭示出道教保佑世人平安、驱灾避疫的作用。
2.劝善惩恶
《耳食录·卷一·竹冠道人》中描绘了人们希冀能从竹冠道人这里学习道家炼丹药延年益寿、点化金银乃至超脱尘世为仙的法术,道人虽苦口婆心劝慰世人“安知仙术何于之误耶”[2],奈何人们利益熏心,听不进谏言,竹冠道人唯有设计使自己忽染重病,考验世人的真心。在人们暴露残忍无德、唯利是图的本性后,道童以寻找师父的名号出现,配合道人上演了一出“假死”之戏,让诸人体会到慌乱、恐惧之感,给诸人以警示。
忽一童子造门请曰:“吾师在此否?”……道人已不能言,但以目视童,泪隐隐承睫。童大恸躄踊,呕血数声而绝。道人见之,长吁一声,亦死榻上。[2]
作者在这里对道童的语言、行为及面部进行了细致描写,塑造了一个单纯、忠贞、机智的童子形象,既符合儿童随机应变、机智狡黠的特点,又恰如其分地展现道童劝善惩恶的道教信仰。在道人和道童假死后,诸人试图掩埋尸体来掩饰罪行,在谋划瓜分道士腰间宝剑和黄金大喜之时,道士与道童“掷其剑化为龙,掷葫芦化为鹤,各乘其一”[2]飞腾而去,大家才明白这是道士仙人想借此考验他们虔诚求道的游戏。
本文虽从人们留下道士渴望“被度化”开始描写,但作者并不是为了描绘道教的“平等度人”的故事,转而重点描绘世人发觉无利可图后的丑陋嘴脸,对经受不住考验的世人进行了变相的嘲讽挖苦,作者在传达道教教化普度众人作用的同时,也表达出了民众对道教拥有绝对的虔诚信仰是必要前提。
(二)佛童形象
作者对佛童形象在语言、行为、性格等方面的刻画,不仅是揭示人物命运、宣扬佛教教义、对人民进行伦理教化的内在动因,更是为了展现现实生活中百姓对佛教的尊崇与向往之心,和佛教解救苦痛生活中百姓作用的外在因素。
1.展现百姓对佛教的尊崇与向往之心
《萤窗异草·卷二·小珍珠》中塑造了鲜明的僧童形象。入京考取功名的苏姓、李姓二考生,因付不起京师房租,无奈到僧庙寻找住宿,僧童愿意帮助他们二人留宿留云观。二生到达观内时不满足眼前普通景象,想见后园的美丽景观,幼僧出于师傅们的教诲,告知二生园内有狐妖作祟,不愿带其前往,无奈二生哀求,再三犹豫后只得引导两人进入园内。
此处幼僧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因,一方面,作者抓住信佛之人乐善好施的特点,让幼僧给予落难的二生援手,另一方面,作者又抓住幼僧作为儿童,原则性不强、易动摇的特点,顺理成章让幼僧带二生进入本不该入内的后园。后果不其然,苏生因品行不端受狐妖惑,暴卒;韦李生心正品端,留有后福,科举高中,僧人所言均实现。此处将佛教预见未来、解救苦难的作用加以强化,进一步将佛教对人民的道德规范加以神化。最后,作者借僧人之口“然早与予言,置经一卷于室中,则苏君亦可以无死”[3],表达出仅有一卷经书便可躲避妖邪祸害的观点,展示出作者对佛家教义经典、佛教义理的信任,亦可以点见面,看出社会实际中不乏对佛教抱有纯粹、真挚信仰的百姓之态。
2.揭示佛教对苦痛生活中百姓的解救作用
《聊斋志异·卷一·偷桃》篇便是以佛教文化为表现主旨的架构和背景下展开,文章从术人表演要去天上的蟠桃园中取桃子的术法开始写起,但因自己年老身体笨拙,担心难以完成任务,便让儿子攀登绳子上天取桃。与一般对家长言听计从的儿童不同,这里的儿子不再仅仅是被动听从吩咐,转而将自己攀爬登天的恐惧和忧虑直接地告诉了父亲,直至父亲向他保证若取桃成功,便将高额的赏金为他日后娶妻所用,他才答应冒险取桃。此处的儿童已不再是“一个事事依赖我们的呆滞的生命,好像他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填充的空容器”[4],是个有血有肉、有自己主见的真实儿童。
作者将重心放在了儿童攀登上天的动作描写,“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5]将儿童敏捷、灵巧的身形特点凸显,为其后天上果真坠落桃子打下伏笔。后作者又将儿童的身躯从天坠落,在术人收取足够的赏金后,儿子却又完好无缺地从筐中出现,向众人道谢赏赐、皆大欢喜的故事叙述完整,以传达法术的神奇之处和民众受法术逗乐的欣奇喜悦之情。
直至最后揭露,只有白莲教——这个在尊崇佛教教义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教派擅长此术,进而点出术人与他的儿子是白莲教苗裔——即佛教信徒信童的事实。清初时期,满族统治初定,汉族人民各种反清斗争不断,白莲教即是反清的秘密组织之一,政治环境不稳,社会中各阶层人群错综复杂,蒲松龄借用儿童表演“偷桃”这个简单术法,透露出任何普通百姓儿童都可能是白莲教教徒,展现出佛教文化在当时已浸入日常、随处可见。而由佛教文化演变发展而来的普通术法,亦可供寻常百姓消遣取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佛教文化已成为缓解百姓心中痛苦和矛盾的工具。
二、宗教类儿童形象生成根源及社会文化内涵
毋庸置疑,小说中出现的宗教类儿童形象,是对现实生活中拥有宗教信仰的儿童的真实写照。而宗教本质上属于一种出世文化,人们在生活平稳顺利之时是不会感受到信仰的珍贵,唯有历经苦难折磨的时候才会追求精神寄托,寻找一方属于自己的净土,以缓解真实生活中的痛苦。
儿童更是如此,无论是体能还是精神上都未发育成熟,在同等情况下,受伤害的几率和寻求宗教庇佑的可能性比成年人大的多。“就自然的状态来说成人能够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小孩不能。因此,成人有更多的意志,小孩有更多的妄想”[6]作者借用宗教类儿童形象,更能鲜明反映出当时社会、国家政权、道德观念等各种情形。
(一)社会现实局面的反映
一方面,政治局面上,尤其是康熙在政的清初时期,百姓刚经历明清政权变动的战乱,本该休养生息,安定复苏,可实际情形却并不如人意,一方面,清政府当权虽已成定局,但南明王朝残余势力仍在,藩王割据,全国没有得到统一,政局动荡;另一方面,相较于全国大部分的汉人局面,掌权的满族贵族统治者有意识拉开阶层差距,满汉民族矛盾尖锐,各种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层出不迭。百姓仍旧每日活在担心受怕中,以个人微小力量找不到未来出路,精神苦闷,容易接受宗教思想,而在战乱动荡中失去父母亲人,自幼被佛教、道教中人收留抚养长大的儿童更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经济层面上,康乾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产生,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相较于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以商帮、集市为市场表现形式,不仅受众人群广泛、流动性大,而且其交换、开放的特征决定了自身较高的不安全系数,人们在激烈竞争中渴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希望能维持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民间宗教信仰恰如其分地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慰藉,人们信奉推崇宗教,祈求上天神明等庇佑,以求自己心中所想能够达成。
(二)国家政权控制的需要
康乾时期,君主专制极大加强,中央集权程度也进一步加深,正如宗教同样无法脱离国家政权独自发展般,帝王为巩固统治,也不得不依靠于宗教以加强对百姓的思想禁锢。宗教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同样拥有着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价值,它依附于封建统治,也服务于封建统治。
伴随着统治者的政策引导,佛教在康乾时期迎来了一段小兴盛期,社会实际生活中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僧童佛童,他们在宣扬佛家的“因果报应”、“业报轮回”思想的同时,也客观上加强了对人们的道德束缚,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佛家宣扬因果轮回,劝人为善,希望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积累好的业报,以解救自身苦难,追求此生或来世的幸福安康,向往超脱苦海的极乐世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稳定发展,更深层地维护了政权的持久长续。
官府对道教采取了与佛教大致相同的政策,既防范抑制其迅猛发展,又恰当地利用道教文化控制百姓,巩固统治。社会中,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层出不穷,除了百姓心中视前明王朝为正统,希望复辟朱明王朝的固有观念外,更主要的还是人们心中无法接受满族的“异族”统治。清朝以八旗子弟代表的当权贵族为满族人群,信奉以天神、地祇为代表的萨满族,这与道教文化中汉族人们尊崇的天帝、土地公就有着相似之处,适度放松道教的发展更有利于满汉民族的融合,有益于缓和民族矛盾,有助于社会稳定,对维系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更有着积极意义。
(三)传统伦理道德的延续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伦理道德纲常为核心,以忠君为民、兄亲弟恭为主导观念,对人们进行精神道德规范,而很多佛家义理、道家教义本质上都对儒家传统伦理纲常起到了延续补充的作用。
康乾时期,统治者对待宗教的整体政策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补充。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三纲五常”建立在以宗法制为基础的血缘关系之上,造成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虽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也遏制了个体的自我发展。每个人因受自身身份等级的约束从而遵从社会秩序,但就自我意识而言,对于为何要遵守与维持伦理道德纲常,人们可能尚存怀疑。而道教宣扬的“神仙信仰说”、佛教的“地狱报应说”则将这种思想意识层次上的道德伦理观念加以神化,通过神仙鬼怪、天界冥间等给人们以威慑,让人们追崇为善,渴望积累功德业绩,早脱苦海登向极乐世界,亦或怕死后下地狱接受严酷惩罚,不敢为恶。如此,人们在心理上获得极大安慰,渴望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个人开始自发追求真善美等美好事物,自主维护伦理纲常。
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们以年幼涉世未深、受世俗影响较小的儿童为代表,一方面,对宗教类儿童和其身上拥有的宗教信仰进行描绘,展现出宗教理念对民间渗透的广泛性和百姓接受宗教观念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作者们又通过宗教观念对人们进行规范与约束作用的描绘,反映出宗教观念对人民发挥着极大的道德钳制作用,凸显出其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延续补充作用。
[1][清]袁枚著,崔国光校点.新齐谐--子不语[M].济南:齐鲁书社,2004.137.
[2][清]乐钧著,范义臣标点.耳食录[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32,32,33.
[3][清]长白浩歌子著,陈果标点.萤窗异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87.
[4][意]蒙台梭利著,高潮、薛杰译.有吸收力的心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23.
[5][清]铸雪斋抄本,蒲松龄著.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2.
[6][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M].北京:商务印书版.19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