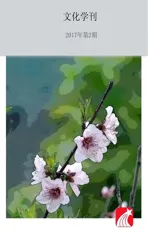试析古勒扎尔短篇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
2017-03-29李宝龙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李宝龙(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试析古勒扎尔短篇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
李宝龙
(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古勒扎尔是印度当代著名小说家,对印度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推动了印度当代乌尔都语短篇小说的发展。笔者在阅读古勒扎尔两部短篇小说集的基础上挖掘他创作语言的突出特色,认为其作品中梵语词源词汇的选用使其区别于传统乌尔都语作家,印地语小说集的出版也使古勒扎尔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印度斯坦语作家。
印度;乌尔都语文学;古勒扎尔;《烟》
古勒扎尔本名森布尔纳·辛格·卡尔拉,1934年8月18日出生在英属印度旁遮普省杰赫勒姆地区迪纳市的一个锡克教商人家庭,幼年迁居德里,印巴分治后一直生活在印度。截至目前,古勒扎尔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乌尔都语小说集《烟》于2002年获得印度国家文学院奖,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他也因在文学领域的杰出成就被印度政府授予第三级荣誉公民奖。其创作的短篇小说语言特色鲜明,有别于传统乌尔都语作家。
一、梵语词汇的影响
小说集《烟》由乌尔都语写就。作者所用词汇词源广泛,除去乌尔都语中常见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源词汇外,作者还选择使用了大量的梵语词源词汇。
在分析这一现象前,必须对印度与巴基斯坦乌尔都语的使用和发展状况进行必要说明。1947年印巴分治后,乌尔都语在印巴两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具体使用上的差别也逐渐增大。在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成为具有法定地位的国语,在全国广泛推广。而在印度,作为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乌尔都语虽是被宪法承认的地方语言,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与印地语的争斗愈发激烈,地位一直较低。但庆幸的是,一大批学者、作家正在为改变印度乌尔都语的现状而不懈努力,古勒扎尔就是其中一位。他曾表示:“事实上,乌尔都语是印度最为世俗的语言之一,它的使用者遍布全国。”[1]
乌尔都语在印巴的不同地位使它在两国有不同的影响。在印度,年轻一代人的乌尔都语因其接受的印地语教育而受到梵语影响;与之相比,巴基斯坦国内使用的乌尔都语则较为传统,主要使用阿拉伯-波斯语词源的单词,梵语词汇相对较少。总的来讲,传统乌尔都语更多使用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汇,极少使用梵语词汇。
古勒扎尔对乌尔都语在印巴两国的不同发展状态持接受的态度,他表示:“毫无疑问,乌尔都语根据它所使用地域的不同而被梵语化或波斯语化,这是一门活语言不断进化的标志。”[2]古勒扎尔分治后一直生活在印度,其乌尔都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语的影响。代表作《烟》也在语言上鲜明地反映出这一特点,这成为古勒扎尔乌尔都语短篇小说语言的一个主要特色。《烟》中梵语词汇的使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般词汇和专有词汇的选用。
就一般词汇而言,小说《半人》中写道:“人们因萨蒂亚无克制地与半人保持关系而感到恶心。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个曾与他们保持关系的女人如今竟要服侍一个侏儒。”[3]该句中作者在表达“关系”一词时两次使用了典型的梵语词源词汇“sanbandha”,而传统乌尔都语中一般使用波斯语词源的“rishta”表达“关系、联系”之意。又如《好买卖》中“陪嫁黄金和珠宝是对孩子的祝福,毕竟还是您的女儿佩戴它们”[4]一句,其中表示“祝福”所使用的“aashirvaad”一词也是典型的梵文词汇。再如,小说《给森林的信》开篇写道:“布尔纳河流经整个特拉伊森林。”[5]在表达“江、河”之意时,作者选择使用了梵语词汇“nadi”而非波斯语词源的“dariyaa”。
同时,小说集《烟》中还出现了“snaan”(沐浴、洗澡)、“baras”(年)、“veshaya”(妓女)、“nashd”(被消灭的、被毁坏的)、“aakash”(天空)、“daaru”(慷慨的、乐善好施的)、“nasa”(血管、筋)、“dukkaa”(一对的、成对的)、“gucch”(串、束)、“bartan”(器皿)、“grihsthi”(家庭生活)、“parivar”(家庭)、“shubh”(吉祥的)、“pita”(父亲)、“pati”(丈夫)、“braata”(迎亲队)、“vayapar”(贸易)等①参考古勒扎尔《烟》,印度文学院,2004年,第23、45、50、70、70、72、76、76、77、86、87、91、92、120、126、128、135页。梵语词源词汇。
专有词汇指涉及宗教、哲学和文化的词语。这些梵语词汇一般在某些特定场合使用,说明作者积极展现独特的文化背景。与一般词汇不同,这些词汇往往根源于梵语,一般情况下不可替换为阿拉伯-波斯词源词汇。以《穿越拉维河》为例,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锡克教徒。锡克教根源于印度教,后期受到伊斯兰教影响发展成为独立的宗教。但就教义讲,锡克教更偏向印度教。所以,在小说中德尔申·辛格的父亲不幸去世后,全家人为他举办了“葬礼”(samskaar),而后被迫迁居印度。句中的“samskaar”是梵文词,意思是“净化、清洗、葬礼”,此处特指葬礼。而在乘车横跨拉维河大桥时,为了能使亡子“圆满”(kalyaan),即“美好”“美满”,受到神灵的庇佑,德尔申将其抛入拉维河。再如《比玛尔大哥》中写道:“因有数以千万的游客前来参加贡帕庙会,其准备工作提前数月就已开始。”[6]作者在行文中使用了“yaatri”一词表达“游客”之意。因贡帕庙会是印度教的宗教盛会,参与者均为印度教徒,所以作者选择了同时含有“朝圣者”之意的单词“yaatri”,而没有使用阿拉伯语词源单词“musaafir”。其余篇目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amar”(不死的、永生的)、“dharam”(法)、“jaat”(种姓、阶层)、“mandir”(庙宇)、“bhagavan”(天神)、“vaidya”(印医)等②参考古勒扎尔《烟》,印度文学院,2004年,第28、70、70、75、120、121页。。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古勒扎尔所使用的乌尔都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语的影响,小说集《烟》作为他的代表作反映出了这一特点,这使《烟》明显区别于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文学作品,展现出印度语言的多元化倾向与融合的趋势。
二、从乌尔都语到印地语
除《烟》外,古勒扎尔还出版了印地语小说集《穿越拉维河》。因两部小说集中所含篇目大致相同,故《穿越拉维河》被认为是《烟》的印地语版本。
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同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在印度历史上被合称为印度斯坦语。多数学者认为,乌尔都语和印地语是不同形式的同一种语言。两种语言语法结构相同,但使用的词汇和传统字体不同。乌尔都语更倾向于使用阿拉伯-波斯词汇,使用纳斯塔里格字体;而印地语则使用天城体,更多选用梵语词汇。
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传统书写字体和所用词汇的词源差异上。而词汇的词源差异突出表现在名词与形容词的选用上。虽然在印度的印地语支持者宣称要构建一种“纯洁”的印地语,非“杂货店”式的印度斯坦语。但根据目前印地语的发展状况看,现今印地语中仍然包含大量阿拉伯-波斯语词源词汇,但更多的是梵语词汇。而乌尔都语,尤其是巴基斯坦乌尔都语与梵语的混合现象则不严重,它多使用阿拉伯-波斯词源的单词。毋庸置疑,印地语较乌尔都语而言受到梵文的影响更大。
古勒扎尔认为其小说集《穿越拉维河》并非是翻译而成,而是被转写成天城体的,这使部分读者认为《穿越拉维河》是“天城体版的乌尔都语小说集”。虽然在现今印度乌尔都语的天城体化现象十分常见,且将乌尔都语书目出版为天城体的情况非常普遍。但笔者认为,小说集《穿越拉维河》并非属于此类作品。
首先,在所谓的“转换字体”过程中,古勒扎尔并未完全将乌尔都语进行天城体转写,而是有选择地将某些词语进行了替换。例如在《黄昏大道》中,作者写道:“希夫德特很清楚自己的职责,他仍旧在外人面前为扎鲁树立名望。”在乌尔都语原版中,作者使用“fraayaz”表示“职责”,该词是阿拉伯语词“职责”(farz)的复数形式,而在印地语版本中作者将其改为梵语词源词汇“kartavy”[7,8]。此篇中作者还用大量笔墨描述了爱慕者仰慕扎鲁的内容,在翻译时同样进行了词语的替换。乌尔都语版本中表示“爱慕者”时作者分别使用了英语词“fans”和波斯语单词“parasataar”,而在印地语版本中这两个单词均被替换为梵语词汇“prashnsaka”[9,10]。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小说《比玛尔大哥》中,“太阳系的九大行星运转连接成一条直线”。在表达“行星”时,乌尔都语版中使用阿拉伯语词“sayyaarah”,但在印地语版中被替换成了梵文词“grah”[11,12]。又如《布偶》中写道:“库苏姆8年级时就已像10年级女生那样说话了。而进入9年级后,她觉得自己已像姐姐那样开始在大学里读书了。”在表达“年级、级别”时,作者在乌尔都语版中使用阿拉伯语词“jamaa‘at”,在印地语版本中则替换成了梵语词“shreni”[13,14]。此外,古勒扎尔在翻译《分离》这篇作品时,还替换了其题目,把乌尔都语版中表达“分离”的阿拉伯语词“taqasim”替换为了梵语词汇“batwara”[15,16]。
其次,作者的再创造体现在对两版本若干篇目中内容的删减或改写。例如,《谁的故事》中,主人公阿奴向“我”介绍了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状况。乌语本中写道:“他向我介绍了一些伟大的作家,有一些是我听说过的——萨达特·哈桑·明都、艾哈迈德·纳迪姆·卡斯米、克里山·钱达尔、拉金德尔·辛格·贝迪。之后,他又向我介绍了卡夫卡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印地语本中则增写为:“他向我介绍了一些伟大的作家,有一些是我听说过的——萨达特·哈桑·明都、艾哈迈德·纳迪姆·卡斯米、克里山·钱达尔、拉金德尔·辛格·贝迪。而之后提到的卡夫卡和萨特对我来讲则是陌生的。之前阿奴一直在讲小说的情节,而现在则在讲象征主义与存在主义,这已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17,18]
由此可见,《穿越拉维河》并非是天城体字体转写版本的乌尔都语小说集,而是经作者翻译加工、再创作而成的印地语小说集。作者在再创作时对乌尔都语原版小说中的一些阿拉伯-波斯词源词汇进行了替换,使乌尔都语小说集《烟》的梵文化程度更高,形成了更符合印地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印地语版小说集《穿越拉维河》。这使古勒扎尔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印度斯坦语小说家。与分析报,2012-01-15.
[3][4][5][6][7][9][11][13][15][17]古勒扎尔.烟[M].新德里:印度文学院,2004.50.134.145.23.33.32-33.23.99.174.44.
[8][10][12][14][16][18]古勒扎尔.穿越拉维河[M].新德里:鲁芭出版社,2014.8.7-8.72.93.53.34-35.
【责任编辑:周 丹】
[1][2]古勒扎尔.古勒扎尔采访录[N].每日新闻

汉 龙纹
I106.4
A
1673-7725(2017)02-0092-04
2016-11-30
李宝龙(1988-),男,河南郑州人,助教,主要从事印度近现代语言文学与南亚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