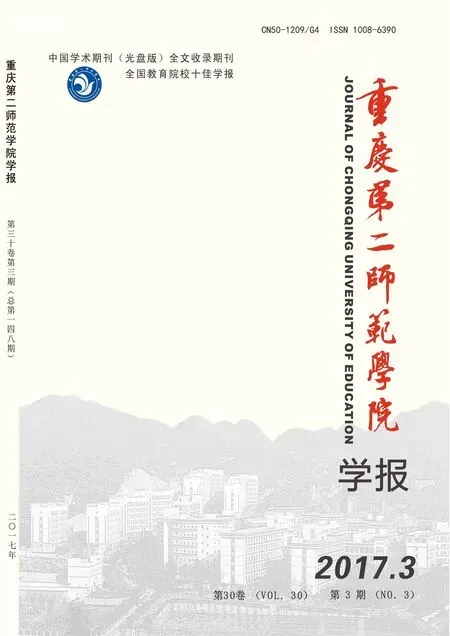韩少功《日夜书》大陆版与台湾版之比较
2017-03-28叶吉娜
叶吉娜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韩少功《日夜书》大陆版与台湾版之比较
叶吉娜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韩少功的小说《日夜书》有大陆与台湾分别出版的两个版本,均以类似纪传体的形式描写知青形象。但两个版本的叙事逻辑有所差异,叙事结构、人物出场顺序及散点透视程度不同。相对而言,大陆版有更多的跳跃、闪回、插入,跨越时空的对比更加鲜明,对知青群体、知青文学、知青心态、时代背景等的批判审视更见力道。而台湾版的叙事逻辑与历史脉络较为清晰流畅,在情感上更能引导读者进入情境,但有向单焦对称结构妥协的倾向,批判力道相对减弱。
《日夜书》;大陆版;台湾版;审视力度;比较
韩少功的《日夜书》除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大陆版)之外,还有台湾联经出版社推出的繁体字版(台湾版)。由于两个版本面对的读者对象不同,韩少功在《日夜书》台湾版中对叙事结构作了相应调整,基本恢复了时间顺序,减少了跳跃、切割、闪回等叙事手法的运用。这就使得两个版本在叙述知青一代的过去与现在、展开多种对话关系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风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话语资源和全新的辩证批判的认识视角,值得比较研究。
一、两个版本的叙事结构有所不同
《日夜书》大陆版以更符合人类自身散漫的、游走的、混乱的思维形式的叙述语言,即通过一种拼贴的、自由的、支离的叙事方式来讲述这段知青史或者说社会史。台湾版相对而言逻辑性较强,有一条较为清晰的时间线,能够更有效地牵引对中国当代史不甚了解的读者顺利进入小说情境。因为叙事顺序的不同,所以其中也会涉及章与章之间的过渡、段与段之间的衔接、人物与人物之间故事细节的糅合与拼接。总的来看,不同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小说前三章的顺序不同;二是大陆版相比台湾版多出三个词条形式的章节,而台湾版根据词条内容已将其拆解并放入相应的人物传记章节;三是马、郭两家人物出场顺序不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故事情节也因此有不同的糅合与嫁接。
(一)小说前三章的叙事顺序不同
《日夜书》大陆版前三章叙事顺序为“姚大甲—白马湖茶场—校园”,台湾版前三章叙事顺序为“校园—白马湖茶场—姚大甲”,两个版本的次序完全颠倒。这种叙事次序的不同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时空跨越的比对”[1]和作者对那段历史的审视态度的差异。大陆版以一个油滑、不正经的人物——姚大甲开端。第一章拾取了姚大甲“公用鳖”、“‘大肠杆菌’隔离事件”和“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等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记忆碎片,与当时那个表面看上去恢宏雄壮、光芒万丈实则夹杂无数艰苦日子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格格不入。韩少功在大陆版的第一章就用姚大甲这个不正经的人物和一系列荒唐可笑的事件解构了我们对那段岁月、那场运动、那段历史固有的印象。正如他曾在与王尧的对话中提及的对于知青群体、知青文学的态度:“在我看来,‘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1]所以,在小说的第一章,韩少功就用这样的处理让我们看到他对那段知青岁月、红色历史辩证的审视态度。
《日夜书》台湾版前三章则遵循了基本的时间次序,第一章条理清晰,直接回忆了未满十六周岁的“我”面对留在父母身边继续升学还是下乡当知青的选择迷惘不定,最后还是自投罗网、青春失足奔赴乡下。但现实与想象的巨大反差却让这个少年失声痛哭。韩少功将彼时看似热烈激动实则空洞乏味的红色时代下少年的迷惘、无依无靠缓缓诉诸纸上。第二章顺时回忆在填不饱肚子、工分任务又重的岁月里,闹了“吃死人肉”和“被雷劈”的糟心事。第三章则继续回忆第二章出场、与“我”同住一屋的大甲闹出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由此可见,台湾版的叙事相对大陆版而言更加晓畅明确,带给读者的阅读难度相对较低,符合“人类单焦对称的内在审美需求”[1]。对于两个版本不同的叙事逻辑,韩少功曾经作过解释:“想比较一下不同的测试效果。”[1]我们认为,台湾版前三章的叙事虽晓畅但没有大陆版叙事结构带给读者的冲击力大,对那段特殊岁月、特殊年代的审视没有那么犀利。
(二)以词条形式独立存在的三个章节
比对之下我们发现,《日夜书》大陆版有三个特殊的章节,以看似独立的词条形式单独存在,而台湾版已根据词条内容将其拆解并放入相应的人物传记章节。这三个章节在大陆版中分别是:第11章“泄点与醉点”,第25章“准精神病”,第43章“器官与身体”。这些都是具有理性思考色彩的篇章。韩少功“不是要用思考代替叙事,只是说思考的介入如果有利于释放叙事、保护叙事、推动叙事,那么介入就是合理的,是小说作者的职业特权”[2]。相比台湾版,读者可以更明确地知道自己此时进入了理性思考环节,比起将这些思考糅合进小说叙事内容中,读者有更多的时间和独立的空间去思考这个命题。
第11章“泄点与醉点”之下集结了N、小安子、姚大甲、吴天保、万哥等人物的“性事”。N夫妻认为圆房是道德败坏、见不得人的事,因此结婚多年不知圆房为何事;小安子则有受虐倾向,甚至有性变态的端倪,喜将红色恐怖的记忆当作诱发春情的最佳情境;吴天保“哪一块膘不好”的女性评价体系;万哥对老婆的嫌弃。作者将这些人物有关“性”的部分集中放置,是为了提醒读者关于“醉点”的哲理。人作为高级动物,在性方面的亢奋受到很多心理信号的驱动,而这些心理信号来源于包括经历、积习、想象、审美偏好等文化信息的影响,忽略这些差异,将人的情欲与简单的动物性本能画等号,是一种巨大的遗忘和自我安慰。正如N的荒唐是由于那个年代封闭的思想环境所致;小安子的性变态,与当年母亲和继父为求一时的鱼水之欢而间接害死小安子年幼的弟弟有些联系,之后小安子也成为受害者(一向胆大的小安子以后见到洋娃娃都会很惊骇),所以她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在性场景中将自己弱者乃至受害者的形象还原出来。而一辈子待在乡里的吴天保,则持有“奶子砣砣的,屁股大大的”好生养就是好女人的评价系统,这是乡村农耕文明下的典型性心理。万哥嫌弃老婆口臭、哈欠多、在床上嗑瓜子、不让自己念诗看小说,究其原因是两人介入生理反应的心理信息不同,其实质是两者文化背景不同。这些人的性心理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受到了历史、社会、文化的多重信息介入。韩少功借这种集中式的议论向那些口头呐喊“回到身体”但实际却无视文化、历史对情致的影响从而变成露阴癖式的畸形文化心理以深刻的理性批判。
(三)人物叙事结构有所不同
韩少功曾说:“如果说《马桥词典》更像笔记体,那么这本《日夜书》可能有点接近纪传体,人物相对独立,但互有交叉。虽然这样不一定好,但也算是我对本土文化先贤致敬的一种方式吧。台湾版的《日夜书》与大陆版稍有结构的不同……”[1]通过对两个版本的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在对人物描写的施力程度上差异不大,只是在叙事结构上略有差异。
在大陆版中,韩少功着墨较多的人物是“我”(陶小布)、吴天保、小安子、郭又军、马楠、马涛、笑月、贺亦民等,着墨较少的人物则有姚大甲、杨场长、阎小梅、马母、秀鸭婆、“酒鬼”等。一般来说,着墨较多的人物出现在多个章节,而着墨较少的人物大多出现在单个章节里。台湾版也是如此。在描写人物时,韩少功参考了中国古代史书的撰写方式,以不同的人物为中心设立独立章节,有利于人物的集中描述与刻画。同时由于人物之间有牵涉,因此A人物会出现在以B人物为主要叙事中心的章节中,比如大陆版第18章是以马楠为叙事中心的章节,但在这一章中也加入了“我”和马楠下村筹备文艺会演而住在一起的故事。这也是必不可少的糅合,如此人物之间的联系才能加强,全文的叙事才不至于断裂。同时,韩少功在借鉴纪传体为人物立传的写作方式时调整了叙事结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传记内容、故事细节被糅合、嫁接。例如,“与有严重洁癖的护士发生性关系”这段故事,大陆版的男主人公是姚大甲,在台湾版中则变成了小安子口中的一个故事,其主角并不是姚大甲。这种叙事差异使得姚大甲和小安子在两个版本的叙事中各自得到了性心理与文化信息关系方面的补充。此外,《日夜书》还将同一人物的传记内容切割打乱,这也是两个版本共有的特点。
二、两个版本的人物出场顺序有所变化
韩少功本人作为知青群体中的个体,“对(知青)这些影子既有珍惜,也有质疑,既不愿意把他们摆在表功会的位置,也不愿把他们摆在诉苦会的位置”[1]。在《日夜书》中,韩少功选择史书中的纪传体形式来呈现他最为熟悉的知青历史,小说中各个角色的故事内容相对独立但又时有交叉糅合,同一个人物的故事也被切割、打乱。韩少功选择这种叙事方式,让人物的过去与现在形成对话结构,不同人物的人生际遇之间也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韩少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知青群体形成一种内部自省,而不是进行简单的叙事呈现和带有情感倾向的单向定位。同时作者也借“陶小布”这个知青个体对特殊年代形成的知青心理进行外部的辩证理性批判。而台湾版《日夜书》的叙事结构作了相应调整,强化了小说的时间次序,减少了跳跃、穿插等叙事手段,这种差异在影响两版小说不同阅读流畅度之外,也造成了不同的审视效果。
基于《日夜书》对已成固定、封闭模式的知青叙事和被简单化、单面化、两极化的知青群体形象的批判审视,结合两个版本中不同的人物出场顺序,本文对马涛、姚大甲、贺亦民三个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分析。
韩少功辩证审视与理性批判的态度在马涛这一人物身上展现得最为深刻明显,这个在暴动喧嚣的红色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具有受害者与施暴者的双面特征。马涛天资聪颖,不盲从不流俗、能独立思考有独到见解,这种知识分子的自觉值得学习。但马涛的这种思想先锋的身份是建立在对家人、朋友的伤害基础上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也是残忍的施暴者。他逼得母亲将压箱底的首饰典当;妹妹一次次的卖血直到晕倒在医院门口,甚至为了解救他这个哥哥失去贞洁导致不孕不育和后半辈子的无穷痛苦,这一切,马涛都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空洞高悬的民族政治,手铐脚镣无疑在此时证明他的高贵和威严,如果家人有一点抱屈和申辩那就是落井下石和助纣为虐。在塑造马涛这个人物时,韩少功注重的并不是马涛的个人观点(无论是对政府的意见、对现代权力结构的创见还是哲学王者的思考),而是看到了其人背后的思想本质——一种人格的自我膨胀。“相对于他的立场和观点,他的人格心态更让我有痛感。这种痛感也许恰好来自我对他的珍惜。”[1]同情与珍惜,疼痛与批判,这是韩少功对以马涛为代表的知青群体的审视态度,解构了人们传统观念中的知青印象。
具体到两个版本对马涛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如何通过叙事表达对这个代表性人物的审视与批判的。大陆版对马涛的描写采用了一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手法。小说第12章,在地下革命此起彼伏的年代,“我”怀揣着马涛寄来的关于国家形势的分析信,这封信让我兴奋到无法自持。但是“我”自己也发出了一连串疑问:农民运动确实重要,但该从何处着手?高层确已出现裂痕,在报刊的字里行间暴露无遗,但那几个色彩暧昧的老帅到底能起什么作用?……这种疑问还不待严肃思考,便被两个红薯打败,于是“我”确认远水不解近渴,红薯比革命更能消除自己的头昏目眩。这一章的处理是否已经在马涛未正式出场前就预示了他及他所代表的知青群体、知青思想的悲剧性。马涛第二次出场是在小说第13章,通过对马涛极度崇拜的罗同学之口,一个在知青群体中享有盛名的思想者形象呼之欲出。之后对马涛“大字先生”“逃票被抓”事件的描述不禁让人想到科学天才与生活白痴集于一身的科学家。“我”回忆在父母双双收监的日子里,马涛给“我”阴暗的人生带来了希望和温暖。自此马涛聪颖过人、不拘小节、热情豪爽的一面被展示出来。在12、13章的侧面烘托之后,进入到以马涛为叙述中心的19、23章。在这两章中,上文所说的施暴者形象出现了,与小说此前的叙事完全相反,给读者已经构建的马涛形象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至此,韩少功完成了对人物的辩证批判与理性审视,对红色年代里知青的自我膨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而在台湾版中,韩少功依照中国常见的熟人逻辑交代了马涛的出场,说明因为马楠的关系,认识了她哥马涛,同时他也是郭又军的一位朋友(第13章)。同时这一章也包括了马涛和郭又军比赛跳水的故事,至此,马涛固执、偏激的人格已现端倪。如此设计,就是让读者心中有所预警,对小说后面出现的施暴者形象的接受难度降低,反差的冲击力随之降低,作者所希冀达到的批判力度也有所减弱。
第二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姚大甲。大陆版第一章以一个看似非常不正经的人物姚大甲拉开小说叙事的序幕。与当时那个严肃正经“文化大革命”、艰苦漫长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基调一点都不吻合,借此解构读者对那段岁月、那场运动的固有印象。台湾版中的姚大甲在第二章“吃死人肉”等事件中作为参与者出现。第三章则作为叙事中心出现,事件与大陆版第一章一致。台湾版的改动将姚大甲这一人物的时代消解意义与反讽作用大大削弱,使小说开头的基调失去了严肃沉重的力度,有转向平庸之嫌。
第三个代表人物是与这群知青截然不同的贺亦民。大陆版中贺亦民集中出现于40-43章、46-48章。第40章讲述贺亦民在家庭和学校受到的歧视和侮辱。41、42章承接时间顺序讲述离家出走的贺亦民走上小偷、老千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代“扒手王”。后来由于避祸躲到“我”所在的乡下,他的到来对“我”的思想产生巨大冲击,“我”终于认识到“艰苦环境对人是一种锤炼”这样的话是一种“屁话”,开始认识到在这个山沟沟里将冬瓜汤喝到共产主义的虚无缥缈,开始对自己的人生产生疑惑。第43章以“器官与身体”的词条形式出现,讲述了关于贺亦民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或X)。贺亦民吃的饭要越硬越好,对老婆粗鲁无礼,甚至动手打人。第46章陈述了贺亦民在油田开发方面进行的惊天动地的技术革命。第47章人物悲剧性初现,贺亦民不愿失信于油田,想为国家出力,却遭到权力机构内部对其的碾压与伤害。第48章,贺亦民爱国情怀变得更为激进,最后无奈选择做了“人肉炸弹”。而台湾版中的贺亦民出场比大陆版早,第23章第一次出现,内容与大陆版第42章一致。第42章与大陆版第41章内容一致,第43章与大陆版第43章内容一致,讲述了贺亦民身体各个部位和器官。第44、45、46章与大陆版第46、47、48章一一对应。
从上述分析可知,《日夜书》两个版本的主要差别在于台湾版比大陆版更早安排贺亦民让“我”对那场运动、自我人生产生怀疑。贺亦民这个个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知青群体和知青思想的巨大讽刺,也是对时代的嘲讽,在讲究政治正确的红色狂躁年代,他如小偷小摸、流氓地痞般顽强生存,“文革”结束后,又红又专的哥哥郭又军渐渐平庸,而贺疤子却走上了发明家、电器大王的大路,混得风生水起,这是否能引起人们对习以为常、所谓正确社会秩序的反思。作为一个结构僵化的知青群体面貌和荒唐的年代历史,贺亦民的出现无疑是正面甚至伟大的,但最后他的结局也让人失落感伤。也许正如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203
三、散点透视下跨越时空的对话与审视
韩少功在《日夜书》中曾经表露其叙事者的身份,大陆版(第37章第2、3段)与台湾版(第37章2、3两段)都有这样的插入:“我常常在想,上帝大概是不读小说的。因为我独自一个人靠近上帝时……内心中闪烁更多的是零散往事,是生活的诸多碎片和毛边,不是某种严格的起承转合。”“对不起,我的写作由此多了很多犹豫,也会有些混乱。”这一段文字与韩少功在与王尧对话中谈论《日夜书》的内容如出一辙:“我只是觉得‘散文化’或‘后散文’的小说是可能的增加项,因为社会生活自身的形式,人类思维自身的形式,往往是散漫的、游走的、缺损的、拼贴的甚至混乱的,其中不乏局部的‘戏剧’,但更多时候倒是接近‘散文’。这构成了另一种小说审美的自然根据。我在这本书里说‘也许上帝是不读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在夜深人静时,似乎最接近‘上帝’时,脑子里哪有那么多起承转合?哪有那么多戏剧化的一幕一幕?如果我们只有一种单焦模式,只是袭用旧的单焦模式,会不会构成对生活与思维的某种遮蔽?特别是眼下,各种所谓宏大叙事正在动摇,很多旧的逻辑霸权需要清理,警觉这种遮蔽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相应的文体尝试也许并非多余。”[1]
这种散点透视的叙事方式使得《日夜书》的叙事线并非是顺畅流利的,而是不停被中断,典型如大陆版第11章、第25章、第43章,在叙述中突然插入具有理性哲思的内容。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并不是韩少功最在意的,通过跳跃、闪回完成过去时空与当下时空的对话才是韩少功所追求的。《日夜书》先后描写了十多位人物,这些人物形象都以单独的纪传体形式呈现,就像中国画中的多个散点透视,焦点与焦点、人物与人物之间没有表面的逻辑关系,互相不阻碍对方的逻辑展开,但同时人物之间又有交叉,最终形成一种独立但不失联系的逻辑结构。
单焦透视的写法带来漫长的叙事逻辑与清晰的历史脉络,散点透视则一击而中,有更巨大的冲击力。相比之下,跳跃、切割、嫁接更多的大陆版其散点透视的特点更为明显,而对叙事结构有所调整的台湾版则散点透视的功力不如大陆版深厚,有向单焦对称结构妥协的嫌疑,因此台湾版所带来的冲击力也相对减弱了。
知青这一群体在艰苦贫瘠但精神振奋的革命年代度过人生最有精力的十年,革命年代过去,他们迎来了物质充沛但精神空虚的年代。韩少功觉察到了两个时代的某种内在联系:“历史发展不是切换式的,是无缝的转换,是要素的重组,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生活巨流。”[1]于是作者在小说中借切割、嫁接、跳跃等叙事手段,实现人物过去与当下的对话。当年无论是在知青圈里风生水起盛名遍识的风光还是因政治罪被捕入狱的苦难,它们殊途同归地都让马涛找到了自我价值和重要性,虽然物质贫乏自由受限,但是精神上却从来不空虚。知青时代的马涛一直处于焦点位置,是整个圈子的精神领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反观当下,虽然物质生活已不成问题,但是马涛却失去了众人的景仰、崇拜和追捧,光环不再,聚焦不再,自我优越感与膨胀感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是马涛最在意也最无法接受的,因此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乖戾。如果让人物自己作选择,马涛一定愿意回到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时代。
《日夜书》犀利地呈现了“知青后遗症”。知青这一代人承载着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的记忆,那个时代的所有历史记忆也都能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上找到对应点。这一批人,被历史塑造,同时也塑造了新的历史。将粗鄙以后现代艺术包裹兜售的姚大甲,在外国文艺界获得了“入场券”,这让作者嗅到了历史的某种气味;而马涛,也许表面上是对革命年代的政治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的,但是当他在指责他人时却不自知地流露出当年红卫兵的口气,俨然一副中纪委工作人员的模样。笑月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一段控诉,可以看作对知青群体、“知青后遗症”的尖锐批判和审视:“你要我说人话?你和我那个爹,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大骗子,几十年来你们可曾说过什么人话?又是自由,又是道德,又是科学和艺术,多好听呵。你们这些家伙先下手为强,抢占了所有的位置,永远是高高在上,就像站在昆仑山上呼风唤雨,就像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玩杂技,还一次次满脸笑容来关心下一代,让我们在你们的阴影里自惭形秽,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尽管这样的控诉失之偏激,但也必须承认其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笑月所指责的,不正是那一代人难以撇清的罪恶吗?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墨家思想,跳出了封建制度的框架,照样可以为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提供依据和革命家们摇旗呐喊的口号。同样的,在革命年代形成的思想观念,剔除个人崇拜和权利话语的部分,也可以成为新一轮革命的导火索。这一批人,正是当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掌握着中国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大权。作家借“我”的眼观察过去的时代与人物,借“我”的口说出对那个时代的质疑,对那段历史和知青群体进行反思与审视。这或许就是作者所说的:“在一个‘自我’神化的时代,在启蒙主义、进步主义、个人主义、激进主义的世纪新潮以后,旧帝王被打倒了,一群群小‘帝王’却取而代之。官僚专制、资本专制、宗教专制等,不过是这些新型帝王的体制外化,是一片有毒土壤里长出了不同的苗。”[1]而这些人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这不该引起我们更深刻的反思吗?在这里,作为作家的韩少功与作为叙事者的“我”重合了,他在《日夜书》中做出如此深刻尖锐的批判,勇气巨大,让人敬佩。
我们不应给《日夜书》扣上简单的“知青文学”的帽子,因为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知青文学的解构,甚至对红色时代与知青群体进行了解构。尽管给作家作品贴上标签是评论家常见的行为,有利于文学史书写,但是作家们通常不愿被这种标签束缚手脚,因为任何一种帽子,都承载不了文学作品的全部意涵。从认识社会和历史来说,小说相当于原料供应商,而不是产品加工商和说明书,小说提供思考的内容对象、提出问题但却不一定提供答案。通过对大陆版与台湾版《日夜书》的比较研究,我们对韩少功在这部小说中呈现的彼时红色年代与当下现实社会的精神危机、思想枷锁和畸形话语应该有了更深刻的透视。
[1]韩少功,刘复生.几个50后的中国故事——关于《日夜书》的对话[J].南方文坛,2013(6).
[2]胡妍妍.韩少功: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N].人民日报,2013-03-29.
[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于 湘]
2016-12-09
叶吉娜(1993— ),女,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7
A
1008-6390(2017)03-00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