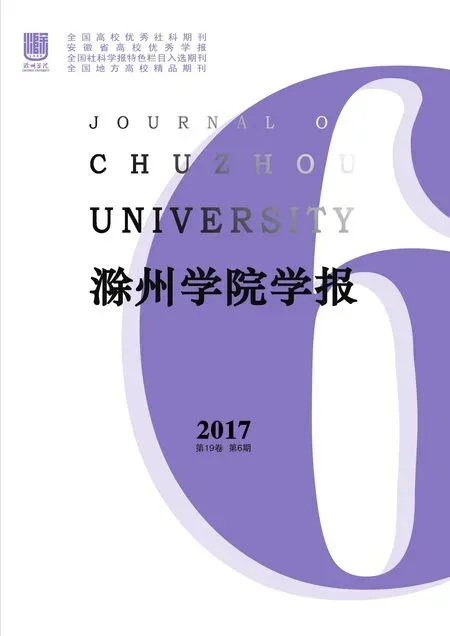论光绪《滁州志》的史料价值
2017-03-28郑益兵
郑益兵
光绪《滁州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背景下纂修的一部通志,是对滁州地区历代自然和社会情况的综合性记述,囊括了该地的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文化、教育、人物、风俗等各方面内容,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这些资料的价值,有利于促进当前相关学科的研究以及滁州地方建设。限于篇幅,本文仅从经济、政治、军事、地理四个方面论述光绪《滁州志》的史料价值。
一、经济方面的史料价值
李史谦指出:“旧方志的修纂普遍存在着重人文、政权和自然面貌的记述,忽略经济记述的偏向。”[1]张文贵、荣竹林也指出:“旧志重人文、轻经济”。[2]不过,从光绪《滁州志》看,该志书对经济方面的内容有着较为丰富的记载,如户口、田赋、土产、盐课、榷政等方面。这些记载主要体现在食货志里面,相当的篇幅突显了编纂者对经济问题的关注。
(一)赋税
赋税是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的重要手段,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主要财政来源,历代统治阶级对此都非常重视。光绪《滁州志》对此有诸多记载。首先是丁税。如卷二《食货志·户口》记载:“顺治三年奉旨清查,丁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一丁半,每丁征银四钱五分六厘六毫二丝九忽有奇。康熙七年,丁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一丁半,每丁征银四钱九分二厘有奇。康熙十二年编审,丁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二丁半,每丁征银四钱九分二厘有奇。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恩诏内开绪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嗣后五年,编审人丁之例,永行停止。”尽管自康熙五十二年后再生人丁永不加赋,但志书对此后滋生人丁数仍有相关记载。如卷二《食货志·田赋》:“从康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二十六年止,滋生人丁一千八十八丁。”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比较全面了解清朝前期滁州人丁数及每丁征银数的变化情况。其次是田税。如卷二《食货志·田赋》详细记载了清初滁州田地、山、塘的数量及这些田地山塘总共折田数,对每亩科征的银数、米数、豆数及各自科征的总数额均一一列出。据此可以知晓清代滁州田税的征收情况。此外,志书还记载了诸多附加税的情况,如卷二《食货志·田赋》在统计丁、田二项通共征银的数额之后云:“随征加一耗银。”这些史料有利于学者对清代滁州附加税问题进行研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光绪《滁州志》还记载了清代后期滁州商税征收的情况,如卷二《食货志·榷政》记载:“布政司岁颁行单,业此(鸦片烟土)者领单开行,岁税上中下三则。上银三十两,中二十两,下十两,有差。每行认税若干。滁境行户率皆空乏,概请下则。初定税甚重,后以贸易细微,递减至五百两。州署招募土勇十名,凡未经投行交易者,谓之私土,拘获惩治,冀旺官销。光绪二十一年,齐任禀请裁撤土勇,奉批后任议复酌中定制,禀留六名,减税为四百两有奇。”这些内容对于研究清代滁州的财政税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土产
滁州土产非常丰富。谷之属主要有稻、麦、黍、菽、麻菽、豌豆、黄豆、蚕豆、麻等。蔬之属有菘、芥、芹、苋、菠薐、莴苣、萝服、菰、瓜、瓠、茄等。果之属有栗、杏、银杏、葡萄、芡、荸荠、莲等。木之属有槐、榆、楸、梓、枫、栩、松柏、柳、椿、桑、文木等。药之属有明党参、桔梗、甘菊等。畜之属有骡、驴、狐、鹿等。货之属有靛、罂粟、酒等。与前代志书如明万历《滁阳志》、清康熙《滁州志》只分类列举土产名称不同,光绪《滁州志》在记载土产时更多地使用说明性文字。有的对土产的适宜产地进行了说明,如:“在两山之间者曰冲田,其稼宜稻,岁一获。山坡曰料田,其稼宜麦、宜黍、宜麻菽之类。”有的对土产的古代名称或作用进行了介绍,如:“麻以苎麻为上,古所谓麻缕也。次则苘麻,子可以取油,干可以为薪,皮可以绹索,亦大利也。”有的对土产的采集、销售等情况进行了说明:“药草甚富,承平时人不知采,乱后客民麇集,藉以为生。岁二三月,男妇携筐以入山,虚而往,实而归。以明党参、桔梗二者为大宗,殷商巨贾捆载而适四方。甘菊产大柳者佳,谓胜于杭产,而不可多得。”此外,有的还对养殖业进行了动态记载,如:“向无蚕,二十年来始有之,而皆饲以野桑。光绪二十二年,请淮北牙厘局给湖桑四千株,环城而植,数年后蔚然成林,可供蚕食矣。”这些不见于其他文献的资料,弥足珍贵,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滁州地区丰富的物产,而且有助于学者对滁州物产进行相关研究,对于当前滁州打造区域特色经济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政治方面的史料价值
历代方志都是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而编纂的,光绪《滁州志》也不例外。光绪《滁州志》政治方面的资料,在公署、马政、田赋、水利、学校、名宦、星野等门类中均有所体现。
(一)职官制度
职官制度是国家对政府机构设置、职官名称、品级地位等所制定的制度。光绪《滁州志》卷三《营建制·公署》不仅比较详细记载了州衙署的设置,还记载了属衙机构,包括医学、阴阳学、僧正司、道正司、税课局、永盈仓、督学察院、滁州卫等滁州行政机构的设置情况。此外,对职官的设置情况也进行了说明。如卷五《兵卫志·马政》关于前朝太仆寺衙门的记载:“旧太仆寺衙门在城南郊,设卿一,少卿二,寺丞三,主簿二。又,令史五名,典史九名,今已革。”比较具体地记载了前朝滁州太仆寺衙门职官的名称和数量。这些记载不仅可与前代志书康熙《滁州志》互相参证,对于考察滁州行政机构和职官设置的历史变迁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光绪《滁州志》还记载了滁州地区官吏的俸禄情况。如卷二《食货志·田赋》:知州员下,编给俸工等银八百三十八两四钱(知州俸银八十两);吏目员下,编给俸工等银六十七两五钱二分(吏目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儒学学正训导员下,原编并新添俸工等银一百三十七两六钱(学正原编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续奉文改食银四十两;又复设训导一员,俸银四十两);儒学廪生廪粮银一百二十四两;滁阳驿驿丞员下,编给俸工银四十三两五钱二分(驿丞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大柳驿驿丞员下,编给俸工银四十三两五钱二分(驿丞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大枪岭巡检员下,编给俸工银四十三两五钱二分(巡检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这些记载为研究清朝地方官员的俸禄制度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料。
(二)施政措施
地方政府施政的措施及其业绩,光绪《滁州志》记载较多。如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灾害治理等。兴修水利的,如卷三《营建制·水利》记载:“光绪九年,左文襄公任两江,委吴壮武公长庆以营勇用火药炸开山石,河道始通,今曰新开河。由张家保分支,至浦口入江,长二十里,径捷易泄,水不为患……圩田又以新复。今南乡九都八都等处有六圩,则甫于光绪二十年修复者也。”这些治理水患的举措以及圩田发展情况的相关记载,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对于当前水利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清史稿》等相关史书对此却缺乏详细记载。兴办教育也是地方政绩的一个反映,方志对此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卷三《营建制·学校》记载:“国初康熙二年,学正尹调羹重修(学宫)。康熙十六年,郡守赵清桢捐俸百两修葺,及训导汤调鼎讫工,复重修明伦堂。”“丰山书院,本义学,李世忠捐建。光绪十七年,署知州余适中改设在土街贡院之东,为屋四重,重九楹。由讲堂后西折,又一院,为诸生肄业之所。后为山长燕居之所,共四十间。”这些有关兴办教育的记载对研究滁州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滁州地方官还比较重视虫害、鼠害的治理。如卷一《舆地志·星野》“祥异”中记载:“康熙十一年夏,蝗蝻生,郡守余国 令民捕之。纳蝗一石,给米三升。蝗势顿杀。”又如卷四《职官制·名宦》关于吕辙的相关记载:“署滁州,硕鼠食苗,设机尽捕灭之。”此外,滁州地方官还比较重视灾年的赈灾工作。如志书卷四《职官制·名宦》关于赵清桢的相关记载:“值岁大旱,力恳上官,题请蠲赈,全活无算。”不论是虫害、鼠害治理,还是赈灾的相关记载,都是研究滁州抗灾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军事方面的史料价值
军事资料也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重视。光绪《滁州志》军事方面的资料主要体现在兵制、邮政、星野等门类中。
(一)兵制
滁州素有“金陵锁钥”“江淮保障”之名,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此地的军事制度建设。如卷五《兵卫志·兵制》:“(滁州)卫设掌印守备一员,岁支俸银二十七两三钱九分四厘,薪银七十二两,心红烛炭银十六两。裁中所,留余所。设领运轮班千总四员,每员岁支俸银十八两七钱六厘,薪银四十八两,随帮官一员,给廪工银五十四两。前帮运船四十九只,内减石灰船一只,运丁四百八十名,额兑苏州府吴县漕粮。后帮运船二十只,内减石灰船一只之四分,运丁一百九十六名,额兑苏州府昆山县漕粮……雍正末,四所全裁,招督运千总一员,近裁。”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滁州卫所机构的设置情况,并对卫所的兵额、薪俸也进行了说明。而记载清朝行政组织、政治、法规和典章制度的权威资料《清会典》中《兵部》只记载了守备、千总等官员的设置情况,至于兵额及薪俸则无相关记载。[3]又如卷五《兵卫志·兵制》关于绿营的记载:“原设驻防城守千总一员,后改把总。马兵十名,步战兵八名,守兵六十八名,隶两江督标浦口营参将管辖。同治八年,拨调五十名,内马六、守四十四,归入新兵中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奉部裁守兵十一名,存马兵四名,战八守九,皆步。”详细记载了从清初到光绪在位期间绿营兵额的变动情况。这对于研究滁州绿营发展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邮驿
邮驿是历代政府巩固其政权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其设立,带有浓厚的军事性质。卷五《兵卫志·邮政》记载了宋元明清时期铺递及驿站的情况,如关于明清时期重要驿站滁阳驿、大柳驿的记载:“明:滁阳驿,在南门外迎恩桥西。大柳树驿,在城西六十里。国朝:改滁阳驿于州治左,粤匪之乱毁,现在西门大街。滁阳驿,旧设驿丞,雍正八年裁。国初沿明制。额马一百匹,后减四十五匹。乾隆二十三年减十匹,五十四年又减二匹,现四十三匹。马夫原设七十名,现二十七名。差夫原四十名,现二十七名。原设抄牌、传差、羽书、兽医、禁卒,共十名;走递敕印里马二匹,马夫二名;夫厂、走递、扛夫一百八十三名。均裁。大柳驿,原设驿丞,后裁。原设马九十匹,现四十三匹。马夫六十三名,现二十名。差夫四十名,现二十名。另抄牌、传差、马牌、禁卒、兽医共十名,裁。”还记载了驿丞,如:“滁阳驿丞:何汝章,天启年。刘桓,雍正七年。大柳驿丞:成国栋,雍正七年。”这些史料有助于了解历史上滁州邮驿的布局及其发展状况,对于当今交通线路的选址及其管理也能提供有益的启示。由于驿站大都与马有关,因此,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利于加深对历史上滁州马政的研究。
(三)兵事战乱
由于滁州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故历史上战火频仍。卷一《舆地志·星野》中“祥异”部分历述了自南朝梁、唐、后周、两宋、元、明、清滁州地区发生的重大兵事,这些记载均值得关注。如:“崇祯八年,闯贼来犯滁州。九年正月,卢象升来援,大败贼于珠龙桥,河水为赤。”表现出战争的惨烈。方志还记载了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在滁州的用兵情况。前者如:“建炎三年,盗李成陷滁州,杀安抚向子伋,纵火大掠,民受歼。时金兀术分兵由滁、和渡江,与成合。成寻引兵至淮西。”“绍兴四年冬十月,金人犯滁州。十一月,滁州陷。镇抚使刘光世使统制王德击金人于桑根山,败之。十二月癸卯,金人去。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屯重兵滁河,造三闸储水,深数尺。秋九月,金将萧琦陷滁州,守臣陆廉弃城走。”后者如:“淳祐二年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扬、滁、和州。德祐元年三月,知州王应龙以城降元。”关于近代历史上太平军、捻军在滁州的活动,也有详细记载。如“咸丰三年四月,粤逆(按:志书蔑称太平军为“逆”“贼”“发逆”“匪”等)杨秀清遣贼将林凤祥、罗大纲,由金陵北渡,分犯六合、滁州,期会临淮,并力北窜。初七日,二贼率众数万渡江至浦口。初八日,凤翔向六合,大纲向滁州。初九日天明陷滁,午后悉西窜。”“(咸丰)九年六月,发逆陈玉成陷天长,约西捻合围滁州。世忠于附城东西筑二营,坚守不敢出战。贼也不敢薄世忠,因与西捻通。阅三月不克,解去。”这些都是研究近代历史上太平军、捻军的重要史料。
四、地理方面的史料价值
方志是记载一地情况的史志,杜泽逊认为方志是“地方史和地理的结合”[4],强调了地理资料在方志记载中的地位。光绪《滁州志》对本区的地理沿革、疆域、山川、湖泊、关隘以及名胜古迹,乃至地质气候等都详加记载。这些正史所语焉不详的资料,价值不容小觑。
(一)建制沿革
建制沿革等重要内容大多为方志所专有。光绪《滁州志》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从古到清代的建制沿革情况。如卷一《舆地志·沿革》中从隋至清的记载:隋初,并乐钜、高塘,改置新昌县,为滁州治,寻改清流县。大业初,州废,县属江都郡。唐初复置滁州,治清流县。天宝元年改永阳郡,乾元元年复旧。五代,吴、南唐地,后入北周。宋初为滁州,永阳郡军,直隶京师。后隶淮南路,又改淮南东路。元至元十五年,改滁州路总管府,二十年仍为州。明初废清流县,以滁属凤阳府。洪武二十二年,升直隶州。永乐后直隶南京,景泰后隶庐凤淮扬巡抚。国朝隶安徽布政使司。”这些滁州历代沿革的记载是研究滁州历史地理较为珍贵的资料,对于今天科学设置行政区划,仍具参考价值。更为可贵的是,志书在记载建制沿革的同时,还能进行相关考证工作。如根据《宋书·州郡志》和《通志·东晋》等文献的相关记载,认为顿邱故城即今州城。通过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为志书的一大特点。这些考证不仅很有参考价值,同时也彰显了方志编纂者对滁州建制沿革的重视。
(二)地情
关于地情方面的内容,光绪《滁州志》主要通过舆图、疆域、山川等目进行了记载。《舆图》中的《滁阳全境图》形象直观,有利于滁州地情内容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字不可替代的作用。卷一《舆地志·疆域》除了记载滁州东西、南北长度以及“四至八到”外,还记载了州治与其他重要城市的距离,如:“由州治达江宁一百二十里,达安庆六百五十里,达京师二千二百五里。”这些记载是研究历史时期交通情况的宝贵资料。卷一《舆地志·山川》除了记载郡城形势外,还重点记载了滁州境内的山、峰、岭、洞、涧、溪、泉等,对山水的位置、名由、特征、走(流)向等也作了较为细致的记述。在行文时,或配以史实,如:“北为关山,南唐置清流关,宋太祖御皇甫晖、姚凤于此。”或配以传说,如白米山:“相传昔有高僧坐禅,山谷中流出白米,每日给足。”或对景色直接描绘,如:“(石濑涧)石生水底,嵯峨突兀,亘数十丈。水流其间,萦纡往复。每盛夏溪涨,水石相激,澎湃有声,波澜眩转,观者忘倦。”此外,还收录了大量文人关于滁州山水的诗文。这对深入了解滁州山水状况,研究自然地理,开发旅游资源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反观正史《清史稿》有关滁州地理志方面的记载[5],则显得非常粗疏。因此,光绪《滁州志》地情方面的资料还可以补《清史稿》之疏,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三)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也称为天灾,指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这种异常现象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即构成灾难。卷一《舆地志·星野》记载了大量自唐代至清代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如水灾、旱灾、寒灾、风灾、虫灾、鼠灾、雷灾、震灾等发生的时间、持续状况、损失情况等。如关于清朝初期自然灾害的记载:“国朝,顺治八年,大旱,米升值钱七十。九年,大旱,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康熙四年六月初八日,大风破屋拔树。六月六日十三日,迅雷击死城中一人。七年五月十五日,虎近东城伤人。六月十七日,地震,民间房屋倾圮无数。十年夏,旱蝗。十一年夏,蝗蝻生。”挖掘滁州方志中自然灾害方面的资料,有利于分析自然灾害的成因,有利于总结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从而有助于提高当前的防灾、抗灾能力。
[1] 李史谦. 浅谈地方志中的经济综述[J]. 广西地方志,1995(1):24.
[2] 张文贵、荣竹林. 方志编纂学概论[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23.
[3] 中华书局影印. 清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91:410.
[4] 杜泽逊. 文献学概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1:334.
[5]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6:2015-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