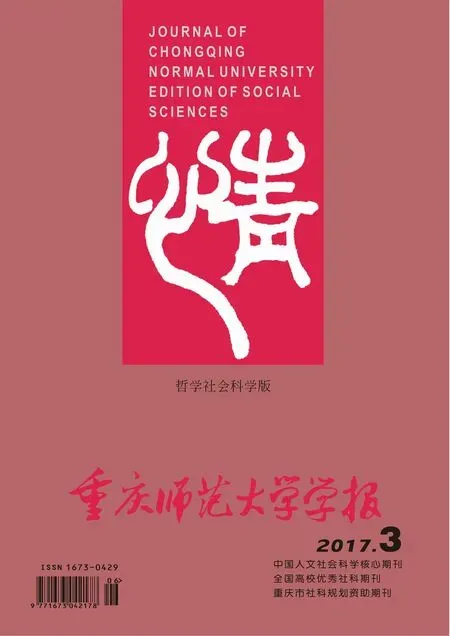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
2017-03-28唐芸芸
唐 芸 芸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
唐 芸 芸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吟咏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命题,而翁方纲的诗歌被指责缺乏性情,实则其在理论论述中,对“性情”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用“缺乏性情”来批评“格调”和“神韵”,要求与创作主体当下的情感切合,即“真”;而情感之出,强调对“事”本身的,即“正面”的摹写;并最终归为温柔敦厚的诗教,特别强调忠孝问题,强化了最传统的诗言志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用“事境”概念将“性情”与“学问”联系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学问入诗的问题。
翁方纲; 吟咏性情; 事境; 学问
翁方纲对于传统诗学命题“吟咏性情”的回归,在理论的梳理上,破除了明七子及清初诗人一直绕不开的性情与格调的问题,直击明七子的理论弱点。他将“性情”和“理”、“雅正”等相连。具体而言,就是对“真”的强调。而且翁方纲还扩大了“性情”的内涵,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在心为志”,“己”之心而已,而是用“事境”一词,包含了时间、地点、事件、甚至与之有关的学识等,这样的扩大,丰富了“性情”唯一性的内涵,体现了一种对“格调”说更彻底的反驳。在对明七子诗学的反驳中,人们必然会重新审视文学史,尤其是宋诗的审美特征,以及文学史传衍的规律。人们已经将性情之真作为诗歌的最高要求,只要是表现“真”性情的宋诗,那么其价值就有被重估的可能。翁方纲也是沿着这条思路走的。
一、“性情”与“格调”
明代七子充分暴露其诗学主张的弊端之后,公安派、竟陵派都各出奇招,但是仍然没有彻底纠正诗学方向,甚至走向另一歧途。明末云间派、西泠十子等,对明七子诗学进行修正,但仍然坚持格调优先的大原则,只在细节处稍作变动。于是,清代对明代诗学的反思,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复古诗学,及其影响下的唐宋诗之争。对明七子的批判,成为清代诗学家们在回顾文学史时绕不开的话题。清人注意到了明代的门户之见,他们在表述诗学观念时,重视的是对诗歌史事实的回顾,及对当下诗坛的影响,更不会因为门户畛域而变得牵强甚至执拗。清人对明七子诗学的批评的集中点,就在于其缺少性情。翁方纲也是如此。除了适应清代诗学的主流,号召回归“吟咏性情”外,他还为这一传统命题在当下的使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清初人们对明七子的批驳集中于其性情的缺失。而古人之格调毕竟无法绕过,后人仍然会在诗歌典范中求得写作真谛。所以,渐渐格调与性情的综合,虽然承认了性情的重要性,但始终无法摆脱格调的笼罩,徘徊在二者之间。这样的讨论,终究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击中格调派的要害。
而事实上,明七子并不反对性情,甚至也强调性情。因为“吟咏情性”正是亘古不变的诗学传统。明七子如李梦阳、王世贞等,论诗也谈到情感。但是为何他们的诗歌后人认为是缺少性情的呢?
原因就在于,在七子的诗学中,存在着性情与格调的矛盾。
格调派对于文学史的把握,总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即“格”和“调”。这样的好处是,在学古的时候操作性比较强。但后果当然是,诗歌创作都出之以古人面目。在七子的诗学中,其用“我情”是被尺寸古法限制的。似乎是文学史的典范给适时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属于个人的“性情”在其中无法自由回转。性情与格调在七子诗学中成为一对矛盾。虽然七子不否认性情,但是显然是性情屈从与格调,或者说认为“自己的性情可以有古人面目”[1]123,惟其如此,才能暂时圆通传统命题“吟咏性情”与模拟格调的矛盾。但这显然是不对的。也就是说,要重新拾起“吟咏性情”的传统命题,就必须解决性情与格调的矛盾。
翁方纲作文,集中批驳了七子诗学。他认为:七子对“格调”的理解和遵从,本身就是错误的。格调是诗歌都有的,每首诗、每个诗人都呈现出其格调。而七子的错误在于,以一时之格调作为典范。
诗之坏于格调也。自明李何辈误之也。李何之徒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也,泥格调之病也。夫诗岂有不具格调者哉!……是则格调云者,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时一代所能专也。古之为诗者,皆具格调,皆不讲格调。[2]421
翁方纲认为明七子以一种格调作为规范,抹杀了文学史的事实。因为“唐人之诗未有执汉魏六朝之诗以目为格调者,宋之诗未有执唐诗为格调,即至金元诗亦未有执唐宋格调者。独至明李何辈,乃泥执文选体,以为汉魏六朝之格调焉,泥执盛唐诸家,以为唐格调焉”[2]421。这是明七子受严羽“从第一义”入手学古的影响,还有严羽对盛唐气象甚至是唐代诗歌分期的影响。但事实上,严羽所执论,仍是在妙悟上,仍然在于“兴趣”,并没有指明盛唐的“格”与“调”具体是什么,正因为如此,也显得较玄妙。明七子无疑深化了这种理论,变成具体的、可操作的学古方法。
翁方纲着重讨论了选体的问题,对李攀龙的“唐无古诗”发难。他认为格调派以选体为古诗的格调,但是事实上《文选》根本就不具备统一的格调:“即以选体言之,《文选》自汉魏迄齐梁,非一体也,而概目之曰选体,可乎?如谓《文选》诸家之诗,共合而目为选体,则只一体,非众体矣。中间何以复有拟古之作乎?”杜甫的“熟精文选理”,正是这个道理:所学的不是选体中某一格,某一调,而是其中蕴含的诗歌创作的真理。“观选体中有拟古之篇,则知古之上,复有古焉,何可泥执而混为一乎?泥而一之则是蔑古而已。此则正受古人之憾,正受古人之笑而已矣。”[2]421
作诗,对于“体”的要求,以最高的典范作为楷模,这是自严羽“从第一义入手”以来更强调更明晰的学古观点。每一体格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及最高典范。如古体诗则是汉魏,近体诗则是盛唐。学习的对象必须是这个最高典范,这就是所谓的“入门须正”。对于这个基本思路,翁方纲其实也是赞同的。他并不反对每一体格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并经历制高点,而后人要做此类诗歌,便是要向制高点学习的。如他认为七律就是要学杜甫、学王维。他反对王渔洋所谓的“先河后海”,从较为简单易学的中唐入手,进而学习杜甫,翁方纲认为必须直接向最高典范的杜甫学习,否则就不得其正。[3]所以,翁方纲说每个人都有格调,只是高下不同。古人的格调,代表的是古人之性情。今人之性情如何能出之以古人之格调?
这就打破了“为格调而放弃性情”这个七子派诗学的理论基础。
翁方纲进一步论述,拟古诗或古题乐府,这种“格”与“调”如此明显的诗歌类型,尚有后作者的性情体现。拟古诗尚有自己的痕迹。翁方纲认为,即使是拟古诗,也该有诗人自己的面目:“东坡之和陶,非复柴桑之五言,非复左思之五言也。”[2]422
“今编刻一集,其卷端必冠以拟古、感遇,而又徒貌其句势,其中无所自主,其外无以自见者,谁复从而诵之?”“夫其题内有拟古、仿古者,尚且宜自为格制,自为机杼也,而况其题本出自为其境、其事,属我自写者,非古人之面,而假古人之面,非古人之貌,而袭古人之貌,此其为顽钝不灵泥滞弗化也。可鄙可耻莫甚于斯矣!”[2]422翁方纲还举了个例子:“吾自日接亲戚宾友,有必应言之言,有必应答述之语,而顾妄作戏场优伶之声音色笑,以为中节。”[2] 422那么,即使是村野山夫,也会嘲笑的。
所以我们必须“凡所求古者,师其意也,师其意则其迹不必求肖之也”,“孔子于三百篇,皆弦而歌之,以合于韶武之音,岂三百篇,篇篇皆具韶武节奏乎?”[2]422
翁方纲与明七子不同之处,就是从什么角度学古的问题。明七子是将作诗的心思全部赋予了古人,以学得像古人为荣,点滴求似,形如临帖。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规格在这些格调里的,让这些格调显得饱满质厚的,正是这些古人熔铸于格调中的热情。翁方纲一直强调“一人自有一人神理”,今人绝对写不出古人之情。明七子囿于模拟格调所写出的诗只能是伪体。而今人作诗,也有自己的环境和心境,就必须道出自己的性情。所以,翁方纲认为,向古人学习的,不在于格调,而在于古人如何运作的“所以然”,即肌理。这样就避开了性情与格调矛盾的问题,舍弃格调的规定,而代之以围绕一定的原则在具体诗篇中又可变化万端的“肌理”,真正做到“变而不失其正”。
故而翁方纲反对执格以定,必须讲究性情:“夫人各有所处之时之地,所接之人之事,而性情襟抱寓焉,而卷轴菁芙寓焉。……则夫言之长短,声之高下,气之缓急舒敛,色泽之疏密浓淡,焉有执格以定之者。”[4]略例
他进一步指出王士禛劝人勿学白居易诗的本质:
按诗无貌古之理。古必天然神到,自然入古,亦犹平淡之不可以强为也。岂可求诗必求其古欤?若学者相率而效为貌古,则蹈袭之弊,竞趋于伪体,是乃诗之大蠹,所以李空同何大复辈之伪体,渔洋惟恐人讥议之,此则渔洋先生之好买假古董,实不能为先生讳矣。吴梅村诗浓艳是其本色,即浓艳之体亦自有极至处,初何伤欤?梅村作古体,一有心仿杜,则伧气毕露矣。人之造诣各有专长,奚其貌古之云耶?渔洋劝人勿学白诗,亦犹是此等貌古之见耳。[3]
翁方纲不是讨论性情优先或者格调优先的原则,而是解决了格调与性情的矛盾。认为诗歌都有格调,不能以一时一人为代表,所以,格调并不具备最基本的诗学原则的价值。而人人都有性情,更不能以古人之性情取代。这样,既化解了文学史的压力,不会如性灵派走入无规则的创作道路,又解决了性情与格调两个范畴的矛盾。其实这两个范畴并不矛盾: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情,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格调。这二者是一致的。而当今之人作诗,也必是有自己的性情,也有自己的格调。
二、对“性情”内涵的规范和扩大
翁方纲对“性情”的具体要求,特别强调“真”。他对王渔洋的批评便集中于这一个字:
论诗曰典曰远曰谐曰则,此四言者典则之内,有一真字而先生未拈出也。……
今人黄景进将后人的诋毁归为四点,第一便是认为王士禛讲风度而少性情[5] 200-202。“真”,即己之谓也。就是作诗要切合诗人当时当地的思想、情感。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注意到,翁方纲对“真”的要求,或者说对切“己”的要求,除了抒情主体自身之外,还有时间、地点、身份、事件等。这就像一个处于宇宙时空中的坐标,每个人所处的当下,这一点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这一点的“性情”是唯一的。
这与他的“事境”理论是相联系的:“诗必切人,切时,切地,然后性情出焉,事境合焉。渔洋之诗所以未能餍惬于人心者,实在于此。”[6]8725诗作对“人”“时”“地”的切合,便是合于“事境”的性情。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翁方纲诗歌多用铺陈的方法,体现出细密、质实的审美特征。他对“事”的强调和完整表现,实则都与其“事境”说有关。
翁方纲“事境”的概念,与“切实”“铺陈终始”是一致的。他反对格调的最有力的话语便是“一人有一人神理”,便不得以古人格调制约,这事实上是时人公认;而批评王渔洋神韵说指导下的诗歌实践,便是抓住“事境”的缺失,赵执信对王渔洋的批评,即“诗中无人”。渔洋在“神韵说”的指导下写作的诗歌,追求的是冲淡平和的韵致。这本无妨,但是由于“王爱好”,用力于搜罗体现韵致的好意象好句子,却忽视了“为何而作”,那么韵致就会体现出一种普遍状态,这种普遍的情感或许会很快赢得一种共鸣,事实却是“无根”的状态,“渔洋通集之诗,皆若摹范唐人题境为之者耳”[6]8726,所以翁方纲同意赵执信对于渔洋诗“诗中无人”的评价,即“不切事境”。
由于明七子及其后裔(翁方纲没有直接批评沈德潜)所导致的创作的趋同性,王渔洋创作的趋同性,翁方纲特别强调诗境的唯一性。所谓貌袭情伪,都是翁方纲所批判的。我们本来可以理解为,王渔洋和明七子,都是貌袭者,情有可能是真的。但是翁方纲认为,“貌袭”和“情伪”是结合在一起的,要表达真情,就必须脱离古人面貌。七子和渔洋诗,情的抒发没有着眼点,所以是“虚”。所以才提倡学习“肌理”——这种不依附于面貌,却深深探入文学史的因素。
看来,“事境”是一个常见的词汇,而且是人们当时开始重视的词语,最是攻击神韵说的利刃。而翁方纲对这个概念作了清晰的内涵说明:“诗必切人,切时,切地,然后性情出焉,事境合焉。渔洋之诗所以未能餍惬于人心者,实在于此。”[6]8725“诗境”当是由人、时、地等要素结合起来体现的一个综合效果,而不是随意伫兴而发的普遍性情感。基于“建安风骨”和“兴寄”说的盛唐气象,也是关注现实,但是在诗歌表达上,是关注现实对情感的触发,而多写情感,在唐中期“情景交融”之后,着力于营造一种韵致。对韵致过分追求,便会导致“虚”的感觉。所以,中唐以后,人们便感觉到诗境的窘迫,而开始寻找更多可表现的对象。入宋后,这方面便成为宋诗人主要的探索之一。
当然,如学界已经认识到的,这是由他对宋诗的美学特征的认知而来:“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7]卷4,122-123宋诗特点主要是事境的扩大,提供了更多抒情议论的可能,且宋诗刻抉精细,即是一种对“事”用心的体现,而不是随意入诗。翁方纲最看重宋诗的就是这个特点。
再加上“盛世情怀”抒发的需要,翁方纲认为只有学问才能更好体现,而他自己又有着对碑版、金石等学问的喜爱,所以,“事境”在他的诗歌实践中,往往被置换成了学问。
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测试与评估规定如下,“考试是一种重要评估手段,但不是唯一评估手段…各校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10]。因此,笔者的视听说采用发展性考评方式。该方式下,教师主要从课堂参与度、学习主动性及语言任务完成度等进行考评,考评情况实时记录在平时成绩册中。
翁方纲极力反对为求完成诗歌而进行一种普遍化的抒情,认为这种捷径写出来的不是真诗。无论寄怀为题,还是咏物、游览,其诗都能还原出一个具体的语境,都能体现作者在当下对人与“事”关系的思考。
翁方纲还把事境与他一以贯之的“理”结合起,认为“事境益实,理味益至”[7]卷8,241-242。从《诗》中的经典开始,至于王维、杜甫等,都是“吟咏性情”的典范,而他们都是讲究事境的。故而,矫正明七子,当然须以“性情”的回归为主旨。重要的是,性情的回归,必须着眼于“实”,着眼于“雅正”,着眼于“温柔敦厚”而出之以理味。
我们可以看到:翁方纲将性情的内涵扩大了:
第一,要求与创作主体,也就是抒情主体(翁方纲主要讨论的是二者合一的情况,没有涉及代言体)当下的情感切合,即真;
第二,而情感之出,强调对“事”本身的,即“正面”的摹写——即由文本呈现,而不是留白由读者想象;
第三,最终归为温柔敦厚的诗教,特别强调忠孝问题,强化了最传统的诗言志观念。
翁方纲批判王渔洋无人即无性情,将“真”与性情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很质实的情感。翁方纲是将视野集中于文本本身,而王渔洋是追求着韵外效果的。并不能说翁方纲反对韵外之致,至少在创作主体与表达情感的真实性方面,他是要求在文本中直接呈现的。而渔洋所考量的范围,则远远超过了文本本身。这就是翁方纲认为渔洋后学会越来越空疏的原因。所以,翁方纲事实上是改变了对性情的文本考量范围,直接限制在了语言符号本身。
翁方纲将性情与“事境”结合,又将“事境”与“理”结合,那么,性情与“理”之间必是有关系的。
其实翁方纲的观念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一衷诸理而已”[2]卷4,390-391,与人有关的一切活动和实践,都必须衷于“理”。万物之理是具有同一性的,“理”是作诗的最高标准,是诗思的终极体现。既然万物“一衷诸理”,“理”便涵盖一切,这其中当然也应该包含性情。这是从讨论诗言志的角度出发的。事实上,翁方纲虽然将性情的内涵扩大了,但最终的归依,仍然是传统的诗言志命题。
我们知道,对于传统命题的“诗言志”,不是如性灵派一样“独抒性灵”,无所忌惮而流入俚俗和轻率。人们对“诗言志”的“志”是有规定的:必须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必须与“止乎礼义”结合,否则就会落入到像南朝宫体诗之类的毫无约制的滥情中去。清前期几代皇帝都提倡“雅正”,提倡温柔敦厚的中正原则,主导诗坛,就是为了要在“诗言志”这样的诗学回潮中,避免出现艳俗或是过于激切的风气。
翁方纲在对“止乎礼义”的讨论中,直接提到“忠孝”二字,认为“诗者,忠孝而已矣,温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8]附录《渔洋诗随论》,304。作为社会稳固最基本的“作忠教孝”,在翁方纲看来,也是性情中应有之事。这是最能体现“雅正”主张的,也是最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言志传统的主张。
也就是说,为何“事境益实,理味益至”[7]卷8,241-242呢?这里的“理”,当然是“义理”之“理”。事境越切于事实,越切近创作主体当时的感受,便越能体现出创作主体的忠孝观念,即更符合温柔敦厚诗教观。这才是性情,而不仅仅是主张抒写性情。但是由于翁方纲未落实到诗歌文本中,而出之以冲淡玄远的韵味,“理味”变得不可把握。
翁方纲将性情与“事境”的观念结合,并直接导出学问入诗的问题,将性情与学问二者合一。这为“以学入诗”的合法化,寻找到了“诗言志”作为理论支撑。但整个思路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性情究竟是与“人”关系更密切,还是与“事”的关系更密切?
翁方纲孜孜不倦地将朱彝尊、王渔洋的此类诗歌作为自己诗学攻击的对象,其中体现的是他对“事”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人”的重视,忽视了“人”在某一时间、地点、事件中触物生情的能力,也就是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何况是敏感的诗人。从“事境”这个概念的使用其实也可以看出端倪。于是,与“事境”相合的“性情”,体现出来的,却是与“人”的疏远。后文在分析具体诗歌时我们有更清楚的辨析。翁方纲对于王渔洋等“诗中无人”而归纳的少“真”即缺少性情的判断,其中的“人”其实可以用“事”来替代。所谓的“一人有一人神理”这个批评明七子的如此有力的武器,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事有一事之神理”。但是,翁方纲在诗歌评点的实践中,对人、时、地、事等变量的斟酌中,体现出来对“事”的过度重视。事实上同一事可以由不同的人经历,便有不同的“境”,我们无法规定“事”之“境”具有统一性。那么,本来追求的“人”之不同的性情,却变成了“事”的相似之“境”,否则便背负“诗中无人”的批评。那么,对某一“事”之境的规定,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格调”,翁方纲终究还是没有脱离“执格以定”的思维。
三、“合性情、卷轴而之一”
在翁方纲的诗学核心概念中,“肌理”是为结构安排上的用心,而“正面”则是着重于内容,当然包括创作主体对内容的把握角度。前一节已经讨论学问对于清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写诗材料,特别是对翁方纲这样一群对金石有浓厚兴趣之人,无论是从个性志趣上,还是从诗歌出路的角度,学问特别是精确到与金石、碑版等有关的学问,都自然地被拉到诗里来。那么,在翁方纲诗学中,究竟如何处理学问与诗的关系呢?
学问与诗,在严羽开始看来,就是“别才”的问题。正题当然应该是传统的“吟咏情性”。这似乎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所以要求得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合法地位,就必须处理好其与性情的关系。这也是翁方纲诗学中重要的一环。
自从严羽批评宋诗以来,为宋诗找了三大特点,以至于大家后来都沿用。我们说过,翁方纲对学问的关注更具体化。这些与经史和考订有关的学问,前人并没有专门的“体”来规范。我们在严羽《沧浪诗话》里,才看到影响较大的论述,即对宋诗的批评。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中以“才学”最为引人关注,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使事”。诗歌篇幅有限,当学问占领了大量篇幅时,诗歌无论是情感表达还是叙事需求都会显得琐碎,即所谓的“以文字为诗”。而既然是显示学问,那么就有文人藏不住的责任感和将这种责任感一吐为快的想法,“以议论为诗”便很自然。“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学问诗的“格”,而关于“调”,严羽认为是欠缺的。
我们来具体讨论严羽的言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9]26严羽的诗学以盛唐为上,这方面开启了后来的明七子诗学。在严羽看来,因为宋诗不是古人之诗,所以对其进行批评,这个观点,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人们对宋诗价值的评价。即使是清初提倡宋诗的人,也是努力找出宋诗与唐诗相似之处。而翁方纲则不同,他的诗学本来就反对“貌古”,认为这是“伪体”。更重要的是,在翁方纲看来,“才”与“学”是合一的:“有才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二者不能兼也。……必合诸学之所得,则学即才矣。”[10]卷1诗歌创作中体现的才力,需要深厚的学识作为保障。
我们注意到,严羽所言为“才学”,即“诗有别才”的问题。后来由于《沧浪诗话》版本的演变,引发了“诗材”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衍伸为不同的诗学观念。大部分清人本来是看重学问的,但一部分讲究“诗才”,即强调创作主体的根坻,如王渔洋。这是对创作主体本身修养的要求,但并不鼓励在诗中直接呈现,甚至是与学识有意间离;而另一部分则强调“诗材”,学问则是成诗不可或缺的材料。翁方纲通过“学即才”,已经将二者合一了。又论:“齐梁以降,才人诗也,初唐诸公,诗人诗也,杜则学人诗也。然诗至于杜,又未尝不包括诗人、才人矣。迨中晚诸家而斯事又离而为三。至于晚唐五代求其适于大道者盖无有也。”[11]杜甫是所谓“大道”者,是翁方纲诗学里一直处于经典化的人物。翁方纲是主张审美理想和师法策略合一的。无论是肌理、正面铺写,还是学问的体现,杜甫都是绝对的标准。
那么,翁方纲就需要为“以学为诗”正名,要批驳严羽対宋诗的三个影响最大的评语。在学理上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严羽说的“不问兴致”。也就是说,“以学入诗”,是否可能而且如何寄托创作主体强烈的感情。这就引出了“性情”的问题。
翁方纲认为,以学入诗,并不是“不问兴致”,并不是缺乏性情,相反的,性情可以与学问相合:
初揭三昧旨,然灯与授记。然否秋窗间,试拈第一义。深之造平淡,浅矣言风致。平淡而非真,尚涉虚夸事。学古岂貌古,一本于言志。性情与学问,处处真境地。法法何尝法,佛偈那空寄。且莫矜忘筌,妙不关文字。[12]卷67,307
又“此时若有真实学古之人,必将引而伸之,由性情而合之学问。”[2]426-427又有“夫诗,合性情、卷轴而之一者也。”[10]卷1性情与学问,在翁方纲的诗学中,是相关联的。二者合一的几点可能性有:
第一,都是以“理”为旨归。前面说到翁方纲将“性情”与“理味”结合起来,而关于具体学问的理论,翁方纲也是主张“考订以义理为主”的。翁方纲主张的“一衷诸理”的问题,在“性情”与“学问”上很好地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第二,都是“实”的内容,与“真”有关。翁方纲强调性情必须“真”,与创作主体相切。在学问方面,翁方纲将学问视为“实”的一个因素。既然是以金石、碑版为描写对象,那么,与金石碑版有关的知识学问,就是“实”的重要内涵。作者需要将这些“实”的内容以诗歌的形式告知读者。只有如此,才能表现出作者的性情。所谓“处处真境地”。其实,性情与学问一样,也是“实”的一方面。表达性情,就是“切实”的一种。他的这种刻意地将二者合一,正体现了一种整合的努力。
第三,学问与性情必须呈现在文本里,这是对“正面”的要求。翁方纲对于渔洋诗学带来的诗风,为追求含蓄冲淡,却带来空虚无物的创作,是极力反驳的。他的诗学归于质实,不但创作出发点是要求切己切时切地,而且要求这种切实之后的成果,必须直接呈现在文本中,而不是一种侧面烘托而出。对性情是这样,对学问也是这样。
第四,都归为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在关于性情与学问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前文已经提过的翁方纲反对“执格以定”。“以学入诗”也是不能作为某一“格”诗歌的特点,即并不是作为宋诗专有的区别于唐诗的特点。这就从立论基础上反驳了严羽将“以才学为诗”作为宋诗无古人之貌的证据,当然同时也反驳了以“格”论诗的明前后七子,以及清代诸人。
翁方纲把学问,在理论上是希望做到一个普遍化的要求。卷轴与性情一样,是无论所处为何地,所接为何人,所感为何事,其中都会寓有情感,寓有学问。这些都不是某一类的诗歌才专注的问题,而是本来就普遍存在的。之所以之前人们有去学问化的现象,是因为没有“正面”入手进行创作,选择侧面烘托而故意忽视了学问卷轴,甚至是真性情。那么,进一步的,“以学入诗”,这并不是一种像严羽所说的由宋诗挑起的异质传统,而是与神韵、格调、肌理一样,都是普遍存在于诗歌中的,无论时代,无论个体,无论内容。只是因创作主体的诗学观念或能力,在诗歌文本中呈现出或高或低,或显或隐的分别而已。这样,翁方纲关于学问的理论,就与其总体的诗学思路合上拍。其超越了风格的边界,超越了唐宋的藩篱, 求得一种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思考,从根基上稳固了学问入诗的合法性,学问便成为诗歌创作的应有之义。这样的一种思路,对于反对以学入诗的观点,或者虽强调诗歌根坻,诗歌创作却流于空疏或貌袭的风气是一个有力的回击。于是,“学问”就和“性情”一样,成为“正面铺写”的核心内容。当然在将学问作为普遍化因素的思考和陈述上,翁方纲做得还不是很完善,以至于往往被忽视。
那么,“性情”与“学问”是通过什么结合起来的呢?这就是翁方纲强化的“事境”理论。
“事境”出于切己切实切事,故而“事境”的要素,就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在翁方纲的诗歌里,每一首诗的“事”都是完整的。包括诗人对该“事”的明确态度。这当然是一种实证的风气。“事境”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使得翁方纲的诗歌每一首都可以区别于其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翁方纲的诗歌,几乎都是缘事而发。为何而游览,为何而吟咏某物,为何而寄怀,每一首诗作的产生,都是有触发点的。而翁方纲会很仔细地记载这些缘由,即“事境”之所出。而在学问取得普遍化地位的诗学思想里,“学问”就是“正面铺写”的核心内容。如果是关于金石的学问,当然就是与金石相关的具体知识。而从这些内容的正面铺写出发,得出对其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的情感,就自然流露在文本中,这就是“切己切时切地”的真性情。这些“事境”之所出,即用铺排的方式完成。从而其诗歌整体呈现出一种细密、质实的美学特征。
翁方纲将学问与性情结合,这同时也是对“性情”内涵的再一次扩大。重印翁方纲《复初斋诗集》的缪荃孙,这样来理解翁方纲的“性情”,实为知音之解:“阁学性耽吟咏,随地有诗,随时有诗,所见法书、名画、吉金、乐石亦皆有诗,以考据并议论,遂有‘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以讥之者。不知《石鼓》、《韩碑》首开此例,宋、元名集尤指不胜屈,正可以见学力之富、吐属之雅,不必随园之纤佻、船山之轻肆,而后谓之性情也。”[13]512缪荃孙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性情”一词的定义与前人有所区别。一般来说,以学入诗,在一定使用数量范围内,方法得当,并不阻碍诗歌中性情的抒发。如果诗歌一味地体现学问——虽然或许作者有如斯写作的理由,也会给人一种印象:字面上的对于学问的沉迷,已经完全掩盖了诗人对描写对象的真实的情感定位,读者无法从这些科学的、客观的,甚至逻辑性很强的文字中,进入作者的内心,更不用说产生共鸣。于是,这样的诗便被划为缺少性情一类。而缪荃孙为翁方纲的学问所倾倒,也为解释其诗歌的写作方式找到一个出路。那就是翁方纲的诗歌写作方式,从韩愈的《石鼓文》、李商隐的《韩碑》就已经有了。正是由于学问富赡,这样的诗作体现出了深厚感,和与六经等神圣的古老文明相接的雅丽。他显然是针对袁枚一派的直抒性灵而言的。袁枚等人对于性灵的一味追求,对于性灵之外因素的强烈排斥性,是翁方纲等人所深恶痛绝的。缪荃孙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并不必如袁枚等人的高举性灵,写出的才是性情之诗。况且,他们的诗歌并有纤佻、轻肆之弊端,只会使得更多不学无术之人混入神圣的诗歌写作行列,扰乱圣人开启、历代文人传袭的诗歌事业,虽然从来不乏娱乐性的文字存世。所谓“解放”,在反对者看来,就是“流放”。所以,缪荃孙给“性情”作了一个新的定义,只要见出“学力之富、吐属之雅”的,也是性情,甚至还是性情之正道。至少在当下文坛应是如此。
在翁方纲的概念中,将“学识”具体化,以及学理探索上表现出的对学问和性情融合的倾向,比清初钱谦益等人参之以学识的见解,要更进一步,也更大胆。“性情”已经与传统的定位发生了变化。
翁方纲这种整合性情与学问的努力,在他的后学中得到了延续。如程恩泽《金石题咏汇编序》:“金石文字自欧、赵著录以后,书不下百种,而裒其题咏为一集,则自甘君宝庵始。或曰:诗以道性情。至咏物则性情绌,咏物至金石则性情尤绌,虽不作可也。解之曰:诗骚之原,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章钜制则瞢然无所措,无它,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况吉金多三代物,其文字与经表里,可补经阙。乐石之最古者,与金同。其文字与史表里,可补史阙。……况训诂、通转,幽奥诘屈融会之者,恍神游于皇古之世,亲见其礼乐制度,则性情自庄雅贞淫正变,或出于史臣曲笔,赖石之单文只词,证据确然。而人与事之真伪判,则性情自激昂,是性情又自学问中出也。”[14]卷7翁方纲、凌廷勘、程恩泽、何绍基及郑珍等人师承关系我们都很清楚。程氏这段文字,即申明诗是性情所出,而性情又自学问中出。这里的性情,已经不是纯粹的情感反映了。只有学问深厚,性情才醇厚,他将这个含义的合法性,上溯到诗骚时代,确立了学问在性情中的地位。
翁方纲对“性情”内涵的扩大,让这个传统概念不再局限于私人化的情感,而是上升到“雅正”的,与忠孝观念结合起来,这是时代的要求。翁方纲在人们都强调的“真”性情之外,还强调了真性情必须出之以“正面”的表达,这与其诗学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在这样的思路下,把性情与学问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较之清初人们只是将二者并提,要深入有效得多。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为清代中期诗风转向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1]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G]//.续修四库全书(1455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10)[O].手稿本,上海:上海图书馆藏.
[4] 翁方纲.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G]//.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6] 翁方纲.苏斋笔记[G]//.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复初斋文集.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7] 翁方纲.石洲诗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8] 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G]//.清诗话.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9]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0] 翁方纲.复初斋集外文[O].1917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11] 翁方纲.七言律诗钞[O].乾隆四十七年复初斋刊本.
[12]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G]//.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 沈津.翁方纲年谱[M].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14]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初编[O].道光丙午(1846)何绍基题刊本.
[责任编辑:朱丕智]
The Return and Amend of “Intoning Temperament” by Weng Fanggang
Tang Yunyun
( College of Literatur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331,China)
“Intoning temperament” is a traditional propositi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ics. Weng Fanggang, whose poems were accused short of characteristics, had considered deeper questions about it. He criticized the verve and pattern theory for their lack of temperament. He required real emotion, especially loyal and filial ones, in positive expression. He focused on the blandness, and poem expressing ideal, which were the traditional poem teaching. It was worth noting that he connected temperament with scholarship by circumstance. Then we knew how to show the scholarship in our own poems.
Weng Fanggang; intoning temperament; circumstance; scholarship
2017-02-25
唐芸芸(1982—),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诗学。
2014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翁方纲诗学与清代唐宋之争研究》(批准号:2014PY36)。
I206.2
A
1673—0429(2017)03—00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