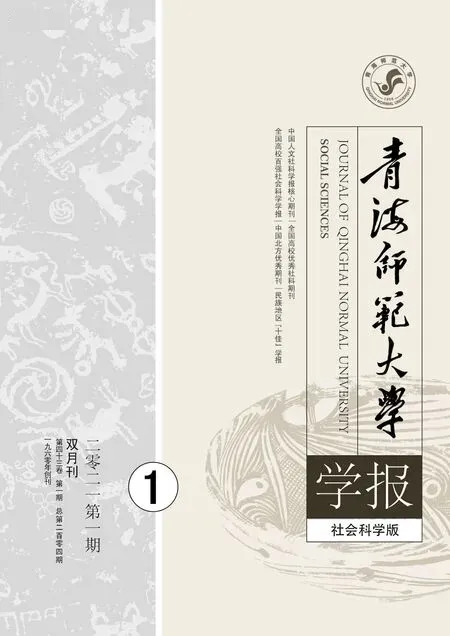王士禛“渔洋说部”研究综述
2021-01-03薛润梅
薛润梅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王士禛(1634—1711),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是康熙时期的文坛领袖。王士禛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笔记杂录,这些笔记杂著被王士禛自己及他人称为“说部”。王士禛说部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体例独特,传播广泛,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又其体例与王世贞“弇州说部”很相似,所以清代学者称其为“渔洋说部”。
“渔洋说部”是王士禛文学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说部文体发展史上关键的一环,有较高的社会意义与学术研究价值。“渔洋说部”从其问世以来,就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是相比其极高的说部地位与学术成就来说,学界对“渔洋说部”的重视还不够,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局限。本论文将对清初以来的“渔洋说部”研究做细致梳理,分析“渔洋说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推动“渔洋说部”研究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
从清初至今,人们对其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由于民国时期学界对“渔洋说部”的研究较少,且成果不多。所以本文主要对清代和1949年以来这两段时期的“渔洋说部”研究成果做详细梳理。
一、清代的“渔洋说部”研究
清代的“渔洋说部”研究中,以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和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对“渔洋说部”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在这两种古籍中,比较而言,《四库全书总目》对“渔洋说部”的评价影响最大。《四库全书总目》将“渔洋说部”分散于子部、史部和集部,其中收录了王士禛《池北偶谈》《居易录》《陇蜀余闻》《皇华纪闻》《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古欢录》《蜀道驿程记》《南来志》《北归志》《广州游览小志》《秦蜀驿程后记》《长白山录》及补遗、《浯溪考》《琉球入太学始末》《国朝谥法考》《渔洋诗话》《五代诗话》共二十种说部作品。
《四库全书总目》对“渔洋说部”的评价主要集中于其内容、体例及王士禛的创作态度三个方面。
在内容上,《四库全书总目》对“渔洋说部”中的谈艺、考证部分评价很高,如《四库全书总目》评《居易录》时说:“中多论诗之语,标举名俊,自其所长。其记所见诸古书,考据源流,论断得失,亦最为详悉。其他辨证之处,可取者尤多。”[1]《四库全书总目》对“渔洋说部”中的谈故、谈献部分也予以肯定,如其评《池北偶谈》时说:“凡谈故四卷,皆述朝廷殊典及衣冠盛事,其中如戊巳校尉、裙帯官之类,亦间及古制。谈献六卷,皆记明中叶以后及国朝名臣、硕徳、畸人、列女,其中如论王缙、张商英、张防之类,间有摘斥其恶者,盖附录也”。[2]《四库全书总目》对“渔洋说部”中的谈异虚构部分不太认同。如其评《四库全书总目》评《池北偶谈》“谈异”部分时说:“谈异七卷,皆记神怪,则文人好奇之习,谓之戏录可矣。”[3]《四库全书总目》还谈及“渔洋说部”记录内容对前人说部的借鉴。如其评《古欢录》时说:“是编皆述上古至明林泉乐志之人,盖皇甫谧《高士传》之意”,[4]认为此书在内容的选取上仿自皇甫谧《高士传》。
《四库全书总目》也指出王士禛在“渔洋说部”中有自誉自捧之弊,“渔洋说部”中有些内容记录错误等问题。如其评《居易录》时称王士禛于此书中:“喜自录其平反之狱辞,伉直之廷议,以表所长。夫邺侯家传乃自子孙,魏公遗事亦由僚属,自为之而自书之,自书之而自誉之,节言言实录,抑亦浅矣。是则所见之狭也。”[5]认为《居易录》中王士禛自誉自捧部分,实在是“所见之狭”。评《香祖笔记》时说其:“论尹吉甫一条,最为纰缪。又如姚旅《露书》以章八元诗为卢照邻,某诗话以柳恽诗为赵孟頫。”[6]
在体例上,《四库全书总目》对“渔洋说部”总体上是肯定的。如《四库全书总目》评《香祖笔记》时说:“是书体例与《居易录》同,亦多可采。”[7]但也有批评,如《四库全书总目》评《居易录》时说:“惟三卷以后,忽记时事。九卷以后,兼及差遣迁除,全以《日历起居注》体编年纪月,参错于杂说之中。……究为有乖义例。”[8]指出其内容混乱、形式“有乖义例”的弊病。另《四库全书总目》也谈及“渔洋说部”体例对前人说部的借鉴。如其认为《居易录》采用的编年纪月体“本于庞元英《文昌杂录》”。[9]
《四库全书总目》亦谈到王士禛的创作态度。如评《分甘余话》时,称其“大抵随笔记录,琐事为多。盖年逾七十,借以消闲遣日,无复考证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谈》《居易录》之详核。”[10]认为创作这部作品时王士禛态度不够严肃认真。评《香祖笔记》时认为其中存在的细微错误,是由王士禛“晚年解组,侘傺未平,笔墨之间,遂失其冲夷之故度,斯亦盛德之累矣”,[11]及其年老多忘造成。
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总体上对“渔洋说部”是予以赞扬、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其缺点与不足。总体来看,其评论较为客观、公允,但也有一些细微问题,如其认为《居易录》中王士禛“平反之狱辞,伉直之廷议”是“所见之狭”,事实上,这些记录保存了王士禛其人及清朝吏治的重要资料,也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四库全书总目》将《香祖笔记》中的细微错误,归于王士禛晚年受“盛德之累”,以王士禛人品及其一生行事而论,将这些错误归于“盛德之累”恐并不恰当。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也对“渔洋说部”做了一定的评价。《郑堂读书记》将“渔洋说部”归于子部和史部,并对王士禛《池北偶谈》《居易录》《陇蜀余闻》《皇华纪闻》《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蜀道驿程记》《南来志》《北归志》十种说部作品做了评论。
总体来说,周中孚对“渔洋说部”也给予高度肯定,其评论的标准和《四库全书总目》编者一样,也是强调“渔洋说部”的诗文艺术性、补史性,对其中虚构部分评价较低。如其评《池北偶谈》时说:“渔洋以诗文为事,其全书所聚精会神处尤在谈艺一门,即谈故、谈献,尚足以备掌故,惟谈异数卷,不过小说家异闻之属,不足以轻重也。”[12]周中孚也谈到“渔洋说部”内容和体例上对前人说部及其他作品的借鉴。如其谈到《居易录》时,说此书“三卷以后,杂书官职迁除,直抄朝报,不嫌凌杂,盖效庞懋贤文昌杂录也……盖其日录庭讼之辞,在廷之议,以表暴其材能,此则源于《孟子》。”[13]认为此书体例效仿了《文昌杂录》,其取材也受到《孟子》的影响。另周中孚对“渔洋说部”有些作品条目篇幅不均也给予批评。如谈到《古夫于亭杂录》时说:“考是书虽成于晚年,而逐条皆考证评品,故不免疏密互见。”[14]
相比《四库全书总目》编者对“渔洋说部”的评价,周中孚较为明显的进步是他已认识到“渔洋说部”的整体性及“渔洋说部”对时人说部创作的影响。周中孚对“渔洋说部”整体性的认识,可从其对《分甘余话》的评价中可见。他谈到《分甘余话》时说此书“所记皆杂事琐语,间有考辨,亦不及《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四书之详核,然中多表耆旧、崇名教之谈,则仍不越前四书之本旨也”,[15]认为《分甘余话》与王士禛其他说部主旨上一脉相承。周中孚亦谈到“渔洋说部”对时人说部创作的影响,如其谈到王士禛好友宋荦《筠廊偶笔》时说此书:“皆追思其生平所见所闻笔而成帙,多述朝章国典前言往行,以及征物类载奇文,体例似仿王渔洋诸说部而不及其广博。”[16]
周中孚对“渔洋说部”的评价较《四库全书总目》编者的评价更为客观、公允,尤其是他已意识到“渔洋说部”各种作品之间的整体性,及“渔洋说部”对时人说部创作的影响。可见,相比《四库全书总目》编者的评价,周中孚对“渔洋说部”的评价有了较大的进步。
另庐见曾、孙诒让、耿文光、孔尚任等人也都在其作品中谈及“渔洋说部”的特殊体例。总体来看,他们都认为“渔洋说部”体例是仿自前人说部,尤其是唐、宋说部。如庐见曾在其《雅雨堂集·刻文昌杂录序》中说《居易录》:“未知其书体例创自何人。及观宋单父庞氏《文昌杂录》,始知先生仿懋贤(庞元英,字懋贤)之书而为之”,[17]认为《居易录》的体例是王士禛效仿宋代庞元英《文昌杂录》。另他们还指出“渔洋说部”体例对当时人的影响。如孙诒让在其所撰《温州经籍志》中谈到金璋《金氏漱芳斋卮言》的体例时说“窥作者之意殆在踵王氏之后尘,骎骎以臻夫刘氏之阃奥欤。”[18]
王澍、陆以湉、翁方纲等人主要谈及“渔洋说部”记录内容的特殊价值。如王澍《南村随笔序》说“新城王司寇《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及商丘宋少师《筠廊偶笔》诸书,有裨国家典故,足为后学津梁,直追汉魏、媲美唐宋,为本朝说部之冠,非若稗官野史荒诞不经者可同日语也”。[19]陆以湉《冷庐杂识》称“渔洋所著《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足以扶翼风雅,增益见闻”。[20]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中说:“近日王渔洋于说部分四目,谈故、谈献、谈艺皆吾所取也。”[21]他们对“渔洋说部”的现实意义,给予高度评价。
总体来说,清代学者对“渔洋说部”的评价是肯定的,他们已认识到“渔洋说部”的特殊现实价值,尤其是其艺术价值、“补史”功能。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渔洋说部”体例非其独创,有对前人的学习效仿。从他们的评论中,我们可见“渔洋说部”在清初的风靡之势,及“渔洋说部”内容及体例对清代说部创作的影响。清代学者对“渔洋说部”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其“谈异”部分,他们对“渔洋说部”中的虚构部分不太认同。
二、1949年后的“渔洋说部”研究
民国时期,学界对“渔洋说部”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就笔者目前所见,只有鲁迅《小说旧闻钞》中谈及“渔洋说部”。《小说旧闻钞》是鲁迅先生搜集整理的小说资料集,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辑录了“渔洋说部”中九条论及前代小说的资料,其中有三条论及《水浒传》(两条出自《居易录》,一条出自《香祖笔记》)、四条论及《三遂平妖传》(两条分别出自《居易录》《香祖笔记》,两条出自《古夫于亭杂录》)、一条论及《西游记》(出自《古夫于亭杂录》),另还有杂说一条(出自《香祖笔记》)。
下面主要从1949年后小说史、专著中的“渔洋说部”研究和专题性论文中的“渔洋说部”研究两个方面,对这段时期的“渔洋说部”研究做梳理。
(一)小说史、专著中的“渔洋说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渔洋说部”逐渐被学界重视,在一些小说史和专著中有了不少涉及“渔洋说部”的内容。这些作品主要有宁稼雨的《中国志人小说史》和《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侯忠义、刘世林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王士禛志》,张俊的《清代小说史》,苗壮的《笔记小说史》,陈文新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王恒展、徐文军的《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等。
在这些小说史、专著中,宁稼雨的《中国志人小说史》是文学史中较早研究“渔洋说部”的作品。在“清初至清中叶杂记体小说”一节中论及“渔洋说部”中的《皇华纪闻》《池北偶谈》《香祖笔记》,此书主要从小说的角度对这些作品予以评价,著者总评王士禛志人小说:“在王士禛的几种志人小说中,《皇华纪闻》的故事成分较多,但就全书看,仍嫌单薄;《池北偶谈》的内容比较丰富,但全书的故事成分,尤其是志人的成分又嫌少;只有《香祖笔记》能兼二者之长,不仅内容丰富,且故事文学成分较重,可视为清初杂记体小说的代表作品。”
侯忠义、刘世林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在“清代志怪小说的内容分类——记怪类”中对《池北偶谈》的思想价值做了论述。认为《池北偶谈》是一部琐闻类笔记,这部作品“不仅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从中亦可窥见作者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此书着重讨论了《池北偶谈·谈异》部分。
《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编纂委员会编《王士禛志》在第四章“文学成就”中专列一节“‘谈异’小说”,这一节对王士禛反对虚构、重视真实的小说观念做了论述,并指出“渔洋说部”主要是传统的笔记体,另有些作品颇类传奇。
小说史、专著中的“渔洋说部”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学者大都认可“渔洋说部”的特殊价值,尤其是其小说价值,称王士禛为小说家;二、对“渔洋说部”的研究,集中于“渔洋说部”中的少数几种大部头作品,如《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陇蜀余闻》《分甘余话》《古夫于亭杂录》,尤其是对《池北偶谈》给予了较多关注;三、对“渔洋说部”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其叙事的小说部分,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小说研究方法,侧重于探讨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另有少数学者还谈到了王士禛的小说观念,王士禛“神韵”诗论对其说部艺术风格的影响等。可见,这些研究相比前人的研究有了较大的拓展和进步,同时它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
(二)专题性论文中的“渔洋说部”研究
专题性论文中的“渔洋说部”研究主要可分为两部分,即学位论文和其他期刊、会议论文。其中专门研究“渔洋说部”的学位论文有四篇,其他期刊、会议论文有六十多篇。
专门研究“渔洋说部”的四篇学位论文中,一篇为博士论文,三篇为硕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即辛明玉的《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22]三篇硕士论文分别为文珍的《王士禛笔记小说研究》、[23]李文慧的《〈池北偶谈〉小说作品研究》、[24]巩怀霞的《〈香祖笔记〉研究》。[25]
在这些学位论文中辛明玉的《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主要对“渔洋说部”中部分作品的小说创作情况作了考述,对王士禛的小说观作了总结。从题材类型、文化特质、艺术特点对“渔洋说部”中的小说作品做了深入研究,认为“渔洋说部”中的小说作品“具有深层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另将“渔洋说部”中的小说作品放于山东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解读山东文化繁荣的原因及规律。
文珍的《王士禛笔记小说研究》对王士禛的小说观,及“渔洋说部”中志怪小说的思想内涵、志人小说的人物形象做了研究;李文慧的《〈池北偶谈〉小说作品研究》主要从社会、家庭、个人等方面分析论述了《池北偶谈》的创作背景,从文化和审美两个方面探析《池北偶谈》的价值;巩怀霞的《〈香祖笔记〉研究》界定《香祖笔记》为杂俎类小说,对《香祖笔记》的写作时间、背景、卷次版本做了考述,对《香祖笔记》的内容做了分类,并重点从文化、思想、艺术三方面探析《香祖笔记》的价值。
这四篇学位论文都主要是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角度对“渔洋说部”中的部分小说作品进行分析研究,都强调“渔洋说部”具有深厚的思想价值,其艺术手法上深受王士禛“神韵”诗学的影响。辛明玉《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将王士禛小说与其人生、山东文化联系起来,巩怀霞的《〈香祖笔记〉研究》也有部分内容是对《香祖笔记》文化价值的研究,二者的研究角度较为新颖独特,尤其辛明玉此文将“渔洋说部”中的小说作品与山东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挖掘。
专门以“渔洋说部”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有六十多篇。这些作品主要从文学、历史、文化三个方面对“渔洋说部”进行研究。另还有一些论文谈及“渔洋说部”与《聊斋志异》的关系。因论文数量较多,故这里将其做统一梳理。
从文学角度对“渔洋说部”研究的单篇论文,主要涉及“渔洋说部”的思想内容、写作艺术,王士禛的小说观念,“渔洋说部”的创作、传播几个方面。在诸多从文学角度对“渔洋说部”研究的论文中,主要从思想内容、写作艺术来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宁稼雨《〈香祖笔记〉的小说价值》、李永祥《论〈池北偶谈·谈异〉——渔洋笔记散论文之一》这两篇谈及“渔洋说部”中部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艺术。两篇论文分别对《香祖笔记》和《池北偶谈》的思想内容给予了较高评价,整体来看,其研究显得较为零散,对二书的写作艺术涉及也较少。本世纪初,主要从思想内容、写作艺术来研究“渔洋说部”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多。如宫泉久《从王士禛小说活动看其进步妇女观》、辛明玉《王渔洋文言小说的结构艺术》等论文。
这些从文学角度对“渔洋说部”研究的论文对“渔洋说部”的思想内容、写作艺术总体上是肯定的。对其小说观念的研究,多强调其“补史”观。对其创作、传播的研究,也都注意到了“渔洋说部”对当时及后世说部创作的影响。
从历史、文化角度对“渔洋说部”研究的单篇论文,主要涉及“渔洋说部”在历史、医学、生物等几个方面的特殊文化价值。这些论文大都是从小处着眼来研究论述,但从研究范围来看,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渔洋说部”特殊的历史价值、医学价值、生物价值等各方面的价值正在逐渐被发现和重视。如王云庆、尉迟慧丽《论清代王士祯的档案史料意识与实践:以〈池北偶谈〉为例》、杨璞《〈古夫于亭杂录〉里的中医笔记》二文分别从历史和医学的角度对《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中的一些条目做了研究。
以王士禛与《聊斋志异》关系为题的论文,主要涉及《聊斋志异》的“王评”、《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的关系、王士禛与《聊斋志异》的一些历史问题三个方面。对《聊斋志异》的“王评”,学界评价不一,但总体上是肯定的,大都认为其在《聊斋异志》创作、传播上的贡献功不可没。对《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关系的研究,多就二者的相同篇目展开论述。对王士禛与《聊斋志异》的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主要谈及王士禛不为《聊斋志异》作序的原因。
专题性论文中的“渔洋说部”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而且论述大都较为合理,可以看出“渔洋说部”的独特之处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其价值也正在逐渐被发现。
1949年后,小说史、专著及专题性论文中的“渔洋说部”研究相较清初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研究范围逐渐变得开阔,研究的深度也有所提升。
从清代以来,“渔洋说部”的特殊性及其价值呈现出一个逐渐被认识和重视的过程。清代的“渔洋说部”研究多关注其艺术性、历史性,对其虚构性小说评价很低,1949年后由于“小说”观念的变化,对“渔洋说部”的研究多侧重在小说方面,尤其是其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另“渔洋说部”独特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也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
从清代至今,“渔洋说部”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较多。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渔洋说部”的范围及其真实著述情况缺少考证性的研究。
王士禛一生著述众多,因王士禛及其他清代学者都没有对“渔洋说部”的概念和范围做明确阐释,所以“渔洋说部”到底包含王士禛哪些类型的作品,学界一直对其予以模糊处理。“渔洋说部”著作众多,成书时间不一,编纂情况多样,致使“渔洋说部”的真实著述情况不甚清晰。另王士禛的文坛声名或其他原因,致使有些与王士禛仅有一点儿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的笔记杂著也冠以王士禛之名,这给全面客观研究“渔洋说部”造成了干扰。由于缺少详细的考证,目前学界对“渔洋说部”中多种作品的成书、编纂情况众说纷纭。在“渔洋说部”的真实著述情况并不明晰的情况下对其做研究,就会使研究基础不坚实。
2.集中于《池北偶谈》等少数大部头作品,对“渔洋说部”其他作品研究不够。
目前学界对“渔洋说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池北偶谈》《居易录》等少数大部头作品。《池北偶谈》《居易录》等大部头说部,作为王士禛的的重要说部著述非常值得关注。但“渔洋说部”作品数量众多,且这些作品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如果把视角仅仅局限于其中的几部作品,这势必影响对“渔洋说部”的整体认识,和对王士禛及其“渔洋说部”成就、地位的正确评价。
3.对“渔洋说部”历史性、文化性、艺术理论性等方面的内容研究不够系统深入。
清代学者已经认识到“渔洋说部”历史性、文化性、艺术理论性等方面内容的特殊价值,但对其研究较为笼统,并没有做深入系统的研究。近代以来,“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渔洋说部”中“谈异”部分较为接近现代的小说概念,使得目前对“渔洋说部”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一方面,其他方面涉及较少。王士禛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正统文人,“渔洋说部”中谈故、谈献、谈艺部分是王士禛创作的重心。所以目前所谓的“渔洋说部”的研究,即以志人、志怪故事为中心的研究,有忽视重点、以偏概全的缺点。而且从现代“小说”概念的角度解读“渔洋说部”,致使对“渔洋说部”的解读存在诸多失误。
4.王士禛及其“渔洋说部”在说部发展史上的贡献认识不足。
目前对“渔洋说部”研究的专著、论文数量不少,但这些论文很少有从“说部”的角度展开研究,致使其研究多抓住“渔洋说部”的一鳞半爪来展开。尽管这些研究大都对“渔洋说部”给予了肯定评价,指出其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但由于研究立足点较小,致使涉及的面较为狭窄,且研究深度有限。这也使学界很难对“渔洋说部”的价值做客观、整体的评判,这给正确评价王士禛及其“渔洋说部”在整个说部史上的成就、地位、影响造成困难。
总体上看,“渔洋说部”还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目前的“渔洋说部”研究也还存在较多问题,尚待做更坚实可靠、丰富广阔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