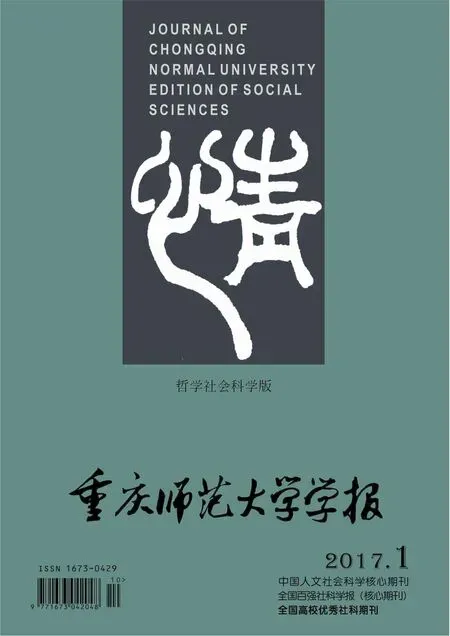创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董泽芳教授教育社会学思想中的特质
2017-03-28胡春光
胡 春 光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长沙 410205)
创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董泽芳教授教育社会学思想中的特质
胡 春 光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长沙 410205)
董泽芳教授是我国教育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纵观先生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其鲜明的特质就是“创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先生倡导及践行的创新取向的本土化,从研究方向上说,是走向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从研究内容上说,是指向教育社会问题的本土化研究。先生秉持“创新取向的本土化”,使先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呈现出强大的理论与实践生命力,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从“西化”走向“化西”树立了研究典范。
董泽芳;创新取向;本土化;特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打入“冷宫”,教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也进入了长达30年的停滞期。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来临,教育社会学才开始重新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董泽芳教授是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期的先驱,先生长期担任中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先生从1984年开始从事教育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经过七年的学术积累和实地研究,先生于1990年完成专著《教育社会学》[1]。该书出版之后,立即被全国许多师范院校选作教材,多次印刷再版,并获得了中南地区优秀图书二等奖,湖北省优秀教材一等奖等荣誉,成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其后先生陆续发表《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新论》《关于社会转型期教育社会学使命的思考》《从二元对立到多元综合——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我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与演变(1979-2005)》等系列论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框架。先生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于2009年出版了新编本《教育社会学》,此书突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注重了对教育社会学学科基础问题的探讨,加强了对重大教育社会问题的研究,是我国教育社会学人在新世纪对教育社会学进行本土化研究的一个典范。纵观董泽芳教授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其鲜明的特质就是“创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正如先生所言:“为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加强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2]19,“追求本土化特色,既是寻求民族文化认同、摆脱‘学术殖民’阴影的要求,也是获取学术独立地位、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要求。”[3]
一、创新本土化:走向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
“本土化”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基本上是与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过程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十六世纪西欧发展出现代性原则,随着西方先进国家在全球政治版图中优势地位的确立,这些现代化原则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姿态强压在其他非西方社会中。这些原先以具有传统的非西方文明乃自愿或被迫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此时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就会与原先本土的传统生活世界产生极大的扞格与张力,这些扞格与张力就是非西方社会产生本土化运动或诉求的基本历史处境,关于本土化的论述是深植于现代性的视野中的(不管是赞成现代性还是反对现代性),本土化正是对现代性的回应。
教育社会学作为兴起于西方的一门学科,当其在我国本土生根茁壮,必然也会遇到上述所言之扞格与张力。我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一直处于忙于吸收西方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模式,似乎已经忘记将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实际情况反映在研究活动中。在缺乏自我肯定与自我信心的情况下,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缺乏个性和特征,不少研究沦为西方理论的解读及行为科学的注脚(如常常引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伯恩斯坦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等来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等),这样的研究对西方社会的理论也许有所启发,或者成为西方理论的特例,即使研究有所贡献,却也只是贡献于西方理论的验证与否。引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结果,不仅让我们成为观察实验的受试者,其结果也在强化西方对我们的认识论,证明着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这不只是让西方取得文化解释的发言权,同时我们也患上了“学术失语症”。如果我们妄想通过这样的研究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教育问题,不但失之于片面甚至于会造成扭曲。如果中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要避免成为西方学术界眼中的“人类学橱窗”,身为研究者更应理解问题是会随着国情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这需要我们勇敢地对西方理论作出修正与批判并与之对话,“增强同国际教育社会学界对话的能力”[3],建立我们研究自身的主体性,而不是满足于担任学术的“贸易商”和“代理商”的角色。遗憾的是,我们从来不曾见到有过研究显示,运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在研究中国教育社会问题时会发生谬误,进而推论出这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适于中国。在我国教育研究上,只要是西方有新的理论出现,国内马上就有学术贩子引进,只要谁引进占得先机,谁就有可能在学术地位上占有一席之地。董泽芳教授正是有这样的学术反省、思考和忧心,才鲜明地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学,要特别重视教育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本土化的问题,不应该“只是”在本土作经验研究的问题,中国过去教育社会学许多所谓的“本土化研究”,大多还是直接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实证的方法)来探究中国本土的教育问题,研究者对于这些理论和方法背后所隐藏的西方人的世界观与身心状态,不是毫不反省的接受,就是有意加以忽略。对此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教育社会学是在一种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建构的,我国社会与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形势,所选择的道路都具有特殊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各种新的教育社会问题,很难用过去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更难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说明。”[2]20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本土化研究不能够不反省所使用的理论、方法、概念架构,甚至是界定问题意识的出发点;本土化研究必须要注意到社会的特殊性,要掌握这个社会中个人的世界观、身心状态以及行事逻辑,而不是一味的以华丽的概念、漂亮的理论套用在本土的教育现象上来解释。教育社会学发端且成熟于西方,合理移植与学习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但各国的教育社会问题的性质、原因与解决方法不尽相同,历史表明,一切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本国的国情才会有生命力。因此,引进吸收国外教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不能盲目复制和照搬,必须与本土化过程相结合[4]。
先生抱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教育社会学”的坚定信念,不仅强调要进行中国教育社会学的本土化创新研究,还一直主张中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要特别注重“中国特色”的打造,走“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之路”。先生认为:“‘中国特色’比‘本土化’内涵更丰富。‘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观点与我国当前的教育社会改革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方向上,要把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关注现实与开展传统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内容上,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把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提倡‘中国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过程的片面性与狭隘性。”[3]先生进一步说道:“在强调‘中国化’研究的同时,要防止将眼光只盯在‘适应于中国国情’上的片面化倾向,而应同时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尽可能从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的教育社会问题,增强同国际教育社会学界对话的能力。”[2]19总之,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只有立足中国国情,从研究我国当前各种最紧迫的教育社会问题入手,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合百家之说,博采众国之长;在不脱离世界总趋势的情况下,讲“中国特色”,才会有出路[4]。
教育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可以从三种不同的取向来理解。第一种取向是“意识形态取向的本土化”。这种取向将本土化视为对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基本上这是属于一种政治运动或社会文化运动层次的本土化,例如所谓的全盘西化派、文化保守派、自由主义等。第二种取向是“实证取向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取向与第一种不同,它不关注是否应对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立场进行选择,而是把重心放在我们是否能更真切地理解本土社会的真实情况,基本上这是属于一种学术层次的本土化反省。本土化在这里被视为对本土社会进行经验研究的一种实证研究,也即本土化是一个真切且如实地理解本土社会实际的历程,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大量运用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概念工具来理解本土社会,当西方学术工具不足时,也可使用本土文化的概念来发展本土化的经验理论,但是最终仍需遵循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原则。第三种取向可称之为“批判取向的本土化”。这种取向将本土化视为对西方现代性原则进行深层反思、解构及批判,并谋求另外的可能出路。第三种取向十分关注西方现代理论与本土生活世界之间的鸿沟与缝隙,以及两者背后不同的意识形态预设与不同的身心状态,它常常以对西方科学与学科体系之反省为本土化研究的起点,所以充满了批判的性格。因此,批判取向的本土化,重点也不在于研究者要采取何种价值立场,而在于对西方学术中所内涵的各种现代性原则进行检视与反思,尤其是对这些学科知识霸权中所隐藏的权力宰制关系进行揭露与批判,例如对西方学术体系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客观普遍主义以及东方主义等的批判。批判取向的本土化除了对西方现代性及学术体系进行毫不妥协的批判外,也试图在现代性的边界上,寻求各种新的可能性与出路。先生倡导和践行的本土化研究其实就是以上述第三种“批判取向”的本土化研究为基础,生发出一种独特的本土化的进路或态度,笔者将其称之为“创新取向的本土化”。此种取向的本土化极具反思性功能,它以颠覆西方知识为中心,过去固态科学理性所形塑的种种夸称具有普遍真理性的思想、认知和知识体系为己任。作为一种理性的心智活动,本土化是运用本土所累积、形塑文化认知的历史经验,以摆脱、修饰或超越西方知识体系几近全盘垄断的状况,并进而树立、实践具有独特性的理解和诠释风格,乃至知识体系理想正当化的过程。正如先生所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学,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为指导,从研究现实的各种教育社会问题出发,按照各种问题自身形成、发展与解决的逻辑顺序,进行深人地实证性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规律,探索其解决对策,逐步积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资料,并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此基础上才能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与知识体系,才能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学理论。”[3]
先生不同意第一种取向将本土化视为一种西化、反西化或其它意识形态的立场选择,因为真实的情况远比简单的立场选定复杂得多。身处全球化时代中,无论如何,我们早已经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没有哪个文明社会在此趋势下可以将自己置于现代化的大门之外,现代化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它早已是我们的制度、思维方式与身心状态的一部分了。“社会现代化作为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活动,离不开对原有社会基础的认真思考,它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下进行的,各国现代化的起点不同,内外环境不同,其方向、内容、道路也有区别,因此很难形成统一模式。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将普遍的现代化特征与本国的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产物,我国的社会现代化绝非‘西方化’或‘欧洲化’”[2]134-135先生也不同意第二种取向的本土化研究,也就是以“实证主义”贴近本土的真实为满足。因为此种“朴素经验主义”心态下的真实不过只是在西方现代学术概念工具下的真实,仍是不自觉地带着西方有色眼镜下的本土经验,这种经验的获得,势必以筛选或忽略许多本土人特有的身心状态之经验为代价,也可能对于此种经验背后西方学术夹杂的特定心态或预设毫无知悉,尤其当这些特定心态或预设常常伪装成具有普世价值时,就如西方学者建构出的“东方学”。虽然“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和注重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等特点,对于提高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和学科威信是有意义的,但它把社会现象完全等同于自然现象,过分强调经验的作用,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选择的意义,又容易使教育社会学实证研究陷入偏颇的困境”[4]。因此,忽略了本土人的主体性和价值选择性的实证主义倾向,不但把科学方法与逻辑独裁教条地供奉起来,而且根本窄化了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最可贵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因为生活环境的不一样,人们的所想、所感、所视、所为常常也是不一样的。第三种批判性取向的本土化意涵与视野非常深广,它超越了第一种取向简单的意识形态或文化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也不像第二种取向那样,只是在“本土”进行验证研究,外表朴素的经验主义却可能导致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盲目跟从。先生在“批判取向”本土化的基础上践行出中国特色的“创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这种研究取向是对于中国教育社会学自身当下研究处境不间断地反省检视、批判与创造,不仅是在加深批判意识的可能性,更针对中国的国情走转化的教育实践行动。因此,先生的本土化就是不断“创新”、“活化”,这是一种朝向未来可能性的重建与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先生的创新性本土化可以视为一种态度:找寻“出口”的态度,找寻一个我们面对西方学术霸权重建中国特色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出口。
“创新取向的本土化”使先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呈现出强大的理论与实践生命力,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从“西化”走向“化西”树立了研究典范。所谓“化西”,就是我们应把西方现代性及其学术文化之精髓在当下历史情境中,彻底吸收、同化与转化,使其与中国实践情况相结合(在这里要彻底检视西方现代性原则的根本预设),并且以此作为学术研究进一步的资源或基础。当然,先生强调的“中国特色”也不是主张中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从此就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建立起唯我独尊的学术中心主义,关起门来作纯粹的“本土化”研究,如此的鸵鸟心态也实在不必,不要忘了正是西方的学术思潮,才带给我们重新建构学术主体性反省的契机,只是我们在引进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时,也应深植创造性的转化过程,避免成为西方理论的“客观性”对象。正是坚持这种创新性取向的本土化研究,先生才建立起独创性的中国教育社会学的“本土化知识”,例如先生对教育社会学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就让我们对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上,先生认为可从三个层面上来揭示:从目的论层面上是探讨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机制及协调发展的规律;从认识论层面上是研究教育社会现象;从选择论层面上应重点研究教育社会问题。研究对象的这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探寻教育与社会互动机制及协调发展规律是研究的最终目的;考察教育社会现象是探寻机制与规律的必要前提;突出对教育社会问题的研究是深化对教育社会现象的认识、探寻机制、揭示规律的有效途径。因此,先生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通过对教育社会现象,尤其是对教育社会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机制及协调发展的规律。这样,既能将教育社会学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体现其独特的学科功能,又能充分反映时代发展对学科的迫切要求,同时有利于促进学科自身的建设与发展。[5]在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上,先生主张从三个层面来把握:从教育社会学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看,教育社会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从教育社会学与教育学及社会学的关系看,教育社会学是一门中介学科;从教育社会学与教育学科群的关系讲,教育社会学是一门中层学科。[2]38-39明确其边缘学科的性质有利于教育社会学在广泛吸纳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滋养的前提下,既能主动划清与教育学、社会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界线,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学科地位,又能在不断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明确其中介学科的性质,有利于加强不同专业出身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树立其学科意识,有利于在研究目的上把学术使命与社会使命相互结合,在研究内容上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西方教育社会学界那种人为纷争,而且可以克服研究中的纯思辨与纯实证的两种倾向。在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先生强调要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综合[4]。受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传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一直存在着自然科学取向与人文科学取向、规范性研究与证验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和谐论取向与冲突论取向、演绎性模式与解释性模式、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二元对立。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这种分裂和对立,严重影响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先生摒弃非此即彼的简单、线性思维方式,以多元综合的思维方式构建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方法论体系:在纵向维度上包括哲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专门科学方法论和具体学科方法论四个层次;在横向维度上包括时间、空间和学科三个视角,具体说既要实现三个“相通”,又要做到七个“结合”。三个“相通”,一是选择性地吸收国外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实现中西融通;二是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的教育社会学方法论,实现古今贯通;三是创造性地移植相关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实现科际会通。七个“结合”,一是自然科学取向与人文科学取向的结合;二是规范性研究与证验性研究的结合;三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四是和谐论取向与冲突论取向的结合;五是演绎性模式与解释性模式的结合;六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结合;七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在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上,先生提出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教育社会学研究是一种物理研究,即为探明事物自身客观规律而展开的研究。这一取向决定了教育社会学研究必须奉行事实判断,其价值取向是研究过程的客观性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其次,教育社会学研究同时也是一种事理研究,亦即为探明事物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而展开的研究,也就是通过研究既要说明事物是什么,又要解释为什么,还要讲出如何做。因此,事理研究既是价值研究,也是应用研究,其价值取向是研究结果的合理性与指导实践的有效性;再次,教育社会学研究还是一种共理研究。因为物理研究所关注的事实同事理研究所关注的意义是不可分割的,事实负载着意义,而意义来自于事实,二者并不相悖。[2]38-39所以教育社会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物事共理”研究。同时因为教育社会现象是古今中外都共同存在的现象,所以教育社会学研究也是一种“古今共理”和“中外共理”研究。共理研究的价值取向是科学与人文的并重,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契合。
先生倡导并践行的“创新取向本土化”研究,是走向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此种取向的本土化研究在理论产生与实践应用上有两条路线:其一为内部本土化,指的是关键性本土概念、方法与理论的淬炼、编码、系统化与应用的历程;其二为外部本土化,“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尽可能从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的教育社会问题”[2]20,最终达成理论上和方法上的适用性转化。换言之,本土化研究中所采用的材质,有来自本土内部和本土外部,前者是从本土情境中重振本土知识与文化,或者从本土根基上有所创新,如先生一直强调要“尤其注重从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2]前言;后者则是吸收外来要素加以融入,形塑本土新的内涵与风貌。总之,本土化不是用他人的理论与方法在本土进行“验证化”,也不是搞狭隘的“在地化”,拒斥一切变化与外来特质的纯粹复古化。本土化要保持蓬勃的生命力与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有源头活水,也必须要不断适应外在环境变迁纳入创新新元素,而且每种本土化都各有其殊异性与独特性。
二、走向实践化:指向教育社会问题的本土化研究
先生认为,“教育社会学应致力于为教育决策与教育改革的实践服务,这既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3]研究即实践。实践是人类尝试去克服限制,致力于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一个相互转换的过程,并且通过实践来生产新的结构关系。因此,先生在长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中一直秉持学术使命与社会使命并重,先生说:“我们研究教育社会学自不应坐而论道,而应该同时承担起学术使命与社会使命,对一些问题既要有理论分析,以揭示规律,解释事实,又要有对策研究,以参与实践,为现实的改革服务。”[2] 前言在先生看来,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追求价值中立的知识,而是追求一种“解放的实践知识”,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不再只是抱着一种客观超然的立场,也不再只是追求对现状的了解而已,而是抱着一种承诺与涉入的态度,通过走向实践的研究,主动提供改变现状的策略,唤醒被研究者的批判意识,摆脱受支配的情形,协助被研究者提高自我组织和转换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把“逻辑的事物”当成“事物的逻辑”,认为只要理论对了,事情就解决了。于是乎许多教育学者(包括教育社会学者)习惯于在书斋闭门造车,崇尚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学术研究方式,热衷于“跑马占地式”地建立“新说”“新学科”“新体系”。要么他们把自己架在高空,远距张望所观察的对象,使教育理论远离了鲜活的生活世界;要么把其它理论作为自身理论合法性的依据,忽视了教育理论发展自身的逻辑和实践基础。这般将理论的逻辑置于实践的逻辑之上,抹煞了实践的独特性,同时又造成了许多理论上的无谓难题。教育社会学研究需要将具体的经验研究和敏锐深刻的理论建构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使之具有鲜明的风格,如此理论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真实空间。真正的创造不仅仅是理论观点或思维与众不同,而是能在实践中产生实效。“完全和解决现实问题没有关系的社会科学学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是得不到发展的”[2]27。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否定学理研究和体系探索的价值,“在学科恢复重建初期有必要注重体系构建,但从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及本土性、时代性特征来看,忽视实践问题研究则可能有失偏颇”[6],中国的教育学理论发展更需要现实问题取向,更需要在日常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体系,教育学(包括教育社会学)只有凸显出实践特性才能彰显出它独特的学科地位。总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需要从整体化上来构想,实践是从一个理论点到另一个理论点的“驿站”的总和,而理论是两种实践之间的“驿站”,任何没有碰过壁的理论都是不可能发展的,而实践就是用来凿穿这堵墙壁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头脑里的一百元不等于口袋里的一百元。因此,先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一直致力于加强对中国重大教育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践研究,先生说:诚然,这些问题都相当复杂,一时确难以认识清楚,有些提法可能也不够准确,但与其回避不讲,不如面对现实、客观反映,提出一些看法,引导和激发其他研究者(学生)自己去思考[2] 前言。
中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热衷于“批评式研究”,这种研究往往充斥着慷慨激昂的陈词,华丽动听的辞藻,激情浪漫的关怀,对现代教育问题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好像自己就是教育真理的最大代表者,教育责任的最大担当者,但热闹的教育批评中却对教育实践的转进之道无动于衷。批评式研究依靠感性主义的诱惑和夸夸其谈的情绪来赢得学术市场的赞誉,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生命压抑下的一种生理冲动,是对现代教育体制僵化、考试霸权主义、工具理性工业、生活程式化等的一种反抗,用韦伯的经典名言就是,力比多造反逻各斯。教育社会学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格,让我们对教育问题必须保持批评的态度,批评的实质是为了改造实践,呵护生命,塑造人性。可是,“批评式研究”并不关注教育实践,或者说他们往往是一种抒情式的“修辞学”研究,把热情消耗在否定和哀怨上,现实的教育及其实践都以负面和畸形的形象出现在批评式研究的战斗檄文中,它目空一切的否定、批评一切现实教育,导致批评式研究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是一种没有教育研究责任担当的虚无主义,除了睥睨万物而又有些老生常谈的“否定”外,批评式研究基本没有自己的研究信仰,变成教育实践的马路放火者和夸大其词的混乱制造者。在无所担当的虚无主义自由中,批评式研究缺乏深刻、严肃的对教育问题和生命本身的思考,陶醉在浅尝辄止的自我恣意的片语中。
针对上述问题,先生反思了我国近年来包括教育社会学在内的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认为在理论研究为教育实践服务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科学研究不是发号施令,研究者也不是行政官员,科学研究的结果不是得出必然的结论,而是陈述客观事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教育科研应服务于实践,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前瞻性的“预测”,是教育研究的真正价值之一。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对教育研究最终价值的认定,以及对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所在认识不同:前者认为教育研究的最终价值在于求真,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是认识世界;后者认为教育研究的最终价值在于求用,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是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还要参与改造世界。先生总结后认为,要正确认识教育科学研究中“求真”与“求用”的关系,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二者结合才能获得教育研究的最大价值。此外,先生还特别强调,要重视由理论成果向实践应用的转化环节的研究。[4]理论研究的成果再先进也不能直接应用于教育改革的实践,必须对中介环节进行细致的研究。如新的教育公平理论是一种以承认多样性为前提的公平论,要应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教育分流制度的改革,就必须首先研究新的教育公平理论对教育分流的各环节,如招生环节、录取环节、分校环节、分班环节、教学环节、学籍管理环节等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研究各个环节应该采取怎样的改革措施,还需要研究各种措施需要的相应的保障条件及机制等等。这些转化环节的研究对理论服务于实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这些研究又往往因不被看作是科研成果而不受重视,不少人也不愿去做。这也是我国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学就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一门学科,教育社会学研究必须秉承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从普遍性中走出来,进入到教育社会现象的实践中去,以发现这些特殊现象的性质。就像看一座山,远看观得的外部轮廓未必就是“庐山真面目”,我们必须曾在此山之中,勘踏过它的草径,漱饮过它的溪流,抚摸过它的石和树,必须曾生活在那里,才能从外形看到实质。看,如果是跳出来看,只是一种回忆,唯曾在者才能识得山之真面目。对于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来说,先生认为只有那些对教育与社会互动、对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重大正负效应的教育社会问题,才是教育社会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所谓教育社会问题,是指教育系统在自主且适应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出现的与社会大系统或其他子系统之间不协调而引起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现象”[2]19。只有对我们自身的教育社会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研究,并作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社会学解释,才能体现出这门学科的终极价值。“教育社会学的问世就同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教育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对这些教育社会问题的研究,使各国教育社会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生长点。”[3]因此,中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如果不研究自身的教育社会问题,不用自己的学科之眼去看待自身的教育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的教育社会学至多仍不过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印迹,我们的学人还是善尽一种“土著报道人”的角色。因此,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需要在对各种教育社会事实、行动实践、文本话语、理念价值反思批判、整合优化的过程和基础上,立足于教育日常生活,能动、敏锐地揭示、评价、把握和预测教育社会环境、教育社会成员生存情境的不断变迁带来的问题、挑战和机遇,真实反映所有教育社会成员相互依存协作和竞争制约的共生共荣的生命天性和生态规则,坦诚面对教育社会成员个体和群体更好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客观需要和能动追求,动态考察学校场域中个人、群体的实践行动和互动的过程和方式,冷静面对教育社会个体和群体生命挤压、个性对峙、生存紧张、理念冲突等行为越轨、制度废弛、组织冲突、结构失调和功能紊乱的现象,科学揭示教育社会变态、扭曲和病变的忧患、机理和原因及提出相应调适、治理和康复的对策举措。具体来说,先生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把握教育社会问题[3]:宏观层次讲有社会结构转型与教育制度的调适问题、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与教育的社会功能重构问题、教育与社会冲突的加剧与教育的整合机制问题;从中观层次讲主要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社会分化而引发的一系列新的教育社会问题,如区域分化与教育失衡问题、社会转型与学校组织的冲突整合问题;从微观层次讲主要有社会行为无序与教育行为失范问题、教育时空拓展与师生关系变化问题、学校内外环境变化与教师角色冲突问题等。[7]
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教育社会问题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很难用以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更难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说明。因此,日益强烈的问题意识对揭示这些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学规律,对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学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先生所言:“教育社会学要立足于问题研究,着眼于学科发展,致力于实践服务。”[3]亦即,教育社会学研究需要一种走向教育实践的智慧,这种实践智慧不仅仅是一种机械技巧,更是一种视野想象的指向中国教育社会问题的创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
[1] 董泽芳.教育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 董泽芳.教育社会学(修订本)[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董泽芳.关于社会转型期教育社会学使命的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 (2).
[4] 董泽芳,胡春光.从二元对立到多元综合: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6).
[5] 董泽芳,黄学文.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新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3).
[6] 董泽芳,张国强.我国大陆教育社会研究的特点与演变(1979-2005)——基于对教育社会学重建以来概论性著作的文本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7,(7).
[7] 苏有.“过犹不急”对“新公共管理”的借鉴必须适当[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5,(2).
[责任编辑:朱丕智]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Based on Innovative Orientation: a Study on Traits of Professor Dong Zefang’s Ideology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Hu Chungua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Professor Dong Zefang,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holars in China,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in China. With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ation, the most distinctive trait of Professor Dong’s thinking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s his localization research based on innovation orientation, whose research direction is aimed at emphas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focusing on the typical issues, related to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China. Not only advocating but also living up to by himself in person, what Professor Dong has insisted make his ideology quite vivid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ing way and naturally become a typical model for china’s researches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a dewesternization way.
Dong Zefang; innovative orientation; localization; traits
2016-08-15
胡春光(1976-),男,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IG40
A
1673—0429(2017)01—008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