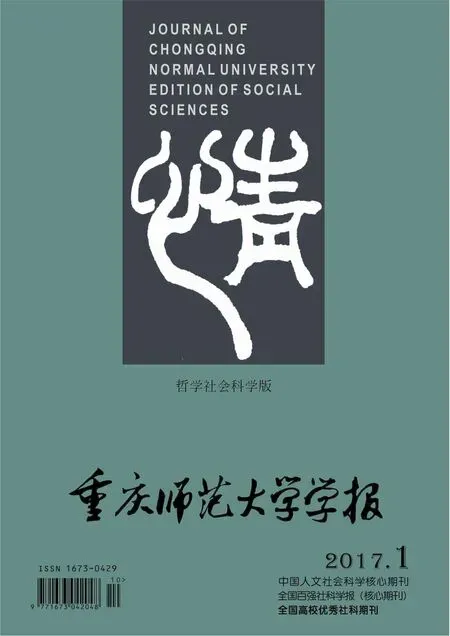“靡然西向”至“异说纷起”
——周秦之变视域下士人与秦政权关系演变探析
2017-03-28刘力姜静
刘 力 姜 静
(1.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 2.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靡然西向”至“异说纷起”
——周秦之变视域下士人与秦政权关系演变探析
刘 力1姜 静2
(1.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 2.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先秦之际,为谋求建功立业,四方游士纷纷西向秦,助其在诸侯争霸中一统六合,成就帝国伟业。进入大一统专制体制后,士人期许在由自身参与开创的帝国政权内依旧“为帝王师”,这与专制皇权需要士人“从于王”的定位相分歧。最终,士人的“异说”“讥议”“挑战”遭遇帝国“焚书坑儒”的威权回击,从而结束两者在先秦所形成的较为同步的双向期许关系,开启了 “道”与“势”“谁寄于谁”的时代。
士人;秦政权;大一统;道;势
战国诸侯纷争铸就“处士横议”。其时,士人四方游走,期遇明主,谋求建功立业。在此过程中,僻居西隅被关东六国在文化序列上 “夷翟遇之”[1]《秦本纪第五》的秦却成为士人的心向之国。“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帮助他灭亡了自己的国家。”[2]4然则,当士人帮助秦最终一统六合,建立首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后,自身却失去了“为帝王师”的政治场域。最终,士人在帝国体制内的“异说”“挑战”遭致帝国威权以“焚书坑儒”方式的回击。对于历史呈现给士人的这一近乎吊诡般的“嘲弄”,笔者拟从士人与秦政权关系演变的视域进行梳理并尝试解析之。
一、四方游士西向秦
春秋至战国,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由争霸转为兼并,纷争更趋激烈。在此过程中,士人凭借谋略才智在其时政治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功效。“六国之时, 贤才之臣, 入楚楚重, 出齐齐轻, 为赵赵完,畔魏魏伤。”[3]266故而其时的诸侯国莫不以尽力招纳四方宾客游士为要。
其时秦虽僻处西隅,但自穆公始,“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4]887。且较之关东六国更甚,“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5]《秦用他国人》,37基于其时谋求事功的现实考量,秦对于士人的招揽任用更为务实更为广泛。
面对各诸侯国君对士人的极尽延揽,从士人的角度视之,得明君而仕之,以实现为帝王师建功立业的价值期许是左右其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抉择的重要杠杆。秦经由孝公时期商鞅变法革新,以军功赏爵,已然国富民强,称雄于诸侯。故而对士人而言,秦不仅有着政策上的感召力,亦有着基于雄厚国力的现实吸引力。由此,尽管“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1]《六国表》,然对于士人而言,其却具有更为强大的吸引力。如李斯,本为楚国人,在师承荀子学成之后毅然驰骛西向,乐为秦王“舍人”: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1]《李斯列传》
正是基于秦对士人的礼遇重用以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的雄谋,吸引了作为楚人的李斯毅然前往,拟图赶上这“万世之一时”。
有学者对《史记》中从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即春秋战国时期列传中记载的60位先秦士人进行统计划分。其原住国及排位为:齐国14人,赵国9人,楚国8人,魏国5人,秦国5人,卫国5人,鲁国4人,东周3人,宋国1人,中山国1人,郑国1人,邹国1人,韩国1人,燕国1人,原住国不明者1人。考察这60人,其流入国及各诸侯国获其实际效力人数排位前三的则是:秦国:本土5人,流入12人,共计17人;齐国:本土12人,流入3人,共计15人;赵国:本土7人, 流入2人,共计9人。比较其时主要诸侯国的人才流入率和流失率: 秦国流入12人, 流入率为71%; 本土人才无外流, 流出率为零。[6]由此可以看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秦不仅是士人(人才)的产出大国,同样也是士人们(人才)的心向之国。
最终,在士人们的助推下,秦一统六合成就帝业: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1]《李斯列传》
我们看到,在秦“乘六世之烈而吞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的过程中,士人们所发挥的“众人之策”是功不可没的。
在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士人纷纷西向于秦。究其由,在秦而言,秦政权的统治者为了谋求霸业而施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文化怀柔政策,“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1]《李斯列传》。一定程度上言之,正是秦基于实现一统天下之需而实行的厚待四方宾客的政策助推了士人的靡然西向。即便在因怀疑“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意欲“请一切逐客”时,最终考量到如若“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而旋即“乃除逐客之令”。[1]《李斯列传》
另一方面,则是秦重实效重军功的社会风尚,尤其是在经历商鞅变法之后,其开始雄霸诸侯,呈现出一统天下的气象,对于拟为“帝王师”的士人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对此,有学者分析认为,其时士人“对其所作所为的一切,他们较少从较为广大的视域来深思、反省。事实上,他们并不十分在意其事行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占据其思想的,乃是如何帮助优礼他们的有势力者达成目的和愿望,并设法改善自己的境遇”[2]52-53。
上述论述说明,在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的过程中,士人与秦基于双方各自的利益诉求而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双向期许的同步,“士以输力纳智行其事业。而诸侯以财货资用、官职禄位这些经济上、政治上显见的利益所赎买的,也正是他们的各样本领、能力。之所以肯下士礼贤,无非是加意笼络,希望藉此博取士人们更无保留的效命。”[2]51-52从而出现了天下之士,纷纷西向于秦的盛况。
二、秦帝国内士人“异说”纷起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秦帝国建立。士人们在面对秦帝国这一“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统一伟业之初,无疑是充满认可与期待的。“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1]《秦始皇本纪》此翻颂扬,除却歌功颂德的成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呈奏者”对于始皇帝所开创的这一伟业的认可,“罔不宾服”。然则,随着帝国政权的运行,士人与帝国间因各自不同的政治期许彼此间开始走向分途。
帝国创建伊始,即欲将先秦四处游走的士人纳入制度之内,其主要表现在博士员的设置。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7]《百官公卿表第七上》,272博士员的设置,是结束诸侯纷争实现大一统的帝国统治者拟图将以儒生为代表的士人延纳进入大一统的体制之内,将春秋战国的私家养士制度一变为王朝养士,从而与帝国政权一统相适应的文化政策上的举措。在帝国言之,其对士人的期许已由先秦时期的出谋献策力争天下转而为大一统政权体制作出为在上者认同的论证,在于认同、服务、效力于新生的帝国政权,而不再是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处士横议”。
然则,对于秦统治者这一变化了的政治期许,士人们却似乎不仅是“辜负”,甚或出现了相反的“异说”,乃至“非议”。
士人们首要的“异说”表现在对于帝国政权建构形式上。随着秦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秦用郡县制取代西周分封制。在秦而言,这一方面是其政权统治形式历史发展的延续。郡县制在秦还是一个诸侯国时就已经施行之。“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1]《秦始皇本纪》另一方面,实行郡县制是秦基于现实功效的理性选择。郡县制下的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官吏与皇帝之间首先和主要的是君臣关系。相对于分封制,其更能有效的保障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贯彻与执行,故对于专制集权的秦帝国而言,这无疑是自然的逻辑的选择。
然则,以儒生为代表的士人作为西周宗法礼乐文化的承载者,却对承载着礼乐文化的分封制更为亲睐。帝国之初,作为儒生的丞相王绾率先上奏:“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1]《秦始皇本纪》而“群臣皆以为便”[1] 《秦始皇本纪》,则说明持这一主张的普遍性。与之相反,作为法家代表的廷尉李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郡县制“甚足易制”,是“安宁之术也”。始皇帝的“廷尉议是”则明确表明了统治者的择取意向。只是,始皇帝的“廷尉议是”并没有让儒生士人就此止步。甚至当仆射周青臣进颂“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时,博士淳于越驳斥其为“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将政见分歧演化为政治道德上的评判。
如果说士人对于在帝国政权建构上郡县与分封的秉持,由先前的各抒己见到其后的对持守者人格的品评,已然演变为政治“异说”。而其后,对于象征帝国威权合法性的“封禅”以及最高统治者的讥议,则无疑是开始挑战帝国的“政治威权”了。“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1]《封禅书》在此过程中,儒生对封禅之礼人言人殊,且所言“繁琐”,“乖异”“难施用”而最终受“绌”,“不得专用于封事之礼”。为此,儒生则以 “讥之”回应“既绌”,“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1]《封禅书》儒生讥议封禅这一行为,在统治者而言,无疑是对秦帝国一统太平合法性的质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封禅,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宗教祭祀活动,更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昭告。故“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1]《封禅书》。儒生士人的“封禅”之讥,无疑是挑战了帝国政治威权的合法性。对此,清人胡秉虔说,“此焚坑之祸所自起也”[8]。
士人秉持先秦“处士横议”之风,一方面对秦帝国的政治建构政治行为进行异说、讥议,一方面还对始皇帝——首开大一统伟业的秦帝国最高统治者进行非议。
在秦帝国统一大业的进行过程中,其时还是秦王的嬴政对大梁人尉缭不仅“从其计”,还“衣服饮食与缭同”,可谓“亢礼”。然则,尉缭的回应却是,“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1]《秦始皇本纪》
为求长生,始皇帝对于方术之士不仅施与重金,更是有求必应。然侯生、卢生却通过对始皇帝“为人”的非议为自己“求仙药”失败开脱: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1]《秦始皇本纪》
不仅如此,始皇三十二年之际,燕人卢生因入海求仙不得而还,遂以鬼神事,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为破此谶,始皇帝“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1]《秦始皇本纪》
上述儒生、方术士人的“品评”“讥议”,不仅是挑战帝国的政治威权,更是触及到帝国政治的合法性存在,这不仅违背了帝国对于士人的期许,更是超越了帝国统治者所能容忍的底线。对此,作为权力的帝国随即展露出另一面目——“焚书坑儒”——在帝国威权受到挑战时以权力的狰狞所予以的反击。
三、“道”“势”的消长
“焚书”与“坑儒”原本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历史事件,其被关联在一起且被彰显放大,从士人与秦政权关系演变的角度视之,一方面表明两者之间先秦以来较为同步的双向期许关系的终结;另一方面则是揭示出进入大一统体制后,士人所承载的“道”与帝国政治所象征的“势”二者间关系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处士横议”,这些促成了士人“以道自命”的自我期许,“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梁惠王上》) ,即为社会价值的承载者与弘扬者。对士人而言,利用自身掌握的道德文化资源言治乱、议政事、论国事,不仅是其时风尚使然,更是自身承载的使命所必须。士人的品格与追求决定了他们热衷于政治批判与政治设计。其时的诸侯国王所呈现出的礼遇宾客厚待游士,究其实质,不过是为了获得由士人所掌握的道义文化资源对其政权合法性予以认同。故士人亦常以“帝王师”自居,以“道”凌驾于“势”。
历经“周秦之变”,经士人“众人之策”所助推出的秦帝国是一种与“处士横议”的春秋战国迥乎不同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在新生的帝国体制下,“天下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1]《秦始皇本纪》这应该是曾经靡然西向的士人们所完全不曾预料的结果,“士人们大都以为,并且希望,天下纷争的结局将是诸侯时代——它由于被秦结束得那么迅疾、那么暴烈,而使他们愿意想象,那只是短暂的被中断——的顺延或再度复兴。……士人原是依凭于诸侯的浮游资源,他们对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既乏兴趣,也不期盼。”[2]52-53故已然置身大一统帝国体制内的士人们依旧延续着“以道自命”的自我期许以及热衷于政治设计与批判的品格。上述士人在专制帝国中的“异说”“讥议”一方面是延续了战国“处士横议”之风,另一方面也似乎部分印证了学者所言之的士人“对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既乏兴趣,也不期盼”的政治态度。
“焚书坑儒”呈现出的是在专制体制内,士人(“道”)与政权(“势”)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磨合的失败。在专制体制内,皇权具有至上性、绝对性,其延揽礼遇士人只是看重士人为皇权服务的功效性,而非目的。然“以道自命”的士人则仍旧拟图秉承先秦遗风,旨在通过舆论品评时政,甚或质疑政权。如此则出现了士人与皇权二者彼此之间期许上的差异:“当由皇权苦心培植的承担教化功能的士人阶层开始成为皇权的反对派,当士人们开始通过控制舆论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质疑和威胁皇权的合法性时,皇权对于士人的礼遇亦或怀柔便不复存在。”[9]“焚书坑儒”即是作为皇权的“势”向士人所承载的“道”所展露出的“狰狞的面目”[10]。对此,士人“缺乏足以反对皇帝的独立自主的权力基础和资源”[2]引言,4,故所能回击的即是将秦帝国置于道德文化的批判席位上:“昔秦以武力吞天下……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塞士之涂,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陨社稷也。”[11]《论诽》
我们看到,士人将“将秦的失败归之于他在道德、智能上的低劣”[1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德”“智能”一直被视为士人的生存之本,秦帝国施行的“焚书坑儒”在士人看来,就是帝国政权的“势”对于以“道德”“智能”为内容的“道”的拒斥与打击。其结果则是“道凌驾于势”的先秦格局逐渐向“道承顺于势”的转变。
“道”与“势”关系的转变,源自于周秦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战国“诸侯并争”为“处士横议”以及士人的“以道自命”提供了条件。诸侯并争,需要国富兵强,而国富兵强离不开延揽人才。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7]《东方朔传》成为其时共识。而士人四处游走,向各诸侯国君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蓝图,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类似于“买方”与“卖方”的关系,韩非称之为“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且士人因可供选择的“买家”众多往往拥有更多的主动权,“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1]《孔子世家》?这铸造了士人“为帝王师”“以道自命”的政治期许与定位,“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1]《鲁仲连邹阳列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然进入大一统体制后,政权与士人之间“买”“卖”双方的格局发生变化,作为“买方”的政权由“多”为“一”,从而使得双方关系的主动权转移到了帝国政权一方。然则,习惯了“为帝王师”的士人似乎“不识时务”的依旧沿袭着先秦时期的政治样态。“他们还在乘战国百家争鸣之遗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希望能在新的大一统政权中实现自身价值。然而秦始皇并不领这个情,尤其是士人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更令他反感。于是便有了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13]
“焚书坑儒”某种程度上言之,乃是帝国威权凭借所掌握的国家暴力资源——“势”向士人所承载的道德文化资源——“道”的一种示强。其结果则揭示了士人群体所承载的“道”与专制政体的“势”二者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关联维度。曾经“为帝王师”的士人必须接受“从于王”的身份与现实。一如有学者所指出,“可以预料,当士人被规范化地纳入集权政治的官僚系统之内,除了向专制君主负责,别无它仕可能的时候,恪守道德人格与用仕进取之间的矛盾和考验,对于他们将变得愈来愈严峻,别无选择,不可回避。其后叔孙通以‘圆滑’著称于世,就是士人群体在权势高压下对专制政体所采取的态度与对策。”[2]49
[1] 司马迁.史记[O].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 王充著, 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晋书[O].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洪迈.容斋随笔[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6] 王磊.得人才者得天下——先秦士人流向分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7] 班固.汉书[O].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8] 转引自朱国伟.略论周—淳之争的缘起——也谈焚书坑儒发生的原因[J].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0.
[9] 姚静波.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J].史学集刊,2001,(1).
[10] 代云.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J].南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 5).
[11] 桓宽.盐铁论[G]//诸子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
[12] 区永圻.论汉儒批法[J].江西社会科学,2003,(7).
[13] 高伟洁,朱晓鸿.从“志于道”到“从于王”——上古士风嬗变一瞥[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责任编辑:刘力]
From “Most Westerners” to “Few Supporters”——The Analysis about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holars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Q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sty Changing in the Turning of Zhou and Qin
Li Li1Jiang Jing2
(1.Editor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2.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some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who came from every quarter went to the west one after another. These ambitious people helped Qin to finish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six states and build a new empire in the contending for hegemony of lords so that they also can make contributions for themselves. After the autocratic system found, the scholars still wanted “to be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emperor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had a hand in the career of building the new regime as pathfinders. But that drove off in the reverse direction with their role assignment which was defined by “submissiveness”. Finally, all the “opposition”, “discussion” and “provocation” fired back by a cruel atrocity, that is “Burning of books and burying of scholars”. It ended the double-expectation relationship that comparatively developed at the same pace in the early time of Qin and began an age to see the rivalry between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imperial power”.
scholars; political power of Qin; the great unification; Confucian orthodoxy; imperial power
2016-11-10
刘 力(1975-),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 姜 静(1990-),女,河北沧州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生。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秦汉民族文化格局下西南巴蜀的地位》(项目编号:15SKG043);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巴蜀在秦汉民族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YBLS104)。
K232
A
1673—0429(2017)01—0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