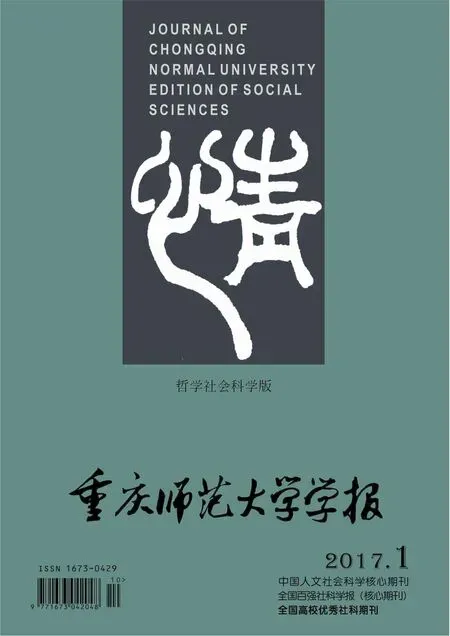《子不语》的美学思想
2017-03-28李天道唐君红
李 天 道 唐 君 红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子不语》的美学思想
李 天 道 唐 君 红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子不语》是清朝著名的笔记体小说,也是袁枚的重要代表作,集中体现了袁枚的小说美学思想。本文侧重从三个方面重点讨论袁枚的小说美学思想:一、社会现实生活是小说的源泉,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二、真实地再现当时的人情世态;三、《子不语》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情感。这三点中讨论得最详细的是第三点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情感。《子不语》涉及的情感有很多类,其中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三类进行阐释,分别是男欢女爱的自然之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之情;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讽刺之情。通过这几个方面重点阐释了《子不语》的小说美学思想,通过其小说美学思想更深刻地了解袁枚在清朝文学史上的地位。
《子不语》;小说美学;情感
《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名字来源于孔子《论语·述而》中“子不语怪,力,乱,神”[1]。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的笔记体文言短篇小说,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并列为“清代三大文言笔记体小说”,在当时和现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迅也在艺术成就上肯定了它的价值:“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2]作者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历经康雍乾三代,是中国十八世纪最离经叛道和最具有争议的文学家。袁枚一生高举“性灵”旗帜,猛烈抨击当时流行的复古思潮和“程朱理学”,离经叛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子不语》这部作品集中展示了袁枚的小说美学思想。
《子不语》一反传统的“天人合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封建伦理观,而是赤裸裸的残酷的把现实剖给世人看,一反大团圆的结局,更多展示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一种深深的无奈。作者不美化,不虚拟,把真实的人生悲剧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人在血腥残酷的事实面前得到一种超越和解脱。下面具体分析《子不语》的美学思想。
一、现实生活是小说的源泉,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任何美学思想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都是现实生活中先有其存在,然后才有描绘这种现实生活的小说。比如《红楼梦》这部小说,先有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等人物的存在,曹雪芹才可能把他们写出来,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存在,曹雪芹不管怎么呕心沥血都写不出这部伟大的作品。小说是对于生活的“摹写”、是“今社会之见本”,任何小说的诞生都是所经历生活的一种艺术反映,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生活这个根基存在,一切小说都变成了无源之水,变得空洞而没有任何意义。袁枚的小说美学思想第一点就是现实生活的“摹写”。先有袁枚的社会生活经历,才有《子不语》这部小说的诞生,《子不语》是袁枚社会生活经历的一种反映。袁枚生活在清朝康乾盛世年代,满清的开国皇帝入主中原,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和一系列文字狱的实施,清朝政府出现了一个空前的盛世局面,中央高度集权,出现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阶段。极端野蛮的文化制度和残忍的文化钳制让广大知识分子“避席畏闻文字狱”,文人普遍的恐惧心理让他们埋首考据,不闻世事,繁琐的考据成为学者的时尚,在不断的考证中消磨时光和斗志,从而滋长了世事无常,及时行乐的心理。文学主体转为对世俗生活的描写,对庸俗生活和色情的欣赏。袁枚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学逐渐自觉成为宣泄人愤懑情绪的年代,文学成为士人寄托理想,消遣人生的一种手段。袁枚少年家贫备尝生活艰辛,后科举成名,踌躇满志时却又因为满文不及格倍受打击,这种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让作者具有了一种悲剧意识,产生了一种悲剧美,在反反复复经历希望,失望,绝望,奋起的过程中,作者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在思想上接受了各种丑恶的现象,这是袁枚《子不语》大量丑恶现象存在的社会基础,正因为袁枚的经历很丰富,当过官吏,所以才让他写出大量反应官场黑暗的小说。
袁枚的生活经历也和《子不语》的产生息息相关,袁枚经常和朋友一起谈神论鬼。“春秋风月佳,彼此具盘餐。看花到日昃,说鬼到更阑”[3]这首诗表达了袁枚和朋友谈鬼谈到了天明。袁枚本人对鬼故事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生嗜好多,老至亦渐忘。唯有两三事,依旧欢如常。推书傍水竹,随手摩圭璋;名山扶一杖,好花进一觞; 谈文达甘苦。说鬼瓷荒唐。七十苟从心,逾矩亦何妨!”[4]袁枚一生都喜欢听鬼故事,这些都是《子不语》鬼故事的来源。袁枚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他笔下的鬼充满了多重含义,有童子作《讨蚊檄》云:“成群结队,浑家流贼之形,鼓翅高吟,满眼时文之鬼。”盖憎其师之督责时文故也。语虽恶,恰有风趣。所以世上先有这样的事情,才有这样的文章去表达,《子不语》不是无根之树,无水之源,而是对生活的“摹写”,这也是《子不语》的唯物主义传统,显示出袁枚思想观的进步性。
二、真实的再现当时的人情世态
《子不语》是志怪小说,内容是荒诞不经的鬼怪世界,神仙妖怪,狐精鬼魂等超现实的东西,写的都是彼岸世界的人,但并不意味着不真实,《子不语》正是通过艺术的想象和虚构展示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情世态,写出了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关系。以“极近人之笔”写“极骇人之事”。
在《蒋厨》这篇文章里,作者就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当权者昏庸无能的现状,借鬼神之口讽当世之事:“常州蒋用庵御史家厨李贵,取水厨下,忽中恶仆地。召巫视之,曰:‘此人夜行冲犯城隍仪仗,故被鬼卒擒去。须用三牲纸钱祷求城隍庙中西廊之黑面皂隶,便可释放。’如其言,李果苏。家人问之,曰:我方汲水,忽被两个武进县黑面皂头来拿去,说我冲犯他老爷仪仗,缚我衙门外树上,听候发落。我实不知原委,今日听他二人私地说:‘李某业已尽孝敬之礼,可以放他回去,不必禀官。’将我解去索子,推入水中,我便惊醒。’御史公闻之笑曰:‘看此光景,拿时城隍不知,放时城隍不知,都是黑面皂隶诈钱作祟耳。谁谓阴间官清于阳间官乎!’”
作者直接批判了官僚的腐败无能,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丑恶现象,作者假托鬼神讽刺着朝廷命官的无能腐败,完全是现实社会的翻版。《赵友谅宫刑一案》讲述了一个父亲拿刀强行强奸了他的媳妇,后来还与人同谋杀人,把杀人结果转嫁到自己儿子身上,真实的再现了此等凶恶已极之人, 不独无人伦道德可言, 连人性亦不复存在了。《叶氏姊》讲述一个丈夫嫌弃自己的妻子长得丑,连同自己的儿子一并杀掉了。《石灰窖雷》讲述女儿女婿担心父妾生子后分其家财, 便贿赂接生婆在其生产时害死婴儿, 全不念父女翁婿之情。这一系列的“极骇人之事”都是现实中人性丑恶和道德沦丧的表现。
杭州闵玉苍先生,一生清正,任刑部郎中时,每夜署理阴间阎王之职。至二更时,有仪从轿马相迎。其殿有五,先生所以莅,第五殿也。每升殿,判官先进铁弹一丸,状如雀卵,重两许,教吞入腹中,然后理事,曰:“此上帝所铸,虑阎罗王阳官署事有所瞻徇,故命吞铁丸以镇其心,此数千年老例也。”先生照例吞丸。审案毕,便吐出之。三涤三视,交与判官收管。所办事晨起辄忘;即记得者,亦不肯向人说,但劝人勿食牛肉,多诵《大悲咒》而已。
到任三月,忽一日晨起召诸亲友而告曰:“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为也。昨晚吾表弟李某死,生魂解到,判官将其生平作官恶迹,请寄地狱审定拟罪,再详解东岳。余心恻然,将狱牌安放几上,再三目李。李自诉平生不食牛肉,作官时禁私宰尤严,似可以此功德抵销他罪。余未作声,判官驳云:‘此之谓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独食人肉?’李云:‘某并未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即人肉也。汝作贪官,食千万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细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答。余知李素诵《大悲咒》,为阴司所最重,因手书‘大悲咒’三字在掌上以示之。李竟茫然,不能诵一字。余为代诵数句,满堂判官胥役一齐跪听,西方赫然似有红云飞至者。然而铁丸已涌起于胸中,左冲右撞,肠痛欲裂矣。余不得已急取狱牌加朱,放李狱中,肠内铁丸始定,方理别案而归。”
诸亲友因问:“到底牛肉可食乎?”先生曰:“在可食不可食之间。”人问故,曰:“此事与敬惜字纸相同,圣所未戒,然不过推重农重文之心、充类至义之尽,故禁食之者,慈也。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语久被老子说破。试想春蚕作丝,衣被天子,以至于庶人。其功比牛更大,其性命比牛更多,而何以烹之煮之,抽其腹肠而炙食之,竟无一人为之鸣冤立禁者,何耶?盖天地之性人为贵,贵人贱畜,理所当然,故食牛肉者,达也。”(《阎王升殿先吞铁丸》)
这里写的官场黑暗也是现实生活的映射,作者做县官多年,熟知官场中人的奸诈,通过鬼的代言真实地再现现实的社会黑暗和世态炎凉,通过善恶报应也寄托了现实生活中人民的美好愿望,这些都是现实人情世故的翻版。
袁枚在写传奇性的同时把小说的真实性放在第一位,突出了小说要写出社会关系的“真情”,写出“人情物理”,再三突出小说的传奇性不能脱离小说的真实性。
三、寄鲜明真挚的情感于作品中
中国小说美学强调,小说创作者要有鲜明的爱憎情感,李贽提倡的“童心”说就是讲的要有真感情,要有强烈的爱憎,“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5]。这里所说的“童心”就是真心,就是真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提出“为情造文”,《毛诗序》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些都强调了情感的重要性。真情是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具备了真情,才能使文艺作品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著名小说美学家金圣叹提出的“发愤作书”“怨毒作书”等等都是同一意思的表达。《金瓶梅》在描述世俗生活的同时抒发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如西门庆之流的愤懑之情,可以看作作者的泄愤之作,《红楼梦》更是曹雪芹强烈真实情感的表达,是“滴泪为墨,研血为字”。
图4是800 ℃下,C钢渣和S钢渣摩擦系数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从曲线可以看出,C钢渣的摩擦系数为0.26~0.43,平均摩擦系数为0.343,具有较低的摩擦系数;S钢渣的摩擦系数为0.22~0.47,平均摩擦系数为0.312。从曲线来看,C钢渣的摩擦系数较为稳定,在0.35附近浮动,S钢渣的摩擦系数波动较大。C钢渣和S钢渣均呈现出良好的抗磨损性能,是因为钢渣硬度高、含铁量多[19]。
作家这些强烈的爱憎最终都指向社会,是对社会的批判和评论。金圣叹的“发愤”包含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其发愤与“入世”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经历过穷困潦倒,经历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才可能“发愤”,才可能有深刻的主观的“积愤”。
袁枚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滋长,袁枚一生特立独行,对程朱理学“禁人欲”“存天理”等主张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认为他们是假道学,是不符合人性的。袁枚高举“性灵”旗帜,大力提倡“真情真性”,袁枚“ 性灵说”的核心就是重真性情、崇尚个性。“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并讥讽摹拟派文人“天涯有客号痴詅,误把抄书当作诗”。下面我们具体阐发下袁枚在《子不语》中抒发的几种不同类型的感情。
(一)对男欢女爱自然之情的歌颂
袁枚一向认为男女之情是人的情感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感情,食色性也,在那个程朱理学盛行于世的时代,袁枚以“性灵”为武器,大力提倡男女之情。袁枚的诗歌理论中直接提出作品由情产生,其《答敲园论诗书》说:“且夫诗者由情生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这段文字不仅点明诗由“情生”,而且认为情感是作品价值和生命力的表现。男女之情是人生中自然合理的存在,马克思说:“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5]恩格斯说:“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这些都说明了真情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子不语》里对男女之真情描写甚多,尽管人鬼殊途,但仍然阻挡不了男女相爱,阻挡不了男人对美色的追求沉溺。
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三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下山。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
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沙弥思老虎》)
这篇小说充分说明男女之情是没法压抑的,是天然的是人的自然欲望,是人的本能本性。
(二)对黑暗现实愤懑之情的抒发
慈溪袁如浩游幕西江,与宁都州程牧交好。乾隆三十一年,程公委署饶州府篆,邀如浩偕往。时郡署新遭回禄,前太守某被焚身死,程公到任,修葺尚未告成。
夜间,如浩持灯往厕中,遇一人年三十许,衣月白衫,举头望月,若有所思,惟下体所著鞋袜,模糊莫辨。见如浩至,拱手问讯。审其音,杭州人也,自言周姓,字澹庵。如浩因署内并无是人,诘所自来,乃欷歔告曰:“我非人,乃鬼也,我系前任司钱谷幕友。上年饶郡被灾,太守某侵蚀赈粮,郡民聂某率领三十余人赴部告准,蒙发本省大宪审问,吊核赈册。不料,太守已早捏造印簿,升斗出入,皆有可凭。大宪为其所欺,遂将数人问成诬告,即行正法。此辈怨魂上诉都城隍,牒阎罗审讯,我系幕友,故被株连,又值公事甚忙,正在查办饶郡灾民册子,候至月余,始得审明,太守某冒赈是实,又冤杀数人,即遣鬼隶擒缚放入火中,以故在署烧死。我非同谋,罪虽获免,而皮囊已腐,不能还魂,只得稽留在此。因停厝处被瓦木匠溲溺,终日秽杂,坐卧不安,先生肯为我移至郊外,含恩不浅。”言讫不见。
如浩次日寻至署后,果见黑漆棺一具停在墙边,诸工作人在旁喧嚷,遂告知主人,舁至城外,择地掩埋,作文祭之。(《饶州府幕友》)
这篇小说里太守在大灾之年反而吞噬赈粮。百姓告发不但没得到赈粮,反而被太守捏造印薄,把告发之人问成诬告,即行正法,这些都是现实社会的写照。作者以艺术的虚构和夸张进行了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封建官吏腐败丑恶嘴脸的愤懑之情,并且通过作者的想象宣扬了善恶有报的美好理想。
杭州钱塘邑生张望龄,病疟。热重时,见已故同学顾某者踉跄而来,曰:“兄寿算已绝,幸幼年曾救一女,益寿一纪。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特来奉探,为地方鬼棍所诈,诬以平素有黯昧事。弟大加呵饬,方遣之去,特诣府奉贺。”张见故人为己事而来,衣裳蓝缕,面有菜色,因谢以金。顾辞不受,曰:“我现为本处土地神,因官职小,地方清苦,我又素讲操守,不肯擅受鬼词,滥作威福,故终年无香火,虽作土地,往往受饿。然非分之财,虽故人见赠,我终不受。”张大笑。
次日,具牲牢祭之,又梦顾来谢曰:“人得一饱,可耐三日;鬼得一饱,可耐一年。我受君恩,可挨到阴司大计,望荐卓异矣。”张问:“如此清官,何以不即升城隍?”曰:“解应酬者,可望格外超升;做清官者,只好大计卓荐。”(《土地受饿》)
这篇小说隐晦地反应了现实社会官场的复杂性,作者当了几年县官,深知清官难当,通过这篇小说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讲操守,不欺诈老百姓的官,不但自身温饱问题没法解决,更不可能升官,反而那些贪官污吏,收刮民脂民膏的官员升迁还很快,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官场这种畸形现象的强烈讽刺之情。当时社会官场内部互相勾结,任由下属敲诈老百姓,“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就是当时社会贪官污吏贪污腐败的真实写照,作者对这种现实是非常愤懑的,正因为有强烈的爱憎感情,写出来的作品才能触动人心,让我们看到清朝盛世下的阴影。
其他如《阎王升殿先吞铁丸》,一针见血指出贪官搜刮民脂民膏就是“食人肉”,鱼肉百姓;《锡锞一锭阴间准三分用》则暴露了当时社会连小小的门卫都受到了污染,通报事情勒索通报钱的恶习,“非重用门包,不能通报”;《蒲田冤狱》更是写出了草菅人命,胡乱判案的黑暗官场:土豪王监生贿赂县令,霸占了邻居老妇人的五亩地,并残忍地杀死了老妇人,又诬谄老妇人之子是凶手,后来老妇人之子也被凌迟处死。这些故事都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批判之情,作者两度出山,两度隐居,对官场的黑暗深有体会,通过艺术的虚构抒发了作者内心真实的感情。
(三)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辛辣讽刺
袁枚的姐姐妹妹中,三妹袁素文和他关系最好,最能心灵相通,小时一起玩耍嬉戏跟着他一起学习。素文深受封建礼教熏陶,遇人不淑,惨遭丈夫虐待却始终不知反抗,最后差点被自己丈夫卖掉,被接到娘家后终日以泪洗面,最后郁郁而终。这件事对袁枚的打击很大,作者悲愤不已,著名的“祭妹文”那发自肺腑的思念和悲伤让一代一代读者心酸不已,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荡山茶肆全姑,生而洁白婀娜,年十九。其邻陈生美少年,私与通,为匪人所捉。陈故富家,以百金贿匪。县役知之,思分其赃,相与牵扭到县。县令某自负理学名,将陈决杖四十。女哀号涕泣,伏陈生臀上愿代。令以为无耻,愈怒,将女亦决杖四十。两隶拉女下,私相怜,以为此女通体娇柔如无骨者,又受陈生金,故杖轻扑地而已。令怒未息,剪其发,脱其弓鞋,置案上传观之,以为合邑戒。且贮库焉,将女发官卖。
案结矣,陈思女不已,贿他人买之,而己仍娶之。未一月,县役纷来索贿,道路喧嚷。令访闻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败絮草纸置裤中护其臀。令望见曰:“是下身累累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裤中物,亲自监临,裸而杖之。陈生抵拦,掌嘴数百后,乃再决满杖。归家月余死,女卖为某公子妾。
有刘孝廉者,侠士也,直入署责令曰:“我昨到县,闻公呼大杖,以为治强盗积贼,故至阶下观之。不料一美女剥紫绫裤受杖,两臀隆然,如一团白雪,日炙之犹虑其消,而君以满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烂桃子色。所犯风流小过,何必如是?”令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行当有报矣!”奋衣出,与令绝交。
未十年,令迁守松江,坐公馆,方午餐,其仆见一少年从窗外入,以手拍其背者三,遂呼背痛不食。已而背肿尺许,中有界沟,如两臀然。召医视之,医曰:“不救矣,成烂桃子色矣。”令闻,心恶之,未十日卒。
作者在小说里辛辣的讽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全姑》里的县令不过是个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的无耻之徒,当他得知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并私通,就把他们抓起来,各打了四十杖,而且把少女头发剪掉,鞋子扒去,后来得知二人竟结为夫妻,大怒,又把二人抓来,把男子打死,女子发官卖,还振振有词:“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这就把一个理学家不通人性的面目栩栩如生地勾勒了出来,作者后面以艺术虚构对这个无耻之徒进行了惩罚,取了他的狗命,充分表明作者对这些虚伪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的愤懑之情。
在《麒麟喝冤》中批判了汉儒“造作注疏,穿凿附会”,又幽默地勾勒了宋儒扛起“稻桶”(道统)“捆缚聪明之人”的形象。同时,他反对宋儒提出的礼教。《替鬼作媒》反映了作者赞同寡妇再嫁的观点;《裹足作俑之报》反对妇女裹足;《淫谄二罪冥责甚轻》为“妇女失节者”辩护。
总之,《子不语》表现了大量的小说美学原则,社会生活是小说产生的基础,小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必须具有真情实感,表达出作者真实的愤懑之情才可能感动读者;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迂腐的科举制度,黑暗的社会现实,炎凉的世态人情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作者把赤裸裸的残忍的现实生活展示给世人看,用冷静的近乎客观的叙述达到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们看,这样更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愤懑之情,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袁枚所处的社会现实,于荒诞中揭示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于虚幻中展示了丰富的美学思想,这正是《子不语》的价值所在。
[1] 孔子.论语·述而[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3]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袁枚.随园诗话[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5.
[5] 李贽.明清文选[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朱丕智]
Aesthetical Thought of
Li Tian Dao, Tang Jun Hong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literature of academicCHENGDU, SICHAUN, 610066
< Zi Bu Yu >; aesthetical thought of novel; emotion
2016-12-05
李天道(1951-),四川彭州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唐君红(1977-),四川达州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专题研究”(13AZD029)阶段性成果。
II01
A
1673—0429(2017)01—0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