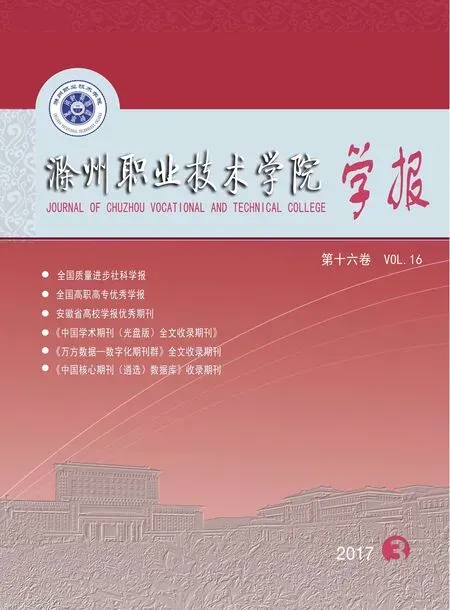浅谈王安忆《长恨歌》的意象经营
2017-03-28陈妍,任强
陈 妍,任 强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浅谈王安忆《长恨歌》的意象经营
陈 妍,任 强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和“王琦瑶”这五个平行意象开篇,形形色色的弄堂最突出的特征是波涛汹涌的“暗”,神性精灵的鸽子窥探着人世间的变化,沪上淑媛王琦瑶没能在单薄脆弱的友情与亲情中找到感情的依托和归属感。小说通过象征与隐喻、诗性与理性交融的语言,营造出独特的审美意象,呈现出别样的审美意蕴。
《长恨歌》;王琦瑶;意象;审美意蕴
王安忆《长恨歌》的开篇非常独特,第一部首先用整整一节对“弄堂”展开描述[1],随后第二节“流言”、第三节“闺阁”、第四节“鸽子”,直到第五节主人公“王琦瑶”才出场。这五个物象作为旧上海的象征物,被作者纵横铺叙,精雕细刻,“繁琐地铺叙着生活的细枝末节,仿佛是阳光光柱里显形的尘埃”[2]。王安忆用一支绚烂的笔,塑造了王琦瑶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将40年间上海的时过境迁变现得淋漓尽致。
一、《长恨歌》中的弄堂和鸽子意象
(一)弄堂——寄托怀旧情思
最能寄托人们怀旧情思的,建筑当之无愧。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曾说:“任何一个城市,他独有的历史都是他的性格史和精神史。文字的历史只能启动想象,建筑的历史才是摸得着的物证。”[3](8)在王安忆的笔下,所关注的正是大上海最古老、最普通的弄堂。
“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里”的概念,顾炎武《日知录》里说:“以县统乡,以乡统里。”[4]对于“弄”的记载,可追溯至《上海县志》,是人们对街巷的方言称呼[5]。杨东平在《城市季风》里曾总结道:“在长达百年的岁月中,上海逐渐形成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区四类居民建筑……里弄住宅则是最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居所,是城市建筑的主体和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载体。”[6]161
茅盾《子夜》里的上海是一个商业大都市,而作为王琦瑶四十年故事发生的主场景,王安忆首先对弄堂的全景描绘了个概貌,那就是“暗”。小说用“像深渊一样”,“像是藏着许多礁石”等形象,描绘了“波涛汹涌”的“暗”。随后,又从整体上对弄堂进行了勾勒:黑色的屋顶,细工细排的瓦,精雕细作的老虎天窗,窗台上的月季花,生了锈的黑铁栏杆,晾衣服的竹杆,裸露出斑驳痕迹的山墙。作者还花了一整段的篇幅来阐述弄堂的性感、带有私情味这一特质。在弄堂里,作者笔触所及之处,无不罩上了一层暧昧的色彩。
“‘上海弄堂'是王安忆最熟悉的地方,是她小说‘地方性'之所在。”[7]弄堂是最接近上海日常生活的“芯子”,作为上海居民赖以生存的私密空间,里面充斥着最真实的上海人的生活,隐藏着形形色色的人生。“要表现上海城市形象文化气质的变迁,弄堂实在是一个绝佳的视角,它最能从底层也最能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反映上海的历史变化。“[8]由于弄堂结构上纵横交织,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生活在这张大网中的人们难免要受到真假难辨的流言的侵扰,上海小姐深闺里的故事也会随之飘向社会,弄堂也被视作各式各样的上海小姐的成长地和流言滋生所。作者不厌其烦地对弄堂作铺叙,在“弄堂”这一小节最后,又用了一个自然段来引出“流言”和“闺阁”两个意象。
(二)鸽子——城市的精灵
鸽子像一只有神性的精灵,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穿梭,它们有时会在至高处俯瞰,窥探着屋檐下的一举一动,它们的目光扫荡着弄堂里外、大街小巷,深入探访在弄堂外壳包裹下的人们的内心世界,捕捉一个城市中最深藏不露的、非同寻常的事情,机警敏锐地将这一场场人类世界的悲剧、人与人之间持久的恨意释放出来。在这一个绝佳的俯瞰全城的精灵背后,有作者对上海城市整体的概观,作者通过鸽子的视角,传达出了独具特色的上海景观。鸽子,它们在大街小巷的上空穿梭,却能敏锐地捕捉到繁华背后的生命原始姿态。文中这样写到:“大街上的景色为它们熟视无睹,它们锐利的眼光很能捕捉特别的非同寻常的事情,它们的眼光还能够去伪存真,善于捕捉意义。”[1]16
随着作品意象叙事的展开,鸽子也为烘托情节造势,原本凝固的时空霎时间灵动非凡。例如,文中追随鸽子的三起三落,仿佛在这三道弧线下完成了对整篇文本的串联。很多情况下,鸽子起到延伸叙述视线和推进故事情节的微妙作用。鸽子的眼睛,仿佛是一个广角镜头,叙事空间在镜头流转间无限放大,甚至于它们的视角一再穿透屋顶,探察屋内。鸽子见证了许多重要的镜头:程先生对王琦瑶苦苦的等候,王琦瑶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下无法平息的内心,还有结尾处王琦瑶悲惨的死亡场景……鸽子的意象真实地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目的就是见证上海的变迁,记录王琦瑶的一生,它们的眼睛犀利敏锐,是对残酷而又现实的人性的指证。
二、王琦瑶——一首无尽的悲歌
(一)可望而不可求的爱情悲剧
当选了上海小姐的王琦瑶,曾被有权势的李主任看中并住进了爱丽丝公寓,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她甘心做一只金丝雀,在李主任的庇护下安静地生活,摆脱平淡的闺阁生活。然而,她不知实际是在用自己的一生作赌注,李主任并不是他的真命天子,他将别人的命运拿去,却给不了负责。所有的荣华富贵,随着李主任的意外身亡而成为镜花水月了。
当程先生出现并用一生要来守护王琦瑶,得到的确实王琦瑶拿他做垫底的结局。聪明的王琦瑶,曾细细做过比较,程先生体贴温柔,却满足不了她对物欲的追求,只能是他感情世界的一个俘虏。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王琦瑶身上根深蒂固的优雅深深吸引了年轻人老克腊。老克腊积极热情,但年龄的差距使这份感情无疾而终,留下的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象。
自始至终,王琦瑶都抓不住一个能与她天长地久,死生相约的人,她只有孤身一人,独自承担起抚养女儿的责任。她那颗孤芳自赏的心在一次次地回归寂寞后变得彻底的无依无傍,面对可望而不可求的爱情,她仿佛一只任意东西的孤舟,尽管有时漂流到能让她暂时栖息的码头,然而命运之缆终不能系牢,漂泊与孤独是她永远的宿命。
(二)毫无沟通的友情亲情悲剧
王琦瑶的生命中也出现了许多影响至深的女性形象,学生时代的同学吴佩珍甘心做她的绿叶,而孤傲的王琦瑶不会被这点小恩惠所吸引,她有自己的打算和心思,于是在试镜头事件后,吴佩珍淡出了他的生活。在与蒋丽莉交往中,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二人本没有情感的共鸣,她们是活在梦想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类人,脆弱的友情也因程先生进入这段三角关系后而终结。
回到了平安里的王琦瑶,曾与严家师母交好,一日三餐,牌局聚会,二人形影不离。而当严家师母发现自己的表弟康明逊竟不理会她那一套“面子”的理论,与王琦瑶私下里约会,她和王琦瑶的这段姐妹情也随之告终。
王琦瑶与女儿的关系更是值得深思,王琦瑶倾其一生,换得一盒金条和一个女儿,母女二人理应惺惺相惜,但就连那最后的一点亲情上的联系,都被种种无法沟通的隔阂彻底瓦解。作为母亲,王琦瑶是不成功的,她的母性建立在保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
整部作品中,这些女人曾真实地存在于王琦瑶的生活中,却都是转瞬即逝。在她们不知底细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处心积虑地交往,这种人际关系看起来是冷酷无情的,但在都市商业社会中却又是是自然的。王安忆曾评价上海人是“现实的,有实用精神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的群体。[9]生活在这种极度缺乏亲情、友情、爱情的温暖的环境下,王琦瑶不得不随时伪装自己,还要存着一份心思,于是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孤独。
三、《长恨歌》的意象表现
(一)象征与隐喻的审美意蕴
萨特认为“意象的功能是象征性的”,隐喻和象征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10]。《长恨歌》中意象众多,贯穿文本的始终,意象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象征意蕴,起到了隐喻人物命运和身份,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第一部中看似没有关联的繁琐叙述,其实是统摄整本著作的点睛之笔,是作者对叙事结构的精心安排。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的生活轨迹都是围绕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展开的,故事的发展与终结都能够在开篇的描绘中找到宿命般的暗示与想象。
先以“弄堂”这一意象为例,作者一开篇就为我们营造了“暗”的基调,低沉忧郁的情结在文中反复渲染开来,例如“在片厂的昏暗灯光下”、“在爱丽丝公寓惟幔笼罩下”、“在平安里灯光摇曳里”,文中描绘的不明丽的景象俯拾皆是,这种暗的描写,隐喻着女主人公的生存空间,指向其人生悲剧的深层意识。再说“鸽子”的形象,“它们是唯一能够俯瞰上海的活物,是见证一些无头案的证人”[1]14。这看似不经意的说明和交待,其实是浓缩了故事的发展情节。鸽子的每一次出现,总是带着哀伤的情绪,预示着死亡,象征着这座城市罪罚祸福的发生。“文革”期间,程先生选择从高楼跳下结束生命时,只有破晓时惊飞的鸽群看得清楚真切;蒋丽利的死和王琦瑶痛苦的分娩,鸽子目睹了整个过程;整本书的结尾处,当王琦瑶因为苦守的金条而祸起萧墙,被长脚杀害时,只有鸽子作了见证,这城市的隐秘和冤情都被鸽子尽收眼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在开篇的意象经营其实是预先为书写上海这座城市创造了一种细腻绵长而又悲凉冷峻的气氛。这样的设置,既点明了小说的叙事视角,也确定了文章的叙事基调,故事还未开始,读者就已经感受到那挥散不去的浓浓情调,人物命运的演进也可以略知一二。
(二)诗性与理性的语言表达
作为王安忆叙述语言中的极致,《长恨歌》呈现出来的密密麻麻的意象描写和她充满诗性与理性的语言表达,引领读者进入了一个冷静细腻的女性世界。王安忆说:“《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11]王安忆也曾强调:“我近来常常感到所谓写小说,就是一定要把小说的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区别开来。”[13]她笔下的文学作品,常自觉不自觉地融入散文化的语言特色,《长恨歌》的众多意象,透过王安忆对生活饱含诗意的眼光,经由她散文式的语言加工,事无巨细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有学者评价,《长恨歌》给人的印象是叙述风格单调沉闷,语言更是平淡无奇,甚至于烦琐絮叨。但细读全篇后,又深深折服于这种密如针脚的描写中传达出的艺术光彩。
《长恨歌》里,不仅有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更有一群带有相同烙印的鲜活的女性群体,她们是王安忆寻求的生活中最实在的依托。作者在《王安忆说》中回忆自己随革命大军进驻上海的经历,认为自己是上海的“外来户”,身份的危机感,家族记忆的缺失,使王安忆确立了对于历史与现实冷静而审慎的创作姿态;知识分子客观的体察视角,也决定其“对自身外的世界与人性作广博的研究,这便可以达成真实的自我与提高的自我之间审美的距离,理性的距离与批判的距离”。[9]《长恨歌》中的意象描写,一方面,由于王安忆独特历史观的影响,体现在对叙事方式的选择上呈现出的宁静深沉之美;另一个方面,王安忆的创作中渗透着对日常生活的理性思考,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种种物像中,发掘出掩映在事物表象下的人性的本真,展现她特有的人文情怀,于平淡中回味无穷,于平凡处充满智慧。
[1]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2]高侠.王安忆小说叙事的美学风貌[J].当代文坛,2000,(04):22-26.
[3]冯骥才.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虑[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上海市上海县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县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杨东平.城市季风[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7]程旸.王安忆小说与“弄堂世界”[J].文学评论,2016,(02):188-194.
[8]谢清.论王安忆上海题材小说创作意图嬗变[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91-94.
[9]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10]萨特.想象心理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11]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N].文学报,2000-10-26(02).
[12]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13]陈思和,王安忆,郜元宝,等.当前文学创作的“轻”与“重”-文学对话录[J].当代作家评论,1993,(05):14-23.
I206
A
1671-5993(2017)03-0088-03
2017-04-25
2013年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重大教育改革研究项目“构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师教育本科课程体系的实验与研究”(项目编号:2013zdjy176),2014年度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卓越语文教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编号:2014zjjh017),阶段性成果。
陈妍(1991-),女,安徽合肥人,淮北师范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语文教育。任强(1966-),男,安徽濉溪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