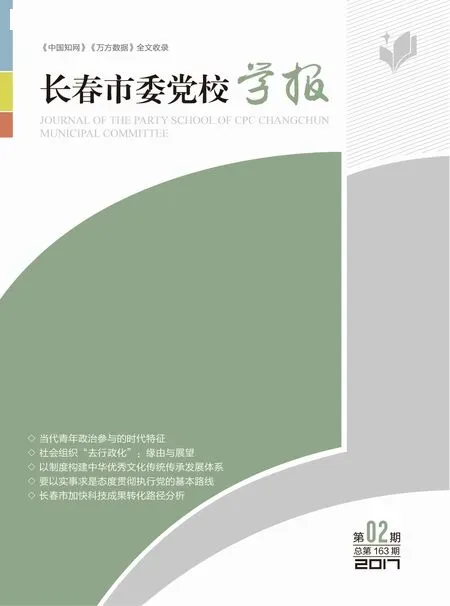张闻天建构文化自信的价值维度和实践向度
2017-03-27马孟庭
文/马孟庭
张闻天建构文化自信的价值维度和实践向度
文/马孟庭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是党内负责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领导人。文化自信既表现在他的理论中,又表现在他的行动上。在延安时期,为了唤醒民众抗日救亡的意识,张闻天以文化为突破口,将全党的中心任务定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极大提升了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在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压力下保持着本民族文化顽强的生机与活力。
张闻天;文化自信;文化建设
一个民族复兴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这其中的支撑力量即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能力的坚定信念。延安时期,张闻天面向革命现实,对建立民族新文化与重拾文化自信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为团结抗日,他提出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并深入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新文化建设以及建构文化自信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价值维度:阐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功能与时代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讲,建构文化自信的价值维度即对所要推崇的文化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进行判断。张闻天对民族新文化建设的功能与时代意义有准确的定位,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与价值关怀共同构成其价值维度的主要内容。
●价值目标:服从于抗战救国的需要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抗战救国,建立服务于此目标的民族新文化是文化建设的直接目的。
在东北,日本不仅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与军事控制,而且还实行深层次的文化侵略。一方面破坏文化名城与古建筑,掳掠中国文物,另一方面在沦陷区实行文化专制、推行奴化教育,迫害进步人士。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势力力图借助宗教麻痹人民,“使各宗教信徒成为日本的顺民” 。[1](P362)长期的殖民统治,对青少年的成长极为不利,奴化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也只能是效忠日本的顺民与知识分子。
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展,国民党仍旧实行专制独裁,鼓吹一党独大;在军事上,坚持片面抗战路线,高度依赖外来援助,使得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损失惨重。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坚持在抗战面前没有党派之争与阶级差别,无论来自哪个党派所属哪一阶级“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 。[2](P38)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广泛的抗日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战的热情,而且使得其政治权利思想和民主思想大大加强。通过抗日与民主的国民教育,人民群众改变了过去依赖式的思维定式。在军事和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了预期的目的,人民群众普遍拥护抗日、拥戴中国共产党。人民的呼声与诉求对国民党构成了外在的压力,正是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才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一结果的产生,也促使共产党人更加致力于抗日与民主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
●价值尺度:坚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文化发展方向问题是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一度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从思想界的纷争来看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派是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他们极力贬抑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充分学习西方文化。他们认为,西方文明为中国文化自信的建立提供了充足的给养,要想建立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必须全盘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另一派是以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为主力的“本位文化派”。他们提出“民族自信力的表现”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而非全盘西化的推行,要建设本位文化必须坚持“不守旧;不盲从”的基本原则,而最终目的即“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力”。[3]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关于何为本位文化、文化建设的方法等鲜有论及。
在激烈的争论中,张闻天对这一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针对建立新文化的方法。一方面,他并没有否定“全盘西化派”中“西化”的观点,也没有批判“本位文化派”中“本位”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忽视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不管是学习外来文化派还是发展传统文化派,都仅仅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在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中,一切能够有助于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因素都可以吸收到新的体系中。对于外国文化,张闻天对其成分进行合理区分,认为“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可以看作新文化的养料,[2](P27)但是外国文化中的反动文化则是必须抵制的。对于旧文化,张闻天认为其中有与社会性质相伴而生的腐朽的文化,如鲁讯所言“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 ,[2](P27)这部分文化不甘自我毁灭正垂死挣扎,这是构建民族新文化的主要障碍。但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子,我们需要珍视并将其传递下去。在此基础上,张闻天提出应该“批判的接受旧文化”,以促进新文化向纵深方向继续发展。
●价值关怀:正确对待文化人和文化团体
在革命时期,在对待文化人与文化团体方面党曾犯过“左”的错误。党内存在看不起文化人的现象,低估知识成果对于革命发展的价值,一度出现用行政强制手段干预文化人进行正常创作的情况,对其劳动成果也未能给予正确评价,并提出文化人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应与其他人一致化等要求。对文化团体,党内某些干部要求与其他群众性组织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布置较多的硬性任务,剥夺团体活动的机会。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党内存在严重的“左”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存在误区。张闻天深知,文化人与文化团体是新文化建设的依靠力量,离开他们新文化建设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获得长足发展,更别说实现建构文化自信这一目标。因此,张闻天在对待文化人与文化团体问题上,一方面致力于纠正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扫除新文化建设的思想障碍,另一方面让领导干部对文化人、文化团体重视起来。张闻天曾说,在战时,全党“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2](P77)可见发展文化以及文化人在他心中的地位。当然,纠“左”并非阶段性工作,在这时所开展的纠“左”工作也非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但是在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形势下,这一工作具有战略层面的意义。应该说,“张闻天在文化领域中的纠‘左’,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4]
二、实践向度: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基本方法与推进路径
张闻天提出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基本方法与具体路径,包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广泛发展区域文化运动。
●关于抗日战线:从单一战线到双重战线转变
陈先达先生提出,真正的文化危机是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出现而出现的,[5]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益加深。针对愈演愈烈的文化危机,中国共产党提出应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战线相配合。
张闻天提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2](P38)这是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总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前,党内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法存在较大分歧。不少人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难以固守阵地,会给革命带来危险。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是建立联合各阶级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基于此,张闻天从文化的特点入手,阐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在承认他们缺点的基础上对其优点进行肯定。例如,他指出文化人有实现理想的强烈追求与为之奋斗的毅力,但部分人仅仅是“感情冲动”而非实际行动;单独的工作环境有利于他们创作但是会造成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等。但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抹杀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应针对他们的特性采取不同以往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关于组织的具体形式,张闻天提倡形式多样化,诸如“文学研究会”“新哲学研究会”等组织可以根据抗战需求灵活组建,且文化组织的数量不在多而在精;就活动方式而言,他认为不应与行政机关等同,不能用“条条框框”规定文化人的活动,而应为他们创作提供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自行创作。与此同时,应避免知识分子出现自视清高的错误倾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战线的建立既联合了党内作家,也联合了党外作家;而且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战线的巩固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关于知识分子:从怀疑排斥向接纳重用转变
延安时期,革命面临新形势,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针对特定情形,张闻天提出“今天所有新文化运动者最严重的任务”[2](P40)是争取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抗战队伍中去,这标志着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还没有能够培养出与自身利益要求相一致的知识分子,对于现有人才,如果能够将他们吸引到革命阵营中,对于革命和建设都是有利的。张闻天提出广泛吸收知识分子,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并提出相应的措施。首先,要从他们的实际需求出发,解决他们自身较为关注的问题;其次,通过学校教育与刊物的传播,提高他们马列主义修养;再次,党的相关工作中也可以吸纳知识分子并将他们培养为党的合格的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最后,根据知识分子的特长分配特定的具体的工作,如负责文教工作、扫盲工作、创办期刊等,做到人尽其才。
张闻天认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造就了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为了找到正确的出路,对于反帝反封建,他们有着迫切的要求。如果能够对其进行号召加以引导,则他们很容易加入革命的队伍,转变为一名革命工作者。
●关于文化运动:从重根据地向根据地与国统区并重转变
针对文化运动这一问题,张闻天于1940年起草了《发展文化运动》的文件,这是党内关于此项活动的指导性文件。其中,张闻天认为文化运动的范围既应包括在国民党区域,又应包括各根据地,两地应同时展开此项活动。
“七七事变”后,随着联合战线的不断扩展,国统区的文化运动以及与文化有关的工作也开始开展起来。在抗战救国的社会背景下,张闻天认为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文化运动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2](P76)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国统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公会”)于1940年11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是实践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表现。蒋介石曾提出文化部门只可以进行学术研究而不能够参与政治活动的命令,但是文公会并未拘束于这一条禁令,为了促进广大民众觉醒并投入到抗战活动中去,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出具有能够启迪民智的人物,通过举办演讲等宣传联合抗日的必要性。此外,国统区的戏曲、小说、电影、话剧等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涌现出的较为有名的作品有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北京人》等,推动了国统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文化运动除了在国统区进行,不同根据地的文化运动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在陕甘宁边区,通过社会教育对群众进行有效教育,通过建立识字组与办冬学的形式解决陕甘宁边区存在大量文盲的问题;同时发动抗战文学运动,在一批文学团体的努力下出现了诸多描绘边区军民英勇抗敌的小说,戏曲、美术、音乐等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晋察冀边区,音乐协会与美术协会相继成立。在晋冀鲁豫边区,文学、艺术等发展较快。戏剧是主要代表,全国剧协晋东南分会就在此成立。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开展得最为彻底,最为有效,成果也最为突出。
[1]王道平.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2]张闻天文集(第3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3] 陶希圣,何炳松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J].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1).
[4]侯且岸.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二)——重视在文化建设实践中纠“左”[N].学习时报,2005-10-31(003).
[5]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N].光明日报,2016-11-23(13).
马孟庭,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董金荣
G129
10.13784/j.cnki.22-1299/d.2017.02.008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16BKS034)研究成果;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研究》(14MLA002)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