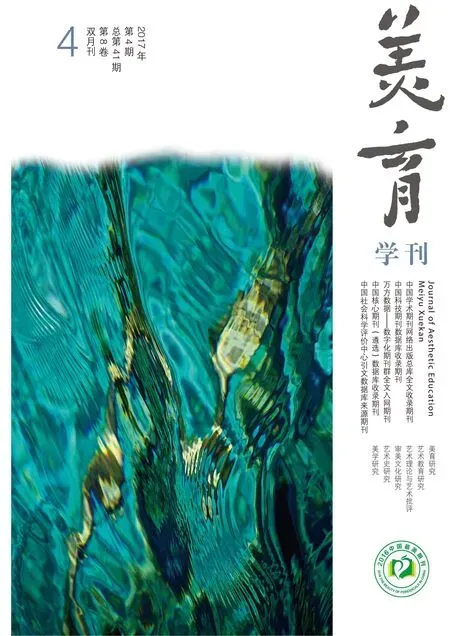近年海内外“坤伶登台”研究热的反思
——兼论“艺术社会学”视野下深化理解的契机
2017-03-24柏奕旻
柏奕旻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近年海内外“坤伶登台”研究热的反思
——兼论“艺术社会学”视野下深化理解的契机
柏奕旻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坤伶登台”是近现代戏剧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近年已成为海内外文艺、文化、历史多领域的研究热点。从方法论视野上,现有研究可分为“性别研究”视野和“社会文化史”视野两大类。性别研究从性别身份议题出发,关注“坤伶登台”现象中女演员的特殊遭际,但多倾向于思想观念的阐发。近来,海内外学界受“新文化史”转向的启发,对话性别研究的同时,以社会文化史视野考察“坤伶登台”的发生机制、女演员的身心状态与身份抗争,但对其身份转换在中国社会历史延续性进程中的意义缺乏观照。基于此,“艺术社会学”视野的引入,强调以底层性、乡土性为核心的研究,能够对前两种路径形成双重反思,同时提供深化理解“坤伶登台”的新契机。
坤伶登台;性别研究;社会文化史;艺术社会学
中国传统戏曲浸润于普通百姓生活,在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传统及近现代社会,主要承担充实民众生活与精神教化的功能,因而是考察特定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社会文化趣味、风俗变迁以至经济、政治状况时,难以回避的大众文化载体。“伶人”是传统戏曲的表演者,对他们的命运沉浮、从业状况的研究,内在扣连于上述议题。
近年来,“坤伶登台”这一近现代文化现象已成为海内外文艺、文化、历史多领域的研究热点。坤伶登台,指的是晚清以降中国伶人群体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即大规模的职业戏曲女演员*“(戏曲)女演员”是相对中性的称谓,指涉以戏曲表演为业的女性。“坤伶”是清末民初对女演员最常用的称谓,“坤伶登台”是对戏曲女演员大规模登台这一历史事件加以提炼的说法。群体开始形成。“坤伶登台”研究热的重要特征在于将它视为观照晚清民初中国社会内在转变的切入口。这些研究集中考问了该现象为何出现、对戏曲界和社会受众产生何种影响、戏曲女演员发生怎样的命运遭际等问题。
从方法论视野上,现有研究可分为“性别研究”视野和“社会文化史”视野两大类。性别研究视野为理解“坤伶登台”提供了性别身份议题的解释路径。而海内外学界近来受“新文化史”转向的启发,在对话性别研究的同时,亦在讨论“坤伶登台”的发生机制及其历史过程方面取得的不少代表性成果。本文对研究热的现有成果在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反思,关注其对加深“坤伶登台”历史理解的贡献,并经由反思其问题意识与方法,指出“坤伶登台”研究的核心议题是身份问题,以及伴随社会身份问题而引发的抗争实践问题。本文从此核心议题切入,讨论研究热的不足,探讨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契机。
一、身份政治与观念图绘:性别研究视野下的“坤伶登台”
性别研究为进入“坤伶登台”问题提供启发。这些研究以戏曲女演员为研究对象,意味着近现代戏曲研究的关注点,不仅从研究“物”转向研究“人”,还进一步实现从“伶人”研究向“女性伶人”研究的问题意识突破。
将“坤伶登台”作为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的有机部分加以考察,台湾地区学人对此作出了独特贡献。其中,周慧玲是较早敏感于“坤伶登台”现象的历史意义,并力图从性别研究角度切入该议题的研究者之一。早在世纪之交,她就撰文讨论近现代中国女演员的登台问题。经由梳理戏曲艺术中男女同台、相互反串的传统,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对女演员登台的禁绝状况,并集中关注“五四”前后男扮男、女扮女表演形式的发生情状,由此管窥国人性别认知的改变。考察辛亥革命前后戏曲女演员登台问题时,她指出:一方面,女演员承受着非难和轻蔑;另一方面,她们的乔装和反串则具有挑衅男权价值体系的意味。甚而,可将戏曲女演员的登台视为五四时期“新女性”登上话剧舞台的前奏。作者看来,这一系列看似摩登前卫、反叛男权话语姿态的内在困境,在于对二元性别意识的更深固化。[1]
台湾地区研究生张远的学位论文,择取20世纪前30年平津沪三个城市中的京剧女演员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时段报纸、画刊、杂志等一手材料的详细考察,力图揭示出女演员的主体身份认同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关系。作者的史料工夫扎实,考察视野专注细腻,对女演员的出生背景与生活、定位与评价、形象建构、所处身的捧角文化氛围、新旧两代女性之间的关系,都分章节逐一做出细致归纳与查考。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平津沪三地,考虑在于,这三者同作为20世纪早期的开埠城市,同时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地区。而位于“坤伶登台”事件中心的京剧女演员,将她们的命运置于这一时空脉络中,更可突显其作为女性所遭际的戏剧化境况,从中发见她们与男性迥异的经验与社会身份的认知境况。[2]
近五年来,“坤伶登台”同样成为大陆学位论文的选题热点。以董虹的研究为例,她通过研究1900年至1937年间京津地区各戏种的女演员群体的日常生活、演出状况乃至情感婚姻情况,提示我们近代女伶群体身上所烙印的复杂脉络,即兼具新旧两种职业女性的特点。而对于她们的性别身份问题,她提出,一方面,在戏曲表演中,女演员在戏中的性别跨界表演,是男性意识形塑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与观戏者、捧角家、编剧人等不同人群的性别互动状况、性别关系演变,都反映了近代性别的权力结构在都市社会中的变迁。这一研究的结论是女伶群体虽衔带传统社会的色彩,但仍对社会迈向现代化作出努力与贡献。[3]
代虹则以近代上海沪剧女艺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她们作为女性经历了从被迫禁演到重登舞台的道路。她们经由拜师学艺、获得职业资格,借助码头、电台、剧场等不同场域,实践并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作者从性别视角切入,同样强调了这些女艺人生存于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社会中,如何深为此种凝视目光所注视,同时又试图通过增加学识、参与慈善等活动,尝试摆脱传统男权社会对自身从艺的限制。作者认为,女性长期受到男权压制,女演员的状况与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而最终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深层改善。[4]
厉震林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中国伶人性别文化研究》,集中以“性别”作为考察戏曲伶人状况的核心视角。该著史料翔实,征引不少西方性别理论前沿成果,以辅助对伶人特殊性别与角色的理解。作者研究古代女性伶人的生存状况,认为她们的悖论在于,处身于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等级序列的同时,又因在“公共领域”中表演而具有男性主“外”的气质特征,而这一男性气质背后,实际又意味着她们堕落、跌入更深的女性化境地:成为公开场合中欲望的投射对象与偷窥的女体对象。他认为,自古对女性伶人“色艺俱全”的要求,其本质是认为,这是她们性暴露与性展览的基本素质。[5]尽管该著聚焦古代社会中女性伶人的社会角色、性别的权利话语编排及性别气质的生成,但可为理解“坤伶登台”语境中戏曲女演员的遭遇提供历史参照。
由上所述,大致可以总结两岸近年从性别研究视野理解“坤伶登台”的共性特征。最重要的无疑是,它们都尝试从性别身份角度介入该问题,通过对女演员特殊境遇的关怀,试图理解她们面临的性别歧视,并探求她们激发抗争动能、改变现状的可能。然而,单纯从性别视角切入看待问题,也同样会存在缺憾。由于以性别关系为重,实际分析时,性别研究易陷入消解问题复杂性的危险,即难以充分顾及戏曲女演员本身并非仅承载性别身份意涵,还衔带地域、阶级等复杂的社会因素。由此,将女演员过快收束于“女性”身份,简单指出社会对女性演员的欺侮与压制,或将救亡话语与男权压制简单对等,都将模糊近现代中国社会民族危亡语境下演员和一般民众普遍生存惟艰这一更焦灼的事实。此外,性别研究重于思想观念层面的阐发,将“坤伶登台”视为风气渐开、妇女解放等观念影响的结果。诚然,从观念渐进、现代化思想影响的角度讨论女性走出家门、走上公共舞台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仅从新观念本身讨论,实则回避了解释新观念与蔑视“戏子”这一传统观念间的冲突是否、如何得到解决的问题*还应该考虑到,呼吁、传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现代化发展等新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具有多大的普遍性与代表性。换言之,为尽可能避免误读历史、精英化思路的限制,就不能单纯以文化观念解释女演员登台的问题,而须虑及当时中国普遍贫苦、文盲率高等真实的社会历史状况。,以至无法有力说明乡村妇女颠覆中国农业传统分工、选择离开家庭的动机。
二、“新文化史”转向之后: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坤伶登台”
有鉴于此,“新文化史”转向影响下的一些研究,积极寻求更具社会感的理解径路。“新文化史”转向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源于法国,流行于欧美,并在近20年间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这一史学转向的突出表现为:(一)将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的研究范畴,转移到注重社会文化;(二)提倡以文化观念阐释历史,充分借助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分析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解释其文化内涵与意义;(三)重视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及通俗性,简言之,是试图以更为宽泛的文化视野,还原普通人的文化与生活。[6-8]中国史学界将社会与文化相结合,开展历史研究的尝试虽早有先例,但作为一种自觉的跨学科交叉视角,一种具有学科理论方法自觉的新学科概念,则是近20余年来的新趋向。学界一般将此类研究称为“社会文化史”研究。[9]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并非局限于史学研究内部,而是作为一种思路、视野与方法,在文学、文化研究等人文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将之应用于“坤伶登台”研究,具体表现为,将它视为晚清以来历史中的特殊社会现象,并试图回归于对其时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的考察。方法上,这些研究尝试以更历史化、反思性的视野看待性别研究成果,在汲取性别研究有益启示的同时,广泛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方法,故在方法论方面也有相当推进。
同是研究女演员登台的发生机制,徐剑雄有意识地避免单从性别角度考虑问题。通过审视社会结构、历史脉络,他将“坤伶登台”扣连于对近现代中国宏观历史变迁的重思。他论证道,尽管历史上乐户制度中确实存在女伶,但考虑到小农经济“男主外女主内”的方式,及五代后缠足对妇女户外活动的实际限制,行动不便的小脚女性难以适应戏班流动奔波的特性,女伶逐渐淡出戏班。[10]314姜进也指出,晚清以降,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男耕女织”兼业传统的解体,意味着一批妇女成为农业家庭消耗者,于是不得不走出家庭寻找工作。因此,晚清民国戏曲女演员集中兴起的文化现象实则反映了相当实际的社会经济变化境况。[11]60-72
此外,对演出接受状况的不同理解,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与一般性别研究的辨异处。后者从审美心理出发,认为受众对女演员的接受,在于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满足了人们的爱美心理,而这又进一步指向男权社会对女演员的凝视。徐剑雄承认这一探讨的必要性。但他追问:这一审美心理又是如何形成的?他以上海为代表指出,上海的现代化发展,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引入和声光化点的广泛应用,令戏曲表演环境急遽改变:从“戏园”走向“戏院”,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意味着,传统戏园中的安全隐患、公共卫生不堪等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同时,戏曲表演过程(舞台布景、伴奏音乐、伶人服饰、化装、行当配置等)也深受物质性条件变化的影响。由此,审美心理的发生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而此心理与其说仅与女演员相关,不如说适于解释整个伶人群体的兴起。那么,社会又为何能接纳女演员大规模登台?徐剑雄认为,一方面,人们为躲避战乱涌入都市,民间戏班、伶人唱戏为都市各阶层日常消遣和文化消费所需。其间,女演员确以异于男性的审美表现,为男性话语主导的市场有效接纳。另一方面,女性观众也发挥了重要影响,有钱有势者携家避难于上海,看戏成为其女眷不可或缺的消遣方式。这点在姜进的上海越剧研究中也十分突出。简言之,它们都说明,对女演员的需要是、但绝不仅是性别视角观照下的“男性凝视”问题。
女演员面向社会演出,不得不与官、商、民甚至帮派组织互动。与社会各结构性层次的纠葛,往往使她们处于被侮辱与剥削的境地。徐剑雄讨论了外乡女演员与上海移民文化间、“捧角”风气形成后女演员与票友票社间的关系。美籍华裔学者程为坤在其《劳作的女人》一书中,则从社会关系角度,更突出地揭示女演员登台后生活与从业状况的严酷性。通过考察20世纪初北京戏曲女演员的现实状况,他较全面地归纳出女演员面临的五重困境:一、男性主导的戏曲行业中,同行的排挤,跑堂、打杂等的欺侮;二、市场和老板代表的商业资本剥削;三、政府、官员、警察等政治势力的管制;四、剧作家、评论家、作家等文人精英的觊觎;五、社会流氓、混混、帮派等邪恶力量的威胁。由此,女演员作为公众关注下的有偿劳动者,其“身体问题”带来的侵扰,不仅使其表演事业,甚至基本安全和名誉都面临危机。[12]167
女演员面对性别压迫,但作为压迫者的“男权”主体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包含诸多异质性。程为坤呼应并扩充了既有性别研究的成果,同时他对女演员应对方式的考察,则具有对话主流性别文化研究的自觉。在问题意识上,他既避免将女演员仅视为父权话语再生产机制的牺牲者、市场主导的男性话语的牺牲品,又有意识规避欧美戏剧女性主义者讨论模式的干扰,警惕过快将中国女演员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归结为挑战男性主宰的斗争。[12]140他认为“坤伶登台”有独属其自身的复杂状况。
以奎德社为例,“台”对女演员来说不仅是工作处所,也是疏离主流家庭生活后的新家。所以,尽管遭受侮辱和歧视,她们却不断尝试灵活地利用“台”的场域,缔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与共同体。尤其是在民族危机的历史语境中,她们自发地选择与民族主义精英合作,演出反映婚姻改革、社会改革等内容的进步戏曲。性别研究者或认为女演员在这些剧目中的扮演,意味着进一步固化正统文化对女性的规训,但程为坤适时指出,不能忽视女演员借由展示充满道德感的女主人公形象以重塑自身身份的策略性。同时,奎德社的相关实践反映了女演员“表演意识”的创造,说明她们对自己广泛影响各阶层观众能力的自觉。
三、“坤伶登台”核心议题:什么“身份”,何种“抗争”
性别研究与社会文化史研究视野下的“坤伶登台”,研究的核心议题,一言以蔽之,是身份问题。如何看待、诠释戏曲女演员的社会身份,如何把握、评价她们为改变自身身份所作的抗争努力,是进一步理解社会历史变迁状况,同时也是理解女演员自身状态的关键问题。
侯杰、秦方以史料为本,具体叙述了郭翠芬、杨翠喜、婷婷、金灵芝、刘喜奎、赵美英、沈芷秋几位戏曲女演员的悲惨经历,展示她们难逃被玩弄的命运。[13]对女演员如何遭受权贵官僚、军阀阔少、帮会分子的逼迫,这一研究作出细致勾勒。但对戏曲女演员“身份”问题的把握方面,仍有商榷空间。作者将戏曲女演员研究归入“艺人”一章,而他们所指的“艺人”范畴既包含伶人、话剧艺人,也有玩杂耍的江湖艺人,新兴崛起的电影明星、新剧演员,还有歌女、舞女、洋艺人。在此,戏曲女演员与其他艺人脉络的差异性未能充分顾及,而这实际涉及如何认识、定位戏曲女演员身份的问题。这一研究的遗憾之处,充分体现了有历史感、分寸感地讨论女演员身份问题作为研究难题性,对研究者历史把握力的挑战。
对此,姜进尝试作出自觉廓清。姜进有十余年美国留学与执教经历,她的专著《诗与政治》系在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具有与海内外现代中国研究对话的意义。在该著中,她充分考察女演员受辱背后的结构性状况,从三个层面阐述女演员遭受轻蔑的缘由:(一)从观念传统看,伶人自古被排挤于正统社会外,“下九流”的身份认知根深蒂固。(二)从职业性质看,明清以降,坤伶和娼妓不同于养在私密内闱的“贞洁”女子,被排除于儒家话语规范之外。又因二者都在公共空间中展示女性身体、提供服务、获取报酬,因此身份界限具有很强的重叠性。(三)从现实情况看,首先,晚清民国的戏曲女演员来源多样,其中包括名妓和倡优;也有女演员从业后迫于生存压力而兼为暗妓。其次,女演员不甘于低贱身份和戏行的残酷竞争,往往选择以婚姻的方式获得社会体系中的合法身份。然而,成为姨太太这一普遍性选择,反而固化了社会对她们的蔑视。最后,晚清民国戏曲演出的内容和尺度尚无规定,主要以市场趣味为准,女演员不得不屈于扮演妓女、娼妇等角色,或直接被迫演出“淫戏”,更造成社会对演戏人与戏中人身份认知的混同。
种种复杂状况下,姜进看到了女演员在身份问题上丧失控制权的无奈事实。但她未止步于此:考察社会对女演员身份采取何种态度、为何采取这种态度的同时,她也指出身份问题的另一维度,即女演员作为能动主体,如何判断、反馈社会对自身身份的态度。对后者的观照,在过往研究中一般阙如,但在社会文化史视野下,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暗含将女演员视为流动历史状况中的主体,正视她们不断抗争以应对、纠正社会偏见的意义。在此,抗争的意涵指向一系列灵活的处理方式,并不必然意指暴力和冲动。综上,女演员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应成为考察20世纪前叶女演员命运转变如何与社会共振的线索。
姜进从传统对女性“清白”的道德要求谈起,揭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越剧女演员身份抗争意识的逐渐形成过程。她提出,女演员自觉地在舞台、印刷媒介和现实生活中表演“清白”,预先断绝公众的性幻想和男性的性挑逗,以期与传统女优、娼妓相区别,获得社会改革者的认可。[11]83-84值得注意的是,她对这些抗争实践的处理,并非过快将其判定为女演员对“平等”理念的高拔追求,恰恰相反,抗争是女演员出于切实应对现实的需要,并且仍然有待成熟。
到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抗战爆发后,戏曲女演员对身份和命运的抗争与民族命运、爱国救亡更紧密地扣连起来。创刊于1937年的《半月戏剧》[14]第1卷第4期刊登了马秀珍的文章《给伶界姊妹的一封信》。马秀珍开篇就强调“谁都承认戏剧是一种人世间不可缺少的艺术”,而“但凡从事戏剧者,其所负之使命至重且大,自不待言”。她在信中直指当时伶界中女演员的自欺自辱现象,并呼吁“伶界”的“姊妹们”在抵抗外侮的斗争中,将戏曲表演作为斗争武器,担负起宣传爱国救亡的责任。[15]该信值得注目之处,是作者自觉将自己与同伴的身份定义为“伶界姊妹”。考虑到“伶”在历史中长期具有的消极意义,作者坚持在此称谓上构筑姐妹情谊和身份认同,体现了赋予旧称谓以新的积极意涵,以重塑身份的抗争实践。
而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在筱丹桂事件中登场,则突出呈现了抗战胜利后,越剧女演员的抗争更成熟、自觉。袁雪芬抛弃“伶人”的传统称谓,将“演员”这一新称谓赋予自己和同伴,并尝试与其他女演员走向联合。她意识到,真正使女演员蒙受侮辱和剥削的是制度本身,因此尝试创立属于自己的戏院来对抗现有体制。在筱丹桂事件中,她和同仁勇于对抗张春帆,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此,姜进呈现了袁雪芬等一批上海越剧女演员真正有力的抗争。从1947年8月28日《罗宾汉》报对袁雪芬的报道,可看出社会对她新身份的认识:“袁雪芬先生(人人都这样称呼她)”。[11]95-96
四、以底层性与乡土性为核心: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坤伶登台”
“坤伶登台”研究热中,大多是在较短时段中开展研究的,因此对于该文化现象在历史延续性进程中处于何种位置,相关理解和把握一般显得较为抽象,或付之阙如。姜进的考察时段最长,从近现代延伸到当代。关于抗战胜利后上海越剧女演员在戏曲和社会两个舞台的表现,她以袁雪芬为核心对象,讲述了以抗争为主旋律的故事。作为故事高潮的1949年,随后成为以“解放”为关键词的新故事之开端:“1949年10月1日,袁雪芬……作为戏曲界的特邀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共同见证了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11]241在此,两个故事的衔接并非天然顺畅,实际上具有质的变化:一位戏曲女演员获得崭新的政治身份,而从先前的“抗争”到真正获得新身份的“解放”,中间过程是如何跨越的?徐剑雄的结论也同样暗含此问题:“伶人地位的彻底改变,伶人真正受到尊敬要等到一场更彻底的社会变革之后。”[10]369问题是,从“被侮辱”到“受尊敬”,中间的巨大跨越又是如何完成的?
姜进在分析袁雪芬时引入一条脉络,即袁雪芬与左翼知识分子、中共党员的互动关系,由此探讨袁雪芬对身份认识的深刻转变,及她同既有剥削制度斗争的思想觉悟何以发生。在此,姜进试图把问题带向更深维度:考察晚清民国越剧的发展、越剧女演员身份的变化,不仅要在社会文化史视野下,还须纳入更长的历史连续性中加以观照,尤其是要关注戏剧文化变迁与重大社会政治变革间的密切关系。诚如其著作标题“诗与政治”所提示的那样,在上述问题意识导向下,她的研究试图揭示袁雪芬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在具体开展时,将中国革命视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变革”(政治)力量来考察它与“戏剧文化变迁”(诗)的关系。而在作者笔下,革命与女演员生命脉络的关系仍是互为外在的。此外,以袁雪芬为主体,对她建国前后的个人经历作历时查考,这一方式将生发出有关1949年戏曲界共时场域的问题:袁雪芬个人的解放与戏曲女演员普遍的解放之间呈怎样的关系?后者的解放有赖于何种物质、制度条件的保障?进一步,假如说“解放”意味着女演员摆脱了异样眼光,那么,为何延续多年的“坤伶登台”至此不再成为“问题”?上述“跨越性问题”为何能够发生,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得以最终发生?
针对这一议题,目前虽有研究尝试探讨,但在思路上往往倾向于将其视为中共对女演员加以政治赋权的结果。[16,17]然而,女演员身份的转变并非全然源于政治赋权,因为“解放”不仅具有政治身份意涵,更涉及女演员自我主体价值感、艺术表演意义感的高扬和发抒,同时涉及社会整体上对女演员新身份的由衷接纳。所以,仅以“政治赋权”概括,将产生忽略历史经验丰富性、创造性的危险。另一方面,“解放”还体现着,它指涉的历史对象已超出袁雪芬等身处都市、境遇较好的女演员状况,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由此,就场域而言,身处都市底层的女演员、广大乡村中的女演员,就剧种而言,除京剧、越剧等主流剧种外的地方戏女演员,她们的身份和境遇转变,都应成为研究时观照的历史对象。
站在这一脉络中,重思近年“坤伶登台”的研究热,将发现其仍有不足:研究展开的空间场域都是作为特例的大都市,即北京、天津和上海。此外,这些都市女演员又以名角居多。由此,更具底层性、乡土性的内在经验尚未被纳入到对“坤伶登台”的考察视野中,进而也就未能经由对相应乡土社会、底层状况的历史化、结构性考察,发掘女演员在此脉络中从受辱到抗争,以至解放这一系列身份转变中蕴含的社会史意涵。
对“坤伶登台”现象更具原理性的、整体性的考察视野如何建立?更具充沛感的社会史意涵怎样打开?在此,“艺术社会学”视野的介入将提供有益启示。著名艺术社会学家豪泽尔曾以“文学艺术的社会史”为其“艺术社会学”理论兴趣的核心,他将其艺术社会学思想的理论基点建基于下述思想,即社会与艺术的联系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动关系。他追求在整体性思想的指导下认识艺术及其复杂的活动,以及体现时代特征的艺术生活中的多种交流过程。[18]受此启发与激励,“艺术社会学”所强调的,与其说是人文研究时采用的一种工具手段,毋宁说是一种建设性的研究视野。借重此“艺术社会学”视野,对“坤伶登台”现象理解的着力点在于考察“坤伶—戏曲艺术—中国社会”这一组充满张力的互动关系,深入把握中国近代、现代以至当代戏曲艺术变迁状况的同时,重新理解其间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性进程。既不满足于对单个现象的“碎片化”研究,也打破对社会人文历史研究予以笼统、抽象、宏观等特质的先在想象,而是借由切实有力地深入对这一代表性文化现象的研究,把握其多面丰富、充实复杂的状态,求索其中蕴含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肌理,以及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重构历史认知的意义。
因此,对“坤伶登台”理解的进一步深化,正有待于此种更广阔的“艺术社会学”视野的介入。在这一案例中,它强调以底层性、乡土性为核心的主体历史经验的意义。此历史性要求将研究落实于对戏曲女演员社会身份理解的扩充,并将其身份转换置于中国近现代、当代社会的历史连续性进程中,置于对“中国革命”之创造性的理解中加以观照。此处的“社会”与“革命”并非简单指政治强力,也非外在于女演员及其戏曲表演实践,而是内在于她们的艺术思想与身份转变,要求研究者充分注目于中国土地上多数女演员的命运遭际,从根本上理解一场浸润于普通女演员与更广大基层民众生活的、改天换地的社会变革运动。综上,“坤伶登台”的故事或将存在新的讲法:在“艺术社会学”视野观照下,在中国革命脉络中,讲一个普通底层女演员从屈辱到解放的身心故事。
[1] 周慧玲.女演员、写实主义、“新女性”论述——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剧场中的性别表演[J].戏剧艺术,2000(1):6-10.
[2] 张远.近代平津沪的城市京剧女演员[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1-2.
[3] 董虹.城市、戏曲与性别:近代京津地区女伶群体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193-196.
[4] 代虹.近代上海沪剧女艺人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1-2.
[5] 厉震林.中国伶人性别文化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12-29.
[6]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4.
[7] 伯克.什么是文化史[M].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
[8] 亨特.新文化史[C].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
[9] 梁景和.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C]//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
[10] 徐剑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1867—1949)[M].北京:三联书店,2012.
[11] 姜进.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2] 程为坤.劳作中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M].杨可,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
[13] 侯杰,秦方.旧中国三教九流 艺人妓女嫖客[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80-87.
[14]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G].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6:755.
[15] 马秀珍.给伶界姊妹的一封信[J].半月戏剧,1937,1(4):22-23.
[16] 傅瑾.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1-2.
[17] 马海丽.中国戏曲演员:毛泽东时期产生的新精英阶层[G]//首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30-38.
[18] 方维规.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9.
Reflections on Heated Research into ′The Appearance of Dramatic Actresses on Stage′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How Aesthetic Sociological Vision Helps to Acqui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BAI Yi-m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Appearance of Dramatic Actresses on Stage" has been the focus of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Gender studies,while focusing on the gender issue and the actress′ special encounters, tend to interpret them from an ideological angle. Recently, the socio-cultural historical studies reveal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the dramatic actresses′ status as well as their struggles for identity, while neglect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ir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in a lo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 aesthetic sociological vision could be an inspiration and centering on subalternity and localism will help to acqui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dramatic actresses′ appearance on stage; gender studies; socio-cultural history; aesthetic sociology
I01
A
2095-0012(2017)04-0102-07
(责任编辑:紫 嫣)
2017-05-12
吴苗淼(1990—),男,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美学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