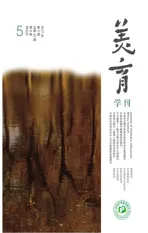论自然审美中的物理距离与“风景如画”
2017-03-24王中原
王中原
(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475001)
论自然审美中的物理距离与“风景如画”
王中原
(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475001)
自然景观的审美欣赏需要人们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而当代西方的环境美学从其自身的理论主张出发反驳了这个审美常识,认为保持物理距离是对本然的自然审美的歪曲。环境美学的这一质疑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然审美中的物理距离的契机。对自然的视觉欣赏必定需要一定的物理距离,但这并不违背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的感知特性,通过视觉透视原理,物理距离使风景在审美欣赏中生成为一幅“天然的风景画”,因此自然审美中的物理距离是揭示自然景观之美的必要感知要素。
风景欣赏;环境美学;景观
风景欣赏需要我们保持适当的物理距离,这是自然审美的一个经验常识。然而,当代的环境美学对此却提出了质疑,认为保持一定物理距离的欣赏是对本然的自然审美的歪曲。环境美学的质疑为美学提供了一个机遇,借此可以澄清我们对自然审美中的物理距离的认识。“风景如画”是自然审美中的一个事实,我们往往以“如画”来描述和体验自然景观的美。自然审美中的物理距离可能是“风景如画”一个根据,因为欣赏绘画必定需要我们保持在适当的物理距离上,“风景如画”必然亦如是。学界对于二者的本质关联并未做出过相关的探讨,鉴于上述考量,本文拟对自然审美、物理距离及其与“风景如画”的关联进行一个美学上的探讨。
一、自然审美需要欣赏者保持适当的物理距离
审美对象的自然的体验特征是其环境性,而环境意味着“一系列感官意识、意义(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的)、地理位置、身体在场、个体时间和弥漫性的运动的融合,没有外部视角、没有遥远的场景,没有与我当下在场相分离的外围世界,毋宁说它是集中于在场处境的当下时刻,一个包含着丰富的内在感觉和意义的参与的境况”[1]34,环境就是人与万物共同此在的存在情态,一种没有主客、物我、身心、内外之分的存在境域。自然的环境的特征正如柏林特所说,是一种人融于当下在场的情境、当下情境将人吸纳入其中的在场性体验,这种体验表现为时间上的无限绵延和空间上的无限广袤。康德对此有精彩的表述:“也许从来没有比在伊西斯(自然之母)神殿上的那条题词说出过更为崇高的东西,或者更崇高地表达过一个观念的了:‘我是一切现有的,曾有过的和将要有的,我的面纱从来没有任何有死者揭开过。’”[2]我们对自然的感知体验就是这种广袤的时空境域,自然环绕着我们在其中的任何一个置身之处,要把这种环绕、吸纳着我们的自然风景收入眼底,我们必须首先保证有足够的物理距离,诚如苏轼的诗句所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风景的感知必须要以一定的物理距离为前提,如宗炳所说:“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以围于寸眸。”[3]583
一定的物理距离也意味着适当的观看点,这对于风景欣赏来说是很必要的。风景园林和风景名胜中的一些人工设施——亭台楼阁、栈道拱桥等——都是风景审美的最佳的物理距离上的地点[4],“天下名山被僧占”的一层意义就是寺庙占据了欣赏风景的最佳位置。
审美的感知经验尤为强调风景欣赏的物理距离,适当的物理距离指向的是感知的完整性,而感知的完整、完善乃是审美经验的本质特征。审美经验表现为一种感性的完善性,一种混乱的意识中的有形式性,如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所说“完善的外形,或是广义的鉴赏力为显而易见的完善,就是美,相应的不完善就是丑”,“美学的目的是(但就它本身来说)感性认识的完善(这就是美),应该避免的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5]杜威对艺术审美中的经验的断语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在艺术中,我们发现了:自然的力量和自然的运行在经验里达到了最完备,因而是最高的结合”,“艺术既代表经验的最高峰,也代表自然界的顶点。”[6]因此,自然风景的美必然表现为一种感性的完善性,这种完善性既指其外观轮廓上的完整,也指其置身于其中的世界背景的完整。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有触觉、嗅觉、肤觉等近感官的感知是远远不够的,必定需要远感官(视听)所拉开的距离才能获得对事物的完整经验,否则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审美经验的完善性需要对事物进行整体性的感知,这一点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非常小的活东西不能美,因为我们的观察处于不可感知的时间内,以至模糊不清;一个非常大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万里长的活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它的整一性”[7],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并不限于“整一、和谐、比例”的古典的优美,这个“一万里长的活物”是不能被称为优美的,审美原理要求对审美对象做整体上的把握。即便是对自然中的崇高的欣赏亦是如此,我们的想象力极力地试图把握风景的整体形象,虽然崇高挫败了想象力表象整体的努力,但这个挫败却成就了另一种整体性——人心中的理念。在对自然景观的视觉审美体验中,人们对风景的整体性把握则是通过物理距离的调适而获得的。
综合上述,从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的特征、自然审美需要一定的观看点和审美感知的完善性出发,自然景观的审美欣赏必然要求我们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
二、环境美学的质疑以及对其质疑的回应
当代西方的环境美学从自然的“环境”特征出发,否定自然欣赏应保持适当的物理距离,在环境美学看来,与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的环境特征相对应的欣赏方式应该是参与式的:
(参与模式)强调自然语境的多元维度,以及我们对它的多向度的感性体验……参与模式召唤我们沉浸到自然环境中,试图破除诸多传统的诸如主体/客体的区分,并且最终尽可能地减少我们自然与自然之间的距离。简言之,审美经验是欣赏者在欣赏对象中的一种全身心投入。[8]
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欣赏中保持物理距离乃是一种主客二分式的体验,这种“旁观式”的欣赏有悖于参与式的体验,因而没有正确地对待自然的环境特征。
然而,在一定的物理距离上的观看并不是判断主客二分式地“对象化”自然的依据,这种误解的一个典型例证体现在绘画上。欣赏绘画艺术必定需要一定的物理距离,与距离相关的就是绘画作品的画框,这个画框把作品的内容“框”成一个对象,成为一个能够纳入主体视野的特定客体。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自然景观的欣赏中于一定距离上把风景分割成为一个个的“景色”,这里所做的就是用画框从自然环境中把它们“框定”住,从而使风景成为一个惬意而且无危险的赏玩对象。在这种误解之下,画框所要求的在一定物理距离上的观看就成为对象化的代名词,然而,这里的画框事实上只是一种审美感知空间的标志,画框不仅为想象的空间设立了边界,而且决定了绘画作品的尺幅大小,这种大小通过视觉透视原理为观看规定了物理距离。从审美的角度看,适当的物理距离乃是进入这个想象的世界中的门槛,因而对于绘画来说,物理距离不但不意味着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观看,反而是“参与式”欣赏的必要前提。关于这一点可以引用梅洛-庞蒂的话作为例证:“绘画唤醒并极力地提供了一种狂热,这种狂热就是视觉本身,因为看就是保持距离,因为绘画把这种怪异的拥有延伸到存在的所有方面:为了进入到绘画中,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让自己成为可见的。”[9]42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在观看绘画作品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并非总意味着主客二分式的对象化注视。
自然审美中的物理距离所招致的误解的根本原因,源于人们对视觉的偏见。由于视觉属于远感官,它对外界信息的接受必定需要一定的距离,风景欣赏对物理距离的要求在感知层面的根据是视觉观看。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风景”一词的含义上,关于英语中的landscape一词,辞典按照词源含义将其定义为:“在人们的视野里通过眼睛所看到的广阔的自然景色”,或者是“表现一部分自然的、内陆的自然风景的画。”[1]5自然风景和风景画强调的都是对自然的视觉感知,这在汉语中同样有所表现,landscape对应的汉语词汇是景观、风景、山水、风景画、山水画等,风景的汉语词意是“供观赏的自然风光、景物”,景观指的是“某地区的或某种类型的自然景色、也指人工创造的景色”。 在自然审美的语境里,景观、风景的汉语本土词汇是山水,而山水指的则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景观。从风景、景观、山水等词的含义来看,它们意指的都是自然的视觉性欣赏,国内学术界通常将landscape翻译成为“景观”。通过以上的词义辨析,不难看出风景(landscape)指的是视觉审美意义上的自然,风景欣赏指的就是对自然景观的视觉审美。
然而在后现代的思想语境中,视觉却被赋予了与形而上学合谋的意义,即所谓的“视觉中心主义”。 视觉的特征使自身得到统治西方哲学史的形而上学的特别青睐,柏拉图的核心词“理念”“相”就是视觉与形而上学结盟的例证,在柏拉图看来是观看决定着存在。柏拉图的“相”隐喻了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人之主体性膨胀的现代所发生的事情,自笛卡尔的“我思”成为承载一切存在和不存在的基础的时刻起,人们把世界的显现理解为人类的自然之光(理性)照亮的结果。在这种思想语境中,视觉和观看表征了主体对作为客体的世界的表象,真相倒不是柏拉图“洞穴隐喻”中获得自由的囚徒对自行运行的真理世界的观看和归属,而是世界唯有在人的观看和表象中才存在,借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说就是:“从此以后生活就通过眼睛的光亮世界去加以把握和理解。这是最大的奇迹,它使人类的万事万物成为它们现在的样子。”[10]
然而一旦人及其眼睛被赋予这种特权之后,必然伴生的是人类在对待世界的伦理行为上的改变,如海德格尔所说:“惟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的。在出现世界图像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11]对世界的表象式观看的伦理后果是,人对作为客体的世界的统治、支配、算计,正是鉴于视觉观看的表象性特征,在形而上学的统治领域之内,视觉观看总意味着主客二分,以及主体对客体的统治。
因为视觉的缘故,自然欣赏中的物理距离被指责为与主客二分的对象化意图的合谋。我们对此的考量是,视觉本身是无辜的,只有在与形而上学结盟的时候才被赋予“视觉中心主义”的内涵,在形而上学的领域之外这个指责是无效的。观看并不仅仅意味着用肉眼看,而且意味着通过肉眼用心灵来观看,即所谓的“应目会心”,此时看“不仅不意味着用肉眼来感知,而且也不意味着就现成事物的现成状态纯粹非感性地知觉这个现成事物。……‘看’让那个它可以通达的存在者与其本身无所掩蔽地来照面”[12],也就是说观看是能够在物我相融的敞开之境中觉知存在的。梅洛-庞蒂就曾描述过这种人与万物同体的现象学经验,于其中人通过视觉看事物同时也被事物观看:“视觉被纳入到事物的环境中或者说它是在事物的环境中形成的——在这里,一个可见者开始去看,变成一个自为的、看所有事物意义上的可见者;在这里,感觉者与被感觉者不可分地割持续着,就如晶体中的母液那样。”[9]37因此,视觉并非总意味着主客二分的对象化感知,立足于其上的景观欣赏中的物理距离也应该做此解。
鉴于此,我们认为环境美学的质疑有其偏颇的一面,物理距离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对自然的主客二分式的对象化,风景的审美感知需要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而这种要求并没有违背自然景观的经验特征——人对作为“环境”的自然的“参与性”感知。
三、物理距离与“风景如画”
在自然审美经验中,我们往往用“如画”来体验和描述自然景观的美,就是说自然景观的美在风景欣赏中表现为“如画”,“风景如画”即美的自然风景看起来像风景画一样。绘画作品的欣赏需要我们与作品保持适当的物理距离,“风景如画”从其所“如”的“画”来说也必定要求适当的物理距离,如画的风景(landscape)本身就意味着“从特定的立足点和距离上看到的景色——通常是宏大的景色(prospect),风景画常常如此再现风景,如画欣赏也归属于这个种类”[13]。为了使自然风景(特别是全景式的宏大的场景)看起来像一幅画,观看者必须在适当的物理距离和立足点上观看。在对物理距离的要求上,欣赏如画的自然风景和欣赏绘画是一致的。对我们的探究来说,值得思考的不只是如画和绘画欣赏一样需要观看的物理距离,更为重要的是,物理距离是否以及如何促成了风景的如画。后者对于美学来说意味着,由于物理距离在审美感知的层面揭示了自然景观的美,从而成为风景之美呈现的一个感知要素。
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谈到山水欣赏的时候说到,“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3]583,这讲的即是视觉透视原理。观看的视野是一个以眼睛为顶点的准圆锥体区域,被看到的物体的形状大小与其到眼睛的物理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远形状越小。因而对于昆仑山上这样的形体巨大的风景,如果“迫目以寸”则只能见到一斑,要像窥见昆仑全貌必须立身在足够远的距离之外。鉴于眼睛的光学透视原理,所有的观看都需要物理距离上的保障,对于风景审美中的形式感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自然风景通过距离布排在透视上,从而呈现为前景、中景和远景,不仅仅是山水的轮廓外形在大小远近上生成层次,而且其色彩通过透视也会呈现出浓淡明暗上的规律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定物理距离上的观看为风景的轮廓、色彩、布局上的视觉特性打开了审美之门,也为风景拥有相似于风景画的线条、设色、构图提供了透视学基础。
在透视学上,人的视野是一个近似于圆锥体形的视锥,视锥并不是眼睛像手电筒那样发射出去的光域,而是从物体身上反射的光线成圆锥体的形状朝向眼睛的汇聚,人的眼睛就是这个视锥的顶点。因而,眼睛在任何一个既定的观看点和特定距离上的视野仅仅是一个卵形的,水平延展约180度,垂直延展约150度的视域,外界的立体世界就在其中得以呈现。如果在人的视野中放置一个与眼睛平行、且保持一定距离的透明玻璃的话,那么事物在这个切面上投下的影像与人眼所看到的事物形象是一样的。实际上,人眼对事物的立体形象的观看就是对事物投影的观看,虽然人们并不会一直在眼前放置一个透明玻璃透视性地观看,但是人眼前的空气介质就是一个天然的“透明玻璃”,我们对所有事物的观看必须透过这个“透明玻璃”,所见的事物形象其实也就是事物在空气中的投影,这种眼睛观看的光学原理就是透视,透视即投影式地观看。
客观世界是没有焦点的,但是人的视野却是有一个焦点的,这个焦点即是人的眼睛,通过视觉透视,立体的世界形象在人的眼前被转换成为一个二维的平面图像,眼睛就是这个图像的焦点,随着人的位置的移动,现实世界的形象会在这个图像中以人眼为中心向四周逐渐消散。在这个以人的眼睛为焦点所形成的二维的平面图像中,事物形象在视野中的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存在,是由人眼与事物之间的物理距离规定的,距离过远的事物会从视野中消失,而事物在透视中的形象的大小和清晰度则与物理距离成反比,如荀子所说:“故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长也。”(荀子·解蔽)[14]因此,对于人眼的视觉透视来说,物理距离乃是一个本质性的因素,不仅视觉透视需要一定的物理距离,而且事物在视野中的呈现本身就是由距离来规定的。透视的最终效果也要落实到物理距离的组织上,这一点在山水画的空间构造上得到典型的体现,中国绘画传统就干脆称透视法为“远近法”。
鉴于人眼的透视特性,一定物理距离上的风景能够在人的观看中被投影成为一幅二维平面的风景画,这就是宗炳所说的“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3]583。对于风景欣赏来说,我们眼前的空气介质就是随时随地携带着的“绢素”,因而透视无处不在,这就使得自然风景在一定物理距离上的透视性观看中必定是如(二维平面意义上的)画的。如果用一个方形的边框来做视觉透视的边界的话,那么自然风景在这个方框中的投影就是一幅标准的(透视)“风景画”,此时的投影具有一个与通常风景画一样的方形画框,自然风景按照透视原理在这个方形的图画中(像风景画的构图那样)排列成为前景、中景和远景。用焦点透视法绘制的风景画就常常使用这样的方形“取景框”,“取景框”就是通过在透视中形成的这种天然的“风景画”来帮助画家作画的,反之,按照焦点透视法制作的风景画则可以被视为透过方形边框对风景的观看,这种图画就是朝外看的“窗子”,如果不拘泥于绘画的二维平面特征,透视图画中的空间与真实世界的空间将是一致的。这就是所谓的透视的“窥窗效应”,风景园林常常利用这个原理来制作天然图画,通过设置窗子或者墙壁上的空洞,让人们看到如画般的风景,如宗白华所说:“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15]通过在一定物理距离上的透视观看,自然风景会生成为一幅二维平面的“风景画”,这使得天然的风景显得如人工创作的透视风景画一样,也就是说一定物理距离上的视觉观看促成了风景美如画。
视觉透视使得人的眼睛成为世界的焦点,从而赋予了人类可以比拟于上帝的身份,但是人并不拥有那双无所不在的、一切对它都毫无隐蔽的“上帝之眼”。世界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透明的,我们的肉身总是把观看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特定范围内的视野里,在时间的线性流逝中,我们只能看见事物局部的侧面和片段。但是自然景物在风景欣赏中从来都不是以一个个“当下”碎片显示给我们的,自然景观总是以其整体形象呈现给我们,这就是想象力在观看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顾恺之的理解是有偏颇的,山水画乃至山水欣赏都需要“迁想妙得”。在有想象参与进来的风景观看中,逝去的曾在和临近的将来都在当下的直觉中呈现出来,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于风景画中,因而王微在其《叙画》中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3]585这种能够“拟太虚之体”的风景画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山水画,山水画通过“步步看”“面面观”“推远看”“拉近看”[16]等画面空间的组织方式,把一时一地的视觉透视整合到当下直观中,严格地按照透视原则把不同的物理距离上的景物“全景式”地图写到一幅画面上(如郭熙的“平远、高远、深远”,以及韩拙的“迷远、阔远、幽远”[17]),由此吴道子才能把三百里嘉陵江的景色画入一图。这种所谓的“散点透视”类的风景画表达了想象力的整合功能,正是通过这种功能,中国山水画才能做到“咫尺千里”,做到“书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不以制小而累其似”,而尽得“自然之势”[3]583。与想象力相关的散点透视的本质性因素也是视觉透视,散点透视无非就是通过画面的物理距离的组织,把视觉透视经验整合到一副绘画中,以此来表达人对风景的完整的视觉经验。也就是说,即便以想象力对真实的风景欣赏经验加以还原,景观欣赏中的物理距离依然是促成“风景如画”的感知要素,只不过这里的“画”是散点透视的中国山水画。
上面的探讨表明,自然审美中的物理距离通过视觉透视,使自然风景呈示为一幅二维平面的“风景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是物理距离促成了风景的如画。由于“风景如画”是对自然景观的美的描述和评价,我们在此宣称,物理距离作为自然景观审美的一个重要的感知因素,有助于揭示和呈现自然风景的美。
四、结 语
文章的探讨表明,自然风景的视觉审美欣赏必定需要观看的物理距离,这并不违背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的感知特性;物理距离通过视觉透视原理,使得风景在审美欣赏中生成为一幅天然的风景画,即“风景如画”。自然审美中的物理距离是揭示自然景观之美的感知要素,它使得风景看起来美如画。文章的结论揭示了物理距离在自然风景的审美感知和景观塑造中的重要作用,这将会从理论上为景观美学和景观设计带来一定的启发。在现实性意义上,文章的结论启示我们在自然欣赏(如景观旅游、园林或风景审美)中应该重视物理距离的作用,充分利用这一因素来呈现自然之美,以提升自然审美的质量,开掘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
[1] BERLEANT A.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61.
[3] 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4] 李遵进,沈松勤.自然风景审美:旅游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77-78.
[5]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42.
[6] 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5.
[7] 亚里斯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2.
[8] CARLSON A.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M]. London: Routledge, 2000:6-7.
[9] 梅洛-庞蒂.眼与心[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齐世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88.
[11] 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8.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171.
[13] CARLSON A. Nature and Landscap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26.
[14]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359.
[15]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1.
[16] 王伯敏.山水画纵横谈[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198.
[17] 王伯敏,童中焘.中国山水画透视法[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3-13.
ABSTRACT: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a natural landscape requires a certain physical distance, but contemporary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refutes this aesthetic common sense from it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contending that keeping a physical distance is a distortion of natural aesthetics. The query from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aesthetics to clarify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ysical distance in natural aesthetics. That the visu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a natural landscape necessitates a proper physical distance does not violate the perceptual features of nature as an aesthetic object.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visual perspective, the physical distance makes the scenery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 "natural landscape painting". The physical distance in is a cognitive element used to reveal the "beauty" of a natural landscape, which makes the scenery look picturesque.
Keyword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landscape
(责任编辑:刘 琴)
A Study on the Physical Distance in Natural Aesthet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 "Beautiful Landscape"
WANG Zhong-yuan
(Center of Literary Theor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2017-05-11
王中原(1981—),男,河南镇平人,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
B83-02
A
2095-0012(2017)05-01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