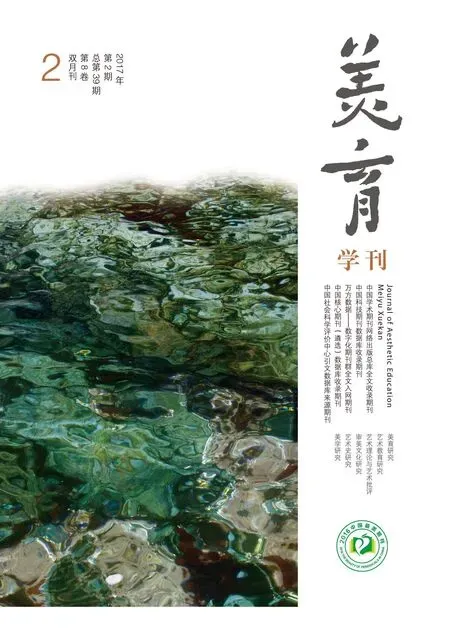木心的艺术美育观与生命完成
2017-03-24邓天中
邓天中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木心的艺术美育观与生命完成
邓天中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木心推崇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这一观念贯穿了木心的整个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过程。梳理木心作品与讲稿中所蕴含的艺术观与美育理念,从中可以看出木心所倡导的艺术的救赎功能。木心认为艺术将“可能”变成“能”,弥补了现实生活中诸多缺失与遗憾。艺术是生命的和谐,可以带着忙碌的人通向理想中的王国,服务于生命的成长;艺术的成长固然需要天赋,但更需要个人后天的努力,还需要各种机缘巧合,因此学习艺术不能急于求成,要把追求艺术作为生命永远的“准备期”,艺术才有可能完善人生;人可以借艺术来制造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并分身出多重平行生命,艺术为人走向生命完成提供了自由空间。
木心;美育观;艺术救赎
引 言
在现代语境下,人们凭着科技理性已经成功地“驱赶”了上帝。然而存在主义哲学的滥觞却并未能解决人内心的精神诉求。人们生活与选择的意义何在?神退隐之后人的精神将归于何处?木心以自己的艺术实践给出了这样的思考:
一个中国的绍兴人说出尼采没有说出的最重要的话“美育代宗教。”这个人,是蔡元培。“代”字,用得好,宗教不因之贬低,美育也不必骂街,斯文之极,味如绍兴酒。[1]116
木心精通佛、道、基督教义,对儒家思想更是从小就耳濡目染、烂熟于胸,作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却又同时是一个“拙劣的、于心不忍的无神论者”[1]68——他的“于心不忍”就在于认为做人不可以没有“灵魂”,不可以没有精神信仰。他提出“信仰事大、宗教事小”,并进一步解释说,“善虽被恶压制,但世界上善还在”。[1]85木心的全部艺术努力,都在围绕人性中的这一丝善念而来,他甚至将艺术推崇到宗教意义上的“上帝”的位置。正是这种无神却又无法放弃灵魂诉求的现代性悖论,让木心成为艺术美育的积极拥趸者,这样既不至于贬低宗教对人的精神呵护作用,又突出了艺术对于生命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木心的艺术美育观,看到他的“现身说法”式艺术自救努力,进而分析他艺术救赎观所强调的宗教意义上的虔诚,即人需要用毕生的精力一刻也不放弃地呵护自己生命的成长,从生活中去发现美、创造美,“一字一字”地拯救自己的人性,使其不至随波逐流地堕落;另一方面,美育也包括积极传导美的理念,育化别人,完成整体的人性,实现以艺术让生命趋向于完成的宏大命题。
一、艺术与救赎
木心试图按照西方话语体系来解释艺术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即生命为什么需要艺术来“救赎”。因为假如人能够如神话与《圣经》记载的那样,永远生活在神的乐园之中,听任神为人安排好一切,人自然会无忧无虑地享受神性的美好天堂。但人性中的自我选择冲动,让自己主动地离开了神的呵护,进而走向理性下的设计与尝试。而凭着人有限的理性与短暂的前瞻视野,难免顾此失彼,产生各种灾难性后果,并最终导致人的失落孤独。木心对人性的深刻认识让他能看到人性黑暗与委琐的一面,只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性,而是更加勇敢地借助艺术来面对人性。他根据《圣经》旧约杜撰了这样一则寓言:
亚当出乐园,上帝说:“可怜的孩子,你到地上去,有高山大海,怕不怕?”亚当说:“不怕。”
上帝说:“有毒蛇猛兽。”亚当说:“不怕。”
上帝说:“那就去吧。”亚当说:“我怕。”
上帝奇怪道:“你怕什么呢?”亚当说:“我怕寂寞。”
上帝低头想了想,把艺术给了亚当。[1]586
人在与上帝的对话中,大自然的一切都似乎不足以让人类感到恐惧,但自身内心深处的寂寞却在深深地困扰人类。木心将上帝赋予人的艺术本能作为解决这种寂寞的唯一手段,甚至讲艺术家可以起到比上帝创造人更加巨大的作用,“上帝造亚当,大而化之,毛病很多;艺术家造人,精雕细琢,体贴入微”。[1]577木心的这种艺术理念与新约思想非常接近:上帝造人之后,人就应该有勇气为自己的成长负责,让自己来重塑人的完美形象,以接近神的完美。始终生活在神的乐园中,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是对造物主的亵渎。
木心对比人的各种尝试与选择,得出了“艺术优先”的结论,认为只有艺术可以拯救人性:“靠宗教,靠政治,都不能拯救人性,倒是只有文学和艺术”[1]991,因为:
宗教、哲学、科学,可能,而“不能”。艺术,总是看到“可能”,接下来是“能”,真的能。写下来:
宗教、哲学、科学,可能而不能。
艺术,可能,能。[1]992
艺术将“可能”变成“能”,弥补了现实生活中诸多缺失所带来的遗憾。木心以音乐为例表明是艺术让心灵拥有了“幸福”的感觉,“人生多少事,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的幸福,其实就到心向往之的地步。整个音乐就是心向往之的境界,是拿不到的东西”。[1]535从这个层面讲,人要敢于尝试一切心为之动的可能性,但前提是对生命与自然有着本能的敬畏之心,不可以胡作非为。在这种向往之“心”与生平之“迹”的巨大鸿沟之间,只有艺术能够赋予人犯下各种人性错误却不至于对世界造成真正的损害的权利。
既然人生必须要做出选择,那就应该选择最有价值的。木心给出的最有价值的选择,就是对于人的生命至关重要的艺术。他认为“艺术的功能远远大于镜子。艺术映见灵魂,无数的灵魂”[1]586。在人类的其他各种行为中,触及“灵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对于人性来说,虽然肉体的生存非常重要,但解决了温饱生存之后,人类的自我发展却不应该是放纵肉体的各种欲望,而是如何呵护自己的灵魂,追求灵魂的成长。在木心的感知中,现实如同遭到诅咒,充满血腥、暴力,缺乏理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艺术的缺位。离开了艺术的呵护,即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诗的国度,自魏晋之后,艺术也退化到只有歌功颂德的简单功能,任由各种恶果泛滥。
木心推崇艺术的救赎功能,就在于艺术首先要求人必须精炼、完善自己的语言。木心从自己卑微不幸的个人命运中推理、培养出一套他认为最为理想的生存模式,木心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
我爱兵法,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人生,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生活。[1]152
全靠艺术生活,就是艺术地、诗意地栖居,从生活中提炼诗,把生活炼成诗,他说:“人类要自救,只有了解自己、认识他人,求知、好奇、审美,是必要的态度。艺术、人类,是意味着的关系,即本来艺术与人类没有关系,但人类如果要好,则与艺术可以有关系。”[1]645顾文豪总结木心时说:“先生是有贵族气质的,把自我也当做艺术品在雕刻。”[2]这种“雕刻”就是语言的磨练。木心说:“人好,语言就会好——艺术本来想救人类的,救不了,结果倒是救了艺术家自己。救不了艺术家,那他是个凡人,不能怪艺术。”[1]858语言是人生磨练的结果,当一个人的语言也得到艺术的提升,能够“合乎艺”的时候,他就能够利用语言创造一种与现实生活相平行、却比现实生活更有意义的完美生活,让自己无论是在现实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理想地栖居于诗一般的浪漫情境之中。但木心也深知“艺术救赎人生”是一个说易却难的命题,因为毕竟有很多人在生活中根本不会去顾及艺术为何物——“个别人,极少数人,他要自尊、自救,他爱了艺术,艺术便超升了他,给他快乐幸福。绝大多数人不想和艺术有什么关系。”[1]645
木心在内心隐约所期待的教化并不是俗世所谓的道德教化或者知识教化。出于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他知道人内心那种根深蒂固的自以为是的惰性是很难被“教化”的,他说:“当愚人来找你商量事体,你别费精神——他早就定了主意的。”[3]11只是艺术教化却另有天地,因为一个愿意接近艺术的人,他进步的动机就得到了解决,在与艺术的互动过程中,他也会得到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不太主张“顿悟”,而是主张在“渐悟”基础之上的“顿悟”——“如果‘顿悟’不置于‘渐悟’中,顿悟之后恐有顿迷来。”[3]11因此,木心的艺术美育观,就是主张人应该知道生活中的诸多不幸需要靠艺术来解脱,而人要有亲近艺术的想法,而且要对艺术救赎有信心、有耐心,“文学是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书法是一笔一笔地救出自己”[4]257。只有这样地主动拥抱艺术,才会有“顿悟”的一天,“你爱文学,将来文学会爱你”[4]289。艺术家为读者准备了一套仿真自然的艺术品,让人在阅读文学或其他艺术作品时能感受生活的喜悦与无奈,并从中得到解脱:“文学上的人真有味,生活中的人极乏味。这样不好,不这样也不好。”[1]12
木心主张艺术拯救生活,可以让人脱离低级趣味或一时情感之忿。他看到了鲁迅以国民性作为批判对象的狭隘之处,指出艺术家所应该看到的是更广泛的人性。他以自己为例说:“我也气过、攻击过很多人事,但终于放进抽屉,不发表,不抬举他们——要找大的对象。”[1]445
艺术家与艺术耳濡目染地亲密接触,自然是首先得到救赎者。但打着艺术旗号行功利之实的凡人是不在其中的。这些人由于别有他图,或许也并不在乎得救与否,也或许是只有在没得救的绝望时分才奢望那不再可能到来的得救。
木心强调他心目中的艺术观是以艺术来提升人格,让人走向成熟、完美,他说“我最心仪的是音乐、建筑、绘画所体现的宗教情操,那是一种圆融的刚执,一种崇高的温柔。以这样的情操治国、建邦、待人接物,太美好了”。[1]115强调培养人性的“圆融的刚执”与先儒的“中庸”思想有一定呼应,这或许也是孔子在自己思想体系中对“诗”关注有加的原因,只是可惜后世儒家理性太强调说教而忽视对艺术教育的尊重。生硬的说教过于刚性,让脆弱的人性不堪其重,也让生命少了色彩。不论我们是多么希望将“真理”传授给受教育方,如果受众没有对真理的渴望与接收能力,一切的教育努力都将是徒劳的。艺术诉诸人的直觉,不主张说教,木心讲“直觉创造艺术”:“音乐全靠直觉,可以使所谓主客体达到无差别的境界。”[1]746人生命的成长,需要学习与教育,而且是终生的教育学习过程。像音乐这样的艺术则直接诉诸生命的直觉,没有因果逻辑,只有节奏与旋律的变化,在与生命合拍律动的过程中将生命不断地推向成熟,其中就有着教育家所期盼的“道德”力量,“我所秉持的道德力量,纯从音乐中来”。[4]257
艺术介入教育是激活人的直觉,让人在直觉的快感与游戏的愉悦中得到成长,艺术在本质上是建立在虔诚奉献基础上纯真的游戏,“从生活模仿艺术来说,生活与艺术是一元的。把艺术作为信仰,全奉献。康德从不出家门,克尔凯郭尔只玩过一次柏林”[4]257。哲学家往往不懂得“玩”,会把多彩的生活变得很枯燥,让经院以外的人“敬而远之”,木心不担心人们“玩物丧志”,而是担心人们玩得不够“大气”——“志大者,玩物养志”[4]245。
艺术之所以可以拯救人类,还在于艺术的目的与动机,“艺术要寻找本质,用鲜明合度的形式,把本质表达出来”[1]876。“鲜明合度”是指以生活的直白浅显方式,把那些本质的深邃晦涩、不容易为人所接受的一面与当下语境中具体的生命对接,人类生命因此而有了可供模仿的崇高对象,“神离我们太远,梦近点,艺术更近——再近,近不了了”[1]879。也就是说,人类的生活如同在黑暗中摸索,需要一种指引。神的指引离人类过于遥远,人类无法充分依靠;梦境,虽然近些,但过于随机,同样指望不上。艺术,在木心看来就算非常接近生命的一种假想完美模式。
二、艺术服务于生命成长
艺术是生命的和谐,它可以带着忙碌的人通向理想中的和谐王国。木心以绘画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画中,人多与狮和羊一起安然共听俄耳浦斯弹奏——这是人类的理想。”[1]16在这个理想国里,不但人可以和谐共处,甚至动物都能安详地享受艺术的洗礼。所以,在木心看来,一个画家不仅仅是将颜色与线条组合起来,他必须是一个集文化大成者,“画家如对世界文化缺少概念和修养,文人画就没有了。对文学、文化没有素养,会越来越糊涂”。[1]358木心因此而特别强调画家的“文学修养”,“画家也特别需要文学修养。中国画,一言以蔽之,全是文化,全是文人画。拉斐尔不及芬奇,文才不及也”[1]202。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木心尤其推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做法:“中国从前讲琴棋书画要通,今天失传了,倒霉了。现在的中国科学家,你问他音乐,他以不懂为乐。我们在西方,要通气些,他们的人文教养正常。”[1]358
人的成长,就是让生命走向完美、追求成为全才。所谓的“全才”很难有一个通行的标准,木心理解为不断地超越当前的自己,这也是对尼采“超人”学说的生动解释:“所谓超人,就是超过自己。”[1]116这种超越,当然不是简单地指身高体重的生理超越,也不是存款数字增加的经济超越,甚至也不是知识积累的心智超越。木心愿意看到的,是人籍由艺术的人性超越,也就是人的真正成长。
在后现代语境里生命仍然一如既往地需要宗教式的“虔诚”。那种对一切都怀疑的犬儒式生活态度是木心所反对的,他提出以一种“修道”的虔诚来体验艺术的教化,“修道,长期的修道。丹青在时代广场的画室,就是他的修道院,天天要去修道的。让你的艺术教育你”[1]1077。
艺术离不开“天赋”,这也是许多人以自己缺乏“天赋”为借口而拒绝亲近艺术的原因。木心用生命的“本能”来解释艺术天赋:“这种本能的选择分辨,使我相信柏拉图的话‘艺术是前世的回忆’。纪德也说得好:‘艺术是沉睡因素的唤醒。’再换句话:‘艺术要从心中寻找。’你找不到,对不起,你的后天得下功夫——你前世不是艺术家,回忆不起来啊。”[1]439无神论者木心自然不会相信什么“前世”与“轮回”之说,他所论及的“前世”实际上就是指某种艺术气质的遗传或异禀天赋。在木心看来,即使是具有艺术天赋之人,要提升自己的素养,也要通过教育来“回忆”、“唤醒”自己体内的这些天赋;而对于不具备“前世”天赋之人,就得后天多努力下功夫,一句话,人必须通过艺术来让自己走向人格的成熟。
其实阮小棉是记得的,她在装傻。她总不能告诉顾盼,那个贼她认得,叫老八,他们是同伙,她也是故意被顾盼撞到,好让老八逃之夭夭。
木心希望弘扬蔡元培所倡导的以艺术代宗教的美育理念,并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在唯心之神“退隐”之后为人性寻找的新的信仰客体。在圣经传统中,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在哲学家眼里,更倾向于接受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的观点。木心延续的正是这种“造神”思维,只不过他希望造出的神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我的定义,是‘仅次于上帝的人’”。[1]232木心生动地以“立体”与“平面”的关系来解释作为艺术家的人与万能的上帝的区别:
上帝是立体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平面的上帝。耶稣是半立体的,十字架只有正面才好看,侧面不好看,非得把耶稣钉上去才好看。艺术家要安于平面。尼采和托尔斯泰都不安于平面,想要立体,结果一个疯了,一个痴了。[1]443
木心持悲观主义生命观,他把人类自我教育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艺术上,“人世真没意思,因为真没意思,艺术才有意思”。[1]394面对人世的“真没意思”,宗教把希望寄托在“来世”,而艺术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将希望寄托于现世:
放下屠刀,不成佛,是艺术。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是宗教。苦海无边,回头不是岸,是艺术。
宗教是面值很大的空头支票,艺术是现款,而且不能有一张假钞。宗教说大话不害臊,艺术家动不动脸红,凡是宗教家大言不惭的话,艺术家打死也不肯说,宗教说了不算数,艺术是要算数的,否则就不是艺术。
艺术难,艺术家也不好意思说。[1]432
这也就是为什么木心会认为艺术比政治复杂很多,“政治家非黑即白,艺术家既非黑又非白”,因此,他的观点是“艺术家另有上帝”(或作“艺术另有摩西”)[1]645,932。艺术家由于具有“人格的自觉”,自觉到好像自然界的花叶山水也竟然“奇妙在似乎有作者”[1]232。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1]645。人的这种艺术追求与自觉需要一种高度的奉献精神,甚至要比宗教的虔诚多出更大的付出。
艺术因而是更高层面上的生命真理,因为艺术忠实地记录了生命的激情与活力。“艺术家是什么呢?现实生活中用不完用不了的热情,用到艺术中去。艺术家都是热情家,热情过盛,情种如歌德、瓦格纳,也还是把最浓的情用到艺术”。[1]414
拥抱这种更高层面的真理需要比死亡更大的勇气,木心说:“‘以死殉道易,以不死殉道难’,……不死而得道,也是‘殉’:死而不得道,是‘牺牲’;不死也不得道,是行尸走肉。牛羊死,有什么道不道。”[1]454这也是木心的艺术生命观,即艺术总是在呵护生命,追求无论在如何艰难的情形下都要努力地活下去,而且要活出生命的精彩与高贵。
艺术区别于艺术品,因为艺术是动态的,与生命同步增长。木心以写作为例,讨论写作如何贡献于书写者的生命质量的提高,他说:“写着写着,艺术家本人好起来。”[1]640他作品中有大量讨论是关于如何才能让生命质量得到提高,特别是让生命有意义。他对生命有着非常不乐观的深刻认识,但是面对并不友好的宇宙,生命却必须顽强地完成自己的美丽风景,而完成的形式却只能通过艺术。
木心讲艺术呵护人们的梦想,让人的生活永远朝向未来,“历史学家要的是‘当然’,艺术家要的是‘想当然’”。[1]50木心通过一字之变来强调艺术的“想象”空间和艺术的未来特性。
艺术的作用在于将人们曾经膜拜的神、把人们希望捕捉的梦境变成具体的审美对象,在这一点上,艺术与梦非常接近,“艺术本来也只是一个梦,不过比权势的梦、财富的梦、情欲的梦,更美一些,更持久一些,艺术,是个最好的梦。”[1]1079但艺术毕竟不是梦。木心看到用艺术创作来弥补生活中所不曾完成的诸多缺失,比如美妙的爱情。在木心看来,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只在造物者的未尽善处尽一点力”。[1]953他颠覆弗洛伊德的观点,因为弗洛伊德不是艺术家,“艺术与梦正相反,梦不能自主,不可修改,艺术是清醒的,提炼而成的”。[5]62
他崇尚纪德的一句话,“最快乐的梦,不及醒寤的一刻”。[1]634人生如梦,而最美的境界就是如梦的艺术,因为在艺术中,人是自由自主的,他的个人意志可以得到充分体现,生命的各种潜能都可以得到极致的宣泄,生命的介入也最充分。艺术中的生命介入,不是利用艺术来做事,而艺术恰恰是要懂得与生活,甚至是与说教保持相应的距离。在《素履之往》中,木心记录了这样的观察:
有这样一个记者,问这样一个画家:
“艺术是为了什么?”
这样一个画家答这样的一个记者:
“为了和平。”
我好久,好多年没有如此大的大笑了。
后来,我以极温静极忠厚的语调,电告一位朋友,他笑得掉在地上,不是身体是话筒掉在地上,笑声还听得到,他拾起话筒:
“如果是你,碰上了这样一个记者呢?”
“不会的。”
“碰上了,也提这个问题?”
“我回答:艺术是为了使人不致提出这种问题来。”[5]106
木心承认“艺术的极致竟然是道德,以音乐表现出来的道德”。[4]256但毕竟“道德”也是一种养成境界,而不是可以量化的目标,他说,“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他进一步以福克纳的观点来表明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微妙关系,“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领诺贝尔奖时说:说到底,艺术的力量,是道德力量。大鼓掌。可他平时从来不说这些大道理。他书中不宣扬道德的。”[1]555艺术践行的是“润物细无声”的间接教诲,木心将政治商业比作“动物性的战术性的”[1]953,而将文化艺术看成“植物性的战略性的”——“看起来是动物性作践着植物性,到头来植物性笼罩着动物性”[5]72,艺术就是让人在面对植物时萌发出生命的本真来,“现实归现实,艺术归艺术。艺术不能跟现实走,艺术也不可能领着现实走。所以普希金全面关注现实,而作品如此之纯。”[1]643
他曾借用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的话说,“耶稣并不是为我而来到世界”[1]596,他将耶稣理解为“集中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分散的耶稣”[1]85,“艺术家能以自身的快乐来证明世俗的快乐不是万能的”[1]86。与耶稣的艺术真诚相比,木心结论说“弄虚作假的人其实是麻木的。他们鉴貌辨色,八面玲珑,而面对自然、宇宙,极麻木。真正敏于感受,是内心真诚的人,所以耶稣见百合花就联想到所罗门。”[1]88
木心如此景仰耶稣,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希望能够重复耶稣“集中的艺术家”式生活方式,将生命作为践行艺术与文学天道的历程。因此,人就应该让艺术来“占有”自己,“如果你真能被艺术占有,你哪有时间心思去和别人鬼混,否则生活就不好玩了”[1]1080。
三、艺术与生命的完成
木心将艺术创作看作与人日常生活相平行的生活层面,“我觉得人只有一生是很寒伧的,如果能二生三生同时进行那该多好,于是兴起‘分身’、‘化身’的欲望,便以小说来满足这种欲望。”[5]61除了将自己的生命分割成不同的角色,他还戏称“美学就是我的流亡”[5]70。在流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乡愁”,在哲学的角度就成了“神学”,在文学的角度就成了“人学”[5]70,人通过这种美学、神学与人学的流亡趋于艺术的成熟。
流亡因而是一切真正艺术的“宿命”,艺术家通过逃离此地的熟悉家园,来摆脱俗世的“此处”羁绊,来通向艺术的“彼岸”:“艺术家逃艺术,是世界性的。达芬奇最要逃。《蒙娜丽莎》画了四年,其实逃了四年。”[1]1006
这种“逃亡”观,就是在希望人能够接受艺术的教化功能,走向一种生活在俗世,却能够诗意地栖居于自己精神世界的理想状态。在木心看来,人囿于自己之所得,很容易走向自恋进而束缚自己的成长,因此,人不但要从自己的物理空间中“逃亡”,而且还要学会从自己当前的所爱、所从事的活动中逃亡出来,以产生必要的审美距离。他说,
我觉得艺术、哲学、宗教,都是人类的自恋,都在适当保持距离时,才有美的可能、真的可能、善的可能。如果你把宗教当做哲学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宗教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哲学当做艺术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哲学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艺术当做宗教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艺术究竟是什么——我的意见是,将宗教作宗教来信,就迷惑了;将哲学作哲学来研究,就学究了;将艺术作艺术来玩弄,就玩世不恭了。原因,就在于太直接,是人的自我强求。[1]33
在木心看来,所谓的天才就是那些学会了如何“逃跑”的人,只有学会了逃跑,才有可能成熟,“天才的第一特征,就是逃。天才是脆弱的,易受攻击的,为了天才成熟,只有逃”[1]83。不但要逃,而且要逃得快,以“飞”的速度逃,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唯一的办法是飞。飞出迷楼。艺术家,天才,就是要飞”[1]32。木心出国去纽约一住14年,就是为了制造这种与自己熟悉生活的“距离”感。“满足于距离,纯乎求观照,一直到生命的最后。”[1]33借助于这种逃亡产生的距离感,他才认为自己看清了艺术的本质,既而学到生命的真谛,“我自己也承认,我是到了纽约才一步一步成熟起来,如果今天我还在上海,如果终生不出来,我永远是一锅夹生饭”[1]838。在生活中,人们迷失于自己的物质所得,甚至将物质所得理解为生命的终极目标,而失去了对生命本真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在另一方面,人们满足于物理家园的温馨而放弃了对精神家园的探索。从两种意义上讲,人都需要“逃离”“自我的流放”,最终流放到自己的故国家园。木心无论走到何处、走得多远,他都不曾离开自己的心、自己的根、自己深深热爱着的中国这方热土,“漫游世界,随时仰见中国的云天”[4]269,虽然他说自己是“希腊人”,崇尚以希腊为源头的欧罗巴文明,但他不忘在前面加上“绍兴的”希腊人。艺术地流亡可以让人不离故土、不违初心,更能让人永葆青春。比如“青春必须动,静的青春往往流于自残”[7]121。“青春必须动”在木心那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因为青春时期富有生命活力,有条件选择“动”,二是人动则拥有了生命活力,就保持了与年龄不太相关的“青春”。木心的“动则青春”观,即让生命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过程中,人的生命就因此而永远不会表现出衰老的迹象。我们理解木心所说的通过流亡来产生与生活的“距离”,更多的是一种审美修辞,强调“心理”审美距离,并不完全是物理意义空间距离,物理空间上的去国离乡有利于人们激活心理距离,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不然,多少人去国离乡日久,却并不足以产生自己的审美距离,并没有真正地拥抱艺术。相反,许多懂得“自我流放”的人,并未去国,仍然创造出了理想的艺术距离。木心讲“一流的艺术家,叫他做件事,他做成艺术品”[1]998。懂得了这个道理,就知道生活处处皆艺术,并不一定要远走他乡。但心要走出去,要制造与能够指向未来的与生活的距离感,不能拘泥于此地当前。只是说有条件就尽量动起来。
艺术的成长需要天赋、个人的努力,还需要各种机缘巧合,因此学习艺术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将对艺术追求的过程作为永远的“准备期”,他的艺术成就才有可能完善,“画家,艺术家,都有准备期,准备期越长,高峰期越高。准备期有两种:一是不动手,光是‘生活’,一是动手,动手的准备期”。[1]1009按照这种逻辑,如果人能够把人生作为永远的“准备期”,不但人永远都不会衰老、可以永远年轻,而且在强盛的生命力驱动之下,可以不断地创作出生命的青春。这样就有可能求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许多人追求艺术浅尝辄止,终无大成,大概就在于其准备期不够长,更在于其“作准备”的心态不够虔诚。所以,他才总结说“天才一定要晚成才好”[1]692。天才尚追求艺术的晚成,何况我们普通众生!任何一个想要成就自己生命全部潜能的人,都应该追求这一目标,不能满足于短期目标的过早实现。死亡是人生的终结,也是人生“瓜熟蒂落”的成熟,人该用自己的一生来实现自己,以期向死而生,完成生命的各种可能。
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准是与他人艺术地共享人生,这是人在其他追求方面所无法比拟的。“权势、财富,只有炫耀,不能共享,一共享,就对立了,一半财富权力给了你了。情欲呢,是两个人的事,不能有第三者。比下来,艺术是可以共享的。天性优美,才华高超,可以放在政治上、商业上、爱情上,但都会失败,失算,过气——放在艺术上最好。”[1]1079-1080
每一种艺术都是一种语言,艺术成熟因而就是在语言里的成熟,即在熟练地掌握或创造一门自己精通的语言之后熟练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意志,“音乐绘画是自己创造语言,文字呢,本身就是语言”[1]815。从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就理解了木心为什么会说“艺术家都是自我拓荒者”[4]269。
阅读木心确实能给我们许多当下语境意义。在一个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木心等于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来重新从艺术的角度学会并定义衰老。他55岁时才走出国门,开始他的艺术新生。对于这一点,他的话语中不时充满各种幽默的调侃,讲人“三十而立,指的是选择对了。选择错了,是‘三十而倒立’”,他不喜欢衰老的感觉,他有着许多人一样的希望自己永远年轻的想法,但他对生命的规律却认识得十分清楚,他以齐白石在“六十岁后才找到路”[1]672的“衰年变法”为例,表达了自己会永远追求成长的意愿——“生命的悲哀是衰老、死亡,在这之前,谁也别看不起谁。”[1]1010木心经历过多次磨难,然而却从未放弃过对文学、艺术的初心,这是他的青春常驻的“不老灵丹”。“常见人驱使自己的‘少年’‘青年’归化于自己的‘老年’。我的‘老年’‘青年’却听命于我的‘少年’。”[8]32
木心在自己的书写空间与生命空间中都一直在试图衔接东西方两大文明,在时间更是希望连接古今未来。他对古希腊罗马神话如数家珍,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自始至终都在滋润着他这块东方心田。他却并没有因此而走上“食洋不化”之路。对于他生于兹、长于兹的东方热土,他一样尽情从中吸收养分。他回忆自己的祖母、外祖母以口述的方式向他讲授《易经》《大乘五蕴论》。木心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对易经命理与释教理论的多大认同,而且他对易经命理思想与释家思想的批判还是非常尖锐的。只是他的批判同样没有妨碍他对这些经典传统哲学的接受。他的文集《素履之往》就是以《易经》“履”卦来命名的,书中不少文章的标题也都来自《易经》。《易经》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有“群经之首”的称号,作为一个中国人,生长在这种文化之中,可以不相信易经的占卜功能,却无法回避这部经典中的精髓。事实上,《易经》经历几千年的各种变迁,依然在当下的汉语文化中默默起着作用,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许多表达,像“潜龙勿用”“否极泰来”“自强不息”等都源自易经。《易经》记载着东方智慧对“天道”的素朴理解。在西方《圣经》传统就是“太初有言”的古希腊、罗马的“逻各斯”传统,在东方相应地就是“太初有象”的艺术诗学传统。
木心是艺术的“殉道者”,他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相关联,自认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他拥有了许多的同道,只不过这些同道在不同的时期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的:
生在十七世纪可能是个苦行僧,生在十八世纪可能是个启蒙运动者,生在十九世纪可能是个花花公子,我宁愿生于二十世纪初叶,得以目睹法西斯的灭亡,基督的敌人败绩了,但不幸也看到艺术被蹂躏,文学奄奄一息。[9]99
他没有喊出“救救艺术”这样的口号,他知道喊也没有用。而且作为一个有着贵族情结的诗人,他也不屑于去喊这样的口号。他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不受干扰地生活在诗的王国里,自己独立为王。
四、结 语
木心一生通过自己的文字、讲课,臧否过不少古今历史人物。他喜欢用“完成”与“行过”来评价别人。他自己到底是“完成”还是“行过”的一生,恐怕要留待更后来的读者在有了一定的阅读距离之后再来定论。但木心在自己一生中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必定是评定他生命成就的不二标准。木心强调在人生的任何节点,当人感觉到自己还能够可以做出选择与判断、能够操控生命进程之时,他就应该以积极的方式去争得生命的最大自由,去印证自己生命的意义,而这种自由却只能通过艺术来获取,他在《此岸的克利斯朵夫》中的一段话,或许能作为他艺术地美育人生的最好注脚:
艺术家如蛾扑火地爱美,必须受折磨受苦,百般奋斗,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欲而是不被卑下的情欲制服,几次三番地死而复活,终于成功,一成功就不会失败了。[10]158
“飞蛾扑火”是一种艺术的执着,如宗教之人对神的信仰,至死不渝。这种执着源自人性的向上追求。艺术让人性得以提升、进步,让个体的人可以永远处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
[1] 木心.文学回忆录[M].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 林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木心:干净地来安静地走[N].中国青年报,2011-12-28(10).
[3] 木心.庖鱼及宾[M]//素履之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14.
[4] 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 木心.仲夏开轩[M]//鱼丽之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9-76.
[6] 木心.舍车而徙[M]//素履之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04-111.
[7] 木心.战后嘉年华[M]//鱼丽之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05-134.
[8] 木心.海峡传声[M]//鱼丽之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38.
[9] 木心.迟迟告白[M]//鱼丽之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7-104.
[10] 木心.此岸的克利斯朵夫[M]//温莎墓园日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55-182.
(责任编辑:刘 琴)
Muxin′s Ideas on Art Education and the Fulfillment of Life
DENG Tian-z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It can be seen in all of Muxin artistic creation and teaching that he espouses Cai Yuanpei′s "substitu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religion". This paper seeks, by a review of his aesthetic thought in his works and teachings, to look at his redeeming power of art. Muxin believes that art turns "possibility" into "probability", making up for what has been lost or is absent in life. Art aims for the harmony of life, leading the busy life to the ideal kingdom. It contributes to growth of life. Granted that growth in art depends on natural endowments, it requires personal perspiration nonetheless, plus an assortment of chances. Consequently, patience is of prime importance in one′s artistic growth. Only when artistic pursuit is treated as a perpetual preparation for life can art help fulfill one′s life. With art one may distance himself from daily life and cultivate parallel lives so that art can furnish a free space for the fulfillment of life.
Muxin; idea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redeeming power of art
2017-02-03
邓天中(1966—),男,安徽宿松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木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理论研究。
I206.7;G40-014
A
2095-0012(2017)02-004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