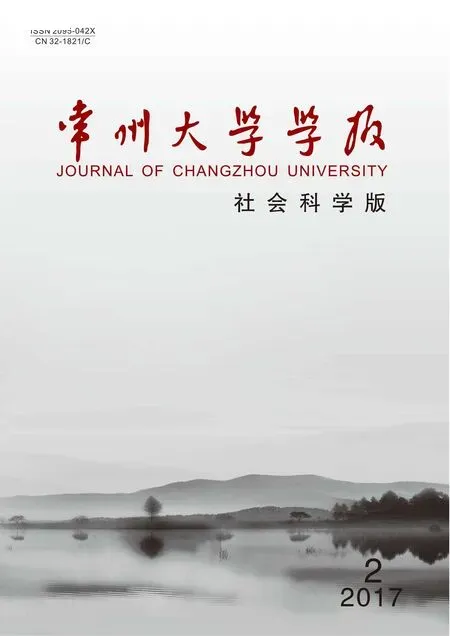论晚明善书对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通俗小说教化性质为核心的讨论
2017-03-24郑珊珊
郑珊珊
论晚明善书对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通俗小说教化性质为核心的讨论
郑珊珊
晚明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和道德秩序的淆乱激起了士人的“经世”意识,劝善的取向日益在当时和后世的言说与叙述中凸现出来。以善书创作和传播为主的各种劝善活动渗透到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对同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文章从纪事性劝善故事、民间劝善文和“圣谕六言”的宣讲三个方面来探讨善书对晚明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
教化;劝善故事;劝善文;圣谕六言;通俗小说
对于晚明以来通俗小说创作中显示出的教化取向,学界多有阐发,所不同者在于各自选取的角度。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小说编撰中存在的教化意图,乃是受到儒学世俗化、实用化的影响[1];或者将教化归因于明末社会精英有激于时代的危机感而产生的强烈的救世心理[2];又或者归因于小说家悲天悯人、欲普渡众生的“宗教情怀”[3]。以上诸论都注意到了时代对于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取视的角度不同,立论自然有所差异,此自不待言。学界对于善书与小说的研究成果不多,迄今为止仅有数篇单篇论文。日本学者小川阳一有《明代小说与善书》《三言二拍与善书》《西湖二集与善书》等专篇论文讨论善书与小说的关系,旨在说明善书对小说存在的影响。而国内讨论善书和小说关系的寥寥数篇文章皆从信仰和观念的角度立论,目前尚未见从小说教化性质的视角讨论善书和小说关系者。
一、晚明小说教化功能彰显的历史语境
晚明以来,善书的制作和传播在民间达到高潮,以此为标志形成了酒井忠夫所谓的“善书运动”[4]17。所谓“善书”,一般认为产生于宋代,兴盛于晚明清初,系融合了三教思想,通过果报观念宣扬福善祸淫思想,以指导人们把握自己道德行为的劝善之书。
对小说教化性质的最早规定应溯源至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班固虽然将小说置于十家的末流,以为“可观者”前九家而已,但仍然期冀小说有“一言可采”[5]。在中国传统文化泛道德主义倾向的影响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一直无法摆脱教化的取向。晚明清初是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鼎盛时期,同时也正是中国传统中的劝善文化臻至鼎盛的时期。除时间的重合外,小说和善书制作、传播的地域空间也多有重合,故善书与通俗小说这两种书写形式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在“善书运动”的影响之下,甚至还出现了清初《雨花香》《通天乐》这种既可视作善书,亦可视作小说的文体边界模糊的书写形式。
晚明以来通俗小说创作的劝善和教化意图从书名中即可看出,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石点头》《醉醒石》《鸳鸯针》《清夜钟》等,在编撰和刊行的序跋中,警世劝善的意图昭示得更加清晰,试举几例:
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6]773
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6]789
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笑花主人《古今奇观序》)[6]793
这种举例可以一直进行下去。以上的序言中,作者无一例外地都对小说的教化功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以为能够补经史之不足,甚至发挥儒家经典所不能发挥的作用。这到底是一种过分的谬赞,是行文的格套,抑或仅是宣传的策略?解读这些言说方式,需要将通俗小说的创作尽量还原到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发掘文本中所隐藏的历史信息。晚明以来蓬勃发展的“善书运动”为我们解读同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中存在的教化取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而“善书运动”的开展又离不开彼时纷繁复杂的历史时空。
第一,晚明“善书运动”的展开与儒家士人的经世意识有密切关系。晚明以来,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酝酿、激化,儒学传统中的“经世”取向在当时和后世的言说和叙述中日益凸显。所谓“经世”,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入世”的精神,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一种思想,并不为某个时代所特有。在晚明,“经世”思想有一种具体表现,即士人期望通过各种“劝善”的形式来引导淆乱的社会价值,重整道德秩序,安顿人心,救治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劝善”甚至成为鉴定士人品性的一个标准,刘宗周《人谱类记增订五·考旋篇》中将“记警不善劝化愚人”[7] 90作为士人“改过”与“修身”的一个内容,这固然体现了晚明道德严格主义者的一种严峻姿态,但也部分显示了此时民间社会中的一种“劝善”的取向。
以往论晚明文化和思想者多注意于当时士风的浇漓,士人的游谈无根,而彼时士人中对“经世”“任事”“实用”“践履”的热衷和谈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陈宝良认为明代中后期自有一种独立于王学之外的“实学”思潮[8]。这一观点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晚明“实学”的标举,如陈氏自己所言,此乃是一种“新说”,然这一实学思潮是否独立于王学之外,却值得商榷。商传也肯定了明后期的“实学”之风,然而恰与陈氏的观点相左,他认为这一“实学”精神的产生正要从王学本身的发展理路中去探寻,并指出泰州学派以“救世之心”将“学术”和民众结合到了一起[9]。赵园在《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中专辟一章讨论彼时士大夫的“经世”与“任事”[10]。赵园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明末社会曾经发生一场士大夫的“修身运动”,认为儒家士大夫通过撰写儒门善书申明儒学原则,校正道德修省中的功利主义倾向,通过“修身”重建儒家道德伦理秩序[11]。如赵园所言,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修身”与“经世”实则已合二为一,这既是对彼时背离正统轨道之士风和世风的纠偏,同时也是对传统儒学的复归。这也正是明清之际劝善文化赖以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背景。王汎森在《清初的下层经世思想》一文中提出了“下层经世”的说法[12],尽管题为“清初”,议论的范围却上溯至晚明。吴震在《明末清初善书运动思想研究》一书中也对“下层经世”的提法一再使用[13]。虽然“下层经世”在学者不同的治学理路中所指有不同的侧重,但是基本都能将儒者通过劝善对民间下层社会进行道德劝化,从而重整道德秩序这一层意涵包括在内。
第二,明代的教化政策,尤其是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对“善书运动”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圣谕宣讲的背景离不开明代的朝廷教化政策,有明一代自洪武开国至崇祯时期朝廷不断地颁布各种类型的劝诫书。据酒井忠夫在《中国善书研究》一书中的考证,一共有五十七种,且大部分是在洪武、永乐、宣德年间颁布的,其中仅太祖朝颁布的就有三十六种[4]23-42,可以说明朝廷的劝化政策在太祖时就基本确定了。由朝廷颁布的各种类型的劝诫书,内容体裁多以民间易于接受的方式著成,对民间教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酒井忠夫认为对民间教化影响尤大的是《大诰三编》《教民榜文》《劝善书》《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五伦书》《女训》等[4]46。
根据酒井忠夫的研究,“圣谕六言” 在明初是在里甲制下通过木铎老人的直言宣讲在民间进行教化,嘉靖八年(1527)以后开始出现与乡约结合的契机,又渐渐地渗透入社学、家训。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由明初的直言宣教演变成解释演义,酒井忠夫先生在《明朝的教化政策及其影响》[4]60一文有详文阐释,此处不赘。圣谕也因其教化和劝善功能而与善书产生种种关联。这表现在,一方面,一些大型善书往往将圣谕也收录其中,作为善书的一个类别来对待,如明末的善书《劝善全书》中收录淮安李长科所辑的《圣谕六言解》,正是将六谕的演说内容作为善书来对待[4]70;另一方面,圣谕的宣讲往往借助于民间流行的善书故事,发展至清代遂成格套,如王尔敏指出,为吸引广大民众,清代“‘宣讲圣谕’通行民间,在内容上就知书之士,多予附加民间流行善书,尤其故事性之短篇说唱,成为《圣谕》之外之附加品,并在民间兴盛流传”[14]。
明中叶以来,致力于民间教化的儒者格外重视圣谕六言的劝善功能。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提到“圣谕六言”,尽管态度并不是十分积极和明确,但有学者认为这是明代社会思想史上“将‘六谕’与《乡约》相结合,以便进一步加强‘劝善规过’的教化作用”的首例[13]45。之后王艮、王栋、罗汝芳、周汝登等王门学者都非常关注“圣谕六言”对于社会的劝善与教化的积极意义[13]45-48。除以上王门学者而外,明末一些具有强烈经世意识的大儒,如陈瑚、高攀龙、刘宗周等在推行教化时亦往往称说“圣谕六言”。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已成为晚明以来“善书运动”中一种不可缺少的资源。
第三,晚明以来的“善书运动”还与心学思潮有紧密关联。心学与善书的关系从善书的撰作者、传播者、同情者多是具有心学学术背景的士人这一现象中能够窥出一些端倪。心学理论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其与“善书运动”必然产生紧密的联属。一方面,阳明学对于下层社会秩序的关注和对于通俗文化教化功能的重视都包蕴了之后“善书运动”所具备的要素。另一方面,心学的发展在消释和解放了原先具有一定程度负面意义的理学概念的同时,也导致了儒家道德严格主义的立场,而这种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儒门善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在晚明汹涌而至的“善书运动”中,儒家士人通过修省和劝善来完善自我道德,并重新厘定社会道德秩序,晚明社会掀起的“修身运动”和“经世思潮”也在这一风潮中统一起来。
通俗文学对民间教化的介入和影响就在这种历史语境下被凸显出来。儒家精英思想能够影响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如果要对广大的下层民众进行宣教,不可能依靠四书五经,而包括小说、戏曲等在内的通俗文学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尽管一些持身严正的儒家士人对小说、戏曲中奸邪淫盗每每痛加斥责,但还是不能无视通俗文学在下层民众中巨大的教化作用,只要能够“化民成俗”,甚至对小说、戏曲中不合于正统儒家思想的果报观念也会采取包容的态度。如,刘宗周曾经严厉地谴责袁黄的《了凡四训》中的功利主义思想,并亲自编撰了儒门善书《人谱》。他在《人谱类记增订五·考旋篇》的第四十一条“记警观戏剧”中谈论戏曲对民间的影响时却能够正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
梨园唱剧至今日而滥觞极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废,但其中所演传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从此设法立教,虽无益之事,未必非转移风俗之一机也。[7]63
又引用陶奭龄的话:
先辈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乐章也。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观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百倍。至于《渡蚁》《还带》等剧,更能使人知因果报应秋毫不爽。杀盗淫妄,不觉自化,而好生乐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则虽戏而有意者也。[7]64
谈论的虽是戏曲,但对小说也同样适用,并且晚明以来的戏曲和小说创作题材往往互有借鉴,如文中所说《渡蚁》《还带》指的是“宋庠渡蚁”“裴度还带”,是善书、小说和戏曲中经常出现的故事典型。从刘宗周和陶奭龄对戏曲教化功能的谈论中,可见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形式对下层教化的巨大影响已成为一部分士人的共识。通俗小说的作者基本上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他们不可能完全抗拒正统儒家崇高的“经世”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下层民众分享着共同的民间文化信仰。在通俗文化日益繁荣的晚明社会,通过小说宣扬“劝善”思想,寄寓情怀的同时教化民众,成为当时士人的一种人生选择。
善书内容驳杂,体例不一,大型善书一直存在着归类的困境。但总体而言,其范畴除包括经典的“三圣经”,即《感应篇》《阴骘文》和《觉世经》之外,还应包括宝卷、圣谕、清言、格言、诫子书、蒙学书等具有教化性质的书写形式。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拟从纪事性劝善故事、劝善文和圣谕宣讲三个方面来讨论“善书运动”对晚明以来通俗小说的教化取向产生的影响。
二、纪事性劝善故事与通俗小说创作
所谓“纪事性劝善故事”指的是各种善书中具有明确的劝诫意图和鲜明的果报色彩的经典叙事模式。民间流传的善书有“说理”和“纪事”两种形式。这种形式的划分只是根据“说理”或“纪事”在善书中所占的分量,其实“说理”和“纪事”往往相随相伴,即便是在说理性善书中也会同时引用一些果报故事,以证明所言不诬。这些经典故事有的来源于历代相传的阴骘故事,多出自于文人笔记;有的则是当下发生的流传较广的果报事件,一般通过比较完整的叙事来宣扬福善祸淫的果报思想,从而最终达到劝善的目的。由于果报思想最易于被下层民众接受,最具有震慑力,故而此类叙事模式常常出现在晚明各类善书的编撰中。由于善书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此类经典的纪事性劝善故事如“裴度还带”“两宋渡蚁”“窦谏议还金”等在通俗小说中频繁地出现[15]276-287。限于篇幅,以下仅以“裴度还带”为典范,简单地讨论善书中经典的纪事性劝善故事对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
“裴度还带”大概情节是裴度因拾得宝带归还失主而救人一命,最后以此阴功受报,位极人臣。这个故事在宋以来的稗官野史、戏曲小说、民间善书中反复出现。袁啸波辑录的《民间劝善书》中有一篇《劝善录》,作者题为秦观,其中收录了“裴度还带”。这篇《劝善录》载于明沈节甫所辑《由醇录》,托名宋秦观编,主要搜集为善获福,作恶招祸的事例,用以劝善。据袁氏考证,《由醇录》与《百川学海》中所收宋陈录之《善诱文》内容相同处不少,而袁氏辑录《劝善录》时正是依据《善诱文》来订正个别错讹处[15]275。由此可见宋明以来,民间社会中流传的劝善资源是如何在不同时代的文人笔下代代相传的。除善书而外,《唐摭言》《玉堂闲话》《唐语林》《类说》《太平广记》《情史》等五代以来的笔记小说对“裴度还带”也都有收录,元明两代戏曲已知有关汉卿《裴度还带》、无名氏《还带记》对之进行了演绎[16]。晚明以来,随着“劝善”在下层社会的盛行,“裴度还带”一类的历史故事作为劝谕教化的资源一再被通俗小说引用、敷衍。限于篇幅,笔者以下仅以分析“裴度还带”对“三言”“二拍”的影响为范式来考察历史上的纪事性劝善故事对晚明以来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
“裴度还带”在“三言”“二拍”中作为劝谕的典型事例反复出现:有作为入话,如《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以“裴度还带”的故事作为入话,引出正话,演绎了另一个阴骘受报的故事[17];也有将裴度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将其生平所作包括“还带”在内的善事串在一起,演绎成裴度积善获福的故事,如《喻世明言》卷九《裴晋公义还原配》[18]142-150;又或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如在《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入话中,卖油郎金孝捡了三十两银子,本想作为贩油的本钱,却被母亲劝住,金母用以劝诫金孝的事例正是“裴度还带”:
我儿,常言道:贫富皆由命。你若命该享用,不生在挑油担的人家来了。……曾闻古人裴度还带积德。你今日原到拾银之处,看有甚人来寻,便引来还他原物,也是一番阴德,皇天必不负你。[18]40-41
这里“裴度还带”的故事成了金母劝诫儿子的典型事例,情节在这里发生第一次转折。金孝因此改变了初衷,将银子还给失主,不料却反遭失主诬陷,双方对簿公堂,最终却经由县尹裁判,金孝反得了银子,失主含羞噙泪而去,众人无不称快。小说情节一转再转,但不过是“裴度还带”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演绎,而金母的劝诫在这里成了故事发展的转折点,这个转折正是通过“裴度还带”的故事来实现的。
以上仅举数例以说明善书中经典的纪事性劝善故事对晚明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通过以上的考察似乎可以认为,宋元明以来的文人笔记小说、善书、戏曲和通俗小说中的劝善事迹,往往是通过世代相传和交互借鉴的形式不断地发展、流传。小说、戏曲和善书由于采取了大众易知易晓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得这类劝善故事流传得更广,比起文人笔记,小说能够更大地发挥劝善教化的作用。
三、劝善文与通俗小说创作
所谓“劝善文”指的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劝谕性的文章,是常见的善书编撰形式。内容包含说理与叙事,一般篇幅短小,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的色彩。这类劝善文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日常道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民间劝善文中的“惜字”观念对通俗小说的影响来进行考察。
劝善文中有不少关于“惜字”的劝谕,如《文昌帝君阴骘文》中的“勿弃字纸”[15]7,《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中以“秽溺字纸”为恶事[15]8,刘宗周《人谱续篇三·纪过格》“业过”中有“弃字毁纸”条[7]10。《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则针对当时不能“惜书”“惜字”的风气,尤其是对儒家书籍的不敬惜,通过一些果报事件劝诫世人敬惜字纸。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事件是宋代王曾因其父敬重字纸而状元及第。“宋朝王沂公,其父见字纸遗坠,必掇拾,以香汤洗烧之,一夕梦宣圣附(疑为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纸之勤也!恨汝老矣,无可成就,他日当令曾参来汝家受生,显大门户。未几,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状元第。”[15]41-42这一事迹在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九“王沂公生”条、刘宗周《人谱类记增订五·考旋篇》“记警弃毁字纸第八十六”[7]96中皆有记录,文字大同小异。可关注者是郎瑛《七修类稿》,该条目中有“《文昌化书》后载梓潼神降笔《劝敬字纸文》”[19]的一句记录,《文昌化书》也即是《梓潼帝君化书》,《明史·礼志四》云:
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20]
《正统道藏》“洞真部谱箓类”收录《梓潼帝君化书》,然而《劝敬字纸文》却并不在其中,而是附在“洞真部谱箓类”的《清河内传》之后。《梓潼帝君化书》叙述梓潼文昌帝君历世显化的事迹,而《清河内传》则是文昌帝君自述家世生平,内容不同,不知郎瑛何以有这样的记录。但是通过以上考察可知,《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在明代是一篇流传较广的劝善文,在文昌信仰遍布民间的同时,“惜字”的观念在当时应当是被人们所熟知的。
“敬惜字纸” 这种观念在通俗小说中时有体现,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入话中有一段文字:
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它不消说;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流传,同于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只要能存心的人,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21]
所引内容前半部分以议论的方式劝人惜字,后半部分用以劝善的果报事件正是《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中的王曾事。
除此外,《西湖二集》卷四《愚郡守玉殿生春》中也讲述了一个阴德受报的故事。主人公赵雄“生来不十分聪明,说话又不伶俐”,但却有不同常人之处——极是敬重字纸。在闻知王曾的父亲因敬重字纸,儿子王曾连中三元的故事后,赵雄对字纸更加虔敬。
遂虔诚发心,敬重字纸,如同珍宝一般,再不轻弃。果然念头虔诚,自有报应。后来父母与他纳了个上舍,不过要他撑持门户而已;将近三十岁,那笔下“之乎者也”一发写得顺溜起来,与原来大不相同。[22]7
这分明又是一桩惜字受报的故事。之后进京面圣,又梦见文昌帝君降临,且帝君对其云:“上帝以汝敬重字纸,阴功浩大,做官爱民恤物,今特佑汝。”又面授机宜,赵雄因此博得龙颜大悦[22]17-18。在这一则故事中,文昌信仰和《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中的“惜字”的观念对小说的叙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劝善文的内容涉及日常道德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各种劝善文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对当时的通俗小说创作产生影响,通俗小说的教化功能在这种语境下自然地凸现出来。
四、“圣谕六言”宣讲与通俗小说的创作
“圣谕六言”或“圣训六言”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出自洪武三十一年(1398)刊布的《教民榜文》第十九条[23]。
“圣谕六言”作为善书编撰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资源对民间教化的深远影响也投射到通俗小说的创作中。晚明邓志谟的《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共十五卷,虽然主要讲述的是道教人物许逊学道求仙和六次斩蛟的故事,但在第一回到第八回的叙事中却不断地插入一些果报事件和对儒家伦理的宣讲。如第二回“孝悌王传授秘诀 汉兰公三生解化”中,借孝悌王之口大谈历史上儒家人物的孝顺故事;第七回“真君辞父母赴任 真君任所施德政”中通过对妻杀亲夫、兄弟争财等几桩关涉家庭伦理的案件的审理,将许逊塑造成了劝善惩恶的“神君”[24]35-39;第八回“许旌阳弃职归回 真君为男女完娶”中,许逊见天下已不可为,于是解官东归,临行时对挽留的百姓道:
尔等子民各务生业,圣谕有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此数句言语,各要遵守。[24]42
许逊口中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正是太祖的“圣谕六言”,不差分毫。邓志谟生活的晚明时代,“劝善”已成为一种很突出的现象。“圣谕六言”通过乡约、家训、蒙学的渗透,已经成为民间熟悉的劝善资源,出现在此时的通俗小说中,也就不足为奇。
除此之外,《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西门庆挟恨责平安 书童儿妆旦劝狎客”中也出现了“太祖圣谕”。这回文字以一首劝谕性的七律开头,接着引出一段议论:
此八句单说为人知父母,必须自幼训教子孙,读书学礼,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各安生理。[25]
除了没有“毋作非为”,“六言”基本上都出现了。这一小段文字的妙处在于,作者希图借助“圣谕六言”来表明自己劝谕的态度或意图。
明末的拟话本小说集《醉醒石》中也有两篇小说提到了“圣谕六言”,分别是第九回“逞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和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 愚术士空设逆谋”。前者只在篇首的一段议论文字中出现:
独有做不好事的,或出孟浪,或极机巧,事成总归奸盗诈伪,不成不免绞斩徒流。这结果,这名目,大有可笑。但担着这没结果,没名目,去图名图利,还道贪几时的快活,也不免是个剖腹藏珠。若到酒色上快活,只在须臾,著甚来由要紧?这正是太祖高皇帝六论中所禁:“毋作非为。”奈何人不知省。[26]1
六言只引用了其中的与全篇主题密切相关的一言。在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 愚术士空设逆谋”中,恰出现在篇末的议论文字中:
我想四民中,士图个做官,农图个保守家业,工商图个擢利,这就够了。 至于九流,脱骗个把钱糊口,也须说话循理。僧道高的明心见性,养性修真,以了生死。下等诵经祝圣,以膳余生。这就是明朝太祖高皇帝所云“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也。[26] 20
用议论文字作结,以“圣谕六言”中“各安生理,无(毋)作非为”点醒心存觊觎的愚妄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拟话本小说集《石点头》的第六回“乞丐妇重配鸾俦”中“圣谕六言”的出现。这回文字说的是以编织芦苇席为生的周六,有一个女儿名长寿,经胥老人做媒嫁给了刘五的儿子刘大。刘大合家却嫌弃长寿,打算将她遣送回家,于是又找到胥老人。正值老人沿门摇铎,念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没念完却被一桩争吵打搅,老人从中解劝了一番,两家方才撒手。于是,老人接着摇铎念道:“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27]6这是“六言”的第一次出现。第二次是在长寿被遗弃之后沿街乞讨,叫唱莲花落。
一日叫化到一个村中,这村名为垫角村,人居稠密,十分热闹。听见他当街叫唱,男男女女,拥做一堆观看。内中一人说道:“叫化丫头,唱一个六言歌上第一句与我听。”长寿姐随口唱道:“我的爹,我的娘,爹娘养我要风光。命里无缘弗带得,苦恼子,沿街求讨好凄凉。孝顺,没思量。”……又有人问道:“毋作非为怎么唱?”长寿姐道:“唱了半日,不觉口干,我且说一只西江月词,与你众客官听着。本分须教本分,为非切莫为非。倘然一着有差池,祸患从此做起。大则钳锤到颈,大则竹木敲皮。爹生娘养要思之,从此回嗔作喜。” 说罢,蹋地而坐,收却鼓板,闭目无言。众人喝采道:“好个聪明叫化丫头,六言歌化作许多套数,胥老人是精迟货了。”[27]9-11
如此一直从“孝顺父母”唱到“毋作非为”。这段文字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首先,根据这段叙述可知,圣谕宣讲和民间说唱曲艺相结合之后,木铎老人直言叫唤可能并没有立即消失,两者应当并存了一段时间。其次,小说生动地再现了民众对新的宣讲形式的喜爱,对木铎老人直言叫唤的腻烦,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后者逐渐被取代的原因。这篇小说艺术成就并不高,但为后世生动地展现了“圣谕六言”在民间宣讲的景象,保留了一段具有史料价值的社会生活场景。
“圣谕六言”作为一种制度虽然颁布于洪武时期,但其思想资源应该可以追溯得更远,至少在南宋时,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士人的民间社会实践理念就为明初的“圣谕六言”提供了借鉴。早期研究善书的日本学者就认为,明初劝谕的内容源自于宋学,酒井忠夫也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推测,“明初的儒学,在以朱子的说教为主流的、实践的方面,在朱子学中把家族,乡闾的规范被整理出来,这是当然的事。六谕中没有忠的项目,也可以理解为六谕的道德意识的源自朱子学的传统而根据四书而来”[4]54。这其实是对“圣谕六言”源自儒家思想资源的一种肯定,也显示了儒家伦理思想通过教化的施行而民间化的轨迹。
五、结语
“教化”是中国文学阐释中一个重要的传统,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对通俗小说教化的解读可能出现两种反差较大的倾向,或是罔顾文本现实,过于夸大小说的教化功能;或是脱离创作的历史和思想背景,无视或歪曲小说的教化意义。本文无意于对晚明以来小说的创作和阐释进行某种非此即彼的断言和概括,对各种思想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也不敢轻率,只试图通过梳理文献,考镜源流,从彼时的言论和叙述中撷取出思想发展中的一种劝善与教化的取向,并将对晚明小说的解读放置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背景下,来重新估量这一时期通俗小说所呈现出的教化意义。
[1]聂春艳.论儒学、理学的世俗化、实用化与明清小说[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32-36.
[2]王言锋.论明末救世心理对拟话本创作的影响[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09(6):112-114.
[3]杨宗红.明清之际话本小说家的宗教情怀[J].天中学刊,2008(3):75-78.
[4]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 [M].增补版.刘岳兵,何英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5] 班固.汉书:卷三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745.
[6]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7] 刘宗周.人谱(附类记)[M]//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8] 陈宝良.明代文化历程新说[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126-127.
[9] 商传.明代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301-307.
[10]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
[11] 赵园.《人谱》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J].河北学刊,2006(1):42-52.
[12]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68.
[13] 吴震.明末清初善书运动思想研究[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
[14] 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J].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22):257-279.
[15] 袁啸波.民间劝善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6] 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7-52.
[17] 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50-351.
[18] 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9] 郎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516.
[20]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08.
[21]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3.
[22] 周清原.西湖二集[M] ∥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一辑.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23] 张鹵.教民榜文[M] ∥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55.
[24] 邓志谟.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M]∥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七辑.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25]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298.
[26]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M]∥明清善书小说丛刊初编:第一辑.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27] 古吴龙子犹.石点头[M]∥明清善书小说丛刊初编:第一辑.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On Impacts of Morality Books on Popular Novels: A Discussionon the Basis of Enlightenment of Popular Fictions
Zheng Shanshan
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confusion of the moral order provoked society-rescue awarenes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a trend of leading to goodness was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in expression and narration at the time and later. Various forms of activities that led to goodness, mainly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books concerning goodness, permeated in all the aspects of social life, and brought impacts to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novels during the period. Influences of morality books on popular novels are discussed concerning goodness-encouraging stories, folk goodness-encouraging essays and Six Words by Zhu Yuanzhang.
enlightenment; goodness-encouraging stories; goodness-encouraging essays; Six Words by Zhu Yuanzhang; popular novels
郑珊珊,文学博士,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儒学的世俗化与民间文化心理”(08JJD840200)。
I207.41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2.014
2016-11-23;责任编辑:陈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