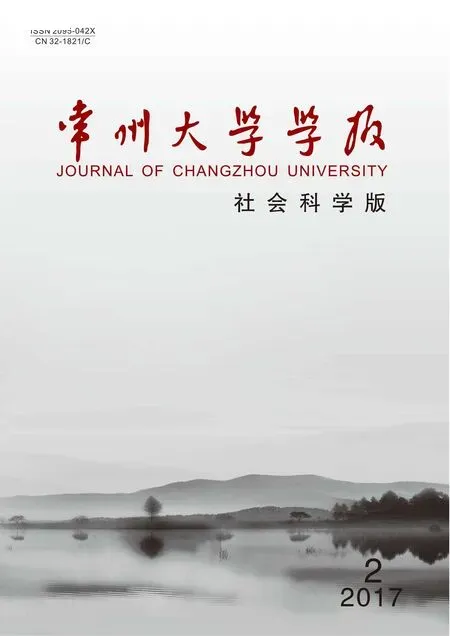汪荣宝与北京政府后期的中日商约交涉
2017-03-24翁敏,陈洁
翁 敏,陈 洁
汪荣宝与北京政府后期的中日商约交涉
翁 敏,陈 洁
北京政府的修约实践及努力,是近代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重要一环。北京政府时期以中比商约期满为契机,掀起了与各国修改商约的外交浪潮,其中尤以中日商约交涉最为当时舆论瞩目。驻日公使汪荣宝几乎见证了中日改订商约交涉的全过程,特别是在北京政府后期进行的中日商约谈判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推动商约交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但是,日本方面的一味拖延,以及交涉中中国自身存在的种种局限,严重制约了商约交涉的进展。
北京政府;中日商约交涉;汪荣宝
中日商约交涉是北京政府后期修约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中外舆论所关注的焦点。北京政府为促使商约谈判取得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亦期之成为中国订结对外相互平等条约之先声。本文拟围绕驻日公使汪荣宝与中日商约交涉的复杂关系展开研究,系统考察北京政府后期中日修改商约的缘起及其交涉过程,深入探讨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驻日使馆在改订商约中的良性互动,以及这一时期中日商约交涉失败的原因,以冀有助于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研究,更好把握近代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脉络。
一、汪荣宝使日与中日商约的到期问题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交流频繁。从清末开始,随着留日学生的不断增多,中日间各领域联系日益密切,中日外交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北京政府成立以后,中日两国为使中日邦交益加巩固,都把发展两国间的关系作为自己外交的优先方向。然而,自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以来,中国外交屡遭挫折,中外关系受到很大冲击,中日关系也因山东问题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同时,中日其他领域的冲突和摩擦逐渐增多,使得原本紧张的中日关系更加扑朔迷离,极大考验着当时中国外交官员的智慧和能力。驻日公使作为处理中日争端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经常为妥善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而忙碌奔波于一线,职责重大。
1922年,中国驻日特命全权公使胡惟德因公回国,导致中国驻日公使一职空缺。为免中日外交不受大的波动,北京政府外交部决定从驻外使节中遴选出色的外交官,以堪重任。虑及当时中日关系正处敏感而又多变的阶段,担任驻日公使的人选除须具备高超的外交艺术外,还须对日本有较深的了解。北京政府外交部通过对驻外官员的综合考察后发现,汪荣宝可堪大任。“汪氏久居外交界,且驻欧多年,除练达普通外交事务,通晓世界大势外,其学术亦颇足称述。西洋学术固颇渊博,东洋学术尤深研究,即人格亦极高尚,素为中外所敬服。”[1]而且,汪荣宝曾留学日本,对日本知之甚深。基于以上考量,外部于同年6月任命驻瑞公使汪荣宝转任驻日公使,令其从瑞士径赴日本履职,处理其前任遗留下的众多棘手问题。按照计划,汪荣宝原拟9月10日由瑞士直往日本履新,但得知政府现积欠使馆经费及留学各费,共有八九百万日金之巨,亦深悉无法应付,故未立即启程前往[2]。汪荣宝深知:“历任驻日公使之最为顾虑者,厥为留日学生经费之困难问题,倘此项经费无着,即漫然就任,则余朝抵东京夕,必遭学生之包围。”[3]为解决各项经费的着落问题,汪荣宝与北京中央政府经过反复的沟通与磋商,达成妥协,“留学生经费,由崇文门税款项下月拨二万五千元,不够之处再由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资金项下拨款补助;使馆经费,如果发行五百万国库券,则可如数支给”[4]。后顾之忧解决后,汪荣宝于1923年12月15日离京赴任,12月底抵达东京。从汪荣宝受命为驻日公使到正式抵日的漫长过程中,足以说明汪氏深谙内政外交之道,实为可用之才。
对于中日关系,汪荣宝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余留欧八年,方始归国,离日已二十余年,今再使日本,中日间外交之纷杂,亦必不如两国外交险恶声势之大,两国苟能开诚布公,则一切问题均当不难解决云。”[3]正是基于对中日时局的正确认知,汪荣宝就任伊始,积极与日方展开相关谈判。由于中日间急待办理事务甚多,汪荣宝选择以中日之间留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作为谈判的突破口,以期促进中日间其他问题交涉的妥善解决。诚如时论所言:“汪氏之赴任,除望其急谋两国普通外交关系之进步外,更信其致力两国文化关系之发展。”[1]历经数次谈判和协商,中日两国于1924年2月签署《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该协定详细规定了日本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举办各种文化事业的内容,对中日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实际上,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也带有文化侵略的某些性质,身为协定签字代表的汪荣宝难免受到来自国内文化界的批评和质疑[5]311-312。尽管责备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汪荣宝依然努力维持着中日关系大局。当中日文化教育事业交涉在招致多方非议的境况下结束时,汪荣宝及使馆人员旋因中日商约的期满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日外交活动。
中日商约系指《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该约于1896年10月20日互换,算至1926年10月20日,复届十年期满。根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第二十六款之规定:“此次所定税则及此约内关涉通商各条款,日后如有一国再欲重修,由换约之日起,以十年为限,期满后须于六个月内知照,酌量更改。若两国彼此均未声明更改,则条款税则仍照前办理,复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后均照此限此式办理。”[6]按照此款条文所载,“自满期之日起六个月内,如有一方提议,可于六个月期内开会协商修改”,1906年和1916年两次期满时,本可为修约之主张,乃因吾国政府未经提议,致令逾期仍继续有效,实为错失修约之良机[7]。今届第三次修改之期将满,国外侨胞及国内官商,均有改订新约之主张,此诚吾国外交史上之重要时机也[8]5。针对中日商约的到期这一问题,有时人大声疾呼称:“但满期之约,若不乘机修改,则将错过时会,永无修改之日矣。”[9]马寅初先生更是直接痛陈道:“今日改订之机会又至矣,若不要求改订,日后之权利丧失,又不可以数计。况中比商约与中日商约,为最先满期之条约,期满而又不能改订,则此例一开,将来凡有条约满期者,均可引以为例,而丧权辱国之条约,将永无彻底消灭之一日矣。”[8]6面对国内日益高昂的“请废旧约,另订平等待遇之新约”之声浪,北京政府外交部及驻日使馆在确知民意难违的情势下,也萌生了修约的想法。
随着中日商约第三次届满之期临近,北京政府外交部和汪荣宝深感中日商约有修改之必要,均言应乘此良机,敦促日方赞成修约。早在中日商约到期之前,外交部曾多次电询汪荣宝关于中日商约修改的看法,电文内容大意是:中日商约于1926年即将届满,亟应另行修订,以维主权;汪使“执日有年,尚望即纾谠论,以资筹备”[10]。对此,汪荣宝曾致电回复称,“中日通商条约期满,亟应另订平等新约,并述前清误将关税司法等,订入商约各节”[11],必须着重加以修订。而且,还指出中国此次提议修改商约,“是按照时势,根据法理,为最妥当最合理之要求”[12]658。在吸纳驻日使馆与国内舆情的基础上,外交部从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角度出发,认为《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订立已经三十年之久,“在此长时期内,两国政治、社会、商务状况,已不知几经变迁,以订立年代久远之约,支配两国屡经变迁之商务关系,自多不能适宜之处,是以修改此约而代以双方同意之新约。由缔约国相互利益言之,不特系应为之事,且实为必要之图”[12]652。因此,“为求适应现时必要起见”[7],《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届期满之日,自应宣告废止,另订平等新约。以上反映出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汪荣宝均主张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依势而为,主动向日本政府言明中国国民希望期满改订新约之态度,以求日本社会之谅解同意。
为使中日修改商约周密妥当地进行,北京政府外交部曾秘密致电驻日本公使汪荣宝,电文中指出中日商约“复届十年修改之期,部拟于期满前数日内向日政府声明,期满改订新约,望预为筹备布置”[13]572,要求驻日使馆方面严密注视日本政府及社会对修约的态度和舆论,及时反馈相关动态。汪荣宝接到指示之后,积极研究筹备。汪氏出于慎重起见,也出于维护国家利权和主权,始终认真对待此事,将其作为当时中日交涉的第一要务。所以,自从北京政府提议修改中日商约之初,汪荣宝就积极着手准备中日商约交涉的相关资料,并针对交涉中如何提出修约要求与外部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二、汪荣宝对中日修改商约的认识及建议
关于旧约到期如何修改之方法问题,民国学者王龄希认为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另订新约,另一种是依据旧约。前者就是将旧约完全废弃,而于互利平等基础上,另定草案编列条款;后者则是仍以旧约为蓝本,就其中条款,为全部或局部之更改[14]。这两种方法简要概况即为“废约”与“修约”。针对中日商约期满之后,采取何种修改办法,北京政府一直举棋不定。这主要是因为民众废约呼声太高,北京政府不敢轻易忤逆民意,因而只提改订新约,尚未提出根本改订一节。据时人评论称,“中国政府初意,本拟提出废约办法,忽于二三日来一变其态度,只主张修约。其原因大致鉴于中比商约交涉经过之棘手,与夫日本近自关税会议以来颇表好意,兼之曾由佐分利委员提示修改商约意见,故不愿过于固执”[15],这一说法虽然不大可靠,却也折射出北京政府不敢轻言废约的苦衷。这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是一个强国,北京政府有所畏惧,是其不敢单方面废约的最主要原因;而五卅惨案发生后,日本采取对华缓和的外交政策,缓解了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也是促成其仅言修约,不提废约的重要因素[16]。
然而,相较于北京政府修改中日商约含糊其辞的态度,驻日公使汪荣宝明确表达了不赞成废约的观点。他以为,“若采用宣言废约主义,则纯属片面自由行动”[12]656,会激起日本的强烈反对,极大阻碍中日修改商约的交涉。与废约主张不同的是,他在1926年9月致外交部的电文中明确指出:“先就关税自主及撤废领事裁判权谋彻底之解决,旧商约尽属片面条款,应全部修改,以顺国民废止不平等条约之主张。”[13]577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汪荣宝是根本改订中日商约的最早提倡者之一。关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改订,北京政府虑及此事乃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事,为慎重起见,多次电询驻日公使汪荣宝对于修改此项条约的意见,汪荣宝则极力劝说外交部采纳其前项主张。经过汪氏的反复陈说利害,外交部最终接受了他的中肯意见。这一点可在1926年10月中日修约照会的修改稿中略窥一斑。文稿中称:“中国政府对于前述各约照现行之方式,实希望不再继续,而愿即进行根本改订事宜,代以双方同意之新约,以图增进两国之公共利益。”*《修约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影像资料,馆藏号03-23-034-02-005。随后顾维钧外长在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的谈话中,则进一步阐明了采用根本改订一节的深层动因,实为“民意力主废旧订新,其势甚烈,然政府以新约须经订约国彼此同意,互相妥协,方可成立,故将稳和态度提议根本改订”[13]595。正是通过对商约修改方法取得一致共识,外交部与驻日使馆间才开始就中日商约改订的内容与具体事项进行实在商酌。
在中日改订商约的准备和筹划阶段,外交部充分发挥了驻日使馆在中日两国外交中的特殊作用,经常性地征求汪荣宝对于中日商约修改的意见,以便了解日本政府的修约态度,减轻修约阻力。在这个阶段,外交部与汪荣宝公使之间主要是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商讨。在1926年9月12日外交部致驻日公使电文中,明确提出了以下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附属文件,以及附属该约之公立文凭,虽未规定有效期间,既系连属性质,是否宜一并提出修改?二是此次对日本照会是仅言修正,还是说明到期失效呢?三是如说明失效,各该约停止效力日期算至何时[12]654-655?由于这三个问题是中日改订商约的核心问题,外交部极为重视,命令汪氏详细斟酌并迅速禀复。汪荣宝对中文、英文、日文三种不同版本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参考以前各国的修约实践,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在该月24日回复外交部的电文中,汪荣宝针对外交部电询的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一一说明。对于第一个问题,他指出《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已经到期,既然现在决定提议修改,则附属该约的《公立文凭》及续约《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均当一并提议修改。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详细分析后指出,此约第二十六款的中文文本仅有“声明更改”字样,却无更改不成立应如何办理的说明;而日文有关继续有效的条件,除“两方无改正要求”一语外,尚有“条约未经改正”一语,上述二语是否侧注,抑系平列,不无疑义。为此,他特意查照该约英文文本,发现前述两语中间有“and”字样,即“无改正之要求”与“未经改正”并非一事也。因中文、日文关于此款有较大出入,假如日本欲以英文解释为准,我方很难辩驳,至于“到期失效”一语则更不便提出。但修约一事关系政府对外方针,如果决计顺应国民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无须拘牵文义,届时日方若不允诺修约,自行宣布废约即可。针对第三个问题,他认为若政府提议修约,则新约未订定以前,旧约仍继续有效;若政府采用单方面废约,则无论何时均可以宣布条约无效[13]586-587。他的这些意见和观点,获得了外交部的赏识与认可,相当部分被写入了中日商约的正式照会稿中。
此外,汪荣宝在商约谈判开始前后,对其主张的根本改订商约一节向外交部和日本政府作了详细解释和说明,尤其是对新约订立的依据和中日商约须根本修改的内容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币原外相曾提出的“根本修改,系作何解释”,汪荣宝辩驳道:“旧约系片面的,今日商订新约,自应采用平等相互主义。所谓根本修改者,即指平等相互而言。”[12]657-658而且,他认为中日商约修改不能仅限于税则和通商各款,凡是商约内含有的一切非平等相互之规定都需要修改[12]657-658。随后,在给全国商会联合会江苏省代表王介安的回函中,汪荣宝再次阐明了自己关于根本改订中日商约的意见,即“将旧约内不平等之点,逐一签出,旧约款项,均系片面的极不平等,今另订新约,应采用平等相互主义,至关税自主暨撤去领事裁判权,尤为最重要原则”[10]。他的上述主张,成为北京政府主动提议根本改订中日商约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成为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汪荣宝关于修改中日商约的独到认识和建议,为中日商约交涉的有序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法理支撑和现实依据。
三、中日改订商约交涉的成效及反思
前已述及,北京政府早在1926年1月前后就开始为修改中日商约作准备,在1月13日外交部发给汪荣宝的电函中明确指出,《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第三次十年之期届满,希望其预先做好筹划,以便应对此事。随着中日商约的期满将至,外交部于9月底撰拟完成对日本照会文稿,征求汪荣宝对于此项稿件的修改意见。汪氏以为照会稿内容极为妥当,但有一处需要修改,即“不愿继续”字样改为“不愿再行继续”,以表明我国政府修约之决心[12]655。由于顾维钧外长对《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期满作废一节,主张“到期再行声明作废”,所以迟迟没有将中日修约照会稿通知日方。直到10月20日《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到期,才正式照会驻京日使芳泽,称“根据该约第二十六条,要求根本修正全约,不以商务条款为限”,冀中日两国迅速开始谈判,于六个月内订成新约,并着重声明:“如新约不能于六个月内订成,中政府保留宣布对旧约表示态度之权利。”[17]115与此同时,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汪荣宝,请其将10月19日收到的照会文稿代转日本外务省,并敦促日方尽快答复。接到修约照会稿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币原外相于10月21日召见汪荣宝,声称“主义上并不反对,彼意请将文内假使修约期满应有权利一段删除,以免发表后惹起日本国民反感,于事无益有损”[12]655,尤望中方三思而行。汪荣宝当即将日方意思转达给外交部,请求外交部迅速回电,以防日方藉词拖延。
针对日方的无理说辞,外交部分别于10月23日和26日两次致电汪荣宝,请其向日本政府代为转达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其一是“此次修约照会,政府慎重将事,几费斟酌,始有改订之决定。修约期满至应有权利一段,如经删去,恐愈惹起中国舆论之反响,于修改前途反多窒碍”[12]655。其二是“关于应有权利一段,因中国既愿将现约加以根本修改,假如六个月不成,自应表示一种态度,丝毫无威胁之意存于其间”[12]656-657,且殷切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谅解中方的苦心,以免滋生误会。然而,日方始终态度强硬,坚决认为中国政府声明保留其应有之权利一项含有胁迫之意,与互相让步互相信赖之精神不相符合。日使芳泽更是蛮横地说道:“在本国当局对于该句未谅解以前,决难同意公布照会内容”[13]596,以此要挟中方,迫使北京政府作出让步。面对此种情势,顾维钧外长和汪荣宝公使两线出击,争取舆论支持,掌握外交主动权。如汪氏在日本特向新闻记者“反复演说约三十分之久,彼等均甚感动”,他们对于中方提出的修改商约照会,深表同情[12]658。另外,外交部也多次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进行会谈,就中日商约改订照会中“关于中方保留应有权利之一节”,反复交涉,以期日方能够谅解中方的内察民意、外顾邦交之举。根据现存的外交部关于修改《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历次会谈纪要中记载,从10月21日至11月10日,中日双方在北京共举行六次大的会谈,讨论中日商约改订事宜,渐渐消除了日方的疑虑[12]659-666。诚如汪荣宝致外交部的电文中所说的,“旬日以来,从舆论方面,暗中疏解,颇见成效”[12]658。事实上也是如此,经过汪荣宝等人在舆论方面较长时间地暗中疏导,日本当局终于有所松动,于1926年11月10日接受了中国修约谈判的要求。关于上月20日商约照会中争议最多的“保留其应有之权利”一段,日本在当日的同意改约照会中,仅使用了“不禁失望”一语,与之前的立场形成巨大反差,着实令人瞠舌!由此不难发现,日本当局从北京政府提议修改商约之日始,即对中方提出的修约要求消极应付,仍谋求旧约的继续生效,以确保其在华特殊权益不受损害。若非北京政府的修约态度坚定,加之中外舆论施加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断然不会轻易放弃旧约,同意另订新约的。
虽然日本方面已经同意修约,但只愿意就改订税率及条约中之通商条款与中方开始商议。至于税率及通商条款以外的其他问题,日方以“要求太广泛,未见可以想象或承认”[17]116,拒绝了中方根本性修正的提议。北京政府出于修约大局着想,并未立即反驳日方的无理要求,而是希望与日本方面从速开议新约,增进两国亲善之基础。然而事与愿违,日本因内阁重组引发政坛危机,致使中日商约谈判搁置两个多月。为避免中日商约交涉陷入僵局,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汪荣宝加紧与币原外相洽谈协商,经过长时间的磋商,双方关于修约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5]317。1927年1月17日,中国外交当局以书面形式正式告知驻京日使芳泽,“请根基(据)十月二十日之中国方面,十一月十日之日本方面,往复文书之精神,准备改订中日商约之交涉,于本月二十一日举行开幕礼”[18],芳泽公使在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意下欣然应诺。1月21日,顾维钧与芳泽在北京进行了中日商约修改的正式谈判,从此时起,中日商约谈判的主导权开始转移到北京政府外交部手里,驻日使馆与日外务省之间的交涉退居次要位置。
在随后的谈判中,中日两国围绕关税自主、最惠国条款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中方主张日本“如承认我关税自主,可与讨论互惠协定及过渡税办法,至最惠待遇不能允许”[13]631,而日方则强调先订互惠协定,再议其他问题。经过慎重研究,北京政府以为“最惠国条款核与互惠协定不能相容,此实碍难准许”[13]647,坚决反对日方以修约为幌子趁机扩大在华权益的企图。因双方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各不相让,中日商约谈判进展十分缓慢,使得北京政府提出于六个月内完成新约的计划落空。为使中日商约交涉不致中途夭折,北京政府向日本方面提议修约照会展期三个月,以便双方继续努力议定新约[12]654。然而,双方谈判的焦点仍是最惠国条款问题,尽管中日商约会议就最惠国待遇问题谈判十多次,但还是毫无结果,遂决定暂为搁置,先议其他事项[17]127。可是未过多久,双方因在一些交涉议题上分歧较大,不易妥协,谈判又陷入了停顿状态,故而不得不再将修约期限延长三个月。事实上,日本政府起初同意修约,本想通过谈判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却不曾想遭到北京政府的强烈抵制,转而采取拖延战术,逼使中方主动妥协。中方出于维护国家主权与回应民众废约舆论的双重考量,无法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因而也使修约交涉几度面临中断的危险。由于中日双方在关键议题上一直争执不下,导致商约谈判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延期。如此周而复始,至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前,中日商约交涉已经展期五次之多,但收效甚微,反而是旧约的有效期得到一再延长,显然与北京政府倡导修约之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北京政府后期中日商约交涉的失败,无疑反映了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北京政府外交部虽然提出了根本改订中日商约的主张,但始终不敢向日本政府提出全面废除中日商约的要求,凸显出北京政府甚为软弱的一面。此外,在商约谈判中,面对日方的蛮横无理,北京政府并未据理力争,而是一味妥协,造成了交涉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局面,被日本方面牵着鼻子走,使谈判时常陷入危机之中,甚至是长时间的停滞状态。如商约谈判正式启动后,中方所拟交涉提案大纲共有五项:一是关税自主;二是取消领事裁判权;三是收回沿岸内河航权;四是两国人民遵守所在地法令有游历营业之权利,法令有特别限制者除外;五是遵守警察税捐章程[13]631。但日方却不赞成上述事项同时开议,仅就关税自主问题与中方进行商讨,非但如此,还狡词拖延,使得谈判交涉进展迟缓,成效十分有限。尽管如此,但是对于驻日公使汪荣宝和北京政府在商约交涉中所作努力,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他们不失时机地主动提议修改中日商约,“在中国不啻为订结对外相互平等条约之先声”[18],其与稍早开始的中比商约谈判一道,掀起了北京政府修改中外商约的浪潮,成为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日商约交涉的全过程,汪荣宝与北京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十分密切,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为中日商约谈判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筹备布置之初,关于中日商约到期问题和对日提议修改商约照会内容,外交部曾反复征询驻日公使汪荣宝的意见,汪氏也相当尽职尽责,除明晰表达个人对中日商约修改的看法外,还深入了解日本各界对中日修改商约的态度,以供外交部参考,正如有人总结称的,“汪氏报告日本政府及国民间之意向,外交当局即引之作为参考”[19],这些都对中日商约谈判产生积极作用。正因如此,中日商约谈判的前期工作进行得还是颇为顺利的。可是,伴随中日商约正式谈判的开始,中日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现,尤其是日本方面修约态度的日趋强硬,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一时变得难以调和。加之商约交涉主导权的转换,北京政府外交当局全权负责起了中日商约交涉,由外交部高级官员在北京与日本驻华使馆进行直接交涉——如顾维钧外长曾多次主持中日修改商约会议,跟日方代表展开了激烈交锋——反而削弱了驻日使对商约交涉的参与程度。从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驻日使馆间的电文往来不如以前那么频繁就可以略窥一二,外交部不再如之前一样经常性地征求汪荣宝的改约看法,更多的是要求其“探询日政府对于修约最近态度。电复外交部”[13]631。汪荣宝和驻日使馆逐渐丧失了对商约谈判的参与权和部分决策权,转而负责中日之间其他问题的谈判与交涉。可以说,汪荣宝及驻日使馆在中日商约交涉中地位和角色的重大变化,极大影响了其与北京政府外交当局在商约谈判上步调的一致性,促使其更加倾向于南方革命政府的废约主张。以上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日商约谈判的进程。其中日本政府的修约态度,无疑是影响中日商约交涉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日本缺乏修约的真正诚意,中方虽然一再让步,但是日方却步步紧逼,使得商约谈判举步维艰,以致中日改订商约交涉成效不尽如人意,遂成悬案。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中日商约交涉的失败,既是囿于时代大环境、两国实力相差悬殊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也是修约策略和方法等运用不当所致,如此多的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注定了北京政府后期发起的中日商约谈判不可避免地走入死胡同。特别是1928年6月北京政府统治的结束,由北京政府外交部主导的中日商约谈判也随之戛然而止。因此,商约交涉的历史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肩上,从而拉开了中日改订商约交涉新的序幕。实事求是地讲,北京政府启动的中日商约交涉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北洋末期中日谈判没有具体成果,主要关键在于最惠国待遇,中日各有坚持”[20]。但是它所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中日商约交涉是继中比商约之后首次开启了与强国修改商约的步伐,充分展现了北京政府外交当局不畏强权,敢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汪荣宝、顾维钧等人顺应时代潮流,尊重民意,利用国际公法,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废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它还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敏感而微妙的关键时期,复杂多变,严峻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因此,从中汲取相关经验,例如对外交策略的灵活使用、对现代国际法的巧妙运用、如何做到外交部与驻外使馆的良性互动等等,对于时下中日关系建设不无有益的启示。
[1]驻日汪公使决定赴任[N].顺天时报,1923-12-12(2).
[2]调任驻日汪公使请假之原因[N].顺天时报,1922-9-11(2).
[3]汪公使将于月底赴日[N].顺天时报,1923-6-25(2).
[4]汪公使准十五日赴日[N].顺天时报,1923-12-11(2).
[5]赵林凤.汪荣宝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666.
[7]外部准备修改中日商约[N].申报,1926-10-19(7).
[8]马寅初.中日现行通商航海条约之研究[J].东方杂志,1926,23(23):5-12.
[9]马寅初.中日商约修改之必要[J].经济学报,1926,2(2):8-11.
[10]外部筹备修改中日商约[N].顺天时报,1926-8-21(3).
[11]汪荣宝对修订中日商约表示[N].申报,1926-11-14(12).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 外交[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日关系史料:商务交涉(1918-1927)[Z].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14]王龄希.修改中日商约刍议[J].外交评论,1932(7):38-89.
[15]中日商约外部不言废止[N].申报,1926-10-22(7).
[16]李育民.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J].文史博览,2005(6):14-19.
[17]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8]各社要电[N].申报,1927-1-19(6).
[19]中日改约交涉正在非公式接洽中[N].顺天时报,1926-11-27(3).
[20]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65.
Wang Rongbao and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ino-Japan CommercialTreaty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Weng Min, Chen Jie
Practices and efforts of the revision of treaties in the period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nti-unequal treaties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ermination of a commercial 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Belgium, and created the diplomatic wave of amending commercial treaties amo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ino-Japan commercial treaty which was the focus of the public. Wang Rongbao, the ambassador to Japan, almost witnesse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ino-Japan commercial treaty. Especially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ino-Japan commercial treaty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he made constructive contributions and promoted the substantive progress of the treaty. However, due to a long delay by Japan and Chinese limitations, the advance of the Sino-Japan negotiation was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ino-Japan commercial treaty; Wang Rongbao
翁敏,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洁,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1926—1930年中日改订商约交涉再研究”(CX2016B190)。
K258;D80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2.012
2016-08-29;责任编辑:陈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