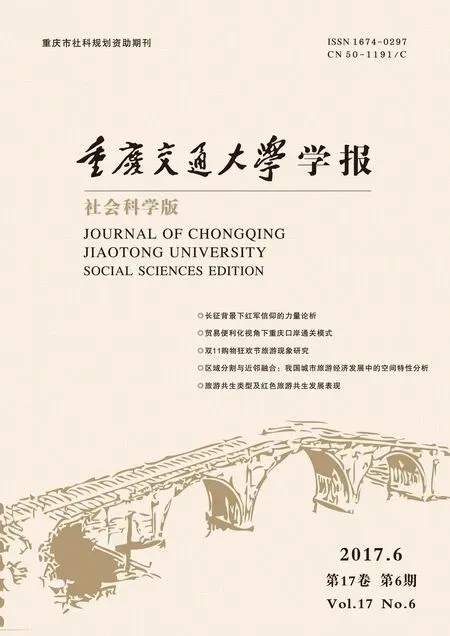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中新女性的诞生
2017-03-22孙丙堂曹冰露
孙丙堂, 曹冰露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文学艺术·
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中新女性的诞生
孙丙堂, 曹冰露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童话教母安吉拉·卡特因其对童话的改写而享誉世界文坛,其短篇小说《染血之室》是在改写法国童话大师夏尔·佩罗的《蓝胡子》的基础上创作的。通过文本分析,探讨《染血之室》中新女性“我”的诞生,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女性身体作为女性发声的新媒介,女性精神作为女性进步的新动力,女性话语作为女性自主的新途径。
童话改写; 女性身体; 女性精神; 女性话语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是20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英国评论家迈克尔·伍德曾将卡特比肩于纳博科夫、马尔克斯、贝克特等世界级作家,称其为“女作家中的萨尔曼·拉什迪、英国的伊塔罗·卡尔维诺”等[1]。在安吉拉·卡特一生的创作中,女性主题贯穿始终。26年来,她致力于解构父权制度对女性本质的界定,颠覆父权社会下女性非黑即白的形象,还原女性真实而完整的本来面貌。
作品出自作家之手,必然会受到作者个人因素的影响[2]。卡特从小醉心于外祖母讲述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少女时代的她已经能够将古希腊、古埃及典故引用于诗歌与散文中,改写经典的想法生根发芽。旅居东京期间,与一名日本男子的亲密关系促使她重新思考女性。文学积淀与人生阅历碰撞出火花,形成卡特独有的文学特质。卡特擅长以传统思想和主流理论为批判对象,对固有的文学形式——神话、童话、宗教故事和民间传奇进行改写,《染血之室》是以夏尔·佩罗的《蓝胡子》为模本改写的现代童话。在1979年出版的《染血之室》中,卡特以第一人称“我”开启了全新的叙事:“我”是一名音乐学院的女学生,成长于单亲家庭,家境贫寒。嫁给富甲一方的侯爵后,“我”重获新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不顾禁令,发现了血室的秘密:侯爵杀死了他的前几任妻子,并陈尸密室中。行刑时刻,得益于情人和母亲的相继帮助,“我”幸免于难。最终,“我”继承并捐出了财产,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关于《染血之室》,已有研究的焦点多集中在小说中的叙事技巧、互文性等后现代手法和策略上,对于小说女性主体重建意义的发掘较少。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曾雪梅博士的论文《论安吉拉·卡特的小说对现实性和主体性的颠覆》[3]通过对卡特其他三部作品的文本分析,探讨了作家对现实性和两性主体性的消解和重建,对本文具有启发性的影响,但是论文较少提及母女关系的传承。本文通过分析女性身体、女性精神和女性话语的重建,探讨了小说的主人公“我”经由女性身体发掘自身价值,通过母女联系传承女性精神,借由女性话语重建女性主体,在自我探索、自我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成长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一、重建女性身体
人的“视觉参与着文化建构”[4],在侯爵单片眼镜的凝视下,“我”的身体取代了“我”本身,“我”成为侯爵的色欲对象,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小说中有两处刻意描写了侯爵对“我”的凝视。第一处:“我看见他在镀金镜子中注视我,评估的眼神像行家检视马匹,甚至像家庭主妇检视市场肉摊上的货色……他那种眼神,那种纯粹肉欲的贪婪,透过架在左眼的单片眼镜显得更加奇异。”[5]10第二处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在一场正式的新娘脱衣典礼之后,“我”成为了罗普斯的蚀刻画中的小女孩:“小女孩一丝不挂……旁边是个戴单片眼镜的老色鬼,仔细检视着她每一部分肢体。”[5]16两次凝视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单片眼镜。据资料显示,早在1720年时,就有古文物研究者佩戴单片眼镜以供仔细地检视古董[6]。随后,单片眼镜在19世纪成为绅士的一种风尚,是财富的象征,常被用来阅读协议等用小号字体写成的附属细则[7]。侯爵借助单片眼镜检视“我”的身体,是生意人在阅读婚姻协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经由婚姻这样一场交易,“我”的身体取代了“我”的存在,同时“我”的身体不再属于“我”,“我”成为了侯爵的肉欲的对象。
不同于侯爵借助单片眼镜对“我”身体进行的凝视,“我”借助男性眼睛对自我身体进行反凝视,“我”的身体不再是被动的、工具性的,转眼间变成了情欲性的主动性的存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提到:“他人的注视和这注视的终端我本身,使我有了生命。”[8]小说中“我”对自己欲望的探索是渐进式的,其中三次重点描写“我”发现女性身体的价值,而这些发现恰恰是在侯爵的“启蒙教育”之下获得的,借助他欲望的双眼,“我”震惊于这样一个发现:“突然间,我看见了他眼中我的模样……第一次在我单纯而受限制的生命里,我感觉到自身的一种堕落的潜能,它将我的呼吸带走。”[5]11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女性的欲望,但是“我”的思想仍然禁锢在男性价值观念中,将女性欲望等同于堕落。在十二面镜子前,侯爵赠送“我”一份来自妓院的“礼遇”——“一番正式的新娘脱衣典礼”[5]17:“他剥去我的衣服,……我第一次以他的眼神看见自己的肉体,此时我也再度大惊失色地发现自己情欲撩动。”[5]28这一次“我”不仅发现了自身的欲望,还发现女性身体对于男性的价值,意味着“我”的身份已经从欲望的客体转化成凝视的主体。伴随新婚初夜的来临,“我”借由女性身体体验到欲望的欢愉,认识到女性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在他那双不反光的眼睛里,我仿佛重生,重生为不熟悉的形体。”[5]28这一次“我”确定自己已经脱离了男性权威的桎梏,成为了身体的主人。
在假借男性眼睛对自我身体欲望重新认识的过程中,权力在最初作为凝视者的侯爵与作为反凝视者的“我”之间实现了易位,女性身体最终成为了女性发声的新媒介。几番两性视觉上的对峙,在侯爵所代表的男性眼中,“我”从一个没有经验但充满堕落因子的处女变成了初尝禁果且情欲缭绕的女人,而在“我”一个普通女性的眼中,“我”从被动凝视的客体转化为主动观察的主体。正是一次次对身体欲望的审视,女性意识得以觉醒,“我”发现了女性存在的价值和力量,获得了自信和重生。事实上,卡特重视经由女性自己的器官发出女性的声音,重塑自身价值。小说中的“我”是一位不为命运羁绊的女性,无论是作为贫困阶级的单亲少女,“我”以文艺女性的气质俘获侯爵,晋升上流社会,还是丧夫改嫁的贵族少妇,“我”委身于权力的弱者——盲人调音师,捐资济世,归隐乡林,“我”一直跟随着自己内心的声音,践行着自主人生的精神,探索着自身存在的价值。
二、重建女性精神
父权制度下,传统的女性被要求具有姣好的面容和顺从的性情,但母亲却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小说中两处细节突出母亲异于常人的性格。小说伊始,母亲便以“轮廓如鹰,桀骜不驯”[5]4的形象登场,贫穷窘迫的生活非但没有令她屈服男性世界,反倒成就她冲破束缚、自主人生、惩恶济贫,成为女性英雄。“曾面不改色斥退一船中国海盗,在瘟疫期间照顾一整村人,亲手射杀一头吃人老虎。”[5]4这些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男性的传奇事迹表明母亲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另外,在婚姻观上,母亲不以世俗眼中的财富、地位作为衡量婚姻的基本准绳,却以爱情作为唯一条件。她自己就是爱情忠贞的践行者,曾经的她“身为富有茶园主的女儿,在中南半岛过着多姿多彩的少女时代”[5]4,为了爱,她心甘情愿地变成了乞丐,手提网袋里总是装着左轮手枪。而且母亲希望作为女儿的“我”同样能够收获以爱为名的婚姻,她再三追问“你确定你爱他吗”,“我”的回答是“我确定我想嫁给他”[5]4。
在男性社会,“我”同样也是一个叛逆的女性,这一点来源于“我”对母亲叛逆精神的继承。法国女权主义者露丝·伊瑞格瑞在《一个不会没有另一个而走动》中描写了这样的母女间的悲剧:“如果母女之间只剩下‘耗尽与被耗尽’的关系,女儿则会为追求更鲜活的存在感而抛弃母亲、寻求父权……”[9]《染血之室》力图颠覆这一悲剧。小说中“我”为了追求富足的生活和别人艳羡的目光,试图嫁与财富,但是面对“我”即将在男性谱系中承担男人之妻的身份,“我”作为母亲的女儿的身份正在失去,“我”感到失落和痛苦,这表明“我”欲逃脱的只是生活的窘境,“我”的内心充盈着对母亲的依恋。事实上,“我”的身体里潜藏着源于母亲的叛逆因子——“我”对丈夫超出传统女性的好奇心,促使“我”发现血室的秘密。在生死关头,从天而降的母亲如蛇发妖女——美杜莎一般的形象现身,拯救“我”于刀剑之下。正如阿德莉安·莉奇在《女人所生》一书中指出,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存在着自发的心理能量[10]。
无论是叛逆的母亲还是叛逆的“我”,卡特重视对女性主体性的传承,重视女性精神的继承。伊瑞格瑞提出建立“女性谱系”的主张,其核心是取代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男性中心,建立一种新型的母女关系。她认为在“女性谱系”中,妇女不再是对象,妇女之间的联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联系[11]。在“我”长久的艰苦生活中,陪伴“我”长大的是母亲和保姆,牺牲于战场的父亲形象是缺失的,“我”的成长环境并没有为“我”提供滋生“恋父情结”的土壤,在情感上“我”是依赖母亲的。“我”被城堡里冷漠的等级制度桎梏得难以适应,孤独寂寞无法排解的时候,最先寻求安慰的对象是母亲;“我”发现血室的秘密,东窗事发,处决时刻再三逼近的焦灼情势下,“我”能想到的救赎对象也是母亲。而母亲既扮演着抚育子女的母亲形象,又肩负着保护家人的父亲责任。她读懂了父权桎梏和压迫的本质,面对生活的困境,不是怨天尤人、乞求怜悯、随波逐流,而是站到了与男性同样的高度,承担起生而为人的责任,伸张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智慧、勇气和行动力为女儿树立新女性的典范。在小说的高潮处,“我”镇定自若地走进密室,“我不畏惧,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如今我步伐坚定,就像走在自己娘家屋里”[5]39。这表明“我”对母亲已经由情感上的依赖升华到理智上的践行,母亲传承的女性精神早已根植“我”心,获得了认同,并内化成动力,驱使“我”前进。
三、重建女性话语
卡特认为在经典的欧美童话故事中,二元对立的性别意识形态极为明显[12]。童话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一例外是男性,主要的女性角色要么被塑造为屋子里的天使,要么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蓝胡子》中的女主人公本应是遵循道德期望的天使,由于偷窥了男性的禁忌,触犯了男性权威,她受到了死亡的惩罚。佩罗创作《蓝胡子》的用意是赋予童话极高的教育意义,传授“孩子们只需有‘好品德’就能获得好结果”[13]的寓意。佩罗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以简单自然的叙述总起,叙述者客观叙事,对情节不加增减,对角色不予置评,但是这一看似公正的叙述实则掩盖了男女两性的不平等,也否认了女性话语的特殊性。
卡特改写的《染血之室》采用第一人称女性叙事视角,女主人公不仅在故事层面上成为了主线人物,而且在叙事层面担当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这种打破传统的叙述是否可靠?胡亚敏在《叙事学》中指出:“有些作品的叙述者并非完全可靠,他们或言辞偏颇,或口是心非,若读者信以为真就会受骗上当。”[14]小说有二处明显表露出不可靠叙事。第一处,故事层面的“我”特意为读者留下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形象,但是在仔细推敲文本之后,笔者发现叙事层面的“我”实际上是一位具有独立主张的女性,“我”是有意识嫁给侯爵的。在“我”看来,婚姻不是追逐爱情的游戏,而是父权社会女性求得物质与地位的保障。侯爵的求婚是对“我”的试验,利用异性关系“我”帮助自己获得一个完整的性别身份,同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女性存在形式。第二处,在侯爵行刑时,“我”将盲人调音师改称为情人,互相扶持,并肩对抗权力的强者——侯爵。不可靠叙事弱化描写了故事层面的“我”与调音师的感情脉络,将叙述焦点转移到侯爵杀戮的可鄙上,不仅令小说的形式新颖独特,增加了小说理解上智性的深度,而且批判了男性淫威的惨无人道,彰显了女性追求自主话语的意义。
卡特的第一人称女性叙事将女性作为童话故事的中心,以女性口吻描述女性的身体体验和心灵感受,同时重视女性话语的力量。小说的结局是“我”并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是和情人结婚,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显然,女性口吻和不可靠叙事拯救了“我”和情人。换言之,这种类似于上帝拯救功能的文学文化语言具有了予夺生死的神奇功效。卡特运用此种叙述模式,意在呼吁女性自己叙述自己的故事,夺回话语阵地,掌握话语权,因为只有发出声音才能发出生命诉求的信号,才能展示自主女性的才干,才能摆正两性平等的天平。卡特的女性叙事为女性寻求性别认同、自主话语和文化存在开辟了新的道路。
卡特在谈及童话改写时曾说过:“我所做的并不是将传统童话改写为成人童话,而是挖掘故事的潜在意义。”[15]《染血之室》展示给读者这样一位女性:她经由侯爵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和自己的反凝视,发掘自我价值;她通过对复杂微妙的母女关系的诠释,继承女性精神;她借由女性话语和不可靠叙事,实现女性自主;她突破男性权威制度和传统社会理念的重重枷锁,在自我探索、自我追求的道路上奋不顾身,最终蜕变,重生为一位独立思维、理智冷静、坚定勇敢的新女性。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创造并宣扬新女性是卡特赋予童话最新的寓意。
[1] 伍德.沉默之子[M].顾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79.
[2] 孙丙堂,袁硕.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中的自我形象探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64.
[3] 曾雪梅.论安吉拉·卡特的小说对现实性和主体性的颠覆[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4] 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9.
[5] 卡特.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M].严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 Monocles[N].Spectacles Gallery,2014-03-19.
[7] LOWDER J B.The one-eyed man is a king[J]. Slate,2012(12):6.
[8] 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328.
[9] IRIGARAY L.母亲身份研究读本[M].刘岩,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70.
[10] RICH A.Of woman borthen[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6:225.
[1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97.
[12] 王腊宝,黄洁.安吉拉·卡特的女性主义新童话[J].外国文学研究,2009(5):92.
[13] CARTER A.Sleeping beauty and other favorite fairy tales[M].New York:Shocken,1989:125.
[14]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12.
[15] HAFFENDEN J.Novelists in interview[M].London:Methuen,1985:80.
BirthofaNewWomaninAngelaCarter’s“BloodyChamber”
SUN Bingtang, CAO Bing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Known as a fairy-tale godmother, Angela Carter’s fame is greatly indebted to her rewriting of the fairy-tale. “The Bloody Chamber” is adapted on the basis of “Blue Beard” written by Charles Perrault, a French fairy-tale master. The birth of the new female “I” is analyzed through closely reading the text, namely, female body as a new medium to voice a woman’s inner world, female spirit as a new impetus to seek a woman’s progress, female utterance as a new means to pursue woman’s independence.
rewriting of the fairy-tale; female body; female spirit; female utterance
张 璠)
2017-03-26
孙丙堂(1965—),男,河北固安人,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批评、应用语言学;曹冰露(1988—),女,天津人,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4
A
1674-0297(2017)06-0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