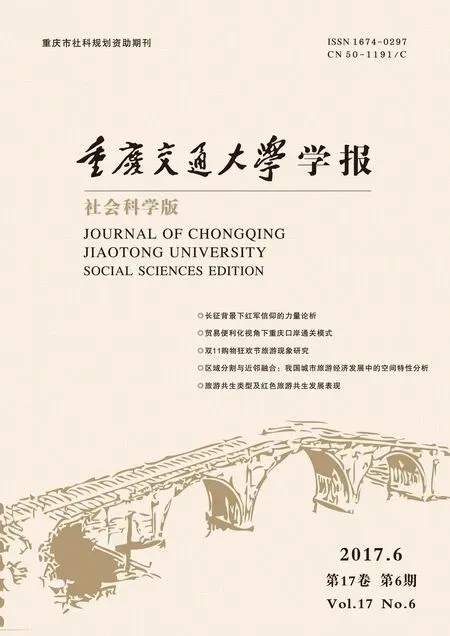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的旅游开发
2017-03-22曾芸
曾 芸
(贵州大学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贵阳 550025)
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的旅游开发
曾 芸
(贵州大学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贵阳 550025)
贵州古驿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城市与乡村、本土与移民、传统与现代等非此即彼的差异消失于其中,呈现出某个定点的静态场景和历史变化的动态画卷的整体性,并就此成为贵州精神的巨大载体。在分析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生成动因基础上,探讨通过空间的表达,旅游开发呈现关联性;以故事性的“叙事方式”,碎片化的文化记忆有序联结;营造地方感,游客获得一种主导性的体验;重构旅游价值体系,“边缘群体文化”得到重新评价等旅游开发新思路,实现驿道的有效保护与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古驿道; 文化景观; 旅游; 地方感
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存在,其中既有古代的创造,又有现代的拓展,更有后续延伸的余地。既有汉移民主体文化的积淀,又有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记忆,更有彼此交融、互动的空间。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是活态的、现在的,与生活状态和生活空间紧密结合,与农耕文明和文化生态密切相关。对其进行旅游开发的意义在于,将地方性的文化纳入到国家现代化语境中,在满足人们追求异文化的时空想象的同时,也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使贵州地域文化更能保留、强化其历史及现实的独特价值。
一、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在地化”阐释
贵州处于西南“腹心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因驿道开通而使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两千多年前,战国有楚将军庄蹻入滇、秦略通五尺道和汉武帝命唐蒙修筑“南夷道”。公元前129年,贵州古驿道上设置邮亭,此后历代君王均十分注重西南地区驿道的开辟和邮驿制度的完善。元代在湖广、四川、云南三省共设“站赤”四百多处,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四条驿道在“贵州”(今贵阳)交会,改变了西南交通的格局,使贵州成为“东进西出、南来北往”的咽喉重地。元代中央王朝统治云南之际,从内地进入云南的道路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自泸州经乌撒(威宁)、毕节至中庆道(昆明),历史上称为入滇“西路”。二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通的由湖南经普安(安顺)进入云南的“东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为确保从内地通往云南道路的安全,明王朝派遣军队以“军屯”的方式在沿湖南至云南的“东路”驿道沿线设置卫所(十八卫),重兵驻守。其兵力总数十余万人,约占当时全国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明永乐十一年(1413),在镇压了思州、思南土司叛乱后,为统一管理这片地域,正式设置了贵州布政使司(即贵州行省)。明代以后,贵州省内有多条连接周边各省的水陆“通道”,但连接西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并对周边发生重大影响的只有这条路。
今天这条陆路通道更成为西南出海大通道和西南与中部、东部的重要连接纽带,带动了国家对贵州公路、铁路的建设。现在主要是从湖南省的洪江和新晃进入,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镇远、施秉、黄平、凯里、福泉、贵定、龙里、贵阳、清镇、安顺、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达云南省富源县。如以沅陵为通道的起点,总长度约有1180公里。其中,湖南省路段约有350公里,贵州路段约600公里,云南省约有230公里。应该说,尽管古代道路艰险难行,但云南进出以贵州为喉襟,川、桂交通必经贵州,又是西南通往内地及缅甸、印度、东南亚的大通道,战略上有不可取代的位置,贵州建省是对这一通道的行政区域政治化的明确。无论是国家军事需要还是西南经济需要,贵州的开发史都烙下鲜明的“通道”烙印。通道既是形成贵州地域文化景观的原因,又是贵州地域文化景观演进的结果。沿通道形成了文化交融带,通道南边如今都是民族自治州;沿通道形成文化走廊,成为一片文化穿越、停留的地方,塑造了贵州文化景观的地域特点。
文化景观是人类在地表活动的产物,是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与服饰等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反映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它是居住在其土地上的群体为满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了自己所创造的景观[1]196。文化景观揭示一个区域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发现人们如何塑造地方。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由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及各种区域性文化融合而成。在古驿道的文化景观中,能够感受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演变过程、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文化变迁、传承和发展的情况。贵州古驿道上的各民族历史上长期和平共处,在毗邻而居的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和吸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的“交融文化”;而在族群迁徙或交流中形成的相同文化记忆让不同文化景观彼此关联。但是长期以来过度强调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反而弱化了任何族群所拥有的文化都具有同质性和内在逻辑性,例如刺绣、鼓楼、傩戏、蜡染等文化符号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而是在各民族互动交融中的文化共性表征。
在贵州古驿道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并没有发生少数民族文化完全消融于强势汉文化的现象,反而出现了汉族的“少数民族化”,即汉族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当地同化。例如,作为汉移民族群的屯堡人在文化表征上与汉文化保持一致,但在文化景观中出现了汉苗融合的特征。屯堡妇女服饰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进行了一些改变,如头戴角质、银质发簪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把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知识称之为“地方性知识”,其重要意义在于,同一族群成员“共享一系列使他们用大致相似的方式思考和感知世界,解释世界的概念、意象和思想。概言之,他们一定分享同一文化的‘代码’”[2]。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是受生存环境限制发展出来的生存性智慧,经受了世代的实践考验,具有特定时空的合理解释性。它既是保持族群边界的基础,也是形成差异性文化景观的原因。
二、旅游场域中文化景观的变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贵州古驿道沿线的许多地方纷纷采取将文化资源优势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文化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发展路径。尤其是新的文化旅游理念把回归自然、感受异域文化、体验生命价值作为产业的重要支点,文化景观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通过旅游发展得以“重塑”,获得一份可能存在的市场份额,使之具有经济价值,实现文化多元化、现代化、全球化在经济基础上的互构。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文化的选择权向“资本”倾斜,在文化景观的“再造”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异化现象。
(一)文化景观单极化表达
文化景观是不断累积而成的,在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中,可以读出王朝时代、军阀时代、社会主义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要素。随着时间的推进,景观中会出现不同的阶段,积累不同的层次,历史会不断对其进行意义附加。在现有的旅游开发中,文化景观却被简化为单一的文化符号,使其背后的意义被解构,并表现出一种碎片式的散落状态,失去了彼此之间的文化勾连和层次性。这种商品化的开发导向让游客停留在对某个文化景观的表面认知,碎片背后的文化全貌与深层的文化精神内涵却无法深入理解。
(二)文化景观与日常生活抽离
通过对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的仔细观察,游客可以了解许多关于不同族群文化活动的重要知识,这是因为文化景观比较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衣、食、住、行和娱乐。正是由于文化景观意义隐藏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旅游开发者才会竭力去创造文化景观的独特意义,把它们加以改造、包装,或对其进行现代话语的阐释,以显示其独特性[3]。在此,日常生活化叙事转换为艺术化叙事,文化景观仅仅是展示给游客观看的场所和构景要素,并不是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许多文化景观原本所蕴涵的意味被剥夺,其所依存的社会场景也不复存在。文化景观意义的消散主要是因为其渐渐失去社区生活的支撑,导致功能性消解,使文化景观缺乏生活的灵动。
(三)文化景观主体“离场”
文化景观的生产过程就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民族气质、文化记忆、创造者的情感都蕴藏其中,它反映了一个群体、一个地域的文化历史沉淀和价值取向。文化景观是以人的“在场”为前提,但“物质性”的视角往往会使我们忽略创造这些文化景观的群体。在商业化的文化景观旅游开发中,当地人处于文化生产的末端,他们并不能掌握文化生产的话语权,文化生产更容易被“他者”所操纵。这种未经文化主体认同的开发,最终只成为“摆设”,文化景观内隐含的族群凝聚力和认同作用越来越小。
三、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旅游开发路径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在地”资源,由于特殊的文化生态理由不可移易,与“在地”资源消费直接相关的行业就是旅游业。文化景观到旅游景观的转换中,文化景观具有了消费价值,是社会生活与商品意识共同发展的结果。贵州古驿道的文化景观积淀着民族的情感、伦理、信仰,留存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记忆,是人们了解、认知、体悟、传承文化的窗口。贵州古驿道旅游不仅带来了地域文化复兴的契机,而且为文化景观的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情境中的文化景观也必将引领 “文化追忆”的消费新时尚、新主张,但这个“追忆”的内容和空间是需要生产和创造的。
(一)构建文化景观的旅游空间表达
构建文化景观的旅游空间,“不是简单地创建一片通行的开放空间,因为只为流通和行动而规划的空间是充满疏离感的”[4]。它是建立空间使用规则以及重整当前的秩序,以充满文化和创意的方式重塑景观环境,构筑多姿多彩的公共生活,并在生活中展现出文化景观的生命律动。在空间视野下,古驿道文化景观的旅游开发将呈现一种有序性、关联性、结构性。
1.文化生态
文化景观不是孤立、静止的文化个体,往往表现出一种勾连时空的“活态性”,只有纳入文化生态环境中才能凸显其价值和意义。文化景观发生和存在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社会环境中,并在人们的交往互动、生存发展中逐渐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形成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可见,文化生态环境因素对文化景观形成和流变有重要的影响,其保护必须在紧密相连的文化生态场域中进行,方可达到最佳效果。
在解析古驿道文化生态内涵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移民文化与原生文化的差异。对外来移民来说,在进入贵州以前,已经拥有强大的前期文化基础,与新环境的结合方式必然会受到原来文化的影响[5]。另一方面,所有文化景观的根基都是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即使经历了产业结构调整,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农业仍是文化景观得以延续和保持文化原真性的基础,同时使其存在方式充满生活气息。
由于特殊的文化生态要求,文化景观只能是“在地产品”,如果离开了当地的社区、环境、民族,其意义也就不再那么迷人。文化生态保护本身就可能成为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稻作梯田文化生态景观系统等。根据文化生态特质,增加旅游的感受性、故事性和娱乐性,让消费者产生回味无穷的文化体验感受。事实上,感受和体验的文化内涵已经逐渐成为旅游消费的最高形式。
2.文化线路
文化景观包含着大量的象征符号,并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要理解文化景观,需要把文化景观置身于具体的时空场景和所属的文化体系来考察,即强调文化景观与其他相关事件或者文化整体之间的互动性关联。文化线路有利于呈现内部关联,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完整、综合、真实地展现文化关联,使文化景观不再孤立存在。同时,文化线路也是文化景观保护的重要载体。由于文化关联导致任何单一文化景观被破坏都会影响到整体的协调,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突出,文化生态链约束了文化景观利用的自由度。
文化线路设计是以居住在同一地理区域中不同人群之间相关联的文化特质为基础和前提,是文化时间与空间所共同建构的产物,通过空间分布的文化特质重建文化景观历史的顺序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6]。对于旅游开发的意义更在于,文化线路不再是散点式开发,而是以不同的文化线路为展现轴承,在不同时空的文化景观变换中满足游客的奇异性追求。但是,文化线路的选择要避免与象征性权力关联在一起,应由本地居民来设计安排。
3.文化空间
文化景观的内容除了一些具体实物外,还有一种可以感受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往往是一种抽象的观感。文化景观总是与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形成一种具有文化精神形态特征的文化空间,用来辨识地域差异。但文化空间本身所承载的独特价值尚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文化表达的最佳途径是文化空间,它使文化景观不再局限于文化符号的单极化表达,展现了异质多元的文化截面,并且在当地社会中保持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人们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安慰。
文化旅游发展需要建立文化意象,留给人们更多的文化想象空间,而文化空间是文化旅游业实现这一转变的最佳切入点。依据文化脉络,营造文化空间,有利于进行统一的文化产品体系构建,提升文化产品意义和附加值。对于一些难以恢复的文化空间场域,则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虚拟呈现,唤起人们对景观的想象。同时,满足旅游者对文化原真性的追求。
(二)展演文化景观的“文化史层”
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由于民族的迁移,一个地区的文化景观往往不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因此,美国地理学家D.S.惠特尔西在1929年提出了“相继占用”(sequent occupancies)的概念,主张用一个地区在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不同文化特征来说明地区文化景观的历史演变[1]197。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景观中会出现不同的阶段,积累不同的层次。即是说,文化景观中有时间、过程、阶段,展示文化景观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让人们感受到历史在文化景观里。
单纯的文化景观本身并没有完成意义的释放,文化景观是在“展演”中实现其意义的。正如王明珂指出,只有将文化视为一种展演,才能见到文化动态的一面,以及文化如何在本土与外在世界的互动中不断呈现与变迁。文化展演以“现实中的动态”和“历史中的动态”两种方式进行,被个人或群体观看、诠释、获知,并产生意义[7]。通过故事性的叙事方式,用文化景观“展演”时间,使碎片化的文化记忆有序联结。在独立的文化景观故事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时代图像里,以拼图式的方式描绘出丰富的生活图景,拼凑出贵州完整的生命历程,并且随着游客“凝视”的变化,呈现贵州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不同的色彩和样貌。
(三)重构文化景观的旅游价值体系
在对具有民族历史价值的文化景观的再现和重组中,唤起地方的历史记忆,增强内聚力和自信心,让游客获得对贵州的新认识,使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边缘群体文化得到重新评价。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的吸引力主要是由新的可能性决定的,正是由于过去的知识使得现在对这些景观的利用如此与众不同。因此,维持与过去的亲密关系变得非常重要。
旅游是一种体验经济,而体验经济的灵魂是主题设计,即是以多元文化的交融作为土壤,从一个诱人的故事开始,在该主题上构建各种变化和延伸,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从而赋予物质的产品和服务以一种象征的意义和情感的内涵,创造值得消费者回忆的一种活动。贵州古驿道文化景观的“追忆”主题体验的思想,就是通过文化景观表述自己的生命历程故事,从而使游客能够回味过往的点点滴滴。通过整体性复原和嵌入式改造,保留原有纵横交错的驿道,也保留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空间,让人们获得一个缅怀历史、解读地方、休闲愉悦和激发创意的共享空间,以此作为文化地标,形成新的商业集聚区[8]。
为了避免文化景观直接变为旅游商品,依附于旅游业的发展而逐渐迷失自我方向,景观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意义被市场需求掩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其一,文化景观旅游本身并不是消费的终端,而是产业链的上游,通过为游客创造文化记忆,培育下游产品的消费市场。文化景观的衍生价值不应体现在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而是把文化景观的衍生开发放到旅游之外,由文化产业来协助完成,避免了文化商品化、原真性等问题,从而实现文化景观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初衷。其二,文化景观旅游衍生开发的文化产品是一种“在场产品”,即在虚拟文化空间内进行消费的“有故事”的文化产品。为了弥补场景性方面的不足,消费者可以利用智能终端设施获取文化产品原生地的可视化信息,进行交互式文化体验。这种“真实再现”是一种意象性的表达,是对历史时空、文化氛围、民族心境的营造。
[1] 王鹏飞.文化地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庄孔韶.文化与性灵:新知片语[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9.
[3] 徐赣丽.民俗旅游与“传统的发明”:对桂林龙脊景区的调查[M]//张晓萍.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170.
[4] SENNETT R.The powers of the eye[M]//FERGUSON R.Urban revisions:current projects for the public realm.Cambridge,MA: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and The MIT Press,1994:66.
[5] 唐晓峰.文化地理学释义[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98.
[6] 侯兵,黄震方,徐海军.文化旅游的空间形态研究:基于文化空间的综述与启示[J].旅游学刊,2011(3):70-77.
[7]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301-302.
[8] 花建,等.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从创意集群到文化空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80-181.
AnAnalysisofTourismDevelopmentofCulturalLandscapesinCourierRoutesofGuizhou
ZENG Y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Courier routes of Guizhou, with great containing ability, obliterate disparitie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natives and immigrants as well a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y show integrity of statics and dynamics, which make them the vehicle of expressing Guizhou spirit. Based on analysis of motivations of gener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s in courier routes of Guizhou, how to mak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how some relevance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pace is discussed, connecting broken cultural memories by “narrative way”. By creating a sense of localization, tourists can enjoy tourist-guided experience. Through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value, a new way of re-evaluating remote culture to realiz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courier routes and sustainability tourist resources is proposed.
courier routes; cultural landscape; tourism; localization
张 璠)
2017-04-11
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项目“西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与农村社区发展研究”(TYETP201555);贵州省教育厅青年学术创新人才项目“西部贫困地区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研究”(GDYB2016007)
曾芸(1980—),女,贵州人,苗族,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旅游。
F592.68
A
1674-0297(2017)06-00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