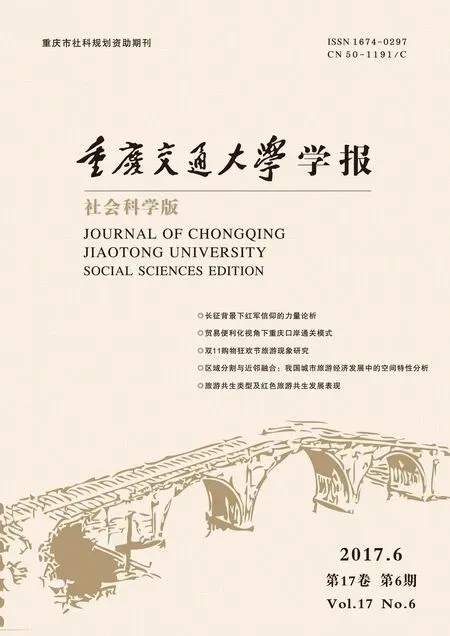上海徐家汇还堂案评析
2017-03-22周红月陈九如
周红月, 陈九如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历史文化·
上海徐家汇还堂案评析
周红月, 陈九如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近代随着清政府的衰落,传教士恃其政府实力要求清政府归还百年禁教期间的教产。上海徐家汇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基础较好,法国传教士便将还堂的第一个目标定为上海徐家汇旧天主教堂。在还堂过程中,传教士利用计谋迫使清政府归还教产,这是近代还堂案的开端,之后传教士借其经验,纷纷要求清政府还堂,引发一系列还堂案。
百年禁教; 徐家汇还堂案; 拉萼尼; 传教士
教案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时期层出不穷,目前学术界对教案的界定没有统一。有学者认为教案是以反对西方以传教为名的侵略,抵制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传播,维护中国文化传统为主要内容的反洋教斗争。其并非是指一般性的外国传教案件,而是专指通过传教案件的发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鲜明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性质的政治性事件[1]。也有学者认为教案是基督教在中国局部或全部取得合法地位后,教会与教外力量之间发生的须立案诉讼的冲突事件[2]237。可见对教案的界定是反洋教性质的斗争,这也是学术界对教案的主流观点。还堂案属于此列。所谓还堂,是指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等强迫清政府归还禁教期间没收的教堂、学堂、坟茔等。由此而引发的案件称为还堂案或还堂交涉。还堂的主要借口是归还禁教时期的房产,主要指清政府在百年禁教时期没收教会的房产。
一、礼仪之争、百年禁教与徐家汇还堂案件
中西分属两种文化系统,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之间势必会有冲突。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三次传入中国: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唐朝时“景教”的传入。第二次是在元朝,有两支:一是景教,一是方济各会,这两支统称为“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第三次是在明代末期天主教传入中国。以来,有关中国传统祭祀礼仪性质等讨论一直不休,康熙中后期甚至发展为教权与皇权之争。为维护统治,“自1721年康熙全面禁止天主教,到1858年咸丰在洋枪洋炮下准许自由传教为止共138年”[2]29,这一时期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被称为百年禁教时期。
礼仪之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的祭祖、祭孔礼仪,其性质究竟是宗教还是习俗;二是造物主应该用何种译名为好[3]。礼仪之争一直存在于传教过程中,康熙中后期福建宗座代牧阎当的介入使事件趋于激烈。阎当非常偏激保守,于1693年3月26日颁布牧函,严禁中国礼仪。在华耶稣会认为这封牧函的内容不利于传教,于是求助康熙,康熙在其上书中回复:“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4]但是当耶稣会士将康熙圣旨的材料送往罗马时,教会认为“关于圣教之事,求判决于外教皇帝,而不请求罗马教廷”,予以拒绝。以后,礼仪之争进一步升级,并转变为政治交锋。于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雷芒十一世发布谕令(即“1704年谕令”)严禁中国礼仪,次年特使多罗到达中国,解决礼仪之争。多罗遵守教宗严禁中国礼仪的命令,康熙认为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属于内政,面对教廷对中国礼仪的干涉,于1706年12月颁布传教士领票*康熙四十五年(1706)规定在中国的传教士由内务府印发凭据,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这实际上是“传教许可证”和“永久居住证”。的命令,拒绝领票者不许传教并驱逐出中国。面对康熙领票的命令,多罗针锋相对,颁布牧函,公布教宗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克雷芒十一世支持多罗,于1715年3月15日公布《自登基之日》的通谕*《自登基之日》诏谕,重申1704年的禁令,并严责不服从者将遭到“绝罚”的重惩。。冲突之下,罗马教廷为了能够更好地管理在华传教士,使其服从于教廷和疏通安抚康熙,最重要的是使康熙允许中国天主教徒遵守《自登基之日》的通谕,于是派嘉乐为教皇特使、亚历山大主教和宗座视察员的身份出使中国[5]84。嘉乐在抵京前给康熙上书表明来访目的,一是请皇帝允许由特使管理在华传教士,二是请皇帝允许中国基督教徒遵照《自登基之日》通谕行事[6]。这一要求与中国传统相悖,康熙禁教不可避免,特别是在1721年1月17日读到翻译后的教皇禁令,大为震怒,写道“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7],这一谕旨被视为康熙禁教的正式通告[8]。因罗马教廷谴责中国礼仪,康熙认为教皇破坏他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冒犯其政治权威,最终导致其下令禁教,并为之后皇帝所继承,雍正朝最为严厉。据统计,1710年传教士在中国共有110多所驻地和250多个教堂[5]60,百年禁教期间基本被清政府没收,这也是晚清传教士要求还堂的借口。
二、清政府、传教士与徐家汇还堂案
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在英国的进攻下以失败告终,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在华获得丰富的经济利益。随后,美国胁迫清政府于1844年7月签订《望厦条约》。法国见状,也想在中国建立威望,特别是树立天主教的权威。于是在1843年派拉萼尼来华,拉萼尼很好地贯彻其政府要求,以武力威胁清政府,于1844年10月签订《黄埔条约》,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9]。这一规定冲击了清政府百年禁教政策,为天主教弛禁打开一个缺口,于是法国传教士利用可以在五口通商口岸的传教权等,开始考察上海旧天主堂。
(一)徐光启与上海天主教发展
法国传教士之所以将目光投向上海徐家汇,是因为“徐家汇确是和天主教有相当的关系,徐家汇实是赖有天主教堂的存在而繁荣”[10]。据说徐家汇的名称是因徐光启而得名。明代末期,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这次来华的传教士均属天主教[11]。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为徐光启提供了多元的选择机会,特别是处于宋明理学和佛老思想整饬社会失效的晚明,天主教的传入对思索晚明走出困境而重建信仰价值体系的徐光启来说是一大精神碰撞。在徐光启信奉天主教的过程中与三个西方传教士有较大关系,分别是利玛窦、郭仰凤(亦称郭居静)和罗如望。徐光启在与他们的接触和交流中深入了解天主教和西方的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天主教的道德教化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吸引使得他信仰天主教。为设立新的传教中心,徐光启选择了家乡上海。徐光启请来西教士郭仰凤为上海天主教开教,在徐光启的请求下,郭仰凤神父于1608年9月被派往上海。在郭仰凤神父和徐光启的推动下,两年的时间里上海的天主教徒已经有了二百多人[12]。徐家汇在徐光启的发展下,人们对天主教的熟悉度相较于其他地方略高,群众基础较好,于是江南教区的主教最终选择徐光启家乡的徐家汇旧堂。
(二)拉萼尼与清政府的还堂交涉
上海还堂过程中法国公使拉萼尼发挥了重要作用,拉萼尼利用他与全权大臣耆英之间的亲密关系,轻易地使天主教在华获得权益。在拉萼尼的推动下,耆英于1844年12月28日上奏皇帝,在奏本中提及“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信仰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这份奏折经皇帝朱笔批阅后成为谕旨施行。这份弛禁天主教的上谕上海道台(宫慕久任1843—1846年间上海道台)也是毫不犹豫地张贴出来。正因为如此,拉萼尼和传教士以为归还上海天主教的旧教产可以很容易实现。但是当拉萼尼向上海道台提出归还旧教产时,谈及两广总督(指耆英)给中国人民信奉教天主的自由,希望道台能跟上耆英的步伐,归还旧教产。但道台并没如拉萼尼所愿,推脱这不在他的范围内,并说:“如果上海民众见到一百多年来已由皇帝敕令充公的产业复归于洋人,他们定将起来反对。”[13]79面对上海道台的推脱,拉萼尼非常愤慨,认为这既有损自身的威信,也有损法国的威严。但他没有放弃,回到广州后故伎重施,又通过耆英向皇帝上奏,结果如他所愿,大清皇帝颁布诏令,宣布对天主教弛禁,准许给还天主教旧产。1846年2月20日道光颁布关于弛禁天主教的谕旨: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14]。
广州于是年3月18日张贴这个上谕,罗伯济主教(时署理南京教区)与南格禄会长(法国耶稣会士,时任江南教区耶稣会会长、代全主教)于8月要求上海地方官归还上海城内的天主教老教堂和旧教产。要求归还的旧教产主要有三处:潘国光神父建造老天主堂,已改为关帝庙;教堂旁边神父住院的房屋和花园,房屋已成为城内儒生们集会的书院;南门外旧耶稣会会士的墓地[13]85。但这些教产年代久远,没有留下明确的产权证明,只能依据民间的口头传说和回忆。为了能够顺利实现得到旧教产的愿望,卡尔代(怡和洋行代理人、丹麦领事代理人)等人谋划了一个万全的方案,要求归还潘国光神父建造的老天主堂,依据上谕已经改为庙宇不可得,但庙后面的花园和大房子是可以归还的,同时并以武力威胁上海道台。面对卡尔代的要求和威胁,道台在请示上级抚台后给予明确答复:“旧传教士的墓地毫无困难地即可归还给教徒,至于附属于关帝庙的那座房屋,由于许多重大原因不能发还,但可以另拨一方合适的土地作为补偿。”[13]86这正中法国教士下怀,最终共拨三块土地给法国天主教,一块在城垣之内,两块在黄浦江边,彼此相距约三公里,每块约有一公顷左右的面积[13]87。
三、上海徐家汇还堂案的反思
(一)上海还堂后引发系列还堂的发生
法国公使拉萼尼和传教士最终凭借政府实力使上海徐家汇还堂得以实现,这是近代还堂案的开端,为之后传教士以还堂为借口侵占中国土地提供了经验,自此各地发生多起因还堂而引起的教案。1848年福州黄竹岐法国教士借口“还堂”强占黄竹岐地方,未获成功。1851年松江府华亭县教士赵方济讨还教堂旧址,未能得逞。1860年北京法主教孟振生讨还教堂,在英、法联军的威胁之下成功索得。1861年山西绛州教会讨还“旧址”,非法强索绛州书院,最后以绛州东雍书院作抵,另强占土地四十三亩。同年,湖北省城法国主教徐伯达讨还教堂旧址,索得成功。1862年上海传教士讨还“旧址”,强占关帝庙。同年山东济南教会讨还“旧址”,赔款三千余两,强迫村民数十家搬迁。1866年南京交涉还堂旧址,传教士强占新地,酿成事端,法国以军舰围城,清政府屈服,等等[15]。近代还堂案从1845年的上海徐家汇还堂开始,以1895年南阳还堂结束而告终,主要集中发生在咸丰末和同治朝中[16]。还堂过程中传教士以政府为后盾,威胁清政府,清政府软弱无能大多予以答应,因而外国传教士纷纷要求归还“旧堂”。
(二)还堂中传教士的影响
上海徐家汇还堂过程充分体现了传教士的阴谋诡计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法国公使拉萼尼在上海还堂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拉萼尼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展开关于天主教在华更好发展的谈判。他在上海还堂过程中充分运用谈判技巧,首先施与压力。在与上海道台谈判中先拿两广总督耆英说事,谈及耆英给予他宝贵的礼物:使中国人有信仰天主教的自由,向道台施压,希望道台能够给予他同样的关于天主教方面的礼物,即归还天主教堂,但是他低估了中国官员的官场之道,道台以不在其职责范围内予以推脱。其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拉萼尼未能够顺利达成初衷,但他没有放弃,转而去广州,利用他和耆英的亲密关系,通过耆英向道光帝传达要求,获得成功,道光帝于1946年2月20日颁布了关于归还旧堂的上谕。这道上谕是天主教徒锐利的武器,凭借这份上谕,他们可以向中国“名正言顺”地要求归还天主教堂。拉萼尼为了达到目的,运用丰富的政治经验在中国官员中展开活动,最终借助与两广总督极亲密的关系获得成功。
传教士在要求归还上海教堂的过程中运用阴谋诡计顺利得到三块土地。首先派上海官员不认识的教士梅德尔神父出面,以法国政府命其调查拉萼尼获得弛禁天主教和归还教产上谕的执行情况的名义与上海道台交涉,变为政府间的交涉,而不是传教士的身份,无形给中国官员施以压力。其次,在谈判过程中加以武力威胁。由于清政府实力衰落,而且刚刚经历鸦片战争的失败,畏惧战争,卡尔代看到这一点,在与道台的谈话中特意提及法国舰长司令即将来到上海,并打算干几件辉煌的大事以表示对国王的忠诚,给道台以战争的压力。在要求归还上海旧堂时,要求归还的是已经改为庙宇的潘国光神父建造的老天主堂,依据上谕是不可得的,但是清政府一定会择地另给或加以经济补偿,事实上清政府的做法皆中法国传教士下怀。法国传教士通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和诱骗恐吓、武力威胁、声东击西的策略,顺利实现了上海徐家汇还堂,并将此种态度和策略运用到之后的还堂交涉中。
(三)还堂中清政府的态度
鸦片战争后法国也想“得到和英国、美国同样的权利”[13]74,拉萼尼以其政府实力为后盾威逼清政府,而清政府因国势衰微,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颓败,被迫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在《黄埔条约》中虽有关于天主教的弛禁,但未能满足法国传教士的要求,拉萼尼为实现天主教在华充分发展,要求进一步放松对天主教的限制,特别是归还禁教期间没收的房产,清政府以咸丰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显然已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稍加威胁就退让,为避免战争,竭尽所能满足对方要求。
在双方交涉还堂过程中清政府官员明显缺乏外交经验和政治远见。晚清的外交官没有接受科学的洗礼,“从总体上讲依然是封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素质低劣,愚昧无知,民族意识淡漠,封建的习俗、腐败的官风在其身上不时地表露出来”[17]。以两广总督耆英为例,他被道光皇帝予以重任,处理政府外交,但他与法国公使拉萼尼私交颇好,成为拉萼尼利用感情牌获取权益的重要方式。当时拉萼尼向上海道台要求归还旧天主教堂时,道台与拉萼尼打太极,推诿不在其职责范围内,拉萼尼无法,就向耆英要求,而耆英替其向皇帝递奏折。拉萼尼通过耆英一步步为法国向道光帝取得信奉天主教自由的旨意和归还禁教期间旧教产的圣旨,耆英作为晚清政府大员、皇帝股肱之臣却缺乏外交经验,固守所谓朋友之道,殊不知自己已被拉萼尼当作棋子,在为拉萼尼实现归还旧教堂的过程中充当垫脚石,间接损失中国利益。作为清政府中央大臣如此,地方官员同样缺乏外交经验,当道台得到自己上司抚台归还墓地和另择土地补偿的意见后依意见办事,不加争取,上面说什么就做什么,只是政策忠实的执行者,而不是坚决地维护地方利益。同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归还上海旧天主教堂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只求一时安稳,以为只要归还就可以满足列强,不曾想这大片属于中国土地上的人民、权益如何处置,外国传教士如何利用中国这片土地作为侵略中国的前站,从事危害中国的事业以及其他列强诸国在华传教士跟随法国传教士的步伐也要求归还禁教期间的旧教产等。在归还上海徐家汇旧教堂过程中,清政府官员从上至下呈现了封建政府官员政治意识低下,不辨是非,不守全国家利益,在近代时局已变之下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没有国家官员所应有的外交之道、应变之道及长远的政治眼光。
四、结语
清朝末年的还堂案与清中叶施行的禁教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清政府禁教是因为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之间的冲突,甚至发展为政治冲突,为维护本国的文化传统,维护自身统治,从统治角度而言清政府厉行禁教无可厚非。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衰落腐朽的实质暴露在外,西方列强在知晓清政府的真正实力之后大肆侵略中国,为了自身发展从中国掠夺尽可能多的利益。特别是来华传教士,有很大一批借传教之名,对中国民众进行文化侵略和从事间谍等活动,为本国侵略出谋划策,在传播《圣经》的背后藏着黑黝黝的枪口。上海徐家汇还堂之后更是掀起还堂风波,在要求归还旧堂的过程中手持清政府颁布的归还旧堂圣谕,背靠其国家军事实力,在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时候,仅凭回忆和口头证据等,以各种借口要求清政府归还旧教产。面对传教士的无理要求甚至是讹诈,清政府因自身实力的软弱,在对方的威胁恐吓和施以诡计之下基本满足其要求,拨相当面积的土地给各国教会,而此时清政府的官员上至朝中重臣,下至地方官员,在处理教案过程中因缺乏外交经验和政治远见,没有做到为国家争权、守利,反而有些所作所为间接促使本国权益丧失,不禁让人沉痛与深思。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1.
[2] 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M].北京:五洲传媒出版社,2004:30.
[4] 黄伯禄.正教奉褒[M]//韩琦,吴旻.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363.
[5] 胡建华.百年禁教始末:清王朝对天主教的优容与厉禁[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4.
[6]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95.
[7]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70-71.
[8] 陈林.中国无神论与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76.
[9]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689-1901)[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62.
[10] 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资料正集:第1册[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226.
[11] 陈卫平,李春.徐光启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4.
[12] 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M].于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97.
[13]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M].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31.
[15]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773-779.
[16] 刘燕.晚清咸同年间“还堂案”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17] 曹倩琴.清末民初外交官群体素质比较:中国外交近代化历程探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02.
CommentontheReturningChurchCaseofXujiahuiinShanghai
ZHOU Hongyue,CHEN Jiur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ir governments’ strength, the missionaries required 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to return the old assets during the great prohibition with the decline of Qing Dynasty in modern times. The people of Xujiahui in Shanghai had a good foundation of Catholicism, so the first goal of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was the old Catholic church of Xujiahui in Shanghai.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turning church cases in Shanghai, the missionaries used the schemes to force 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to return the old assets, which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returning church case in modern times. Learning from their experience, later missionaries asked 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to return the old assets, which led to a series of the returning church cases.
the great prohibition;the returning church case of Xujiahui;Lagrene;missionary
张 杰)
2017-03-30
周红月(1993—),女,江苏盐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陈九如(1963—),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K252
A
1674-0297(2017)06-0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