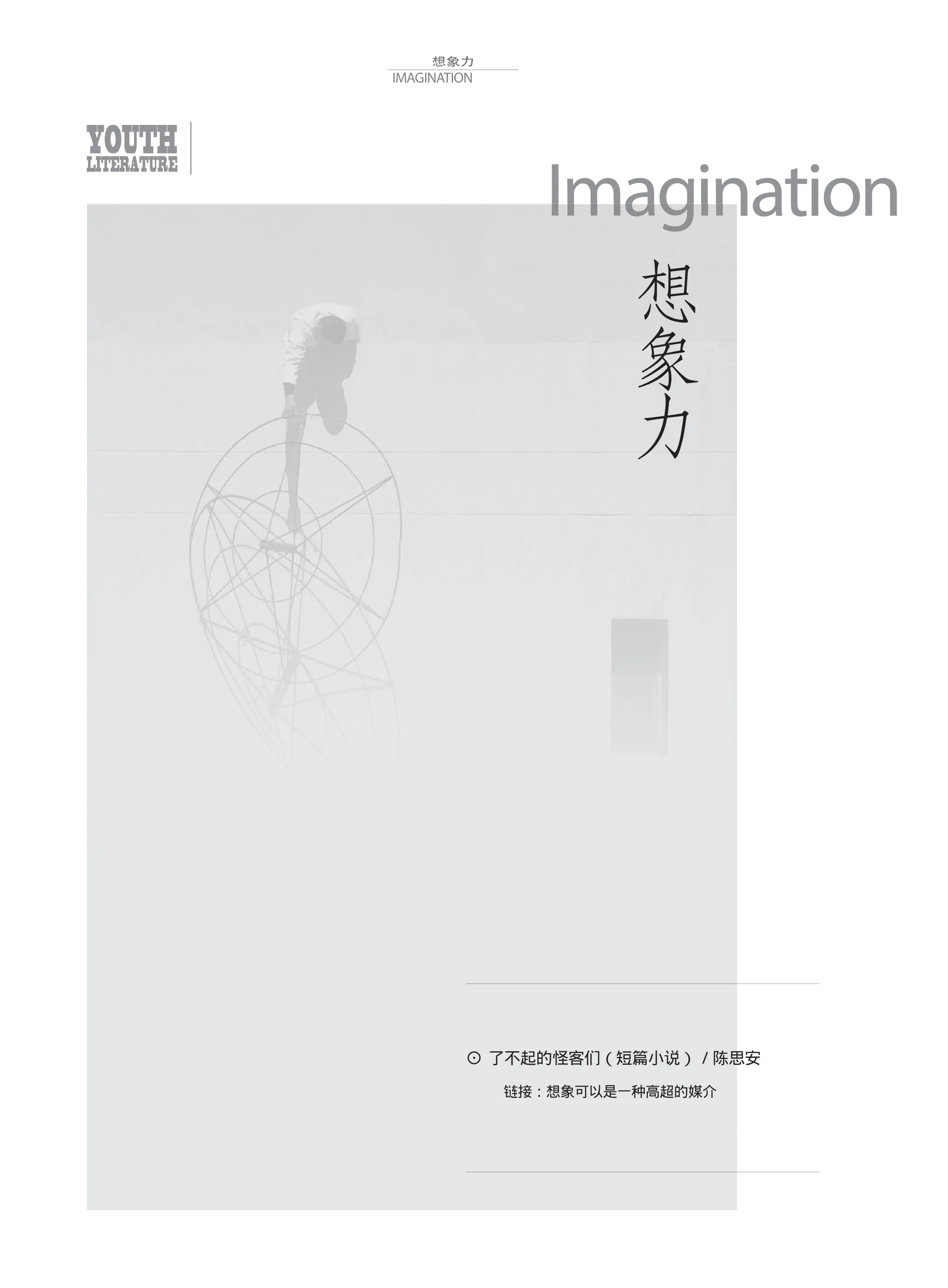落雨声
2017-03-20⊙文/梁豪
⊙ 文 / 梁 豪
落雨声
⊙ 文 / 梁 豪
梁 豪:九〇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人民文学杂志社实习编辑。曾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等处发表文章,小说曾获第二届马识途文学奖一等奖。

一
多拉是那种看起来再大的事摆在她面前,都一副云淡风轻模样的女人。然而在这样一片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天知道有多少男人陷在那暗礁与漩涡里头。
用她的话说,这世上没有哪个女人天生就是冷血动物,也没有哪个男人是好鸟。“男人不出轨,不是上头有问题,就是下头有问题。”她说这话的时候,吴楚正坐在她对面故作绅士地抿着卡布其诺。
外面下着雨,天气预报说东南亚九号台风行将来袭。现在雨还不大,却很是掷地有声,一粒粒分分明明地打在落地窗外那株上了年纪的使君子上,像一场漫漫无尽的鞭刑。吴楚感到自己的心境跟雨天的空气一样,有种说不出的沉郁,尽管他确定自己还蛮享受现在的一切。
话说这家咖啡馆的历史比吴楚降临人世还悠久,那年曼德拉才刚刑满释放,结束了他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之灾。而离吴楚父亲酒醉之后把母亲推到沙发上肆意寻欢,然后顺水推舟似的将他带到这世界,大概还有一年光景。
必须说多拉跟吴楚很像的一点是,他们都认同吃东西选老店更靠谱,而买东西选贵的总不会差到哪儿去。但她讨厌在任何咖啡里加糖,而他最喜欢吃甜食,就像现在这样,她点的是一杯意式特浓咖啡,而他还伸手示意服务生多要一块提拉米苏。
今天多拉的打扮多了几分知性,这让吴楚不由自主地多瞅了好几眼。一条淡蓝色的紧身牛仔裤,上头配一件酒红色的宽体针织衫,隆起的胸部就算再宽松的上衣也无从躲藏,那紧致而细长的腿形永远是如此摄人眼球,配上那双学生坡圆头搭扣的金色凉鞋,让美得以一览无余地延续到白皙的脚趾和那深红的脚指甲。吴楚不敢过分明目张胆地盯着多拉,他的目光躲躲闪闪,时聚时散。必须承认,这种静水深流的韵致太具有魅惑力。如果不是当初多拉从手机翻出她一岁女儿的照片,吴楚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她是个已经而立之年的女人。这话的意思是,多拉看起来真的顶多二十出头。
他们分坐在彼此对面,一张手臂长的桌子的距离。两人见面很少会说那种营养十足的话,无非是多拉轻描淡写地娓娓讥谑一番男人的种种劣根,抱怨一下上司的不近人情、男同事的色胆包天和工资的微薄可怜。吴楚则会跟进附和几句,他主要是在咖啡与甜品的味道上做些口头文章,更多时间里他只是赔笑,那种不露齿的自以为男人味十足却略显迂腐的微笑。吴楚不愿也不敢说太多话,因为谈话的兴致一旦过分高涨,他二十三岁短短且乏善可陈的人生阅历,就会将他不谙世事的纯理论派身份给出卖,就像上次用餐后,他搞不懂为什么多拉让他把餐巾纸留着,她那时对他说了一句不知是无心之谈还是意有所指的话:“男人不都需要它嘛,在餐桌上不都是男人拿出纸巾的吗?”自从目睹了那张跟多拉一样脸蛋挂着两个深深酒窝的一岁女孩的照片以后,吴楚就对“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话认识得格外通透。

⊙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2015剧照)·张亦蕾
但在今天,他们说话的质量和容量都提升了不少,对话间隙的留白却比以往都来得漫长。就在刚才,多拉用她那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语气告诉吴楚,她老公前两天跟她坦白了自己的外遇。“再老实的男人,也脱不了这口嗜好。”那时多拉散漫得十分迷人的眼神,一直盯着杯中早已冷却的半杯咖啡。
直到这时,吴楚才突然惊喜地察觉,今天多拉身上喷了香水,清淡芬芳,时隐时现。他不谙香水的品牌和类别,但他喜欢这个味道,与学校留学生公寓里的那些重口味相比,简直天差地别。
二
吴楚是在快到饭点的时候回到家的。而偷偷挤出两个小时工作时间跟吴楚碰头后,多拉还得回去给女儿做饭。她总说是去给女儿做饭,但吴楚心里清楚,这些饭菜都是三个人的分量。吴楚在到家后才发现两边的衣角已被雨水打湿。这场本来乏人问津的雨越下越大,看来势必要惹起人们的注目。
吴楚正站在紧闭的窗边望着窗外,雨珠闷里闷气前赴后继地撞击在窗玻璃上,变成一条条扭曲错综的线条,这让吴楚猛然想到新闻里看过的关于抹香鲸的集体搁浅自杀。但这种联结是转眼即逝的,他的心思更多地被刚才的约会场景牵绊,情境正在他的脑袋里重新过滤,胸口的心跳声在这个本该放松的节骨眼却显得有些放纵。
其实,吴楚并不情愿将这个地方称之为家,那不过是这座繁华都市中某处落寞角落里的一间廉租房。闹中取静,却也肮脏苟且。母亲的钱一打过来,他就把月租打给房东,从不拖欠,他时刻谨记这不过是桩实际得不剩感情的买卖。尽管他寄居在这里行将迈过第五个年头,但除了那张充斥着自己体味的床,他觉得一点归属感也没有。或者说,他从来就没在任何地方产生过归属感。
隔壁房间又传来了不友好的动静,这种不友好是在其内部发生的,但往往会波及隔音效果奇差的吴楚这厢,隔墙有耳有时是个零和的把戏。
一墙之隔的那边,住着一对应该跟吴楚同龄的研究生情侣,对于邻居的认知,吴楚几乎全由那边传来的声音去拼凑。男生口中叫乌美的女友可不是善茬,他们无数次的骂战基本都由她挑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一个人构筑起了两个人的争吵,也是包括吴楚在内三个人的聒噪,而那叫子俊的男友几乎从不还嘴。
吴楚曾在某个早睡的晚上被乌美给吵醒,他起身猛烈地敲打那面纯粹起遮羞功能的墙面。薄薄的墙体那头先是片刻的肃静,随后传来了女生更强烈的敲打和谩骂。第二天子俊一手拖着那副无边框厚镜片的眼镜,一手摸着后脑勺跟吴楚道歉;而最困惑吴楚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才能妥帖地回应别人的道歉。因此从那之后,三个本就无话可聊的同龄邻居,在偶然的碰面中显得更加尴尬。吴楚后来索性直接对两人视而不见,不管是在他眼中几近可怜的子俊,还是那飞扬跋扈的乌美。
公元前四〇八〇年萨拉米斯海战,希腊海军有战船三百五十八艘,波斯海军拥有一千二百零七艘。在战役前夕,由于不熟悉天气与航情,波斯海军在实施包围行动时先后两次遇到飓风,六百艘战船被飓风刮走,战斗力损失近半;希腊海军将领特米斯托克利斯利凭借对风力知识的了解,轻而易举地扭转了战争的形势,希腊文明得以发展繁荣。
“好屌哦!”
瘦削文弱的子俊是个资深的军事迷,只是吴楚搞不懂为何他总要把那些武器装备或历史战事的讯息大声念出来,就像那些痴迷留学的学子高声朗读英文。当然这世上搞不懂的事情何其多,吴楚无须为此进行费力劳神的猜测,正如他不懂为何会有人如多拉那样喜欢下雨天,“晓来雨过,踪迹何在,一池萍碎”。而为什么男人总是三心二意朝三暮四,为什么水性杨花只用以形容女生,而男生却是风流倜傥?
倒是这样一来,吴楚很被动地了解到很多“军情”。比如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美军依阿华级战列舰威斯康星号、密苏里号参加海湾战争,炮击八十三次,发射四百零六毫米炮弹一千零一百发,相当于冲绳战役射弹量。“好屌哦!”心情舒畅时,吴楚总爱装腔作势地模拟子俊的口吻,蹦出这句他仅有的脏话。
“哎,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张口闭口飞机坦克大炮啊,你把家当兵工厂吗,你把我当女人吗?整天这舰那舰的,再这样下去我就跟你说再见!”
“子俊,你听到没有,闷声发大财吗?拿出你辩论队的气势来啊,别说我蛮不讲理,是你自己太过分,谁男朋友整天买军事手办模型啊,在一起那么久,你扪心自问,你有送过我什么像样的礼物吗?”
“三,二,一……好,不说话是吧,你有种,有本事一直给我哑巴下去!”
三
北回归线附近的仲夏季空气很闷,人像被抽出水面的鱼,呼吸跟不上肺的呼唤。
多拉提议去码头坐坐,吹吹聊胜于无的热风。她的机车在路过加油站时顺带进去买了几罐啤酒。吴楚坐在后座上,这是他第一次坐上多拉的机车,他刚放在多拉腰际的手旋即被她打开。她的长发顺着风势不断挠着吴楚的脸,于是他用手替她抓了一个马尾。吴楚看见了多拉嫩白的后脖颈,他的手小心翼翼地放在上头,就像放在一块无比光滑的海绵上。
码头上人迹寥寥,他们并排坐在码头的堤坝上,荡漾着脚,一拳之隔,彼此轻轻碰了一下酒罐。中型集装箱船停泊在岸,只有渔民的小艇在泛浑的江面徐徐挪动。玫瑰色的天空映照出玫瑰色的大地,似乎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才能用一个傍晚的红霞,洗出最逼真最动人的世间景象。
“落雨声,哪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越头呒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起畏寒,寂寞的雨声,捶阮心肝。”
多拉用手机放起了江蕙的歌,江蕙是她最喜欢的歌手。他们初次见面时,多拉放的就是这首《落雨声》,她说这首歌其实更适合吴楚。当时吴楚告诉多拉,他最喜欢的歌手是小野丽莎。这个名字是他从另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那里听来的,在认识多拉之前,他跟那个女人断了联系,但吴楚却记住了这个叫小野丽莎的日本爵士歌手,那低哑的歌喉如一粒粒安眠药,使吴楚度过了长达半年的失眠。
“男人坏,女人贱,喷香水的女人,一来想勾引男人,二来要气死男人家里的女人。我又不傻。”
“你觉得我老吗?”吴楚坚定地摆了摆头。
“我很久没有男朋友了。”多拉难得看着吴楚说话,“应该是一直。”
这回是吴楚主动躲过了多拉的眼光。对于一个已婚母亲的这番话,吴楚不知如何作答。江风湿漉漉暖烘烘地打来,裹着鱼的腥味。他两眼生涩地盯着江上渔民船头的炊烟,自顾自地嘬着啤酒,嘴唇与铝罐之间发出噗噗的声响。
吴楚想到那个跟多拉去唱歌的雨夜。他发觉一到下雨天多拉就特别活跃。那天晚上其实吴楚已经躺在了他那弹簧咯嘣响的床上。作为国文系研究生,吴楚习惯睡前翻翻小说,他还记得那段时间他正在看村上春树的《1Q84》。
手机是这时候响的,手机里多拉的分贝比以往见面时高出不少:“嘿,小帅哥,还没睡吧,快出来唱歌,算陪陪我啦!”吴楚在打扮完毕打开房门时,才发现外面正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Fuck!”他还是打了一辆出租车。
KTV包厢里已经很热闹,吴楚除了多拉谁也不认识,他不无尴尬地坐在多拉旁边。几根香烟向他飞来,几个老男人正冲他微笑致意,他们在挤出笑容时眼角一并出现的深邃皱纹,使吴楚突然想起多年未见的父亲。在父母离异以后,他再也没见过他。
话说多拉这晚上的表现有些奇怪,她很坦然地贴在吴楚的耳廓里说话,她的话湿答答的。吴楚试探性地把手放在她的后背,多拉没抓麦克风的那只手从后面一把抓住了吴楚的手掌,她把他捏得很紧,很舒适。作为反馈,吴楚的指尖迫不及待地抚摸起多拉没有留下任何岁月痕迹的手背。
“多拉,在哪里认识的后生?可以喔!”长相跟歌声一样丑陋的男人意味深长地说,露出粗俗狡黠的笑靥。多拉并没有搭腔,她招呼吴楚跟大家一起玩骰盅,输者罚酒,好几打未开封的啤酒泡在冰水里蠢蠢欲动。
这晚上多拉输得特别多,一杯杯的啤酒往肚里送,吴楚帮她喝了不少,但吴楚感觉得出,多拉并没有醉。她的酒量应当跟她的容貌一样,出人意料的好。
在多拉的提议下,两人是在零点左右提前离开的。多拉那时走路已经有些不稳,吴楚知道那是刻意为之的醉态,他不相信那个擅于交际的多拉不胜酒力,他不相信一贯冷淡以至于冷酷的多拉的步伐可以如此娇弱。不过吴楚很乐意扶着东倒西歪的她,前胸贴后背,自己跟着带点趔趄。他感觉他们正在上演一出戏,这场戏的主题暧昧不明,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很上心,甚至比多拉还要更投入。
多拉在无人而昏暗的街边蹲了下来,吴楚托着她的腋窝将她带到打烊店面的台阶上坐下。吴楚的右手带点颤抖地上下抚摸着多拉瘦削的肩膀,这时候他是有些不知所措的,他的眼睛扫了一眼不远处夜雨朦胧中招牌依然刺亮的便捷酒店。他的内心竟然没有渴望,吴楚到这时才恍然意识到,他在错失将自己的处子之身在对的年纪献给一位理想中的纯情恋人之后,并未完全做好自暴自弃的准备。
这时伏在双臂下的多拉说话了:“你知道吗?刚才里面的一个男人是我的老相好,我们热烈地爱过,也许还爱着?我说过我可以为他离婚,那时他就不说话了。我奋不顾身的勇气在他看来是一种轻浮。你懂吗?男人原来最怕一个女人的真心。操!”
“好了好了。”吴楚的安慰尽是敷衍。他正趁机亲起多拉,手也变得勤奋起来。他在暗示自己他需要。
这时多拉忽然抬起头,把她的嘴贴到吴楚的嘴上。吴楚到现在也不会忘记那一刻的感觉,那是成功的讯号,那是他跟多拉交往的目的之一。不是吗?吴楚将真正意义上保留了二十三年的初吻交给了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他正在努力回忆、搜集所有关于接吻的信息,以便即刻付诸行动。他们的舌头终究在彼此的口腔里碰头并挑逗,在充斥着啤酒淡淡苦涩的密闭空间里,它们各怀鬼胎,各取所需。
吴楚将手掌放在多拉的胸部摩挲,他感到自己真切摸到了子俊口中那款俄罗斯“撒旦”洲际导弹。多拉像是猛然清醒,她一把推开了吴楚。
“男人是不是都用下半身思考啊?!”
吴楚明白,这场戏该要收尾了。
多拉是自行坐上出租车消失在茫茫雨幕中的。吴楚则一个人兴奋地在雨中飞奔呼喊,直到天际微亮才全身湿透回到家。
在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就跟从来没有过那个雨夜一样,模棱两可,不进不退。多拉只对吴楚说过一次,她说那天晚上是自己失态了,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不过还是谢谢你的陪伴”。吴楚习惯性地一笑带过,他不会去拆穿什么,只是偶尔想来会觉得有些好笑。
四
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在空袭中大量使用AGM-86及BGM-109C“战斧”巡航导弹,但在巡航导弹做低空或超低空飞行,特别是飞越高山时,因受到云雨等视程障碍影响,导致导弹命中精度明显下降。据美联社报道,美海军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约有百分之二十未命中目标。
一连有好几天不见乌美的动静了,隔壁房间除了子俊军事信息的朗读外,几乎毫无声响。抛开那不可解释的军事“播报”,子俊是一个如此轻易让自己销声匿迹也叫人忽略的家伙。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反倒让吴楚觉得生活似乎缺失了点什么。连廊里乌美的衣服已几日不见晾晒,或许她真的一气之下,买了回家的机票。
吴楚最近在看卡佛的小说,现在他把《大教堂》盖在肚脐眼上,开始思考乌美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他竟突然十分关心起墙那边的情况。
吴楚记得那个跟多拉喝完咖啡便回家的黄昏。那天的雨下得很拖沓,天气预报说九号台风就要登陆,事实证明气象监测再次摆了大家一道,台风从正步改走猫步,打了个擦边球接着往北走,没过两天太阳就恨不能把人晒脱两层皮。
就是那天晚上,乌美对子俊有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思,她的指责越发漫无边际,她的语气变得很是强硬,而且可说是出言不逊。

⊙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2015剧照)·张亦蕾
“你喜欢吃辣我忍,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喜欢吃甜的感受,为什么每次买回的鸡排都是麻辣的,你就不能多买一份加蜂蜜的吗?”
“闷葫芦,书呆子,你真以为你军事家啊,废材!”
“人生走错一步,接下来就是步步错,我算满盘皆输了。当年为什么就不坚持自己的意志去香港念大学?离家近语言通,结果在这边认识了你,瞎了眼,要到这步田地!”
“你这么看我几个意思,想造反吗?陈子俊我告诉你,老娘早就不想跟你过了!”
吴楚当时忽然听到一声犹如瓦斯爆炸的怒吼,那是子俊的声音。他似乎说了句什么,但吴楚没听清楚,他的心不由得惊颤了一下。吴楚现在再去回想,发觉其实就表达愤怒的方式而言,声音比言语要有效得多。
或许就是那个夜晚之后,乌美不见了的吧。这些天吴楚不是混迹学校,就是跟多拉在一块儿,此刻他竟为自己的疏忽生出了一点自责。
这天晚上吴楚做了一个怪诞的梦,梦里强烈的紫外线将他全身灼伤,他在滚烫的藏青色的泥土上睡成一个大字,源自地心深处短促的吐纳声,从泥土的缝隙里蒸发而出。吴楚就这样被焦灼地热醒了。
这学期结束后吴楚就要去美国上学,他不知道除了不停念书他还能干吗,他甚至连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多拉算吗?他并没把这事告诉她。现在,吴楚倒是很想找多拉当面聊聊,把刚得知的江蕙宣布退出歌坛的消息告诉她,或许她早就从网上获知,现在正在郁郁寡欢。但是这时候的多拉很可能没空搭理他,昨晚是多拉值夜班,现在她应该回家补觉了吧。就算没有,多拉也是不会闲着的,要知道吴楚的朋友圈有多窄,多拉的人际网就有多广。
一丝不挂的吴楚好不容易从床上爬起来,他来到窗边将窗帘拉开,他的全身布满葡萄干一样的汗珠。此刻他被完全浸淫在炫目的阳光中。
今天天气晴朗无云,烈日灼灼,看不到任何雨的迹象,多拉的脸色肯定不会很好看。但吴楚知道这世上总有别处在下雨。或许他可以试着邀请多拉,去一个有雨的地方度个两三天的小假,就他们两个人,来场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吴楚觉得自己是该主动一点了。
或许在那里,也住着一个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