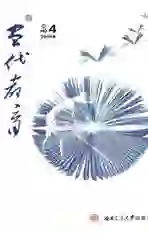守望
2017-03-18何灵燕
何灵燕
贵阳的天气很是让人捉摸不透,清明节前夕竟热得让人想穿短袖了,但还是听了妈妈的话折了一件薄棉衣在箱子里准备带回家。这是我们家一个默认的传统,即每年清明节都尽可能回老家。收拾好了,我们便和同校的堂哥一起先去了四爹家,第二天早上和四爹一起回去。
还在公交车上的时候,奶奶便打了电话过来,问我们什么时候到,她好准备晚饭。果然等我们刚到,饭就准备好了。奶奶今年七十六了,要把点点滴滴的岁月痕跡刻在脑海里好像是很难的,我能记起奶奶的时候是我五岁那年。奶奶把我抱在怀里,松软的脸贴着我的脸,用她粗糙宽大肤色暗沉的手掌一遍遍摸着我的头说:“这么小的年纪就去读一年级会不会受到欺负啊……”而那个时候她也已经六十二岁了,把头发全部盘了上去藏在了白色的圆帽子里。十多年的光景,我怎么绞尽脑汁地回想也讲不出来她一年比一年有什么变化。但现在看到奶奶慢慢夹菜的样子,心里却总是生出这样的念头:奶奶越来越老了。大概岁月的痕迹还是刻在心里了。
爷爷过世得很早,离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奶奶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住在乡下而不肯和她的任何一个子女同住。今年,因为8岁的堂弟一直缠到她让她来陪他才勉强答应来住几个月。听说我们要回老家,奶奶有些期待地说:“我也想回去,但是我回去就不来了,唉,还是等阳阳(堂弟)放暑假再回去。”我不太赞同奶奶一个人住在乡下,但看到奶奶低落的样子内心又十分不忍。我默然。这个时候四爹说话了:“你再耍几个月吧,等我这次从老家回来后就带你坐飞机到五弟家耍几天,然后暑假再送你回去。”奶奶低落的心情便明显地好了一点,说道:“那也好,他最小却又隔得最远,趁我还算硬朗能去一次是一次。”末了,便去睡了,等我去睡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我便蹑手蹑脚地进屋睡在了她旁边。
第二天很早的时候,奶奶就叫醒了我们。吃完早饭,她和我们一起下楼。我说:“奶奶,你别去了,上上下下的太麻烦了。”她一边扶着扶手下楼梯一边回道:“我又没什么事做,我看着你们走。”想了一下,我便牵着她的手慢慢走下去。等我们都坐上车,四爹也对她说:“妈,你回去吧,早上风大别感冒了。”奶奶应着:“唉,唉,我就上去。”四爹倒车的技术不太熟练,车子又多,我们折腾了好久才倒出来准备出发。“唉,那不是你奶奶嘛,她怎么还不上去?”四爹突然说道。我看向倒车镜,奶奶果然还在后面的石梯上站着,我便打开车窗伸出头去大声喊道:“奶奶,你回去吧,我们走了。”四爹缓缓开动了车子,我看到奶奶还站在那里,直到车子出了小区转了弯,我便看不到了,或许她回去了,或许还站在那里。这个场景突然让我想起了好多个与这个极其相似的记忆片段。
幽静的村落里,曲折蜿蜒的山路上平整、稀疏地铺着石板,走上十来分钟的样子便可看见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竹林旁边便是一栋雄伟却陈旧的木房子了。房子前面有一个宽广的院坝,院坝边有一排梨树。奶奶就经常在树下对我们说:“回来啦!”或者站在树下对我们说:“走吧!”然后静静地看着人影消失在蜿蜒的石板路上。有时她旁边的梨树正开着白花,整个坝子都飘逸着清香;有时她旁边的梨树已经结起了婴儿拳头般大小的梨子,茂密的叶子刚好给奶奶投下一片阴凉;有时她旁边的梨树只剩一些渐枯黄的叶子,果实已经被我们欢快地采摘了;有时她旁边的梨树连枯黄的叶子都不剩了,只积了一树的白雪。奶奶就站在那里说着:“回来啦!”“走吧!”
和四爹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吃完饭便睡去了。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便全家一起回了老家,下了车便走上蜿蜒的石板路,竹林一片生机勃勃的浅绿。哇!梨树正开着花儿呢,柔柔的嫩叶俏皮地藏在白玉般的花瓣下,默默地散发着清香。奶奶家的木房子也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大门紧闭着。我们就在梨树旁站了一会儿便去给爷爷挂清了。爷爷的坟墓就在房子旁边不远,也就两三百米的样子。坟墓上没有长什么杂草,坟前倒是还残留了旁边树木去年的枯叶。说来我是很怕这些坟墓的,但在爷爷的坟前却觉得很亲切。我们取出清子给爷爷挂在坟头上,又按辈分磕了头。再次回到奶奶家的房子看看屋里,妈妈去看了她柜子里的棉被有没有被漏雨打湿、有没有被耗子啃坏,四爹又和我去房子后面的园子里,里面还种着奶奶年前种的蒜,蒜苗已经被杂草包围了,我们便索性把这一小块蒜苗全部拔了带走。这次倒是走的利利索索,没有人依依不舍地站在院坝的梨树下望着我们走,这样反而让我心情低沉下来。
踏着石板走过竹林边,我突然想起了以前回这里的场景。通常是和妈妈一起回来,有时还有堂哥和我们一起。走石板路的时候我总是刻意地去一步踩一个石板,不一会儿就被妈妈甩了一段距离,我又赶紧小跑跟上,然后再一步踩一个石板……当我可以看到奶奶院坝前梨树的时候就开始大声喊道:“奶奶——奶奶——奶奶……”奶奶果然应声出来站在梨树下,等我和堂哥跑近,对我们笑道:“回来啦!跑什么跑,摔在石板上还是很痛的。”等妈妈到了,我们便一起进屋,奶奶便开始忙活做饭,妈妈就去帮她,堂哥也忙去帮她拿柴,我便坐在炉灶前开心地生火,这是我回奶奶家最喜欢做的事了。把干草放在灶里,把纸屑点燃放进去,再用吹火筒不停地吹,火就慢慢地生得越来越大,我就继续兴奋地吹吹火筒,直到炉灶里面的柴燃得“噼噼啪啪”响,我也不停下来。这个时候妈妈总是会阻止我的,说这样费柴,而奶奶总是笑着说:“你让她玩,没事的。”奶奶每次做菜,总是有好几盘肉,不会说让你多吃饭,只是说:“多吃肉,多吃肉。”吃完饭我便和哥哥去旁边的竹林里玩。哥哥爬树很厉害,光溜溜的竹子他也能“滋啦滋啦”地就爬上去,我就只能在地上的断竹桩上走来走去地玩一下,有时被他嘲笑得恼羞成怒了,便作势要去摇他的那棵竹子,他便麻溜地“刷”的一声就下来了。然后就和我一起在里面玩自创的“竹林微步”了,即走路不能沾到地,必须踩在断竹桩上或裸露出来的竹根上,一直到天黑才回去。妈妈、奶奶和我睡在一起,我就在旁边听她们细声地说着村前村后家里家外的种种琐事,渐渐地在她们温暖的嗓音里睡去。每次走的时候,奶奶便大包小包地给我们装了许多东西,腊肉、豆子、竹笋……和送我们一起走到梨树下,我们无外乎就是和她说“保重身体啊”“下次我们再回来”等诸如此类的话,她点点头,对我们挥挥手说:“走吧!”我们便走了。在能看到梨树的范围里,每每回头都看见奶奶站在梨树下静静地看着我们。等我从回忆里抽身回头的时候还能看到梨树,可梨树下面空落落的,似此时的心情,便隐隐地有些懂得奶奶为什么一个人也要守在这里的心情了。
天气急变,第三天早起准备回校的时候冷得刚好可以穿上带在箱子里的棉衣了。两三天的假期实在太短,回家没有过多久的欢乐时光,倒是徒增了离别的伤感。妈妈站在大门口的身影慢慢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还来不及看到她变成看过的书里写的那样缩成一个小点,车子一个转弯,牵挂的景象便戛然而止,一颗心也沉了下去。不,应该是两颗心。
节假日的高速如预料中的那么堵车,奶奶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等天黑了好久我们才终于到了。奶奶当然不是像我们离开之前的那样低落,甚至让我想到了“雀跃”这个词,从我们进屋起她就问个不停:“房子还好吧?”“没漏雨吧?”“屋里没有进耗子吧?”“我园子里的蒜苗呢?”……直到吃过饭,她才好像问完了所有问题,坐了一会儿,便去睡了。我去睡的时候再次蹑手蹑脚地躺在她旁边。我刚躺下,她却转过身来对着我。“奶奶,你还没睡啊?”我惊讶道。她叹了口气道:“哎,有点睡不着。一会儿就睡了,你明天还要上课,好好睡吧!”屋里又安静了下来。半响,她又突然说:“你爷爷的坟上没有长什么杂草吧?”我说没有啊。安静了一会儿,她突然又出声:“虽然他过世得早,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他过世的时候你四爹和你五爹还在上高中呢,我虽然为他们吃了一些苦,我也不后悔。因为现在他们几兄弟也还是有出息。只是你爷爷比较命苦,一点福也没有享到,不像我现在什么福都享到了!”听了这话,心里突然觉得有些酸涩,却不知道该怎们做,想了半天只说了一句:“奶奶,别想了。我们早点睡吧!”她也回道:“嗯,不说了,我们早点睡吧。”
屋里再次安静下来,好久好久都没听到她说话了。当我昏昏欲睡时,突然又听到奶奶说:“等你们放暑假了,我就和你们回去。我在家里,你们回去才有个家。家里有我守着,你爷爷才放心。”
这次,我没有答话,奶奶也没有继续说了。不久,就听到了她浅浅的呼吸声,我便准备安心睡了,恍惚中看到奶奶在满树挂着熟透了的梨子的树下笑着说:“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