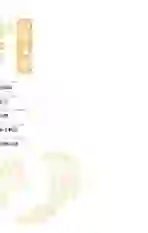荷花
2017-03-16郝炜华
1
从前,付春风还不叫付春风的时候,在一个三等火车站做上水工。早上七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第二天休息一天,然后再晚上六点上班,早上七点下班。
六点下班或者上班的时候,付春风都要经过一片坟地。坟地里种着杨树、柳树、榆树,还有一些付春风叫不出名字的树。树下面长着密密麻麻的青草,有的青草比人的个头还高,青草里藏着一个又一个坟堆。也有坟堆没被青草覆盖,那是刚刚垒起的新坟,它们像才印到报纸上的新闻,还散发着墨香和纸张特有的新鲜味道。新坟通常插着白纸与黄表纸,堆着三个或者五个花圈。风吹过来,花圈上的纸花还有写着某某永垂不朽,某某敬献的挽联哗啦啦响成一片。
丁一浩告诉付春风,坟地属于一个名叫粮店的村庄,村里祖祖辈辈死去的人都埋在这里。丁一浩与付春风的单身宿舍就在坟地旁边,丁一浩住付春风楼下,有事找付春风时就用拖把捣捣房顶。夏天,丁一浩买来一只浅口瓷盆,盆里绘着荷花还有金鱼。他到粮店村的藕池采来荷花,搁在瓷盆里,有事没事就叫付春风下来看荷花。
丁一浩是火车修理厂的木匠。
火车修理厂在单身宿舍的南面,铺着四条铁道线,白天,铁道线上停着一趟绿皮火车,晚上,则停留两趟绿皮火车。那是从这座城市开往深山另一座城市的火车。火车修理厂负责维修养护它们。白天晚上,火车修理厂里都有人,他们检查车轮、弹簧、车窗、座椅是否有问题;检查车门锁闭是否牢固,风扇转得是不是正常,锅炉里的火能不能正常燃烧。凡此种种,保证火车的运行安全。白天下午,会有一帮女人,戴着胶皮手套、举着一根绑着黑色胶皮管的长杆子,清理列车卫生。这是这趟绿皮火车的列车员,她们原本跑长途列车,后来因为年龄大、不听领导指挥或是身材发胖变得不好看了,就调到了这趟绿皮车上。在列车上除了检票、查票、扫垃圾,她们还兼职卖煮花生、煮毛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全民经商,付春风上水的车站每晚都有下了班的铁路职工卖开水、卖包子,列车上的列车员自然不例外。
上班的时候,丁一浩修理火车上的窗户、座椅,下班的时候坐在书桌前面做木雕。光着头的小和尚、抱着孩子的老人、看书的女人,做得像真的一样。做木雕做烦了,丁一浩就坐在单身楼前面的杨树下吹箫。箫声幽咽,偏偏又是夕阳西下,飞鸟归林的傍晚,付春风每每看到,一颗心就要滴出水来。
有一天,是个狂风大作的夏日,付春风的窗户被风刮到地上,她拿着窗户去找丁一浩修理。木匠房里只有丁一浩一个人,他举着一根细木板,眯着眼瞧曲直,浅灰色的工作服撩上去,露出了一段结实的肚皮。付春风看了,心唬得一跳,脸扭到一边,两朵红晕浮上脸颊。
单身宿舍缺少一扇窗户,风雨呼啦啦地吹进来。付春风站在窗前,看到坟地里枝叶飘摇,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从旁边经过,一边骑一边“嗷嗷”大叫。这样的天气,也忘不了学鬼叫吓唬人,不,也许是用这种方式排遣对坟地的恐惧。
丁一浩害怕坟地吗?看上去,丁一浩是不害怕的。坟地中间有一条羊肠小路,丁一浩从单身宿舍出來,总是从羊肠小路通过。他说:“跟死去的人比,我更怕活着的人。”
风雨停下来,丁一浩才将修好的窗户送来。他蹲在窗台上装窗户,付春风坐在单人床上看。快装好的时候,丁一浩一个趔趄,似乎要从窗台上掉下来。付春风伸手扶,不知怎么的,丁一浩倒在了她的床上,他侧对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尔后嘴巴贴了过来。
付春风闻到了芳香的茶叶味道。茉莉花茶,是丁一浩的最爱。因为他的茶水好喝,火车修理厂的职工都去喝他杯里的茶水,他索性将茶叶含在嘴里,喝一口水,晃晃,咽进肚里。
离开的时候,丁一浩坚持着将窗户修完。付春风躺在床上,想看着丁一浩离开。可是,她太疲倦了,下了夜班,又与丁一浩进行了鱼水之欢,实在累得不行。付春风闭上眼睛,努力想睁开的时候,却睡了过去。
凌晨四点,付春风从睡梦中醒来,她是被宿舍外的哭声惊醒的。断断续续的,忽高忽低的,夹杂着男声、女声的哭声,在她耳边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付春风睁开眼睛,看到一层白光铺在新装的窗户上,那是比月光强烈,比日光暗淡的白光,看上去似乎透明,可是却严严实实地遮盖了外边的情景。
付春风爬起身,跪在床头,伸出手,像擦灰尘一样擦着窗玻璃。随着手指、手掌的划动,窗玻璃上的白光“扑啦啦”地飞走了,墨蓝色的天空、星星,还有细细的月牙露了出来。
凌晨四点,天空大地不是黑色的,月光将树木、房屋、道路照得亮堂堂的。付春风的眼睛贴在窗玻璃上,看到十几个戴着白帽、穿着白衣,举着花圈、白旗的人列队向坟地走去。
2
很多年以后,付春风已经叫付春风的时候,想到那天凌晨的情景,内心诧异不已,她认为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人们都是上午或是中午到坟地埋葬骨灰,哪有凌晨三四点去坟地的。如果不是记忆出了问题,那么,那天所见就不是人,而是——鬼。
付春风遇到过鬼。她所在的上水班组,在火车站的站台尽头有两间更衣室,外面的一间是男更衣室,里面的一间是女更衣室。每次独自在女更衣室时,她总会看到一个穿着绿军装,戴着软沿军帽的男人大跨步走进男更衣室。回头看时,却踪迹全无。
是个清亮亮的白天呢。同事说,白日见鬼,付春风肯定活不长。可是付春风一直活了下来,离开铁路,经过二十几年的打拼,成了文化公司的副经理,负责市场开发。
付春风坐在办公桌后面,拿一支签字笔在一张白纸上乱戳。前几天,她遇到一个房地产老总,兴许盖房子盖烦了,老总要开发主题公园,并且是铁路主题公园。
付春风端着酒杯走到房地产老总身边,问他为什么要开发铁路主题公园。她以为老板的回答不外乎三样,一他是铁路子弟,二他曾经是铁路职工,三喜欢火车。这个世界上喜欢火车的人多的是,有人搜集了不计其数的火车模型,有人辞了工作,满世界地追火车。
房地产老总的回答出乎付春风的意料,他说:他喜欢读书,读过一本《过分喧嚣的孤独》,里面有个退休火车司机,在自己家的花园修了一个火车站。车站有站房、信号灯,有道岔、钢轨、火车头和车厢。他把自己的那帮退休老伙计叫到家里,有人负责开火车、有人负责指示信号,有人负责扳道岔,还有人负责维修铁路、管理站房。每天这趟火车都会拉响鸣笛,在退休司机家的花园跑来跑去。这个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想弄一个花园,也有趟火车在花园里跑来跑去。不过,他的花园要跟退休火车司机的花园不一样,退休火车司机的花园没有乘客,他的花园要有各种各样的乘客。
付春风告诉房地产老板,自己曾经在铁路上工作,房地产老板便将这个项目交给了她。他对她充满了没来由的信任,没有像其他听闻她在铁路上工作过的人那样,问她做什么工作,又为什么离开铁路。
为了购买火车头、车厢与钢轨,付春风联系到一个在铁路局工作的人。那人告诉付春风,火车头、车厢与钢轨属于特殊商品,不卖给铁路之外的人,不过有一家物流公司存放了五节抗日战争时期的绿皮车,价格出的合适,他们会卖给她。
铁路局的人将物流公司的地址发给付春风,特意注明:粮店物流园的西侧。
粮店物流园就是付春风住单身宿舍时的粮店村,现在它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物流基地。因为将种粮食的土地租给商人做物流,村里人成为富人,修建别墅的同时,将坟地改造成 “墓园”, 墓园的四周垒起高墙,所有的树木换成了柏树,每座坟墓的前面立着统一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面用金字刻着墓主的名字。
付春风开车来到粮店物流园,打听物流公司的地址,有人指着墓园旁边的柏油路,说:“从这往北,穿过两条铁路线,有一个红墙围起来的院子,就是物流公司。”
柏油路紧贴着墓园的高墙,苍翠的柏树挣扎出围墙,展示着绿得发黑的树冠。墓园门口,两扇黑色的铁制大门紧紧关闭,透过铁栅栏,看得到一条又一条笔直的石板路,路两边一座又一座黑色的墓碑,有的墓碑前面放着菊花与白玉兰。
墓园大门正冲着的地方,是一道老旧的围墙,墙体斑驳,一副没人打理的样子。一幢二屋小楼从围墙内斜斜探出脑袋。是单身宿舍楼。二十几年过去了,它依然立在这里。
3
物流公司的人对付春风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在仓库上方挂了一条横幅,写着:热烈欢迎文化公司领导莅临指导。
付春风连忙摆手,“太过分了。我只是副经理。副的呀,正的都不是,怎么能这么隆重?”
物流公司的经理说:“我们就是这个规格,再大的领导来也是这个接待标准。”
转了一圈,付春风想起来,物流公司所在的地方原来是铁路的一个仓库,放着转向架、轮对、轴承、弹簧等等火车更换下来的配件。因为经常有人翻墙偷盗,铁路安排了保卫看守。有个保卫也住单身宿舍,经常跟付春风讲值夜发生的事情。比如有女人偷东西被抓后,说:“大兄弟,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放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女人正偷着,一见保安过来,马上蹲下身脱裤子。
五节绿皮车在物流公司的东北角。说是绿皮车其实是淡蓝色的,比平常所见的绿皮车短且窄。车厢全是木头做成。公司的人打开车厢,一车厢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在座椅、地板完整。
付春风探头进去,耳朵里面一片嗡嗡的声音。付春风隐隐看到一个男人弯着腰,背对着她坐在靠里的一张坐席上。眨了兩下眼睛又去看时,男人不见了。
“叮当叮当”铁器敲在另一件铁器上的声音从车厢外边传来。
“什么声音?”
“火车修理厂的人在干活。”
噢,火车修理厂还在,那趟绿皮火车依然运营,作为“慢生活”的代表,它成为这座城市的旅游名片。
出了物流公司,沿着一条长满杂草的土路,拐了几个弯就来到火车修理厂。修理厂没有人,四条铁道线静静地躺在地面上,两条铁道线上停着一趟绿皮车,另外两条铁道线空荡荡的,反射着强烈的阳光。付春风记得,从前,这里有一百多名职工,开叉子车的、修电器的、更换火车车轮的、调度指挥的、看澡堂的……当然也有做木匠的,白天晚上,这里总有人走来走去。现在,它空无一人,仿佛一个荒凉的偏僻所在。
叮叮当当的声音又传了出来。付春风循着声音走进一个院子,一个男人拿着一把尖角锤从一间屋里出来,问:“找谁?”
“谁也不找。”付春风说:“我到这里看看。那边,”她抬手指指,“单身宿舍楼,我在里面住过。”
男人疑惑地看着付春风,说:“我怎么不认识你?”
付春风说:“我也不认识你。”
他们分别说了几个铁路职工的名字,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从2005年开始,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火车修理厂一会儿归属这个单位,一会儿归属那个单位,几易其主后从一个车间变成一个只有六名职工的班组。六名职工三班倒,每班有两个人检查停留在线路上的那趟绿皮车。原先的老职工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留下的只有三四个,不过今天都不上班。
原来如此。付春风心里升起淡淡的怅然。
“那你肯定不认识吴芙蓉了。二十几年前,她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南方。”
“吴芙蓉,吴芙蓉。”有人在付春风的身后轻轻叫着。
4
二十多年前,做上水工的时候,付春风叫吴芙蓉。这是父亲给她起的名字。父亲是上世纪60年代的同济大学生,不知为什么大学没毕业就回了村里,虽然后来同济大学承认了他的大学生身份,每月发工资,报销医药费,隔几年便喊他去学校开个会,但是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从谈吐到外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最初吴芙蓉没感觉这个名字特别,70年代出生的女孩,起类似名字的多的是,王冬梅、高玉兰、赵杏芳、李春花……她以为自己的名字就是常见的芙蓉花、木芙蓉,色彩艳丽而招摇的那种。
听到有人叫她,付春风转过身来,吃惊地张大嘴巴,是丁一浩站在身后。二十几年过去,丁一浩似乎没有变样,还穿着从前的浅灰色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把木工常用的刨子。
“你还认得我?”付春风知道自己的变化。与二十年前比,她足足胖了四十斤,长发变成了短发,小蛮腰变成了水桶腰,好在,一直做与文化相关的工作,身上堆着淡淡的书卷气,看上去与普通中年妇女有所区别。
“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还能见到你。”丁一浩说,眼睛里像嵌了一块玻璃,亮晶晶的。付春风怕他失态,转头看物流公司的经理与拿手锤的男人。物流公司的经理正在跟拿手锤的男人说话,“这趟绿皮车卖不卖?现在还有谁坐绿皮车?”
“怎么没有?坐车的人多得很。爬山的驴友、观光的游客。这趟车都上报纸、电视了。现在的人你还不懂吗?东西越旧越老越值钱。”
丁一浩用手指指单身宿舍楼,“走了后,再没回来吧?过去看看。”
“现在还有人住吗?”
“不是有我吗?”
“不是有我吗?”听到这样的话,付春风万分难过起来。她想起去年开发一个德式建筑群的情景。那些一百多年的老房子几乎塌了一半,没塌的一半里住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有老伴的,儿女不管的,精神失常,一辈子没有结婚,没儿没女的。那个精神失常的男人将付春風当成政府领导,跟她告状:“隔壁的老太太天天在草丛里拉屎,弄得我没法吃饭。”从年轻时起,男人就在室外将饭碗举到头顶吃饭。他说,唯有如此,才没有人往他饭碗里投毒。
跟在丁一浩身后,付春风来到单身宿舍楼。如她所想,单身宿舍楼里住的人寥寥无几。一楼只住着丁一浩,二楼住着一对老夫妻。好在,楼道打扫得干净,走廊北边窗户全都装着玻璃。
二楼的老夫妻打开走廊的窗户,探头看付春风。付春风冲他们笑笑,他们慌忙缩回了脑袋。
丁一浩的房间洁净得不像话,墙面白得仿佛刚刚拆开封的A4白纸,水泥地面擦得如同包浆的玉石。桌子、椅子因为用得久了,像镜面一样光滑。那些木雕,光着头的小和尚、抱着孩子的老人、看书的女人依次摆在桌子上,跟二十几年前一模一样。付春风站在窗前向外看,窗外是老旧的红砖垒成的围墙,上面全是尘土和杂草。围墙遮住了视线,看不到外面的墓园。
“吴芙蓉,吴芙蓉。”付春风转过身,看到丁一浩端着一只浅口瓷盆站在身后。瓷盆还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盆底画着荷花与金鱼,半盆清水上浮着两朵荷花,一朵白荷花,一朵粉荷花。
第一次在丁一浩宿舍看荷花,丁一浩吟了两句诗:“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他说:“你知道吗?芙蓉是荷花的别称。你的父亲是同济大学的学生,他怎肯用木芙蓉形容你。你就是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付春风将瓷盆接过来,放到了桌子上。盆里的清水轻轻晃动,白荷花与粉荷花像在风中一样轻轻摇摆。
丁一浩的身子贴过来,手环到她的腰上。“吴芙蓉,芙蓉,”他说:“这些年你去了哪里?你真的跟一个男人去了南方吗?芙蓉,你可知道,我天天想你,你想我吗?”
辞职,下海,去南方,是当时所有梦想有追求有勇气的人的时髦行为。火车修理厂与付春风所在的上水班组都有人辞职做生意。政府官员下海经商的比比皆是。那个时候,似乎机会遍地是,几乎所有人都有经济头脑,所有人都可以在商海里扑腾,从而收获一笔财富。
付春风躬起后背,想摆脱丁一浩的拥抱,可是她不仅没有摆脱丁一浩,反而更紧地与他贴在了一起。久违了的,热乎乎的男人气息从丁一浩的身上传递进她的每一个毛孔,她感觉到了丁一浩的膨胀与壮大。
从单身宿舍走的时候,她跟所有人说她去南方,她爱上一个男人,他将带着她从上水的火车站出发,到深圳到珠海开始新的生活。为了显示她即将成为南方人的样子,她特意穿了花衬衣,带上一条假的黄金项链。
没有人为她抛弃铁路工作感到惋惜,也没有人为她抛弃丁一浩感到不应该。在即将到来的财富面前,平淡的工作与做工人的男友如同小蚂蚁在巨大的车轮面前不堪一击。
丁一浩没有挽留她,只是坐在杨树下吹箫,一支曲子又一支曲子,直到把太阳吹得血红,心碎了一般坠到地平线下面,丁一浩站起身,将箫摔得粉碎。
5
付春风抓起毛巾被盖在身上。她实在没有勇气在丁一浩面前袒露自己的身体。乳房下垂,小腹隆起,大腿上堆满赘肉。她的身体很忠实地出卖了自己的年龄。丁一浩却不一样,他双手枕在头下面,两腿伸直,身材看上去跟二十多年前没有两样。
这些年是怎么过的?通常旧情人相见都会问这样的问题。丁一浩却没有问。他断断续续地跟付春风讲一些事情。单身宿舍楼外的坟地,本来铁路想买来修建大型修理厂,可是价格没跟粮店村谈妥,搁置下来后,铁路开始改革,再没有人提修建大型修理厂的事情。
“火车都提速了,你上水的车站取消了上水业务,更衣室改成了派出所。”
更衣室改成派出所,那个穿绿军装的鬼不敢再去了吧。
丁一浩转过身,抚摸着付春风的后背,他说:“你知道吗?二十多年前,你的房间总是传来奇怪的声音。啪啪啪,小圆珠不断地掉到地板上的声音。唰唰唰,双脚在地板上擦过的声音。越是半夜时分,声音越响。那个时候,咱俩还没好啊。那个时候,我就想,楼上的这个姑娘,不睡觉吗?深更半夜的,做什么呢?”
付春风不记得没跟丁一浩好的时候都做了什么,只记得跟丁一浩好了之后,他们像要来不及似的找准一切机会欢爱。起初在单身宿舍内,后来单身宿舍又安排进了别人,两人就来到室外。深夜时分,停在铁道线上的绿皮车;没有车辆通行的桥洞;坟地旁边的小饭馆。白天的小饭馆经常有一男一女坐在里面吃饭,男的将手放到女的大腿上一下一下抚摸。晚上,小饭馆的主人锁闭房门回市里睡觉,丁一浩就带她到饭馆的后面欢爱。前面是黑黝黝的坟地,背后是坚硬的可以依靠的墙壁。
可是,有一天,她在丁一浩的冲撞中突然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女人从坟地里钻了出来。那个女人个头矮小,衣衫破烂,背着一个大袋子,像遇见鬼一样,满脸惊恐地看着他们。
“我没有去南方。”付春风说,“也没有爱上别的男人,我一直留在这个城市,现在,是一家文化公司的副经理。”
“这不重要。”丁一浩看着她,“这不重要。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在哪里,你都是我爱的女人。”
付春风将头埋在丁一浩的腋窝里。浑浊的男人的气息熏得她的眼睛流出泪来。“我爱你”“你是我深爱的女人”她听到很多男人跟她说这样的话。她踩着这些男人的话,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她有了可以在高楼里看青山,看夕阳,看像玉带一样绕了城市一圈的护城河的生活。她再没有遇到鬼,所有的爱都是在宽大柔软的床上做的,没有人突然从某个地方钻出来,像看鬼一样地看着他们。
可是,最近几年,应该有五年了吧,没有男人再跟她说“我爱你”,手机里暧昧的短信,挑逗的语言几乎消失不见。男人在她面前突然正经起来,有一次,在公司的办公室,她遇到曾经挑逗她的一个男人,那个男人话都没跟她讲,逃避什么似的转头就走。付春风知道她老了,有白头发了,并且丑了,男人不肯在她身上动心思,所以都变得正经起来了。就连她的丈夫,都几年不碰她的身子了。
付春风并没有觉得这种变化不好。坐在办公室里,她经常回想过去的时光,她感觉过去的每一天每一步里都躺着自己的尸体。她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老年后,信了佛或是信了基督,他们试图依靠宗教洗刷罪恶,救赎自己。付春风没有信仰宗教,她只是努力地做到最好,認真工作,谨慎做人,爱戴下属,她甚至买了很多提高品德修养的书读,她照着书里的描述做,在脸上、身上涂上一层又一层膜,最后这些膜变成了坚硬的外壳。所有人看她,都觉得她是个有着良好出身,受过良好教育,在父辈的庇护下,顺风顺水过上好生活的人,所有人看她都觉得她的过去充满阳光、鲜花,还有掌声。
只是,夜深人静的夜候,每个月的生理期即将来临的几天,她会想起丁一浩。她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去掉所有伪饰,赤裸裸的真实的自己。可是,第二天,坐在办公室里,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到脸上,她召集下属开会时,又觉得那个自己不是真实的自己。
“哗啦哗啦”,门口响起钥匙晃动的声音。付春风一下子坐起来。她应该想到丁一浩有妻子的。二十几年过去,丁一浩怎么可能还是单身。他的房间里应该有女人的痕迹。脸盆架上挂着两条毛巾,刷牙杯里放着两只牙刷,床底下有一张粉红色的女式拖鞋。丁一浩似乎睡着了,双手枕在胳膊下面一动不动。
房间的门打开了,夜色一下子透了进来。不知什么时候,天完全黑下来。 一个比付春风年轻得许多的女人站在门口。她看着付春风,看着丁一浩,突然大叫一声。
仿佛潮水涌来一般,门口一下子聚集了很多脑袋。这个单身楼不是只有丁一浩与楼上的老夫妻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的人。他们挤在门口,对着付春风与丁一浩指来指去,嘴里嚷来嚷去。
丁一浩从床上跳起来,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冲到房门口,啪一声,将房门关闭了。门口爆发出年轻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房门再一次被打开的时候,付春风与丁一浩已经穿好衣服。年轻女人冲过来,抓乱了付春风的头发,撕破了付春风的衣服。丁一浩抓住女人的手,将女人压到床上,付春风揪着衣服领子夺门而逃。
火车修理厂的灯光亮了起来。那趟奔跑了一天的绿皮车慢腾腾地进站了。“咣当咣当”车轮行驶在钢轨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呜”的一声,车头从付春风身边经过时,发出一声长鸣。
付春风站住了,头脑随即清醒过来。她退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低头看自己,撕破的衣服,踩坏的鞋子,裤子上粘满黄色的污物,是别人扔过来的屎吧?
她为什么没能抵制住丁一浩的诱惑?以至于丢这么大的人,受这么大的侮辱。爱情或是情欲就这样重要吗?
6
隔三分钟,付春风就要看一下手机,她担心丁一浩或是丁一浩的妻子打来电话。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丁一浩与他妻子始终没有打来电话。付春风反倒感到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打电话?丁一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平息了事情?丁一浩的妻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原谅了她?
打电话来的是物流公司经理,问付春风是否购买那五节绿皮火车。付春风的心跳得厉害,这个男人看到了她在单身宿舍的狼狈相吗?他是以此要挟她购买绿皮火车?如果不买,他会到文化公司宣扬她的丑事吗?
握着话筒,付春风的心头千万个念头闪过,她轻声询问绿皮火车的价格。经理说的价格和两个星期前一样,付春风说:“我想想,我想想。”
付春风给房地产老总打电话,讲明:可以跑的火车买不到,只能买到报废的绿皮车。她盼望房地产老总打消做铁路主题公园的念头,这样,她就可以将物流公司经理的要挟解释成“买卖不成,反目成仇”。可是,房地产老总说:“报废的绿皮车也要,我们可以做成铁路主题的文化餐厅。”
又一次,付春风来到物流公司。物流公司依然在仓库上方挂了一条横幅,写着:热烈欢迎文化公司领导莅临指导。付春风仰头看着,觉得条幅的底色太红,写字的白色亮得刺眼,她想叫公司的人将它拿下来,可是又不知道找个什么样的理由。
五节绿皮车厢被清理出来,地板、座椅、窗户擦得干干净净,散发着好闻的木头味道。付春风走进去,车厢里没了那种“嗡嗡”的声响,阳光从打开的窗户照进来,到处亮堂堂的,没有一点阴影,也没有男人弯着腰,背对着她坐在坐席上。
“这些车厢可以作为古董保存。为什么舍得卖掉?”
物流公司的经理告诉付春风,他们是做钢铁产品物流的,因为钢厂不景气,没有业务可做,造成资金链断裂,经营遇到困难。付春风给的购车费,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所以,”经理用热切的目光看着付春风,“你就是我们的救命菩萨。”
救命菩萨?付春风脸红了,这个男人没看到她在单身宿舍的狼狈相呀。可是看到了又怎么样,如果影响了他的生意,他可以看到。如果不影响他的生意,他可以不看到。人们看重的是利益而不是道德评判。
付春风叹口气,说:“签合同吧。”
“叮当叮当”铁器敲打另一件铁器的声音从车厢外传来。
付春风走出绿皮火车,透过物流公司的围墙,看到西边的天空升起一团灰雾。
物流公司的经理说:“那里有座闲置已久的单身宿舍楼。粮店村买了下来,要建成墓地。现在筑坟的规格越来越高,原来的墓园不够用了。粮店村的人正在拆楼呢。”
“单身宿舍?闲置已久?那里不是有人住吗?”
物流公司经理不说话,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付春风。
这个时候,丁一浩年轻的妻子从绿皮火车后面转了出来,她手里拈着一朵白色的荷花,似笑非笑地看着付春风。她将荷花举到鼻子下闻了闻,然后一手拈着花柄,一手一下一下地撕着花瓣。
白色的,娇嫩的,如同玉片雕成的荷花瓣落了下来。
一层又一层的冷气从脚底往上升,很快笼罩了付春风的全身。付春风只觉得脸上有东西被揭了下来,一层又一层被硬生生地揭了下来,她脸皮底下的筋、血、肉,骨头马上就要露出来了。那个剥去了一切掩盖与修饰的不堪一击的她马上就要露出来……付春风大叫一声,捂住脸,昏了过去。
郝炜华,1970年代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1993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北京文学》 《清明》《山花》《中国铁路文艺》《人民铁道》等期刊、报纸发表中短篇小说1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古琴》。作品多次入选年度选本、被 《小说选刊》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