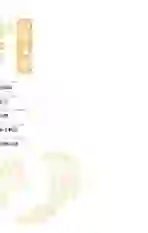吴伟峰诗作
2017-03-16吴伟峰
乡村之夜
房间的顶灯是惨白的,
墙壁的电视机是漆黑的。
一具床上的肉体,漂浮在
一片细碎的虫鸣中……
这是一个人的乡村之夜,
怜悯和救赎都已经远离,
孤独,重新回到指尖。
以最柔软的手势触摸自己,
仿佛在爱,又仿佛在背弃。
感觉到:窗外的青山在悄悄移动,
风已经很凉了,黑夜里有两个人在说话。
听得出,是两个路人
在说话。他们都说要回家。
色身
这是自性的天地。犹如宇宙中
明灭的火光和尘埃中一朵花的涅槃,
从来都有秘密的法则。是谁?
以空空的妙手,描画出这尘世的美景。
柔软的,温热的,精妙的祭坛
——带着黄金的重量和种子里的闪电,
与草木一起繁盛。我们青春的肉体——
勃动着自成一体的弹性与张力,
缘起的原力和寂灭的因果一应俱足。
我们,深陷于泥土的心灵——
被我们的肉体摘除。那裂隙中的哀鸣
发出空洞的回响,满头的秀发如落叶,
把我们深埋在身体的秋风里。我们听得见
自己的呻吟:就在血液,高潮,疲惫
和疼痛之间。犹如月亮引发的潮汐,将
汪洋
之中的一叶小舟,高悬于虚空之上……
我们,受制于这强大的自性之力。我们
屈服于欲望的布施,旋转着陷入——
生命的眩晕和死亡的幻觉。枯萎的词语
开始书写我们苦难的传奇,我们双手合掌
——让血液从左手流到右手。仿佛
在暗夜里,自己摩挲着自己的肚脐。直至
坚实的小腹里又鼓荡起潮湿的季风……
每一具肉体都是一个传奇。从到来
到离去,“多么奇妙!”我们说。
我们活在无声无息的时间里,但是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重构时间——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那闪电般击穿肉体的
心念,赋予肉体温度、颤动,以及喜悦
和忧伤。“多么奇妙!”我们说——
色。声。香。味。触。法。我们俱足。
那些神秘的曲线勾勒的影子,月光下
的睡莲,晃动着银瓶中的琼浆——
美得让我们哭泣。我们用温暖的泪水浇
灌着
娑婆世界的花花草草,等待春天的嘴唇,
落在饱满的乳峰上。那些修长的手指
总是不甘寂寞,在玫瑰的腰间滑来滑
去……
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我们贪婪地品尝着
——爱神的舌尖那最后一滴甜蜜。
而当陈年的疤痕说出我们的伤痛——
曾经流失的鲜血,又瞬间回到我们心间。
我们听到了骨头开裂的声音,一如来的
时候
我们在子宫中花一样绽放。我们明
白——
终点就是起点。当我们双手合掌,天地
就是圆满的。掌纹里,藏匿着生命的密语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我们手中的念珠捏得更紧,就像捏住
自己的身体。仿佛一不小心它就会
滑落深渊,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总是
充满恐惧,恐惧那不可预期的消灭。
但总有一个刹那,死亡会把我们捉住
——它捉住我们的色身,让尘世的传奇
止息。
我们头顶那片星空迅速飞离,而只有寂静
——是永恒的。
隔山的那头牛
我突然想起我的师父张三丰,
他传授我的武功,我已
还给他三分之二了。老人家
在云端是否還惦记着我这个徒儿?
他曾说太极这玩意儿只是
你的一个念头。别看好像是
老牛拖破车,其实是快如闪电无人敌。
我喜欢师父这老头儿的那股
邋遢劲,但他说起话来一点也不含糊。
那天夜里师父密授我隔山打牛的功夫,
不想被师姐小蝶儿偷偷瞧见,
从此小蝶儿就恨我入骨也爱我入骨。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好想我师父张三丰,
也想我师姐小蝶儿。说实话我学会了
这手绝招儿,却从没有打过牛。
师父说太极这玩意儿只是
你的一个念头。自从师姐那天夜里
露出了会反光的胸,我就不知道
牛是什么样子的了。那时我只有十六岁,
除了太极还真不知道世界有这么美好。
我想着师姐胸前的两颗仙丹,武功
就会徒增两倍。终于有一天我元神出窍,
神游太虚。但没有人知道我的寂寞和悲伤。
其实我一直在等待:隔山的那头牛。
那么多年过去了,纵然我神功盖世,
师姐你不牵来那头牛,世上的一切,
对于我都毫无意义。
吴伟峰,浙江象山石浦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原则诗群主要发起人之一,新闻媒体文化版编辑。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诗,尔后辍笔,2014年重拾诗笔。著有个人诗文集《自珍集》,编有纪实图文集《两岸石浦人》、旅游散文集《山风海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