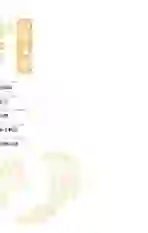村庄的黄昏
2017-03-16周华诚
1
父亲把屋檐下的打稻机搬出来:这手续颇有些复杂,先是去除攀结的蛛网,然后卸去覆盖其上用以蔽雨的石棉瓦及草束,解开缚角的绳子,再缓缓放平。一身的灰,不管是父亲,还是打稻机。
那是一架历史悠久的机器,半个多小时后,父亲用布擦去厚厚的灰尘,灰尘下面的字迹便会浮现出来:前面是“颗粒归仓”,左面是“1986年”,后面是“五谷丰登”,右面是“周全仔办”。这些都是青年农民周全仔的笔迹,当年他从公社农机厂用平板车拉出这架崭新的打稻机,十几里路花了他整整半天时间才走到家——路不是很远,打稻机真的太重。那是一个大家什,那时整个生产队30多户只有三架打稻机。
农机厂厂长叫做傅克昌。父亲一边用水擦洗打稻机上的灰一边和我这样说。28年前的父亲咬牙买下这台打稻机,在整个村庄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百五十元的价格还是有人情的因素在里面:厂长傅克昌和父亲关系不错,那时父亲是乡电工,认识的人不少。厂长专门用杉木板做的打稻机谷仓,用杂木做,不仅死重,而且不耐用。父亲为什么肯花150元钱置办一台打稻机。因为种田季节不等人。生产队的打稻机不够用,一家一户轮着借一天都不行,每年总有几户落在了后面。
四亩多田每年要交400多斤公粮,1400多斤余粮。公粮是一定要交的,你不交,当兵的人吃什么,公家人吃什么。余粮也是一定要交的,国家粮食紧张,你不交粮,人家就要到你家里去搬。交余粮,国家是给钱的:100斤稻谷9块5。卖1000斤余粮,国家也不过是给你95元——卖2000斤稻谷,换不来一台打稻机。那时猪肉是8角一斤,你想想看。
有了打稻機的青年农民周全仔,在村庄里成了吃香的人,总是有人来跟他借打稻机。借打稻机的人排着队上门,他们商量好了各自收割的时间和插秧的时间。他们把时间用得密不透风,当然也滴水不漏。
现在父亲把屋檐下的打稻机搬出来。因为再过一天,水稻就要收割了。
打稻机后面有两根突出的木头棒子就像打稻机的尾巴。我小时候跟这两个棒子有着深厚的交情:两个大人在前面拉打稻机,我们小孩在后面推,满仓的谷子沉沉的,不推它,打稻机自己不会走的。小孩有多少力气自是不能知道,但是你推了那也是在有劲一处使。几个人一起使劲让打稻机在稻田里前行,这样的时候应该有风在空旷的田野里吹起来,那是很快乐的时候。
收割稻谷并不轻松,跟插秧比起来,割稻简直是一件痛苦的差事。它是强体力劳动。同时稻叶会在手臂上割出浅浅的血痕,不痛,但是很痒。长时间的弯腰挥镰割稻,也使人感到疲惫至极。一边脚踩打稻机,一边手捧稻把脱粒更是一件技术活。奔前跑后“落窝怕”(方言,意思是“搂稻把”)则是孩子们的事,那件农活乍看起来颇为轻松,实则十分累人。所以,在这样繁重而辛苦的劳动中,推打稻机,都成为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推拉,用力,滑行,停落——这是繁重的割稻劳作中的调剂:腰可以直一直,头可以抬一抬,看一眼远方,感受一下风。
好了,这跟打稻机的尾巴有什么关系。
关系就是:在打稻机快速滑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地站在那个棒子上,随着打稻机一起滑行。
冒着被呵斥的风险,偷偷地站上去,三秒钟,或者五秒钟,飞翔。
在父亲弯腰为老旧的打稻机上润滑油的时候,我弯腰查看那两根尾巴棒子:那上面还可以看到脚丫子泥印。那三秒钟或者五秒钟,真的很快乐。比你现在玩上一整天的游戏还要快乐。
1979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年份,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中美正式建交,很快邓小平访美,那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那之后,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还是在那一年,国家领导人万里到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肯定了那里的农民顶着掉脑袋风险尝试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那些遥远的事件如同一只只蝴蝶穿过电脑屏幕飞抵眼前。时隔多年了。那些缥缈而宏大的叙事离我实在太远,它们并不存在于我的真实记忆当中。对于我那偏居浙西农村的父亲来说,那一年同样深具意义。与那些遗留在历史上的年度大事相比,在他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事件是关于自己的小事——在那一年的9月份,他参加了工作,成为一个叫做“五联村”的中国最基层的行政村里的一名电工。
父亲一辈子都在朝着一个目标努力:脱离农民身份。我现在这样说来恐怕不太准确,对父亲也是不公平的,但现实是,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没有人会认为做一个农民值得自豪。哪怕父亲在“当农民”这件事上做得很成功,那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
在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父亲向我讲述那些陈年旧事,我打开电脑,记录了父亲说的那些话。
父亲周全仔,学历高中。他毕业的时候,已然成为村庄里的佼佼者,因为全村1300多口人,总共只出了三个高中生(直到后来才又增加了两个)。
于是父亲担任了生产队的总会计,兼全村的会计。会计干什么,就是给生产队记账。队长说,今天大家割红花草。那么大家就一起割红花草。割了要称。称了要记。父亲在生产队的账本上用蘸水钢笔写下清晰的蓝色字迹:某月某日割红花草,多少人,多少斤。
村口有一棵老柿树,无人知道那棵柿树长了多少年,只知道每年的深秋,满树火红的柿子会成为村庄里最耀眼的风景。在霜降之前,这棵柿子树上的果实会被村里的男人们统一在某天采摘。男人们纷纷爬上高高的枝桠,一竹篮一竹篮的柿子被吊下来。会计拿着账本站在柿子边上,一担担过秤,一担担记录在案:一共摘下12担,这担200斤,那担180。总共2000斤。整个生产队是130口人,不论老小,一个人头分得十几斤柿子,一家一户的人端着脸盆,拿着柳筐在等着分柿子。
村会计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岗位。一个务必要知识分子才能担当的工作。会计很忙,几乎跟生产队长一样忙。每天晚上生产队长要为每个队员安排工作,明天张三干吗,挑粪;李四干吗,挖渠;王二麻子干吗,走30里路去集镇抓两头猪崽。一日一日地排。整个生产队的日子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生产队的账簿上。挑了粪,挖了渠,抓了猪崽,摘了柿子,割了红花草,每天晚上大伙都会集中起来,由会计记下他们的工分,然后大家纷纷在账簿上严肃认真地戳上红指印。
1979年,村里有了电。有了电,电灯泡亮起来。有了电,还需要找个电工,收收电费,修修线路。这是一个比当会计更有前途的事业。我大字不识一箩的爷爷是村里的老党员,村支部开会的时候,他深思熟虑地提出,这个电工让我崽来当行不行。支书向大家征求意见,经过党员们的讨论,这个提议得以通过。
毕竟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文化程度高,他写的稿子还在广播里播出。他完全有能力管这个电。这一点毋庸置疑。后来果然,父亲又通过考核,成了乡一级的电管员。每个月的工资是27元5角。作为乡电工,父亲每个月都要走很多路,到每个村去,把村电工手上抄的电表数字核对一遍,再把电费一点一滴地收上来,统一上缴。父亲是十里八乡颇受欢迎的人:谁家的灯泡不亮了,找他。谁家的电灯拉绳断了,也是找他。谁家要拉根电线,安个灯泡,还是找他——也没见谁要安别的东西,灯泡,已然是最高级的家用电器。黑白电视机,还要十多年以后,才会在我们村里出现。
但父亲依然是一个农民。忙完了与电相关的工作,他还是要回到家里下地,一件接一件的庄稼活儿摊开在土地上等着他和母亲去完成。因为与电相关的工作太多,常常田里的水稻已经黄透等待收割,耕田佬安排翻耕土地的日程已经逼紧,绿油油的秧苗又迫在眉睫赶着插下,而父亲还得抛下自家田间的事儿往外赶,母亲不得不说一些牢骚话。但那也没有办法。年少的我学着大人的样子站在打稻机前,一只脚踩蹬着打稻机,两只手捧着一把稻穗,稻桶里谷粒纷飞,我早已汗流浃背。那时的我只比打稻机高了那么一点点。在我的边上站着母亲。她要用更大的力气踩踏打稻机,以减轻我的负担。弟弟则举着稻把在泥巴里奔走“落窩怕”,一次次把沉沉的稻穗举过头顶递给我们。
辽阔的稻田和做不到头的活计令人绝望。
更多的时候,我们和父亲母亲一起躬身在田间。四季中与稻田相关的劳动周而复始。烈日与汗水就这样裹挟了我们的童年。
但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让我们重新回到一九七九年。那一年的一月和二月,一些后来叫做周杰伦、佟大为、邓超、章子怡的人相继出生。那一年的农历九月,我出生。
我坐在父亲身后。摩托车突突地响着。寒风凛冽。
小时候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父亲就这样驮着我们。我已经不记得多久没在父亲的身后这样坐着了。
路边的人,看到父亲,会和父亲打招呼。第一句,去哪儿啊?第二句,这是你崽啊?
父亲单脚踮地,说,是哎。
你崽这么大了啊。很多年没有看见了,完全认不着了啊。
父亲说,是啊。一直在外面读书,你们是认不着了。
他们又问,现在是在杭州上班么?
父亲说,是啊。
我就想起,好像童年时候,父亲把我们带出去做客、拜年的情形。也是这样认人,叫这个叔叔,叫那个伯伯。而现在,那些叔叔伯伯,面孔依旧是陌生的。村庄里全部都是陌生面孔了。
我三十多岁,离开村庄已经多年。乡村风景,及小时候熟悉的草木,已然变了模样。村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更是早变了模样。
过了一会儿,父亲扭头问我说,刚才,路上有个人骑车过去,是你小学同学。你不认得了么?
我说,哪个?
父亲说了一个名字。我绞尽脑汁,没有想起来。
2
这是前年冬天的事,父亲带着我去寻访村庄里最后一位耕田佬。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种田这件事感兴趣的,父亲其实并不清楚。小时候我们在田间挥汗如雨,父亲总是对我们说,你看,你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读书,好好读书考上学校,就能不当农民了,不受这个苦了。
后来我就真的考上了学校。那是一所中专学校。我的成绩不错,在全县排名第一,好好为父亲挣足了面子,至于我自己,当然,我也倍觉荣光,同时深感欣慰。那年暑假我们家请了几桌大酒,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被父亲请到家,一一敬酒表示感谢。那时候中专比高中录取分数线还高,考上了中专就要转户粮关系,我的户口被拨出去,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居民户”。
那年暑假,很显然,父母都尽量不让我下田了。
现在这个儿子突然对种田有了兴趣,父亲不甚理解,但是他很尊重儿子的兴趣。他用摩托车载着我去找耕田佬,听耕田佬聊聊耕田的事儿。儿子喜欢写东西,这不是什么坏事情。
那个耕田佬叫马岳云。
马岳云的父亲叫马如德,已经八十岁。在分田到户之前,马如德曾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掌管着村里的畜牧场。畜牧场里有几十头牛。马岳云从十多岁开始,成了放牛倌。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岳云当放牛倌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谁让他的父亲是生产队长呢,这一点权力总是有的。
马岳云就这样跟牛处了一辈子。
牛群,漫山遍野散落的牛群。马岳云与牛朝夕相处,没人比他更熟悉牛脾气了。现在他已经五十五岁,有着一张因长年劳作而被晒得黧黑的面孔。他脸上的皱纹也已很深。我给他递烟。这个中年人是现今村庄里唯一还在用牛耕田的人,在我看来简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他向我抱怨着他的工作没有价值,太辛苦,又赚不到钱,现在连田都没有人种了,还要犁田佬做什么。
他说的是实情。现在村庄里确实连田都快没有人种了。
这二十年,差不多全村的壮年劳力,都进城去打工了,一半以上的农田被抛荒。那些尚未抛荒的农田,主要是靠老人在耕种。
年轻人呢,村里哪里还有年轻人。
所以水稻田在快速地萎缩。那些原先种植两季的水稻,现在仅种一季;原先除了种水稻,还要在水稻收割后种上小麦、油菜、萝卜、紫云英,水田里一年四季变换着不同的颜色,鲜艳夺目,内容丰富,现在很多时候只生长一种植物:野草。
还有些水稻田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承包给农业大户。种蔬菜、苗木、养鱼。承包期,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一亩田一年的租金,100元到300元不等。拿到这笔钱,没有了田的田主人就像城里人一样去买大米吃了。不种田的日子,农民们纷纷去县城打工,去建筑工地上做临时工。出卖力气挑沙子,一天能挣130元,而靠种田,仅能维持温饱。想从土里刨出钱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想通了的农民,就这样离开了土地。
村里原先有六七十头耕牛,耕田佬穿着蓑衣行走在烟雨朦胧的田埂上。那是春天。是我从课本里知道的春天,是从唐诗里知道的春天,但更多时候,是我从村庄的耕田佬身上看到的春天。
现在耕田佬像约好了一样从田埂上消失了。只剩下一个马岳云,又疲惫又艰辛,赶着一头牛,扛着一架犁,走得有气无力,走得自信心相当不足。
如果不是家里那个淘气的儿子,他也早就从田埂上离开了。哪怕是去打工,也比耕田要强得多。
他说的那个淘气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经常跑出去,用石头扔人家的瓦背,或者躲在哪个山头的角落里淋雨,或是爬上一棵大树,从早晨一直待到黄昏,直到他的父亲像玩捉迷藏一样把他从枝繁叶茂的藏身之处找到。
我和父亲还有马岳云一起,在村庄的黄昏里坐着,目光望向屋外的田野。我的父亲给另一位父亲递烟。打火机点着了烟,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3
某某死了。
母亲说了一个什么名字,我没听清。我离开家乡读书工作,一年中回村的时间屈指可数,村人面孔依稀有些记忆,但能叫上名字的则实在不多了。母亲又说了一遍,那名字好像听过,但想不起人是怎样。母亲又说,那年夏天,他的孙女被汽车轧掉了一只手臂——你记得不?
我一下子记起来——他,怎么突然死了?
喝农药死的。喝了两瓶草甘磷,还有一瓶开了,没喝下去,喉咙和舌头都被药水烧焦了……真惨啊。
我们村口的供销店,是村中闲散人员的集聚地,每天从早到晚人声鼎沸,无它,就是赌博。这些生活拮据、油水贫瘠的乡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会驱使他们从衣缝角落里抠出令他们几乎难以承受的金钱额度,轻易地扔到赌桌上。直到输光了一个月甚至半年的辛苦劳作之后,他们才会灰头土脸地离开。
但他们不会吸取教训。等到口袋中好不容易又有一点闲钱的时候,他们照样会把钱扔到赌桌上来。这足以使我误认为,这些人在生活中的抗击打能力是超强的,似乎命运的任何灾难都无法击垮他们。
那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妇,每天都会带着两岁的孙女去代销店里玩,实际上,他们是去观战赌局。那里的赌局风云,简直就是乡村平庸日子里的好莱坞大片,刺激着每个人的眼球和神经,同时也像吸食鸦片,叫人欲罢不能。即便只是观战,也不例外。
就在一场扣人心弦的赌局进入高潮的时刻,悲剧发生了,一辆满载的货车从公路上驶过,而独自玩耍的两岁小女孩踉踉跄跄地迈向了公路中间。
小女孩在她的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失去了她的右臂。
从赌局中回过神来的祖父母发了疯一样冲出门外,但已经无济于事,他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剩余人生里的所有欢乐,以及儿子、媳妇一家人——他们把受伤的女儿带走了,再不愿回到这个家;也许他们不会恨他们,但无法原谅他们,这个家庭再也无法回到虽然清贫但仍显和睦的昨天了。
我远远地看见那个老男人。那个身材高大、胡子拉碴的人佝着身子坐在阴影里,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槁骸。
他说,他已经无法再补偿给那么小的人儿一只手臂,如果可以,他宁愿把自己的给她。
在那之后的几年,我都没有再见过他。当然我知道,这个男人还在村子的角落里活着。我以为时间会埋葬掉曾经的悲伤,一如那些输个精光却仍然会从头再来的赌徒们,生活的打击不过如此——逆来顺受惯了的农民,从来自有一种思维去解释和接纳它,并且把它作为自己命运里理所应当的一部分。
但终于,在事隔多年以后,命运还是一并清算了他。
村民传出的消息,说他在临死前已经安排好一切。他年纪大了,健康每况愈下,春天准备好的五斤谷种,都无力播种到田间了。出事前的几天,他的老婆还跟他吵了一架,据说她经常骂人。两年前他去一家工厂守大门,至今存下两万块钱,一分都没用过,是交给儿子的,算是对小孙女的补偿。
然后他洗了个澡,去曾经是赌场的代销店买了五瓶草甘磷——那是一种效果显著的除草剂。喝下去之前,他还给远嫁的女儿打了最后一通电话,但女儿并没有听出父亲的话外之音。
那是一个性格很硬的人——村人说,他决定了的事,没有人可以拦得住他。他一定是觉得这个世界,已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了吧。活了一辈子,活成这样,不如死了算了。
他死了以后,他养的一条狗,在遗体前哭了两天,呜咽不绝,赶都赶不走。因为这条狗,前去看望者没有不落泪的。
我怎么会想起这么一个悲伤的故事来呢?我不知道。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我还是会想起。
就好像,那么一个决绝的背影,石头一样嵌在村庄的道路上。细细看,那是一个沉默的、坚忍的、村庄里所有的男人们的背影。有时候,我几乎会觉得村庄里所有的男人们的背影里都有这么一种共通的东西,固执而内向,说一就不二。
4
我的小舅从前是一个木匠。当他爬上山的时候,他会对着一棵树发呆。有时,他还会闭上一只眼睛,瞄一瞄那棵树是不是足够直挺。我知道这是一个木匠的职业习惯,他看见一棵树的时候,其实在心中出现的是一个板凳,或是一个五斗柜。
小舅15岁拜师学艺,成功地从一个下田的农民转型成一个操持手艺的木匠。他做了许多桌子、椅子、大衣橱、床、粮仓、风车、长凳、短凳、高凳、矮凳、骨牌凳、扁担、砧板、锅盖、碗橱架、脸盆架。他的成果遍布十里八乡的人家。人們结婚的时候,他做的家具被人们排着长队抬来抬去,上面贴着红纸,喜气洋洋。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乡下人结婚,渐渐地不时兴打家具了。他们直接去县城的家具城置买。那里的家具,式样更好看——都是三合板钉成的;价钱便宜,还特别轻巧,不像自家打的木头家具那么笨重,打家具费时费力费木头——那个时候的审美,就是这样的。就像很多人家里,会摆上几盆买来的塑料花,鲜鲜艳艳,四季不败,而门前小径边的野花开得葱茏,四时常新,却并没有人去采来插在什么瓶子里。
小舅渐渐地不那么吃香了。人们不再需要一个木匠。小舅于是进城去打工,他成了中国最早一批“打工仔”中的一员:辗转在各个沿海城市打工,跟着建筑队的人在一个又一个工地上干活,搭脚手架,给人装修房子;住漏风的工棚,吃最差的粮食;存下一点钱,结了婚。后来他成了橡胶厂的流水线工人。因为橡胶厂有害气体多,干了几年身体吃不消,就不做了。再后来,小舅回到了老家,托人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成了机械厂工人。机械厂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经常会放假。作为一名计件工人,他常常一个月只能拿到一千多块工资。
小舅大我十来岁,小时夏天,我常跟他一起在小溪中捉鱼。溪水清冽,鱼儿机敏,小舅手执一根八号钢丝,瞅见鱼儿在水中蹿过,便眼疾手快,挥动钢丝。那钢丝呼呼作响,劈开空气,劈开清流,劈翻小鱼。
记忆中的小舅,常在农忙时候帮我们家劳作农活。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叫藕塘的地方,有一丘我们家的水稻田。好多年中,我和弟弟,都跟着小舅一起去耘田。藕塘,大约原先是一口烂泥池塘。那是个冷水塘。别处的田水,被太阳一晒,都热乎乎的,这里却还是冰冰凉。最让人吃惊的是,赤脚站在这田里,人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往下陷。
我们出门的时候,母亲会关照一句,你们站拢些,要是陷下去,就相互拉一把。
又说,戴一顶笠帽去。这样,人陷下去的时候,至少水面上还有一顶笠帽啊。
这话当然是玩笑的,但是仍然让我们感到恐慌。
现在,小舅的儿子,已经上了大学。
去年考上的。那是位于台州临海的一个职业技术学院。供一个大学生,对小舅这样的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舅也早已抛下了他的田地。田地里刨不出钱来。小舅和舅妈两个人,都去机械厂上班,他们每天都盼着多做活,少放假,这样能拿高一点的工资。
我记忆中的小舅只有十七八岁,那时,他英俊高大,有一身的力气,甚至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木匠。他不仅是一个好的木匠,他还能种植粮食,玉米,丝瓜,柑橘,南瓜。他买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录放机整天放着小虎队的歌。
现在的小舅,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每天一脸愁容,骑着电瓶车往返于县城与小村庄之间的道路上。
下雨的时候,闲在家中没事,小舅仍然会拿起锯子刨子和斧头,静静打量一块木头。
有一天他做了一块砧板,送我。那块砧板很厚、很重,是用老松树做的,为了做那块砧板,他上山找了大半天,才看中一棵老松树。
砧板很好用的,放在那里也会散发出好闻的松木的清香。
我在小舅的家里,还看见一些小凳、矮凳、长凳、短凳,都是他自己做的。我对着那些小凳、矮凳、长凳、短凳,愣愣地看了半天,我觉得那些小凳子都好像要跑走了。
5
从前,在每一个收割季开始之前,篾匠都是乡村里最受欢迎的人。每家每户都要把箩筐、谷篼、竹簟、扫帚等等农具整修一番。篾匠开始走村串乡。他把山坡上生长得恣意无章的毛竹,变成一条一条无比柔软的篾片。他把那些无比柔软的篾片,缝补在箩筐、谷篼、竹簟们的棕色老篾之间。新篾与老篾相互穿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经沧桑、破绽百出的箩筐、谷篼、竹簟们于是焕然一新,容光焕发。再经过一季的收割使用,新老成色的篾片就会浑然一体。
可是那摊晒谷子用的竹簟,现在到底是没有了。我们家好多年没有用竹簟。收割来的稻谷摊开在竹簟上,在阳光底下曝晒。竹簟是稻谷的舞台。现在竹簟不见了,人们直接把稻谷摊开在水泥地面上。靠近公路的人家,直接把稻谷摊开在宽阔的水泥路面上。
“禁止在公路上晒稻谷!”
这样的标语在公路边的山墙上写了好久,终究没有人太当一回事。“路又不是你家的!”老妇人一边翻晒稻谷一边对劝她注意安全的人这样说。大路朝天,你走半边,另半边留给我晒稻谷,老妇人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么,篾匠又到哪里去了呢?
从播种谷种开始,到催生秧苗,再到秧苗生长拔节,直到成为金黄色的稻穗,在这漫长的时光里,父亲会一直担忧着天气。担忧着水源。担忧着蝗虫。担忧着稻飞虱。担忧着耘田或收割的人手。他总是有许许多多值得担忧的事。尽管如此,许多事情仍然不尽如人意。比如去年村边的桃花溪就发了大水,把我们的稻田淹了四天四夜。
现在水稻终于要成熟了,就好像一个孩子历尽艰辛终于考上了大学。
所有的忧心可以放下。父亲感到心满意足。
父亲把打稻机搬出来擦洗一新,上了一遍油,把镰刀磨好,把箩筐上的绳子整理完毕,然后又走到稻田里去。稻田在夕阳里呈现出朦胧的暖色调。明天就要收割了,父亲脱了鞋,分开稻株,远远地走到稻田中去。
四野一片寂静。
田埂上看不到几个人。整个村庄居然如此寂静。
我忽然想到,一个农民的一生,耕种次数其实是有限的。从前村庄里的水稻是两年一熟。现在是一年一熟。一个人活到八十岁,也就看到八十次水稻成熟。
不过如此,而已。
周华诚,1979年生于浙江常山,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新荷人才”。從事媒体工作12年,于2014年发起“父亲的水稻田”城乡互动文创活动,回到老家与父亲一起耕种三亩水稻田,并带领城市人一起下田劳作,引起广泛影响。曾在《人民日报》《江南》《芒种》《文学报》《散文选刊》等发表散文、小说数十万字。出版有《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一饭一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9)《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我有几只狗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5)等作品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