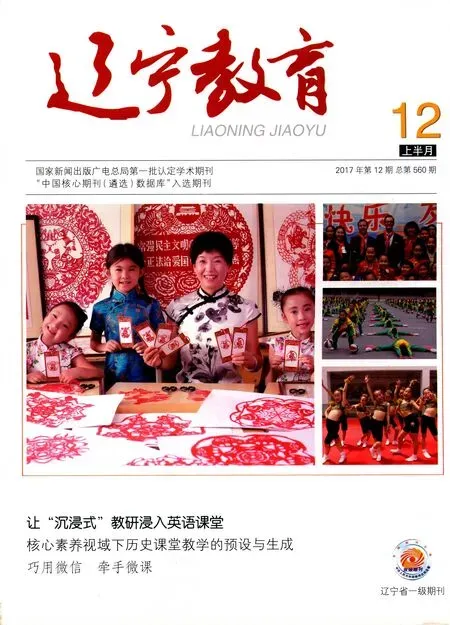从“教课文”到“教语言”
2017-03-13汤虹飞
◎汤虹飞
从“教课文”到“教语言”
◎汤虹飞
一位同事要执教公开课《九色鹿》,她的教学设计主要是通过朗读体会九色鹿的见义勇为和调达的背信弃义,即以理解人物形象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样的教学设计平时并不少见,写景的课文就讲景,写人(或物)的课文就讲人(或物),把课文作为教学内容原原本本地呈现给学生,这是典型的“教课文”。其实,对于文本内容,绝大部分学生通过初读就完全可以了解大概的,比如《九色鹿》,学生只要读上一两遍,肯定就会生出强烈的爱憎来,人物形象也会非常鲜明,我们老师再煞有介事地引导学生把表现人物形象的词语、句子画出来并读出感情来,其实就已经是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情了。教学应该立足于学生所不会的、不懂的及需要发展和提高的地方,而不能不顾学情、不作取舍。
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以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为第一要务。基于本课,如何实现从教课文到教语言的转向呢?
一、建立词语的联系
词语是语言的最小单位,语文教学中不能回避词语的学习。仅仅理解了词语还不够,重要的是让学生把词语进行意义和逻辑编码从而实现语言的内化。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把词语类别化,或从意义或从结构的角度对词语进行群组化定义,让学生形成思维相似模块,运用接近联想的方式实现词语的内化;二是把词语叙事化,包括文本叙事、生活叙事两种,文本叙事即是运用词语表述课文的文本内容;生活叙事则是联系自己的生活来运用词语。
如在本文之中,有大量的带有“义”的词语——“见利忘义”“见义勇为”“背信弃义”等,我们就可以采用以上两种方式建立词语的联系,不仅可以积累语言,而且也可以实现对文本内容概括能力的训练。如这三个词语在意义上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和“见义勇为”意思相反,所表达的感情色彩不同;“见利忘义”和“背信弃义”都属于动宾式的构词,富有节奏感,由此还可以联想到“说三道四”“见异思迁”等词语。同时还可以由这几个词语联系到文本中的人物,并试着运用这几个词语来说一说文本的故事内容。这样一来,词语的教学就有了更为宽广和有效的训练空间。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应有敏锐的词语意识,让词语教学成为对话文本的有效途径。
二、扣准训练的核心
语文教学应该关注文体,还课文本来的面貌;但很多的语文课堂却忽略了这一点。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说明文,教学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无非读读,抓住所谓的关键词语体会一下,最后还非得整出点文化、思想方面的东西。这样的教学训练形式单一,学生的语言能力很难得到有效提高。
很多时候,课后习题会给我们清楚的提示。比如本文课后第一题这样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复述课文就相当于讲故事,也就决定了本课教学最重要的语言训练任务就在于此。如果把精力都放在人物形象的把握上或诚信文化的传承上,那教学就真的错位了。
复述课文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教师把课文塞给学生,让他们去练习,教师自己可以退出了,而是应该教给他们方法。比如,九色鹿救调达的那一节,我们就可以这样设计:(1)看谁把这一节读得最熟练。(2)读得熟练了,请试着把它讲出来。(3)要想把这个故事讲好,你觉得不能忽视哪些词语?为什么?这里,“立即”表示时间短暂、毫不犹豫;“纵身”表示奋不顾身;“汹涌”表示浪高水大、充满危险。这些都是讲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词语,讲好了才能生动形象。(4)学生抓住交流所得的词语进行复述训练。
很显然,这样的设计是立足于语言训练的,而不是以理解文章的内容为重点。让学生通过讲故事来自主发现一些词语与通过抓住“见义勇为”来圈画一些词语,在训练的理念和语言形成的途径、效果上也不相同。首先,“讲故事”立足于一个“练”字,把对词语的理解放到一定的语言交际活动中来,学生是在形成自己故事语言的“建构”,是为自身的发展而去进行的练习活动。而“见义勇为”这样有着道德取向的词语是顺应文本的价值取向,为了完成文本和教师的要求而做的事情,好像与自己无关。其次,“讲故事”是一个相对宏观的要求,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有自主的选择性,不是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可以是从九色鹿的角度出发,可以是从调达的角度出发,也可以是从当时环境的角度出发,学生的思维更具有内发性、自主性。而道德判断则仅仅立足于九色鹿的表现上,所理解的就相对狭隘了,学生的思维被束缚,很难以实现对文本的全面把握。
三、活化文本的语言
语言不仅仅通过所描述的内容来表情达意,而且也会把这些情意巧妙地蕴含在语言的形式中,这也是文本语言文学特质的重要体现,而这又能够极大地提高语言的神秘感,激发学生对语言的兴趣。所以我们在解读文本的时候,就要努力关注作者的话语方式,他为什么单单选择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其他?这里面是否还有着其他秘密?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教学的视野就会豁然开朗。
课文中九色鹿斥责调达的那一段话,很多老师都觉得很重要,一定得引导学生透彻理解、认真体会,通常的做法是抓住“气愤”,把语气、语调、语速调整到气愤的程度,然后还可能让学生带着相应的动作来表演读。学生拿腔拿调的朗读、夸张滑稽的动作往往只能引人发笑,而九色鹿的怒不可遏、义正辞严被庸俗化、扭曲化了,问题的根本就出在对语言解读的肤浅上。
如果我们深入研读文本,就会发现这段文字有着鲜明的节奏感。我们来看一看:
九色鹿非常气愤,指着调达说:“陛下,您知道吗,正是这个人,在快要淹死时,我救了他。他发誓永不暴露我的住地,谁知他竟然见利忘义!您与这种灵魂肮脏的小人一起来残害无辜,难道不怕天下人笑话吗?”
读这一段话,我们的语调就会自然而然地高了起来,语速也会自然而然地快了起来。原因何在?就在于这段话几乎都是短句子。短句子有两种表达效果,一是可以表达轻快、活泼、有趣、跳跃的感觉,二是可以表现矛盾、激动、悲愤的心情。很显然,这段话属于后者。如果我们把对话文本从与文本思想内容的纠结之中跳出来,回到语言本身,就会发现别样天地,学生也会对这种语言形式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如何处理呢?我们可以采用句子对比的方式;(1)正是这个人,在快要淹死时,我救了他。(2)我曾经救过当时快要淹死的这个人。这两个句子存在着什么样的异同呢?学生在反复朗读比较后,很容易就能够把握这种独特的语言表达张力。这样的练习,会在学生心中植下语言的种子,他们在阅读和写作的时候就会关注这种语言现象,从而提升语言能力。而这,也正是我们语文教学所追求的。
通过以上三点解读,语文教学基本上实现了从“教课文”到“教语言”的转向,从而更贴近了语文教学的本质诉求。
(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责任编辑: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