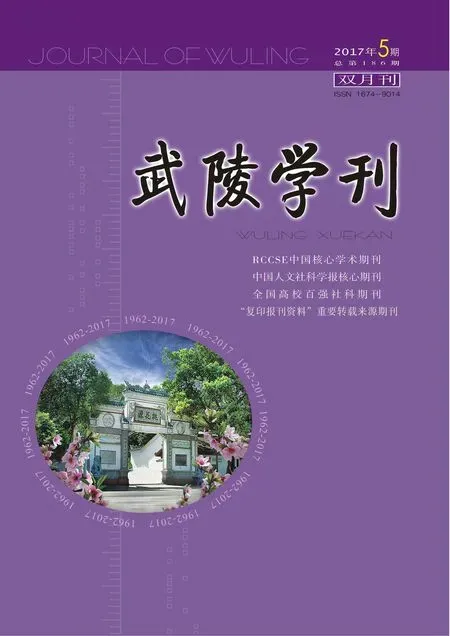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西学渊源正考
2017-03-11邓影,尹恒
邓 影,尹 恒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2.北京百衲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古籍部,北京100022)
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西学渊源正考
邓 影1,尹 恒2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2.北京百衲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古籍部,北京100022)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西学渊源国内学者主要以为来自叔本华,事实上应该是源自康德。无论就王国维自身在《人间词话》中所言,还是通过对“有无之境”二者是否关涉理性概念的具体分析,都可论证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崇高”与“优美”有着互相对应的关系。但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又很难包容康德的“崇高”与“优美”的全部内涵,其对康德概念移用时的不彻底是否是有意的,以及中西学术话语之间的融通是否可能,都使得其渊源一直模糊不清,难以定论。
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崇高;优美
一、“有无之境”的两种阐释策略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所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中国近现代批评理论史上的重要评论话语,在学术界内一直颇受关注。从众多对此话语的研究中,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阐释取向:一种是建构取向。此种阐发重视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建构性阐发,试图把握住在话语背后的诗学思考与阐释系统。就有影响力的著述而言,从朱光潜的“同物”与“超物”之说,到叶嘉莹的“利害关系”说和佛雏的“客体与主观性”说,都是在不同层面上对王国维此说之系统建构性阐发。就国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言,许多的观点更倾向于考察出此说的中西学渊源,而在讨论西学渊源的论文中,观点基本上倾向于强调此说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学说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则是解构取向。此种阐发之策略,是从文本内部去演绎出文本自身的自相矛盾之处,对意义中心确定性与可明确把握性提出质疑。这种解构性阐释取向的文章,以罗钢的文章《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说探源》为代表。
两种阐释不仅丰富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解读空间,同时本身也是对中国批评理论可能性的出色探索。可以看到的是,在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探源中,都提到了此说所受西学之影响,尤其是康德与叔本华。在罗钢文章中曾经提到了此一层思考,并质疑了“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说与康德和叔本华之美学相承传这一传统看法。文章认为“叶嘉莹显然并不清楚‘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真实的思想来源,而且退一步说,她以有无利害关系来区分二者也是不妥当的,和她声称依据的康德、叔本华美学并不吻合”[1],进而论证了康德、叔本华的审美超利害关系说以及“优美”和“崇高”说都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利害物我对立”说所存在的矛盾性。罗钢最后认为:“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说,是王国维在西方理论背景下所进行的一次不成功的理论建构。”[1]此文具有丰富的资料溯源与严谨的逻辑推证,为我们理解“有无之境”提供了重要理路,但是仍然没有厘清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说是与西学中哪些概念紧密相连或相对应而又怎样发生了矛盾和断裂,当然也不能很好地让我们信服其结论。
同样,在其它有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西学渊源的论述中,少数文章提到了此说与康德的学说有直接关联,但这些文章要么在史料上论证稍欠不足,要么就并未说明王氏此说是否与康德的“优美”与“崇高”范畴划分的重要依据有所联系,即有无“理性概念”的介入。本文在对“有无之境”的西学渊源重新梳理中认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其实源自于康德的“崇高”与“优美”这一对范畴,并试图通过分析,探讨此说渊源不明的原因及其意义。
二、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之前深受康德哲学影响
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曾就王国维所受康德与叔本华之影响进行过详细的考查,认为“静安先生所提出的‘有我’与‘无我’二种境界,实在是根据康德、叔本华之美学理论中由美感之判断上所形成的两种根本区分”[2]231。而罗钢在论证王国维所受泡尔生之影响时也看到,“除泡尔生的影响之外,谈及艺术时,王国维采择康德的观点较多,如康德认为艺术无关乎认识,无关乎真理”[3]。由此可见,王国维所受康德美学思想影响之重大。
王国维在自己的著述中也不断提到康德对他的影响。在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他不断提到康德的美学思想,譬如“‘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自巴克及汗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类矣”[4]37。同时,王国维还提到“优美与宏壮之判断之为先天的判断,自汗德之《判断力批评》后,殆无反对者。此等判断既为先天的,故亦普遍的、必然的也”[4]39。由此可知,王国维对康德美学理论的理解绝对不可能只限于一二观点,而且无论王国维是否全部通读过康德《判断力批判》原文,但至少对此书之大体美学理论是有所了解的。且在王国维其他文章中也依旧可以发现其对康德之了解绝不会是浅尝辄止。
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和康德与叔本华之关系的一段论述已经可以看出其对康德思想了解之状况——“哲学者,世界最古之学问之一,亦世界进步最迟之学问之一也。自希腊以来,至于汗德之生,二千余年,哲学之进步几何?自汗德以降,至于今百有余年,哲学上之进步几何?其有绍述汗德之说,而正其误谬,以组织完全之哲学系统者,叔本华一人而已矣。而汗德之学说,仅破坏的,而非建设的。彼憧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故其说仅可谓之哲学之批评,未可谓之真正之哲学也。叔氏始由汗德之知识论出而建设形而上学,复与美学伦理学以完全之系统,然则视叔氏为汗德之后继者,宁视汗德为叔氏之前驱者为妥也。”[4]76在这里,虽然王国维对康德整体哲学体系之认识尚为欠缺,导致其评价也并非没有偏颇,但其原因也在于王国维主要是通过叔本华之书来了解康德的。他曾写道:“癸卯之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性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4]226由此可知王国维对康德之重视与了解,并且其对康德与叔本华学说之间的关系都是颇为清楚的。
在王国维其他非介绍西学类文章中依旧保持着对康德思想的热衷与运用。譬如《释理》《原命》《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等,都可以看到其对康德之关注与思考。再者,王国维对康德的关注其实并不亚于对叔本华之了解。在《汗德像赞》中王国维也写道:“笃生哲人,凯尼之堡;息彼众喙,示我大道……万岁千秋,公名不朽。”[4]246
在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之秋,王国维为自己的《静安文集》所作之序言中曾道:“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4]226而在1908年10月到1909年1月的《国粹学报》第四十七、四十九和第五十期上首刊了王国维所著之《人间词话》。从王国维所写可以推测出,自1905年之后王国维已经开始研读自己所理解之康德而有意要摒除叔本华之康德的影响。三年后其发表的《人间词话》则应该可以窥见出王氏这些年来对康德之了解。而1907所写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正是王氏这段时间独自研读康德之书的一篇心得。这篇文章多处提及康德之说,尤其提到了康德最为有名的美学著述《判断力批判》。由此可以推测出,王国维在这几年中所细心阅读之康德著作中,《判断力批判》是其中的一部,从而可以推测出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时是应该受到过此书之影响的。进而我们还可以推论出,王氏“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提出与康德《判断力批判》之影响亦应该极为有关。
三、“有无之境”源于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崇高”与“优美”
《人间词话》关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论述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夕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5]1
我们认为,王国维所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与康德《判断力批判》中所提出的“崇高”与“优美”范畴相对应的。比较重要的明证就是在王国维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后,王国维还提到“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中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5]2。根据《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可以知道,王氏这里所用之“优美”与“宏壮”即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提出之“美”与“崇高”两个概念。而且王国维还曾在《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中写道:“美之物有两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6]《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上的,而此对概念正是后来在《人间词话》中“优美”与“宏壮”概念的前身。在对“优美”与“壮美”的辨析中,何兆武早已在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译本序言中指出,“王国维的‘壮美’一词即是‘崇高’”[7]8。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优美”与“宏壮”这对范畴正是与康德《判断力批判》中所提出的“优美”与“崇高”相对应。继而推之,其“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也应当正是与康德《判断力批判》中所提出的“优美”与“崇高”相对应的。
不过,既然我们可以从王国维的文本中推出这种结论,但在实际阐释语境中是不是真的就具备这样的对应关系?或者即使是来自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两对概念就真的具备一一对应关系吗?
在这里先看对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之理解。王氏定义“有我之境”为“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里可以这样解读,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鉴赏,而主体所鉴赏之对象必然是在主体鉴赏能力之内进行,也即是康德所说的“愉悦的普遍性在一个鉴赏判断中只表现为主观的”[8]48。而“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中之“泪眼问花”既是主观之行为,“花不语”则不一定是花真的能语,而是审美主体所赋予花之能语状态或是想象为花能语。在这一活动中,重点在于书写者首先需要知道“花”的概念,即“花”是植物之一种,是不能够言语的,因此才能有“花不语”之拟人效果。所以作为这种创作状态,是需要具备理性概念在先的。
在“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夕阳暮”中也是如此。“馆”本是物件而无生命,并非人,怎会有“孤”之感?“孤馆”者乃是审美主体以己之感而赋予客体也,故“馆”方能“孤”之。这句词的妙处也就是把理性概念中一种物件赋予了人的感受,从而获得了拟人之效果。但这样的前提是,“孤馆”的“馆”的概念在整首词中是与审美主体建立了一种先在理性概念的联系,要是没有“馆”这一非生命物体概念的先在,那么这种拟人审美效果就不能获得。在“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中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要是没有“我”头脑中“物”的概念之先在,就不会有“我之色彩”的着予,对“我之色彩”之理解必须建立在对“物”的理性概念之上。因此,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这种理性概念关系的建立虽然难以完全拒斥感性因素,但确必然以对理性概念之先在把握为基础。
以上两个文本例子都极为形象地说明了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理性概念之获得是审美创作活动的前提。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因为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虽然不可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却正是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合适性而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来的。”[8]83感性形式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理性概念却是绝对的在场,且理念通过与感性表现的冲突而激发出崇高感。康德认为,不同于带有促进生命情感的美,崇高感可称为消极的愉快。比如,大自然在其极端狂暴、无序与野蛮中体现出其伟大和力量,体现出人的渺小无力而激发出人心中的崇高。“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所以它作为激动并不显得像是游戏,而是想象力的工作中的严肃态度”[8]83。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花不语”“孤馆”都符合康德所谓生命力的阻碍与不适感,这种想象加工下的理念性对象与主体生命之内在期许具有着强烈的冲突与背离,表现出主客之间一种动态的张力,其当然不属于直观性的优美,而是一种强烈的消极愉快感。因此可见,王国维之“有我之境”与康德所定义的“崇高”是极有渊源关系的。
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来理解“无我之境”呢?叶嘉莹认为:“《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无我’,实在只是为了立论方便起见,藉此一词以指称物我之间没有对立之冲突,因之得以静观外物的一种境界。所以此种境界虽称为‘无我’,然而观赏外物之主人则却依然是‘我’。”[2]234叶嘉莹的分析是极为重要的。虽然说是“无我”,但却并不是真的“无我”,因为一切所观,皆是由“我”发之,审美主体是不可能缺席的,所以“我”是必然在场的。
王国维定义“无我之境”为“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先看“以物观物”,这里出现了两个物,但显然这两个物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层面上发生的。既然是“以物观物”,那必然是审美主体先观此物,然后再凭借自己所观此物再观彼物,这里有一个时间顺序。所以在这里审美活动可以划分为“以我观物”与“以我所观之物再观彼物”两个审美行为,第一个以我观物之审美活动正是前面王国维所提出之“有我之境”,也就是刚才论证的在活动中必然涉及理性的概念。
“以我所观之物再观彼物”,其已经不再仅仅是停留在“有我之境”的境地,因为“有我之境”关注点在“于由动中之静时得之”,并非求得完全之“静”,其关注者乃是理性之概念,具有主客之冲突与张力。而“无我之境”所对应的正是“优美”。作为“优美”之理解,也就正如康德所写到的:“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8]39,而“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8]46,也就是说理想中“优美”感是不涉及理性概念的。而在“无我之境”中也恰恰就是在已获得“有我之境”的理性概念认识上,要摆脱理性概念的规约而获得不涉及概念的这种状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对这两句创作的理解恰恰就不能拘泥于对诗句中具体概念的理解,不能去追问所采之菊花是什么品种,颜色怎样,也不能去追问所见的“南山”是在哪个地方,是高还是低,如果这样就不可能把握到陶渊明或是元好问在创作时与其他人创作诗句时之不同处以及独特审美效果。只有对“菊”“南山”“寒波”“白鸟”不做清晰概念性理解时,只有以一种真正“静”的状态去体验时,诗人才可能去把握住句中之悠远、淳净的诗意境界,也才能知道何为“人惟于静中得之”的创作境界。故而叶嘉莹也指出:“‘无我之境’则是指当吾人已泯灭了自我之意志,因而与外物并无利害关系相对立时的境界。”[2]230同时,康德曾举例区分“崇高”与“优美”:“高大的橡树,神圣丛林中孤独的阴影是崇高的,花坛、低矮的篱笆和修剪得很整齐的树木是优美的”[7]3。前者给人以张力冲突,后者示人以静谧轻松。此处王国维“无我之境”的例证,也正是康德所谓与生命相合的积极愉快感。
综此可见,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标准之划分的确与康德的“崇高”与“优美”范畴之划分标准——是否关涉理性概念——相关联,并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应该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崇高”与“优美”呈现出一种对应关系。但仍需要面临一个问题,前面所阐述的“有我之境”是否就真如康德“崇高”范畴中的“不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无我之境”就真能逃脱理性概念的纠缠?问题出在两方面:
一方面,从康德本身之美学论述来看,所谓的“崇高”自然理应拒绝感性形式之介入,但在现实中却并不一定是这样,康德本人也并没有完全把话说死,所以也提到理念需通过在感性表现出来的不合适性而被激发出来。在“有我之境”之阐述中,王国维还提到“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里的“我”是感性情感,而“物”就是理性之概念。同样,在康德关于美的论述中也提出自由美与依存美之区别,“有两种不同的美:自由美,或只是依附的美。前者不以任何有关对象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为前提;后者则以这样一个概念及按照这个概念的对象完善性为前提”[8]65。康德所强调的不关涉理性概念的美只是他预设之自由美,现实中更多的是依存美。而诗歌创作只能与依存美相对应,因为在康德那里,文学不属于美或是自由美的范畴,这一点朱光潜早已指出:“就纯粹美不能涉及内容意义来说,诗与文学当然不能列入纯粹美”[9]358,而“绝大部分的自然美和艺术美都要归到依存美”[9]359。所以即使从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可以找到与王氏此说相对应的范畴,但也绝不是一一完全对应,其中必然会因为康德本身美学理论的内在理路的回环往复而有所损益。另外一方面,王国维本身是否有意要移植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整套美学理论,他对康德理论的吸收目的何在,他是否愿意做康德美学在中国之代言人,抑或还是别有他意?这里我们都不能简单认定王国维此说是照搬康德学说,不仅因为很多学人都阐发出此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紧密,更在于不能轻易对王国维自身之学术理想过于低估。
结语:有意的断裂
叶嘉莹认为:“康德所分别的‘优美’与‘壮美’在性质上虽有不同,然而就美感经验言,则同样是产生于超于利害的‘直观’,所以优美与壮美的区分与前一点我们所提到的美学的‘直观’观念实在乃相辅而相成的,叔本华之学说原曾受康德之影响,静安先生则兼受二人之影响,虽然他所掌握的不过只是康德及叔本华美学理论之一部分而并非其全体,然而美之欣赏当为超利害之‘直观’以及美可以区分为‘优美’与‘壮美’二种之不同,则确实乃是静安先生得之于康德及叔本华美学的两点重要概念。”[2]157此句评论重要之处在于点出了王国维对康德“崇高”与“优美”这一对概念把握到的恰恰只是“一部分而并非其全体”。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崇高”在数学与自然界力学上的分析,都没有进入王国维对“崇高”概念的分析与理解并内化到“有我之境”当中;同时康德还提出的审美情感与自然合目的性之间的关系、美的理想以及快适与善等有关“优美”的论述,也没有被王国维吸纳到他对“无我之境”的建构之中。从而也就致使此说渊源一直模糊不清,难以定论,以致认为王国维的探索中由于矛盾和断裂而成为了一次不成功的理论建构。其中原因当然很多,除了王国维可能本身不一定完全精熟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以及概念本身移用的可操作性问题外,恐怕更可能与王国维自己有意建构中国自身之批评话语而不欲照搬西学话语有关。
王国维在中西文化对话上是一位承故启新的关键人物,他对中西之思考绝对不可能是简单固守传统或是盲目照搬西方,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文化当如何应对西学的问题上,他显然不可能轻易处之。余虹曾论证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诗学’(文学理论)的结构性差异和不可通约性”[10],从对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西学渊源考察中,可以深刻感受到王国维在化用西学概念如何与中学传统话语之融通上的才思卓绝和用心良苦。但事实还不能证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在许多文学作品批评阐释上不具有其可操作性。而如何评判王国维这种化西为中的学术探索在中西文化对话上的意义,想来在我们未能对中学与西学的较为系统的理解与阐释之前,还尚难有此能力回应。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谈到,王国维一生之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中一方面即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11],陈先生之评价亦是持平之论。
[1]罗钢.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说探源[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6(2):141-172.
[2]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3]罗钢.王国维与泡尔生[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23-30.
[4]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5]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9.
[7]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9]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0]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7.
[1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M]//陈寅恪先生全集:下册[M].台北:里仁书局,1979:1435.
(责任编辑:田 皓)
Abstract:Domestic scholars hold that the western source of Wang Guowei's"ego-involved realm"and"ego-absent realm",which put forward in Jen-ChienTz'u-Hua mainly comes from Schopenhauer,in fact it should be derived from Kant.Both Wang Guowei's own opinion in Jen-ChienTz'u-Hua and our concrete analysis,can prove a conclusion that"ego-involved realm"and"ego-absent realm"should correspond with kant's"sublime"and"grace"category,which put forward in The Critic of Judgment.At the same time,whether it is intentional forWang Guowei to transform Kant's concepts unthoroughly,or whethe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discourses has the possibility,both result in the fact that it's hard for Wang to contain all the meaning of Kant's categories,and it alsomakes the source always obscure and difficult to define.
Key words:Wang Guowei;ego-involved realm;ego-absent realm;sublime;grace
The Source ofW estern Learning of W ang Guowei's Ego-involved Realm and Ego-absent Realm
DENG Ying1,YIN Heng2
(1.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2.Beijing Baina International Art Auction Company Limited,Beijing 100022,China)
I0
A
1674-9014(2017)05-0106-06
2017-04-07
邓 影,女,四川乐至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尹 恒,男,四川西昌人,北京百衲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古籍部经理,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