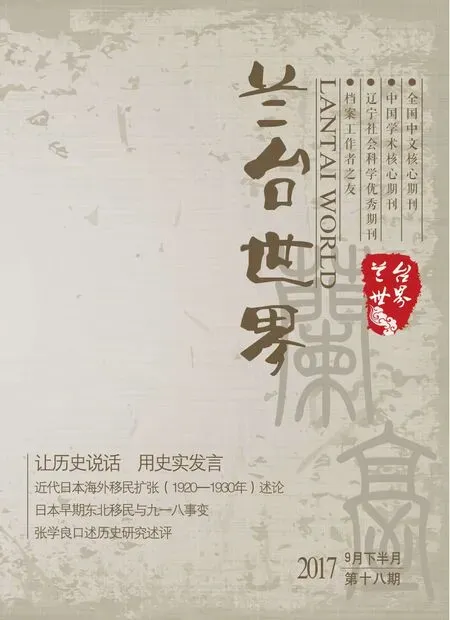明代革新派文人“尚俗”观的形成及完善
2017-03-10韩伟
韩伟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150025)
明代革新派文人“尚俗”观的形成及完善
韩伟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150025)
“尚俗”是明代革新派文人的主要特征。革新派文人的“尚俗”倾向具有文学和心学的双重基因,以李东阳、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为其提供了文学准备,发端于王阳明,成型于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思想,为其提供了思想动力。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使革新派的“尚俗”思想走向纵深。最终,王骥德以“尚俗”而不“滞俗”的美学追求,使革新派的“尚俗”思想趋于完善。
明代革新派俗文学心学
一、“尚俗”的文学准备
革新派是对明代中叶以后具有创新意识的众多文人的泛称,它并非是一个具体的学术群体,更没有固定的文学纲领,只是由于时代思想、师承关系等原因,表现出相似的文学旨趣,代表人物如李开先、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冯梦龙等。
客观来讲,明中期蔚为壮观的“尚俗”潮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文学与心学的双重背景。就文学而言,这种潮流在明初文坛就已经有所萌芽,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就指出,哪怕是小夫贱吏、妇人女子,只要情感真挚,口中所吟便是佳作,而所谓的文人墨客、学士大夫则往往流于造作,而“不能得其妙”[1]132。在李东阳看
来,自然之歌是“不待于教”的,这就肯定了民歌存在的合理性。除了李东阳,“台阁体”诗人也有推崇民歌的言论,其代表人物杨荣在《逸世遗音集序》中说:“嗟夫!诗自《三百篇》之后作者不少,要皆以自然醇正为佳。世之为诗者务为新巧,而风韵愈凡;务为高古,而气格愈下。曾不若昔时闾巷小夫女子之为,岂非天趣之真与夫模拟掇拾以为能者,固自有高下哉!”[2]1240册,169虽然“台阁”诗风因其柔靡典雅,多为人诟病,但杨荣对自然醇正传统的倡导却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从中不难看出在“三杨”内部实际上也不乏较具修正性的认识。与推崇“自然”相一致,杨荣亦对当时“务为新巧”者进行批判,甚至认为他们的诗歌难以与闾巷歌谣比肩,这种评价在当时可谓十分大胆。
对民间歌诗的推崇,也在前后七子的思想中有所体现。在这一点上,复古派与革新派表现出了一致性,并为明中叶以后俗文学的大行其道奠定了基础,也为革新派“尚俗”观的展开提供了动力。李梦阳提出了著名的“真诗乃在民间”的观点,在《诗集自序》中他一方面肯定了“途巷蠢蠢之夫”的吟讴之作,认为这些市井之人的歌谣是古代风诗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他也对“胡乐”充分肯定,在他看来经历了金元时期的文化濡染,明代俗乐必然带有胡乐的色彩,因此没必要固守所谓的夷夏之防。市井歌谣只要具备“自然之真”,便可以成为学习的对象,因此晚年的李梦阳曾以“予之诗非真也”,慨叹自己诗歌中蹈袭僵化的不足。李梦阳的这种倾向,亦对何景明有所影响,李开先在其《词谑·时调》中称:“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何大复继至汴省,亦酷爱之。曰:‘时调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每唱一遍,则进一杯酒。”[3]1276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亦有类似记载:“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4]647由此可知,李梦阳与何景明尽管在文学主张上有所差异,但在对待民歌的态度上则非常相似。实际上李梦阳、何景明等复古派“尚俗”的原因在于,试图恢复先秦音乐文学传统。而先秦音乐文学传统实际上就是“风诗”传统,其本质就是通俗的民间歌谣。
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在当时文坛都是领袖人物,他们对民间俗文艺的喜爱一方面代表了文艺思潮的潜流,另一方面也必然对文坛产生深入的影响。沈德符如此描述当时的世俗文艺状况:“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4]647甚至在他看来达到了“真可骇叹”的程度。在具体实践层面,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是李开先。他不仅编订了《市井艳辞》、《改定元贤传奇》,而且也亲自进行创作,《宝剑记》、《断发记》、《园林午梦》、《打哑禅》、《中麓小令》等作品都具有十分鲜明的民间色彩。他亦非常推崇元代散曲,一生创作此类作品二百余首,在《西野〈春游词〉序》)中他说“传奇戏文虽分南北、套词小令虽有短长,其微妙则一而已”[3]494,不仅将南戏与北方杂剧等而视之,而且也肯定了元代的文学传统。南戏与北方杂剧相比较而言,更加典雅,情感表达更加委婉,文人化气息更浓,但是在李开先看来则并非如此,北曲由于鲜明的民间性,往往更接近文学的天然形态,他对元人乔吉的小令、杂剧、散套都非常推崇,并刊刻其作品,认为其作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为文”(《乔梦符小令序》)。由此足见,李开先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践行了“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的文艺主张,从而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一起为通俗文艺的深入人心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准备。
二、“尚俗”的心学基础
以上情况表明,明中叶以后革新派的“尚俗”倾向是存在十分明显的内在线索的,下面将考察心学中存在的“尚俗”观念。客观来讲,心学学者从自身的哲学体系出发,他们对“百姓日用”的形而上提升,为明代世俗生活、世俗情感、世俗文艺的合理性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持。早在王阳明的观念中,就已经包含这方面的成分了,与宋代理学家不同,“愚夫愚妇”的道德也是王阳明肯定的对象,在他看来“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时”是重要的获得“良知”的手段。试看下面文字: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5]113
在王阳明看来,绝对地复兴古乐是不现实的,但“今之戏子”所奏、所唱是具有古乐的特质的。诚然,在王阳明思想中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仍在强调圣人的作用,重视“德”对音乐内容的充实,更加以“化民善俗”为手段,最终实现对“良知”的回归。然而,在文艺的外在形式上,则肯定了“愚俗百姓人人易晓”的存在形态,这在客观上已经对通俗艺术有所肯定了。
明代中期以后,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最主要的传承者,泰州学者一方面突出了王守仁思想中的情感性因素,同时也对其世俗文艺观进行了发展。其中,王艮开始明确指出“百姓日用即道”:
集同门讲于书院,先生(王艮)言百姓日用是道。初闻多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自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惟其不悟,所以愈求愈远,愈作愈难。[6]72
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者,他将王阳明思想中的“尚俗”基因加以生发、延展,极大地拉近了心学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实际上,王艮关于童仆往来与日常之道的况喻,其雏形亦与王阳明有关,在《传习录》中,王阳明曾以童子洒扫应对来阐发良知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他说:“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5]120可见,王艮的“童仆往来”与王阳明的“洒扫应对”如出一辙,其因袭的痕迹非常明显。王艮之后,其子王襞进一步对“百姓日用是道”的观念进行夯实,其三传弟子罗汝芳言“捧茶童子却是道”,凡此种种,都可以视作对王阳明“与愚夫愚妇同德”及“洒扫应对”思想的具体化。
泰州学者的这种倾向,在他们的文艺思想中必然有所呈现,其中表现最为明显者就是李贽。具体而言,李贽对自然的推崇、对世俗文艺的认同、对民间真情的肯定就带有明显的“尚俗”色彩。在李贽看来,“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7]99,这可以看成是李贽“雅俗观”的集中呈现,他眼中不存在古雅近俗的情况,从文学发展的宏观角度,对元代以后盛行的通俗文学给予了充分肯定。事实上,对世俗生活和真实情感的肯定是这一时期很多思想家的共识,比如与李贽有密切交往的焦竑就曾说“寻常闲语,无不是道”、“以至穿衣喫饭,举手动足,无非此心”[8]717,而焦竑的老师耿定向也说“道之不可与愚夫妇知能,不可以对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说乱道也”[9]819,又云“天下道理无论六经诸子之奥旨微言,只此百姓日用之常”[10]342。无论是王艮,还是李贽、焦竑、耿定向,在当时思想界都地位显赫,他们的这些理论倡导,对革新派“尚俗”美学观的形成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
三、革新派的“尚俗”实践
事实上,革新派中的核心学者大都与心学学者关系密切,且他们的思想亦带有明显的心学色彩。加之,以“复古派”开创的“尚俗”风习作为内因,这些都为革新派“尚俗”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徐渭是明代开“革新派”风气之先的人物,在复古派占据主导的明中期文坛,“文长(徐渭)、义仍(汤显祖)崭然有异”[11]567,徐渭早于汤显祖成名文坛,由此可见徐渭对“革新派”的意义。具体而言,徐渭反对以雅词入戏曲,在《南词叙录》中他直言:
以时文为南曲,……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12]49
在他看来,《香囊记》有卖弄学问、过分文雅的弊端,是文坛一大“害事”。他的这种认识是较具代表性的,后来王骥德《曲律》中也认为《香囊记》“以儒门手脚弄之”,而对南戏的后续发展起了不好的作用。徐渭认为戏曲作品与其“文而晦”不如“俗而鄙”,重在让普通百姓能够欣赏,体会其中真情。甚至,他不无极端地认为以“经、子之谈”融入诗歌尚且有待商榷,何况将之运用于符合大众口味的戏曲呢?同样,在《歌代啸》的“凡例”中他又重申:“此曲以描写谐谑为主,一切鄙谈猥事俱可入调,故无取乎雅言。”[13]1232由此可见,徐渭在对待所谓“雅言”的态度上是极为苛刻的,表面看来徐渭似乎借助否定“雅言”来否定文统,而实际上这正体现出了他文学思想辩证、通变的一面。在他看来,与时俱进、肯定世俗艺术恰是对“文统”的真正回归,在《奉师季先生书》中他说:“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13]458就是说以《竹枝词》为代表的民间歌诗是可以产生审美共鸣的,它的传播往往不以地域不同、文化差异为障碍,究其原因在于它是对国风传统的继承。因此,结合徐渭对《竹枝词》、《歌代啸》的肯定,以及对《香囊记》的否定,可以明显看出徐渭的基本审美取向。
袁宏道是继徐渭之后,另一位推崇民间文学的“革新派”文人,而且其基本观点亦带有徐渭影响的痕迹。徐渭年长袁宏道47岁,加之徐渭很早就扬名文坛,所以袁宏道对徐渭非常敬服,称其为“我朝第一诗人”[14]506,甚至“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14]770。在对待民间歌诗的问题上,袁宏道表现出与徐渭相似的主张,在写给徐渭的信中,他说:“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14]492袁宏道反对时人“以诗为诗”,而主张通过点化民间俗曲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很显然,他的这种倾向与徐渭对“雅言”的反对如出一辙。严格意义上说,袁宏道对“性灵”的强调,对通俗文艺的肯定,都与其对文学史的通透认识相关,《雪涛阁集序》中他说:“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14]709这种认识仍与徐渭的辩证文艺观异曲同工,甚至最终袁宏道不无极端地强调“宁今宁俗”,直言“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14]81。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袁宏道在继承徐渭“尚俗”思想的同时,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推进,很多认识较之徐渭更为彻底。
另外,上文提到了徐渭对以《竹枝词》为代表的民间歌诗持肯定态度,对此,在袁宏道这里也有体现。事实上,徐渭和袁宏道两人都十分热衷于《竹枝词》的创作,在徐渭文集中现存《竹枝词》31首,袁宏道文集中存26首。这些作品的共性特征是都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民间风味,“纵观徐渭和袁宏道的竹枝词创作,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刘禹锡的初创,在各自文人化与世俗化、社会化与个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个性的特色更加鲜明”[15]。由此可见,徐渭与袁宏道不仅在理论倡导层面,也在创作实践层面表现出十分相似的特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革新派力量在当时社会中的逐渐壮大。
四、革新派“尚俗”观的完善
我们知道,明代革新派阵营中除了徐渭、袁宏道之外,还包括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限于篇幅,下面着重讨论一位具有特殊性的人物——王骥德。
王骥德是徐渭的弟子,与徐渭相似,他不仅能够亲自进行戏曲创作,也具有十分深厚的理论素养,其《曲律》是明代戏曲理论的一座高峰,冯梦龙在《曲律叙》中如此评价王骥德及其《曲律》:“虽有奇颖宿学之士,三复斯编,亦将咋舌而不敢轻谈,韬笔而不敢漫试。”[16]47与何良俊《曲论》、吕天成《曲品》不同,《曲律》不仅涉及宏观的美学问题,也涉及具体的律学知识,体现了王骥德全面的音乐学素养,从音乐角度丰富了革新派的“尚俗”观念。在王骥德之前,明代戏曲实践异常繁荣,其中以汤显祖和沈璟为主要代表。临川派(汤显祖)主情,重视辞句上的通俗流畅,吴江派主律,侧重声律的和谐自然,在王骥德看来“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16]165,正是由于他看到了临川与吴江都存在弊端,所以王骥德试图调和这两种倾向。
王骥德的戏曲理论以推崇“本色”见长,其对“本色”的认识便带有鲜明的“尚俗”痕迹。这种观念导源于徐渭的影响,王骥德回忆称:“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虾》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釂,赏为知音。”[16]167-168徐渭与王骥德之间以“知音”视之,那么徐渭对“雅言”的反对,对“鄙而俗”的戏曲语言的肯定,必然影响到王骥德。事实上,王骥德亦多次表达了与之相类的看法,比如在戏曲语言方面,他说“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故吾谓: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16]160;在文采方面,他反对生搬典故,称“世有不可解之诗,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曲之不可解,非入方言,则用僻事之故也”[16]154;在艺术效果方面,以令村童野老能够理解为目标,“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须奏之场上,不论士人闺妇,以及村童野老,无不通晓,始称通方”[16]139等等。
但是,王骥德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尚俗而不滞俗。实际上,王骥德想要做的是处理好俗与雅之间的关系,一味“崇雅”容易流于机械模仿,片面“尚俗”则容易丧失文学性,前者以前、后七子为代表,后者以徐渭、汤显祖等革新派文人为代表,因此他说“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雕镂”。那么如何实现“本色”与“文调”的结合呢?在王骥德看来,获得“文调”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取决于内在丰厚的学养,另一方便也要在声律上下功夫。他说:
词曲虽小道哉,然非多读书,以博其见闻,发其旨趣,终非大雅。须自《国风》、《离骚》、古乐府及汉、魏、六朝三唐诸诗,下迨《花间》、《草堂》诸词,金、元杂剧诸曲,又至古今诸部类书,俱博搜精采,蓄之胸中,于抽毫时,掇取神情标韵,写之律吕,令声乐自肥肠满脑中流出,自然纵横该洽,与剿袭口耳者不同。[16]121
很显然,王骥德主张在广泛学习前人的基础上,配合自然声律,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事实上,王骥德强调的学养,与“尚俗”并不矛盾,他的意思是以点化、隐括等文学手段,以类似“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方式,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王骥德亦对声律知识非常熟悉,在《论宫调第四》中专门讨论了宫调的沿革、搭配等问题,在《论平仄第五》中讨论了平仄的配合规律以及演唱技巧,在《论韵第七》中分析了戏曲的用韵、押韵问题,在《论腔调第十》中总结了演唱规律以及唱与曲的配合问题,等等。总体而言,在声律问题上,他一方面重视戏曲在宏观层面的适合歌唱,推崇音声之自然,认为“纵横该洽”是声律的必要条件,对此,他以“本色当行”的概念进一步加以解释,在分析《荆钗记》时,他认为《荆钗记》由于里巷俗语过多而“粗鄙之极”,这方面固然难以与《琵琶记》、《拜月记》比肩,但由于其“用韵却严”,所以反而具有“本色当行”的特质,这恰是《琵》、《拜》不具备的。另一方面,在微观角度他亦非常重视声调与内容的契合程度。在他看来,“夫曲之不美听者,以不识声调故也。盖曲之调,犹诗之调”[16]122,这种主张显然有别于汤显祖,同时还认为“用宫调,须称事之悲欢苦乐,如游赏则用仙吕、双调等类,哀怨则用商调、越调等类”[16]137。很显然,内容、情感与形式、声调的和谐搭配是王骥德追求的终极目标,对此他在《曲律·曲源》中以“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加以概括。事实上,追求戏曲的“合律”、“文调”属性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王骥德《曲律》的重要特征,一方面这是调和临川、吴江的尝试,另一方面则回归了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审美特质。
虽然王骥德“曲之始,止本色一家”[16]121的主张,表面看来似乎与徐渭、袁宏道、汤显祖等人并无不同,但实际上王骥德对“本色”的认识则更加全面,其中既有“尚俗”的考虑,也有雅化的特征,既兼顾了辞句方面的自然性,又配以声律上的可唱性,既重视学识底蕴的重要性,也强调深入浅出的必要性,某种程度上这些特征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革新与复古的门户之见。综合来看,我们不仅可以将王骥德视为明代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甚至亦可将之看成是明代构筑“自然美学”的完成者。
[1]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校释[M].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杨荣.文敏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李开先.李开先全集[M].卜键笺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王艮.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7]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焦竑.澹园集[M].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9]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耿定向.耿定向集[M].傅秋涛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徐渭.《南词叙录》注释[M].李复波,熊澄宇注释.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13]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汪沛.徐渭与袁宏道“竹枝词”创作比较[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16]王骥德.曲律[M].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G].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Valuing Vulgarity”View of Reformist Literati in M ing Dynasty
Han Wei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25,China)
“Valuing vulgarity”is themain feature of the reform ist literati in M ing Dynasty,which takes literature and m ind philosophy as its basis.Conservatives such as Li Dongyang,the Former and Latter Seven W riters provide literary preparation while the“people's daily use”thought,which originated in Wang Yangming and completed in the Taizhou school,provides the ideological power.Theory advocacy and w riting practice by Xu Wei,Tang Xianzu,Yuan Hongdao etc.led the“valuing vulgarity”thought into depth,and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valuing but not stagnating vulgarity”by Wang Jide led it into perfection in the end.
M ing Dynasty;reformist school;vulgarity;literature;mind philosophy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18.3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ZW 001)、黑龙江省普通高校青年学术骨干项目(1254G031)、黑龙江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UNPYSCT-2015055)、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学者支持项目(SYQ 2014-01)。
韩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美学、文论。
I206.2
A
2017-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