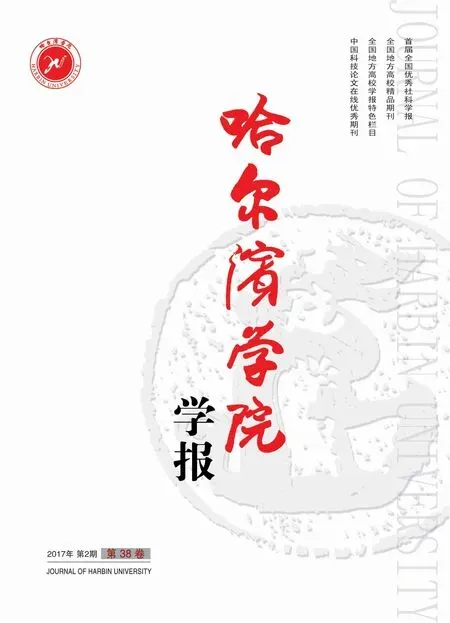论志怪小说对神话消歇的影响
2017-03-10王东辉
王东辉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论志怪小说对神话消歇的影响
王东辉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中国神话过早消歇人所共知,其消歇与定型几乎都集中在汉魏六朝这一时期,自此其主体结构几乎再未发生改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此现象的出现,盖因汉魏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兴起。由于时代背景及神话、志怪小说两者各自体式的因素,志怪小说逐渐替代了神话而蓬勃发展,神话再未突破既有模式并自此消歇。
神话;消歇;汉魏六朝;志怪小说
作为原始初民的集体口头创作,神话在历代传承的过程中,必然会被传承者依据自己的喜好、理解或传播的需要而加工改造。大体而言,神话的演变是由简入繁、自质朴到华美不断演进的。如希腊神话就是经过荷马、赫西额德的整理,再在后世的悲剧、喜剧中不断被加工演绎,整体结构才日渐成形,终成蔚为大观。中国神话的发展,大体也是由简单到繁复不断演进的。但中国神话尚未充分发展便已消歇。大体到汉魏六朝为止,中国主要的神话便停止发展,并基本定型。流传至今的神话基本保留着汉魏六朝的风貌,情节、人物等再没有新的发展,神话的历史影像就此定格。
通过几个经典案例,可以一窥中国神话演进的特殊风貌,发现其在汉魏六朝这一时期突然消歇的情况。
一、几种经典神话的演变
西王母神话形象演进的例子,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里面已有很详尽的阐述,不需赘述。概其形象演进,自《山海经》始,至魏晋而止,基本完善定型。西王母由一位近于怪的形象,变为一位颇具仙风母仪的神的形象,完成了定型,至今未变。
女娲造人。女娲这一神话形象最早见于《楚辞·天问》及《山海经》中。《楚辞·天问》中记载:“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这是屈原对谁是女娲形体创造者的发问,其暗含的前提应该是女娲为天地万物之始,鸿蒙之初的第一人。甚至可推测,《山海经》作者认为女娲造了人类,不过在他还没有明确提出女娲造人的神话。
时至东汉,在《楚辞章句》中,王逸对“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作注,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此时女娲的形象得到发展。女娲的形体如何,王逸明确地加以描绘,即“人头蛇身”。对比《说文解字》中“娲”字的解释,“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可以得知,这里“一日七十化”中的“化”,指的应是“化生”“生育”的意思。女娲一天化生七十种生物。这如同基督教中的上帝,第一天造出白天黑夜,第二天造出天空、云和风,直到第六天造出人来。至此,女娲创造万物的神话故事有了具体的记载。
应劭著《风俗通义》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者絙人也。”这里,应劭不仅明确地提出来女娲造人的丰功伟绩,甚至连为什么会有富贵人、贫贱者的区别,都给出了解释。这虽已剥离了神话初始的面貌,而掺杂了封建的阶级观点,但它变得比以前更为生动传神,相较于之前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然而,女娲造人的神话并没有沿着这条路子继续前进,没有再增添内容、丰富细节。而是就此止步、定型,直至今日,其故事架构还保留着《风俗通义》中的形态。
共工触山。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妇孺皆知。关于共工的神话发展,先看文献中的几条记录: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山海经·大荒北经》)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山海经·西次三经》)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天文篇》)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颓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
可见,在《山海经》里面,共工与不周山并无牵连,其中介绍了共工所居之处即“共工之台”,不周山的地理方位等,但不曾见共工怒触不周山的记载。到了汉代,共工的神话便进一步发展,他同不周山也有了联系。《淮南子·天文篇》交代了共工触山的原因,即“与颛顼争为帝”,触山所引起的后果,即“天柱折,地纬绝”。相对于春秋战国之时,在汉朝这一历史阶段,共工神话的发展已经相对完备。《列子·汤问》虽托名列御寇,实应是晋人所做。藉由此可见,到了晋朝,共工的神话在“怒触不周山”的基础上又前进一步,同“女娲补天”的神话融合在一起,把共工触山之前“天”的状态作了交代,告诉我们在他触山导致“天倾西北”之前,天是不足的,是被女娲补好的。虽然两个神话在此粘贴的痕迹还是清晰可见,但神话毕竟朝着熔铸、整合的方向发展,出奇的是共工的神话就此止步,直到今天,我们所认知的共工神话依然只有“怒触不周山”这一伟迹,其他神圣之事以及同别的神话人物之间的关系再未有新的发展。
此外,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流传至今的经典神话,虽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引用,但其故事的基本架构无一不是在汉魏六朝这一时期定型,并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几乎再未发展。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盖神异之说,晋以后尚为人士所深爱。然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熔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
二、神话在汉魏六朝消歇的原因
关于神话消歇的,茅盾认为源于文人对神话的历史化修改:“他们抄录的时候,说不定也要随手改动几处,然而想来大概不至于很失原样。可是原始的历史家以后来了半开明的历史家,他们却捧着这些由神话转变来的史料皱眉头了。他们便放手删削修改,结果成了他们看来是尚可示人的历史,但实际上既非真历史,也并且失去了真神话。所以他们只是修改神话,只是消灭神话。中国神话之大部恐是这样的被‘秉笔’的‘太史公’消灭了去了。”[1](P16)
“历史化”的观点为茅盾之后的神话研究学人沿用不绝,尽管这一理论有其部分的合理性,然而神话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消歇的原因仅以“历史化”的说法来解释,显然过于单薄,论证并不充分。例如,女娲这一形象,虽然在应劭之前就被归入“三皇”,完成其历史化的过程,但这并不妨碍其“抟土造人”神话的演进。并且它是以造物者的神话形象,而不是历史化的形象完成消歇。其他如共工、嫦娥等,都不是以历史化的形象而消歇。此外,神话历史化的观点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神话会集中在汉魏六朝这一历史时期突然消歇。所以,除去“历史化”的原因之外,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神话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消亡。
对于神话的消歇,鲁迅先生的观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认为神祇、人鬼同为世人所膜拜敬仰,神鬼信仰的杂糅,阻碍了神话的发展。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2](P10)
尽管鲁迅先生所陈述观点并非用以解释神话在汉魏时期消歇的原因,但藉由此论,我们也许能得到一些启示。汉魏六朝时期宗教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佛、道二教渐为流传,鬼神之说大为盛行,神话在传播的过程中与志怪作品渐相杂糅。在慕神求仙、称道鬼神的时代背景下,神话的文学地位被志怪作品悄然侵蚀、替代。汉魏六朝时期,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就是志怪小说的兴起。笔者认为,志怪小说的兴起是造成神话突然消歇的重要原因。
“志怪”,作为一种记录怪异神奇的非文体创作活动,源自先秦,语出《庄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化,至汉魏时期而发展成文体的“志怪小说”。“汉魏六朝既是志怪小说创作的肇始期,又是兴盛期,同时又是对后世志怪小说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3](P14)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有的炫耀地理博物,有的讲述鬼怪灵异,前者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等;后者有干宝所著《搜神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及托名陶潜的《后搜神记》等。此外,还有的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尽管此时志怪作品多有散佚,但还是可以一窥汉魏志怪小说蓬勃发展的风貌。这一时期的志怪作品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创作技巧也有很大的突破。相对于“志怪”,“志怪小说”在内容的丰富性与创作技巧的完善上有了较大发展。虽然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还能看到“志怪”的孑遗,但“志怪小说”的成长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神话与志怪作品,二者都记述神异不常之事,各自都建构了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并在这个超现实的世界中给予世人希望与安慰,使世人的好奇心理得到满足。但为什么志怪小说的勃兴造成了神话的消歇呢?
首先,神话受志怪小说的影响而消歇,同此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自汉以后,佛教、道教逐渐盛行,鬼神迷信之说盛行,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这就是志怪小说兴起的背景。东汉以后,佛教、道教之说逐渐流布,世人对神仙方术倍加推崇,于是阴阳卜筮、精怪灵异之说大行其道。神话虽亦记神奇之事,然而同时代需求并不相符,既不能作为方士宣扬得道升仙的佐证,又不能喻诫幽明殊途,传播惩善扬恶的观念。加以时代高古,故不如以搜奇记逸为主的志怪作品更为人所喜闻乐见。
汉魏六朝时,神话经过不断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文人的加工,神圣化、道德化成为其重要特色。无论是女娲造人、后羿射日,还是神圣如黄帝、母仪如西王母之类,大都雄奇烂漫,其神话形象都庄严神圣不可侵犯。即便如刑天——同黄帝争帝的败北者,不但未受后世成王败寇观念的影响,相反,却被涂上一层坚韧奋进的色彩,而被人赞扬。如陶渊明《读〈山海经〉》中就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而魏晋六朝时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士人百姓多罹其苦,生离死别乃是人之常事。思想上,自西汉奠定的儒家一统的局面被破坏,而变为儒、释、道三家并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更愿意相信仙界神都以逃避现实的残酷,用命运无常来解释生命的短暂,用神奇鬼怪来抵抗名教的虚伪。神圣化、道德化的神话故事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而志怪小说搜奇记逸,或记方士导引服食、远年却老,或写妖祥卜梦、精怪灵异,或写人、神、鬼的交通恋爱,更契合社会现实的需求,故能蓬勃发展并取神话而代之。
其次,神话受志怪小说的影响而消歇,亦同二者体式相关。古代典籍中的神话,多记述简略,趣味淡薄,更类于“志怪”,而不是“志怪小说”。如上面提到过的《楚辞·天问》中,对女娲的记载只有“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抱朴子·释滞》中更是简单地记载为“女娲地出”四个字。其他如保存神话最为丰富的《山海经》,其记载神话的内容,少则十几字,多则几十字而已,直白叙事,乏修饰,少细节,可读性不强。反观志怪小说则篇幅体量增大,多有叙事曲折、语言生动的作品,可阅读性强。如《搜神记》中“秦巨伯斗鬼”,先写秦巨伯醉酒遇鬼,二鬼诈为巨伯之孙殴巨伯;再写巨伯佯醉捉鬼,执火灸之几死,而鬼又逃走;最后写巨伯佯醉,遇孙,谓是鬼而杀之。[4](P198)如这样曲折动人的作品,同简言辞而少滋味的神话相比,明显鲜活生动许多。
另外,神话记载错简混杂,舛误颇多。如“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虽名声昭著,但具体指的是那些人物,典籍记载多有不同。对于“三皇”的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天皇、地皇、泰皇”。《风俗通义》中,应劭更是列举了《春秋运斗枢》《礼号谥记》《含文嘉》《尚书大传》等书中不同的记载,分别有“伏羲、女娲、神农”,“伏羲、祝融、神农”,“虙戏、燧人、神农”,“遂人、伏羲、神农”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5](P2)“五帝”所指,也有“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及“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多种说法,其所在历史年代顺序也多不同。其他如,射日之羿同有穷之羿是否为同一人的问题,伏羲同女娲的关系问题等,都是神话母题混乱的例子。
所以说,中国古代神话不仅“简”,而且“乱”。混乱淆杂的神话故事,不仅在阅读过程中使人迷惑丛生,同时也增加了整理加工的困难。神话人物及相互关系的错杂,让著述者很难把握到一条清晰的脉搏。与此相反,志怪小说则几乎没有这些负累,脱离了神话题材的束缚,或述逸闻,或记奇怪,天南地北,海内海外无所不包。其创作发挥的自由程度,较之加工神话要大的多。另外,志怪小说所记多为当世或近世之事,既生动鲜活,又征实易信。如《风俗通义·怪神》“世间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语声气”条、“世间多有伐木血出以为怪者”条,其内容就是当时为民间所迷信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变体至今依然不绝。如此贴近生活的故事,显然比高古简乱的神话故事更具吸引力与生命力,更容易实现人们好奇心理的满足与释放,更容易得到传播与流布。
综上,志怪小说在汉魏六朝的兴起,截断了神话发展的径流,致使其在这一时期突然消歇。之后,志怪作品一路发展,影响后世,而神话再未突破原来的模式获得新生。神话的消亡,固然令人扼腕,但文学自有其发展的规律。志怪作品搜奇记逸的传统为后世继承,从唐传奇到《聊斋志异》,历代演绎不绝。中国古代志怪文学的发达,在世界文学史上一枝独秀,这怎能不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园林里结出的硕果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可以说是文学一大幸事。
[1]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王连儒.志怪小说与人文宗教[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4]干宝,汪绍楹.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应劭,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张 庆
The Influence of Mythical Stories on the Declining of Myth
WANG Dong-hui
(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400,China)
It is known that myth had been declining. The declination of my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totypical myth happened in the Han-Wei period. Since myth stopped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This is a unique literary phenomenon. Han-Wei saw the prosperity of mythical stories. Due to the temporal background and the style factors of both myth and mythical stories,mythical stories developed fast and took the place of myth. Myth failed to make a quality breakthrough and then declined.
myth;declination;six dynasties from Han to Wei period;mythical stories
2016-06-07
王东辉(1987-),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1004—5856(2017)02—0083—04
I206.2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