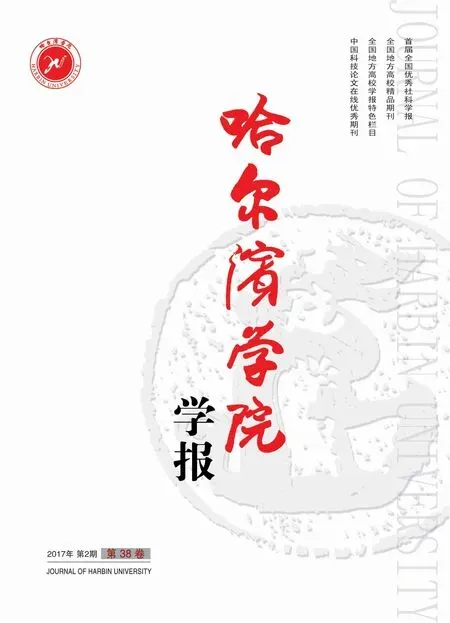《幼学琼林·文事》四家注补正
——书写制度与书写材料的误读
2017-03-10李宝
李 宝
(哈尔滨学院 文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幼学琼林·文事》四家注补正
——书写制度与书写材料的误读
李 宝
(哈尔滨学院 文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幼学琼林》“文事”部有诸条涉及中国古代书写材料与书写制度的文字,各家注释多有疏漏之处,亦有意犹未尽之感。文章对其中涉及的“缣缃”“黄卷”“寸楮”“操觚”等注释进行了补正。
幼学琼林;古代书写制度;古代书写材料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编写的最好、影响最大的蒙学读物之一,昔人曾对它有过很高的评价:“读过《幼学》会看书,读了《幼学》走天下”。自这本书诞生之后,代有人为其注译、增补,特别是近几年“国学”大热,注家蜂起,质量比较好的有如下几种:曹日升、谢胜文译注《幼学琼林》(岳麓书社,2006年,以下简称岳麓本);王诒卿注解《幼学琼林精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人民文学本);李正辉、刘洪霞注译《幼学琼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中州本);刘志伟、孔留根注释《幼学琼林诵读本》(中华书局,2013年,以下简称中华本)。本文所论,即以这四家所注“文事”部为主。
注译古文,劳心劳力,由于涉及知识包罗万象,任何注家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幼学琼林》“文事”部涉及多条关于中国古代书写材料与书写制度的文字,各家注释均可圈可点,但仍有疏漏,本文试举几例探讨之。
“缣缃”“黄卷”,总谓经书,“雁帛”“鸾笺”,通称简札。
人民文学本、中州本、岳麓本注释“缣缃”为合注,中华本为分注,似分注较合理。因为“缣”“缃”并非同物,更重要的是颜色有区别。据《说文解字》,只有“缃”明确记为“帛,浅黄色也”,[1]“缣”并没有明确说是什么颜色,所以笼统注释“缣缃”为“供书写用的双丝织的微带黄色的细绢”并不确切。中州本注释为“书写用的绢帛”已然可以,但合注后,又分注“缣”“缃”,其中注释“缣”为“双丝织的浅黄色细绢”,不知这个“浅黄色”从何而来,遍查字书,均未获见。所以,中华本分注为“缣,用来书写的白色细绢。缃,包书的黄色细绢”较为合理。另外,人民文学本、中州本和岳麓本注释“缣”都提到“双丝织”的问题,查考《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缣”字条:
许慎:缣,并丝缯也。马叙伦:钮树玉曰,《广韵》引同,《玉篇》注无“并”字,盖脱。沈涛曰,《龙龛手镜》引无“并”字,乃传写偶夺。沈乾一曰,唐写本《玉篇》引作兼丝缯也。又引《释名》:缣,兼也,其丝细致,数缣于布绢也,足以证兼丝缯之义,今作“并”者,乃形近之。伦按,高山寺《玉篇》引作兼丝缯也,盖本作兼也,以声训。并丝缯也,《字林》文耳,字见《急就篇》。[2]
综上可知,三家注“缣”为“双丝织”,有可能依据《说文解字》或者《广韵》“并丝缯”得出。然据上引马叙伦先生考证,《玉篇》《龙龛手镜》等并无“并”字,沈涛认为是“传写偶夺”,沈乾一引唐写本《玉篇》《释名》,认为是“并”与“兼”形近而误,马叙伦先生按语基本同意沈乾一观点。如此,则三家注“双丝织”并不确切,中华本注为“细绢”最合“其丝细致,数缣于布绢也”之义,言简而意赅。
关于“黄卷”注释,中州本所引《宋景文笔记》卷上:“古人书写,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或曰:古人何须用黄纸?曰:檗染之,可用辟(避)蟫”最为广泛流传,也最确切。杨金萍有专文[3]论述古书“入潢”技术,可参看,兹不赘述。中华本注释最为轻佻,“古人用辛(苦味之物)染纸成黄色”。按惯例,括号内为解释之前文字的说明,去除括号并不影响文句通畅,然此处若除去,则变成“古人用辛染纸成黄色”,文句已然不通,况“辛”并非“苦味之物”,此处所用括号匪夷所思,恐“辛”为“檗”之误,如此,则文句通畅,括号解释自然。
连篇累牍,总说多文;“寸楮”“尺素”,通称简札。
“牍”的释义,中州本和中华本均未单独出注,人民文学本注释“牍”为“古代写字用的竹、木简”,岳麓本注释“牍”为“书版”。关于简牍形制与名称,张显成先生《简帛文献学通论》一书中有详尽的考述,转引如下:
《说文·竹部》:“简,牒也,从竹,间声。”段玉裁注:“《片部》曰:‘牒,札也。’按:简,竹为之。牍,木为之。牒、札,其通语也。”又,《片部》:“牍,书版也,从片,卖声。”段玉裁注:“按:牍专谓用于书者……古人多云尺牍……《木部》:‘椠,牍朴也。’然则粗者为椠,精者为牍。颜师古曰:形若今之木笏,但不挫其角耳。”又,《片部》:“牒,札也。”段玉裁注:“按:厚者为牍,薄者为牒。”总的来说,简,就是竹制书写材料——经过加工的竹片;牍,就是木质书写材料——经过加工的木片,故书于竹者谓之简,书于木者谓之牍。因为“简牍”常连称,故木牍也可称简,或称木简。[4]
显然,张先生认为,简和牍的主要区别是书写材料,简,是竹制书写材料,牍,是木质书写材料。然而,林沄先生在《古代的简牍》一文中,通过对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考索,又认为“简和牍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质料,而在于形状。简是狭长的薄片,可以编连成册。牍是宽厚的版,宜于单件使用。简在起源上很可能是先有竹简,因为竹子容易加工成狭长的薄片。后来才有用木仿制的。牍多用木制,但也有竹制的”。[5]综合诸家所论,大意有此两种观点。如此,无论是书写材料还是形状,虽然简和牍常常连用,但简和牍不是同样的东西,这大概已成为学界公论。所以,人民文学本注释“牍”为“古代写字用的竹、木简”似不是很准确。岳麓本注释为“书版”比较精准。
关于“寸楮”,四家所注,均无问题。楮纸又称楮皮纸,是采用楮树皮纤维所造的纸,两晋时期楮纸即被广泛使用,至唐代流行颇广,文人墨客戏称为“楮先生”,《幼学琼林·器用》即有“纸号‘楮先生’”之谓,至有“败楮遗墨人争宝,广都市上有余荣”的赞誉。据学者考证,现存最早的印刷品,1966年出土于韩国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即为楮纸印制。[6]
但岳麓本在注释完“寸楮”之后,进一步注释“楮,木名,亦称榖树。皮可制桑皮纸,因以为纸的代称”则有点问题。楮树皮所造纸称为楮纸或者楮皮纸,不太可能称为“桑皮纸”。中国古纸中确有桑皮纸,但系用桑皮纤维为原料制成,此两种纸均为晋代纸名,但所用材料截然不同,似乎没有通称之先例。[6]
邪说曰“异端”,又曰“左道”;读书曰“肄业”,又曰“藏修”。
各家注释“肄业”为“研习、学习”均无误,但人民文学本也提到“肄业”今意一般指“在校学习而未毕业”。
查考《古文字诂林》,对“肄”字,前辈学者做了充分的考释工作,学界目前基本认定“肄”和“肆”在古文字中属于同一个字。如徐协贞《殷契通释》卷五:
肄、肆实为一字,特字形之变耳,许书分肄、肆为二,非也……《周礼·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郑注:“肆,陈骨体也。”引《士丧礼》曰:“肆,解去蹄。”……观上各训,均谓祭祀时杀牲解体而陈尸以祭之礼也。《论语》“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注,“肆,陈尸也,”与此肆意亦同。[2]
王蕴智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对“肄”和“肆”这两个字的联系与分化进行了论述:
周代以后,祭之礼不复存在,这一时代色彩浓重的字形亦失本谊,字音有变,异体并生。《说文》部不仅有肄字,另于长部还存有肆字。肄字下训“习也”,肆字下训“陈也”。训“习”乃周秦时期的一种假借用法,训“陈”(布陈)则是古字杀牲陈之以祭本谊的自然引申,这一用法古书中多以肆字表示。[2]
如此,“肄”和“肆”这两个字虽字形有异,但乃一字分化当属无疑。这两个字在使用过程中,其字义是否会互有影响?肄字是否也有训为“陈也”的时候?或者后世在使用过程中望文生义,将虽属同源但已经分化的“肄”和“肆”的释义混淆使用。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理解“肄业”从“研习、学习”转变为“在校学习而未毕业”大概就会顺畅得多。众所周知,“业”原义指“大版也”,是古代木质的书写材料,一般称为牍,与竹简合称为“简牍”。随着尺寸的大小,木牍有不同的专名,如一尺见方的牍称为“方”。“木版如果再做得大一些,就叫做‘业’。现在学生在上学的过程中有‘肄业’、‘毕业’的说法,这种说法是行古代的书册制度演变而来的。所谓肄业,原义是指读大版子书,毕业则指大版子书读完了。”[7]如果我们把“肄”字训为“陈也”,“肄业”是否可理解为把大版子书放在那里,没有读完就放在那里,这与今天的“在校学习而未毕业”意义就很接近了,忽发奇想,不知可否备此一说。
作文曰“染翰”“操觚”,从师曰“执经”“问难”。
诸家释“翰”均为笔,大意不错。考《说文解字》:“翰,天鸡赤羽也。《逸周书》曰:‘大翰若翚雉,一名鷐风。’”[1]从此意引申,又有羽毛之义。左思《吴都赋》:“理翮整翰,容与自玩。”进而引申,遂有毛笔之意。曹丕《典论·论文》:“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所以此处将“翰”释为毛笔应该更为确切。
人民文学本、岳麓本、中华本释“觚”均为“木简”,中州本释为“简”。其实,在古代,木制书写材料有多种名称,如方、版、牍、觚、槧、檄等。古时多把方、版、牍统称木简,在解释上也彼此通用。但“事实上,方、版、牍三者是不应当混同的,它们在名称上不但有所区别,就是在形制、功用上也是有很大差异的。”[8]“觚”在形制与功用上与上述其他三者差别更大。李更旺先生曾有专文考析,今转引如下:
根据古籍记载和后人考证,方,又名觚。《汉书·酷吏传》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觚,方也。’”《后汉书·杜林传》李贤注云:“觚,方也。”《文选·陆机文赋》注云:“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书,犹今之简也。”《史记·酷吏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应劭云:‘觚,八棱有隅者。’”颜师古《急就篇·急就奇觚与众异注》说:“觚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苏颚于《苏氏演义》中也说:“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或以六面或以八面皆可以书,以有圭角,故谓之觚。”[8]
在出土的书写材料中,也多有觚的实物出现。《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载《敦煌汉简》附录)中称,“觚,形制较复杂,多数为等腰三角形,长与简同,文字书写于等腰两侧,其用途多作官府正式文书,即‘檄’的书写材料;除此,还有四棱形和不规则形,长度不等。四棱形的觚,四面或三面书写,多为《仓颉篇》、《急就章》等字书。”[9]
所以,觚虽然如颜师古所说“盖简之属”,释觚为“木简”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知道觚和简还是有区别的,林沄先生说,“或许……称为觚牍,更为周到一些”。[5]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李圃.古文字诂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3]杨金萍.从“妄下雌黄”谈古书的“入潢”与“灭误”[J].中医文献杂志,2003,(3).
[4]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林沄.古代的简牍[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1).
[6]刘仁庆.中国古纸谱[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7]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李更旺.古书史中竹木制书写材料考析[J].文献,1986,(1).
[9]甘肃省文物研究所.敦煌汉简(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
责任编辑:李新红
Four Versions of Annotations to “Collected Readings for Children·On Writing”: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Misinterpretations on Writing Regulations and Materials
LI Bao
(Harbin University,Harbin 150086,China)
In “Collected Readings for Children”,there is a part,called “On Writing”,concerning writing regulations and materials in ancient China. It seems that the annotations are not quite enough to understand it clearly. Additional annotations and corrections are made to explain “jianxiang”,“huangjuan”,“cunchu”,and “caogu”.
“Collected Readings for Children”;ancient writing system;ancient writing materials
2016-06-27
李 宝(1979-),男,吉林大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1004—5856(2017)02—0080—03
I106;H109.3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