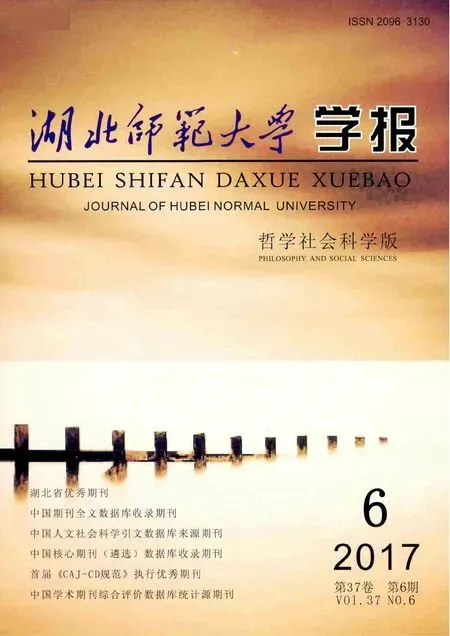创伤叙事、疾病叙事之比较研究
2017-03-10秦海涛
蔡 祎,秦海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湖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创伤叙事、疾病叙事之比较研究
蔡 祎,秦海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湖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20世纪以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关于疾病和创伤的书写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创伤叙事和疾病叙事作为两种全新的叙事方式,也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分析之中。然而两种叙事方式间的界限并不明晰,存在着交叉重合的地方,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含混模糊之处。本文通过对创伤叙事及疾病叙事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进行回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厘清两种叙事方式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创伤,创伤叙事,疾病,疾病叙事
1.创伤叙事的渊源与发展
1.1 创伤与创伤理论
关于“创伤”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与工业事故创伤相关的临床医学和19世纪末的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后渗透到文学、哲学、历史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陶家俊,2011)
创伤理论的发展可以梳理为以下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心理创伤的研究,这一阶段关于“创伤”的探索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框架和概念的雏形,其代表人物有夏科、贾内、弗洛伊德和美国精神病学家亚伯拉罕·卡丁那。弗洛伊德最早将“创伤”引入精神分析领域的研究。在《歇斯底里研究》(1895)一书中,弗洛伊德首次阐释了“创伤”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一跃成为现代创伤研究起点的原因在于此研究以一种新的症候形式描述了焦虑记忆所带来的不可控制的后果。(Parziale,2013)在《精神分析引论》(1917)一书中,弗洛伊德进一步提出了“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es)这一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创伤研究主要聚焦于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即“炮弹震荡”(shell shock)。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一书中,弗洛伊德写道:“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大量的这样的疾病(指‘创伤性神经官能症’),不过,它至少结束了人们试图把精神错乱归因于神经系统器官的损害……”。(李桂荣,2010:18)这一时期的创伤研究旨在分析战斗神经官能症与患者道德人格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受害者康复。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越南战争退伍军人以及大屠杀幸存者受到的精神创伤和证词进行研究。这一阶段的创伤研究关注历史、文明、宗教等等对于人的心理影响(洪春梅,2014),标志着创伤研究从精神分析领域转向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代表人物主要是凯西·卡鲁斯,之后,朱迪思·赫尔曼、苏珊娜·费尔曼、杰弗里·哈特曼以及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丰富了卡鲁斯的创伤理论。卡鲁斯(Caruth)认为,创伤在战争中表现的最为普遍和明显,只是表现的症状分别以不同的名称命名,比如“炮弹休克”或“弹震症”、“战斗疲劳症”、“创伤后紧张综合症”或“延迟压抑症”等。(Caruth,1995:1)拉卡普拉(LaCapra)进一步对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进行了区分。历时性创伤一般是指历史事件所引发的,如大屠杀、奴隶制、种族隔离等; 而结构性创伤通常指超越历史的失落,如与母体分离,进入语言象征系统,不能完全融入集体等。(王欣,2013)这种区分可以避免将历史性创伤泛化为结构性创伤,防止淡化与创伤相关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避免将结构性创伤的原因“神秘地归因于某一事件,推定其为创伤产生的原因(LaCapra,2004)。
第三阶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创伤研究从精神病临床实践转到历史、文学、哲学和文化研究以及批评理论等人文领域,关注性别、种族和战争创伤的公共政治话语,与当代文化研究的热潮合流,聚焦于当代历史与文化中的创伤,汇集后殖民思潮、女权主义、后结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形成了薪为壮观的研究热潮(洪春梅,2014)。随着创伤概念意义的不断丰富,创伤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在当代社会的核心内涵: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这些行为影响受创伤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导致其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其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王庆蒋,苏前辉 2015)
1.2 创伤叙事的范畴与意义
在《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中,李桂荣(2010)将“创伤叙事”定义为“对创伤的叙述”,“对创伤时间、创伤影响、创伤症状、创伤感受、创伤发生机制等的叙述。”在区分文学中医学性创伤和文学性创伤的基础上,李(2010)提出了医学性创伤叙事和文学性创伤叙事的概念。医学性创伤叙事是对科学性创伤的叙事,其叙事依据事实,叙事并不能改变事实本身,其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如实记录病人的情况以适应治疗、适应研究单位的制度要求,并以此作为研究病人情况、对症下药和进行科学研究的依据等;而文学性创伤叙事则是对文学性创伤的叙事,其主题广泛,既可以以人类历史题材或个人经历为根据,叙述历史上导致人体身心受创的真实事件,也可以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后现代以来,在文学作品创作及文学作品研究中,大量的文学文本所用的“创伤”概念主要特指由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王庆蒋,苏前辉 2015),因而更偏重于文学性创伤叙事。
文学性创伤叙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性创伤叙事为创伤的疗治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弗洛伊德率先认识了叙事的心理学动力能量,指出叙事具有引导意识、激发潜意识的双重功效,提出了运用“谈话疗法”(talk therapy) 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案。(刘荡荡,2012)当代叙事学认为,“叙述是讲故事的行为或活动本身,而被表述出来的故事为之叙事”,于是,叙事作为当代展示创伤的方法被广泛应用。小说家通过模拟创伤场景使创伤者再次回到创伤发生的历史瞬间,重构过去可以帮助创伤幸存者实现由潜意识转化为意识的历程,使创伤得以医治。(李曼曼,汪承平,2012)
其次,文学性创伤叙事为边缘群体发声提供了一种可靠方式。创伤叙事关注战争、大屠杀、奴隶制、殖民化、种族歧视等多种因素给个人及集体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创伤的受害者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创伤叙事以其特有的方式给予边缘群体以关注,为其抒发内心情感、表达群体诉求、寻求社会关注及帮助提供了有效途径。
最后,文学性创伤叙事通过对创伤事件的描述能够对读者起到启迪和教化作用。创伤叙事充分发挥创伤对人的心理的作用机制和对人的心理影响力,以创伤为媒介,创作出更发人深省的作品。文学性创伤叙事的思想意义和社会功能使其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创伤叙事都能更好地起到警示、感染、触动、教化和引领作用。(王庆蒋,苏前辉, 2015)
2.疾病叙事的渊源与发展
2.1 疾病与疾病文学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苏珊·桑塔格,2003)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时常受到疾病的困扰,根据《剑桥疾病史》,疾病是随着人类聚居的脚步日渐肆虐的。人类由部落聚居,到村落、城市的形成,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生活环境却趋恶化,导致了疾病的频频爆发。(刘明录,2013)
文学中的疾病从來就不会仅仅等同于医学中所指的疾病,疾病的产生和发展被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思维的印记,它的发展变迁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文化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变成了承载社会文明、文化的载体,反映出作家同时代的社会风貌(刘明录,2013)。在《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叙述研究》一文中,刘明录(2013)对文学史上疾病内涵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在古希腊时期,由于人们对疾病认知的有限性,往往将疾病归因于不可抗拒的神谕和强大的自然力,疾病代表着难以预测的、难以克服的恐惧,被视为一种惩罚,后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疾病做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将其归因为身体机能问题,但人们大体上仍将疾病视为一种神谕;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个人及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病理生理学的发展淡化了疾病的神秘色彩,同时,疾病的自然环境归因逐渐降低,人们开始关注疾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文艺复兴之后,疾病的象征不断泛化——浪漫主义时期,疾病象征着优雅美丽,现实主义阶段,疾病被视为苦难的象征,疾病成为了作家鞭挞社会丑恶,倾诉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工具;20世纪70、80年代艾滋病等疾病肆虐造成大量人员病亡,疾病更是大量出现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作品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同时,疾病和文学也因作者的特殊身份联系起来。一方面,作为创作主体,许多作家都曾患疾病,在与疾病顽抗的过程中,引发了他们对于人生深邃的思考,疾病给他们带来灵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一些作家本身就是医生,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真实的素材,同时自身的病理学知识为其疾病的描述增强了可靠性。
2.3 疾病叙事的范畴与意义
疾病叙事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源于社会对一些疾病(如艾滋病)的宣传和恐惧的日益加重,以及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度越来越高。疾病叙事在90年代以后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形成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它是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的特征之一。(唐伟胜,2012)亚瑟·克兰曼(Kleinman,1988:3)指出:“疾病叙述就是与疾病相关的描述或陈述。狭义上的疾病叙述仅指病人对于自身疾病的描述或陈述;广义上的疾病叙述则泛指文学作品中与疾病相关的描述或陈述,这种描述或陈述不仅仅止于疾病本身,还包括病人、与病人相关的医疗服务、家庭成员、人们对于病人的反应等方面。”
当前疾病叙事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
一类是疾病叙事在人文医学领域的研究。
戴维·赫尔曼等将疾病叙事分为三类:一是病人讲述自己的疾病和痛苦,以及重建被疾病摧毁的身份;二是医生使用叙事归纳、传播医疗知识;三是作为治疗工具的叙事,即在医院使用叙事辅助治疗。在此划分基础上,唐伟胜(2012)探讨了叙事学与人文医学的视域融合,表明在叙事学与人文医学的界面上有着众多尚待开垦的领域。杨晓霖(2014)在叙事医学和医学人文的情感转向这两大理念基础上,提出将医学叙事文本按照创作方式分为虚构疾病叙事和非虚构疾病叙事两大类型,并按照作者身份分为文学疾病叙事、自我病情书写和医生病理书写(平行病历故事),同时探讨如何将叙事学基本知识融入疾病叙事阅读中,切实引导医学生提高医学叙事能力,达到医患视域融合和医患沟通效果最佳化。
另一类是在文学领域内的研究。
在文学领域,疾病叙事的研究范围较广。在理论层面上,安·霍金斯(Anne Hawkins)在《疾病重构:病志研究》(Reconstructing Illness: Studies in Pathography)(1997)一书中,分析了病志作为一种新的疾病叙事体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只有当医生和患者的声音都被听到时,才能找到真正的治病良方。”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A Metaphor)(1978)一书中对疾病的隐喻意义进行了研究,她对疾病的隐喻持一种否定和批评的态度,其创作意图在于“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桑塔格,2003)从疾病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式来看,疾病叙事包括对疾病进行叙事和书写的文本以及病患作家和医生作家的创作等。从疾病书写的目的来看,安·霍金斯区分了四类疾病叙事:一是教育类(didactic)疾病叙事,旨在帮助患有相同疾病的病人或者提供经验教训;二是愤怒类(angry)疾病叙事,旨在表达对现行医疗体制或者机构的不满;三是另类疗法(alternative)疾病叙事,旨在探索医院正规治疗之外的治疗方法;四是生态(ecopathography)疾病叙事,旨在思考疾病与环境、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唐伟胜,2012)从疾病叙事的文体形式来看,包括病志,医嘱体和病人日记体等。病志指的是“患病的叙述,作者通常为病人或病人的亲友”(琼斯,2000)医嘱体是指作家以医生的心态自居,使用与疾病相关的语句构筑读者视野中的病态世界,在句式上采用祈使句或命令句的语式,表现医生的权威(郭棲庆,2016)。病人日记体是以病人视角、日记形式架构全篇结构的文体形式”(宫爱玲,2014: 103)
3.创伤叙事与疾病叙事的相异与相同之处
纵观创伤叙事和疾病叙事的研究,可以发现两种叙事方式之间存在很多相同和不同之处,下文将从这两个宏观方面进行微观的对比分析。
3.1 相异之处
创伤叙事源于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最初用于研究人所经历的心理创伤,后随着一战、二战和越南战争的爆发,逐渐从精神分析领域转向历史、文学、哲学、文化研究、批评理论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其发展具备完备的体系。同时,由于创伤叙事主要从精神分析领域衍生而来,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离开精神分析的指引,或多或少带有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特征,因而创伤叙事相较于疾病叙事而言更注重心理和精神层面,即更多地关注心灵所遭受的创伤(psychological trauma),以及更为抽象意义上的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民族创伤(national trauma)和历史创伤(historical trauma)。
疾病意象在文学中由来已久,其发展变迁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文化相联系,承载着社会文明,反映时代风貌,但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叙事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源于社会对一些疾病的恐惧以及对健康的日益重视,并且是90年代以后才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很多理论尚未得以建构,因而现阶段的疾病叙事主要侧重于分析文学作品中的疾病意象或患病作家的文学创作,其研究也主要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分析,研究范围不及创伤叙事广泛。但是,从现阶段疾病叙事的研究来看,疾病的内涵较创伤更为丰富,不仅包括创伤叙事中心理层面的创伤,即心理疾病,同时也包括生理上的疾病。
3.2 相同之处
尽管创伤叙事和疾病叙事起源时间、发展背景和研究范畴不尽相同,但两种叙事方式之间仍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疾病叙事和创伤叙事在研究内容上有所重合;两种叙事方式都被赋予隐喻意义,由此增添了作品的思想内涵;都存在一定的虚构性;并且都作为一种疗救方式而存在;最后,两者都属于“身体叙事的范畴”,下面将逐点进行分析。
3.2.1 精神和心理创伤/疾病的重合
如上文所提及,疾病叙事和创伤叙事在研究内容上有重合之处,主要体现在心理创伤(疾病)和精神创伤(疾病)的研究上。郭棲庆(2016)在以《夜色温柔》为例分析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时,分析了“炮弹休克(shell shock)”,指出“炮弹休克症实质上是一种‘创伤性神经病’”,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人们经受了诸如战争和重大事故之后,如果不能应付强烈的情绪体验,便会形成‘创伤性神经病’,这种病症主要表现为对创伤当时情境的执着,病人无法从中解脱”(弗洛伊德,1997: 216)。由此可见,作为创伤的一种表现形式,“炮弹休克”在此文中被归到疾病的范畴;同时,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个体遭受强烈的威胁性、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出现的精神障碍,它以对创伤事件的病理性重现、对创伤相关线索的回避、持续性的高唤醒,以及对创伤经历的选择性遗忘和情感麻木为显著的临床特征(陈俊、林少惠,2009: 66)——作为创伤的又一表现形式,也被用于分析《夜色温柔》中人物的疾病特征。
3.2.2 隐喻引申形成的叙事张力
“创伤”和“疾病”最开始都源自医学领域,是一种生理现象的表征,后其意义逐渐向社会科学范围内延伸并被赋予深厚的隐喻内涵。“创伤”(Trauma)一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刺破或撕裂的皮肤”;在医学上所指的是“细胞组织受到损伤”。弗洛伊德将“创伤”引入精神分析,隐喻性地使用“trauma”这个字,比喻人类的心灵就如同皮肤组织一般,亦会遭受意外事件的伤害。(李桂荣:20)随着创伤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创伤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创伤不仅仅指心理创伤,其内涵及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文化创伤、民族创伤以及历史创伤的研究。
“疾病”的隐喻意义也较为丰富。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对“疾病”的隐喻进行了研究。在书中,她指出:“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苏珊·桑塔格,2003:68)虽然桑塔格的目的是为了对疾病的隐喻进行否定和批判,但这一切都是基于“疾病”被赋予深厚的隐喻意义之上的。
从对各种疾病叙事作品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疾病”在文学中已经不单单指疾病本身,作家往往凭借人物的生理或心理疾病来反映社会的病态。郭棲庆(2016)分析了《夜色温柔》中疾病的道德隐喻、政治隐喻和女性政治隐喻,借此折射出作家身后纵酒狂欢、敏感自恋、有些精神失常却又闪耀着光芒的时代;刘明录(2013)分析了品特戏剧中种族文化、宗教文化、政治语境及战争语境中的疾病隐喻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内涵。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众多叙事作品中,“创伤”和“疾病”尤为垂青少数族裔群体,他们往往受到各种形式的创伤,深受各类疾病的折磨。一方面,这种现象隐喻着少数族裔在种族歧视下生存和发展的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也为少数族裔作家的创作提供灵感和契机,为身处社会边缘的族群寻求一种发声方式,并借此抒发内心情感、表达群体诉求。
3.2.3 叙事方式上存在的虚构性
创伤叙事和疾病叙事的共同点还体现在其叙事方式的部分虚构性上。
创伤叙事和疾病叙事中不乏对现实状况的如实描述,如创伤叙事中的医学性创伤叙事以及疾病叙事中的病人的自我病情书写以及医生的病理书写,但在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以“虚构”的形式出现。虚构疾病叙事主要涉及小说家在行医或疾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虚构的故事(杨晓霖,2014);文学性创伤叙事也具有一定的虚构性,除了以人类历史题材为源泉叙述历史上真实事件(为文学创作而非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还有个人经历为源泉的创伤叙事,也有“纯粹”想象的创伤叙事(李桂荣,2010)。
近20年来,不少关于创伤研究的理论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关于创伤再现中语言选择的问题——写实意义(literal language)还是修辞意义(figuration)(师彦灵,2011),即创伤叙事的虚构性与真实性的问题。创伤事件产生的影响具有延宕性,因而不可能对创伤的叙述进行高度还原,同时,整个叙事过程还受到叙事者当下情感态度的影响,因而创伤叙事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3.2.4 作为一种疗救方式而存在的叙事
怀特和伊普斯顿曾提出“叙事文本”和“叙事治疗”等概念,将治疗比喻成“说故事”或“重说故事”。卡姆斯和弗莱曼认为,叙事取向的治疗凭借问题外化,将人从问题中“抽离”出来,产生人与问题之间的“空间与距离”。伊普斯顿认为,叙事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隐藏着意想不到的治疗潜能。(唐伟胜,2012)20 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治疗被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中,咨询者运用适当的语言形式,帮助当事人找出遗漏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故事,并以此为契机重新建构生活意义、唤起当事人内在力量。叙事治疗的核心是叙事。(程瑾涛,刘世生,2012)
疾病叙事和创伤叙事作为叙事的两种方式,无疑也担任起了治疗的角色。创伤叙事中,小说家通过模拟创伤场景使创伤者再次回到创伤发生的历史瞬间,重构过去可以帮助创伤幸存者实现潜意识转化为意识的历程,使创伤得以医治。(李曼曼,汪承平,2012)疾病叙事中也是如此。疾病本身产生一种宣泄的需要,需要克服对疾病的恐惧。作家通过对疾病、痛苦的描写,使疾病得到理解,从而让人们在身临疾病威胁时保持与外界的交流;而读者作为接受者,通过参与作品的解读,使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疾病客观化,从而获取与之斗争的勇气和经验(邓寒梅,2012),因而疾病叙事对疾病治疗的重要意义。郭棲庆(2016)在分析《夜色温柔》中的疾病叙事时也指出:“菲氏通过疾病书写让自己在面对疾病威胁和折磨时保持与外界的交流,有助于疏导心中的痛楚,平复创伤的心理,达到精神疗救的作用,力图通过个人自救达到治疗社会的最终目的。”
3.2.5 隶属于后经典叙事学下身体叙事
后经典叙事学较经典叙事学而言,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或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叙事作品之意义的探讨。(赵一凡,2006)后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作者、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相互作用,将文本与围绕文本的语境相结合进行研究。疾病叙事和创伤叙事是对疾病和创伤本身的一种反映,是时代背景的一种投射,同时强调叙事对叙述者和读者的疗救,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范畴。
身体叙事学由身体研究与经典叙事学结合演变而来(许德金,王莲香,2008),属于后经典叙事学范畴。后经典叙事学下身体叙事有两种含义,广义上指的是以身体为叙事符号,以动态或静态、在场或虚拟、再现或表现身体,形成话语的叙事流程,以达到表述、交流、沟通或传播的目的;狭义上的身体叙事指的是女性主义的身体叙事。(郑大群,2005)疾病和创伤叙事体现的是广义上的身体叙事。在对身体叙事中“身体”进行区分时,许德金和王莲香(2008)认为应该以性别、疾病(伤残)、种族、阶级及身份的认同为标准,其中重要的一类是物理的身体,即“真实作者身体的健康与否,或正在写作时身体所处的状态(兴奋、癫狂、烦躁等等)都会对其写作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作家本身所罹患的身体疾病也会影响该作家所采取的叙述方式。”(许德金,王莲香,2008)由此可见,疾病和创伤作为受伤躯体的一种表征,是身体叙事的一部分。
同时,疾病叙事和创伤叙事中,身体对于叙事具有驱动作用。创伤或疾病叙事的运动轨迹,主要体现为从内在自我到外部世界,再从外部世界到内在自我的一个双向位移进程,两个位移之间因疾病因素而形成一个叙事张力,这种叙事张力并不由观念或心智决定,而是由疾病身体推动而成。著名文论家丹尼尔·庞德 (Daniel Punday) 进一步提出了“身体叙事学” 理论。他认为,传统的线性情节观使阅读和写作都成为了一种身体缺场的、重理性和心智的经验活动(王江,2014)。疾病和受创的身体促使叙事张力的形成,使叙事运动处于前后摇摆的不稳定状态,形成一种动态的叙事。
4.结语
近几十年来,疾病叙事和创伤叙事的研究逐渐引来人们的广泛关注。两种叙事方式虽然起源时间、发展背景以及研究范畴上不尽相同,但同隶属于后经典叙事范畴下“身体叙事”的“疾病叙事”和“创伤叙事”之间也存在很多相同之处,两者突破了经典叙事学的限制,在以文本为关注对象的同时,也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对读者产生的效果考虑在内,关注叙事的治疗作用。此外,两种叙事方式在研究心理创伤(疾病)和精神创伤(疾病)上存在交叉重合之处,同时,两种叙事方式富于隐喻内涵,具有一定的虚构性,大大增强了文本的叙事张力和阐释能力,成为作家借作品中人物的不正常来反映社会病态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成为作家自我疗救和救助社会的一种方式。
[1]Cathy Caruth,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1995.
[2]D.LaCapra,History Transit: Experience,Identity,Critical Theory,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3]Kleinman,Arthur.1988.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Healing and Human Condition [M] New York: Perseus Books Group.
[4]Parziale,Amy Elizabeth.2013,Representations of Trauma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Film: Moving from Erasure to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D].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5]陈 俊,林少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预测因素[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4) : 66-69.
[6]程瑾涛,刘世生.作为叙事治疗的隐喻——以《简·爱》为例[J].外语教学,2012,(1):76-80.
[7]邓寒梅.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疾病叙事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8]弗洛伊德,西格蒙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9]宫爱玲.论疾病叙事小说的文体形态[J].文学教育,2014,(8) : 102-104.
[10]郭棲庆,蒋桂红.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疾病叙事研究——以《夜色温柔》为例[J].外国语文,2016,(5):1-7.
[11]洪春梅.菲利普·罗斯小说创伤叙事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4.
[12]李桂荣.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3]李曼曼,杨 阳.创伤叙事语境下的《最蓝的眼睛》[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3,(5):98-101.
[14]刘荡荡.表征精神创伤 实践诗学伦理——创伤理论视角下的《极吵,极近》[J].外国语文,2012,(3):11-15.
[15]刘明录.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叙述研究 [D].重庆: 西南大学,2013.
[16]琼斯,安·H.医学与文学的传统与创新[J].聂精保,孟辉,译.医学与哲学2000,(5) : 59-61.
[17]桑塔格,苏 珊.疾病的隐喻 [M].程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8]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兰州大学学报2011,(2):132-138.
[19]唐伟胜.视阈融合下的叙事学与人文医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9-28(B01) .
[20]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125+159-160.
[21]王 江.疾病与抒情——《永别了,武器》中的女性创伤叙事[J].国外文学,2014,(4):128-134.
[22]王庆蒋,苏前辉.冲突、创伤与巨变——美国9·11小说作品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23]王 欣.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24]许德金,王莲香.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8,(4):28-34.
[25]杨晓霖.疾病叙事阅读:医学叙事能力培养[J].医学与哲学, 2014,(11):36-39.
[26]赵一凡.西方文化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7]郑大群.论传播形态中的身体叙事[J].学术界,2005 ,(5):183-189.
(责任编辑:胡光波)
I109.9
A
2096-3130(2017)06-0032-06
10.3969/j.issn.2096-3130.2017.06.007
2017—10—28
蔡祎,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秦海涛,男,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