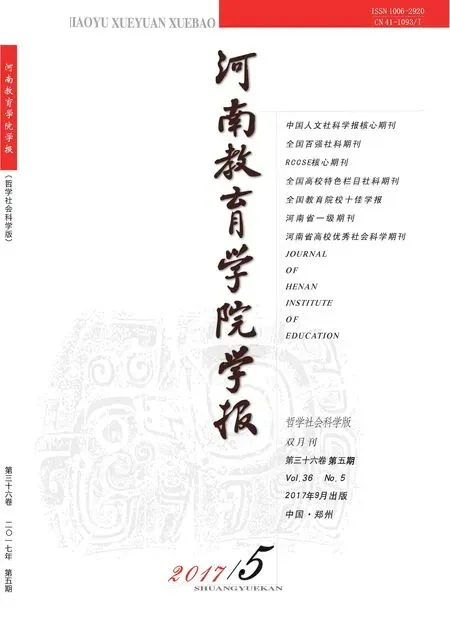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武德政治乃贞观之治基石
2017-03-10张超
张 超
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武德政治乃贞观之治基石
张 超
初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与李渊广施德政是分不开的。后世对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多有讴歌,对李渊的武德政治却少有赞颂,但事实上根据对初唐诏敕文的考察可知,贞观之治正是以武德政治为基础的。
初唐诏敕;武德;贞观;奠基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受隋恭帝禅位,于长安称帝,成为了唐朝二百八十九年基业的开创者及奠基者。
李渊的《即位告天册文》中,肯定了灭隋兴唐乃天命所归、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
生人以来,树之司牧,眷命所属,谓之大宝。历数所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让而兴虞夏;汤武兼济,干弋以定商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后之创业,咸取则焉。
他的显赫身世也得以展现:
某承家庆,世禄降祉,曰祖曰考,累功载德,赐履参墟,建侯唐旧。地居戚里,门号公宫,承绪建基,足为荣矣。
他严词谴责隋朝的失政:
有隋属厌,大业爽德,饥馑师旅,民胥怨咨。谪见咎征,昭于皇鉴,备闻卑德,所不忍言。
他于太原起兵,平定乱寇,一统天下,最终当之无愧地接受了隋帝禅让,登上了皇帝宝座:
某守晋阳,驰心魏阙,援手濡足,拯溺救焚。大举义兵,式宁区宇,惩边荒之辫发,辑兆庶之离心,誓以捐躯,救兹生命。扫除丧乱,期之乂安,有功继世,无希九五,惟身及子,竭诚尽力,率先锋镝,誓以无二,再蒙宏诱,克济艰离,电扫风驱,廓清天邑。传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关陇。西戎即叙,东夷底定,非启非赞,孰能兹速。尊立世嫡,翼奉宗隋,戮力辅政,无亏臣节。
天禄将移之时,李渊临危受命,三让乃受:
值鼎祚云革,天禄将移,讴歌狱讼,聿来唐邸。人神符瑞,辐凑微躬, 远近宅心,华夷请命。少帝知神器有適,大运将去,逊位而禅,若隋之初。让德不嗣,群情逼请,六宗阙祀,七政未齐。罪有所归,恐当天谴,请因吉日,克举前典。[1]43
这篇诏敕文体现出了李渊开创新政之后,立志革除隋朝弊政、有所作为的雄心。后来的史实证明,李渊在九年的执政期间,确实实现了其政治抱负。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面临的社会形势十分严峻。当时政乱民贫、经济萧条、人口锐减;士人多不思进取;为数不少的流民仍然“逃亡山泽,挟藏军器”,伺机反抗;突厥、吐谷浑等亦不时对唐朝边境进行侵扰,威胁新政权的安全。[2]6021李渊登基之后,为了振兴新朝,便针对各种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关于任用人才的诏书
李渊能够于隋末乱世中戡平群雄、统一全国、建立新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高明的用人策略。
李渊在唐朝开国之初首先褒奖了那些为了大唐的创建而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的开国功臣。他的《褒勋臣诏》曰:
朕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材。尚书令秦王世民、尚书右仆射裴寂等,或合契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特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1]22
李渊十分重视自己在大唐基业创立之前结识的旧交,正所谓“接待人伦,不限贵贱, 一面相遇, 十数年不忘”[3]7。他的《赐许绍敕书》曰:
昔在青衿,同游庠序,博士吴玉,其妻姓仇。追想此时,宛然在目,荏苒岁月,遂成累纪。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辽之时,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阔,累叶同之,其闲游之处,触事可想。虽卢绾与刘邦同里,吴质共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称焉?而公追砚席之旧欢,存通家之曩好,明鉴去就之理,洞识成败之机。爰自荆门,驰心绛阙,惠怀士庶,纠合宾寮,逾越江山,远申诚款。览此忠至,弥以慰怀。[1]45
李渊身为隋朝的旧臣,极为赏识隋代宗臣中的一些才能卓越者。因此在开国之后,他大力提拔任用这些隋朝的宗亲及旧臣。他的《选用前隋蔡王智积等子孙诏》云:
近世以来,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诛绝。历数有归,实维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前隋蔡王智积等子孙,并付所司,量才选用。[1]21
李渊起用的隋朝旧臣中,也包括昔日的“大手笔”,如曾任隋朝内史舍人的陈叔达,“颇有才学”, 唐武德年间“方禅代时, 书册诰诏皆其笔也”[4]3925。李渊任用的这些隋朝旧臣中有些人虽于大唐的创建无功,但却理政有术,在新朝各显其能,各尽其用,从而使得唐朝的政局在开国不久便大有起色。
李渊在唐朝开国之初招抚了许多隋朝降将,《褒高开道来降诏》曰:
褒德叙功, 有国彝训, 任贤赏善, 列代通规。伪燕王高开道, 家本海隅, 志怀慷慨。有隋之末, 州域雕残, 招集徒众, 自保边塞。缮修斥堠, 捍御寇戎。民吏肃清, 仓库完实。既而审达机变, 远慕朝风, 阖境献诚, 归款内属。请申经略, 辑宁燕代, 厥功以茂, 宜从褒宠, 礼命之差, 用常超级。可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蔚州总管。加授上柱国,赐姓李氏, 上属籍宗正, 封北平郡王, 食邑五千户。[1]28
高开道原本是隋末的地方割据势力之一。“既而审达机变, 远慕朝风”,主动降唐,李世民对高开道“宜从褒宠, 礼命之差, 用常超级”,授予其“可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蔚州总管。加授上柱国……封北平郡王”的政治身份;并赏赐他“食邑五千户”;另外还“赐姓李氏, 上属籍宗正”,以抬高其出身。
《册府元龟》卷二百一十五对此评价曰:
招携以礼, 怀远以德, 是知有国者务辑宁于初附者, 将诱致于来者, 而外示其优礼, 而内彰其大度, 俾危疑者得自安之地, 翔引者无失所之嗟, 诚接物之宏猷, 经远之大略也。[5] 2566
李渊还沿用隋朝科举、荐举的方式, 广泛搜求贤才。《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记载:
始自武德辛巳岁(四年)四月一日, 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 明于理体, 为乡里所称者, 委本县考试, 取其合格, 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6]1
武德四年(621年),李渊颁布了《令诸州举送明经诏》曰:
朕受命膺期,握图驭宇,思宏至道,冀宣德化,永言坟素,深存讲习。所以捃摭遗逸,招集散亡,诸生胄子,特加奖劝。……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渐戢,搢绅之业,此则可兴。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加阶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状,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州县及乡,各令置学。官僚牧宰,或不存意,普更颁下,早遣立修。[1]35
李渊于武德年间开创了制举。《旧唐书》卷七十四载,崔仁师“武德初应制举,授左卫兵曹,累迁左武候中郎将”[7] 2620。
李渊还采用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来选才取士。武德五年(622年)三月,他颁布了《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
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自古哲王,宏风阐教,设官分职,惟才是与。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藉左右之容,义自搜扬,理宜精擢。是以贡士有适,爰致加锡之隆,无益于时,必贻贬黜之咎。末叶浇伪,名实相乖,取非其人,滥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职于是隳废。朕膺图驭宇,宁济兆民,思得贤能,用清治本。招选之道,宜革前弊;惩劝之方,式加常典。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己具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赏罚之科,并依别格。所司颁下,详加搜别,务在奖纳,称朕意焉。[8]518
这篇诏敕文准许士人“自举”,从而为出身寒微且无人举荐的人才开辟了宽广的出仕途径,体现了李渊求贤之心的真诚。
李渊对待人才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对臣子的“忠君”“爱民”有着较为高明的认识。邓小军教授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中讲道:“在君主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士的政治品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人民的态度是热爱维护还是麻木不仁,对专制君主的态度是坚持道尊于君还是愚忠。士人挺立其道德主体,才能具有真正的士的政治品格。”[9]352
因而,李渊对于大臣的谏诤,能够做到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他的《令陈直言诏》就是最好的说明,体现了他对于人才的尊重。
总之,李渊在初唐百废待兴之时,在短时间内能够整合多方面的人力资源,为己所用,开创了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社会局面,实际上正得益于他卓越的用人策略。
二、关于发展经济的诏书
唐武德年间,李渊为了振兴经济,遂大力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减免各种苛捐杂税,以减轻百姓负担,恢复农业生产。
他的《简徭役诏》曰:
自有隋失驭……肆行暴虐,征求无度,侵夺任己。下民困扰,各靡聊生……上天降监,爰命朕躬,廓定凶灾,乂宁区域。念此黎庶,凋弊日久,新获安堵,衣食未丰。所以每给优复,蠲减徭赋,不许差科,辄有劳役,义行简静,使务农桑。至如大河南北,离乱永久,师旅荐兴,加之饥馑,百姓劳弊,此焉特甚。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阻,土旷民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其河北江淮以南,及荆州大总管向西诸州,所司宜便班下。自今以后,非有别敕,不得辄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8]578
他的《申禁差科诏》曰:
隋末丧乱……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今寇贼已平,天下无事,百姓安堵,各务称职……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修产业。犹恐所在州县,未称朕怀,道路迎送,廨宇营筑,率意征求,擅相呼召。诸如此例,悉宜禁断,非有别敕,不得差科。不如诏者,重加推罚。[1]33
为了节约财政开支,减轻隋末以来京城寺庙道观因结构庞大、人员芜杂造成的资源浪费,李渊诏令澄清释迦、阐教。其《沙汰佛道诏》云:
自觉王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闤阓,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又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已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趣喧杂之方。缮筑崎岖,甍宇舛错,招来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近鄽邸,邻迩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为元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1]38
他于此文中要求沙汰僧、尼、道士、女冠,对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加以优待,对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则令罢遣。
为了避免臣民因沉湎酒醪欢娱而大行屠酤,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导致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耕牛数量减少,他发布了《禁屠酤诏》以提倡节俭、禁行屠酤:
酒醪之用,表节制于欢娱;刍豢之滋,致甘旨于丰衍。然而沈湎之辈,绝业忘资;惰窳之民,骋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宁,年谷不登,市肆腾踊。趣末者众,浮冗尚多。肴羞曲糵,重增其费。救弊之术,要在权宜。关内诸州官民,宜断屠酤。[1]24
与此内容相似的诏敕文还有《断屠诏》:
有隋失驭,丧乱宏多,民物凋残,俗化逾侈。耽嗜之族,竞逐旨甘;屠宰之家,瓷行刳杀。刍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资;胎夭之群,莫遂蕃滋之性。伤财堕业,职此之繇,敚攘穿窬,因兹未息。《礼》曰:“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非惟务在仁爱,盖亦示之俭约。方域未宁,尤须节制,凋弊之后,宜先蕃育。岂得恣彼贪暴,残殄庶类之生,苟循目前,不为经久之虑。导民之理有未足乎?其关内诸州,宜断屠杀。庶六畜滋多,而民庶殷赡。详思厥衷,更为条式。[1]27
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的干预,武德年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三、关于加强武备、征伐平叛的诏书
李渊在唐朝开国之初,为了早日平定地方叛乱,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便大集诸军、加强武备。他的《修武备诏》开篇云:
天生五材,司牧资其器用;武有七德,拨乱所以定功。故黄帝垂衣,尚有阪泉之战;放勋光宅,犹称丹浦之师。禁暴安人,率由兹道,创业垂统,莫此为先。是以周置六军,每习蒐狩;汉增八校,毕选骁雄。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蛮,奸宄不萌,虔刘息志。[1]25
这段文字列举了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帝尧有“丹浦之师”,且“周置六军,每习蒐狩;汉增八校,毕选骁雄”,以此来说明修武备之必要,正所谓“禁暴安人,率由兹道,创业垂统,莫此为先”。可谓言之凿凿,有理有据。
接下来的内容是对开国伊始的军事形势所进行的描绘:
自季叶凌替,军政湮亡,行列不修,旌旗舛杂。部伍符籍,空有调发之名;逗挠乏兴,竟无讨袭之用。遂使戎狄放命,盗贼交侵,战争多虞,黔黎殄丧。
诏敕文的末段点明了自己大修武备的必要性以及目的:
朕受天明命,抚育万方,爰自义师,克成帝业。至如超乘之士,莫匪百金,彀骑之才,岂惟七萃。今虽关塞宁谧,荒裔肃清,伊雒犹芜,江湖尚梗。役车未息,戎马载驰,武备之方,尤宜精练。所以各因部校,序其统属,改授钲鼓,创造徽章,取象天官,定其名号。庶使前茅后劲,类别区分,玉帐绛宫,刑德允备。蹈兹汤火,譬彼椒兰,大定戎衣,止戈斯在。[1]25
李渊军事方面的诏令文,有些是关于唐军在开国之初征伐平叛的,展现了他从容精妙地部署威武之师、克敌制胜的昂扬斗志。如果将这些诏敕文按照发布时间的前后顺序进行排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唐军在唐朝开国之初东联李密,北和突厥,先后消灭陇右的薛举、河西的李轨、山西的刘武周、洛阳的王世充等地方割据势力的行动路线。如他的《讨薛举令》云:
大业丧乱,兵革殷繁,天下黔黎,手足无措。孤所以救焚拯溺,平此乱阶。蜀道诸郡,深思苏息,远勤王略,诚有可嘉。方一戎衣,静兹多难,而薛举狂僭,吞噬西土,陇蜀道途,恐相侵暴。今便命将授律,分道进兵。其冲要诸郡县,宜率励各募部民,随机底定。斯则暂劳永逸,贻厥子孙,守国刑家,同享安乐。[1]18
又如《命秦王征王世充诏》曰:
取乱侮亡,圣王于是致治;民和众泰,汤武所以成功。兵革之兴,义资靖难,出军命将,盖非获已。自隋氏数穷,天下鼎沸,豺狼交争,黔庶凋残。朕受命君临,志存宁济,率土之内,咸思覆育,声教所覃,莫不清晏。惟彼伊雒,尚隔朝风,世充作梗,肆行凶暴。害虐良善,拥迫吏民,反道乱常,日月滋甚。祸盈衅积,夭亡有征,心腹猜携,党援孤绝。农亩荒废,粮廪内空,城隍社稷,势皆殄溃,吊民问罪,今实其时。可令陕东道行台上柱国秦王世民总统诸军,东逾崤渑,分命骁勇,百道俱进,救彼涂炭,诛其凶渠。凡此授律,义在拯民,府库货财,一无所利。克敌制胜,效策献功,官赏之差,并超常典。其有背贼归款,因事立勋,即加宠授,务隆优厚。[1]28
随着统一战争纷纷告捷,黄河流域、长江下游、江西、岭南一带逐渐被纳入了唐朝的统治范围。公元623年, 唐军又击溃了割据河北的刘黑闼势力。
李渊的《命太子建成讨刘黑闼诏》中反映出了他克敌制胜的从容与自信:
罪止凶渠,诖误胁从,并无所问。其有弃恶思顺,自拔而来,随即安罪。给其优赏,咸使附业,各令安堵。虽贼之魁帅,久同叛逆,必能临机效节,因事立功,并即叙勋班赏,量才授任。如其不从告谕,敢怀迷执,然后肃正军法,齐以大刑。其陕西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其间经略筹筭,赏罚科条,要在合机,皆以便宜从事。[1]32
刘黑闼的败亡,标志着李渊以将近五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稳定了唐朝于河北、山东等地的统治。与此内容相似的诏敕文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关于规范律法、减轻刑狱的诏书
在律法方面,李渊于太原起兵之时就曾颁布宽大之令,使得那些先前苦于隋朝苛政的百姓竞相前来归附。
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更是对唐军“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 余并蠲除之”[7]2133。
登基后,李渊于武德元年大赦天下,减轻刑罚。在此后的执政期间,他更是遇事便行大赦,对百姓务从宽宥。他的《改元大赦诏》曰:
宝历初基,普天同庆。所宜布兹宽惠,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自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罪无轻重,已发露,未发露,皆赦除之。子杀父、奴杀主,不在赦限。[1]20
武德年间,在全国统一大业完成之后,李渊遂命令裴寂、刘文静等人对隋朝《开皇律》“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 又制五十三条格, 务在宽简, 取便于时”[7]2134。
同时,他还颁布了《颁定科律诏》:
禁暴惩奸,宏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有隋之世,虽云厘革,然而损益不定,疏密无准,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加以微文曲致,览者惑其浅深;异例同科,用者殊其轻重。遂使奸吏巧诋,任情与夺,愚民妄触,动陷罗网。屡闻厘革,卒以无成。……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宪则,贻范后昆,爰命群才,修定科律。……是以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从体要。迄兹历稔,撰次始毕,宜下四方,即令颁用。[1]36
通过删削隋炀帝大业年间的严酷律法,《武德律》最终修撰完成,并颁行天下。“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书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7]2085武德律从此成为了唐律的基础。唐高宗时期,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加以注解,形成《唐律疏议》。
李渊在律法方面务从宽宥,他坚持以德治国,不滥施刑罚,从而使得百姓能够在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安心地生产和生活,这对于初唐的社会繁荣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关于倡兴文化的诏书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来倡兴文化事业。
其一,李渊鉴于隋朝“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序之仪,泯焉将坠”,遂大力振兴教育。他于《兴学敕》中申明:
自古为政,莫不以(儒)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8]537
李渊创立了中央官学,并以国子学来统摄六学。同时还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庙、孔子庙,四时致祭,并礼遇其后代。他的《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指出:
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人,宏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于兹。自八卦初陈,九畴攸叙,徽章既革,节文不备。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创设礼经,大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冠于终古。[1]25
文中指出,从春秋战国开始:
暨乎王道既衰,颂声不作,诸侯力争,礼乐陵迟。粤若宣父,天资睿哲,经纶齐、鲁之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宏宣旧制。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徒,风流无攵。惟兹二圣,道济群生,尊礼不修,孰明褒尚。
因此,李渊于文中提出:
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土。
李渊倡兴文化,崇儒兴学,还表现在他于中央官学中延请的教师多为当时知名的儒士,并常常对这些人进行赏赐。
他的《赐学官胄子诏》云:
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揆,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王公以下,宁得不惭。朕今亲自观览,仍征集四方胄子,冀日就月将,并得成业,礼让既行,风教渐改。使期门介士,比屋可封;横经庠序,皆遵雅俗。诸王公子弟,并皆率先,自相劝励。[1]36
除了中央官学之外,李渊还大力发展地方官学及私学,并且对于那些勤修经业、教授门徒、倡兴地方教育的士人十分尊崇。他的《擢史孝谦诏》曰:
自隋以来,离乱永久,雅道沦缺,儒风莫扇。朕膺期御宇,静难齐民,钦若典谟,以资政术,思宏德教,光振遐轨。是以广设庠序,益召学徒,旁求俊异,务从奖擢。宁州罗川县前兵曹史孝谦,守约邱园,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并幼童,讲习《孝经》,咸畅厥旨。义方之训,实堪励俗,故从优秩,赏以不次。宜普颁示,咸使知闻,如此之徒,并即申上,朕加亲览,特将褒异。[1]37
在李渊大力倡兴之下,初唐教育发展到了“学者慕响,儒教聿兴”的程度。
其二,李渊倡兴文化的措施还表现在他对于前代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整理。他于执政过程中十分重视修史,正如他的《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开篇所云:“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32文中提到了从上古时期开始,直至两晋、南朝宋,历代都很注重修史:“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然而“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於时”。由于这些朝代对史籍的疏于整理,从而造成了“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
文中写道,李渊开国之后为了“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遂诏令:“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并要求他们“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李渊诏命修史的初唐群臣多为当时身居要职、文名极高的大儒,由他们修撰的魏周隋梁齐陈史,使得大批史籍得到了整理和保存,不仅对于唐朝的封建统治有可资借鉴的作用,对于后世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也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李渊于武德年间广施德政,在政治上选拔重用才德兼备、清正廉洁的官吏,并积极听取大臣的谏言。在经济上注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大力发展生产。在军事上一方面重视军队的建设,大修武备,以备抗击敌对势力之需;另一方面也常使用招抚政策来化解干戈,避免战乱祸及无辜百姓。在律法方面务从宽宥,不滥施刑罚。在文教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倡兴文化事业。
总之,因为有了武德政治奠定的雄厚基础,才有了后来贞观之治的顺应承接,武德政治对于唐朝盛世基业的开创功不可没。正如《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所云:“高皇创图,势若摧枯。国运神武,家难圣谟。”[7]19
[1]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王钦若.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6] 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9] 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1006-2920(2017)05-0099-07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7.05.018
张超,文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郑州 450001)。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学视角下的唐代诏敕研究”(15CZW022)。
(责任编辑范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