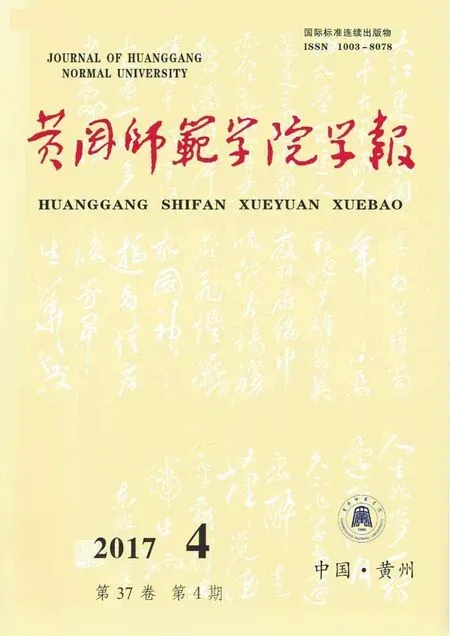试论《好逑传》中“情”与“礼”的碰撞
2017-03-09郭海峰
郭海峰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系,安徽 淮北 235000)
试论《好逑传》中“情”与“礼”的碰撞
郭海峰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系,安徽 淮北 235000)
《好逑传》作为近代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无论在创作初衷、情节安排,还是在人物塑造、道德探询等方面,其“情”与“礼”的激烈冲撞都表现得尤为突出。才子佳人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以“礼”制“情”的婚恋观念在《好逑传》中有了一次极致的表现,显示出其极端性和理想性,并折射出时代思潮和文学发展的丰富折光。
《好逑传》;情;礼
《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又因其为“十大才子书”中第二才子书,坊本亦名《第二才子好逑传》。其撰者不署,编次者署名为“名教中人”,小说创作于明清二代,流行于清代。《好逑传》的书名取自《诗经》第一篇《国风·关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全书共计4卷18回,以大名府秀才铁中玉和水冰心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两人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同时严守礼教,最终获得圣旨赐婚的故事。《好逑传》是第一部译成西方文字并得以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在西方文人中产生过较大影响,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如果你问一位学者或作家,他所了解的中国最优秀的小说是哪一部,那么,他一定会告诉你,是《好逑传》。对于这部作品,前人评价它“文辞较佳,人物性格亦稍异”[1],“别具机杼,摆脱俗韵”[2],但这篇小说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其中“情”与“礼”的激烈冲撞。可以说,才子佳人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婚恋观念在《好逑传》中进行了最登峰造极的一次表演,显示出其全部的极端性和理想性,并折射出时代思潮和文学发展的丰富折光。
一、小说叙述中的“情”“礼”对立
在《好逑传·叙》中,作者“宣化里维风老人”开宗明义点明了他的写作目的:“因谱兹《好逑》一案,使世知天才佳丽,原有安排,人每自轻,不知消受。惟德流荇菜,方享人生之福;礼正斧柯,始成名教之荣。”[3]179为了达到使人“觉人伦不苟,玉性无他,而名教中自有乐地”[3]179的目的,作者设置了众多二元对立的价值概念,要求人们“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是以恩有为恩,不敢媚恩以辱体;情为有情,何忍姿情以愧心?未尝不爱,爱之至而敬生焉;未尝不亲,亲之极而私绝焉”。[3]180而这“伦常”“美色”“廉耻”“婚姻”“恩”“体”“情”“心”的种种对立,归根到底就是“情”与“礼”的对立。与其他才子佳人小说序言中对“才”或“情”的强调不同,维风老人“情”“礼”对举、以“礼”制“情”的意识是十分自觉而明显的。这样的写作目的也就决定了整部小说无论从情节、人物还是观念上都打下了“情”、“礼”对立的深刻烙印。
在情节设计上,才子佳人小说的一般情节模式是“一见钟情——小人拨乱——中举团圆”,促使矛盾展开,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才子佳人和破坏他们爱情的小人之间的斗争。而《好逑传》以第七回为转折,在此之前,两位主角铁中玉和水冰心在各自的舞台上进行着独立的表演,矛盾集中于他们各自与小人的斗争,这种斗争与他们的爱情无关,只是展示了两人侠义机智、有胆有识的风采。而在此之后,情节开始与爱情有关,矛盾也转向于“情”与“礼”的斗争,这种斗争在铁水两人的心中进行,在努力促成两人美满婚姻的人和守定礼法的才子佳人之间进行,而铁水两人与过其祖、大夬侯、仇太监等小人的斗争,从根本上也是围绕“礼义”“名教”展开的。“情”与“礼”的冲突,在《好逑传》的情节安排和故事进展中发挥了远比在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中更突出的作用。
第七回题为“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描写水冰心将病中的铁中玉接到家中照料,两人孤男寡女,共居一室,相对五夜的情景。透过鲍县令派去躲在梁上窥视两人的单祐的全知视角,读者看到的是这样一幕景象:“大厅的正中间,垂下一挂朱帘,将东西隔做两半:东半边帘外设了一席酒,高高点着一对明烛,是请铁相公坐的;西半边帘内,也设了一席酒,却不点灯火,是水小姐自陪坐的”[3]235,铁水两人隔帘对拜对谈,“讲一会学问,又论一会圣贤,你道我说的好,我赞你讲的妙”[3]239,“就吃到酣然之际,也并无一字及于私情”。[3]239
长时间的相对相处的情节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是很少见也很极端的,而隔帘相对的场景更是极具舞台感和戏剧性,两人“礼则礼,情则情,全无一毫苟且之心”[3]241的品质在这一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极端化和戏剧化的情节设置,无疑与作者“瓜田李下,明侠女之志;暗室屋漏,窥君子之心”[3]232的写作目的密切相关。
“五夜无欺”一段之后,铁水两人“恩爱反成侠义,风流化出纲常”[3]223,而此后的许多冲突和波澜都是围绕这对矛盾展开。水冰心的叔父水运要促成两人婚事。水冰心以“铁公子人品才调,非不可然,但所遇在知己之间,去婚姻之道甚远”[3]242答之,而铁中玉则怒言“今忽言及婚姻,则视我学生与水小姐为何如人也,毋亦以钻穴相窥相待耶”[3]245,拂袖而去。鲍知县为不使“千古好逑当面错过”[3]246,再三劝勉两人成亲,铁中玉表白了对水冰心确实有情,但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冲突后,还是决定“唯有拿定主意,终做个感恩知己之人,便两心无愧矣”。[3]253及至铁水两人的父母要为两人议定婚姻,他们仍然连连摇头,一个说“今若成全,则前之义侠,皆属有心。故宁失闺阁之佳偶,不敢作名教之罪人”[3]299,另一个说“此乃义侠之举,感恩知己则有之,若再议婚姻,恐不可如是之苟且也”。[3]303这里已不是众人千方百计破坏才子佳人的婚姻,而是才子佳人千方百计抗拒他人的美意和自己的真情了。一次次的撮合,一次次的拒绝,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前发展。
同时,铁水二人与“小人”的斗争从根本上也是围绕“名教”展开,故事的高潮和结局“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和“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逑”就是以假名教谋私的小人的失败和以真名教持身的君子的胜利:大夬侯向水冰心逼婚,铁水两人不得已“名结丝萝以行权,实虚合卺以守正”[3]307,过其祖向皇帝进馋,诬告两人“孤男寡女,并处一室,不无暧昧之情;今父母徇私,招摇道路,而纵成之,实有伤于名教”[3]321,皇后着人验明水冰心仍是处子之身,两人才得以“表明心迹,毫无愧怍,欢欢喜喜,真结花烛”。[3]335在这里,“礼”直接成为了维护“情”的工具,作者也通过才子佳人的胜利证明了“名教”的胜利。
总之,“情”与“礼”的二元对立作为联结全书各个段落的线索,作为推动情节发展和造成故事波澜的动力,作为造成矛盾的原因和解决矛盾的钥匙,在《好逑传》一书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人物塑造中的“情”“礼”冲突
在人物塑造上,从“情”、“礼”冲突的角度看,《好逑传》的两位主角的特色正如书中的鲍县尊所说:他们既“心灵性巧,有恩有情”,又是“负血性的奇男子”,“讲道学的奇女子”。
铁中玉、水冰心二人皆是有“情”的。铁中玉初见水冰心“亭亭如玉、灼灼如花,虽在愤激之时,而私心几不能自持”[3]252,“‘水小姐’三字,魂梦中也未成能忘”[3]224,而水冰心亦倾心铁中玉“天地间怎有这样侠烈之人,真令人可敬”[3]225,两人不仅是一见钟情,还可谓是一见知情。后来铁中玉病倒长寿院,危难之时,水冰心不避嫌疑,将铁接到家中悉心照料,两人隔帘对语,“千言万语,相亲相爱”[3]238,彼此认做至交知己。两人分别后,铁中玉偶然听闻水冰心遭过其祖逼婚,更是为报知己,不辞辛苦,千里赴难。书中称美他们的爱情是“恩为有恩情有情,自然感激出真诚”[3]228,“慢道灵犀通不得,瑶琴默默有知音”。[3]284可以说,与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主人公们或因早有婚约而由义生情,如《铁花仙史》中的王儒珍和蔡若兰,《二度梅》中的梅璧与陈杏元,或因美文佳篇而心生爱慕,如《玉娇梨》中的苏友白和白红玉,《玉支玑》中的管彤秀和长孙肖,或因才貌双全而一见倾心,如《铁花仙史》中的陈秋遴和夏瑶枝的爱情相比,铁中玉和水冰心之间既有足够的接触和精神交流,作者对他们爱情的描述也是较为细腻、真实和富有层次的。
然而,与其说铁中玉和水冰心是“情”的代表,毋宁说他们是“礼”的代言。他们不会像《定情人》中的双星和《宛如约》中的赵如子那样出门游访,寻找佳偶,不会像《定情人》中的江蕊珠和《玉娇梨》中的白红玉那样不由父命,私订终身,也不会像《玉娇梨》中的卢梦梨和《驻春园》中的曾浣雪那样自媒自嫁,大胆私奔,更不会像《金云翘》中的金重和《麟儿报》中的廉清那样要求越礼之欢。他们不仅没有为自己的爱情做出过任何主动的追求和努力,反而在“情”与“礼”的矛盾中时时重“义”,处处守“礼”,这固然与他们义肝烈胆,冷眼热肠的侠义性格相关,但更与作者赋予他们的名教代言人的身份相关。
我们看到,铁中玉和水冰心心中不是没有过矛盾和挣扎,铁中玉曾经感叹“有情转是无情,有恩转是无恩,有缘转是无缘,老天何颠倒人若此”[3]297,水冰心也曾忧虑“空有感激之心,断无和合之理。天心有在,虽不可知,而人事舛错已如此矣”。[3]301但是与早期才子佳人小说的主角相比,铁中玉和水冰心两人表现出了更加严苛和保守的道德自律。例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观念在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都受到嘲弄和批判,如《玉娇梨》中的卢梦梨曾言:“不知绝色佳人,或制于父母,或误于媒妁,不能一当风流才婿而饮恨深闺者不少。”[4]154而铁中玉却坚持“凡婚姻之道,皆父母为之,岂儿女所能自主哉!……若徒以才貌为凭,遇合为幸,……非学生名教中人所敢承也”。[3]246两人甚至“宁失闺阁佳偶,不作名教罪人”[3]299,礼的规范总是无声无息,自觉而迅速地浇灭了情的火花。
作者不仅使两位主角的一言一行符合礼教,更时时跃出纸面,借才子佳人之口进行着苦口婆心的道德说教。铁水两人与自己辨,与水运辨,与鲍知县辨,与父母辨,甚至在新婚之夜互相印证剖白,在奏章之中向最高统治者一再辩明。这些令人头昏脑涨的长篇大论中充满了与从“叙”中一脉相承下来的众多二元对立的价值概念,如“义侠”与“婚姻”,“守正”与“行权”,“君子”与“小人”,“大义”与“小节”,“人事”与“天命”,“正”与“邪”,“公”与“私”,“情”与“礼”,“义”与“不义”等等。此时我们会觉得那个与人一言不合,便要使气动粗的铁中玉在和那个抗拒过其祖逼婚时不动声色、沉默机智的水冰心突然变得啰里啰嗦起来了。全书的后半段,现实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观念的斗争,生动的情节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概念的演绎,两位主角真正成为了名教的“代言人”。
对于这种“情”与“礼”的冲撞和以礼制情的观念,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把《好逑传》看作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婚恋观念发展的高峰和极端的个案。而这种婚恋观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潮背景的。
三、“情”与“礼”冲突的原因探究
研究者们多认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是远承明朝中后期反理学思潮对“情”“真”“欲”的肯定,又受到入清之后程朱理学统治地位加强和“实学”观念蔚然成风的影响而形成的。清初的大思想家们既反对心学的“空谈心性”,又接过李贽“人必有私”的命题,并以此为基点,将“欲”与“理”统一起来。在这样的文化思潮影响下,具有反理学意义的“真情”论被部分继承下来,并开始对明末小说中泛滥的“欲”、“俗”进行反拨。才子佳人小说既肯定“真情”论中关于情的合理要求,但又用情礼合一的价值标准,节制乃至摒弃“欲”的内容和“俗”的趣味,此时小说家们审美注意已经不是情礼对立、以情反礼,而是情礼合一、以礼制情,是尽可能地用礼作为情的合理内核,尽可能地在情中输入礼的血液。“维风老人在《好逑传序》中提出的‘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的观点,不仅在明教才子铁中玉和明教佳人水冰心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愈趋偏激和张皇。”[5]
康熙亲政之后,清朝统治逐渐稳固,程朱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逐渐得到确立。到康熙中叶,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理学色彩也日趋浓厚,《好逑传》正是这一趋势的真实体现。另一方面,《好逑传》中表现出以礼制情,情礼和谐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与明末清初小说创作的文人化、个人化密切相关的。
首先,《好逑传》中的两位主角“既美且才,美而又侠”[3]336,相比于早期才子佳人的才色兼美显得更加理想化,更关键的是,他们是作者着意塑造的真正的“好逑”,是作者心中道德探求的结果和理想人格的化身。
在《好逑传》的“叙”中,维风老人从追问什么是“好逑”开始,接连否定了富贵、佳丽、贤才之必为好逑,也一笔抹倒了武牝、绿珠、西子、阿娇、姜后、无盐、明妃、班女、红拂、文君、张敞、梁鸿、孟光等历史人物。作者认为自古至今的众多贤人佳偶都不足以称为“好逑”,而他写作这篇小说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描绘和展示他心目中的卓绝千古的理想人物——真正的“好逑”。这样的写作目的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十分个性化的,这种从古而来,独此一家的优越感和“漫道稗官野史,隐括《春秋》旨”[3]330,“兹一编当与《关雎》同读”[3]180的自豪感也是文人所特有的。
其次,《好逑传》中描写的道德也具有高度的理想色彩。这部小说所树立的道德标尺是高出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这一点仅仅从书中显示出的对卓文君的态度就可见一斑。在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相如文君的故事是作为千古佳话被歌颂和效仿的。例如《定情人》中的双星曾经仿效相如“四海求皇”,《玉娇梨》中卢梦梨赞扬文君“既见相如,不辞越礼,良有以也”[4]154,而苏友白则称美两人“始于琴心相挑,终以白头吟相守,遂成千古佳话”[4]55,而《好逑传》中则把文君作为“好逑”的对立面来看待,不但在序言中说“识英雄之红拂女,感琴心卓文君,侠肠明眼,亦自过人;然律以好逑,则不足数也”[3]179,而且在铁水二人隔帘相对,五夜无欺时作者为他们所唱的颂歌是:“白璧无瑕诚至宝,青莲不染发奇香。若教坠入琴心去,虽说风流名教伤”。[3]239我们自然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保守和倒退,但是从封建礼教的角度看,这却是道德的提升和强化。
娱乐与劝惩作为俗文学的基本功能,主要是群体意志与需求的反映,《好逑传》中理想化的道德描写使它超出了一般的娱乐或者劝惩意义。因为若为娱乐,则不需要偌多道德说教,若为劝惩,也不需设立偌高道德标尺。高度的道德要求超过了一般水平的道德劝惩意义,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个人追求真、善、美的纯粹性和寻求自我证明的表现。这也是才子佳人小说由俗文学写“真”向雅文学写“善”发展而逐步雅化的表现。
实际上,“理想化的人物和理想化的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们共同表现了文人精神对文化本体和道德理想的探求,也表现了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社会责任感的转移——由积极用世的热情转向对人的道德品质的深入考量”。[6]而作者在创作目的上的个人化,“创新性”也是文人精神和文人面目的体现。自然,我们现在看来作者并没有达到什么实质上的创新,但是“叙”中表现出来的抹倒前人,独此一家的口气说明作者是以创新来自我标榜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创作初衷、情节安排、人物塑造、道德探询上,《好逑传》都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以“礼”制“情”的观念发展的高峰。这既体现了当时理学色彩日渐浓厚的时代思潮,也体现了小说由民间创作走向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发展趋势。经过明末清初文学家的努力,“情”终于取得了自身在文学观念、审美观念中的合法地位,但是才子佳人小说以牺牲对情礼冲突的鲜明认识为代价,换取情礼和谐的廉价满足,或许只能说是一种倒退的革新。这种倒退的革新的理想性和局限性,都可以通过对《好逑传》的阅读和分析得到窥斑见豹的展示。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150.
[2][清]吴航野客.驻春园小史[M]//明清小说序跋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102.
[3][清]黄荻散人,[清]名教中人.玉娇梨好逑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4][清]荑秋散人.玉娇梨[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5]李鸿渊.情礼调和,皆大欢喜——从社会文化思潮看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团圆结局[J].船山学刊,2003(3)118-122.
[6]刘勇强.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新发展[J].文学遗产,1998(6)74-86.
责任编辑 张吉兵
2016-11-14
10.3969/j.issn.1003-8078.2017.04.16
郭海峰(1981-),女,安徽淮北人,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系讲师,硕士。
I206.4
A
1003-8078(2017)04-006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