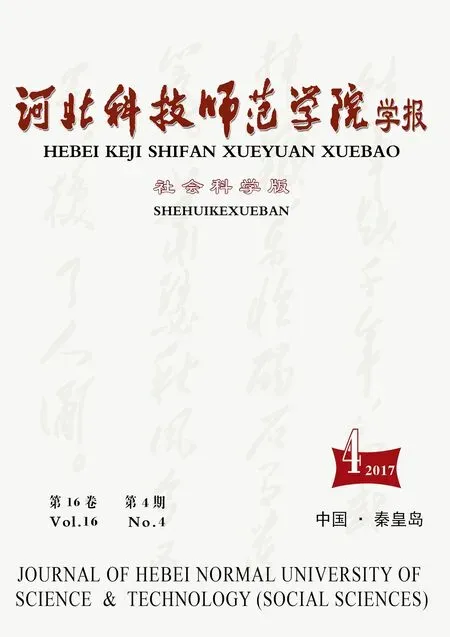石崇《金谷诗序》与王羲之《兰亭集序》比较研究
2017-03-08尹雅萍
尹雅萍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石崇(249~300年),字季伦,小名齐奴,渤海南皮(今属于河北)人。石崇是功臣子弟,因其父石苞为西晋开国元勋,而深得晋武帝司马炎器重,多任重要官职。石崇是一位饱受争议的文人,主要原因在于他人格的二重性,他谄媚权贵、奢靡无度,但他又爱好文学,才情满溢,为西晋著名“二十四友”文人群体首领。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是琅琊临沂(今属于山东)王氏世族后人,自小聪颖,颇受长者喜爱。羲之注重个人修养,自带风雅才情,尤擅长各体书法,是东晋有名的书法家,并有“书圣”之称。羲之在文学方面亦有造诣,是东晋时期重要文人之一。
《金谷诗序》是石崇在金谷集会中为《金谷诗集》所作的序文,写于西晋晋惠帝元康六年,即公元296年;《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于兰亭集会为《兰亭诗集》作序,兰亭集会是在东晋晋穆帝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举办。两次文人雅集相隔47年。结合时代背景,将两篇诗集序文进行比较,亦是对两次集会的比较。对比两晋文人雅集,探讨西晋时期文人自发组织文学活动的特点,观察西晋到东晋士人们的心态转变,亦是本文写作目的。
为方便比较研究,现将石崇《金谷诗序》一文兹录于下: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
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一、序文活动内容的比较
石崇《金谷诗序》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后文简称石序、王序)是两晋时期文人自发组织雅集活动的历史记载。两次文人雅集都成为了历史佳话,对后世文人的文学活动有着重大影响。两篇序文的内容与现当代的记叙文颇相似,记录了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和过程。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兰亭集序》的序文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模仿着《金谷诗序》,并且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
(一)《兰亭集序》对《金谷诗序》内容的模拟
“汉末魏晋,由混战及其他原因,促成都市及庄园的发展……所谓庄园,有供给经济的庄田,还有供给游居的园林。当时的园林很发达,最有名者,北为石崇的洛阳金谷园,南为王羲之的会稽兰亭。一时的文人,不是自有庄园,就是做有庄园者的清客。”[2]128-129由此可知两晋时期多有文人雅集活动,而《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便是来自金谷园与会稽兰亭这两大著名庄园的文人雅集。
“西晋石崇等人组织的金谷雅集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文人自发组织的雅集活动。”[3]115此次集会不由统治者组织,文人名士在石崇的组织下,一同赴宴金谷园,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并将集会中创作出的诗歌作品编集,由东道主石崇为诗集作序,即《金谷诗序》,此序开启了一场专属文人群体的文坛盛宴。作为文人雅集的先驱,金谷集会与《金谷诗序》都有着不俗的开创之功。
《世说新语·企羡》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1]346这段话记载了王羲之听说世人将《兰亭集序》与《金谷诗序》进行了比较,又把自己与石崇相匹敌,感到非常的开心。西晋金谷集会对后世文人雅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可见一斑。在相隔半个世纪之后,东晋王羲之不仅有意从形式上模仿金谷雅集活动,就连序文写作也对《金谷诗序》进行了模拟。
《金谷诗序》的序文内容是后人王羲之为《兰亭诗集》作序的重要参考模板。序文内容大致为描写集会的时间、地点,集会活动的缘由,集会之地的优美风景,记载集会参与对象,集会的过程以及作者的思考感悟。两篇序文都是为活动中产生的诗歌结集作序,但都没有对诗歌作品进行评价,纯粹由作者记录一场文人雅集以及抒发对人生的感慨。整体观之,可见王序对石序的模拟。
(二)王序内容详细、议论深刻,整体超越石序
《兰亭集序》不仅是对《金谷诗序》的模拟,更是对《金谷诗序》的超越。石序内容架构有序、清晰明了,但整体较为简单、浅显。而王序内容比石序更有层次,主次更为突出,不仅描写丰富到位,议论也更加深刻,羲之对生命哲思的高度与深度是超越石序的重点所在。同时两篇序文也展现出晋代文人自发组织文学活动的某些特点。
1.文人雅集的主要内容
两次文人雅集活动的起因不同,石崇在序文中交代是为了送别征西大将军王逸,可见其重情义的一面;兰亭集会是“修禊事也”,修禊是古时一项很重要的礼俗活动,人们利用这个风俗聚在一起,到水滨洗濯祈福。虽然缘由不同,但两次雅集活动都以饮酒、赋诗、酬唱为活动主要内容。在石崇笔下,金谷集会可谓盛况空前,金谷园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1]291尽显士人纵情游玩不知疲倦之态,并在“琴瑟笙筑”“鼓吹递奏”下赋诗叙怀,展现文人赋诗酬唱于丝竹声色中,乐趣无穷;而兰亭却无丝竹管弦相伴,与金谷园的嘈杂相比显得静谧怡人。兰亭雅集以水流声为乐,洗涤世俗之心,文人于一觞一咏间畅叙幽情,在天朗气清的山水怀抱间赋诗酬唱。两次集会赋诗酬唱皆为文人雅事,乐趣无穷,但羲之笔下的兰亭集会透出文人特有的高雅,优美的的措辞、俊逸的文笔让读者身临其境,在活动内容的展示上比石序更胜一筹。
赋诗酬唱是文人雅集的重要内容,为此两次集会都产生了诗歌结集,组织者也都为诗集作序。可惜《金谷诗集》失传,无法对两次集会的诗篇做直接的比较。虽然《兰亭诗集》保存较好,可惜兰亭诗歌充满了“玄言”之味,没有突出的佳作。两次盛会在诗歌作品上没有取得突出成就,实为两晋诗歌憾事。
2.文人雅集的参与对象
石崇是西晋首富,时任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又是著名文人团体“二十四友”首领,颇有才情与威望;王羲之是东晋第一门阀王氏世族后裔,时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为会稽郡的地方长官,与石崇皆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上层人物。但石崇人格具有二重性,他耽于享乐、沉迷财富与清俊高雅的王羲之形成鲜明对比,也给两次集会抹上了不同的色彩;二人都于集会中思考人生,石崇在欢乐的集会中只叹息“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1]291。相较之下,王羲之花大量笔墨书写对人生的思索,以人生基本问题发论,推古及今,放眼高远,对生命的哲思占据了整篇序文的三分之二,成为了《兰亭集序》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王序超越石序的重点所在。另外两次参加集会的人员亦是有着一定身份地位的上层人物。石序记载参与者30人,但名单没有完整保存下来。根据石崇与“二十四友”文人团体交往频繁来看,可推测金谷集会以“二十四友”为主;而王序中记载兰亭集会有41人参与,多为会稽地文人名士。
从组织者的身份来看,可知举办盛大文学集会当有一定的权利、财力、物力,同时还需一定的文学影响力与个人魅力。能否成功举办一场盛大的文学集会并对后世产生影响,组织者的能力是重要的前提。另外从参与者的身份来看,两次文人雅集从侧面反映出晋代的文人雅集多为上层人物的文学盛会,盛大的文人集会是贵族身份的象征。晋代的门阀士族不仅是对政治权利、物质财富有着绝对的占有与垄断,对文学不能说全面垄断,但也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占有权,文人雅集更为门阀士族所左右。
3.文人雅集的活动地点
西晋的社会风气整体崇尚奢靡,作为突出人物石崇,颇受后人诟病的奢侈生活更在集会地点中充分展现。石崇选择在自己的私宅金谷园中举办集会。金谷园位于天子脚下洛阳郊外,因金谷水流入而得名。金谷园依山而建,自然景物与人工造景相结合,再加之其序文写到“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1]291金谷园的豪华壮阔、高贵奢靡一览无遗,石崇追求享乐不免给《金谷诗序》增添了低俗的趣味。
王羲之举办的兰亭集会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是南方缤纷秀丽山水景色的代表。“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4]2099在羲之诗人的眼光与优雅的笔墨中极尽展示着兰亭山水的秀美。集会众人在纯天然又景色怡人的兰亭里心旷神怡,精神上的陶冶与享受是金谷集会无法比拟之处。再加上给人感知能力创造有利条件的“天朗气清,惠风和畅”[4]2099,更是让众人置身于自然美的无限遐想中。
两序都用笔墨来突出集会环境的优美,反射出两晋文人寄情山水的情怀。亦可见晋代文人自发组织的集会多与自然为伴,追求心灵享受。而西晋金谷集会沉迷物质上的享乐又给文人雅集带来俗气的一面,后世当引以为戒。
《兰亭集序》对《金谷诗序》的模拟,兰亭雅集对金谷集会的超越,让我们看到文学史的推进,就在于后人对前人的模仿与学习中实现的超越,在否定之否定中得到的进步与完善。王羲之是一位善于模仿与学习的文人,正如他的书法成就来自于对书法前辈的学习与超越。他对石崇的金谷集会的模拟亦是如此,因而王羲之对金谷集会并不是全盘照抄、盲目吸收的学习与模仿,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金谷集会中文人寄情山水、饮酒赋诗的雅逸情趣,舍去金谷集会中沉迷物质享受的低俗趣味。这也是兰亭集会在对金谷集会的模拟中实现的巨大超越,并对后世产生更为重要影响的关键所在。
二、序文思想情怀的比较
两晋在玄学思想、社会风气上仍有许多关联,但从总的思想风貌上看,西晋与东晋又大不相同,从《金谷诗序》到《兰亭集序》所传达出的士人不同心态正是两晋士人思想风貌发生转变的缩影。
(一)人生理想的世俗化与艺术化
西晋时期儒家思想失去控制力度,不作为规范约束众人行为的强大力量。再加上西晋政权比较稳固,统治者采取宽宏纵任态度,导致政失准的,士人没有是非价值标准。西晋士人心态普遍呈现为追求名利、崇山奢靡和纵容己欲,石崇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石崇早年亦是一个有理想抱负的青年,其文《思归引序》言:“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5]2041这篇序文不仅被萧统编入《昭明文选》,还被李兆洛收入《骈体文钞》评之气体不俗。只可惜建功立业之心终究掩埋于奢靡的社会风气中,石崇的人生追求化为“士当身名俱泰”[4]1007,随波逐流地沉迷于对财富权力的占有,与石崇交好的潘岳亦是如此。在西晋普遍平庸的士风中,无须过于苛责石崇人生理想变为世俗化。石崇的晚年亦是被金谷园豪奢的生活所占据,但在世俗化的追求中,他又有对诗文、音乐上的艺术追求,但这方面的比例过少,于物欲面前显得娱乐化。
东晋王羲之基本将人生理想变成艺术化追求,这与东晋南迁政权稳固之后,士人面对南方的佳山丽水产生的偏安心态有关,另一面东晋玄学日益繁盛,士人相聚必清谈,深刻影响着士人的精神生活。东晋中期门阀士族注重文化修养,王羲之人生理想追求的艺术化实乃顺势而为。在东晋建功立业无望的政治环境中,王羲之的人生追求转向了明山秀水的江南庄园,常在文学与书法的艺术中修身养性,把生活变得艺术化。羲之带领众人聚于山阴兰亭,把酒言诗,畅叙幽情,兰亭集会正是人生理想艺术化追求的表现之一。
(二)雅逸情趣追求的层次不同
罗宗强提到:“金谷宴集,在两方面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士人留恋山水的心态,一是诗文创作作为留恋宴乐的雅事出现。”[6]73文人雅集不论是留恋山水或是诗文创作留恋宴乐,都是晋人追求雅逸情趣的思想表现,也是对魏晋风度的传承。魏晋风度以竹林七贤团体为代表,他们常聚于山林,饮酒、赋诗、服药、清谈等行为受到后人争相模仿,形成魏晋时期特有的士人风气,后世文人雅集追求雅逸情趣亦是对竹林七贤的模仿。
两次集会对魏晋风度的传承存在差异性,金谷集会多是停留于表面的学习,从形式上学习竹林七贤山水中饮酒赋诗,对魏晋风度内涵领略不多。首先金谷园的“美”是石崇作为个人私有财产占有,无法给予集会众人自然美的意境;再者金谷集会中文人赋诗酬唱、清谈表现形式是娱乐化的。金谷集会主要目的是以享乐为主,无法与竹林七贤相比拟。
兰亭集会则大不相同,东晋士人用诗人的眼光欣赏佳山丽水的美,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享受。以王羲之为代表,不仅倾心于道家的自然学说,同时也批判物质上的纵欲。羲之常通过书法、音乐、山水来提升自我修养,《兰亭集序》写得诗情画意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在王羲之组织下的兰亭集会,是一种高层次的雅逸情趣追求,士人纵情于山水间,领略人生真谛,用诗人的眼光欣赏美妙的事物,岂不快哉!
(三)二序悲哀情怀的基调不同
两晋文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存在价值,是文人雅集感叹生命苦短的重要原因。石崇与王羲之皆于人生过半之际举办文人雅集。看着生命之烛犹将燃尽,难免会产生悲哀的情怀。刘跃进指出:“石崇《金谷诗序》有‘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悲哀,《兰亭集序》有过之而无不及。”[7]50文人相聚本是一件乐事,可是两次集会的情感都出现悲喜相交的情况,可谓乐极生悲。相较而言,王羲之在宇宙中畅想遨游所发出的悲叹力量来得更加厚重,乐极生悲的情感更富有感染力。
西晋是司马氏家族用阴谋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石崇深谙“荣华于顺旨,枯槁于逆违”[4]1005之道,只有采取与政权合作的态度,日子才能过得轻松愉快。但是外在的富有永远不能弥补人生价值无处实现的缺憾,再加之元康之年政权跌宕,名士之心常有不安,这给“少有大志”却无处建树的石崇带来惶恐。《金谷诗序》表面上是纵情声色、追求享乐,内在却隐藏着人生的悲苦与无奈。宴会的快乐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短暂的问题,因而石崇贪婪地享受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以及时行乐之法来对抗生命的苦短。石崇在序文中详细罗列自己的官职,以此换取一丝精神上的慰藉。他的怀抱只能在集会中与文友诉说,他的追求只能寄托在山水诗乐当中。所有的不安也只能化为“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叹息,相比于《兰亭集序》,这句感慨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波澜不惊却蕴含着看不到希望的无限悲哀。
而身为东晋第一门阀王氏家族的子弟,王羲之并没有恃宠而骄、追名逐利。他以一位清俊雅逸的文人身份举办兰亭集会,在俯仰天地宇宙间,探索客观世界与自我认知。宇宙广而深厚、山水美而长久,与生命的短暂形成强烈对比。意识到“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4]2099的羲之不由得悲叹“岂不痛哉!”思索之处皆悲痛万分,也与聚会短暂的欢乐产生强烈冲突。情感由欢乐突转急下变成痛苦悲哀,其中的感染力、震慑力是石崇序文远不能及。另外玄学之风在东晋盛行,但是王羲之依旧保持着独特的个性,没有被玄学完全同化。在他的序文中勇敢提出了对老庄思想的质疑:“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4]2099否定生死等同观点,没有随波逐流附和老庄思想,不同于石崇陷入西晋奢靡之风失去自我。再者东晋玄学受到佛教思想的融入,常有僧人加入玄学清谈。多种思想的碰撞与融合,致使玄学家对抽象世界的认识超过老、庄、易三玄的认知范围,也正是基于这点,王羲之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人生命运的认识,比石崇来得更到位、深刻,对生死名利问题的哲思,也体现了羲之超人的豁达情怀,因而《兰亭集序》的思想表现得更加深刻厚重。羲之的悲哀是建立在生命的崇高之上,石崇的悲哀是与世俗名利相结合的,二者的情怀基调大不相同。
从二序的思想情怀对比中,可见两晋名士不受名教束缚,率性而为,在不同于以往的宽松政治文化氛围中,更加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思想上的最大变化,就是缺少建安时期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人生理想,因而两晋文学缺乏慷慨激昂的情怀,两篇序文亦是如此,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但二序表现出追求雅逸情趣的思想却为后世所追捧。
三、序文形式的比较
序文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褚斌杰介绍了“序”体:“实际上序或叙,就是在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和目次,加以叙述、申说。”[8]389石序与王序皆是为诗集作序,通过序文向后世交代诗集出现的缘由,展现文人雅集的盛况。两篇序文写法上各有特点,以下做具体的对比:
(一)石序多用长短句,王序多以四言为主
在句式上,石序的最大特点就是长短句的交叉使用,开篇首句介绍自己的身份:“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1]291此句长达25字;而介绍游宴盛况之处:“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1]291多以 4 字短句为主;另有“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1]291仅有“及住”的二字短句与六言句搭配。在句式上石崇没有追求齐整,写得比较随心所欲。序文随心记录集会盛况,文笔自然流畅,语言上无铺张辞采,与“绮靡”的西晋文学较为不同。
王序虽然也以散句为主,但整体较于石序更为齐整。王序多以四言为主,长句不超过九字。王序第三段关于人生命运的哲思遐想:“夫人只想与,俯仰一世。”[4]2099以五言、四言搭配使用为主,强化了感慨力度。王序不似石序长短句的悬殊,也不像骈文那样死板。句式上的穿插变化反而给人错落有致,读来朗朗上口的美感。王序的语言清新自然,如写景之句:“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4]2099辞藻优美却无修饰之感,比石序显得更为庄重典雅。
(二)石序风格浅显朴质,王序风格清朗俊逸
石序篇幅短小,仅有二百余字,全文主要以写集会之象为主。在行文上多是对现实之物的直接记录,开篇直接摆列出自己的官职以及金谷园拥有的物资,在遣词造句上自由随意,对事物描述的文字也是贴近生活,整体呈现出浅显朴质的风格。句式上虽然错综变化,但由于平实无华的文字,导致石序的语势没有跌宕起伏。后人常用“繁缛”评价太康诗风,西晋的文、赋也有这个特点,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骈体文,辞藻华丽,雕琢堆砌成风。石崇与潘岳等人交往密切,而此序不受影响,实乃“繁缛”化的西晋文学中一道特别风景。
东晋文学受到政治环境与玄学的影响,相比西晋文学较为平淡,加之东晋门阀士族注重精神文化修养,整体风气偏清虚恬淡,王羲之便是代表之一。王序的行文舒卷自如,文笔优美自然,情景交融的描绘给人营造出诗情画意之美。序文整体上较为齐整和谐,给人以舒适之感。在用典上王序灵活自如,概括后的典故自然的镶嵌于文中表达己意,例如引古人之言“死生亦大矣”[4]2099,加重序文的悲慨力量;或用“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4]2099否定老庄思想中绝对化的生死观念。《兰亭集序》饱含了王羲之的审美感受与哲思遐想,在其优雅的文笔中呈现出清朗俊逸的风格特点。
总体来说,两篇序文都是叙中夹议。《金谷诗序》是以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作为线索,语言简朴叙事清晰,是一篇朴实无华的记叙文。《兰亭集序》是以议论为主的序文,作者的思考为主要部分,文章积满感情,在生命苦短问题上劈空而起,是一篇情理兼长的议论文。王序强烈的情感抒发与深刻的哲理思考相融合,给人触动与深思,较于石序更为后世所认可。再者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不应绝对化的完全取决于人品,石崇是文学史上较为特殊的文人,切不可因人废文。正如王世贞之论:“石卫尉纵横一代,领袖诸豪,岂独以财雄之,政才气胜耳。《思归引》《明君辞》情质未离,不在潘陆下。”[9]122作为文人,石崇亦有着独特的才情与优点。《金谷诗序》虽不及《兰亭集序》,但两篇序文皆为古人追求雅逸之事,它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流传于世,必有其文学价值与内涵,后人皆当多给予关注。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罗建伦.再论金谷雅集[J].齐鲁学刊,2012(4):115 -118.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萧统.昭明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M].西安:世界图书西安出版公司,2014.
[8]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王世贞.苑卮言校注[M].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