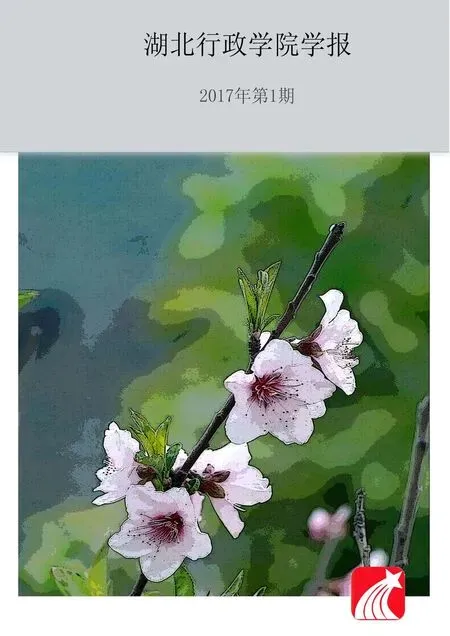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
2017-03-07施远涛
施远涛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
施远涛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可知,中国家户制是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并为中华农业文明与农民价值伦理奠定了基础;印度村社制则源于雅利安人与达萨的冲突与融合,其鲜明的特点是种姓制度与宗教思想的嵌入,它是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内部事务不受国家干涉。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生成过程可知,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本源型传统和基础性制度,是村落社会的根基。当前农村家户的离散和流动破坏了家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损坏了乡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得乡村社会的治理及其现代化转型面临新的挑战。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塑农村家户,筑牢乡村社会的基础。
家户制;村社制;制度起源;本源型传统
DOl:10.3969/j.issn.1671-7155.2017.01.011
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过程中。在探索乡村社会未来转型之路时,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1]。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过去”,并引用中国经典文论《诗品》中的名句:“结合故旧,产生新颖”[2](P20)。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中国的家户制与印度的村社制,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与沉积后所形成的制度因子,生长于农村社会的本源型传统中,构成了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基础的“底色”以及制度创新的“源头活水”,并规制着未来农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然而,作为两个东方国家村落中的本源型传统,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东西方之间。因此,需要从微观层面去厘清二者的差异,把握二者的个性。不了解二者之间的差别,哪怕是细微的差异,都无法准确把握这两个均具东方农业文明的本源型传统对后来农村发展及其制度变迁的影响。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历史深处,选取中国家户制作为切入点,以印度村社制为参照,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的分析范式,通过深入细致地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的生成过程,准确把握“家户制”这一具有“中国特性”的本体制度,进而从传统中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建立起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
一、理论基础: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
制度在动态的历时性过程中生成并维系,故制度的生成、维系与变迁在形式上构成了制度运作过程的不同阶段,而解释制度的生成和变迁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卡尔·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分析和研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而马克斯·韦伯从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来观察政治制度的产生;行为主义则因为忽视制度而基本上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生成理论。现代政治科学真正从自身的生成变化规律角度来研究和解释制度生成和变迁的是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从产权理论、囚徒困境和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制度的生成和变迁进行分析,并构建出精致的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模型。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深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影响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视角,并基于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一套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是因为相关的利益主体基于利弊的考量而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的契约规制,这种规则能够为相关个体带来较之于其他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
但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种制度起源理论虽然为政治科学的制度起源提供了精巧的解释,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如它的功能主义视角、目的主义以及自愿主义色彩等[3](P221)。因此,在融合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生成理论将个体视为扩大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观点,以及谢茨施耐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冲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制度生成理论框架。第一,新制度的创设或采用是在已经充满了制度的世界中进行的。第二,制度起源于既存的制度偏见所引发的冲突而不是合作,或者旧制度在新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机,从而引发出原有制度之下的政治主体产生改变现存权力的企图。第三,新制度的建立虽然存在着制度设计的成分,但制度的起源并不在于理想化的设计。第四,制度形成的偶然性。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都受制于其背景提供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又是另外一些事件的偶然性联系的结果。所以,他们在对制度的形成进行解析时,一再强调历史进程的无规则性而不是规则性。另外,历史制度主义者积极进行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观念(理念)这一重要因素纳入其研究的范畴,将制度与观念结合起来,并将观念与制度纳入到“结构——能动”的框架中去进行讨论,故制度与观念之间的结构性互动成为解释制度生成的又一关键性变量组合。
从以上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生成的解析可以看出,旧制度、环境、观念和行动者是制度起源主要涉及的变量,制度起源的方式和时机就取决于这几个关键变量之间的组合。
二、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的起源
(一)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
1.家户制的形成: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生成的理论内核与关键要素,本文接下来将从宏观环境、旧制度、思想观念与行动者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进行一个归纳性的总结与阐释。
首先,从宏观环境及时代背景来看,家户制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方面,铁制农具较多的使用以及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但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当时的上层建筑依然是以奴隶制为主的奴隶社会。奴隶制社会的特征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其政治统治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维护其统治的组织形式是分封诸侯以维系天子的天下。各诸侯既是“王”的助手,又是“王”的制约力量,它是阶级统治还不甚成熟的一种松散的统治形式。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体系。奴隶主利用此国家机器对广大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奴隶对生产毫无兴趣,而且不断破坏生产工具,成批逃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此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有一种适应其发展水平的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
其次,从旧制度方面来看,如果说奴隶制度是主导这一时期的宏观制度环境,那么,支撑这一上层建筑的核心下位制度(中观层面的制度)便是以血缘内聚力为基础、通过分封建国的宗法制度。随着宗法制度内部所蕴含的冲突矛盾在新的宏观环境背景下变得愈发激烈,既有制度偏见所引发的冲突成为了新制度产生的重要因素。宗法制度所蕴含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其一,诸侯分封制。分封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必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4](P155)。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血缘的内聚力因代际相传而间隔式变弱,越来越难以起到有效凝聚统治力量的功能,故各诸侯国的地缘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独立性越来越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地域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政治上则逐渐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而脱离了周王室控制的各诸侯国,在对财富和疆土扩张的驱使下逐渐走向战争和冲突。其二,财富的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度中规定,家族的君位、王位和财富由嫡长子来继承,这也激发了宗族内大、小宗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其三,世卿世禄制度。世卿世禄制度的存在使得有能力的普通人无法凸显,造成板结式的社会堵塞,当新兴的异性大夫或贵族取得一定的地位后,势必希望打破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因而,便展开了与旧贵族间的矛盾冲突。
第三,从观念与行为方面来看,随着宏观制度环境的逐渐变化,以及上述宗法制度中这些矛盾冲突的加剧,优雅的周礼在这些诸侯国间以及各诸侯国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被彻底颠覆。一些诸侯国特别是弱小的诸侯国谋求变革的思想与图强的决心逐渐产生。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不仅使得秦国从一个弱国逐渐变强,最终统一了天下;最关键的是,商鞅变法中形成的家户制度以及高密度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即“两千年皆秦制”。可以说,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不在于修建万里长城,而在于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亿万自由家户小农的制度[1]。
2.家户制的形式与性质: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
通过上述过程形成的家户制具有如下形式与特性:第一,“五口百亩之家”是其基本形态。根据《汉书·食货志》中关于战国时期李悝为解决当时农民丰歉之年粮价波动很大而算的收支账目中的数据记载,当时一个个体家庭,一般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这不仅是普通平民的家庭形态,也是其他社会阶层的主要家庭形态。第二,个体家户既是基本生活单位,也是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在宗族制度下,大的宗族组织虽然也是由个体小家庭组成,但这里的小家庭还仅仅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生产的基本单位一直是宗族公社。而在家户制基础上形成的个体小家庭,不仅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所有的生产活动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一户小农,占地百亩或数十亩,全家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用简单原始的农具,在小块土地上辛勤的耕作。同时,个体小家庭也是一个独立的消费单位,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而且,这样的个体小家庭还是一个进行社会活动和交往的单位,由家长或者家中长者代表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积累家庭的社会资本。第三,个体家户是一种农工商结合与互补的自然经济生产单位。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家庭,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家中的女劳动力也利用房前屋后种的桑麻,田边地角种的瓜菜,从事采桑、养蚕和织帛及饲养家畜、家禽等生产活动,以补贴农业生产的不足,从而形成了农工商结合与互补的基本经济形态。第四,个体家户是国家户籍登记以及征收税赋、兵役与徭役的基本单位。国家在对人口的户籍进行登记时,以个体小家庭为基本单位编制户口,并确定家庭中的一位作为整个家庭的代表,也即“户主”,这样国家直接将个体小家庭置于管辖之下,而无需再经过宗族组织这一层关系;同时,国家以个体小家庭为基本单位征收税赋和征发兵徭。
3.家户制传统的历史地位:中华农业文明与农民价值伦理的基础
可以说,家户制传统的生成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首先,家户制传统形塑出的个体家户同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农业文明。对此,著名历史学家胡如雷在其经典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中这样写道:中国封建社会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而自耕农在经济上又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同样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很长时期内,经济、文化比西方相应阶段远为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5](P127)胡如雷先生这里所说的自耕农其实就是“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家户小农。可以说,在中国封建历史上,自耕农(个体家户小农)经济的繁荣或枯萎,实际上是测量社会经济兴衰、阶级矛盾缓和与激化的晴雨表。而且,在这样的个体家户基础上,形成了辉煌的后来学界所谓的“传统小农经济”。
其次,它形塑了中国农民的价值伦理。在家户制传统的形塑下,中国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家庭观念,一切行动以家庭为中心,并进而形成了一种家庭(家族)伦理或信仰。对此,金耀基先生所引用的几位学者就有如下的说法。艾勒塔斯称:“中国人对财富、荣誉、健康拥有强烈的动机,对家庭与祖先有能力表达虔敬,这些毫无疑问是决定性的文化因素,足以开出一种勇猛的经济行动。”勃格的论证最后也归结到传统的家族心态上:“这是一套引发人民努力工作的信仰和价值,最主要的是一种深化的阶层意识,一种对家庭几乎没有保留的许诺(为了家庭,个人必须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及一种纪律和节俭的规范。”由此可以看出,在家户制的形塑下,家庭不仅成为个体生活和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成为个体心灵的归属乃至信仰。很多时候,中国人并不是为了个体的存在而生活和工作,家庭(家族)意识才是激发大部分中国人肯定其生命意义和工作伦理的原动力,这个原动力塑造了中国人勤劳、节俭和“卖命”工作的形象。
(二)印度村社制传统的起源
1.村社制的形成:雅利安人与达萨的冲突与融合
关于印度村社制的起源,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它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产物。马克思根据共同体分解程度的不同,将全世界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共同体分为三类,即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其中,亚细亚的共同体在历史上出现最早,分解程度最低,因而也是一种较原始的、陈旧的形式[6](P357)。而印度的村社是属于亚细亚共同体的典型形式,它起源于古代原始社会的部落共同体,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一系列的分化和解体而形成。故此,在我们探究印度村社制传统的起源时,首先得将历史的镜头聚焦到印度雅利安文明时期。
早在雅利安人到达印度之前,印度河流域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犁耕农业,并兴起了城市文明,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虽然逐渐走向衰落,但犁耕农业依然存在。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有一支操“印欧语”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定居,随后逐渐开始往东向恒河流域推进。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雅利安人的活动中心逐渐从旁遮普移向恒河——朱木拿河河间地区和恒河上游,并进而向恒河中下游迁移。早期印度——雅利安部落是游牧民族,当他们第一次迁入印度河——恒河平原时,碰上的是被称作达萨(Dasas)的其他定居者。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雅利安人是落后于继承哈拉巴文化的当地居民的。因此,当雅利安人开始在恒河平原安顿下来时,便在和当地居民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渐掌握犁耕技术,并改变自身的生产方式,从单一游牧业转为游牧业和农业的混合;同时,他们也逐渐改变以前游牧生活的习惯,在所到之处建立居民点和村落。
印度——雅利安的村落称为格拉马(Grama),村落带有氏族社会的残余,普遍采用农村公社的形式。当然,由于印度国土辽阔,如前所述三个亚地理区域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不同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在同一时期,印度各地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同(主要指公私比重不同)的农村公社。英国学者巴登·鲍威尔(B.H.Baden-Powell)在《印度村社的起源与变迁》一书中就特别强调:“必须承认有两种类型的村社:一种是存在共有或公有现象的村社,另一种是不存在共有或公有现象的村社。”[7]巴登·鲍威尔称前者为“共有制村社”(Joint Ownership Village),称后者为“分有制村社”(SeparateOwnershipVillage)。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村社,它都属于村社制范畴,都具有村社的性质。
2.村社制的特点:种姓制度与宗教思想的嵌入
当雅利安人首次来到印度时,他们自己被划分为三个广义的社会阶层,被称为瓦尔纳(Varnas,阶层):分别是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与贵族)以及吠舍(平民)。在雅利安人逐渐往印度西北部以及向恒河流域扩张的过程中,随着被征服的当地人的加入以及雅利安人和当地人联盟的后裔逐渐融入到雅利安社会当中,这三个阶层与第四个正在形成的首陀罗阶层一起产生了四个瓦尔纳阶层,这四个瓦尔纳为印度社会的演化提供了一个宽泛的理论框架。在随后的实践中,瓦尔纳又进一步被细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对内通婚的职业群体,从各式祭司、商人、鞋匠到农民,形成了职业秩序的神圣化,最终演变为重叠于血缘结构之上的种姓制度(Caste)。从经济层面看,种姓制度是一套严格的职业分工。从婚姻层面看,为了维护高级种姓的特权地位,种姓制度还确定了内婚制,也即任何人通常不得与自己瓦尔纳之外的人谈婚论嫁。这种严格的内婚制原则在种姓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以至于一些研究种姓制度的学者把族内婚视为种姓制度的本质。从等级层次看,种姓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由此,种姓职业的世袭化和种姓内婚制共同奠定了以婆罗门为主导、等级森严、层级分明的种姓制的基础。
与此同时,在种姓的演化过程中,为了使这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合理化和缜密化,人们也给种姓制度提供了一种宗教和哲学上的基本原理与思想。这种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婆罗门创造出的“业报轮回”思想。他们认为社会升迁在现世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指望来世,个人在来世到底获得升迁还是降级,则取决于自己在现世是否履行了所属迦提的法(Dharma),即良好的行为准则;未能遵守准则的,将在来世等级制度中降级。在这种教义思想下,人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从事不同的职业,履行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享有不同的地位和报酬,乃是一种神安排的自然秩序,对每个人都是公平合理的。对于一个低种姓或不可接触者来说,业报轮回思想告诉他,他悲惨的命运并非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人间压迫所致,而是他前生的罪孽造成的,他受的苦难是在偿还他自己前生欠下的“债务”。要改变这种地位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接受命运的安排,严格遵守“达摩”(种姓的职业以及各种行为规范和义务)。只有这样,来世才有提高地位的可能,否则,“阿特曼”会记录下他们今世的“不轨”行为,来世可能会更悲惨。而高种姓认为,他们高贵的种姓地位是他们前生“善行”的结果。故马克斯·韦伯曾说:“种姓本质即为社会阶序,而婆罗门之所以踞有印度教的中心地位,根基即在于社会阶序决定于婆罗门。”[8](P40)
由此可见,种姓制度和宗教思想的结合可谓是天衣无缝,二者结合在一起犹如一张无形的网嵌入在村社中,将村社内的成员牢牢地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使得古老的印度村社具有高度的稳定性。韦伯将这种结合称之为是“神来之笔”的结合,他说:“种姓的正当性与业报教义,因此也就是婆罗门特有的神义论,这种可谓神来之笔的相结合,根本是一种理性的伦理思维的产物,而非任何经济‘条件’的产物。直到此种思想的产物通过再生许诺而与现实社会秩序结合,才给了这个秩序无与伦比的力量,超越过被安置在此秩序中的人们所抱持的思想与希望,并且立下确固的架构,致使各个职业团体和贱民部族的地位,可以在社会上与宗教上被编排妥当。”[8](P168)
3.村社的形式与性质: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
由种姓制度和宗教思想嵌入所形成的印度村社构成了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印度传统村落社会。除了残留有一些原始氏族公社的特征之外,印度传统村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第一,村社内已形成了以种姓制度为主的阶级结构与剥削关系;第二,村社土地所有制具有公私二重性;第三,村社内部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第四,村社内存在着以种姓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第五,村社内形成了相应的权力关系与治理形式;第六,这种村社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综合上述这些特征,可以将这种村社看作是一种“半野蛮、半文明的村社”和“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马克思对印度这样的村社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制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9](P682-683)而摩尔在其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谈到印度村社时,也这样写道:“这里,我们可以把种姓制度作为世袭的和内部通婚的群体组织加以描述。在种姓集团里,男子执行着某种类型的社会功能,如僧侣、武士、手工业者、种田人等等。制裁玷污罪的宗教观念强化了这种社会分工,在理论上使得等级制度严密得滴水不漏。种姓制度在当时和现在起到组织村庄共同体生活的作用,构成了印度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元。”[10](P255)
4.村社与国家的关系:村社内部事务不受国家干涉
与中国家户制传统下,个体家户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不同,在印度村社制传统下,村社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同国家直接发生关系。国王直接任命村长,《摩奴法论》规定国王“应该任命村落长、十村落长、百村落长和千村落长”。而在向国家缴纳田赋时,也是以村社为单位。由于在村社内由种姓和宗教创造的社会分类形成了稳固的村社内部结构,这大大限制了国家权力向村社内部的渗透和掌控。因此,村社除了向国家缴纳税赋之外,其内部事务几乎不受干涉。而居民们生活在这种村社共同体之内,对王国的崩溃或分裂毫不在意。正如摩尔所说:“作为一种制度,种姓能在某一特殊地区有效地安排生活,这就意味着全国政权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凌驾于村社之上的政府一般只是外部强加的赘瘤,而不是出于需要,是一种必须忍受的事务,即便当环境变得很不协调时也不能加以改变。政府在村社里确实无事可做,因为事无巨细都由种姓包揽了。”[10](P273)只要村社保持完整,他们就不管隶属于什么权力,也不管受哪个君主统治。一份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官方报告对此也曾描述道:“(村社)居民对各国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11](P66)
三、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传统起源的归纳比较
“形形色色的历史种籽播撒在不同的历史土壤中,在某块土地上这一类种籽破土而出,茁发为参天大树,而在社会历史环境悬殊的另一片土地上,却遭到摧折,以致不得不让位于另一类植物群落,由此形成了风格迥异、类别歧出的社会景观。”[10](P3)那么,在这两个均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东方社会里,又何以会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制度传统呢?
在中国,自私有制形成后,原始社会出现分化,中国逐渐从原始社会过渡到三代(夏、商、周)时期。由于私有制导致社会分化并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处于支配(统治)方面的阶级为了维系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一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从实践中生产出一套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对内管理家族对外统治王国的宗法制度(思想)。这种制度(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维系家族内部的分配秩序以及统治整个王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与宗教思想相比,还远未达到通过教化逐渐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以维系整个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世俗权力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随着在宗法制度中通过分封获得资源的各诸侯(宗子)实力日趋增强,为了提高自身在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争夺更多的权力和资源,纷纷产生各种冲突,包括与中央权威的冲突以及各诸侯间的冲突,旧制度所蕴含的冲突在宏观制度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愈发恶化。而持续的战争冲突一方面使得宗法制度逐渐式微,另一方面催生了许多新的制度,比如在持续的战争冲突中,各诸侯国逐渐发展出一套体系健全的官僚机构,郡县制的兴起使政权脱离族权而独立等;同时,持续的战争冲突还产生了对兵役和税赋的大量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处于统治地位的阶层为了能够将自身置于更有利的地位,开始进行改革尝试。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秦国商鞅变法这种新思想、新观念的输入,正好契合了当时的背景,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因而,在君、臣、民三位一体的行动中,商鞅变法取得成功,家户制得以产生。而秦国凭借家户制的改革,实力得到增强,并最终统一其他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家户制传统也在高度统一的集权制权威的保驾护航下,在全国得以强制性推广,使得家户制随即蔓延渗透到整个帝国,家户制由此得以确立和巩固。
而印度在从公有制基础上的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以职业世袭和内婚制为特征的层级分明、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的嵌入,将人们牢牢的固定在某一位置上;宗教思想的嵌入从意识形态(思想)方面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种等级序列,使得人们没有改变和打破这种常规行为模式和社会生活形式的任何激励。同时,由于宗教思想的嵌入与发展,印度的世俗政权始终没有取得至高无上的合法地位,物质力量被认为低于精神力量,掌管世俗权力的刹帝利在种姓序列中排在操持宗教事务的婆罗门之下。由此,印度农村社会形成了以共有制大家庭为基础、公私二重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互惠和分配制度,对外部政权具有极大的独立自主性而对内自给自足、高度自治的村社共同体,以及与这种组织相一致的村社制度。
综上所述,在中国和印度由公有制基础上的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进程中,由于印度社会中种姓制度和宗教思想的嵌入,二者相互加强,相互拱卫,形成了严密的、能够有效调控和维系不平等等级序列的制度和关系网络,从而使得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村社的大部分形式得以保留,部分得以改进,从而形成了以共有制大家庭为基础的、公私二重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种姓为基础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工的村社制度。而中国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宗法制度(思想),本身并不具备有效调控其内部所蕴含的冲突的能力。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宗族内部的冲突不断,并在持续的战争冲突中,产生了制度变革的需求。秦国商鞅变法思想的引入,使得家户制出现,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又使得家户制得以确立和推广。因此,家户制传统最终在中国乡村社会产生并延续和发展。
四、结语
从上述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路径可以看出,与印度的村社制不同,家户制才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本源型传统和基础性制度,是村落社会的根基。虽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其外在表现有所变化,但内核却相同。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效法苏联的集体村社制而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断裂期,但家户制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本源型传统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永久地留存在中国农民的意识里。故当条件成熟后,家户制思想从农民的意识深处苏醒过来,再次回归其本源,并在延续家户制本源性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从而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前,农村家户的离散和流动,破坏了家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损坏了乡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得乡村社会的治理及其现代化转型面临新的挑战。因此,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塑农村家户,筑牢乡村社会的基础。而在未来乡村社会转型的道路上,我们在昂首向前,邯郸学步的同时,也要俯下身看一眼脚下的土地,回过头望一望走过的历史,因国因地制宜,尊重本源型传统,跳出“东施效颦”的怪圈,用“历史的耐心”走好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之路。
[1]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8).
[2][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许倬云.西周史[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5]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B.H.Baden-Powell.TheOrigin and Growth of Village C ommunities in India[M].London:Swan Sonnenschein& Co.,Li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9.
[8]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M].康乐,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M].拓夫,等.华夏出版社,1987.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李淑芳)
施远涛(1986—),男,湖北襄阳人,管理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印地方治理比较研究。
D691.7
A
1671-7155(2017)01-0056-06
2017-01-01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印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比较研究:基于实地调研”(项目编号:15JJDZONGHE0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