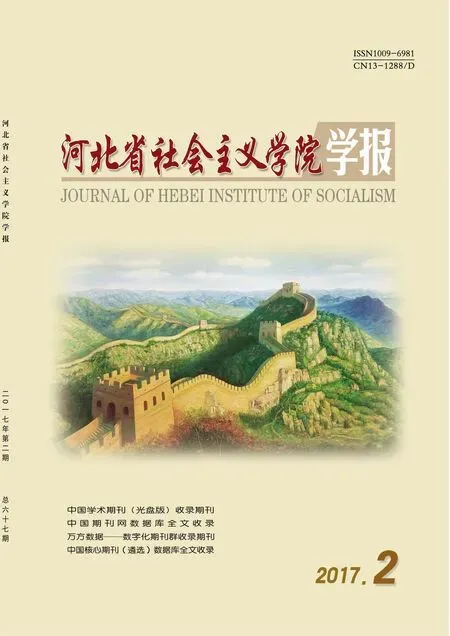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的历史际遇
2017-03-07温小勇班爱荣郑建敏康小莉
温小勇 ,班爱荣 ,李 娟 ,郑建敏 ,康小莉
(1.4.5.石家庄学院 西柏坡文化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35;2.石家庄学院 外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3.石家庄学院 马列部,河北 石家庄 050035)
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的历史际遇
温小勇1,班爱荣2,李 娟3,郑建敏4,康小莉5
(1.4.5.石家庄学院 西柏坡文化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35;2.石家庄学院 外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3.石家庄学院 马列部,河北 石家庄 050035)
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协商民主进而转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制度安排。西柏坡协商民主实践的推进,是近代中国历经传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碰撞的产物,彰显了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主的历史逻辑。对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历史际遇的考察,更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独特属性,深切认知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实在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西柏坡;协商民主;马克思主义;传统价值理念;民主革命
研究表明,“西柏坡协商民主由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民主理想和协商精神落实为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实践运动,其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在‘大历史’背景下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不是偶然的历史碰撞,而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产物。西柏坡时期,在各种趋向民主的力量的酝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万水朝东、众星拱北的态势,其本身也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实践的伟大成果和必然结局。”[1]既然“不是偶然的历史碰撞”,那么,协商民主由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的一种理念成长为西柏坡时期的一项“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实践运动,并最终转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必定包含着深刻的历史际遇;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必定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史洪流“大浪淘沙”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八十年前的红军长征时指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经历了近代中国传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碰撞,彰显了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主的历史逻辑。
一、传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碰撞
马克思主义形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用于指导彼时欧洲工人运动和未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在几乎同时,伴随着西方列强在华设厂,中国刚刚出现了早期的工人阶级。与欧洲工人阶级寻求自身解放的使命不同,中国工人阶级肩负着解救民族危亡和获得自身解放双重使命;与欧洲工人阶级需要同资本家阶级展开不妥协的斗争不同,中国工人阶级需要同压榨他们的资本家阶级以及与其紧密勾结的封建主义势力进行殊死卓绝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便显示出了中国传统理念不适应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巨大弱点。以儒家思想作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崇尚“正德”之学和“养德”实践,进而实现“王道”,即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者社会架构的和谐理想。“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之德也。”[3]即通过道德的教化、推广,以端正人们的德行。“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4]即通过对崇高人格和德行的景仰和崇拜,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可见,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当中对于理想的追求路径是通过“内求”而逐步向外彰显的。因为没有内在的“仁”就无法让自己安身立命;没有内在的“德”就无法建立起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孔子讲,“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5]。“正德”、“养德”的起点是“仁”。钱穆在解释时认为,“若人人能安仁利仁,使仁道明行于人群间,则善人尽得人好,而善道光昌,恶人尽得人恶,而恶行匿迹。……人人能了解此仁,人人能好恶人,则人道自臻光明,风俗自臻纯美也”[6]。就整个社会架构而言,“由家庭内部开始,推广至全社会,这就是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德治’。也就是说,其价值理性的途径是通过政治人格、崇高德行的塑造和弘扬,来赢得民心,最终达到其工具理性目的,即‘王道’目标”[7]。尽管在数千年封建统治稳步推进过程中,也有着弥足珍贵的协商民主实践,但也是为了维护专制特权的稳固统治。诸如“周召共和”十四年,由周公、召公二相协商行政,其目的不过是消弭“国人暴动”之后厉王出逃而引发的“王道”真空。在“至尊唯一”的制度背景下,协商只能在“家天下”目的框架下展开,否则便是“谋逆”。
可见,传统价值理念在个人目标层面,在一系列经由修身、齐家然后治国而平天下的阶段性目标推演过程中,根本没有激烈对抗的“阶级斗争”的因子在里边;在社会和国家目标层面,由历史经验感知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统治者居多,但真正将“民贵君轻”奉为信仰、与民平等协商者极为罕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关系及其所决定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的阶级关系使得正心诚意进而修齐治平的理念数千年来“一以贯之”受到推崇和景仰。正因为如此,“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处于风雨飘摇没落时期的中华民族,无论藏书楼中有多少传世的经典宝鉴,传统文化中有多少令世人受用无穷的智慧,儒学中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和治国理政观念如何熠熠生辉,都不可能避免中华民族被瓜分豆剖的命运”[9]。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中国传统的强化“内求”的价值理念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现实危机的背景下传入中国的。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是因为满足了中国社会变革以及阶级力量变革的客观需要。
首先,马克思主义从阶级立场出发解释近代中国现实问题时显示出打动民众的正义性。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近代中国,一方面封建所有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得到解脱,如同马克思指出的,“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者就是国王”[10]。只不过“国王”变成了中国的独裁官僚。另一方面由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中国工人阶级摆脱不了与农民的天然联系,因而遭受着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多重压迫。比起欧洲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革命性更强,寻求“制度解体”和“否定私有财产”的意愿更强烈、更彻底。马克思在回答“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时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1]。在向传统“内求”而不得道,向日美“外求”而不得法的境地下,马克思主义像一道“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了中国无产阶级“朴素”的思想“园地”,从而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认识到只有树立阶级斗争的意识追求“解放成为人”的道路才是领导中国民众能够走得通的唯一正确道路,原有的改良式的、渐进式的、幻想式的、依靠式的道路只能使中国的局面越来越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2]。
其次,马克思主义从革命视野出发解决近代中国现实问题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必然走向垄断的过程是一个资本由分散经过积累和增殖逐步走向集中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阶级由分散状态走向联合、团结的过程。而联合和团结恰恰是“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因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首先生产出来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属性决定了其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在必须实现自身联合、团结的基础上,也必须“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3]。不论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联合、团结,还是争取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都不可能采取革命或斗争的方式,协商民主是唯一有效的途径。马克思在1842年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提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4]。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述到,“政治的实质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15]。经过广泛的团结与协调,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6],结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进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要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由独裁专制统治的旧中国向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传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碰撞之下产生的协商民主理念终于走上了民主团结、协商建国的实践轨道。
二、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主的历史逻辑
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念中有“民本”而无民主,尽管相对于“君本”而言,“民本”体现了集权统治者重民贵民、仁民爱民和安民保民的观念认知。这是内在“仁政”伦理的延展和外化,但更主要的是源于维护“家天下”统治的需要。唐太宗李世民就提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7]。可见,“民本”是为了克己以顺民、简政以安民。历史行进至近代之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逐步加深,晚清政府以及继起的北洋军阀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维护“民本”。就拿军阀“轮流坐庄”的民国政府来说,孙中山在分析辛亥革命成败得失时就认识到,“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惜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18]。因而近代中国唯一的出路便是推行民主革命,以一种新兴的有别于统治阶层之外的力量来挽救民族危亡。但恰恰是民主理念与实践的“统一”还是“分裂”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寻求民主道路的成色以及革命领导权的最终归宿。
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就发生了走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的分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力量主张在不动摇封建皇权政治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西方改良传统法律制度以探求富国强兵之道。然而,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仅仅凭借软弱的新兴力量和对于封建保守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最终无法从根本上触及近代民主革命的本真。尽管他们呼号“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但是“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19]。梁启超在总结改良派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20]。“除旧”缺乏实力,“布新”没有勇气,这不正是软弱的表现吗?因此,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21],而且这种“软弱”“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
改良运动失败之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积极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经过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暴动起义的屡败屡战,终于通过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是,面临民主革命持续下去的任务,革命党人束手无策,既没有能力通过抗拒帝国主义列强来维持新政权,又没有胆量通过发动群众来巩固革命新成果。因此只能通过“新瓶装旧酒”的办法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由此可见,辛亥革命没有将民主革命的道路坚持到底也在于其民主理念与实践的“分裂”。1924年,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说,“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2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取得统治性地位的境地下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软弱性是先天的;但近代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又使其不得不扛起民主革命的大旗。因而在一方面渴望突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而另一方面又有着与之谋求妥协、寻求“间接相调和”的冲动之间陷入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的“分裂”。
其次,国民党集团内部一直陷于继承民主主义精神和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分裂”之中。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便发生了理念和主张的“分裂”。以宋庆龄、廖仲恺、李济深为代表的爱国民主力量积极主张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打倒军阀列强,争取民族独立;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力量主张同列强合作,破坏国民革命以达到反共反革命之目的。两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经历“三次分化、三次集结”之后,国民党左派爱国民主人士于抗战胜利之后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派组织,成为了向往民主,同中国共产党在目标上一致、有深切合作愿望的民主力量。
蒋介石也曾有过“火星一闪”的民主思想,比如他曾提议对省港罢工工人“酌加编制,施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以植工人军之基础”[23]。但在当权实践中,完全违背了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精神,“把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变成了蒋介石‘实行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挡箭牌’;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体制发展为‘党魁独裁制度’,扼杀了党内民主,束缚了党员自由;并以特务政治来维持其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24]。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大肆镇压革命,争权夺利以现实其独裁一统,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不顾人民对于和平民主的呼声,发动内战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进行自卫和反击。
在近代中国追求民主的各种力量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高举着团结与联合的旗帜,将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自由幸福作为最高的目标。要对付力量异常强大的反民主反革命力量,团结和联合一切革新党派、进步人士是革命实现成功的必然选择。团结与联合的根本途径,就是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协商中求共识。这种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做法,成为了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列的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首。而建立并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方法便是一种通过协商扩大民主的形式,即协商民主而非独裁统治。其中,典型的形式如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在建立共产党员、非党员进步分子以及中间力量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中,既需要有选举民主,又必须包含协商民主。所以说,协商民主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协商民主理念和探索到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再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而积极地扩大统一战线、联络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与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协商建国事宜,均是在以实践的形式拓展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与外延”[25]。
孙中山先生曾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近代中国,求民主、求团结、反独裁、反专制不仅是一种“潮流”,而且已成为凝聚力量顺应民心的“大势”。在“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烧成烈火”[26]的追求民主的氛围中,任何“自私”和“分裂”的力量必将被送进历史的坟墓。协商民主效能的最大化发挥需要主导者以及参与协商的各方能够将脱离个体私利着眼于民族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的价值观,而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属性恰恰被赋予了这样的使命和责任。从此意义上讲,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一切民主进步力量,走到了民主团结、协商建国的关键一步,将协商民主从建党以来一直秉持着的一种理念追求着实落实成为一项实践运动,实在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1]温小勇,班爱荣.西柏坡协商民主实践初探[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2).
[2]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N].人民日报,2016-10-22(02).
[3]宋〗蔡沈.书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
[4]黄晖.论衡校释(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438.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38.
[6]钱穆.论语新解[M].成都:巴蜀书社,1985:80.
[7]温小勇.怡养涵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理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0-71.
[8]王秀梅.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99.
[9]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N].光明日报,2015-07-03(01).
[10][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17.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3.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3.
[15]李景源.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15.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0.
[17][唐]吴兢.贞观政要全译[M].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
[18][2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5,114.
[19][2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四册·专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85,81.
[21][2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02.
[23]张殿兴.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恩恩怨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9.
[24]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对一个政党迅速衰败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剖析[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458.
[25]温小勇.西柏坡多党合作文化论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76-177.
责任编辑:袁树平
2017-01-12
2016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6ZZ017);石家庄学院西柏坡文化研究专项课题(XBPZX1501)
温小勇,男,法学博士,石家庄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班爱荣,女,石家庄学院外语学院讲师。
D613
A
1009-6981(2017)02-00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