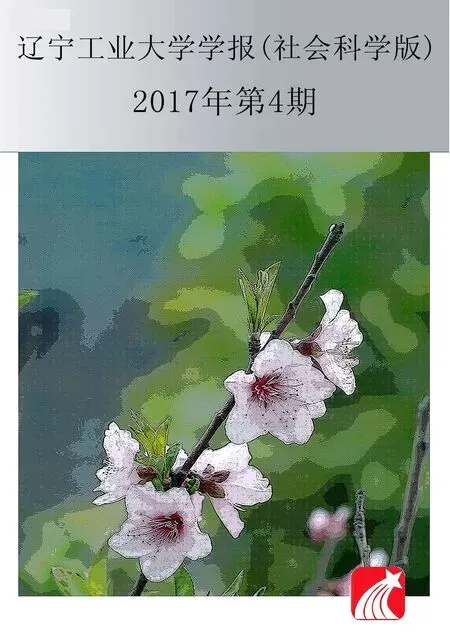悲凉的民族追寻永恒的心灵坚守——评阿苏的诗歌创作
2017-03-07孙小竹
孙小竹
悲凉的民族追寻永恒的心灵坚守——评阿苏的诗歌创作
孙小竹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031)
民族史诗一直都是伟大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历来就形成了关注民族命运的文学传统,各民族都在以其特有的民族形式、心灵关怀去追忆一个民族的发展演变历程。阿苏是新疆锡伯族具有新潮意义的诗人,并以自己的情感建构了一个特属于锡伯族文明历程与心灵寄托的诗语世界,诗史互渗的诗体形式将渗入骨髓的民族忧思厚重地从诗歌行间传达出来。通过民族感、心灵史、诗体结构三个层次对诗人阿苏建构的诗歌世界展开分析,以体味在阿苏情感汁液的浸润下拥有了超乎寻常文化意味的民族史诗。
阿苏;诗歌创作;民族情怀;心灵寄托;诗体结构
阿苏,锡伯族诗人。60后,苏慕尔氏人。儿时处于伊犁河边的生长环境,使得伊犁河一直在阿苏的诗歌创作中自然流动,阿苏倾泻在诗歌中的情感也如伊犁河一般随意流淌,形成阿苏跟随情感的走向自由抒发内心情感的诗歌风格。锡伯族最原始的口传历史传统也使得阿苏在童年时代就从爷爷那一辈老人的口中得知新疆锡伯族的雄阔的西迁历史和屯垦戍边的边防历史。阿苏在童年时代就确信自己是国家民族边防军人的后代,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家园追寻感。长大之后的阿苏,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民族的个体认知,这种认知并没有脱离民族的胸怀,而是将这样的胸怀融进了自己的血液流淌之中,并将这样一种民族家园的热爱转化成为了更深层次的民族的寻根意识与情感思考。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诗歌创作中,阿苏的民族追寻与心灵书写逐渐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之中,《写写扎昆古萨》《对一茎椒蒿的吟诵》获得了2011年新疆作协和伊犁州文协联合举办的“绿宝杯”诗歌比赛的一等奖。阿苏的那种带有强烈锡伯族民族归属意识的创作引起人们对于民族情怀的情感响应,充斥着众多情感因素的民族意象成为了阿苏诗歌情感构成的重要元素。锡伯族民族的心灵通过阿苏的诗歌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看到了经历了历史巨大变迁的人民心灵在寻找着一种民族寄托,我们看到一个民族在面临变革时所迸发出的抗争心态,我们看到一个作家个体的“疼痛”与整个民族的悲痛在诗歌中交融,我们看到民族文化的“黄昏”带给一个有民族担当作家的忧虑与思考。越走进阿苏的诗歌,就离一种自觉的民族、心灵探寻更近一步。
一、民族家园的无限热爱
“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是一个将爱国主义视作生命的民族。”[1]锡伯族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有着由来已久的悲壮苍凉之感。“明代以前,锡伯族居住在我国大兴安岭一带,在17世界末,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之中。在1764年,国家出军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之乱之后,为了加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同时也是为了除掉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之患,国家抽调出1 000多名锡伯族的官兵,于农历4月带着自己的家眷亲属,共计3 275人,赶着牛车,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出发,去到新疆伊犁驻防。”[2]一路经历了病痛伤亡、跋山涉水,历经重重艰难终于在来年7月22日到达新疆伊犁一带,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完成西迁的民族英雄壮举。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巨大变迁的民族从此在伊犁河边扎下来,为了祖国的边防和边疆的建设都付出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力量。
西迁的这段历史从此成为每一个锡伯族人民心中的悲壮之歌。阿苏的诗中也传达出这段西迁历史特有的沧桑之感。民族家园的热爱在这一点上呈现出了对于故土家园的深沉追寻。“最后的牛车走在日落的边缘/辙印深刻/辚辚之声如祖辈的泪光/直抵我的内心。”[3]22这带有时间印记的牛车,“以诗歌的形式”与阿苏无限接近,作者仿佛看见“故乡的草木间”,远行族人的沧桑脸庞,“疯狂的牛车”驶进河谷中心后,牛车之外村庄的“纯粹”。阿苏将自己的全部情感都倾诉在这牛车之上,牛车被冠以苍凉的历史情怀,以一个具有历史意味的意象出现在诗歌之中,传达出了对于故土的不舍与追忆。阿苏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情感宣泄道出了一个民族内心的悲壮慨叹,将自己的故土情怀与牛车拴在了一起,锡伯族的迁徙从牛车开始,锡伯族的新的生活同样也在牛车上展开。
这种对于故土的渴望渐渐地深化为一种寻根意识,“我风尘仆仆/自万里之外的伊犁远道而来/在祖先流血流汗的地方见见骨肉亲朋/再看看山水景致/然后寻寻苏慕尔氏的根。”[3]37在阿苏的心中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去寻找故土,去找寻自己民族的精神之根源,这种对于民族历史的追寻是因为“那里是我的根所在啊!”这样对于故土的寻根构成了阿苏诗歌的主要情感线索。
锡伯族顽强的民族生存能力,在伟大的西迁壮举中显露无疑。天生具有乐观抗争精神的锡伯族在新的地区依旧延续了自己的开拓精神,并在适应新的环境的同时,表现出了对于现在家园的无限憧憬与热爱。经历一年西迁的锡伯族,在新的生存环境面前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坚韧气质,“而早年的人们尾随木犁/在土地上流浪/闪亮的犁尖扎入春天的深处/让血汗开出花朵/让骨头疼痛。”[3]26“把血汗在身上流尽/历经七个春秋/创造了叫做察布查尔的百里大渠。”[3]33对于新环境一无所知的锡伯族人民,硬是在新的环境中凭借勤劳、坚毅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民族的新家园,新家园的建立付出了几辈人的“血汗”,现在的族人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并依然以自身的乐观与向往继续实现美好家园的希冀。“天亮了/我们就来到田野上/所干的活儿/就是把脚放进土里/把一冬天积攒的牛羊粪撒出去/然后扶着铁犁/开始耕种。”[3]39“苏慕尔氏的人啊/一生一世/把自己热衷于劳动的手/和虔诚的心/交给了身边的家。”[3]37作为锡伯人,过去颠沛流离的历史给了民族流浪之感,在探寻故土、寻找精神之源的同时,锡伯族人依然守望着现在的美好家园,“在堆齐牛录/我醉心于春种秋收/并且养活诗歌。”[3]16
锡伯族人民以其宽阔的心态接纳了历史赋予民族的一切,寻根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互渗透,形成阿苏诗歌中特有的交织之感。
二、永恒的心灵寄托
阿苏的诗歌代表了锡伯族人们最为深刻的历史感受,诗歌在背负了民族历史的沉重印记下,贯穿了阿苏等族人个体的心灵感受。从幼时就深存记忆中的伊犁河、牛录、旷野、河谷此时在阿苏的诗歌中构成了诗人个体情感的最佳见证。每一个在诗歌中出现的意象都是长久以来阿苏心灵的永恒情结,每一个事物都见证了阿苏诗歌情感的倾诉过程。意象是在作者的情感炼狱中提炼出来的带有特有味道的载体,它是作者全部感觉的寄托,打着阿苏情感印记的意象在诗歌中的书写构成了锡伯族人永恒的心灵寄托。
“牛录”与“萨满”是诗歌中充满民族色彩的意象,它们在阿苏的诗歌中以相当高的频率担当了诗人情感的安置对象。“牛录”,相当于兵营。伊犁锡伯族八旗制度改革后,牛录改革沿用为自然村落。“牛录”是阿苏人生经历的开始之地,自然在阿苏的情感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后来的阿苏去到城镇生活,他依然保持着与“牛录”最本质的心灵链接。“凉风中/贫寒的八个牛录/默默地背过身去/连绵的荒坡如一张残破的兽皮/微微有些颤动。”[3]60时代的牛录在饱受风霜的民族阶段成为人民心灵苦难的见证,它的存在提醒着所有锡伯族人民——历史上的心灵苦痛真实存在。“萨满”是阿苏笔下最具民族民俗气质的意象,锡伯族人民以萨满教为其信仰,萨满已经渗入民间人们的血肉心灵之中。“持矛的萨满/站在摇曳的烛光里/缓缓转动头颅/原始的眼神注视我们。”[3]24萨满的形象在阿苏的诗歌中成功地担任起心灵的监督角色,是锡伯族民族精神的守卫者,诗人运用一种神秘原始的叙事方式将这样一种宗教元素带入诗歌,让我们真切感受几千年来锡伯族人们的心灵坚守。
“疼痛”、“黄昏”是阿苏诗歌意象的第二心灵链条。“疼痛”是阿苏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是谁的目光/让我疼痛了九千九万次。”[3]20“这时候,我把来不及喊出的疼痛/在内心里藏好。”[3]138过去历史的心灵印记带给阿苏精神上的“疼痛”,这种“疼痛”也渗透在阿苏对于民族未来的期待之中,民族的发展是否会进入人们视野,民族的文化是否引起文学界注意,这些都是牵动阿苏心灵“疼痛”神经的关键因素,因而阿苏的“疼痛”绝不是仅限于民族历史的苦难追忆,更是对于社会和当下人生的思考。“眼看着日头西斜/自然而然就想起过去的岁月/和丢下我们的先人。”[3]31“黄昏”、“日落”、“夕阳”在此处也同样担负起了作者对于未来的思考。首先,我们看到这里的黄昏代表的是对于已逝祖先和过去岁月的回忆。但是阿苏对于“黄昏”的理解是否仅仅限于对于过去时光的怀念呢?阿苏曾经这样谈论过自己对于“黄昏”的理解:“黄昏是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刻,而我想到我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像是走到了黄昏,很多东西都在流逝,让人痛心。我梦想能让它走回来,可是现在只能为它唱一首黄昏的挽歌。”这说明这位有着强烈历史探寻意识的诗人,同样也有着超乎他人的前瞻意识。他坦率地表露对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忧虑,因而诗歌中出现的极具民族色彩的物象与风俗在此时就具有了超出民族欣赏范畴的更深内涵——文化珍视。这就让阿苏的诗歌具备了更高的文学特质,具有了更多文学社会学、文学传承的价值意义。同样,在阿苏的诗歌中也将自己内心最为诚挚的情感系上了民族文化的情怀,民族未来成为作者心头之重。
三、诗史互渗,汇贯三美的诗体结构
阿苏作为一个经历民族文化历史沉淀的一个作家,自然会在其诗歌中展现历史的厚重与思考,这也将阿苏与其他诗歌创作区分开来,阿苏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的夹杂家国情感的诗歌,锡伯族的民族特质促使阿苏形成诗史互渗的诗歌创作结构,在历史的沉重情感叙述中运用诗意的意象去传达出现代人的民族之感,而在诗意描绘自然风物的同时又会带进历史的变化沧桑。心灵感受与历史沉淀的双重交叉在阿苏的诗歌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也形成阿苏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阿苏作为一个现代诗人,他的创作同样也有现代手法的兼收并蓄,首先就是阿苏诗歌融汇了“三美”的创作原则。“三美”诗歌创作原则是由前期新月派的理论代表闻一多提出,他强调诗歌创作应遵循“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在路上/谁把久远的念唱/交给了半个月亮。”[3]105“上”、“唱”、“亮”可见阿苏在创作过程中十分注意韵脚的合辙,诗歌的编排在其字词的音乐性上做过一定的推敲。阿苏的诗歌是跟随感情的波动所连贯成篇,这样他所见的景物在情感线索下就构成一副有意味的民族风物绘画,读者通过意象、意象的描绘就可以在心里构画出一副民族图景。阿苏在《第四个牛录》这首诗歌中,诗歌分为三大段,每一段讲述了一个人与“第四个牛录”之间的血肉联系,阿苏在这首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是注意到了整体结构的一致性,这样就完成了诗歌“建筑美”的形式规范。
阿苏的诗歌创作来源于民族给予他的丰富资源,阿苏在整合这些民族资源的基础上融进了自己对于民族悲壮历史的追寻以及个体——群体的心灵探索,阿苏对于民族的思考无疑是深刻的,他对于个体以及群体的心灵开掘也是具有深度的,阿苏通过自己的诗歌将一个受人们遗忘的民族壮阔历史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并向人们真实坦露了民族心灵的磨练历程。这种民族、历史的积淀促成了阿苏的诗歌创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阿苏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诗歌中充斥着太多重复意象,对于情感载体的开掘还不够;诗史结合的创作形成厚重的诗歌风格,但也限制了对于当下人生的独立情感表达。
[1] 贺元秀. 论新疆锡伯族诗歌创作特征[J]. 民族文学研究, 2006(1): 154-157.
[2] 吴孝成, 翟新菊. 质朴的乡土底色──锡伯族诗人阿苏诗歌创作谫论[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52-56.
[3] 阿苏. 阿苏的诗[J]. 西部, 2015(3).
(责任编校:叶景林)
10.15916/j.issn1674-327x.2017.04.019
I207
A
1674-327X (2017)04-0065-03
2016-09-29
孙小竹(1993-),女,辽宁大连人,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