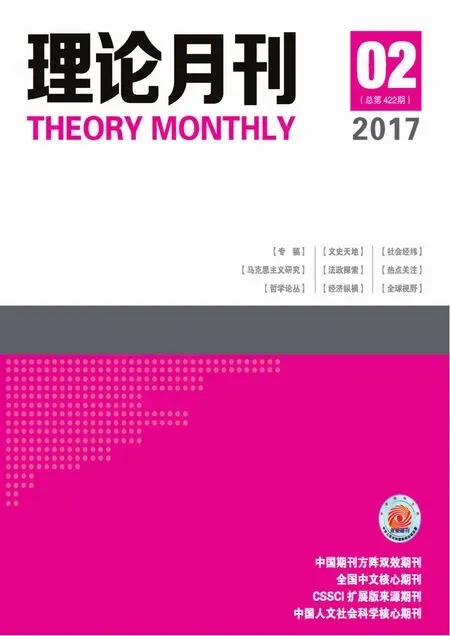茅盾自然主义的创作实践与认同危机
——以《子夜》为中心
2017-03-06龙其林赵树勤
□龙其林,赵树勤
(1.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2.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茅盾自然主义的创作实践与认同危机
——以《子夜》为中心
□龙其林1,赵树勤2
(1.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2.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茅盾受到了自然主义文学的直接影响,其作品《子夜》与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茅盾在《子夜》的结构、内容和表现手法上都受到了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影响;《子夜》以《金钱》为参照系,在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诸多相似之处;茅盾不断扬弃左拉自然主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涉及到了许多复杂的文艺观点和意识形态因素。
茅盾;左拉;内容;手法;认同
1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与西方文学所存在着的多维复杂关联,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既有的研究在分析西方文学与《子夜》的关系时更多分析的是托尔斯泰对于茅盾的影响,而左拉对于茅盾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则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通常地,认为茅盾在创作《子夜》时不断扬弃左拉的自然主义而更近于托尔斯泰,有两点重要理由:一是认为在具体作品的比较中,二者在表现社会、人生以及结构、艺术框架有不少相似之处;二是认为茅盾的《子夜》在人物出场、心理描写、环境氛围等方面从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进行了借鉴。
在我们看来,通常对于茅盾和托尔斯泰创作关系的描述倒更适用于茅盾和左拉。抛开《子夜》和《卢贡·马加尔家族》篇幅、形式的差异,我们可以在作品之间的构思和展开中发现一系列共通之处。茅盾是一位创作宗旨很明确的作家,“他的创作十分注重作品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要求创作与历史同步,自觉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广阔的历史内容’,反映时代全貌和发展的史诗性。”[1]为了实现对中国社会全景式的扫描和对社会性质的考察,茅盾在创作《子夜》时有着较为明晰的定位,小说力图展现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民族工业与帝国主义经济、小镇居民与知识分子群体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贯穿其中的线索则是以吴荪甫为代表的吴氏家族网络。这种以家族为圆心、反映出一个时代与社会风貌的写作目标也正是左拉写作《卢贡·马加尔家族》时所追求的。左拉在确定表现第二帝国时代社会生活的全貌时,他在着手写作之前就有整体计划,而贯穿这一整体计划的内在联系就是一个家族的血缘关系。为此,左拉构建了卢贡·马加尔家族的谱系图,并使这个家族的几代成员经历诸多变迁,使其生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与他们周围的各色人等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树形图和社会网络。
在《子夜》和《卢贡·马加尔家族》这两部家族史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阶级的生活、习俗和心理,其中既有政界、官场的争斗,也有王公大臣的宅地、奢华荒淫的生活;既有上流社会的觥筹交错,也有底层贫民的艰难困苦;等等。这些内容叠加在一起,真正构成了作家对于中、法社会的全景式扫描。左拉在创作时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加以观察,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具备科学实验的精准与摄影师般的细腻,他在进行创作之前总要大量地搜集、阅读资料、了解生活,甚至为了写作具体的场景还要进行实地考察。左拉创作中的这种实地考察与实录性途径,是茅盾极力推崇和追求的。茅盾在写作精神上接受了科学的方法,因而他也采取了相同的创作模式。茅盾在写作《子夜》的过程中,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知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一九三0年冬整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2]。“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悉”[2]。
从这里不难发现,茅盾是怀着左拉式的实地观察、资料搜集之后才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之前必然存在着一个熟悉生活、观察人物和环境的过程。正是由于在上海时较多地了解了银行家、企业家、公务员、商人们的生活与状态,所以《子夜》中有关资本家、企业家们的叙述最为深刻、逼真。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农村生活的隔膜在小说的第四章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几乎是模糊不清的。正如作家所解释的:“这部书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与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得多了。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愿意向壁虚构,结果只好不写。此所以我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的。”[3]叶圣陶先生在谈及茅盾的创作时,认为其创作中的许多内容“虽为小节,他也不肯一毫含糊”[4],而这恰恰是对左拉文学精髓的学习和实践。
同时,一些研究者认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开场是以上百名人物开始的,这些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而《子夜》的开端和《战争与和平》颇为近似。在这些观点中,出现了一系列讹误之处:首先,《子夜》的开端并不是以人物而是以环境描写开始的。《子夜》的开头描写的是上海的黄昏景色:“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这种细腻、生动的环境描写,不是更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描写极其类似吗?其次,以众多人物开场并非《战争与和平》的专利,何以能够确定茅盾的《子夜》是受到托尔斯泰而非其他作家的影响呢?事实上,就心理描写、环境氛围表现而言,《子夜》更近于左拉而非托尔斯泰。左拉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通过观察、调查、实验的方法来达到对自然与社会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尽量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通过文字精确的剖析与分析来实现作品对于科学性的追求。《子夜》呈现了一种与此前新旧两派小说所不同的地方:它不再停留于故事、情节等单纯的动作层面的表现,而且对于自然和社会环境也给予了仔细的描绘;它突出了作家对于生活的仔细观察和详尽描写,使小说从真实的误区中走了出来。左拉以临床医生和实验观察者自居,茅盾也努力成为社会生活的实验员和观察者。正如普实克指出的:“茅盾追求客观性的努力表现在他煞费苦心地从叙述中排除了作者本人的因素。他的小说没有显示出与任何人有关联的痕迹。作者的目的是让我们亲眼看到、亲身去感觉和体验到每件事,消除读者与小说所描述内容之间的一切中间过渡,使读者进入小说的情节,好像亲眼看到正在发生的一切。”[5]茅盾在创作《子夜》的过程中,大都是采取客观、理性的分析方法,一般不轻易地夹杂个人的情感痕迹。《子夜》这种客观、理性的描述,非但不是人们分析的对于托尔斯泰心灵的艺术的借鉴,反而是在尽可能地剥除主观因素的介入。
2
也有的研究者依据1930年出版的《西洋文学通论》中茅盾对于《卢贡马惹尔》中《金钱》的介绍“大抵都是普泛的文字”,断定“茅盾在《子夜》的创作中,没有受到《金钱》的直接影响”,“《子夜》和《金钱》的某些近似现象”“并非出于时间过程中的承传、输出或接受的影响关系,而是在不同空间中平行发展的理解”[6]。
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茅盾在文艺随笔中自我剖析中对于托尔斯泰的亲近和对左拉的规避这一态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未能认真分析茅盾的思想构成和知识储备。一些研究者在查看茅盾《西洋文学通论》中关于自然主义一章的论述中,只看到作家对于左拉《金钱》一文的简要概述,加上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中所说的“我虽然喜欢左拉,却没有读完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全部二十卷,那时我只读过五、六卷,其中没有《金钱》”[7],便认为《子夜》没有受到《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影响。
实际上,茅盾不仅对于这部巨著有着总体的、到位的分析,而且对于每一部作品的内容都是了解的;即便对于《金钱》的介绍并不详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对作品内容梗概的了解和熟悉。尽管茅盾认为他当时并未读完过《金钱》这部作品,但是对于小说的人物、内容却是熟悉的,否则茅盾不会在《西洋文学通论》中介绍《金钱》的梗概。这至少表明了茅盾对《金钱》内容的了解。而就两部小说的内容来看,也是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金钱》描写了萨加尔和甘德曼两大集团的斗争。萨加尔凭借其哥哥卢贡大臣的力量创办了一个世界银行,他一方面将从银行股票中拿到的钱做投机生意,一方面利用工程师哈麦冷进行东方开发赚取高额利润。面对甘德曼这个顽强对手的存在,萨加尔通过不法手段抬高股票行情,最后终于彻底破产。左拉在《金钱》中讲述的故事,被茅盾吸收和改造成了《子夜》中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两大集团的争斗。吴荪甫是一位具有胆识、才能和野心的民族资本家,他组织益中公司发展民族工业,同时也积极地投身公债市场,最后吴荪甫在公债市场和工业发展中同时陷入了困境。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也颇有精神气质上的共同点。萨加尔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家、投机家、野心家,他确立了一幅征服世界的宏伟图纸:“这些铁路线,正象一个渔网一样,从中亚细亚的这端到那一端,这对他来说便是一件投机事业,是金钱的生命线。一下把这个古老的世界抓住,一如抓住一个新的俘获物一样,而这些俘获物还完整无缺,蕴藏着无以数计的财富……”而《子夜》中的吴荪甫也是一个刚毅、果断、具有现代管理才能、野心勃勃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也渴望着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业王国:“吴荪甫拿着那‘草案’,一面在看,一面就从那纸上耸起了伟大憧憬的机构来: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他不由得微微笑了。”事实上,早在北大预科时,茅盾就学习了英语,并选择了法语作为第二外国语。对于精通英文、熟悉法语的茅盾来说,他要通过其它途径阅读,至少是了解《金钱》的内容并非难事。
茅盾之所以在《西洋文学通论》中对于《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小说的介绍比较普泛,很大程度上是由该书的性质决定的,即“这本书是想在‘怎样入手去研究西洋文学’这意旨上,简略地叙述了西洋文学进程中所经过的各阶段”[8],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作者受到《卢贡·马加尔家族》中系列作品的影响。对于作家来说,有时一些内容上的基本了解便会对其创作产生重要启示,并不一定要按照作品的原文、理论作为指导,这种内容上的熟悉“不一定具体地‘指导’了作家的创作,但却可以成为理解一部作品的认识角度”[9],从而对创作者产生隐约却根本的影响。在《子夜》出版之后,瞿秋白即敏锐地发现了小说与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小说中的《金钱》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子夜〉与国货年》中,瞿秋白分析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L’argent’——《金钱》)。”[10]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4],这既表现了茅盾写作的严谨性、科学性,同时也揭示出了《子夜》与左拉及自然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此,那么茅盾在其文章和创作谈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更近于托尔斯泰,该如何理解呢?是否仅仅由于他们的创作倾向和意趣上的切近?
其实早在1920年的《小说月报》中,茅盾就主张中国要介绍新派小说,其中就包括左拉的作品。之后,茅盾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继续在中国作家和文化界中提倡自然主义文学。到了1922年,《小说月报》掀起了介绍自然主义的热潮,杂志相继刊登了一些关于自然主义论争的文章,从而将自然主义的介绍更加向前推进一步。针对周作人认为自然主义专门在人间发现兽性的问题,茅盾撰写了《“曹拉主义”的危险性》一文为左拉进行辩护:“自然主义的真精神是科学的描写法。见什么写什么,不想在丑恶的东西上面加套子:这是他们共通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不但毫无可厌,并且有恒久的价值;不论将来艺术界里要有多少新说出来,这一点终该被敬视的。”[11]茅盾不仅在理论上倡导自然主义和为左拉辩护,而且还在介绍、翻译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上费力不少。茅盾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他对自然主义也经历了由陌生到熟悉、由大力倡导到渐渐疏离的过程。茅盾在谈到自己所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时,曾这样说道:“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12]。在《茅盾论创作》一书中,茅盾曾这样分析左拉的创作方法:“凡此一切‘材料’,剪报,抄书,谈话记录,观察和‘观光’时的札记,他都细心地研究了,分类排比,于是在他觉得够用了时,他就根据这些材料来写创作。”[13]“我们要排斥贪省力的走马看花似的左拉式的方法”[14]。
3
实际上,茅盾之所以突出自己与托尔斯泰作品的关系,而在中后期对于左拉及其《卢贡·马加尔家族》有所忽略、回避甚至是否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涉及到了许多复杂的文艺观点和意识形态因素。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茅盾自己在早年倡导自然主义之际便对其抱有某种警惕意识。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茅盾就指出:“物质的机械的命运论仅仅是自然派作品里所含的一种思想,决不能代表全体,尤不能谓即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一事,自然派作品内所含的思想又是一事,不能相混。”[15]在《“曹拉主义”的危险性》中,茅盾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于左拉及自然主义作品的担忧:“由现代人的眼光看去,他的创作的态度是很不妥当的,因为人生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而且科学的实验方法,未见能直接适用于人生。”[11]由此必然导致茅盾对于左拉及作品在艺术上的高度接受与思想立场上的对立的奇特局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茅盾始终对自然主义表现出一种警觉”,“在茅盾看来,左拉自然主义至多只是一种工具,而非一种程式,在茅盾思想中更多渗入中国传统政治与道德内容”,“茅盾借助于左拉,却最终远离了自然主义,这种实用理性主义的借用,正是贯穿于左拉介绍之始终的”[16]。
其次,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突出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成为《子夜》创作的潜在背景。左拉隐匿个人态度、追求客观真实的创作方法,在当时迫切的现实要求、政治意识形态和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文坛显然不受欢迎。瞿秋白就曾对自然主义提出过猛烈的批评,认为“左拉自己所谓‘科学性’,其实是联结着非道德主义,非政治主义的,这是使得‘社会’小说不致于转变到社会主义小说的一种靠得住的担保”[17],“左拉理论的实质和他客观上的政治作用,的确包含着反动的成分”[18]。茅盾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文学家,面临自然主义存在的否定革命倾向的必要的问题自然不会等闲视之。茅盾思想中的“儒家思想中通过进入庙堂直接参与政治的方式实现士大夫所追求的‘道统’、传统士大夫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19],也对其创作方法的选择产生了影响,于是茅盾对于自己创作受到左拉作品影响所表现出的犹疑乃至否定态度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再者,茅盾之所以在创作谈和文艺随笔中屡次否认《子夜》受到左拉作品的影响,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在于作家对于外来影响的一种焦虑。从茅盾受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影响的事实来看,对于作品的阅读与熟悉必然沉淀为作家知识背景之一而对之后的创作产生潜在的影响。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的众多文章、杂志、著作中大力提倡自然主义方法,并在创作实践中明显地吸收、借鉴了自然主义的观念、方法,甚至其笔名佩韦即是取自自然主义理论家圣·佩韦,那么到了创作《子夜》之际,左拉作品的影响势必仍然对作家产生某种规约。茅盾曾这样回忆:“一九二七年我写《幻灭》时,自然主义之影响,或尚存留于我脑海,但写《子夜》时确已有意识地向革命现实主义迈进,有意识地与自然主义决绝。但作家之主观愿望为一事,其客观表现又为一事,客观表现(作品)往往不能尽如主观所希冀。”[20]茅盾之所以会有意识地表现出对左拉和自然主义的规避,其原因或许还在于作家试图竭力摆脱左拉的影响,“这种‘摆脱’并非通常语义上的‘摆脱’,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担心与影响者雷同而不能创新的焦虑。换而言之,茅盾对左拉影响的拒绝,正显现左拉对茅盾创作思想内核的强劲渗透”[21]。
事实上,茅盾与西方经典家族经验和技巧对接之后,既有进行创作所需的丰富的精神资源,又有社会生活赋予的生命体验,本可以在家族小说领域内继续前行,创作出中国式的《卢贡·马加尔家族》。但令人遗憾的是,茅盾构建中国宏大家族叙事的可能性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1]凌宇,颜雄,罗成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6.
[2]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N].新疆日报,1939-06-01.
[3]茅盾.再来补充几句[M]//子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479-480.
[4]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J].文哨,1945(3).
[5]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G].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34.
[6]赵婉孜.托尔斯泰和左拉的小说与《子夜》的动态流变审美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9(2).
[7]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M]//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7.
[8]茅盾.例言[M]//西洋文学通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1.
[9]张清华.境外谈文[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231.
[10]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G]//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71.
[11]郎损.“曹拉主义”的危险性[J].文学旬刊,1922(50).
[12]茅盾.从牯岭到东京[J].小说月报,1928(10).
[13][14]茅盾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462,463.
[15]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J].小说月报,1922(7).
[16][21]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339,335.
[17][18]瞿秋白.关于左拉[G]//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01,202.
[19]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3.
[20]茅盾.致曾广灿[G]//贾亭,纪恩,选编.茅盾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562.
[21]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335.
责任编辑 文嵘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2.007
I207.4
A
1004-0544(2017)02-0036-0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2JHQ037);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13C05);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项目(2014WZDXM021)。
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文学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复旦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赵树勤(1955-),女,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