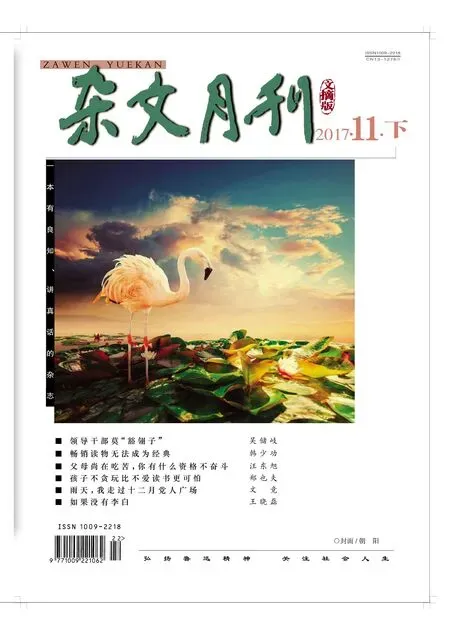雨天,我走过十二月党人广场……
2017-03-02□文竞
□文 竞

这里,历史上曾有多个称谓:元老院广场、枢密院广场、参政院广场、彼得广场……
但在一百九十多年前,三千二百余名全副武装的禁卫军官兵在这里集结誓师,高呼口号,宣读宪章,要求废除农奴制、实行民主与自由,并在这里与尼古拉一世派来镇压的军队殊死决战,血染涅瓦河……为了纪念他们,彰显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1925年,这里被正式命名为:十二月党人广场。
现在,这里绿茵铺地,古木参天,是圣彼得堡难得的一片静谧天地。2016年7月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了这里。站在青铜骑士跃马扬蹄的塑像前,前面,越过马路,是千年流淌的涅瓦河;左面,是俄罗斯宪法法院,也就是昔日的参政院(或枢密院)大楼;右面,穿过树林草坪就是俄海军部大厦;后面,则是世界四大教堂之一的圣伊萨基耶夫大教堂。环顾四周,我觉得一百九十多年间,这里似乎变化不大。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疑问:八个身着黑红相间军服的作战方队,一字儿在参政院门前排开,军官刀出鞘,士兵弹上膛,那是何等的英武豪气。为什么从早晨列队到下午,就是不发起冲锋、发起攻击,非得等到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发炮轰击呢?傻呀?这还叫革命叫起义吗?直到临行前做功课,读到学者王康的《高贵与美丽》,才知道这叫贵族精神。十七世纪以来,欧洲贵族盛行决斗,认为这是维护贵族荣誉和尊严的最佳方式。领导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军官都是深受欧洲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的俄罗斯青年贵族,他们认为沙皇的专制、农奴制以及俄国的黑暗愚昧、野蛮落后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和信念,起义,是他们和沙皇帝国之间的一场集体决斗,因此,他们不搞暗杀,不搞突然袭击,也坚持不开第一枪……
大概因为这里叫十二月党人广场,我以为总会有点与十二月党人有关的东西,所以在青铜骑士塑像前拍完照后,我就开始在广场四周寻找。但奇了怪了,找了半天,居然就没找着。这个遍街都是雕塑的国家,怎么就没想到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事发地为他们立尊雕塑呢?
如果有这么一尊雕塑,我想我是会去表达一下我的敬意的。因为对我来说,认识他们已经很久很久了。那时,我还在四川大竹县的一个乡村当知青,就着煤油灯昏暗的光亮,我读普希金的诗歌,读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在注释中,我知道了他们。当然,那个时候让我景仰让我感动的还不是为理想为信念献身的这些青年贵族军官,而是站在他们身后的妻子——高贵、美丽、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俄罗斯贵族女性。是她们的惊世骇俗之举、是她们感天动地的爱情将记忆深深地根植在了我的心底。
西伯利亚是什么地方?也许现在的年轻人觉得飞过去不是个事。但那时,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有五千七百五十公里的路程,没有汽车,没有飞机,要走到那里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俄国画家列维坦的名画《弗拉基米尔大道》,画的就是当年通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古道。看看那画面的空旷、荒凉,看看那地平线尽头的遥不可及,深不可测,你能想象它的恐怖和可怕吗?冰天雪地,荒凉贫瘠,气候酷寒,人迹罕至,那个时候,人们把西伯利亚称作“被抛弃的世界”“没有围墙的监狱”“死亡和枷锁之乡”。但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挡那些俄罗斯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那些巴黎上流社会的成功女士。作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或情人,她们宁可放弃雍容华贵、养尊处优的生活,告别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也毫不迟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跟随丈夫赴难。她们不怕西伯利亚的风雪肆虐、豺狼出没,她们要与亲爱的丈夫为伴。她们说:只要她们到那里,丈夫就不会太悲惨太寂寞……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今天的好多人流泪、汗颜。
时至今日,如果再来复述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故事,那就话长了。近两百年来,她们的故事已被不同的国别、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反复吟咏反复歌唱。我只讲一个细节:十二月党人妻子中的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去世后,留下一本法文撰写的《札记》。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在她的子女那里看到了这本《札记》。当夫人的儿子给涅克拉索夫翻译这本《札记》时,涅克拉索夫感动至极,常常听着听着,就叫暂停,忍不住跪倒在地,像孩子一样抱头痛哭……涅克拉索夫的经典长诗《俄罗斯妇女》,不是创作,而是改编,蓝本就是《玛丽娅·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札记》。所以,我敢断言: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故事,绝对是人类爱情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只要有人愿意了解一下她们的故事,没有谁不会为之动容。尽管这些伟大的女性现在已经远去了,但是,她们——卡特琳、玛丽娅、穆拉维约娃、唐狄、波利娜、列丹久……就像天上的星辰,将永远在历史的时空中闪烁。
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里有一幅克拉姆斯科依的油画《无名女郎》。多年来,人们一直对画中的女性有多种猜测。有人说她是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有人说她就是一位演员,因为背景上隐约可见圣彼得堡著名的亚历山大剧院;还有人说她就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我宁肯相信最后一种说法。看看坐在敞篷马车上的那位贵族女郎,高贵的气质、刚毅的面容、淡淡的忧伤,睥睨一切的目光……不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谁?
有人说,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所作所为是把爱情的意义升华到了时代的最高度,她们“殉”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自由和解放。我觉得有点拔高。十二月党人妻子中最后辞世的亚历山大拉·伊万诺芙娜·达夫多娃曾说:“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这话实在、质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许并不完全理解她们丈夫的信念和追求,很多妻子事发前甚至不知道她们的丈夫在干什么,但因为那是她们的丈夫,她们就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呵护他去温暖他。哪怕冰天雪地,哪怕海阔山重,哪怕亲友规劝,哪怕沙皇命令,她们也非去不可。在俄语中,“爱”一词的含义,不是简单的“爱恋”,更有“怜惜”之意。俄罗斯女人与生俱来母性十足,最善温暖失意者的心,她们是男人天然的守护神。这一点,只要去看一看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吉扬娜,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阿克西妮亚就会明白。所以,苏联时期的历史小说家索洛涅维奇才说:俄罗斯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它是由俄罗斯女性塑造的……
雨,又开始稠密起来了。我没带伞,只得匆匆往回走。我想,再过九年,就应该是十二月党人起义二百周年了。一百周年的时候,这里有了命名,那么,二百周年的时候,俄罗斯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来纪念她们的优秀儿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