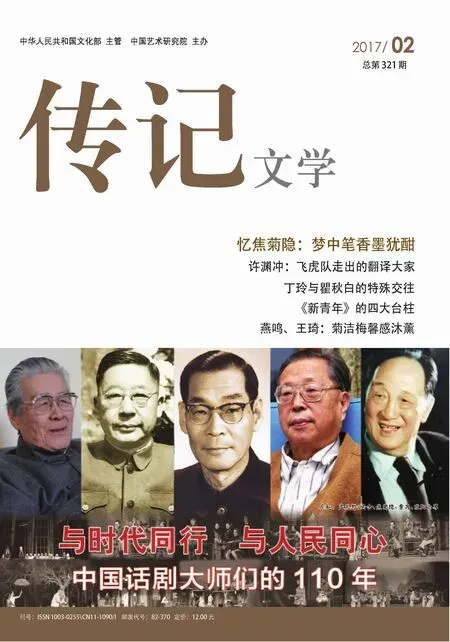张恨水传 选章八
2017-02-28文解玺璋
文解玺璋
张恨水传 选章八
文解玺璋

平居
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民国八年(1919)秋,他在朋友的鼓动下,“质衣被入京,拟入北京大学”。然而,居京不易,何况他“一身之外无长物”。在北京“漂”了三四年,不仅读书的愿望未能实现,而且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那个时候,他不是住会馆,就是住报馆或通讯社,始终没有自己的家。
民国十二年(1923)秋,张恨水与胡秋霞成婚,他的“北漂”生活才算告一段落,慢慢稳定下来。次年初春,他租下宣武门外铁门胡同的一所住宅,安了个家。他的老朋友、芜湖《工商日报》副刊编辑张香谷写信向他表示祝贺,他在《复香谷电》中特别提到:“水于真日迁入铁门七十三号丁宅。”他的复电发表于三月十六日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这里提到的“真日”,即三月十一日。十天后,三月二十六日,该报又发表了他的《春明絮语(续)》,其中讲到:“予近迁居铁门七十三号,为青衣票友蒋君稼故宅。友人张香谷作函贺之,并谓蒋善歌,必有绕梁余音可闻。其事甚韵,予因作骈体文复之。”
铁门胡同地处宣武门外,北京外二区之西南,北起西草场街,南至骡马市大街,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距离张恨水前些年住过的歙县会馆、潜山会馆,都并不太远。近代著名作家、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圣手的包天笑,晚年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记下了与张恨水在铁门胡同做邻居时的轶事:“自从定居了铁门以后,有许多朋友知道了,时来见访。后来方知道张恨水也住在这条胡同里,我住在前进,他住在后进。他的朋友去访他,却也是我的朋友,先来访我。不过我们两人,这时还不相识,直到他后来到上海后方见面哩。”
在包天笑的记忆中,“铁门是小四合院,可也有北屋三间,南屋两间,东西屋各两间,门口还有一个小门房”。而且,屋子里“既装有电灯线,又有了自来水管子,并且是新造的,租金不过十三四元吧,与北京老房子比较,也算是高价了”。前院既如此,后院的格局也就可以想象。张恨水数月前刚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夫妻二人租住这样一个小院,在北京城里,虽非豪门大宅,也算是相当舒适的了。那时,他兼了几份工作,给北京、天津、上海的几家报馆写新闻通讯,“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那个时候的一二百元,是个相当引人羡慕的数目”, 足以支撑他们婚后幸福、温馨的日子。
不久,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特邀张恨水主持副刊《夜光》。报馆就设在宣武门内手帕胡同35号,靠近今天的佟麟阁路北口,从张恨水家到报馆,步行也不过数十分钟。胡秋霞的存在,使张恨水感受到家的温暖,他不再是没人疼,没人爱,病了也没人嘘寒问暖、端汤送药的“北漂”了,他有了自己的家,家中有了惦念自己的人,也就有了一份牵挂。每天报馆的事情一办完,他立马往家赶,去享受心目中所向往的“齐眉举案”“红袖添香”的夫妻生活。
胡秋霞是苦出身,勤劳是她的本质,担水劈柴,洗衣做饭,洒扫庭除,她样样在行。张恨水回到家里,饭菜是热的,人是温存的,更兼有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的环境,看着就心舒气爽,不能不由衷地赞叹家里有个人的好处。但他毕竟是有些才子气的,对身边的女人,不仅希望她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希望她能与自己有些共同的志趣和爱好,类似“小红低唱我吹箫”之类,如果能与她在闺房之内诗酒唱和,更是再好不过了。然而,胡秋霞不识字,对张恨水来说,虽有美中不足之憾,却也使他有机会在新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学。那时,胡秋霞只有十七八岁,他则大她十余岁。他相信,经过教育,人是可以改变的。胡秋霞自幼被拐子骗卖,没有读书的机会,对自己的身世亦一无所知,只记得娘家姓吴或姓胡,小名招娣。婚后,张恨水为她取名“秋霞”。这两个字,来自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时,在张恨水的心里,落霞与孤鹜在秋水长天的背景下,或已融为一体。
张恨水要带着胡秋霞一起“飞”了。他们双双出入于影院、戏园,在他们的生活中,听戏、看电影成为很重要的内容。他还为妻子“制定了学习计划,规定了学习任务”。他与胡秋霞的小女儿张正在忆及父母这段生活经历时写道:“爸要塑造一个新的秋霞。纸笔是现成的,老师就是爸本人。他手把手地教她握笔,从描模子开始,每天认几个字,很快妈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爸爸的指导下,几年后,妈妈居然能粗读报纸,通读爸写的长篇小说了,像《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她十分爱读,常常在爸爸创作时,她就已经先睹为快了”。
张恨水很少写到他与胡秋霞的这段生活。30年代初,他以《落霞孤鹜》为名,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其中男女主人公就分别叫江秋鹜和落霞。江秋鹜是中学教员、进步青年,落霞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小说所写的正是江秋鹜如何帮助落难孤女落霞并与之喜结连理的故事,还描写了所谓慈善机构——社会福利院的种种内幕和孤儿们的悲惨生活。熟悉他们的人不难看出,张恨水是从他与胡秋霞的生活经历中得到灵感的,而江秋鹜和落霞就是以他们二人为原型。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就曾写道:“张恨水有一姬人名秋霞,张喜宠之。所著说部《落霞孤鹜》,其中即有秋霞影事。” 但小说就是小说,不能视为信史。生活经过加工虚构可以成为小说,小说则无论如何不能还原为生活本身。因此,张正的记述在这里就显得尤为可贵。
民国十三年(1924)农历九月初一,张恨水与胡秋霞的长女大宝(张恨水在文章中称她“慰儿”)出世了。女儿的到来,给这个二人世界平添了许多烦恼和乐趣。不料,这个女儿只活了八岁,民国二十一年(1932)初夏,北平猩红热流行,先是小女儿康儿染上此病,医药均不见效,九日而夭;继而长女慰儿,亦染此病,不及二十日,不幸夭折。两个女儿一先一后离开人世,让张恨水深感人生之不可捉摸。他在《〈金粉世家〉自序》中追叙了女儿的音容笑貌:“当吾日日写《金粉世家》,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常窃视曰:勿扰父,父方作《金粉世家》也。”
就在慰儿刚刚学步的时候,张恨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要把全家从安庆迁居北京。起因是这一年大妹张其范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张恨水不想让母亲挂念女儿,索性把全家都搬到北京来了。他在京漂泊数年,眼下虽已娶妻生子,有了温馨的小家庭,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想起远在家乡的母亲和弟妹,仍不免于天涯游子的孤寂之感。某年除夕,他结束了手头的工作后,从报馆出来,走到宣外粉房琉璃街口,看着熙熙攘攘采办年货的人们,遂口占一绝:“宣南车马逐京尘,除夕无家著此身;行近通衢时小立,独含烟草看忙人。” 这首诗真切地表达了一个游子“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情。现在好了,大妹来京读书,仿佛天赐良机,全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张家此时已是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张恨水兄弟六人,他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妹妹尚未出嫁,弟弟中二弟啸空、三弟仆野都已婚配。张恨水则在原配徐文淑之外,又娶了二房胡秋霞,并有了女儿。这样一来,铁门胡同的小四合院就显得非常局促了。为了能让全家住在一起,妥善地安置两个有家室的兄弟以及他的两房妻子,张恨水不得不设法承租一所更大的院子。那时候,在北京租房,供给大于需求,因此,没费什么事,就在未英胡同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住所。多年后,张恨水还在《影树月成图》一文中描述了这座宅院令人神往的概貌:“未英胡同三十号门,以旷达胜。前后五个大院子,最大的后院可以踢足球。中院是我的书房,三间小小的北屋子,像一只大船,面临着一个长五丈、宽三丈的院落,院里并无其他庭树,只有一棵二百岁高龄的老槐,绿树成荫时,把我的邻居都罩在下面。”
这种超大规模的四合院,简直就是为张家这种兄弟、妯娌、姑嫂、妻室关系较为复杂的大家庭量身定做的。张其范也曾忆及当初在未英胡同30号时的生活情景,她在《回忆大哥张恨水》一文中写道:“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我们推门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她还记得:“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小说里的一个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未英胡同在西长安街南侧,这条南北向的胡同,北迄西绒线胡同,南抵宣武门东大街,明代为府卫军驻扎地,由此得名卫营胡同;清代或称纬缨胡同,俗讹为未英胡同,也有叫喂鹰胡同的,不知何所本。然而巧的是,张恨水所居30号院右邻,是一旗籍旧家,尝自夸为黄带子,意为皇亲国戚。他曾在张恨水面前吹牛,说:“少年富贵无所事,弹歌走马,栽花养鱼,驾鹰逐犬,无所不能。不料今沦居陋巷,寒酸增人谈笑也。” 不过,张恨水的确看到过这家人处理所养老鹰时的情景:
其家有老仆,以衰病谋去未能。一日于院中树下缚老鹰,将割之。予曰:噫!其肉可食乎?仆曰:当吾主人坐高车,住华屋时,是曾捕杀多禽,深得主人欢者。吾不彼若也。今主人贫,当谋自立。不复以杀生为乐,是物留之无用,嘱吾释郊外。然吾殊不耐,有斗酒,将烹之以谋一醉也。言时,鹰目灼灼视予,若欲为之乞命。予怜之,以二角钱向老仆购取,纵之去。鹰受伤不能高飞,纵翼复落予院中。小儿辈喜其驯,以厨中腊肉喂之。三日,为狸奴所创,死焉。
不知这个插曲能否成为此地曾经“喂鹰”的佐证。但这毕竟是张恨水笔下不多见的对未英胡同那段生活的记述。其实,关于这所宅院,在张恨水之前,谁在这里住过?房产的所有权属于谁?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查清代王府地址简表,以及列入文保单位的四合院名单和未列入文保单位的名人故居及王府名单,不仅没有这所30号院,甚至没有未英胡同。这所院子固然不小,但月租只有30元,在张恨水看来,“就凭咱们拿笔杆儿的朋友”, 租一所这样的院子住,并不特别地为难。或者你以为这是个“布尔乔亚之家”,他会告诉你:“不,这是北平城里‘小小住家儿的’。”
尽管如此,以张恨水的实际收入而论,每月三十元的房租仍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加盟《世界日报》之前,张恨水兼职较多,收入也很可观,“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然而,自从与成舍我一起创办《世界晚报》以来,他把所有的兼职都辞了,为的就是专心做好这件事。另一位创办人、后与成舍我因身份问题产生争议的龚德柏,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办报之先,成舍我同我两人,只言合作,绝未谈及谁主谁从?故两人都吃自己的饭,不由报社拿一分钱薪水,只共同努力,把报纸办好而已。” 对此,张恨水也曾有过表示。“我们决不以伙计自视。”他说,“我和龚君,都是为兴趣合作而来,对于前途,有个光明的希望,根本也没谈什么待遇。后来吴范寰君加入,也是如此。”不过,与龚德柏不同的是,他还支“三十元月薪”。
这应该是民国十三年(1924)《世界晚报》初创时的情况。当时,由于报纸的销路和广告来源尚未打开,处处花钱而收入欠佳,经济上就显得十分紧张,人员的报酬都很低,编辑、记者的月薪只有三十元。不过,成舍我是很善于经营的,他的新闻意识很强,社交又广,因此,《世界晚报》的消息要比北京同类报纸快捷得多。适逢第二次直奉战争,《世界晚报》因报道及时而声誉日渐提升,再加上张恨水所撰之《春明外史》,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成为刺激报纸销量持续增长的兴奋剂。成舍我顺势而上,又先后创办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张恨水则包办了《夜光》《明珠》两大副刊,并同时撰写两部连载小说。龚德柏与成舍我分手后,他还担任过总编辑一职。这时,他的月薪据说提高到了八十元,但开支时,只给三十元现金,另外五十元,则给一张成舍我具名的借据代替,也就是白条。后来,由于张恨水没有很好地保存这些“白条”,成舍我便拒绝支付,最终导致了二人的不欢而散。至于张恨水为两报撰写的多部连载小说,成舍我也始终没有另外支付稿费。直到单行本由报社结集出版,张恨水才得到一部分版税。
可见,民国十六年(1927)以前,张恨水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的收入离全家的实际生活需求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据张其范回忆:“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生存压力之大,由此亦可想见。在重庆的时候,张恨水写过一篇《做长子难》,就谈到了自己的苦衷,作为长子,他是有义务的,“上要供养寡母,下要抚育诸弟妹,对内对外,还要负担着经济上的责任”。为了肩上的责任,他必须想办法多赚钱。但他是个文人,所能做的,只有卖文。他在许多场合都曾表示,写作“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混饭,其二是消遣。混饭是为职业而作文字,消遣是为兴趣而作文字”。 有个朋友很赞赏他的毅力,说:“我看了世界日、晚报五年,天天看见阁下的文字。而且除了世界日、晚报,又在其他的报上,日日看见你的文字。在这五年之中,我曾离开北京四五次,而每次回来之后,总不见你离开本职。这种恒心,实在难得了。”对于朋友的恭维,张恨水只报以一笑,说:“我们干的这个职业,是做一天的事,才能拿一天的钱。一天不干,一天不吃饭。他见我天天发表文字,却没见我天天吃饭用钱。”
大约从民国十五年(1926)起,张恨水开始给外报写小说。先是写了长篇小说《京尘幻影录》,逐日在北京《益世报》连载。“这部书,完全是写北京官场情形的”,“前前后后,也写了两年多,总有五十万字以上”。不久,北京《晨报》也约他写个长篇,于是,他便写了《天上人间》。民国十七年(1928),蒋、冯、阎军队进驻北京,《晨报》被迫于六月五日停刊,当时这篇小说并没有写完。直到《上海画报》、沈阳《新民晚报》、无锡《锡报》先后转载,才把它补齐。在为外报写作时,张恨水似乎也考虑到了成舍我的态度,但是他说:“既然《世界日报》欠着我薪水,我在编余时间为外报写小说,他们也不便干涉。”这时,由于《春明外史》的影响,他的稿约多起来了,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写了《春明新史》,给《上海画报》连载,未能载完,后由沈阳《新民晚报》连载收尾;《京尘幻影录》之后,他又为北平《益世报》写了一部《青春之花》,也未完成;继而又在北平《朝报》上连载《鸡犬神仙》,《朝报》创办于《晨报》停刊之后,后台老板是冯玉祥,故它也是短命的,随着冯玉祥的势力退出北平,该报很快也就关张了。在这期间,张恨水还曾兼任该报总编辑,约有半年之久,由此也能想象到他与西北军不一般的关系,几年后他赴西北考察,这种关系帮了他的大忙。有意思的是,停刊后的《晨报》很快便与新贵阎锡山搭上了关系,两个月后,即八月五日,《晨报》更名为《新晨报》恢复出版,张恨水随即写了《剑胆琴心》,在《新晨报》上连载。民国十九年(1930)夏,他又为沈阳《新民晚报》写了长篇连载小说《黄金时代》(又名《似水流年》)。
这样看来,在民国十五年(1926)到民国十九年(1930)这四五年间,张恨水除了完成世界日、晚报的编辑工作,写两报的连载,通常还有两三部长篇同时进行。他白天写小说,编副刊,夜间还要编新闻,看大样。极度劳累却不能按时领取全额薪水,而一家人的吃喝总要他来打发,这时,他也只能“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当然也有牢骚,心绪不佳,无以排遣,便作《也是离骚》自娱,其中写道:“嗟予生之不辰兮,幼不习工商。挥秃笔之兔颖兮,绞脑汁以养娘。每鸡鸣之昧旦兮,茫茫然而起床。乃昏灯之既掌兮,而犹差稿之数行。” 有人说他“无病呻吟,非近时所许”,但这回他真的病了,他在病倒五天后勉强坐起写了一篇《由病榻上写来》,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无病呻吟的这四个字,那是新文豪批评旧式文人的一个铁案。其实,无病呻吟,照目下看来,倒不论什么新旧。有些人无病固然不呻,可是矫枉过正,几乎有病也不敢呻,那又何必?昔人说:时非南唐,人非重光,何必为悲天悯人之句。太平之时,可以这样说。以言今日,我们哪个不是岁月干戈里,家山涕泪中。不必有病,也就可呻,何况是有病呢。”
这场大病之后,张恨水第一次向报社提出了辞职。成舍我当然舍不得他离开,说了许多挽留他的好话,他碍于情面,只好收回辞呈。没过多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北京城挂起青天白日旗的时候,成舍我由南京回到北京,继而发生了“欠薪”风波,张恨水再次愤然提出辞职,成舍我依然是好言相劝,不肯放他走。无奈之下,张恨水没有坚持非走不可,又勉强留了下来。他曾说过:“只要人家不来砸我的饭碗,我是顺来顺受,逆来也顺受。一天两足一伸不吃饭了,也就不必拿笔了。等我进了棺材,有人把明珠当金科玉律,我也捞不着一文好处。有人把《春明外史》换洋取灯,我也不皮上痒一痒。” 这话听上去总让人感到一丝辛酸和悲痛。过了不久,张恨水再次病倒了。病稍愈,他又马上提笔工作,并在一篇《小月旦》中针对“停了药罐就提起笔杆”的生活发了一通感慨:“躺着不能吃喝,要吃喝也没钱买。不躺着有吃喝,又不能不心力交瘁。倘是能躺着吃喝,又不浑身难受,岂不大妙!然而不能也,于是乎耗你的心力,去补充你的心力,就这样一耗一补,葬送三千世界恒河沙人数。呜呼造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民国十八年(1929)春夏之交,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结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次年春天,便有了《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的连载。这时,张恨水第三次提出要辞去《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所有职务,成舍我不好再强留,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四月二十四日,张恨水作《告别朋友们》一文,在与他相伴了七年之久的《夜光》《明珠》两副刊上同时发表:
我并不是什么要人,要来个通电下野。我又不是几百元的东家,开了一座小店,如今不干了,要呈报社会局歇业。所以我对《明珠》《夜光》的编辑,虽然已卸责两月之久,我并没有登什么启事。但是为了省这一点事,倒惹了不少的麻烦。外间投稿的诸位先生,有所不知,由文字更牵涉到事务上,不断地和在下通函。因此我只好来作这一篇告别书。
在《世界晚报》未产生以前,更不论《世界日报》了。在那联合通讯社里,我便是一分子,虽然我到现在,还是一个被雇佣者,我与本报,是有这样久长的日子,一旦云别,能毋黯然。而诸位投稿先生、读者先生,在文字上也早已做了神交,我也不愿突然地叫声再见,所以只得含糊着直到不能含糊的今天。
我为什么辞了编辑?本来无报告之必要,然而也不妨告诉诸位朋友的,就是人情好逸而恶劳。我一支笔虽几乎供给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我把生活的水平线总维持着无大涨落,现在似乎不至于去沿门托钵而摇尾乞怜。小人有母,我不敢步毕倚虹的后尘,不及颜回短命的岁数便死了,因之钱我所欲也,命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钱而取命者也,于是决定了节劳。这节字从那里下手哩?我除了本报编辑而外,还有六篇长篇小说,本市三篇,上海两篇,沈阳一篇,都是早有契约,不能中断的。其间可以节省下来的,只有编稿了,所以我决定了辞掉编辑。交代已过,请诸位朋友,以后不必以编辑事务来有所询函了。
一个读书不多而思想腐化的我,和诸位相见许多年。虽然打通的也有,而喝彩的也不少。兄弟这里给诸位鞠躬,多谢捧场。下场来不及抓诗,填阕《满江红》吧,那词是:
弹指人生,又一次轻轻离别。算余情余韵,助人呜咽。金线(疑为“钱”)压残春梦了,碧桃开后繁华歇。笑少年一事不曾成,霜侵发。抛却了,闲心血。耽误了,闲风月。料此中因果,老僧能说。学得曲成浑不似,如簧慢弄鹦哥舌。问看得几清明?东栏雪。
张恨水的性格是温厚而隐忍的,不像以“大炮”闻名的龚德柏,既然不认可“被雇佣者”的身份,便马上与成舍我闹翻,拉起一哨人马,自立门户。张恨水却不能不顾及朋友的情面,撕破脸皮的事他是做不来的,连辞职都是一而再、再而三,拖泥带水,久议不决。这一次,他的不满情绪虽稍有流露,却也还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算得上深得“温柔敦厚”之旨。不过,无论如何,他总算了结了与世界日、晚报的这段情缘,虽说还有小说在两报连载,他也时常为两报写些短文,但他的精神是大大地放松了,情绪也得到了疏解和释放,心情好了,生活便平添了许多乐趣。
这期间,他与胡秋霞又添了一双儿女。儿子小水于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出生,民国十九年(1930),小女儿康儿也降生了。添人进口,喜气盈门,张恨水也感受到了一种春风得意的满足和幸福。尤其是仰仗着《啼笑因缘》带来的声誉,他竟成了南北报馆和出版商争抢的香饽饽,不仅新的稿约应接不暇,许多旧作也被翻了出来,除了在报纸上连载、转载,还被人结集出版,为他增加了不少收入。十一月间,他应邀赴沪,在赵苕狂先生的撮合下,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版权以千字四元的价格卖给了世界书局,并以千字八元的价格与世界书局签了四部长篇新作。此外,他还答应为赵苕狂主编的半月刊《红玫瑰》写一部长篇,以谢朋友热心推介的厚意,这便是后来在《红玫瑰》连载的讽刺小说《别有天地》。而《啼笑因缘》的单行本也将于年内由三友书局出版发行。
张恨水此次南下,在上海停留不过四天,而当他离沪北上时,则可谓满载而归。当时就有传言,说他在十几分钟内就收了几万元稿费,回到北平就买下了一所王府,还备了一部汽车。对于无聊小报漫无边际的“呓语”,张恨水既无奈,亦无语。多年后,他忆及此事时还说:“中国卖文为活的人,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他这样提到当时的情形:
这年秋天,我到了上海,小报上自有一番热闹。世界书局的赵苕狂先生,他约我和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沈知方谈谈。我当然乐于访晤。第一次见于世界书局工厂,约有半小时的谈话。他问我还有什么稿子可以出售的,我就告诉了他《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而《金粉世家》,那时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写完呢。他说,你这是出过版的、登过报的,不能照新写的作品算,愿意卖的话,可以出四元千字。我说,容我考量。第二次,沈君请我到“丽查”饭店吃饭,约苕狂君作陪,极力劝我把两部书卖了。据我估计,两书各有一百万字。沈君愿意一次把《春明外史》的稿费付清。条件是我把北平的纸型交给他销毁。《金粉世家》的稿费分四次付,每接到我全部的四分之一的稿子,就交我一千元。我也答应了。同时,他又约我给世界书局专写四部小说,每三月交出一部。字数约是十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稿费是每千字八元。出书不再付版税。当时我以家庭里有几笔较大的费用,马上有一笔完整的收入,于我的家庭有莫大的好处,我也就即席答应了。
这一次,张恨水拿到了八千元钱稿酬,其中四千元是卖掉《春明外史》的版税,另外四千元是为四部小说预支的定金。卖文卖了十几年,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钱呢。他首先想到写信给老朋友郝耕仁,“叫他到上海来玩玩”。他们已经十一年没有在一起相聚了,此番相见,真是百感交集。张恨水说:“他来了,我分给他一些钱,又同路去逛西湖。” 郝耕仁劝他回芜湖看看,他固有此愿,但年关将近,有许多事需要他速回北平去处理,芜湖之游,只好作罢。他则希望郝耕仁能来北平,给自己帮帮忙,郝耕仁倒是满口应承,准备过了年就到北平去。
张恨水在年底之前离沪返平。离沪之前,他在《上海画报》刊发《张恨水启事》,以表达他对此次上海之行旧友新欢盛情款待的感激之情:
恨水此次南下,蒙诸前辈、诸友好盛情款待,宠誉有加,私衷惭感,楮墨难宣。比以北平来电,匆促言旋,沪上地阔途疏,不能一一走辞,尤为歉仄,北上而后,益当勉竭驽钝,力治所业,以答诸前辈友好奖劝之至意。临颖依依,不尽欲言,特此申谢,并乞鉴原。正恨水拜启,二十日。
张恨水回到北平时,他手上大概还有六七千元。十八年后,他回忆此事时说:“若把那时候的现洋,折合现在的金元券,我不讳言,那是个惊人的数目。但在当年,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这笔钱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把弟妹们的婚嫁教育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寒家连年所差的衣服家具,也都解决了。这在精神上,对我的写作是有益的。我虽没有癞蛤蟆去吃天鹅肉,而想买一所王府,但我租到了一所庭院曲折、比较宽大的房子,我自己就有两间书房,而我的消遣费,也有了着落了。”
他这里所说的房子,即西长安街大栅栏12号。这条胡同也是南北走向,南临西长安街,北接力学胡同,由于它的东侧50年代建了一座电报大楼,遂更名为钟声胡同。在未英胡同30号住了五年之后,民国二十年(1931)一月,张恨水将全家迁到这里。他在随后给钱芥尘的信中提到:“弟十二日迁寓西长安街大栅栏十二号。此‘大栅栏’三字,读‘大扎啦’,别于前门外之‘大珊滥’(大栅栏)也。” 关于这所宅院,他在《影树月成图》一文中也有生动的描述:
大栅栏十二号,以曲折胜。前后左右,大小七个院子,进大门第一院,有两棵五六十岁的老槐,向南是跨院,住着我上大学的弟弟,向北进一座绿屏门,是正院,是我的家,不去说它。向东穿过一个短廊,走进一个小门,路斜着向北,有个不等边三角形的院子,有两棵老龄枣树,一棵樱桃,一棵紫丁香,就是我的客室。客室东角,是我的书房,书房像游览车厢,东边是我手辟的花圃,长方形有紫藤架,有丁香,有山桃。向西也是个长院,有葡萄架,有两棵小柳,有一丛毛竹,毛竹却是靠了客室的后墙,算由东折而转西了,对了竹子是一排雕格窗户,两间屋子,一间是我的书库,一间是我的卧室。再向东,穿进一道月亮门,却又回到了我的家。卧室后面,还有个大院子,一棵大的红刺果树,与半亩青苔。我依此路线引朋友到我工作室来,我们常会迷了方向。
这样一所宅院,月租金只有四十元。此时大约是张恨水居京以来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间。虽然很忙,“约有六七处约稿,要先后或同时写起来”, 但他并不感到紧张和压力,反而“心广体胖”, 神清气爽。他颇有些得意地回想起民国二十年(1931)居住在大栅栏12号时的情景:
我坐在一间特别的工作室里,两面全是花木扶疏的小院包围着。大概自上午九点多钟起,我开始写,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去。吃过晚饭,有时看场电影,否则又继续地写,直写到晚上十二点钟。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加油的工作不错,否则我永远落在民十以前的文艺思想圈子里,就不能不如朱庆余发问的话,“画眉深浅入时无”了。
这时,张恨水不再为钱而苦恼,他说:“其实我的家用,每月有三四百元也就够了,我也并不需要许多生活费,所以忙者,就是为了情债。往往为了婉谢人家一次特约稿件,让人数月不快。”这是他的新苦恼。虽然他已如老母亲所言,“成了文字机器”,很想减少些工作,但稿约还是接踵不断,他无可奈何地说:“殊不知这已得罪了很多人,约不着我写稿的‘南方小报’,骂得我一佛出世,二佛涅磐。” 本来,他约郝耕仁来北平,就有意请他帮忙分担些文债,并一起搜集整理资料,准备编写《中国小说史》。他在抵达北平后写给钱芥尘的信中就曾提到:“一切旧稿,须候郝先生来平,再为整理寄上。”旧历新年后,郝耕仁如约来到北平,但他没能像预想的那样常住北平,两个月后,就因妻子病重而返回安徽。他的女儿郝君仪(漾)曾在《回忆我父亲郝耕仁与名小说家张恨水的友谊》中写道:“那时恨水先生在北京已经租了一所大宅院。院内屋宇庭院错落有致,花木扶疏,环境幽静。我父亲去后独自住了一小院。二人兴致勃勃地分了工,拟定了搜集史料的计划。刚两个月的光景,不料我母亲得了‘狂疾’……日夜哭闹不休,惊恐失常。我和两个姊妹十分害怕,我只得写信要我父亲回家,父亲不得不抛弃他心爱的工作回来给我母亲延医治病。”
结果,张恨水的忙碌依然如故。这一年秋天,他把第三个妻子娶进了门。这个在婚后被他改名为“周南”的女人,几乎小他二十岁。然而,他们的婚后生活却可谓琴瑟和谐、意趣相投,有着说不尽的喜悦和甜蜜。张恨水对这次婚姻由衷地感到欣慰,他相信,这正是多年来他一直渴望得到的爱情之果。这时,虽说全家都在大栅栏12号的深宅大院里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他还是另租了铁门胡同的一所小院,与周南共建了一个小小的爱巢。次年八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张恨水的次子二水。得子之乐总算给了两个月前经历丧女之痛的张恨水一些安慰。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得华北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军队在占领东北全境之后,开始把战火烧向华北,威胁平津。先是锦州、热河战事频发,中国军队被迫撤离。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山海关战事又起,继而失守,日军随后总攻热河,进占承德,迫近冷口、古北口、喜峰口一线,长城战事爆发。局势由此更加恶化,北平城内人心浮动,惶惶然不知所措。为了躲避越来越迫近的战乱,张恨水开始考虑在适当的时候举家南迁,把母亲和妻儿送回安徽老家去。于是,张家十几年的“平居”生活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