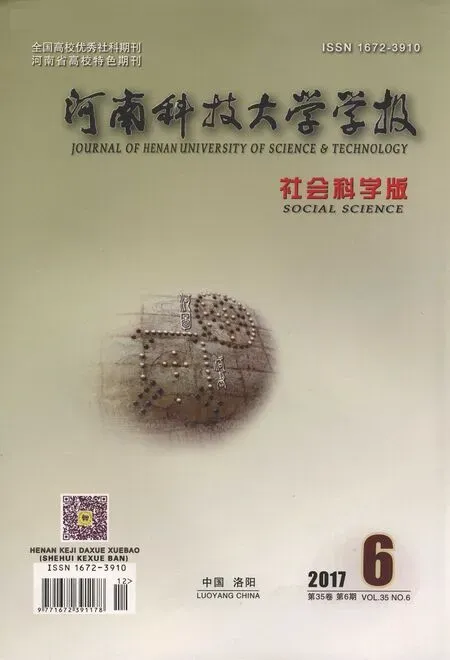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理论的符号哲学研究
2017-02-25李泉
李 泉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65)
【哲政阐赜】
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理论的符号哲学研究
李 泉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65)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神话学注重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推崇实证性分析和逻辑推演的研究范式,不但在探索“心智”哲学中获取了深刻洞见,而且对打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壁垒的深化性跨学科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从符号哲学体系的认知论、本体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解读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神话学分析,能够从体系上透视列结构主义神话批评范式理论的可行性与局限性。基于结构主义人类神话学的符号哲学批评为学界从符号表意之维认知人类自身和人类处境,以及从人本符号哲学视域的文化结构层面把握人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文学哲学基础。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符号哲学;二元分析;野性思维
西方现代神话学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神话学的创立,泰勒、弗雷泽和涂尔干对此功不可没。此外,现代神话学的创立促使学者把原始部族神话纳入了神话研究体系,大大扩大了神话研究领域。第二个方面是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理论,它促使学界开始发掘“无意识”同神话与梦境之间的关联。第三个方面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开创了结构主义人类神话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在广泛吸收结构语言学、法国社会学派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以融合实证科学与思辨哲学的学术精神、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宏观视野对原始氏族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成果至今仍对现代文化符号的表意与传播以及人类思维哲学的认知与解读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著作翻译与研究名家李幼蒸先生所言:“他把其哲学理论眼光射向一直偏于经验性的人类学具体资料对象上;把主要基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模型’带入知觉经验领域,在人类学术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在社会文化现象中将具体性和抽象性加以统一的理论化方向。”[1]在王立志看来,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研究的本质性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神话的逻辑结构所体现的精神的逻辑结构”,是“在创造物中直观人自身”[2]25的人类科学基本原理投射到神话研究的延展性应用。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引入传统人类学后又让结构主义思想放射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促使研究者“在杂乱无章的事物中发现了一种统一性和一致性”,进而揭示了单纯的史实描述性研究所不能完成的深刻思想。这一研究范式“不仅从根本上转变了人类学(人的科学)的研究方向, 而且促进了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和方法论革命”[2]22。王立志如此阐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神话研究中的符号学思想:“他强调文化中普遍的东西与自然中普遍的东西是不同的,文化中普遍的东西在象征体系中。只有在记号分析的层次上才能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对立, 把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结合起来。提供结构的结构躲进了人类创造的符号里,情感转移到了符号里,人类的不朽性在符号的世界里传递。”[2]26因此,从符号学意义生成的角度透视作为思维方式的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对于认知结构主义如何成为人文学界中开展科学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符号学理论视域切入,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理论资源进行认知论、本体论与方法论多维度的哲学体系批评,进而深化对结构主义人类神话研究理论可行性与局限性的整体认识。
一、神话的结构与表意:认识论研究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把神话视为人类的一种交流模式,它包括人类的经济交往、通过交换妇女形成的联姻交流以及其他多个方面的交流主题。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所有神话都被创作人植入一个目的,即构建一种媒介模式来中和人类世界观中的二元对立冲突,因此所有神话都具有“在两个极端相互对立中产生一种中和媒介”的核心神话结构,而神话的内在思维推进模式也与神话结构相一致,总是通过有意识的二元对立抵达最后的解决。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机制决定了神话传递的信息非常抽象,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神话的整体结构、各个层面结构组建的错综复杂关系以及其中的中和媒介来发掘神话传达的信息。
首先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研究中神话整体结构的超内容存在。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同一神话不同版本的表面意义也许千差万别,但是该神话的结构和基本关系是恒定不变的,有时表面符号的改变、倒置或是其他形式的细微变化反而更能凸显神话结构的恒固性。这种暗含意义的结构通常是无意识的(至少在氏族部落里是这样),而且这种无意识结构并不影响它如实反映部落群体中盛行的关注(比如说对社会或是季节性冲突),不少关于植物起源、人成长与衰老、妯娌关系之类神话都体现了部落群体对自然或文化冲突的关注。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解读即是从共时性角度分析神话情节,以此“揭示神话的深层无意识性质”[3]。列维-斯特劳斯曾以普布洛创世为例,揭示了神话中神话信息的展现模式与神话中生与死主题间的重要关系。在普布洛创世神话中,狩猎作为一种获取食物的方式,可被视为生与死的中和媒介,因为狩猎是一种介于农业(一种既可获取食物、延续生命又不杀生的觅食方式)和战事(一种引发死亡的特别狩猎方式)之间的谋生手段。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指出,如果食草动物代表着生的一面,食肉动物代表死的一面,那么介于二者之间的食腐肉者就成了中和二元对立的第三个方面,因为食腐肉者既不杀生,又以动物们的生肉为食。由此推断,古代人从自然界事物的二元独立关系中生发出了一种逻辑,以此种逻辑诱导众人把死亡纳入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从而促使他们更加坦然地接受死亡。
接下来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研究中神话结构各个层面的复杂关系。依列维-斯特劳斯之见,神话结构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结构层面或结构符码,包括社会符码、烹饪符码(技术-经济学符码)、声音符码、宇宙符码和天文符码等等。任何一个神话都有可能包含以上所有或者大部分符码,这些符码组成了神话暗含的“信息”——有意义的关系结构。因此,一个完整的神话大都可以从中提取或多或少的相似性符码。解读神话的信息、神话信息的意义或相关中和媒介的信息、中和媒介信息的意义的前提,是先深入发掘处于隐秘层面的深化结构神话的隐秘结构层面,破解衍生自基本符码并在不同结构层面形成的交叉性指称体系中发生变异的相似性符码。但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承认,在不少情况下神话的作者或是制造者并没有意识到神话最终会产生何种意义,有些意义其实是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注入的。对此列维-斯特劳斯辩解道,神话分析不应将展示人类如何思考作为研究目标,因为神话本身并没有阐明神话在神话中的思考方式,而是显现了“神话如何在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通过人来展现神话的思维”[4]20。英国古典神话学家柯克将这一说法视为典型的列维-斯特劳斯式悖论,不过是想说,人们允许思想中的潜意识借助故事元素的构成方式流露出来[5]44-45。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第2卷末尾进一步阐述道,他所有的分析都在论证“发掘神话间各种差异的重点不应将重点放在数量众多的神话例子本身,而应放在发掘这些差异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一种共同属性”[6]407,“这一属性通过一种几何学术语表达,而且以一种代数学方式实现彼此间的灵活转变”[6]407。如果这种抽象的分析方法属于神话而不属于神话讲述者,我们就会发现“神话性思维超过了神话本身负载的内容和引发思考的内容,超越了意义镜像但仍然依附于对概念世界的确切感受……(确定)不再由外在现实世界进行指称,而是根据它们心智结构上的相互吸引或是互不相容进行自我彰显”[6]407。在阐明“心智”(esprit)这一概念时,列维-斯特劳斯像其他人类学家一样大谈起了古希腊,声称这是希腊神话转变为哲学的阶段。就本质而言,列维-斯特劳斯眼中的“心智”其实就是指人类的思维结构,具体说来就是决定思维方式的先天性倾向——“二元分析模式”。他将这种类似于黑格尔式二元辩证法的“二元对立式思维结构”视为具有“世界共同性”的人类思维方式,无论是尚未开化的原始部族还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群。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显而易见的思维模式,二元对立思维把多个方面的人类经验划分为一系列便于区分的二元范畴,比如说左—右、上—下、男—女、我们—他(她)们。列维-斯特劳斯从人类的心智之维审视神话,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神话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内容完全是通过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且能够以代数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神话并不是“关于”世界或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特定方面的描述,而是要“关注”社会问题或是冲突,“关联”到人类诸般思维方式和人的总体特质如何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环境之中。如果原始人的神话的确意在揭示或者能够揭示关于自然和人类思维模式的某种真理,那这类研究就会很有价值,也值得深入进行下去。然而可惜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他提出的“代数式”研究范式也只是从神话中机械地抽取一些不同类型的符码,这导致了符码间的有机联系被人为切断。通常情况下神话符码只有同神话内容相互关联才能产生相应意义,脱离了具体语境的神话符码是不足以完成表意的。
如柯克所指出,列维-斯特劳斯一方面极力否定涂尔干的见解,不认为神话反映了社会群体的集体性表征,另一方面又在全力探寻神话传递的信息,所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比较倾向于关注神话反映的社会生活或是经济生活现实中的困难问题。比如他在《从蜂蜜灰烬》一书末尾的总结中就试图通过考察客观社会存在的方式发掘神话的最终意义,于是发现了神话折射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列维-斯特劳斯写道:“首先,烹饪神话中出现了对火、肉以及栽培植物的出现和缺失的关注,关于地界划分的烹饪神话又涉及到了众亲戚在场和缺席,由此得知,基于烹饪神话,人们以一年中丰足和不足的不同状况来划分不同的时期。其次,更重要的是……关于烹饪起源的神话牵涉到了联姻中的生理学问题,烹饪艺术行为代表了联姻的和谐功能……同样,处理烹饪边界的神话发展出了婚姻病理学,其根源通过解释烹饪艺术和气象生理学的象征意义而被揭示出来……”[6]405不错,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前两卷中分析的很多神话都“暗中揭示”这些部落采用的妇女交换系统源自于不同的倾向和张力,这一结果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亲缘观”和“图腾”思想相吻合,但同他“所有神话都包含着一种代数式”的论断又相冲突。第三卷中一个重要的图库那(Tukuna)“指称性神话”就展现了一种支持反向结论的故事境遇。列维-斯特劳斯在此神话中发现了它的社会层面符码,即表面上英雄所经历的一系列婚姻经历,然后进行了更深层面的发掘,却发现越发掘社会层面符码的主题越肤浅,最后对深层符码的探究竟沦为了“对狩猎和钓鱼作为生活方式的比较性阐述”[7]。 因此恰如柯克所言,神话基础层面符码的意义并不是抽象的或是代数式的,神话的意义由神话的整体结构决定,而且负载神话意义的是神话内容本身而不是神话结构。
由于过度阐释神话结构、轻视神话内容,列维-斯特劳斯没有从系统功能层面充分论证无意识结构到文化建制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发生过程。王伟涛亦指出,列维-斯特劳斯并不重视“结构”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作用过程[8]。格尔茨亦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将“解读神话、图腾仪式、婚姻规则和其他各种有待阐释的文本视为解读密码的过程”[9]449,“他不求理解符号表征形式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发挥建构人类认知(意义、情绪、概念、态度)的功能,只求完全理解其内在结构”[9]449。
二、神话的野性思维:本体论研究
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思维》中指出,包括青铜时代在内的氏族部落根据无形的规则、采用了一种在西方人看来十分偏执的原则将动物和植物快速分类,然后利用那些分类来组织抽象思维、安排社会结构。这种无形规则背后的逻辑与相对发达的西方社群截然不同,因此是一种迥然不同西式思维的“野性思维”。如柯克所言,这种“野性思维”与勒维-布鲁尔(Levy-Bruhl)及其追随者提出的旧式“前逻辑性”,以及几乎具有半开化阶段性质的“原始人”没有相似之处。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思维》中引入“Bricolage”这一重要词汇来比喻“对随机抽取的临时性材料进行即时发挥”的行为,生动地揭示了野性思维模式。拼凑者(bricoleur)则指可以制造随时可用材料的人,不管所用的是否是最好的材料。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制作者允许神话自身思想结构的成型,但其自身并没有创造神话的结构,只是复制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以便他或她能在神话符号中寻找他或她置入神话的结构或是相互间关系的所指踪迹。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制作者只需将这些符号堆叠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一个神话,这些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且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神话符号在建立相互关系的过程中为彼此赋予的相应意义。柯克将神话制作者的这种工作方式比之于“手工业者”,因为二者都只是“依据手中的现有资料临时搭建起一种结构”[5]82。 保罗·利科也持赞同态度,认为在“材料安排比材料内容本身更重要”的部落中,“人们的思想确实是拼接而成的(Bricolage)”[10]607。利科还发现,与相对发达的氏族不同,野蛮氏族中的人们尤为强调对手头材料的安排,却并不关心材料安排好之后材料之间的兼容性。
可惜,列维-斯特劳斯对“野性思维”运作方式的分析歧义顿生。他在《生食与熟食》(Le Cru et le Cuit)的导论中写道:“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像‘生食’和‘熟食’、‘新鲜’和‘腐化’、‘潮湿’和‘烧烤’之类的经验性范畴如何被人从抽象的概念中抽取出来,作为一种概念性工具来塑造成一种观念。”[4]9这一观点同他前一本书《野性思维》的主题基本一致:人类学家已经证明,“原始”氏族对植物、树木、动物和其他事物做出的精细划分极具典型性,其诱因是他们需要在不同层面的经历之间组建一个全方位的交叉性指称体系。这一体系允许人们形成一种对生命总体结构的大致看法,而且是非常抽象的看法。列维-斯特劳斯却没有考虑到,野蛮人或是原始人倾向于把自己在多重世界的经历浓缩成一个有序的系统,通过这一系统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预测。由于这种系统的建立依据是环境中每个独立部分的即时性差异化属性,所以与预期相关的所有其他属性的堆积都依赖于系统的外在表征和内在功能。从表面来看明显不同的关系类比太过复杂,而且“代数式”和“从抽象概念中抽取范畴”的方法是否可行有待验证,因为它们的操作目的与经验世界无关。从表面看来原始人的思维似乎深深根植于亲身经历的实体性世界,所以他们必须超越这个世界的诸般现象,对其中的空想性因素进行严格检视,以此促成精细分类系统的产生,并明晰确切经验在思维模式中发挥的作用。列维-斯特劳斯有时候会列举一些与神话实际目的毫不相关的范畴划分,且自认为抽象和范畴归纳的力量在原始部族人群潜意识中发挥的作用同科学社会中发挥的指导作用一样重大,却忽略了他本人对抽象化或是范畴归纳的过度兴趣,冲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扰乱了他立足于客观观察基础上的推演分析。
列维-斯特劳斯欲借助林奈式的范畴划分实现对原始社会中科学考察实证的哲学理论升华,结果却在科学实证与哲学思辨中来回穿梭。另外,“野性思维”方式主导的文化所孕育出的神话,其表层之下的运作机制必然不同于先进的、非图腾社群的高级神话。列维-斯特劳斯基于对“野性思维”主导下的原始氏族神话展开了结构主义分析,提出了“所有的神话都是为了中和一定的矛盾”的通用性观点。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因为这一论断夸大了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适用领域,也在于这一论断夸大了原始神话的“中和性”功能。
由上述分析可知,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在强调实地材料考察的人类科学和强调意识思辨的本体哲学之间摇摆不定。他的一段论述非常有名:复杂的结构是否能在神话中客观实在地展现并不重要,是否能被现代解读者解读也不重要,因为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本质,即“心智”,这表明了它作为一种思维与另一种思维(或是一整套思维体系)之间进行联络或交流的产物,因此结构是在吸收一种强加的结构(存在于评论者的思维模式中)之后形成的。这一观点可能是异想天开。列维-斯特劳斯的绝大多数论证倾向于人类学与科学,他将实证性范畴描述为“每次都只通过特定的文化视野和精确的民族志观察方式获取”[4]9。 恰如李幼蒸所言,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神话学研究其实只是对文学现象的一种“科学式扫描”[1]25。以此观之,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具有一名人类科学观察者的实证主义素养,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名哲学家的主观主义气质。从人类科学的角度研究神话和神话作者的确是一块值得深入的领域,但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哲学科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界限的,二者不应也不能混为一谈。
三、语言—神话推论:方法论研究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源出于语言,并构成了同语言、音乐和有节奏的声音相并列的“第四种听觉模式”,神话像语言一样,无法在孤立的语境中产生意义,而只能在相互关联的语境中产生意义,因此研究者也应在整体语境关系中解读神话的意义。语言中的基本构成符号——音素或音位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同其他语素符号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相应意义。同理,神话也应当有基本的构成符号,即单体叙述符号,单体叙述符号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就像语言只有在成为一种交流方式时其潜在结构才会为语言赋予相应的意义,神话的单体叙述符号也无法在无机的符号堆积中能产生意义,而只能靠置身于神话潜在结构暗含的相互关系来建构神话的真正意义。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神话推论研究范式也并不是没有弊端。笔者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神话推论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过于频繁地使用语言-神话推论,导致神话的结构主义剖析歧义丛生、晦涩难懂。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细节解读上有过分夸大神话系统体现出的、人类二元分析思维倾向的嫌疑,比如说关于“上”—“下”两极结构对应的情节,列维-斯特劳斯非要用耳朵来对应代表与肛门相反一极的洞孔,将其强制阐释为与“下”和“后”相对应的、最贴近的“上”和“前”的代表,显得非常牵强而又十分怪异。
第二,完全抛开神话内容,纯粹依赖神话结构来解读神话意义的研究方法有点本末倒置。的确,语言功能的全面实现在于语言内容得以完整表达,而不是语言自身结构—语法规则或句法规则被编码性表述。若语言—神话推论成立,神话的意义就不应单靠神话结构来传达神话意义,因为语言的意义就不是只靠句法结构来传达的。因此,语言—神话推论得出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不应将神话内容逐出研究范围。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一方面宣称神话的意义与神话内容毫无关联,一方面又依靠特定的内容来寻求对神话意义的最终解读。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内容与神话结构在神话意义表达方面的极端论断,柯克所持的是一种居间性的调和态度:神话表达的意义生成于神话表面内容和神话结构间的关系,但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关系“结构”,而是一些“由特定材料组成、从某种程度来说决定神话结构的结构体系”[5]43。
第三,列维-斯特劳斯把仪式、图腾制度、亲缘关系、婚姻法规、烹饪习惯以及社会文化现象体系视作具有历史宏大叙述的社会语言系统加以研究,这一研究方式过度倚重对已有文本的封闭式分析,而忽略了文本的生成与作者的主体性这些人文关怀性问题。在肖伟胜看来,运用语言学模式研究人类社会的研究方法“使得像语言一样运作的社会成为用功能主义方式构想出来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社会性、交换系统和相通的人性,但缺少了权力层面上的冲突与支配”[11]。列维-斯特劳斯将文化系统视为宏大的社会语言系统,社会在文化系统自身逻辑的决定性作用下运行,以此塑造人们在虚拟神话和现实婚姻生活中的行为机制,“这种抽象的文化观念无疑否定了人的能动性,这就导致野性的思维看起来像是一种脱离了实体的、集体而超验的思维”[11]。
第四,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中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作为全人类神话乃至文化的“普世性分析范畴”,这一做法有时显得过于主观随意,在用于具体分析对象时往往会出现先验性判断。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中野性思维和亲缘关系的结构性分析可以看出,他常常会有意地只提取利于自己观点的佐证材料。董龙昌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把源于现代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然后在神话、诗歌、音乐及原始艺术造型等文艺研究领域中进一步验证和深化,这种以“诗意的联想方式”建构的研究思路体现出了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12]。但与此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结构方法(以二元对立为主要标志)充满了主观随意性,以神话研究为例,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的结构不过是人类心智之无意识结构的体现,它是先天存在的,所以他对神话结构的分析更多地是立足于他本人的‘结构’通过演绎得来的,而不是真正从客观存在的神话的‘结构’出发概括出来的。”[12]程代熙先生亦指明:“列维-斯特劳斯把‘二元对立’当作一个框架,把他所需要的东西往框架里一放,并根据自己的心愿来加以解释。因此,他的‘二元对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武断色彩。”[13]
四、结论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宏观层面追问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倡导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是否有助于解读神话的意义?即是说,《神话学》前两卷中对南美印第安神话和第3卷中对部分北美神话的分析是否正确?这些神话是否存在一种十分相似且复杂稳固的神话结构?如果第一个观点成立,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否所有神话都可以从中提取出一种用以中和一系列冲突的特定结构?来自其他文化的神话,比如说希腊神话是否也存在类似于美洲神话的神话结构,它们的神话结构模式是否也会以相似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理论有何依据?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取得了开拓性进展,揭示出了氏族部落神话整体上超出预想的系统性,其中一些神话的确包含着多层含义,这种含义可以在同一种结构模式中被复制下来。通常情况下神话也存在着一种“隐秘”层面,这一层面使神话能够保持其他类型的特质(比如叙事性、规约性、表面性或是隐寓性解读等等)。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与这些特质紧密相关的因素是神话内容而非神话结构,而列维-斯特劳斯在解读和评述神话的最终意义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这些因素。这是我们在进一步研究中需要注意和避免的。
另外,列维-斯特劳斯声称,结构主义是解读非西方氏族神话的最好方法,因为西方观察者没有注入个人偏见,能够站在他者文化的立场进行客观观察。的确,鉴于美洲神话叙事结构和流传版本的繁杂性与复杂性,再加上神话功能与意义叙事之间的错综纠葛关系,原始氏族人类的思维方式“大体而言的确与结构主义理论有着密切关联”[10]608。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确实也是目前唯一能合理解释大多数巴西“原始社会”和“图腾”社会神话的理论。列维-斯特劳斯采用人类学的跨文明结构主义神话阐释方法,把非西方的“原始社会文化”当作一面镜子,以西方视野考量了原始社会的价值观,一方面如李幼蒸所言,产生了深刻而又独特的“文化批评共鸣”,另一方面过于简单化的推导结论也使其理论解释力有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柯克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最显著的成在于他展示了二元对立模式如何在巴西中部印第安人及其邻居的思维和想象中占据主导性地位。[5]79确如柯克所言,我们可以从二元抉择范式中发现人类广阔的视野和对自身生活的强烈兴趣,比如说对生与死、自然与文化的关注。列维-斯特劳斯率先发现并阐明了一些文化中部分神话(包括西方传统神话和非西方原始氏族部落神话在内)的解释性功能。这些神话案例证明,神话的结构和内容可以提供一种中和矛盾的模式。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的绝大多数神话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列维-斯特劳斯推导结论意欲表明的问题——生食与熟食的对比是阐述最常见问题(比如说人类借用火、烹饪以及自然腐化过程等现象)的绝佳模式。不过列维-斯特劳斯论证的“二极对立谋求中和”这一神话功能只是神话多种意义与功能中可能存在的其中一种,而非唯一一种。神话的意义与功能在多种文化中有多种可能性,比如立法性功能、讨论土壤肥力和四季变换、代表对死亡世界的恐惧和对死亡世界的信仰、关于自然和诸神、伴随不同职位、事物或食物生产方式的评论等等。在某些情形中,一个神话可能会同时具备并完成上述一种或多种功能。从神话的社会功能目的来看,二元思维方式推动人类发展出一种为神赋予人性和异族通婚(部落建立两部族合一的原则)的观念;从人类社会层面来看,神话系统系统性反映了人类对亲缘关系和社区生活问题(包括食物生产方法、狩猎方式、一年中不同季节的限制性条件与决定性因素)的持续性关注,所以两极选择模式并不是一种能够以一概全的通用性范式,只是反映出了人类生活中的部分问题,而没有反映出人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此外,神话内在的幻想性或是超自然因素诉求也会使起源解释性神话彰显出极强的故事性。
至于第二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选材,保罗·利科在《结构和阐释学》(Structure et hermeneutique)一文中反复提及,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神话性思维的例子“总是取自于崇拜图腾的地区,而从未选取来自闪米特地区、前希腊地区或者是印—欧地区的神话例子”,同时指出“图腾”神话(比如说印第安神话)和文明地区神话(包括苏美尔-阿卡迪亚神话、希伯来神话、埃及神话、迈锡尼神话和伊朗神话)有着根本性区别,所以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分析的合理性需要质疑[10]607。确如E.R.里奇所言,列维-斯特劳斯选取的神话都设置在“人和动物之间的显著区别被模糊化、同时具体历史纪年缺失的真实性或想象性场景中”[14],但笔者认为,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而完全否定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分析的合理性。人与动物紧密关联缺失的神话系统的确会具有不同于其他神话的特质,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分析也充分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图腾神话类型本身、神话分析以及神话结构步骤分析中的洞见往往潜藏着一些比文明神话类型与神话分析更为深刻的思维哲学。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研究的理论价值。对于结构主义神话研究范式能否扩展到希腊神话研究的问题,首先,就研究对象来看,如柯克所言,我们所理解的希腊神话在形式上已被“非常严重地污染了”,表现出了多次“逐步重构”(progressive remodeling)的迹象,尤为典型的就是思想性或阐述性因素与民间故事成分的此消彼长现象,民间故事成分常在牺牲思想性或是阐述性因素的前提下被过度夸大[5]50。里奇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部分观点,认为希腊神话的结构能在博学庞杂的注释或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展开的新型现代精神分析阐述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因为“神话总体囊括了神话本体的所有版本”、“神话会给人们以一种长期不变的神话感”[15]。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笔者无法赞同,柯克也持否定看法,因为逐渐发展的文学性能够、也经常干预甚至完全改变传统神话的初衷。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列维-斯特劳斯式神话分析将只能用于解读一小部分希腊神话,而不具有列维-斯特劳斯所倡导的“理论通行性”。就研究内容来看,虽然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在《俄狄浦斯》一书的分析论证和之后E.R.里奇展开的列维-斯特劳斯式分析引入了一些有趣的研究方法(诸如差异对照、类似对应和倒置转换等),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方法的应用都不太成功。至于闪米特神话,列维-斯特劳斯武断地认为不应该纳入分析范畴,因为神话研究应当从具有“古老性和神性残迹”的神话起点开始[16],而《旧约》神话的“神话性残留和古老性”在修订和学者阐述过程中被叠加了起来、由此丧失了其客观性[10]631f。对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力所不及或是不易操作的神话案例,列维-斯特劳斯作了一个危险的选择,直接贴上“非真正神话”的标签,将其逐出了研究范围,这一处理方式与他倡导的“科学研究”实在南辕北辙。
简言之,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看待结构主义神话理论,一方面,汲取其中的有效理论资源、借鉴它的独特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并正视它的局限性。从严格意义来说,虽然结构主义神话学具有一定的理论可行性,也提出了一些极具洞见的观点,但总体而言结构主义神话研究范式并非列维-斯特劳斯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研究法”。我们对列维-斯特劳斯理论进行批判的价值不仅在于指出观点的谬误,更在于纠正他试图以一种“通用性”研究方法或研究视野来总括全人类整体神话思想的非科学性研究倾向。文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兼容实证性科学考察分析和人文性本体哲学推演的学科,应当采取科学的研究步骤、从哲学的思维高度展开研究,首先广泛搜集各种文化的神话材料、然后实证性探寻神话中的思维规律,而不是首先以一种或多种可能存在的“先验性”范畴概念来定论所有神话的人类思维规律,然后在主观预设的操纵下靠有意选取的片面材料来佐证自己的“通用式”理论。神话的内容和其他很多方面是由叙事和戏剧规则决定的,而这些规则并不一定非要包含“两极分化心智”的意识。
最后,对于神话结构理性分析的局限性问题,笔者认为,从文化生成之源审视文化思维具有一定的深度和价值,同时要从文化结构层面把握人的本质特征,从符号表意的哲学视域综合审视结构思维的人本主义内涵。的确,我们所生活的符号世界本质上是不断生成与变化的关系结构,理解符号表意对认知人类自身和人类处境有着重要意义。人类的情感表意如何注入符号的表征,人类不变的思维如何彰显于符号的世界,这个问题需要展开更深层次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追问。正如王立志所言,“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是一种指引:理性内在于人的生存方式中, 人文世界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符号世界,人文科学应该通过获得与自然科学可通分的更佳真理强化自身”[2]。
[1]李幼蒸.列维-斯特劳斯对中国社会科学启示之我见[J],山东社会科学,2010(2):22-30.
[2]王立志.人的科学如何可能——从方法论视角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12):22-26.
[3]方汉泉.二元对立原则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7):37-41.
[4]Claude Lévi-Strauss.Le Cru et le Cuit,in Mythologiques,vol.I [M].Paris:Plon,1964.
[5]Geoffrey Stephen Kirk. Myth Its Meaning and Functions in Ancient and Other Cultures [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6]Claude Lévi-Strauss.Du Miel aux cendres, vol.II of Mythologiques[M].Paris:Plon,1966.
[7]Claude Lévi-Strauss. L' Origine des manières de table,vol.III of Mythologiques [M].Paris: Plon,1968:26.
[8]王伟涛.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研究理路探析[J].世界民族,2011(3):42-47.
[9]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by Clifford Geertz[C]. NewYork: Basic Books, 1973.
[10]Paul Ricoeur.Structure et hermeneutique[J].Esprit,Nouvelle série,1963,322(11):607.
[11]肖伟胜.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与“文化主义范式”的初创[J].学习与探索,2016(3):118-129.
[12]董龙昌.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在中国——兼论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研究的意义[J].民族艺术,2014(1):116-120.
[13]程代熙.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结构主义[J].文艺争鸣,1986(1):72-78.
[14]Edward Leach.The Legitimacy of Solomon: Some Structural Aspects of Old Testament[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1966,7(1):60.
[15]Claude Le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M]. Claire Jacobson﹠Brooke Grundfest Schoepf(Trans.) New York: Basic Books,1963:217.
[16]Paul Ricoeur.Résponses à quelques questions[J].Esprit,Nouvelle série,1963,322(11):632, 630 ff.
ACriticismofLevi-Strauss’StructuralMythologyfromaPerspectiveofSemioticPhilosophy
LI Qu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065,China)
Levi-Strauss adopted a method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to explore the deep insight hidden behi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is academic method, which focu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logical deduction, form a pioneering paradigm for the future studies to break the barrier between the liberal arts,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e science. From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of Semiotic Philosophy, this paper makes holistic study on Le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ical Mythology upon three levels: Epistemology,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n makes a deep investigation on its theoretical feasibility and limitations as an analytic paradigm in the field of mythology. Based upon those analyzing, the academy could gain a fuller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signs from the Structuralism Mythology, then give a deeper cultural, structural reflec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the basis of semiotic basis of Ontology Humanism.
Levi-Strauss; structuralism; mythology; semiotic philosophy; binary analysis; savage mind
10.15926/j.cnki.hkdsk.2017.06.005
I0-02
A
1672-3910(2017)06-0035-08
2017-06-01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6XZW007)
李泉(1987— ),男,河南安阳人,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