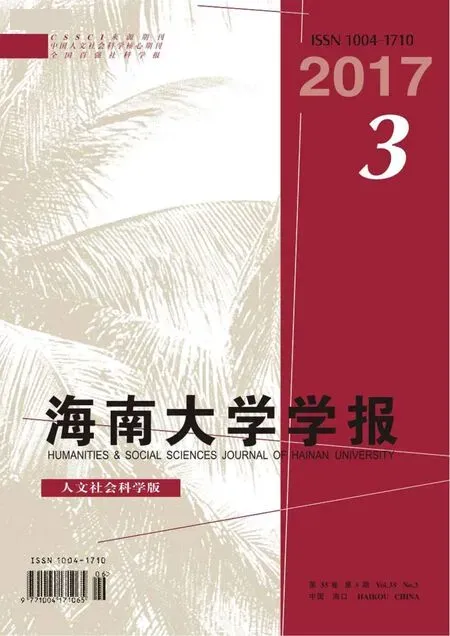历史书写与文学想象:论日本核文学的叙事策略
2017-02-24刘霞
刘 霞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湖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历史书写与文学想象:论日本核文学的叙事策略
刘 霞1,2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湖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日本核文学是日本文学中所出现的涉核题材的作品总称。从原爆文学发展到原发文学,日本核文学受主题表达的需要其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呈现出了不同的表征。首先,纪实与虚构在日本核文学的文本实践中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彼此衬托。其次,多种叙事视角的运用也使其具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效果。在历史书写与文学想象之间,日本核文学始终贯穿着一种悲悯情怀和批判意识,蕴藏在文本深处的人文价值与理性精神,使文本的内涵与深意得到了升华。
日本核文学;原爆文学;原发文学;叙事策略;历史书写
日本核文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文学中所出现的涉核题材的作品总称,主要包括原爆文学、原发文学(原子能发电题材文学)以及其他核题材的文学。从日本广岛和长崎在二战中遭遇原子弹爆炸之日起,以原爆文学为发端的日本核文学持续发展至今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涵盖小说、诗歌、戏剧、随笔、散文以及评论等多种文学样式,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整个战后文学史,是日本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核文学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并产生强大的社会修辞效果,不仅在于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悲悯情怀和批判意识,而且跟它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是分不开的。从技术层面看,它没有精心编织的故事,没有曲折跌宕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粉饰的文字,但其震撼力却直击读者内心,引发共鸣。日本核文学从原爆文学发展到原发文学,其主题意蕴在政治、文化、社会等综合语境的制约下表现出了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受作品主题表达的影响,其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也呈现出了不同的表征。本文将立足日本核文学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依托叙事学理论,对日本核文学的叙事策略进行考察,进而明晰核文学独特的叙事效果和文本意蕴。
一、纪实与虚构的叙事方式
首先,在叙事方式上,纪实与虚构在日本核文学的文本实践中各有侧重,并相互补充,彼此衬托。原爆文学作为暴力和创伤的历史书写,它的叙事素材直接源于二战中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这一历史事件。叙述的焦点主要聚焦在核爆对被爆者身心造成的深远伤害,偏重于个人体验和历史史料的纪实,具有较为浓厚的现实主义气息。早期的原爆文学更是如此,与其说它是小说倒不如说是作家们重拾记忆片段的历史书写。如原民喜1947年发表在《三田文学》上,翌年荣获水上龙太郎奖的《夏之花》,就是作者在避难所八幡村以记录原子弹投下惨状的笔记为蓝本,讲述了广岛被爆后自己在避难途中所见所闻的种种惨象。还有广岛出身的大田洋子,基于自身的被爆体验,在避难的郊外农村遭受脱发、痢疾等肉体的折磨下撰写的《尸横遍街》,全篇由30个章节组成,每一节独立成章,记录了原爆瞬间那万劫不复的毁灭景象以及之后数月人们劫后求生的人间地狱之惨状。此外,20世纪70年代新生代原爆作家林京子的许多作品,与早期的这种叙事模式也一脉相承。曾荣获芥川奖的处女作《祭场》就是作者在被爆之后30年基于自身的被爆体验,详细切实地记录被爆之时及之后的各种细节。《钻石玻璃》前后共由12个短篇连载组成,这些故事真实、具体、细节生动。在《如无》中写道:“她是个被爆者。所以她想尽可能忠实地讲述8月9日。正因为如此,她一直抑制着自己多余的情感。”*本文所出现的《日本原爆文学》中文译文均为笔者自译,下同。[1]278从8月9日到战后30年,她在作品里呈现的不仅仅是记忆的一种搜寻,而且还不断地进行由表及里的思索。
虽然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可能产生偏差,但在面对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这一历史惨剧时,诸多作品在忠实史实即真实性层面上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跟真实作者的身份息息相关,源自于创作主体的心理情感逻辑。“真实作者虽然处于创作过程之外,但一个人的背景、经历等往往会影响个人的创作。”[2]75在原爆文学中,真实作者身份可以分为体验者和非体验者。其中,体验者又可分为老一辈原爆亲历者和新生代原爆亲历者。
原民喜、大田洋子、峠三吉等老一辈原爆文学家,作为原爆的亲历者、幸存者和见证人,直接的原爆体验以及相关阅历的丰厚基础,是他们真实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首要前提。原民喜在《夏之花》中写道:“非得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不可,我在心里喃喃自语道。”[3]大田洋子在《尸横遍街》完整版的序言中说:“背负着死亡的阴影,一定要赶在死亡来临之前完成创作。”[4]12并坦言自己的所见所闻迟早必须得写出来,“因为这是看到这些的作家的责任。”[4]60由此可见,对于那些曾亲历过原爆这场劫难的作家来说,他们无法规避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内心震撼。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必须真实地记录这一历史事件。因此,他们在这样一种叙述语境下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为历史、时代和正义代言的重任。“广岛的不幸是无法回避历史性意义的,每当我念及如此便觉得,即便是小说也无法容忍虚构和怠慢,应该在不随意破坏原型、保证其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创作。”[4]12大田洋子应该是道出了老一辈原爆作家的心声。
无论是广岛、长崎的原爆,还是1954年的比基尼被爆事件,对日本人来说都是惨痛的血的教训,肩负时代使命的作家们带着灵与肉的疼痛对原爆、核以及战争进行着独到的思索。在这种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亲历过原爆的一些少男少女,作为新生代的体验者,其创作虽不再纯粹着力于灾难场景的还原,但借助自己的记忆和感知来书写原爆体验成为其重要的叙事策略。他们以此关注被爆者战后的生存苦痛与艰辛世界,同时也抒写现代性侵袭下的各种畸变。诸如林京子的《祭场》《钻石玻璃》《如无》等一些作品,虽然都基于30年前的被爆体验,但作者显然更侧重于拷问作为一个被爆者是如何在战后有尊严地存活下去。既不故意宣扬,也没有刻意回避,只是关注被爆者的种种伤痛、困境和尊严,注重在各种内在关系中去展现人的精神状态,从而使作品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内涵。
不管是老一辈原爆亲历者作家,还是新生代原爆亲历者作家,原爆体验是他们心理情感逻辑的共同出发点。他们对那场灾难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从而达成创作理念上的共识,由此构筑了特定社会政治语境中的创作主体意识和文本模式,其作品建构了民族甚至世界的集体记忆。但恰恰这种心理情感的抒发又成为原爆文学自身的一种局限。尤其在早期的原爆小说中,作家对原爆场景的纪实及情感抒发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对情节跌宕起伏的把控,致使作品的情节性远不如传统小说。因为历史事件的特殊性质,在记录和还原层面上反复书写,如同德国本哈德·施林克曾论述大屠杀书写 “把人们的想象力束缚起来,逐渐使之僵化老套”[5]一样,原爆书写也逐渐表现出一种麻木不仁。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也曾指出大屠杀书写被“简化”十分危险,同理在见证者个人的、微观的、反复的叙述中,原爆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简化成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而这种简化同样也是十分 “危险的”[6]。日本评论家小田切秀雄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1955年在《原子力与文学》中指出:“原子力问题对现代人而言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其规模之大之复杂,涉及层面之多之深刻,自比基尼事件以来已急速明朗化。对此日本文学仅仅从现有的原爆文学展开努力是否就可以了?是否可以仅仅停留在只有受灾地有过直接体验的作家才能写作的格局?原子力与文学的关系是否有必要且是否可能在传统原爆文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7]
小田切秀雄的时代呼声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响应。确切地说日美安保条约生效后,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北的日本渐渐恢复其独立国家主权,随着从美国舆论管制中解放出来,作家的话语权开始得到尊重。一批没有亲历过原爆的作家开始以原爆或被爆为题材进行创作。这些非体验者作家以旁观者和审视者的身份,对原爆的历史叙事主要依赖史料和想象,自主地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原爆及核认知。他们的叙事重心不再是单纯地还原历史真实,而是将反思和追问融入到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更多地展现对人类命运及人性这一恒大命题的追踪与思考,“历史”在文学想象中呈现出新的面貌。
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井上光晴、小田实、堀田善卫以及饭田桃为代表的作家,他们的重要代表作《大地的群像》、《HIROSHIMA》(广岛)、《审判》以及《美国的英雄》等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以往直接以原爆为主题的作品不同,纪实色彩不像早期的原爆小说那么浓厚,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是在故事情节中援用原爆素材,即原爆题材的二次运用特征较为明显。为了主题的表达需要,这些作品在叙事技巧上更侧重于宏观的架构,厚实的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如井伏鳟二的《黑雨》,在结构上采取日记体小说的形式,通过侄女矢须子和闲间重松在原子弹爆炸前后写的日记相互印证,强化真实可信感,从而凸显被爆者遭受歧视的主题。小田实的《HIROSHIMA》主要人物设定为美国人、朝鲜人、日裔美国人,向广岛投放原子弹的美国士兵是加害者的同时作为被爆者也是被害者,而作为被害者的广岛人对朝鲜人以及日裔后代进行歧视的同时加害者形象也跃然纸上,作者以广岛原爆事件为背景,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和情节的设定,冷静地思索加害与被害问题使原爆文学的主题得以升华。
此外,大江健三郎以随笔《广岛札记》为反核起点,此后的《治疗塔》《洪水淹没我的灵魂》《核时代森林的隐遁者》等一系列核文学作品,都更加体现了文本的重要属性——虚构性。《治疗塔》及其续篇《治疗塔行星》甚至以浓厚的科幻色彩呈现。作者借助合理的想象和虚构直击时代命脉,把广岛体验国民化,并把这种“屈辱”附上普世价值从而达到世界化的目的,强烈呼吁废除核武器实现世界和平,向人们提出如何面对核时代这一重大课题。
如果说一些非体验者作家以原爆为写作素材从而去揭露社会问题、反思历史以及关注人类命运等现实问题,那么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以及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大背景下催生的日本核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即原发文学(原子能发电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井上光晴的纯文学《钚之秋》《西海原子力发电站》《输送》自不必说,一些大众文学如生田直親的《原发·日本灭绝》、高嶋哲夫的《原发危机》、山川元的《东京原发》等作品,纷纷以原子能发电为题材,具有一定的科幻性质,寓言色彩浓厚。在巨大历史灾难带来的重创以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道德维度全面崩溃等现实困境中,预言想象的转化力量是原发作家及其作品的意义之所在。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8]作品的本体意义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复制或镜像反映,而是再现与创作,实现其一定的教诲功能。所以原发文学的现实性是建立在作者合理的想象之上,在虚构中完成了对现实的关照,从而全方位展示了作家们对核的多元化思考。它集娱乐性和警示性于一身,虽说只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先知预言,但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故使原发小说从虚构走向了现实。
美国文学理论家蒙特洛斯认为:“文本与历史之间是文史互相交错的,包括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这种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开启了文学与历史的对话,认为历史事实与文学文本再现的不是客体与主体、被动与主动的关系,而呈现出交叉性和重叠性。”[9]无论是原爆文学,还是原发文学,都是日本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文本与历史语境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意识。面对原子弹爆炸这一史实,作家们勇敢地站出来为受害者发声,用文学手段来反对战争、抗衡歧视等社会问题,使历史事实与文本进行平等地对话,使历史转化成文本,即实现“历史文本化”,体现了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这一论点。张荣翼认为,“历史的文本化可以理解为历史是通过文本记录来得以显示。文本成为历史事实的构成要件,没有文本就没有我们所知晓的历史”,同时他还指出:“反过来,又有文本的历史化这样一个层面,它表明,本身并非事实的文本,在历史过程中被作为事实来看待,而这种看待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和后果,形成了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作为日本核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原发文学,对核电的破坏性充满想象地进行描摹,触目惊心的原发泄露事故在文本中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预演。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故打破了科学万能主义神话,也使日本核文学实现了向文本事实化和历史化的重要转变。同时也使“去核化”运动从文本走向街头,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在历史与想象之间、在纪实和虚构之间、生活和艺术之间,日本核文学通过历史真实与虚构想象的平衡与完美结合,实现其书写历史并反思时代精神的价值。作家们有的通过记忆书写来再现历史的真实,通过反映重大的核历史事件来呈现历史,强调这些历史事件带给普通人的痛楚与伤害。有的则借助自己的文学想象来表现历史的真实,充分利用文学的虚构性来虚拟了一个令读者深信不疑的历史空间,从而使得原本虚构的情节承载核历史的真实,实现文学书写的历史性,从中巧妙地言说和彰显作者的主观感受与体验。
二、多种叙事视角的运用
日本核文学从原爆文学发展到原发文学,除了真实作者有无直接的原爆体验与叙事方式呈现出不同的文本特征和文本深意之外,多种叙事视角的运用也是其一大特色。众所周知,叙事视角在小说叙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决定小说的叙事结构,而且有利于叙述者传情达意。通过对日本核文学的叙事视角的审视,笔者发现作家们或善于采取第一人称叙事,或善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复合式叙事。这些叙事视角有利于增强小说的叙事艺术和叙事内涵,更是日本核文学在历史书写和文学想象叙事策略下的叙事需求。
首先,原爆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基本都是从第一人称视角介入叙事。无论是早期如原民喜的《夏之花》《来自废墟》、大田洋子的《尸横遍街》,还是后期林京子等作家原爆题材作品,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作为亲历过原爆的体验型作家,往往以幸存者的视角和方式,向读者讲述他们人生中的那场劫难,作品中“我”既是叙述者,通常也是故事中的人物。“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时,拥有第一人称内视角与外视角的双重叙述。一方面用一种经验内视角,此时的“我”作为原爆事件的受害者,跟众多幸存者一样正在经历着原子弹投下时刻的错愕、随后的逃生以及原爆后遗症的折磨,以及逃亡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另一方面穿插使用外视角,“我”置身当下,对过去的记忆进行梳理时不时展现现时的感受,对原爆事件本身、对战争的认知、对周围的人或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第一人称回顾外视角与主人公体验内视角的双重叙述,是原爆文学很多作品惯用的叙事策略之一。原民喜的《夏之花》自不必说,林京子的《同学会》《钻石玻璃》也拥有以上的传统特质。只不过叙事时间的时距有所差异。老一辈原爆亲历者作家们一般是在原爆事件事隔三五年之后进行的回顾性叙事。而林京子、竹西宽子等新生代的原爆亲历者作家们是在事隔三四十年后的原爆记忆书写。如林京子的《钻石玻璃》,在处理第一人称的回顾性视角时把叙事时间设定在事隔原爆事件30年之后(原爆三十周年忌)的现在立场,通过对同学大木、原、西田等人的现状讲述,向读者展现了被爆者的战后艰难人生,以及时代造就的非被爆者的错位人生。而在向读者呈现她们当年所经历的原爆时自然使用经验性内视角,这跟上述的前辈作家在叙事策略的运用上毫无二致。如果要说不同,除了上面提到的叙事时距的差异外,就是前者在原爆场景呈现时更为具体,而后者更加着力于被爆者30年来艰难人生的书写。
正如徐岱所言:“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最大好处,首先在于真实感强。这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有某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11],对于这些被爆作家而言,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契合。众所周知,隐含作者是叙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2]7。因为第一人称叙事既具有回溯性质,也有当时在场性质,虽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叙事会带来不同的修辞效果,但是无疑这种“我”的视角与原爆小说的历史叙事是相协调的,致使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具有诸多的相似性。
但也不乏原爆文学在求得第一人称叙述中的真实现场感之时,也不放弃第三人称叙事所特有的理性和超脱,即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叙述模式。如林京子的《如无》,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女子”交替出现。“我”以一种原爆亲历者的身份出现在35年前那场事件的回忆叙事中,作为人物在故事层运作,放弃目前的观察角度,采用当初处于原爆事件时的眼光来聚焦,从自己当时的角度和立场来参与和观察往事,真实的在场感使读者可以感同身受。而第三人称的“女子”却处于往事之外,是当下时间下事件的参与者,以一种外视角作为叙事者在话语层运作,读者聚焦于她讲述的往事以及她对往事的评价。“女子希望自己是八月九日的叙述者。她是个被爆者。所以她希望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忠实地讲述八月九日的事。为此,她抑制了自己其他多余的情感。”[1]278显然作者是为了在运用第三人称叙述时,寻求的是一种置身事外的客观感觉,刻意回避了作为故事层面人物内视角 “往往比较主观,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而“故事外叙述者的眼光往往较为冷静、客观、可靠”[12]。也就是说,《如无》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融合,它保证了从始至终的现场感和超脱性。
当然,日本核文学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其叙事方式也并没有被模式化。后期一些没有亲历过原爆的作家作品,如大江健三郎的一系列核文学,以及原发文学在人称设定和视角选定上显示出了相对的自由,这与核文学发展到后期不再着力于历史的还原而是表现出核时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大时代主题是息息相关的。
在第一人称双重叙事和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叙述模式中,日本核文学在叙事时间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无论是原爆小说还是原发小说在叙事中都明确了现在的时间立场,通常现在是回忆或故事展开的起点,过去和未来都是通过现在得以呈现的。但原爆小说在时间维度上通常首先指向过去。过去是创伤的源发和痛苦的记忆,各种亲历讲述形成了史诗记忆,构建了灾难历史的集体记忆。正是对过去的记录与对事件的还原,使得那场浩劫转化成一个“现时在场”,历史记忆才不会被遮蔽和被遗忘。
具体而言,在原爆文学中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是创伤的源发和起点,8月15日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意味着二战的结束,但对被爆者来说灾难才刚刚开始。因为战后不久被爆地开始出现瘢痕疙瘩等各种原爆病症,并有大批被爆者因此相继离世。正如大田洋子在《尸横遍街》中所言“战争的恐怖不是在战争之时而是在战争之后才真正来袭”,“原子病的症候之一就是让人呈现出一幅无欲无求的表情。但我觉得这种表情并不是罹患原子病而出现的,而是自8月6日以来就一直是这个表情”[4]100。“一般媒体都会在8月6日这一天对原子弹爆炸进行旧事重提,但对我们而言,每一天都是八月六日”[4]294。大田样子认为8月6日的原子弹爆炸体验,无疑可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流刑事件相匹敌。不仅如此,林京子也曾坦言,经历了8月9日的人生就是用一本被爆者手册构筑的人生。8月9日不仅在自己的生命中挥之不去,而且还在儿子的生命中打下印记。过去的痛苦带来了现在的创伤和不安,这种不安像影子一样还将与未来的生活相随,在与原爆后遗症抗争的同时未来的希望指向也蒙上了一层阴影。未来作为创伤消弭和希望指向,在原爆叙事中呈现出惶恐不安的沉重感。
原爆文学中所呈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被爆者的一部人生写真集。发展到后期的原发文学,尤其是占据大量市场份额的大众文学,跟绝大多数科幻小说一样,通过原子能发电泄漏事故导致东京(日本)或地球毁灭这样的一些结局幻想,对未来进行警示。置身核电站不断扩建以及核武器不停研制的时代大背景下,基于原爆文学的历史经验和作家们自身的合理想象,原发小说在时间处理上通常由现在直接指向未来,通过对未来毁灭性结局的幻想来实现危机预警。这跟纪实与虚构各有侧重的叙事策略在文本传统上保持了一致。
三、独特的叙事效果
日本核文学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文本内涵,受主题表达所需其叙事策略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叙事策略的灵活运用使日本核文学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效果。即始终贯穿着一种悲悯情怀和批判意识,以及蕴藏在文本深处的人文价值与理性精神,使文本的内涵与深意得到了升华,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着过去的苦难主题,而且对当下也有强大的借鉴作用,让人们在反观历史和展望未来的时候拥有一定的理性高度,从而获得人类精神和人性的纵深自省。
首先,历史书写与创伤记忆是日本核文学的重大历史命题,持续拷问着日本乃至世界。原爆文学反映重大历史灾难的主题和时代精神首先是从再现原子弹爆炸这一历史惨剧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入手的。原爆不仅毁灭了城市和家园,也摧毁了人的肉体和意志。通过记忆的言说和历史的证言,广岛和长崎人间地狱之惨状铭刻在历史里程碑上。此外,暴露受害者肉体和心灵的创伤,并以“伤痕”控诉灾难,追究直接可见的历史罪人是原爆文学最直观的表达。跟个人主观意志无关,原爆以暴力形式直接侵入私人生活,其创伤书写既包含对城市瞬间夷为废墟的震惊,也有对受害者肉体和精神双重伤害的痛诉与怜悯。原爆文学在全面展示原子弹爆炸给人们身心带来难以愈合的伤害的暴力书写背后,对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的暴力成因进行思考是一种必然。站在个体情感立场上对美国投掷原子弹这种政治暴行进行控诉可以说是创伤记忆的间接表达。
然而,在历史书写和创伤记忆的主题呈现过程中文本却呈现出悖论与统一的辩证关系。原爆文学一方面希望通过记忆的加强来抵抗风化,以期以史为鉴;另一方面倡导遗忘痛苦体验来实现创伤治愈。原爆文学本来就是以广岛和长崎被爆为题材的文学,尤其是早期的那些偏重纪实的文本,本身就是一种记忆。作为释放民族情感和集体受害情结的有效渠道,原爆文学的文学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控诉被害,唤起受害者群体甚至整个民族的共鸣,因为它所记载的是集体的创伤和记忆。虽然这种记录和描述跟叙事者的身份、读者的认知以及时代生态背景等理性建构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至少它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逻辑,为后人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但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对于被爆者来说这种创伤体验很想被封存,即选择性的主动遗忘。大田洋子借《暴露的时间》里的主人公之口道出人们内心的纠结。“只要有机会,我就很想倾诉。但只要我一倾诉,这个城市的人都表现出一副很厌烦的样子,那表情似乎在说我好不容易在试图忘记这些事情。”[4]169人们之所以表现出一幅很厌烦的样子,就是不想伤心往事旧事重提,但这种试图遗忘并不是真的遗忘,仍旧潜藏在记忆深处。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本身也会风化,即自发性的被动风化。就像林京子《如无》的主人公作为8月9日的受害者,永远无法忘怀这一天,但她却感到了记忆风化的无力。“她之所以决定言说,是因为想尽力抵抗8月9日的风化,但讽刺的是,说得越多反而8月9日风化得越快。”[1]319时隔多年置身爆炸中心地的“她”,却看到祭奠仪式的8月9日,爆竹声声,气球空中飞舞,祭祀成为一种轻浮骚乱的仪式。两个8月9日的违和感,完全是异质的东西。一方面是风化,另一方面是捏造的热闹。这种变味儿的祭奠仪式与捏造的气氛,与厚重的历史格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时间会使人们遗忘,也会渐渐抚平创伤。
其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变革的不断进展,日本核文学有了历史的反思深度。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作品不再把重心置于个人创伤的倾诉上,而是从客观立场上分析这场灾难产生的历史原因,思考的重心开始由外到内,由过去到未来。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 而开始反省整个民族在这场历史浩劫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难能可贵的是日本核文学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别,对践踏人类尊严的种种暴行进行严厉地批判,从中寻求人类的普世价值与普遍道义。这是原爆文学痛定思痛后的病蚌成珠。堀田善卫的《审判》突破以往原爆文学的固有视角——国内视点或个人体验的宣泄,立足国际视野对原爆这场灾难的实质进行思索和反省。饭田桃的《美国的英雄》把主人公设定在美国内部,通过书简“广岛 我的罪与罚”的来往,触碰到道德根本问题的核心之处。如果说《审判》和《美国的英雄》是一种横向的宏观国际视野,那么井上光晴的《大地的群像》则是纵向的国内视野,揭露了人类的丑恶、悲惨和愚蠢。高高桥和巳的《忧郁的党派》与《大地的群像》在笔致上一脉相通,对人类的恶与欲望发出了绝望的呼喊。长冈弘芳对这一时期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一时期“毫无疑问是原爆文学史上新的收获,既不循规蹈矩,又不像前期那么空洞。而且也彻底肃清了初期由于报道管制在思想和文学中潜在的原爆禁忌,把原爆主题引导到现代文学大道的光明中来了”[13]。
从原爆文学到原发文学,虽然它们能够超越民族和国界站在人类的角度上对核反人类的本质进行控诉,但日本核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总体倾向中, 民族的忏悔意识和自省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诚然,原爆事件的直接受害人对暴力和灭绝人性的战争进行谴责,具有其必要性与正义性。但是绝大多数作品过分强调本民族受害者的角色,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民族在历史浩劫中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管怎么说,作为核时代的见证话语,原爆文学记录着时代的血和泪,甚至它还超越民族和国界站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历史高度警示后人,让世人铭刻历史悲剧不可重演,这也是原爆文学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另一种重要意义。
马克思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4]诚然,原爆是日本人的问题,但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因为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它是文明社会的畸形产物。日本核文学有机地将作家的情感体验与理性思考融入于文本中,树立了人类灾难书写的文学典范。它在呈现主题的同时满足了大众情感宣泄的需要,具备了心理疗伤和警示后世的功能,尤其其鲜明的教诲作用使之拥有了与众不同的当代文学特质与意义。另一方面,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全球大背景下很多国家仍在积极开发核资源,甚至有一些国家高举自卫的旗帜竞相实施核试验并研发核武器,人类步入核时代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日本核文学不仅对日本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对核思考的思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此意义上,作为拥有并正在研究使用核能技术的中国,日本核文学的教诲价值不仅对于我国自身核能源的健康发展和安全利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我国当代文学中的核书写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 林京子.日本原爆文学:3 [M].东京:ほるぷ出版社,1983.
[2]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原民喜.日本原爆文学:1[M].东京:ほるぷ出版社,1983:16.
[4]大田洋子.日本原爆文学:2 [M].东京:ほるぷ出版社,1983.
[5]哈德·施林克.朗读者[M].钱定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41.
[6]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67.
[7]小田切秀雄.原子力と文学[M].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5:44.
[8]亚里士多德.诗学[M]. 罗念生,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1.
[9]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82.
[10]张荣翼.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文学史考察的视点问题[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47-53.
[11]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6.
[1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7.
[13]长岗弘芳.原爆文学史[M]. 名古屋:风媒社,1973:136.
[1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9.
[责任编辑:吴晓珉]
Writing of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in Literature:On Narrative Strategy of Japanese Nuclear Literature
LIU Xia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Japanese nuclear literature refers to the works concerning with theme of nuclear in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atomic bomb literature to nuclear power plant literature, narrative styles and strategies of Japanese nuclear literature display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due to the needs of theme expression. Firstly, document and fiction are highlighted differently, but mutually complementary and supportive, in the textual practice of Japanese nuclear literature. Secondly, the employment of multiple angles of narrative fosters a unique narrative effect. Between writing of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in literature, sympathetic emotion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lways run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Japanese nuclear literature. And humanistic value and rational spirit implied deeply in the text have sublimed the connotation and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
Japanese nuclear literature; atomic bomb literature; nuclear power plant literature; narrative strategy; writing of history
2016-12-20
湖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7Q015);湖北大学人文社科基金(040-098334)
刘霞(1982-),女,湖北十堰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研究。
I106.4
A
1004-1710(2017)03-01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