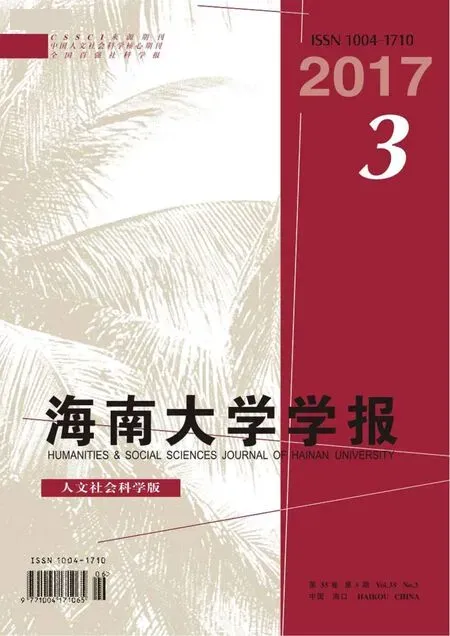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历史叙事的方式与向度
2017-02-24侯玲宽
侯玲宽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历史叙事的方式与向度
侯玲宽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面对20世纪历史的创伤记忆,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以一种非亲历性叙事的他者视角,重新审视了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探寻了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精神流变,也反思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政治的规约下被同构的命运悲剧。对知识分子复杂而深邃的人性的深入揭示是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对20世纪8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苦难书写与情感书写的超越,作家们也由此对20世纪历史的沉重与混沌进行了新时代语境下的体认与重构,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的理性书写特征因而更加突显。
知识分子小说;历史叙事;革命;政治;人性
随着20世纪历史的渐渐远去和当事人的慢慢逝去,新世纪*本文中的“新世纪”即21世纪,是相对于刚刚逝去的20世纪而言的。作家该如何重新讲述这段沉重的民族记忆?作家们在完成了代际更替的同时,对历史的认知又进行了何种程度的推进?从精神世界最为复杂的知识分子楔入,新世纪作家对20世纪历史的混沌与革命政治的残酷进行了新时代语境下的体认与重构,既审视了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复杂而深邃的人性。相对新时期*“新时期”即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段历史时期。的创作而言,无论是对历史叙事方式的革新,还是对历史与知识分子人性的深度洞察,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都显现出了其成熟性与超越性。
一、他者视角:“非亲历性”叙事
对中华民族而言,整个20世纪就是一个充满创伤的世纪。殖民入侵、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反右”、“文革”等都构成了中华民族最惨痛的历史记忆。新时期以来,对这些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遭际进行表现与反思的作品不断问世,作家们均以真切的亲历性体验,书写了特定历史阶段个人和国家的创伤记忆。对刚刚逝去不久的历史创伤与民族苦难进行审视与反思,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资源与文化资源,成为30年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世纪之交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批表现这一主题的力作,但与新时期“复出”的右派作家的亲历性叙事不同,新世纪的创作者采取的是对历史体验的非亲历性叙事。
非亲历性叙事是与亲历性叙事相对而言的一种叙事姿态。“亲历性”意味着在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中,作者曾主动或被动地亲身参与了这一进程,故而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叙述或书写的时候,作者能以当事人的身份还原历史现场,力求逼真地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与人情事态,尽管作者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偶尔加入了一些虚构的成分,但这些虚构因为是合情合理的,更由于作者亲身经历的缘故,读者反而信以为真,无论纪实还是虚构都增强了作品的历史现场感与真实感,这是亲历性叙事所具有的独特效果。在亲历性叙事中,主人公往往就是叙述者,他控制着叙述的节奏、频率和方向,作者虽不完全等同于主人公,但主人公身上却深深打上了作者的烙印,让读者在潜意识中将两者视为一体。“非亲历性”是指作者在对某一历史时期进行叙事的时候,历史对作者而言已成为无法跨越的过去,作者本人并没有参与这一历史进程,故而作者无法出现于历史事件之中,但为还原或凸显历史的本真性,作者特安排亲历过那一历史阶段的人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从而达到亲历性的效果,但在故事的主人公之外往往还有一个叙述者站在故事之外实际操纵着整个文本的叙事,从而也以一个“他者”的视角客观冷静地观看主人公和整个历史事件。叙述者虽然在故事中处于次要位置,但在叙事功能上却有统领全局的能力。在非亲历性叙事中,作者也许无法真正抵达和还原某些历史真相,但他们都在以自己的艺术方式尽可能地逼近这一真相,并以此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裸露出深邃的人性与被遮蔽的真实。
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在面对历史的记忆时,之所以大多采取的是“非亲历性”叙事,从时间的推移来看,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有这种亲历性体验的作家只属于那一批受难者的右派作家,这批作家在二十多年后大多已丧失了创作能力,有的甚至已不在人世,在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一主题的书写与表达只能交给更年轻的作家来完成,他们也就不可能再有这种亲历性体验,他们的写作只能借助史料、采访等途径再加上艺术的虚构来完成,以后所有对这一历史创伤记忆的表现与审视都只能通过具有“他者”意味的非亲历性叙事来进行。但这种非亲历性叙事在新世纪小说中又是如何呈现的呢?我们不妨以《花腔》《父亲和她们》《陆犯焉识》等几个典型的文本为视点,看向这种叙事内部。
《花腔》在叙事方式上采取的是多角度内聚焦叙述,葛任的故事是通过曾与其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三个亲历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忆讲述出来的,但讲述者因身份不同以及讲述的时间不同所讲述出来的故事在关键处也大相径庭,他们的讲述也均呈现出了一些观念上的错误,葛任的故事由此成了“罗生门”,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叙事方式。葛任的故事被讲述多次,历史的真相就在这种“被讲述”中被永远地淹没了,只剩下一个供人任意演说的空壳。三个讲述者的回忆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部分建构起了葛任故事的完整性,相互交叉的部分所显现出的迥异处则展现了历史的诡异性,这才是让人们质疑和深思之处。在三个讲述者以自己的视角“看”葛任的同时,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叙述者——葛任的后人“我”这个非亲历者——在“看”三个讲述者及葛任的一生,也看整个历史的真假是非。另外,文本还设立了正本和副本两个相互照应的文本,正本是三个讲述人所讲述的葛任的历史,副本则是有文字记载的客观资料,包括人物、回忆录、谈话、史料等,也有历史的细枝末节,副本对正本的关键内容做出了必要的阐释。如此,故事、历史、史料(事实)形成了相互印证、去伪的关系,而历史的真相则交给读者去辨别,让读者去琢磨,去反思。《父亲和她们》中父亲的故事同样是由三个亲历者讲述而来的,这种历史的记忆以录音带的方式保留了下来,文本采取的是多重第一人称叙事,即多个当事人的直接叙述与后代人的间接叙事交互杂糅,娘、母亲、父亲的回忆构成了各自独立的叙述主体,复调叙述形成了多重叙述声音,叙事人的不断变换给人们的阅读经验带来了强烈冲击。而作为非亲历者的“我”则是以三个亲历者的儿子身份出现的,他不仅是资料的收集者,更是超文本叙述者,他以高屋建瓴的姿态统筹着所有的叙事,限知叙事的不足则由“录音带”的方式来弥补,历史的空白与故事的空白也由此得到了有效填补,父亲完整的一生由此呈现于读者面前,父亲与三位女性的爱情史暗含了家族命运的兴衰沉浮,折射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作者由此将笔触伸到了历史的纵深处,文本通过这种方式再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生的曲折与磨难,也思考了他们为什么会在几十年后不但回归了现实和平庸,而且变成了奴性十足的卫道者,并将这种思考指向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在《陆犯焉识》中,陆焉识的一生在文本层面上也不是由陆焉识直接叙述的,而是陆焉识把自己的一生通过回忆录与书信集的形式交给了他的孙女“我”,陆焉识的故事同样也是在“我”整理与加工之后才与读者见面的,文本采用时空交错的方式由两条线索编织而成,一条叙述陆焉识劳改服刑的生活,一条叙述陆焉识劳改服刑前的人生历程,两条线索根据叙述的需要不断交叉,将陆焉识的现在和过去进行对比,展现了知识分子陆焉识在20世纪中国乖谬的悲剧性命运,非亲历性限知叙事的不足则由陆焉识和“我”共同誊写的回忆录和书信集来弥补,历史的空白与故事的空白同样由此得到填补。这样一种隔代性叙述更具温情也更加客观,文本从一个和陆焉识有血缘关系的“他者”视角,由亲情的疏离来审视政治对人性的挤压、亲情与人情的淡漠,以及陆焉识更加苍凉的人生。
在这些非亲历性叙事的文本中,作者均采取了一种很巧妙很智慧的叙事策略,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与亲述的方式产生了亲历性的效果,这种叙事既能让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真切感,又能站于文本之外冷静客观地审视故事中的人物、事件以及所描述的历史本身,从而使文本显得颇有意味。这种由当事人的直接叙述与后代人的间接叙述交互杂糅的叙事方式,一方面增强了真切的历史现场感,另一方面从历史的高度对主人公一生的悲剧性命运进行更加客观冷静的反思,从而对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精神困境进行深度挖掘与审视。
同时,非亲历性叙事还有效地祛除了亲历性叙事的遮蔽迷雾。亲历性叙事是一种主观叙述大于客观呈现的叙事,历史的真相因人因境在主观叙述中难免走向偏差。尤其这些“反右”运动的受难者,他们大都历经磨难和危险而幸存,因而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在公众心目中都是被当成“文化英雄”看待的,那种惨痛的亲历性体验在英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容易变成一种“青春无悔”的豪情。他们在创作时,也往往于潜意识中进行着不自觉的自我矫饰与自我美化,有时甚至演化成了成功者的怀旧与迷恋,以及对昔日苦难的“辉煌”构造,他们“最后都在讲述一个无法论证却只须相信的、抽象的‘历史神话’”[1]。这种亲历性体验有时也因个体的切身之痛而无意识地遮蔽了历史的共性体验,遮蔽了迥异于己的其他苦难体验,甚至由于作家几乎等同于小说的主人公的缘故,也会导致作品对主人公的精神与性格中的负面因素进行有意遮蔽,从而限制了作者与作品获取更阔达的历史视野,限制了对历史、事件、人物更深刻的省察与反思,这是在个人与时代的双重作用下无法克服的局限。在亲历性叙事中,由于没有参照系,我们的阅读往往被叙述者的经历、思想、情感、节奏所控制,从而无法感知到这种遮蔽,而当事人对事实的遮蔽问题在非亲历性叙事的作品中却被呈现了出来。譬如,在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中,叔叔过去的平庸、卑贱、屈辱、堕落,经过他自己的改编、加工、创造后,反而成为他后来自我炫耀的资本,并以精神导师的姿态赢得了鲜花和掌声,还有女孩子的青睐以致献身,达到了一种极致的荒诞。但这些看似非常辉煌的故事在经过叙述者的拆解之后,那些被神圣和高尚遮蔽的虚伪假象,那种虚妄的个人理想主义信念和时代理想主义精神却显现出了一个时代的荒芜和丑陋,作者也由此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反省。同样,在《父亲和她们》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那就是马文昌后来在给青年学子作报告时,经常把他的瘸腿作为朝鲜战场留下的创伤展示给学生们看,而他真正的战争创伤却是肚皮上留下的伤疤而不是腿伤,因不方便掀起衣服给众人展示肚子上的伤疤,于是瘸腿被马文昌偷梁换柱代替了肚子上的伤疤,而他瘸腿的真正原因,却是当年因为饥饿在肖王集偷牛料被人毒打所致,他在肖王集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时遭受的异常耻辱在他给学生的讲述中,却变成了乡亲们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他也总是满怀激情地讲述一些不存在的感人情节使听众热泪盈眶,讲得多了恐怕连马文昌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真实的历史在这里遭到严重改写。马文昌篡改历史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自我英雄形象的塑造只能依靠光荣的历史而不能有屈辱的过去,二是经历了太多的历史教训已不敢说出历史的真相。其实,马文昌和叔叔一样,他们都在用这种遮蔽完成对过去的自我救赎。在亲历性叙事中,人们得到的是一个英雄形象,被蒙蔽的是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在非亲历性叙事中,人们失去了一位英雄,却看清了历史的真相,看到了一个悲剧,并让大家反思这一悲剧。
亲历性叙事多以切近生活的原色展现了那些苦难时代人的命运,尤其是知识分子灵与肉的磨砺,这之中既有焦虑与恐慌,也有愤怒与悲哀,同时他们也在令人震颤的苦难中努力挖掘理性的光辉与理想的亮色,在坎坷而沉痛的人生感悟中,表现出了一种饱经忧患而洞察世态人情的人生姿态,他们的作品也时时透出一种孤独、悲怆、苍凉、沉郁的格调,这种基于真切的生存体验而建构的文学世界表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深度思考,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沉痛异常的历史创伤记忆。亲历性叙事在个人苦难经验与民族深重灾难之间建立的普遍联系,使个人的苦难具有了超越的意义,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执著信仰与不屈不挠的人性力量的礼赞,也体现了他们构建知识分子神话的努力。非亲历性叙事因缺少了一种真切的体验与切肤之痛,也许不会像亲历性叙事那样轻易打动读者的心灵,但他们追求的不再是历史场景的绝对真实,而是一种历史精神的真实和人物心灵的真实。在此类文本中,非亲历者虽然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也不处于小说的核心位置,但在叙事学的意义上,他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所得知的所有历史事件、故事内容、人物行为都是经过这位非亲历者的转述才知晓的,也就是说亲历者所讲述的故事与历史,实际上都已经过非亲历者有意无意的筛选,因非亲历者处于历史的旋涡之外,他有效地避免了亲历者对自我的遮蔽问题,他对全部叙事的高度统摄更有助于作者思想与作品主题的表达,更能客观冷静地对历史进行全面地透视与反思,能保持足够的距离对历史与事实形成更加透彻的理性认知与批判,从这种意义来说,非亲历性叙事对历史创伤记忆的文学书写形成了一种深度推进。无论亲历性叙事还是非亲历性叙事,它们分别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写作方式,都有各自的特征与优势,但并无高下优劣之别。
二、个案审视:革命、政治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沉重主题,如南帆所言:“无论是一个政治风景亲历者刻骨铭心的经验,还是从中引申出来的理论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始终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不言而喻,这两个概念也是大半个世纪中国历史演变的关键词。”[2]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驱者,他们不仅代表着一种思想理性和文化方向,而且一直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翼。革命是古老的中国在内焦外困的历史境遇中最为根本的一个任务,它制约和影响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发展走向,“革命的发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3]在知识分子和革命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关键词:政治,“‘政治’是现代中国一切变革的核心和枢纽”[4]18。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中,政治成为一个统摄一切的词语,即使革命也是政治操控下的革命,革命和政治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最具内在统一性和复杂性的实践,而革命、政治、知识分子也将是很长时间内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三个关键词。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知识分子无疑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都曾根据自己的思想主张对现代民族国家进行过不同层面与方式的思考和设计。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生与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积极变革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5]五四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即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启蒙的核心是祛除国民精神的蒙昧、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因为只有“立人”才能“立国”,没有“人”的觉醒就没有现代国家的强大与崛起。“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前导与助力,不仅为政治革命培育和创造精神与人力的资源,而且能够使政治革命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形成统一的整体,既能保障革命的成果又能尽可能地纠正革命之偏。”[4]40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吸取了西方的科学、民主等现代理念,同时依然秉持着“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人理想和道德情怀,他们一方面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同时出于一种大局观念和革命胜利的需要,他们亦会服从革命和政治的领导,并积极地投入到“救亡”“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热潮中去,甚至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体现出了传统的道义精神、革命(民族)气节和社会责任感。但毕竟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伦理和革命政治逻辑是两种不同的符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和绝对服从、集体意识之间不免发生龃龉,这就会导致某个时期知识分子与革命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从而产生了文艺与政治的冲突。“当政治救亡崛起、国民革命高涨、阶级意识觉醒之后,作为坚持启蒙话语和社会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不能适应这种转变,必然有疏离社会、站立边缘的感觉,当这种边缘化倾向出现以后,也就随之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危机。”[6]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演进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悲剧性的逆转,他们不但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反而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连其成长道路都处于被规定性之中。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不但认同了在时代需求基础上的革命与政治意识,及其用残酷手段达到的同构,还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丧失了对革命与政治的适度审视与反省,知识分子对政治的顺从往往是以自我思想的丧失为代价,这就变成了一种“臣服”。革命与政治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无论什么样的革命,最后无不被控制在一种强大的政治之中,知识分子怀着一种现代理性参与革命进程和政治制度的建构,最终却被革命和政治同构,在这种必然的结局中也蕴含着最具反讽意味的悲剧。
新世纪以来,文学所承载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进一步弱化和消解,尤其是“革命历史小说”再也不用担负起图解政治、重构历史观念的沉重使命,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新世纪的小说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审视与观照,曾经被理性叙述意图所遮蔽和涂饰的真实历史景况得以浮出历史地表。新世纪小说重新审视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政治规约下被同构的命运,通过知识分子的复杂经历和苍凉人生,探寻了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精神流变,以及历史定论背后的沉重与混沌。
《花腔》将质疑直指历史本身,彰显了革命与政治控制下历史的扑朔迷离与不可信任。在葛任身上,看到了人们“真实”的空洞与诡异。葛任属于革命知识分子,作为马列学院编译室的译员,他从思想与立场上都是拥护革命、与革命保持高度一致的,但他又保持了自己思想的清醒和独立,对时事和问题不盲从,然而他遭遇的却是一段混沌的历史。“真实”在《花腔》中成了一个虚幻的概念,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葛任之死的原因及过程,他真实的思想及精神状况已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历史是模糊的,关键就在于它的细节,知识分子葛任在被讲述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一个符码,一个模糊的身影。围绕着葛任之死以及对葛任的寻找,葛任本身反而逐渐失去了重要价值,而葛任的利用价值才是各个政治集团的目的所在,这彰显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主导下的革命进程中的荒诞命运。在二里岗战斗中大难不死的葛任反而成为各政治集团的一块心病,侥幸活下来的葛任却又必须死去,葛任最终死去了,还是作为一个“民族英雄”被悼念的,“葛任死得早,也就死得巧,死到日本人手里,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田汗充满复杂情感的诉说隐隐显现了当事人对历史的无奈与酸楚。但葛任连死都是不自由的,死法都处于被安排之中,对葛任的死亡时间、地点以及是如何死亡的,水火不容的各政治集团却又于此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真正的死亡时间与方式随着知情人的相继去世将会永远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如作品所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7],1942年的二里岗战斗作为葛任死亡的时间和地点,已成为一个事实被人们当成常识,历史的真相就这样永远被深深掩藏于胜利者的定论之后,成为一种被言说的历史,知识分子也成了一面被宣扬的旗帜,葛任的存在也成为一个被动的能指,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真实历史在政治的规约下变得荒诞不经,人的命运成了文字记载的命运,历史也成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父亲和她们》最尖锐地突显了知识分子与革命和政治的纠结与碰撞,马文昌的一生不长,但却在他身上体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波诡云谲,也呈现了知识分子被逐渐同构的全过程。马文昌是一个接受了启蒙思想与抗日救亡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和林春如以自由和爱情的方式进入革命,但在革命队伍的发展过程中,马文昌逐渐丧失了当初强大的精神资源,政治的诱惑所产生的趋时心理和政治的高压所产生的恐惧心理,让马文昌经历了对革命和政治由不理解不适应到努力理解努力适应的过程,并在革命逻辑与政治威权的双重作用下,最终完全臣服于这种意识形态,变成了全然没有个性的同构体。马文昌后来一连串的婚姻都与爱情无关,仅仅是政治规约下的一种自保,在土改事件中他以扭曲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和革命忠诚,呈现了政治对人性的挤压和异化,以及政治对日常生活的颠覆和规约。在不断被改造的过程中,马文昌完全丧失了自由的意志,变得越来越平庸与奴性十足,继而形成了他犬儒主义式的精神世界。当马文昌的思想已完全被国家、革命、政治等意识形态与文化哲学所主宰时,他最初那种对自由的理解也演变成了革命政治意识中定义的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想怎么就怎么,自由是对现实的认识和适应。”[8]1可以说,这是马文昌综其一生的经验教训对自由最精辟的概括。而马文昌与林春如当初纯净的爱情观也已被实用价值取代,马文昌为了自保而回到肖兰芝身边度过余生,林春如为了权力而与大老方结合,这是他们用实际行动对爱情的最有力诠释,也是最令人压抑与震惊的蜕变。马文昌与林春如的前后变化既寄予着作者对革命与政治的批判性反思,也包含着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反思,如作者所言:“两个男女主人公综合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他们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们年轻时都曾满怀激情,意气风发,追求自由和梦想。几十年后,我发现他们不但回归了现实和平庸,而且变成了又一代奴性十足的卫道者。他们的人生,是不是就是中国人的缩影?”[8]封底同是卫道者,马文昌卫的是政治之道,林春如卫的是生活之道,田中禾于人性与革命、政治的冲突中透视了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人格异化与精神畸变。
《陆犯焉识》同样以个体知识分子的一生遭遇折射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变迁,陆焉识是一个在思想上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拒绝任何政党的拉拢,也不为任何政党作出承诺和服务,只为自由和学术而生存。在追求自由的方式上,陆焉识与马文昌不同,他没有选择奔向革命,而是选择了个人道路,他拒绝对任何政党的加盟,也把自己阻挡在了革命之外,他想以这种方式保证自己的绝对自由。可他与马文昌一样,都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自由,反而陷入一场场阴谋之中,“因为现代中国不间断的救亡压力和武装对立的政党政治的相互作用,知识分子的‘自由’已经变得非常可疑,很难有虚拟的或自我指认的‘第三种人’存身的空间。凡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实质上很少能获得西方自由知识分子那样的精神品格,而这种精神品格和追求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中也是行不通的。”[4]18-19陆焉识对知识分子精神和自由理想的坚守,在特定政治氛围中就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不谙世故和没有用场,这甚至导致了他在国共两个时期两次足以夺去他生命的牢狱之灾。陆焉识虽然没有像马文昌一样根据自己的一生总结出“自由”的定义,可他以同样的行为与屈从阐释了对自由的重新理解。陆焉识一生都未向政治靠拢,但政治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不但让他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以至肉体和精神遭受了严重摧残,这种影响还伴随着他的余生,影响着他的儿女们。回到上海后的陆焉识,在儿女与邻居的嫌弃中成了一个“多余人”,他的政治身份并未因他的释放而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从心底对政治产生的恐惧和对陆焉识的厌恶,让儿子冯子烨成为陆焉识的现实监管者,“身体归家”的陆焉识依然没有享有“精神归家”的自由。将他精神彻底摧毁的并不是婉喻的死去,也不是两条阵线对他的推脱,而是在巧克力事件中孩子们对他的本能拒绝和排斥,这让他明白在一代代后人的眼中他始终是一个无法清白的历史文物。陆焉识的离去具有逃避的意味,更多的是对遭受政治挤压和人性变异的家庭的逃避,是对蝇营狗苟的儿女们的逃避,他在无奈之下才离开了令他魂牵梦绕的上海,回到了让他一生都想逃离的西北大草原,那里充满了形式的自由,却注定了要忍受心灵的孤独与寂寞,晚年的陆焉识生命中完美的自由至少应包含一种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一种大家庭的幸福与温暖,失去了这一点他的余生注定充满了凄凉与悲哀。顺应政治、融入体制的马文昌,尽管是在愤激中死去的,但他享受到了人生最后的温暖和虚拟的尊重与荣耀,陆焉识却只能在孤寂中回望一生的沧桑与不堪。陆焉识是无情历史的见证者和承受者,他的一生都在自由与禁锢间游离,从才华横溢、追求自由理想的公子哥陆焉识变成唯唯诺诺、见风使舵的囚犯老儿,《陆犯焉识》以个体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社会变迁中的磨难和精神流变,展示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反思了历史、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与纠缠,也让我们在陆焉识人性的不断蜕变中一再审视历史的怪诞与残酷。
本时期的历史记忆不仅再次触及到“反右”“文革”等当代史,更将笔墨伸展到了20世纪的前半期。“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9]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的历史叙事在一种从容的叙述中颠覆了人们曾有的阅读经验,重构了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与理性体认,它们在再现历史创伤的同时,更注重探索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历史中知识分子在政治与革命规约下的命运遭际,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和历史的双重反思,亦思考了造成民族历史创伤的政治、文化与人性根源。这些作品重新检视了知识分子在残酷的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也以宏大的视野展现了历史的风云诡变,拨开了历史沉重的混沌与迷雾,于新世纪之初让人们再次铭记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和血淋淋的事实,它们均以超越历史的方式走进历史,这之中人性与革命的碰撞、日常生活与政治运动的冲突、知识分子在残酷的历史境遇中经历的蜕变、国家之殇与历史的沉重性,都给了我们深广的思考空间。
三、深度对比:知识分子的人性探微
相对于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对历史苦难的崇高化书写倾向,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摒弃了“苦难崇高”的情绪化写作,开始冷静客观地展现历史的混沌与革命政治的残酷。新时期那种充满激越和高昂的创伤书写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冷静之后,在新世纪的文学中变得更加理性和深沉,激烈的情感淡出了文本,这些书写都不再具有自传性质,也不再纠缠于个人的恩怨得失,而是着眼于一种历史的共性体验,它们都通过象征性的个体从历史普遍价值的角度来反思知识分子群体与整个历史,从而建立起受众对创伤和历史的普遍认同与深刻认知。作家们在对历史悲剧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在对知识分子的人性悲剧进行反思,“人性是小说最后的深度”[10],在这些作品中知识分子都被寄予了很强的寓言性和象征性,作者通过他们展示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走向死亡的过程,犀利地解剖了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也呈示了人性的复杂和深邃,知识分子那种独立不倚的人格建构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与迫害下终究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反思历史,拒绝遗忘,这本身也是作家的良知与职责所在,书写知识分子在20世纪历史中的苦难与创伤,是新时期以来文学书写的一个持续的主题,随着历史的推进、反思的深入,作家的理性书写特征更加突显。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英雄塑造不同,在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创伤书写中,作家们更注重挖掘的是知识分子复杂而深邃的人性。80年代的历史反思,尤其是对“反右”“文革”的反思很大程度上突显的是一种政治性控诉,知识分子本身的人性特质被有意无意地遮掩了。知识分子在一次次历史的劫难中,完全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形象,他们被动地接受突如其来的打击、迫害,却不承担任何历史的责任,作家们在剥夺了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同时,也轻易地卸掉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承担,遮蔽了知识分子在苦难中显现出来的复杂人性。因作家们是亲历者的缘故,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作家的影子,故而触碰知识分子的性格缺陷就显得比较困难,而一味强调知识分子本身是无辜者、受害者,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文化力量、为生存而抗争苦难的“壮举”,文化英雄就伴随着“神圣苦难”诞生了。而在新世纪以后对此类知识分子的书写中,人性的光辉有时还在,但知识分子长期被遮蔽的人性弱点被展示了出来,这种弱点不但让他们无法抗衡人世之恶,反而纵容助长了人性之恶,让乱世之恶更加泛滥,新世纪作家对知识分子复杂人性的深入揭示是对80年代知识分子苦难书写的超越。客观与理性是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对历史反思的最大特点,这也是此类创作走向成熟的突出表征。
同是书写苦难,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苦难对知识分子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在一种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默认中,他们往往丧失了对极左政治与错误路线的反省与抗争能力,并进而认同于这种改造,他们把这种改造甚至视为一种人生的磨练,视为与主流意识形态融合、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一种途径,比如章永璘,为了成为一个纯净的人,他要经过清水、血水、碱水的三次洗礼,改造的过程尽管艰难而痛苦,但这也是他蜕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过程,章永璘在理想与现实、灵与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张力中走向了新生,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这种政治带来的苦难有时也成为呈现知识分子道德情操与爱国之心的重要载体,他们以一种坚定、高贵的人格力量维持自己在苦难中的精神自信,比如范汉儒,这是在新时期的同类文学书写中一个让我们无法忘记的崇高形象,作者从维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灵魂像蒸馏水一样纯净”的知识分子,范汉儒曾被视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榜样和楷模,即使在死亡面前,他也从来没有丢失自己的精神高贵与人格操守,范汉儒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士”人精神和理想是他做人处事的根本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等这一套价值体系让他在困厄之中一直保持着严格自律,尽管身陷囹圄,他始终不变的是那一腔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对祖国的“大爱”让他抛弃了个人的“小爱”,这种对祖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让他成为了一个现代屈原形象,也让他在苦难之中愈发显得英勇而悲壮。此时苦难反倒成了对知识分子品格与气节的考验与反衬,范汉儒身上寄予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与精神操守的完美想象,也使作品凸显出一种精神的力量。在80年代的文学中,苦难造就了一个个大写的知识分子形象,精神的优越伴随着他们改造的始终,这不但让他们在苦难之中没有走向沉沦,反而使他们对苦难有一种超越的渴望与坚信,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成为照亮黑暗世界与苦难深渊的强力之光。而在新世纪以来的书写中,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崇高的精神力量和高尚的爱国情怀消失了,政治的高压和现实的苦难让他们诚惶诚恐,甚至造成了他们人性的异化与扭曲,他们的精神畸变也因此而起,苦难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品格起的不是塑造而是改造作用,人性之复杂在生存的极致环境中愈加彰显,作者对历史与政治的深层反思也正是借助这些知识分子的复杂人性来完成的。曾经那个大写的知识分子形象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甚至由于人性的自私与恶而显得有点令人失望,比如在马文昌、陆焉识、丁子恒(《乌泥湖年谱》)、周文祥(《中国一九五七》)等主人公形象身上就消失了那种传统的“士”人精神,尤其是马文昌,在革命逻辑和政治威权的双重作用下,他最终完全臣服于了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全然没有个性的同构体。当苦难结束之后,马文昌像《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一样,甚至以一种说谎的方式在演绎与美化一个高大的“文化英雄”形象,他的“青年导师”身份也是在配合一种政治宣传。完全被政治同构了的马文昌,已经没有了知识分子丝毫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他余生所做的就是如何充分认识和理解现行政治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并努力从思想上适应它融入它。从世俗的眼光看,马文昌是一个“好人”,在任何环境中他都没有违背良知去害人,马文昌身上并没有体现出人性之恶,他体现出的是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依附性与奴性,马文昌人性的极度变异寄予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痛苦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马文昌这样一个完全被政治同构者的形象也因此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因而,崇高的知识分子信仰、伟大的爱国情怀和理想的人性期待在新世纪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是看不到的,在苦难的挤压和死亡的恐惧中,他们的明哲保身思想和犬儒主义行径反而暴露出了这些知识分子内心的怯懦与精神的无所皈依。他们充当的角色,不再是高尚的道德受难者,而是具有理性、自由精神的历史批判者,这是前后两个时期知识分子形象在精神上的断裂之所在。
在新世纪这些知识分子的创伤展现中,我们看到那种刚正不阿、不向命运屈服、在苦难的折磨中依然保持着坚定信仰与崇高理想的这些知识分子最后要么向命运屈服了,要么就被政治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趋于矮化了,他们失却了精神的高地,不再是一个道德与人格上的英雄,也没有了传统“士”人的精神气质,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自保意识和犬儒心态,应该说,这才是历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这也是作家们试图从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缺陷重新反思造成民族劫难与国家之觞的人性因素。在马文昌这样被意识形态完全同构的知识分子之外,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或者源自于自身遭受的重创,或者是在别人的重创中自己颤栗了退缩了。在新时期的同类文学书写中,范汉儒、许灵均、罗群等很多知识分子都被塑造成了“圣洁受难者”的形象,他们映照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诉求与文化想象。新世纪以后,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精神诉求与文化想象都显得不是那么迫切与急需了,反思倒成为了一种理性的需求,知识分子软弱性的一面显得更为突出,面对不堪忍受的打击与迫害,他们表现出了一种本能的反悔与退缩:皇甫白沙(《乌泥湖年谱》)因为自己的正直而导致了儿子的死亡,他因此对自己表示出了痛恨:“为什么要顾及自己的良知呢?良知又是什么呢?”可以想象,皇甫白沙以后再也不会出于人性的良知而为别人仗义执言,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在他身上就此消失了;丁子恒(《乌泥湖年谱》)看到身边人一个个遭到厄运,尤其是亲眼目睹好友苏非聪在政治打压下的灵魂崩溃,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必须克制自己,我必须尽可能沉默……”,这种沉默不是“独善其身”,而是“明哲保身”,它折射的是知识分子精神的侏儒化,丁子恒此后过着“除了夹着尾巴而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人”的生活,但这种没有一点尊严的生存状态更让他痛苦不堪生不如死:“一个不知为何而活,也不知自己会活成怎样的人,一个每日里心下茫然着来来去去的人,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自己思想的人,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没有了表达自己欲望的人,与行尸走肉何异?”林春如(《父亲和她们》)面对生活的挤压和政治的暴虐同样表现出了如此思想:“为了孩子,我变得自私了。”为了生存与孩子,她甚至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念与追求,用婚姻来作交易,彰显出了人性在暴政下的裂变;周文祥在政治的审判中也变得妥协、软弱与犬儒,这种在灾难面前的恐惧退缩和明哲保身的犬儒行径暴露出了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和心里痼疾,他的四个“梦”其实隐喻了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精神畸变;陆焉识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不再追求政治的公正判决与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而是学会了在流放地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学会了如何逢迎与讨好对自己有利的人,陆焉识人性的蜕变更令人触目惊心。这些知识分子知道自己对抗不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暴力,他们尽管没有被政治意识形态同构,但他们的沉默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最大顺从与适应,尽管他们没有展露人性之恶也没有助长人世之恶,但这种“不言说”的沉默也是知识分子性格中潜在的“恶魔”性的表征,“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诚然是值得同情的,但这种命运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无力之力’所造成的。这是绝大的历史讽刺。”[11]即使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他们的这些反思也只是一种生存意义上的反思,像章永璘那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如果仅仅为了活着,人也就降到了禽兽的水平”的形而上的精神反思消失了,范汉儒身上体现出的那种传统文化精髓也不见了,这是一种更加生活化与个人化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精神的矮化中同时伴随着人格的分裂:他们想坚守理想与德操却滑向了人性的深渊,他们不想向暴政妥协却又低下高贵的了头颅。作家们于此打破了人物塑造的惯性思维,展露出了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在对历史的混沌与政治的悲剧进行深刻理性反思的同时,也探幽了知识分子更复杂的人性,让知识分子直视自己的内心与灵魂,更对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警醒。在这些知识分子精神被毁灭、肉体被摧残的同时,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是一代人的精神与创造力,这对一个国家与民族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损失与扼杀。这些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似乎也在不经意间告诉我们:范汉儒、章永璘式的知识分子,终究不过是作家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想象与美化。
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创伤书写而言,新时期的这些知识分子人性内涵更趋复杂化了。人是历史的制造者与推动者,知识分子因其自身知识与思想的力量而成为人类中最具智慧的一个群体,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无论什么时代,知识分子总被人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是思想变革、社会变革的先驱者,担负着思想启蒙、道德重建乃至政治教化的重任,他们必须要“弘毅”、“志于道”,必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应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但知识分子身上也体现出了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现实中他们因自身的软弱性和依附性却又无法肩负起这一重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永恒悖论。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精神衰变往往是由知识分子精神的萎缩畸变引起的,故而人们往往从知识分子身上寻找国家之殇的精神与文化因素。对历史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书写中,从知识分子的个体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深邃,从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上则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复杂与深邃,而新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叙事也正是通过审视知识分子的精神流变与复杂而深邃的人性来反思20世纪中那些不堪的历史的。
[1]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05.
[2] 南帆.革命、浪漫与凡俗[J] .文学评论,2002(2):46-55.
[3] 王春林.知识分子、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J] .平顶山学院学报,2011(3):68-75.
[4] 古世仓,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5] 毛泽东.五四运动[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559.
[6] 王卫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04.
[7] 李耳.花腔[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96.
[8] 田中禾.父亲和她们[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9]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 .上海:三联书店,2003:1.
[10] 曹文轩.小说门[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258.
[11]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147.
[责任编辑:吴晓珉]
Way and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Novel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New Century
HOU Ling-kuan
(School of Commercial Media,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Facing traumatic memories of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novel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new century reexamin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revolu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an “other” perspective of non-personal experience narrative. While exploring the spiritual evolu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se novels also reflect on the tragic fate of intellectuals’ homogeneity under the restraint of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A thorough revelation of complex and profound human nature of intellectuals show that the novel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new century have transcended the writings of tribulation and emotion of those intellectuals in the 1980s. The writers hence start to recognize and reconstruct the chaos and heaviness of the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under the context of a new age, further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tional writing in the novel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new century.
novel of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narrative; revolution; politics; human nature
2016-10-12
兰州财经大学科研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侯玲宽(1982-),男,河北邯郸人,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
A
1004-1710(2017)03-01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