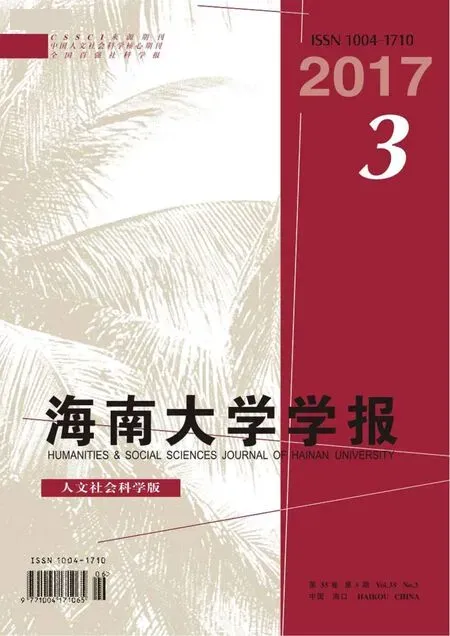庄子哲学启发《红楼梦》的三个层面和三种模式
2017-02-24李春光
李春光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庄子哲学启发《红楼梦》的三个层面和三种模式
李春光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红楼梦》的叙事格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宇宙神话层,社会人伦层和个体心理层。庄子哲学同样以这三个层面架构其哲学理论体系。《红楼梦》作为极为开放的文本样板,吸收了先贤时哲的优秀文化成果,庄子哲学便是各中显者。庄子哲学在《红楼梦》的宇宙神话层面,通过“点化模式”,来沟通天理人欲的关系,为行文铺设了宿命轮回的超验存在;在《红楼梦》的社会人伦层面,通过“死生模式”,来间离道德与欲望的关系,为行文奠定了乐生累死的情感基调;在《红楼梦》的个体心理层面,通过“体悟模式”,来圆融生活与人格的关系,为行文开掘了齐平万物的理想源泉。
红楼梦;庄子哲学;影响研究
解盦居士在《石头臆说》一文中开篇名义:“《红楼梦》一书得《国风》、《小雅》、《离骚》遗意,参以《庄》《列》寓言,奇想天开,戛戛独造。”[1]这就明确指出了《红楼梦》与《庄子》在建构模式上存在着深层次的渊源关系。庄子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借助寓言的形式,阐发其深刻的哲学思想要旨,这种言说方式对后世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阮籍在《达庄论》中认为《庄子》这种:“述道德之要,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2]的陈述方式是成功的。《红楼梦》作为叙事类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在诸般源流中也承继了庄子哲学“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的壸奥。故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哲学的也”[3]253。刘再复先生认为“《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理性哲学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悟性哲学则是直观的,联想的,内觉的”[4]。从“悟性哲学”的视域来说,《红楼梦》与《庄子》从根脉上是一脉相承的。
具体言之,庄子哲学从三个层面以三种模式启发了《红楼梦》的创作。第一个层面是宇宙神话层,对应的模式是“点化模式”。在超时空的叙事环境之中,以古典叙事文学中经典的点化神话为文章神髓,为《红楼梦》的轮回宿命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第二个层面是社会人伦层,对应的模式是“死生模式”。在宇宙神话层的笼罩之下,《红楼梦》中关于生死观的呈现,除了其肌理之宿命性之外,更多的则是社会人伦关系与个性自由之间的张力淬炼的结果。第三个层面是个体心理层,对应的模式是“体悟模式”。既然宿命轮回乃是天定,社会人伦亦不可忤逆,每个人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意欲找寻自己的存在价值,只有在心理层面,去感知、去开掘、去体悟,进而达到与天地合一、与万物齐平之目的。
一、宇宙神话层——点化模式
明清小说以神话为开篇者时常可见,此举在提升文本神秘性的同时,更加注重的是天命循环、天理昭彰的古意。而比较容易实现天理与人欲对接的当属点化。点化,这里专指世外高人指点迷津者,迷津者被点化后,往往达到顿悟的效果,进而对未来的期许和生命的真谛有了重新的审视与考量。而点化的生发过程,往往能深谙宿命归真之要旨,进而弥合甚至幻化天理人欲之畛域。《庄子·在宥》记述了如下一个事件: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 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5]379-383
这里,广成子点化黄帝,已经粗具中国古代文学点化模式的雏形。被点化者主动要求点化者对其进行点化,被点化者问,点化者答,一问一答完成点化的过程。黄帝意欲“治身长久”,广成子要求黄帝平心静气、摒弃杂念,带他到“至阳之原”,经由“窈冥之门”,最终到达“至阴之原”。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发生—磨砺—复归一个大循环之周天,被点化者经由点化者点化,从迷惘之处来到凡间,在凡间历经诸般磨难之后,终究会回到自己生发的原点。这一点化模式和《红楼梦》的艺术构思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红楼梦》中最能说明这一过程的当属第一回一僧一道点化石头的故事。先是被点化者(石头)主动要求点化:
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6]3
石头请求一僧一道点化其入凡间享受几年的过程,比起广成子点化黄帝有了长足性的进步:先是贬低自己是“蠢物”,然后褒扬点化者的羽化气质、慈悲心肠是“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造成天分的差异,进而提出自己的要求,最后加以感谢。这样的后果就是点化者不得不答应被点化者的要求,于此同时提出告诫性话语:
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怂级,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6]3
此处较《庄子》的发展之处在于,广成子直接告诉了黄帝达到目的的路径,即“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却并没有加以必要的告诫,而一僧一道却给了石头以必要的告诫,即“美中不足,好事多魔”,“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整个过程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石头偶尔也会放泼耍赖,使得整个画面不至于过分严肃。值得注意的是,一僧强调了“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的要求,刚好契合了《庄子》发生—磨砺—复归的轮回模式。
如果把上述过程称之为“有意识点化”,那么把“发生”这一环节去掉,则就成为了另一种点化方式,即“无意识点化”,是有意识点化的子模式。此类点化亦可在《庄子·徐无鬼》中找到: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适遇牧马童子,问涂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适有瞀病,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夫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为天下者,则诚非吾子之事,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辞。黄帝又问。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5]830-833
在这里,黄帝向牧马童子打听“具茨之山”“大隗”的所在,只是普通的问路行为,当黄帝问道如何“为天下”之时,牧马童子告知黄帝“为天下”犹如“牧马”,黄帝才恍然大悟,称其为“天师”。这个事件表面是有意识点化,其实质则是无意识点化,黄帝遇到迷津,在没有途径的情况之下被牧马童子无意点化,当他顿悟之时,才知道是被仙师点化。
故而,凡人在人世间经历诸多磨难,最终看破红尘,在无意间被高人点化而去,甄士隐被癞头和尚和跛足道士点化、柳湘莲被道士点化,便是《红楼梦》中此类点化的明证。“不能洞悉明白”“愚浊”的甄士隐曾在梦中让二仙师“大开痴顽”,以求“稍能警省,亦可免轮回之苦”的要求没有达成,也就意味着“有意识点化”的搁浅,亦为后来的“无意识点化”种下了前缘。后来,寄居于岳丈家“露出那下世的光景”的且本有“宿慧”的甄士隐,拄杖挣挫在街前散心时,无意间听到跛足道人吟讴《好了歌》,在道人阐发“好”“了”的关系之后,便“心中早已彻悟”,进而作出了《好了歌》的解注,最终与疯道人“飘飘而去”。 同样,柳湘莲在梦中与尤三姐诀别后,醒来后并非薛家小童所引之“新室”,
竟是一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个跏腿道士捕虱。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柳湘莲听了,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6]924
柳湘莲“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观”,与甄士隐听闻《好了歌》后大彻大悟一样,均是被“无意识点化”。二者都没有主动询问,只是在听闻与闲聊中被高人的无意义之语点通窍窈,最终悟得人生真谛,飘然而无所踪。
至此,《庄子》中的两种点化模式均在《红楼梦》中有所体现。推而广之,这种“发生—磨砺—复归”的原型模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当与道教文学发生交集之时更为明显:
下凡历劫故事的原型可以追溯到远古巫师使神降临凡间的通神活动。这类通神活动衍生了早期的下凡济世仙话,下凡济世仙话在后世又演变成了降凡历劫仙话……悟道成仙故事的原型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后来,演变成道教“人生如梦”这一哲学观念的最佳叙事母题……文人利用这个故事宣扬宗教哲学和宗教教义,把这个故事改造成了彻头彻尾的渡脱故事。由于这个故事在“人生如梦”的旗帜下可以包写无限的人生,因而造就了中国最伟大的哲理性文学著作。[7]
在强大的原始宇宙观念之中,在奇异的诸星临凡神话之内,下凡历劫,返璞归真,已然成为此类叙事文学作品圆融结构、调和天理人欲的不二法门。第一回中,道人有“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僧人有“凡心偶炽”的神瑛侍者“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的说法,可见红楼诸人原本于警幻仙姑处挂职,后经点化,历经凡间沧桑变幻与人事纠葛而复归天班,在警幻仙姑处“销号”,最终在“情榜”处得知自己的定位,脂批中曾多次强调“情榜”的存在,而这“情榜”也为诸人历劫归真之过程画了一个最终的句点。正如第六十六回“尤三姐入梦柳湘莲”那样:“一手捧着鸳鸯剑,一手捧着一卷册子,向柳湘莲泣道:‘……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误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6]923-924王夫之认为:“至阳之原,无所喜而物自生;至阴之原,无所怒而物自杀。”[8]的确,诸般情意随缘到,缘灭诸情亦自灰,“来自情天,去由情地”,这正是一种下凡历劫—复归本原的解注。
二、社会人伦层——死生模式
在神秘的、不可抗的宇宙神话层的氤氲之下,宿命轮回之观念,已经浸淫到每个人物的文化基因之中。诸人在历劫的过程中,除了要逡巡于不可捉摸的宿命观念,更多的是要与现实社会的人伦物理相龃龉。当个性人格不能得到社会规约的容受之时,个人的存在价值偃旗息鼓。这其中最明显的当属《红楼梦》借道《庄子》而阐发的死生模式。道光年间的红学家诸联在《红楼评梦》中说:
人至于死,无不一矣。如可卿之死也使人思,金钏之死也使人惜,晴雯 之死也使人惨,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愤,二姐之死也使人恨,司棋之死也使人骇,黛玉之死也使人伤,金桂之死也使人爽,迎春之死也使人恼,贾母之死也使人羡,鸳鸯之死也使人敬,赵姨娘之死也使人快,凤姐之死也使人叹,妙玉之死也使人疑,竟无一同者。非死者之不同,乃生者之笔不同也。[9]119
同样是写“死”,因为人物性格、地位的差异,对于死的评价也就各有不同。“红楼四烈婢”之死,多少透露出她们的地位使之然的凄凉,呈现出“惜”“惨”“骇”“敬”的评价趋向;而五位金钗之死,多少透露出她们的性格使然的尴尬,呈现出“思”“伤”“恼”“叹”“疑”的评价趋向。以往的评论对于红楼死亡事件多是从“同中见异、犯中求避”的角度加以阐发,其实,在这些死亡事件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评书者对于《红楼梦》生死观的争鸣。为何“金桂之死使人爽”“赵姨娘之死使人快”,这其中就存在一个伦理价值的判断标准,休谟认为:“德的本质就在于产生快乐,而恶的本质就在于给人痛苦”[10],此二人作恶多端,死后自是大快人心,因此是“爽”和“快”。与此同时,应该注意这些人的死只能从道德伦理层面进行评判,是《红楼梦》生死观中最通俗、最浅表的载体,而真正能代表《红楼梦》本质性、超验性生死观的人物只有贾宝玉一人。贾宝玉经常会说这样的“胡话”:
宝玉忙笑道:“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侯,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6]262
宝玉又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6]785-786
在贾宝玉看来,人死留骸还能证明自己存在过,即使化成有“形迹”与“知识”的“飞灰”也并非了局。只有化成烟被风吹散,才是彻底的解脱。这就说明了贾宝玉“乐死累生”的情感倾向:以死为乐,以生为累。贾宝玉动辄把死挂在嘴边,说明他是向死的,因为现实人生叫他活的很累,自己无心仕途经济学问,而周围的人偏要耳提面命;自己钟情于林妹妹,而周围的舆论都偏向于宝姐姐;自己要结交自己心仪的朋友,而周围的人不给他合适的空间与权利。因此,贾宝玉出现“不自由,毋宁死”的倾向是在情理之中的。“乐死累生”的观念可以在《庄子·至乐》中觅得渊薮: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5]617-619
庄子所问之事基本囊括了人生所有的不利处境:贪求生命,失去真理;亡国灭种,斧钺之灾;不行善事,累及父母;贫寒交加,冻馁交迫。当庄子要为髑髅起死回生时,髑髅却选择死下去,因为死后就没有上述的烦恼了,便是过起了“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的“南面王”之生活。这个故事从反面证明了庄子“乐死累生”的倾向。所谓“忘尘息念方名死,死后翻成慧命长”[11]331,生前为尘世所拖累,死后终得妙悟,均已于事无补,故再观察贾宝玉,人生对他来说只是累赘,还不如早死的好,死后还不能留下痕迹,也少了些彼岸的烦恼,这比《庄子》更为进步。《庄子·刻意》认为:“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5]539圣人死后要像自然物一样融化在大自然之中,与天地同一。这个过程很需要一段时间,而贾宝玉的死亡观则是立刻化灰化烟,立刻消失在自然之中,与自然脱离,比庄子更干净决绝。贾宝玉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倾向,究其根源就是“哀莫大于心死”,见《庄子·田子方》的论述。颜渊对孔子亦步亦趋:
仲尼曰:“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5]707-709
哀莫大于心死,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思想顽钝、麻木不仁,只知亦步亦趋、邯郸学步,“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忘了本我的存在,如同空市找马,一切皆空。丁大同先生在《论欲望的道德化》一文中明确地将“欲望的节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原欲阶段,即广义的原始情欲需求。表达与满足体系主体的本能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外观或展示;
阶段二:续发欲始阶段,道德社会化对人的道德方面的最初结果;
阶段三:后原欲阶段:道德社会化作用之下出现的一种欲望道德化体系,分为受潜抑欲望与获允许欲望两种——
受潜抑欲望:欲望中被社会道德化所遏制范围内的欲望;
获允许欲望:欲望中被社会道德化规约允许实现的欲望。[12]
既成社会文化体制对于个体个性发展的规约,直接导致了原欲的埋没,个体无法改变社会体制只好被动适应社会人伦物理之存在,所以亦步亦趋才能成为可能,哀莫大于心死,才有了广泛的社会根源与心理基础。康德认为:“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假使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自己的理性中明确地思维到的,那我们便不应当认为自己有理由来假设‘自由’这种东西。”[13]也就是说,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其自由是建立在道德的约束之上的,若想跳“自由”的舞蹈,必须戴“道德”的脚镣。进而言之,如果欲望中“被社会道德化规约允许实现的欲望”没能(从根本上)实现,那么哀莫大于心死的社会人伦温床,也就成了一种无形的培养皿。反观贾宝玉,在亲情方面,承载了太多的家族压力,不能象普通同龄孩子那样尽情欢乐,只有在姐妹、丫鬟之间才能得到该有的快乐;在友情方面,想结交象柳湘莲、蒋玉菡这样的社会边缘人物,以发“义”慨,却没有出府和使用银子的权利,只有混迹于姐妹、丫鬟之间才能满足友情的缺位;在爱情方面,与林黛玉明朗的爱情关系,却因为家族的前程问题而化为泡影,只有在姐妹、丫鬟之间重温爱的旧梦。难怪贾宝玉会说出如下的话:
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宝玉笑道:“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6]989-990
有学者认为:“在逍遥的背后,在庄子生命的底层,未尝不奔腾着愤激与焦虑之情。”[14]对于贾宝玉,那偏激的言论,那焦躁的情绪,又何尝不是如此?相反地,也有学者认为:“庄子的逍遥之游是对付生死的一剂看不见的心理式的仙丹。”[15]庄子可以做到用逍遥游化解生死危机,而贾宝玉对现实的体制厌恶至极,却又回天无力,只能选择乐死累生的死生模式在现实社会人伦的泥沼中苟延残喘。因此说,《红楼梦》死生观念对于《庄子》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王国维先生从悲观主义哲学出发论证《红楼梦》的悲剧性是极为合理的: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3]245
欲望之多寡尚是其次,实现之成色最是要紧。贾宝玉的悲观情绪,无论是乐生累死,还是哀莫大于心死,都可以转化为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Seligman)于1967年提出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理论。当人连续受到挫败之后,个体会产生丧失信心、自暴自弃的心理状态。而习得性无助产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情绪上的创伤”,其终极表现就是悲观抑郁。反观贾宝玉的种种行止,又何尝不是一种习得性无助!
三、个体心理层——体悟模式
文化基因里的宿命轮回观念不可扭转,现实人生的社会人伦不能超越,只能以乐死累生徒增玄想。既然生活不能给予,那就只好在个体心理层面上,找寻慰藉,体悟人生,领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诸般美妙。诚然,《红楼梦》是本极会养生的书,除了饮食调理之外,还有类似于道家修炼内丹的理念。以修炼内丹之法来完成艺术创作,是《红楼梦》特有的艺术心理现象。就《庄子》而言就是要“心斋”“坐忘”。
“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心斋?”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5]146-147
为什么要“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林希逸在《南华真经口义》中认为:“听之以耳则犹在我,听之以心则犹在我,听之以气则无物矣。”[16]只有做到无我、无物,才能做到虚而待物,这个“物”就是“道”,因此才有“唯道集虚”,这个“集虚”并非数月“不饮酒不茹荤”可比,故晋人郭象有注云:“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也”。《云笈七签》卷37“说杂斋法”条中介绍了道教的三种斋法:
斋法一:设斋供——积德解愆;
斋法二:节食斋——和神保寿;
斋法三:心 斋——疏瀹其心,除嗜欲也;澡雪精神,去秽累也;掊击其智,绝思虑也。[17]273
这三种斋法,逐层递进,剔除人心中的诸多杂念,最终形成心灵的斋戒。对于作家自身而言,在创作的过程中,应该保持一种“唯道集虚”“澡雪精神”的“斋”的状态。唐代诗人权德舆在《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一文中说:“上人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固语甚夷易,如不出常镜,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故睹其容览其词者,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这说明灵澈上人空静的心境对其诗境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也强调了“心斋”的重要性:“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18]这些观点正如黑格尔在评价“伊壁鸠鲁的道德学”时所言:“从存在这个思想出发,这种思想比较容易迁就,并不象那样追求向外活动,而是追求安静。它的目的是精神的不动心,一种安宁,但是这种安宁不是通过鲁钝、而是通过最高的精神修养而获得的。”[19]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心斋呢?不二法门当为“坐忘”,《庄子·大宗师》有言: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旡好也,化则旡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5]282-285
成玄英《庄子注疏》解释说:“外则离析于形体,一一虚假,此解‘堕肢体’也。内则除去心识,悗然无知,此解‘黜聪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之益,谓之‘坐忘’也。”郭象注曰:“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即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20]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物我合一。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21]贾宝玉经常与花鸟鱼虫对话,正好体现了“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理念。如第五十八回:
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6]800
这里的“呆性”便是一种坐忘的感慨,此回后戚序本有评曰:“杏子林对禽惜花一席话,彷佛茂叔庭草不除襟怀。”[22]694周敦颐不除庭草以存天意,与邵雍的“乐与万物同其荣”有异曲同工之妙处。这里贾宝玉与万物齐平,以一种“离形去知”的姿态去观照世间万物,则刚好符合了庄子坐忘的题中之义。类似的,宝玉曾将香菱等人玩过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菱蕙安放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6]862,还曾想过“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6]254。这种在别人看来有异于常人的“呆性”,却正是宝玉齐平万物以达到坐忘心斋的慧根。
向浅显的方向阐释,便是说明人应该专一、虚心且善于内省,才能到达对于常规思维的超越。《庄子·知北游》认为:“若正汝形,一视汝,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5]737端正的你的形体,集中的你的视力,天然的和谐自然降临;收敛你的心智,专一你的思绪,神灵将光顾你的肉体。《红楼梦》中的熔心斋坐忘于一炉的显例便是“香菱学诗”:
香菱拿了诗,回至蘅芜苑中,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他也不睡。
香菱听了,喜的拿回诗来,又苦思一回作两句诗,又舍不得杜诗,又读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
香菱听了,默默的回来,越性连房也不入,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土,……只见他皱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宝钗笑道:“这个人定要疯了!
昨夜嘟嘟哝哝直闹到五更天才睡下,没一顿饭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听见他起来了,忙忙碌碌梳了头就找颦儿去。一回来了,呆了一日,作了一首又不好,这会子自然另作呢。”
香菱满心中还是想诗。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后上床卧下,两眼鳏鳏,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去了。……只听香菱从梦中笑道:“可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宝钗问他:“得了什么?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学不成诗,还弄出病来呢。”……原来香菱苦志学诗,精血诚聚,日间做不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6]649-651
香菱学诗的过程先是夜里不睡;接着是茶饭无心,坐卧不定;然后是不进屋,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土,一会皱眉,一会含笑;最后干脆是在梦中作诗,觅得佳句。这个过程刚好是“坐忘”的全过程,它做了“心斋”(即“精血诚聚”)的清道夫,“坐忘”的目标是“心斋”,坐忘不得,心就不能斋戒,只有坐忘的好,才能“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而香菱作诗的灵光之“神”,便是通过梦境来到香菱之“舍”的。庚辰本在第四十八回结尾处有如是评语:“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是梦,秦氏家计长策又是梦,今(香菱)作诗也是梦,一柄风月鉴亦从梦中所有,故曰‘红楼梦’。”[22]578
在现实生活中,《红楼梦》也得到了“心斋”的礼遇。诸联在《红楼评梦》中说:“余自叹年来死灰槁木,已超一切非非想,只镜奁间尚恨恨不能去。适来无事,雨窗展此,唯恐擅失,窃谓煮苦茗读之,燃名香读之,于好花前读之,空山中读之,清风明月下读之,继《南华》、《离骚》读之,伴《涅槃》、《维摩》读之。”[9]120诸联的潜台词是读完《庄子》再去读《红楼梦》会对理解后者有所助益。无论是“煮苦茗”还是“燃名香”、无论是“空山中”还是“明月下”来读《红楼梦》,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经典的绝妙的体悟方式呢!
吕思勉先生在评介先秦诸子学说的时候认为:“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览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23]吕思勉先生认为道家是中国学术之根本,庄子哲学是道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此,庄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众学之“体”。
作为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翘楚的《红楼梦》,在宇宙神话、社会人伦、个体心理三个层面,全方位地消化了庄子哲学“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的叙事神髓,以点化模式、死生模式、体悟模式为突破口,建立起了《红楼梦》与庄子哲学的脐带关系。宇宙神话观念之阐发,让天理与人欲互通,以行点化之实,宿命轮回之惑遽然而生;社会人伦规约之阐发,让道德与欲望互轻,以成死生之念,厌世累生之叹怃然而生;个体心理萌动之阐发,让生活与人格互溶,以达齐物之巅,玄思冥臆之妙陡然而生。宇宙神话层是天理基础,社会人伦层是现实呈现,个体心理层是感性超脱。点化的目的,是来凡间的社会人伦中体验一番,而凡间的生老病死,则会成为体验者因人而异的个性体验,在社会人伦的羁绊中寻找个性的超脱,体悟人生,体悟浮世绘的美妙,才是历劫达观之正途。逍遥游于宇宙之间,与万物齐平共生,用心斋坐忘体悟世间万物的玄妙,最终复归本原,道法归一。如果说道家哲学是中国学术之“体”,那么,《红楼梦》则是庄学之“用”。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言:“《红楼梦》第一得力于《庄子》……像这样汪洋恣肆的笔墨、奇幻变换的章法,从《庄子》脱胎,非常显明。”[24]
[1] 解盦居士.悟石轩石头记集评[M]∥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184.
[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12.
[3]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
[4] 刘再复.《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J].渤海大学学报,2010(2):6.
[5]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3.
[8] 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4:90.
[9] 诸联.红楼评梦[M]∥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64.
[10] 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30-331.
[11] 方以智.药地炮庄[M].张永义,邢益海,校点.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2] 李建华.罪恶论——道德价值的逆向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50-152.
[13]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2.
[14] 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25.
[15] 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113.
[16] 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64.
[17] 张君房.云笈七签:下[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273.
[18] 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黄叔琳,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369.
[1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83-84.
[20] 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163.
[2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713.
[22] 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M].霍国玲,紫军,校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23]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27.
[24]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6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210.
[责任编辑:林漫宙]
Three Levels and Patterns inADreamofRedMansionsEnlightened by Zhuangzi Philosophy
LI Chun-gu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The narrative pattern inADreamofRedMansions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of the cosmological myth, the social ethics and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which are also used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Zhuangzi philosophy.ADreamofRedMansionsas a model of exoteric text absorbs the outstanding cultural achievements from the predecessors, and Zhuangzi philosophy is a significant one. In the level of cosmological myth inADreamofRedMansions, the “revealing mode” in Zhuangzi philosophy is used to bridge the heavenly principle and human desire, which enhances the transcendent existence of fatal transmigration in the text. In the level of social ethics inADreamofRedMansions, its “living-dying mode” is adopted to separate morality from desire, which lays the emotional keynote of happy living and weary dying for the text. In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its “comprehending mode” is applied to integrate life with personality, which digs the ideal origin of making all things equal in the text.
ADreamofRedMansions; Zhuangzi philosophy; impact study
2016-12-31
李春光(1986-),男,辽宁阜新人,湖北大学文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I 242.4
A
1004-1710(2017)03-007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