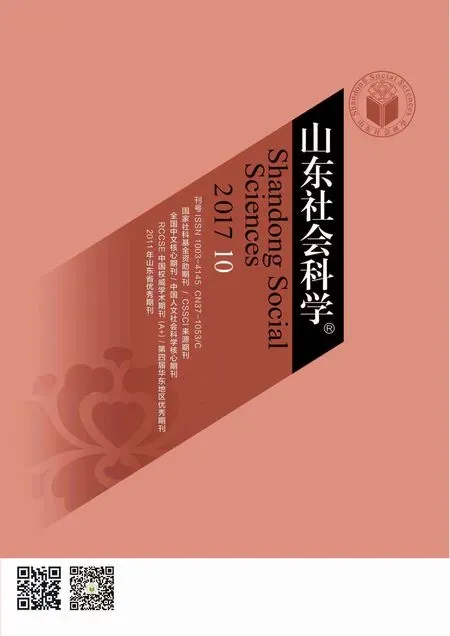分裂、无力与孤独:新媒体文化对个体心理的负面影响
2017-02-24于小植雷亚平
于小植 雷亚平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部,北京 100083;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分裂、无力与孤独:新媒体文化对个体心理的负面影响
于小植 雷亚平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部,北京 100083;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本文致力于描述和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普通个体的负面心理状态:由于个体随机或依据愿望选择互联网上无限信息中有限的一部分来达成对世界及自我的理解,会使个体的这一理解走向虚妄,进而形成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分裂;新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量与个体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反差、个体面对信息的主动感与其现实力量的反差、缺少行动支撑的网络化生存的精神符号属性等都会带来个体的无力感;个体依据信息碎片面对现实世界、网络空间中群落间的对抗,以及对物理居住空间的疏离则会给其带来孤独感。作为一种解放力量出现的新媒体同时使个体成为时代的失落者。这种情形需要依靠理性重建对世界的完整把握、自己与他人的和谐以及自我的力量感。
新媒体;心理;分裂;孤独;理性
一般而言,媒介的变化被认为是文化嬗变的一个重要推动要素,而新媒体的出现无疑给当下文化带来了时至今日我们也无法全面认识的巨变。
近来的研究对其变化大致形成了这样的描述:网络化生存的人们处在无比广阔、瞬息万变的信息的汪洋大海里。网络载体巨大的容量带来了信息的膨胀,它不仅表现在同一时间点信息的丰富上,还表现在时间的纵向轴上信息更迭的迅捷上。与传统媒介不同,新媒体带来的是文字、音频、视频相互整合的超文本,能够营造更强烈的真实感。新媒体带来的一个更加实质性的变革是信息制作和发表的多点化。只要你愿意,便可以取得一个自己专有的、可以对无限公众开放的发表空间,而发表所需的音频、视频的制作也因小型移动制作设备的普及而变得非常便利。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变成了集信息的制作、发表与接受于一身的“网众”。这些网众在网络信息的海洋里渐渐聚合成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群落①本文选择“群落”这一用词,意在强调网络化生存的散漫的精神性集合的侧面。与其意义相近的“集体”“群体”“部落”“集群”等词语虽然也被其他研究者用于指称精神性的网络化集合,但它们都有与精神性网络化生存的集合特征不符的侧面,如“集体”有偏向于组织性的含义,“群体”偏重于现实的物理性的存在,“部落”则倾向于指具有均质性的原始人的群体,“集群”则有随机性、无纪律、疯狂等含义。,这些群落往往只停留在精神向度的分享方面,而现实支撑则较为少见。当然,在一些问题上,同一群落或多个群落间会形成一种共同关注和呼喊,使其在沉默的信息海洋里成为一种可见性②Daniel Dayan,"Conquering Visibility ,ConferringVisibility:Visibility seekers and media performance "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1).p.5.的存在。
对这种变化,学界有两种对立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它带来的民主化的个体性的表达,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一种声音认为它使信息、信息的表达乃至人群都走向碎片化,进而带来了理性深度的消失。
评价新媒体带来的文化得失,无法绕过对新媒体文化下人的心理和实存本相的考察。文化究其实质而言,是人的一种创造物,它的流传和延续都是以人的行为作为再生产的动力的。换言之,文化考察的根基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考察。而且,就一种人造物而言,它的价值是以给人这一主体带来了福祉与否为评价标准的。所以,本文将对新媒体的使用者(同时也是被使用者,因为大多数个体在时代里都是被动的)的存在状态和心理状态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期给这个提问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本文选择以可以想象与把握的新媒体文化下数量最大的中下层个体为对象,对其网络化生存的较常见的心理与处境进行分析,以给这个群体一个较多出现的侧面的素描。
一、人设化的自我精神赋形及精神分裂
传统媒体几乎由意识形态或精英所掌控,信息的制造者和发布者比较单一,它照亮社会生活的可见性是被设计好的。与新媒体相比,它的信息量较少,信息与信息之间容易形成统一的口径,这些少量的、相互合作的信息共同营造了一个影响公众现实感的拟态环境*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5页。。虽然传统媒体下的民众也会有其各自独特的选择,但总的说来,一个稳态社会是以压倒性多数的合作性的公民为基础的,而拟态环境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些合作公民进行精神赋形的工具。这些合作公民并不知道拟态环境的存在,他们以为,被拟态环境有意照亮的可见性信息就是世界本身,它是自然而然的,而依据这些信息形成的理解和情感选择是自己的理性和意志的结果。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性质的拟态环境:首先,互联网形成的信息共享造成了信息数量的急剧膨胀,想要对这些海量信息进行统一的“拟态”处理是不可能的;其次,这些已有的信息往往来源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信息紧密结合在一起,当需要利用这些信息的时候,就难以把意识形态完全排除在外,因而“拟态”处理的难度就变得非常之大;再次,个体性信息制作和信息发布的便利,使信息的生产和发布发生在“拟态”处理之前,“拟态”处理只能弥补它对“拟态环境”的破坏,而无法从源头上阻止难以预见的破坏;最后,这些原生态的信息往往是口径不一的,它的披露本身就破坏了“拟态环境”存在的基础,使从前代表“理性”“正当”的“拟态”声音变成了众声喧哗中的一个。这个后果恐怕并不是无数原生的信息发布者的初衷,但它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走向。
因为新媒体打破了“拟态环境”这个给个体精神赋形的基础,个体在海量的相互冲突的信息里,只能自己来选择“正确”的信息,以它们为自己的精神赋形。这种自我精神赋形与传统的以“拟态环境”为基础的精神赋形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的精神赋形是以“全面”的信息为基础的,而新媒体文化下的精神赋形则是以部分信息为基础的。这种依据部分信息进行的精神赋形必须首先以在海量的信息里进行选择为前提,但是这种选择并不是在掌握了全部信息之后剔除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而是在无法获得和分析全面信息的情况下的一种随机行为。
当然,个体选择信息并不完全是随机的,也会有所依据。与现代阐释学所阐明的“前理解”*[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278页。概念相似,个体在选择之前一定有其“前选择”。可以把这里的“前选择”定义为借以选择的依据。如果说前理解在与新的被理解之物遭遇后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被理解之物所改变从而实现主体精神的跃迁的话,“前选择”则根本不给被选择之物改变自己的机会。“前选择”里大致会有观念、愿望、品味等各种内容。与观念、愿望、品味不符的信息会被过滤掉,而与其相符的信息则会以其外在性、“客观性”身份加固个体原有的观念、愿望和品味。也就是说,前理解会促成自身的变化和丰富,“前选择”则倾向于故步自封。也就是说,“前选择”往往不给前理解与新的被理解之物遭遇的机会,使前理解无法与新的被理解之物遭遇。“拟态环境”下的个体必须被动与某些自己并不愿意选择的信息遭遇并试图理解它们,因而“拟态环境”给予了个体遭遇新信息的机会,由此需要个体运用自己的前理解去消化它,并进一步实现个体理解的更新与跃迁;而新媒体环境下以保持全面性来进行信息摄取的出发点不存在了,海量信息的随机性使个体依据其自身的观念、愿望和品味进行选择变得有机可乘。因此,前选择扼杀了前理解,使个体难以实现对世界与自身理解的跃迁。就此而言,“拟态环境”下的个体是倾向于自卑的,而新媒体下的个体则容易自以为是。(关于二者的关系,应该并不仅限于这一个侧面,但其复杂性互动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不作赘述。)
信息订制会加强个体的固有选择倾向。无论是个体发现某些信息搜集或制造者与自己的选择意愿接近,还是这些信息搜集或制造者根据搜索痕迹等发现潜在的客户而进行推销,都会作为一个更加具有外在性的身份使个体更坚定自己的“前选择”。与传统媒体作出全面性、客观性承诺不同,新媒体环境下订制信息的出售者往往更倾向于信息的特性,也不回避自身的倾向性。信息订制这种交易是个一对多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一样,信息制作者要把握和扩大定制者的心理需求。不同的是:传统的大众传媒为了争取更多的受众,往往倾向于刺激人性中最具身体色彩和及时享乐性的部分,因为传统大众传媒基于大众工业的巨大规模甚至垄断力,原则上会以更广大的受众为目标;新媒体的信息制作者面对的则是分化了的市场,订制信息的出售者为扩大和留住客户,会引导个体向某种与其相似的固有类型发展,而这种发展会带来更多与个体的相似性,从而进一步加强个体对自身选择的客观性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订制信息的个体还可以通过订制某种信息为自己贴上一个确证自我的标签,它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明确化的表达,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与他人进行交往的依据。
新媒体环境下个体自身对信息进行随机选择的精神赋形还不能满足其社会交往的需求,而且这种孤独个体的精神赋形一般来说还是缺少外在支撑的,而网络群落则能满足这种需求。但网络群落不同于物理空间里的现实群落,“网络空间中的群体不限于以各种熟悉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具有亲情性的群体”,“这不仅表明观念空间有了自己的群体形式,观念空间可以被组织起来,而且还说明群体也可以表现为观念形式”*刘少杰:《网络空间的现实性、实践性与群体性》,《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2期。。实际上,考察一下网络空间里的群落性质,其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是以观念、意见和品味等的相似性为基础形成的群落。这种基于观念、意见和品位而聚集起来的群体,导致了同质性认同的大量生产,长时间沉浸在同质性的观念类群体里,会导致自我重复、自我认知的虚假性,以及对异质性群体的对抗性倾向。同时,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参见王逸、蒋一斌:《网络群体极化及其心战功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的新媒体部落的领袖往往会由极端的声音构成,符合标签的理念和情绪才容易聚集人气。进而,与生活常态相似的体验和声音往往无需传达,而独特奇异的、少见的、与常态生活迥然不同的事件、理念和情绪才容易被重视、被识别,依赖网络空间认知世界的个体则往往会形成错觉,把千奇百怪的特异事件当作现实生活的全貌映像,从而产生巨大的认知偏差。因而,依靠新媒体群落自我赋形的个体往往容易形成“极端信息依赖症”。
新媒体文化下个体的这种自我精神赋形,依据的是自我选择的信息,而其表达则只表现为个体在网络空间发布的信息,网众对个体自己发布的信息以外的信息一无所知,“新媒体传播具有中介化人际沟通功能,而这种功能使得人际交往具有理想化和欺骗性的特点”*梁颐:《新媒体传播对人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探略》,《东南传播》2010年第10期。。也就是说,与传统媒体根据“拟态环境”的“现实信息”进行的精神赋形不同,它不是在传统的社区、单位里,众多个体共同进行的精神赋形,这些众多的个体在现实里可以互相监督,从而使外在评价成为个体精神赋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文化下的个体精神赋形是缺少现实监督的,它带有更多的理想性和愿望性,有更多的自欺欺人的成分。
总之,这种精神赋形依据的是随机的或愿望选择的信息,网络群落的内部认同使其更加合理化,而群落代言人的极端状态则使群落中的普通个体自我认知走向极端。简言之,这种精神赋形的基础是虚妄的。它类似于荷妮所说的作为神经症的一个重要源头的理想自我*[美]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陈收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页。,只是这个理想自我比荷妮论述的理想自我更加有脱离现实的理由,因为新媒体文化下个体的精神赋形依据的是随机选择的信息,以及网络表达的中介性带来的现实匡正的匮乏。
当然,与荷妮的论断相同,这种理想自我会导致个体与现实的分裂,因为新媒体文化下的个体无法通过精神赋形改变包括自己的阶层、居住空间乃至容貌、年龄等在内的强硬的现实。可以说,这种人择的精神赋形越接近自己的美好愿望,它就越容易脱离自己的真实处境,与现实的分裂就越巨大。如果说荷妮论述的理想自我导致的是现实里数量较少的神经症,那么新媒体带来的则是大规模的常态神经症。
二、网络空间里的力量感与现实自我的无力感
有研究认为,新媒体会带来真正的大众的声音,会带来重塑社会的力量。*施芸卿:《表达空间的争夺:新媒体时代技术与社会的互构——以 7·23 动车事故相关微博分析为例 》,《青年研究》2013第3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新媒体同时也会带来个体自我认知里强烈的无力感。
首先,新媒体带来的个体精神赋形与其现实的强烈反差,不仅会带来个体的分裂感,还会带来个体力量的削弱。根据荷妮的研究,神经症者会借助理想自我的幻象带来自我的荣誉感,但现实自我根本无法达到理想自我的要求,因而神经症者会贬损现实自我——他时而活在荣耀的幻象里,时而活在无能的现实里。理想自我苛责现实自我的无能与怠惰,现实自我则以其无能和虚弱来证明理想自我的虚幻。这不仅会带来惭愧等负面情绪,而且会削弱主体的力量,使其陷入自我冲突中而无法专注于创造。*[美]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陈收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9页。我们只要把荷妮的理想自我换成新媒体带来的个体的精神赋形,对比一下个体的现实处境,就可以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稍稍不同的是,新媒体带来的个体精神赋形会更加强大,原因是网络的中介性导致他人依据对神经症个体的观察而进行的反向评价匮乏,同质性网络群落的内部精神支撑泛滥,因而使神经症个体更容易逃避在网络环境里,成为网络寄居里的强者、现实里的无能为力者。另外,新媒体环境里众多信息制造者发布的信息的可信度容易受到质疑,传统媒体在新媒体面前也成为一个相对平等的信息制造者(虽然它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权威,但毫无疑问,信息垄断者的地位已经动摇),因而信息的客观性成为一个难题,当无数互相冲突的信息同时传来时,接受者也会倾向于相信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更接近的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越动听越真实,越美丽越真实,越契合接受者的神经症需求越真实。这种现象会导致新媒体下进行精神赋形的个体的理想自我更加虚妄,当然,它所带来的个体的无力感也就更加强烈。
其次,新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量与个体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反差也会导致个体的无力感。对于传统社会的空间分隔来说,人们处在自己的区域里较难了解到其他区域的生活细节,而新媒体造成的无数个体的自我呈现,导致理论上每个个体都可以对其他区域或群落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有细节支撑的观察。个体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他可以看到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无限丰富的信息展示,但其现实可能性却并未同比例增加,相对而言,他的现实可能性反而急剧缩小了。看到了丰富的世界,自己却被困守在狭小的牢狱里,失落与无力感的增加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网络空间里他人的展示还是他人的人设性展示,充满了被他人理想加工过的人造美丽,而个体无法洞察这种人设性,依据这种过度的美丽观察自己可感的现实,二者的对比就更加明显了。
再次,新媒体环境下的个体面对信息的主动感与其现实力量的对比也会带来个体的无力感。在面对物理空间时,人是处在环境之中的,是一个小的个体面对大的物理实体的过程,自身的有限性会被强烈地意识到。传统报纸、广播等媒体更主要的是借助符号来帮助受众面对虚拟的世界,也相对可以还原人在物理空间中相对较小的位置。电视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点,媒体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大的个体面对小的环境的假象,个体被凸显出来。但因为电视的制作需要巨大的经济支撑,往往被社会上的大型机构所垄断,只要它的合法性尚未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它的垄断性制造信息的权力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其发出的信息也被认为是客观、理性的代表,所以在还原视觉符号时会被这种力量的对比所修正,电视的时间方面的线性传播、频道有限等形式也会加深信息发布者的控制感、受众的被动感,这与受众的现实处境是相对应的。而且,总的说来,传统媒介的传播都是自上而下的、以一对多的传播方式,它会带来受众获得真理的幻象。新媒体则通过电脑屏幕、手机等更小的画面载体传播,扩大了接受者与信息的大小对比,加之非线性传播、海量选择性,以及与信息发布者的对等地位,甚至作为选择者、关注者而可能使某种信息成为公众可见的信息,因而成为了信息的裁决者。这就使人直接面对物理空间时的思考方式得到了颠覆性的改变:个体面对新媒体制造的“世界”处于裁决者的地位。这无疑是与大多数个体由其经济、阶层、地域、相貌等决定的真实处境不相对应的。加之,网络的匿名性导致的无差别发言权、随意发泄而较少会受到制约等情形,导致个体更难以接受现实里的真实处境。简言之,网络“现实”与现实的落差是巨大的,而这种巨大的落差无疑会带来巨大的无力感。
最后,新媒体环境下个体的网络化生存只能是精神符号化的生存,而缺少行动的支撑,当需要行动去解决问题的时候,网络的无能也会带来个体的无力感。笔者相对同意刘少杰的观点,网络空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虚拟空间,而是一种现实空间。*刘少杰:《网络空间的现实性、实践性与群体性》,《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2期。如果“虚拟”一词有任意虚构的意思的话,那么网络上的空间绝不是虚拟的,而是现实的,它是技术克服了信息传递的物理空间的延展性而形成的一种只要我们意识到技术的存在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测还原为物理空间的现实存在的一种中介性的技术空间。但它又不能说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现实空间,因为它无法带来主体主动传达的信息之外的副信息,只是一种技术模拟形成的符号中介,有信息无实体。而且目前新媒体环境下的符号传达只能模拟影像和声音,无法带来味觉、嗅觉和触觉,因而它还是某种程度上的虚拟空间。简言之,就知识、意见、情感等精神方面的传达来说,它具有现实性;就无实体无行动而言,它依然是虚拟的,一旦意见的表达、关注的累积都无法促成真正的行动主体采取行动时,它的虚拟性就暴露无遗了。而这种有精神无实体的窘境无疑也会带来个体的无力感。
三、精神共通感的消失与孤独感的加剧
传统媒介虽然饱受诟病,但它无疑具有一种统一性,可以提供公共的思考和交流平台,它是共同经历、共同事件、共同体验的制造者,进而可以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公共领域而言,传播、媒介的目标与价值体现在哪里?提供信息、生产现实、达成共识,这是既有新闻传播学理论的理解,它彰显了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生活以及民主政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孙玮、李梦颖:《 “可见性”:社会化媒体与公共领域——以占海特 “异地高考”事件为例》,《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2期。作为传统媒体的一个重要分支的大众传媒往往提供倾向于肉体享乐的信息和理念,它是以模糊阶差性为特征的无数平等而相似的众生的狂欢,其狂欢是普天同庆性的,有普泛的沟通性,也容易形成共通感。与此同时,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期待的新理性,也需要一个具有共通性的平台,所谓共同语言、共同规则也都需要一种共通的经验和认知为前提。虽然传统媒介带来的这种共通感是以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性的某种程度上的信息控制为基础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精神共通感的营造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正向功能。但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兴起,这种共通感在慢慢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孤独感的蔓延。
这种孤独感首先是由新媒体环境下的个体不得不以局部信息进行精神赋形所带来的。如前所述,传统媒体下的个体精神赋形是以拟态环境为信息基础的,它所承诺的是个体与整体的一种连接。也就是说,个体通过建立起这种对世界的认知、价值感和审美趣味等,建立了一种与世界整体的统一性,建立了自身与世界的和谐互动,个体行为有了充分的整体依据,同时也能以自己的行为推动整体的改变。其他个体依据的也是同样的信息,这就意味着自己与他人的相似性和与他人的联合。而新媒体环境下的个体精神赋形依据的是随机的甚至是人择的信息,它们只能是部分信息,代表的也只能是世界的局部,这也就意味着个体与世界的联系是不完善的。而且,自己依据世界的这个局部建立起来的对世界的认知、价值观、趣味与他人依据世界的那个局部建立起来的对世界的认知、价值观、趣味注定是不同的,那么,自己与他人的差异也就是无法避免的了,与他人的联合也无从说起,甚至是对抗的也未可知。因此,可以说,新媒体使传统媒体建立的共通感分裂了,个体从整体里疏离出来,个体与个体的合作感也消失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孤独感的产生。
其次,网络空间中群落间的对抗也会加强个体的孤独感。依据不同的局部信息产生的个体间的疏离不只是理论上的,它还现实地表现为不同网络群落间的疏离和对抗。如前所述,网络空间里的各个群落往往形成了群落内部强化认同、群落间走向疏离和对抗的倾向。传统媒体环境下个体间的价值观念的矛盾往往被拟态“真实”所压抑,而新媒体的发展则瓦解了原有的拟态,所以当这种矛盾被表面化后,矛盾的每一方都得到了群落内的认同,群落内更具代表性的极端信息使个体更加确证了自己的“正确”并走向极端,这无疑会加剧对其他群落的疏离甚至敌视。这种对其他群落的疏离和敌视会加强个体的孤独感。就此而言,网络群落本身就是若干局部从整体里疏离出来的存在,它的出现就意味着普天同庆感的衰落、孤独感的加强。如果自己所属的群落占据人数的绝大多数的话,会减轻这种孤独感,但网络空间中的群落往往分化得比较细碎,很难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而且,网络的连通使基于封闭的夜郎自大式的自我中心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异质性群落信息的大量传播使差异性时刻被意识到,也使自身的渺小感时刻涌现。不仅如此,争强好胜式的群落间的论辩、攻击等敌视行为会时刻触及这种对差异性和渺小性的感知,因而使孤独感如影随形。
最后,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化生存的个体精神上对网络群落的依赖、对物理居住空间的疏离也会加重其孤独感。对于传统社会的空间分隔来说,人们处在自己的区域里较难了解到其他区域的生活细节,对其他区域的情感相对漠然,而对自己居住的空间则形成物理—心理一体式的了解和依赖。居住空间对传统社会人的限制,导致个体为维持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而不得不屈从于政治、阶级等同一群体的意识形态,而表现出某种压抑性。但它同时又会营造温馨的连带感,而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现实上,群体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压抑是隐藏着的,而连带感则被刻意强调出来。就此而言,传统媒体下的人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是统一的。而且,个体除了自己居住的物理—心理空间外,也很少具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传统媒体下的个体与其居住的物理空间的关系往往是和谐共生的。“社会空间就成为具有共同属性的社会群体所组成的地域,并且地域内的群体具有相似的感知和强烈的区域认同感。地域与其他形式的空间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社会意识形成的主要工具之一。”*曾文、张小林:《社会空间的内涵与特征》,《城市问题》2015 年第 7 期。
新媒体的出现和个体对它的依赖,导致个体的心理空间更多地定位在自己选定的网络部落里,在那里寻求认同和安全感、归属感。这种情况下,个体的主观社会空间出现分裂,对自己选择的精神空间更加亲近,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居住空间则走向疏离。而且,网络空间里群落间的对抗相对酷烈,而寄托精神的网络群落与现实居住的物理空间往往是不一致的,现实的物理居住空间的邻居可能就是网络上的敌人,因而网络群落间的对抗越激烈,个体与其居住的物理空间的疏离感就越强烈。
不仅如此,虽然个体会在其网络群落里建立起归属感和安全感,但这种归属感和安全感是相对脆弱的。因为,一方面,网络群落里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缺少触觉等现实支撑,仅具有精神属性;另一方面,它受到了对现实居住空间的疏离甚至敌意的消解。因此,新媒体环境下个体的这种主观社会空间的分裂导致了个体在其身处其中的居住社区里的孤独感。
四、结语
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新媒体的崛起,个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增强了,这种声音无疑会带来个体参与塑造社会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它也给个体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心理特质:陷在局部信息里的个体塑造自己的精神时带来了与其现实的分裂;网络空间里的主体感的增强同时也会带来其现实力量感的缩减;个体与整体的分裂、群落与整体的分裂带来了个体的孤独。不可避免地,那种万众共同拥有的乌托邦等在慢慢消失,人的分裂性、短暂性、渺小性和差异性都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萨特所说的不堪自由的重负而放弃承担责任走向逃避?人们会逃到哪里去?娱乐至死吗?这恐怕是一个目前还无法回答的问题。但笔者想要强调:这些看起来比较负面的词汇最好能够以中性的心情去看待,它更应该是一种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批判。一方面,由“拟态环境”带来的完整、长久、和谐等美丽的描述本身在根本上说来带有欺骗和操纵的成分;另一方面,分裂、孤独、无力等也许是我们生存中无可逃避的部分。但毫无疑问,这些心理侧面并不能直接带给人幸福感。在笔者看来,就当下而言,对于新媒体的到来,我们还处在懵懂和摸索里,对它的正面和负面价值,还缺少充分的探讨,也没有构筑起理性的藩篱来收留和规约它。就这种状态而言,笔者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渡,面对一种新的技术与文化状态,从懵懂到建立理性是历史上的常态;但理性并不是势所必至的,而是需要靠人的努力来完成的。如果并不想沉陷在娱乐至死的浑噩状态里,首先就需要认真地去看到人自身的现实状态,然后重建人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弥合自身的分裂,建立群落间的和谐,在承认自身有限性的同时重拾自我的力量感。
(责任编辑:陆晓芳)
G124
A
1003-4145[2017]10-0061-06
2017-06-06
于小植(1978—),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雷亚平(1970—),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雷亚平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6YYA001)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基础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411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