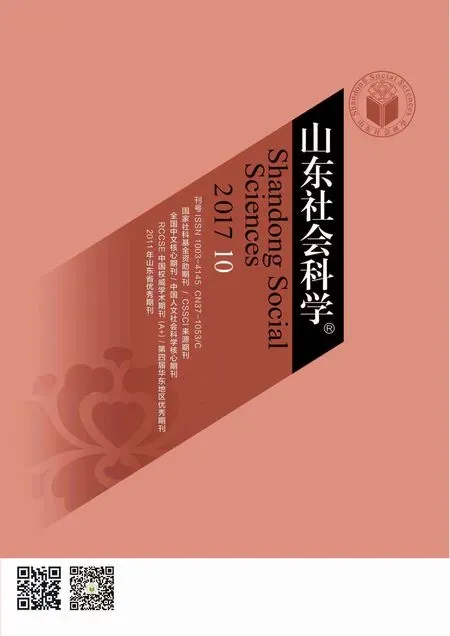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伦理导向
2017-02-24孙丽君
孙丽君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伦理导向
孙丽君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有着重要的商业价值,它以经典的解构为生产方向,通过戏仿、拼贴与荒诞的情节处理来解构特定的价值观念。在重构秩序的时代里,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较容易受到关注,但解构型文化产品容易导致对特定传统的质疑并进而影响文化体的价值观。在解构的过程中,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要特别注意经典、形象和价值观的选择。
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文化产业;价值观;文化共同体;经典
大众文化产品不仅是文化产业商业运作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大部分公众直接面对的文化载体,因此,相对于精英文化产品,由于大众文化产品的影响更为广泛,也由于大众文化产品的受众更易被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念所影响,我们要特别关注大众文化产品的伦理导向。在大众文化产品中,有一种特殊的类型,这一类型本身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与特定的社会思潮相结合,在当代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在商业化运作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是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随着商业上的成功及其影响力的扩大,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本身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价值体系的破坏。典型的如当红喜剧演员贾玲在《欢乐喜剧人》节目中对花木兰形象的解构,其所形成的伦理导向确实反映了当前我国大众文化产品在过度商业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这一作品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了作品本身,而指向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本文拟通过对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特点的解析,探讨这一类型产品在伦理导向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法。
一、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特点
大众文化产品是相对于精英文化产品而言的,它以传播大众文化为主要目标,“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①[德]西奥多·W·阿多诺:《文化工业述要》,赵勇、曹雅学译,《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大众文化并不追求创新,而是追求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可。由于大众文化产品的受众广泛,在当代新的信息技术的帮助下,极容易被产业化。可以说,大众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商业运作的核心产品。大众文化产品为取得广泛的关注度,必然会采取受众喜闻乐见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从生产方式上来讲,作为一种内容产业,大众文化产品在内容生产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大众化与商品化,其内容生产的各种变化趋势,都与这种性质在不同语境中的需求有关。在追求大众化与商品化的过程中,从构建价值观的角度来讲,大众文化产品有两种基本的生产方向:建构价值与解构价值,这两种价值生产方式形成了建构型与解构型两种大众文化产品。前者指那些以构建人物形象、倡导某种价值观念为导向的大众文化产品,后者则是以解构人物形象、破坏某种价值观念为导向的大众文化产品;前者的目的在于建构或强化某种观念,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解构或破坏某种观念。这两种大众文化产品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影响力,总体上来讲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特点包括下述两个方面:
(一)以解构经典的文化产品为方向
在人类的文化史中,产生了许多经典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因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广受人们的好评,并在世世代代的文化传播中形成了各民族文化体的共同记忆,某些文化产品甚至成了某一民族特殊的文化基因或代表形象,比如西方的《蒙娜·丽莎》、中国的《论语》等。这些文化产品通过自身的语言、形象和故事产生了不同的意蕴,并在构建某一民族特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经典的文化产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一些大众文化产品逐渐意识到经典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特殊商业价值。文化产业是以注意力为基础的产业类型,“注意力是企业或个人的真正货币”*[美]达文波特:《注意力经济》,谢波峰等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但是,在众声喧哗的当代,注意力同时也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对于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文化产品来讲,如何获取注意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经典的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基因,或者作为一种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文化结构,构成了营造注意力的重要手段。注意力经济的本性,决定了大众文化产品必须用充足的创新来吸引注意力。因此,经典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记忆,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是获取注意力的重要手段。
经典进入大众文化产品有两种方式:一是沿用经典的结构,即在经典结构的基础上运作一个新的故事,向经典致敬。好莱坞大部分商业大片所遵循的正是这一逻辑。这一生产方式也有着自身的优点与风险:其优点在于可快速唤起受众的记忆,大部分时间内运作风险较低;其风险在于创新性较差,适合于一些年轻观众和被规训的读者。但是,如果一个经典的结构被过度开发,必然导致观众对这些文化产品的厌倦。目前,由于观众对某些经典文化结构的过度熟悉,导致这种文化产品已经很难形成创新并吸引观众。好莱坞一些商业大片在北美票房的遇冷,已经显示了过度开发经典结构有可能导致的后果,这也是好莱坞商业大片寄希望于中国票房的原因。当前的中国观众完全了解好莱坞经典商业大片的结构尚需一定的时间;但是,可以想象的是,总有一天,中国观众也会像北美观众一样了解经典的结构。二是经典的解构。即用解构的方式来面对经典,解构经典的人物形象、经典的故事结构和经典的意义营造方式。在目前的语境中,对于注意力经济来讲,解构经典是一种重要的商业手段。首先,由于经典作为一种民族记忆,与经典有关的文化产品吸引了经典所处文化体中大部分人的关注。其次,对经典的解构可采用多种方式、多种视角,因而极易出新。如果说,经典的建构是一个不停地证明观众期待视野的过程;那么,经典的解构则是一个不断地打破观众期待视野的过程。这种对期待视野的打破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性、娱乐性和强烈的陌生化效果,这些都形成了文化产品强烈的吸引力,从而为这些文化产品的产业化运作提供了前提与保证。再次,对经典的解构只需观念或形式上的创新,对于文化产品来讲,其生产成本普遍低于沿用经典结构的文化产品,可以说,成本相对较低,技术要求相对较低,而吸引受众的能力相对较强,这就变相地降低了文化产业的经济风险。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当前以经典解构为方向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勃兴。
(二)解构经典的手段
总体上讲,建构型文化产品通过道德天平中的人物、完整连贯的线性情节结构、激烈的矛盾冲突和闭合式结局等方法来倡导一种特定的价值观。*何群:《文化生产及产品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5页。自“五四运动”以来,尽管我国文化价值观念的建设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过程之中,但是,从我国古代到当代文化的建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宏大叙事。我国主流的文化都强调民族性、集体性的“大我”,认可文化产品为民族代言的价值建构模式。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讲,这一模式作为“民族的脊梁”为我国文化的构建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追求商业价值和娱乐化的文化产业来讲,这种正面的价值建构方式有着自身的问题:那就是重视英雄、忽视小人物,重视民族性“大我”、忽视个体化存在等。文化产业的商业化追求,要求大众性文化产品必须能表达大众的心理需求,表达大众的梦想。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大众梦想的表述,使得以解构为方向的大众文化产品有了广阔的市场。
在上述文化模式中,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解构手段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人物形象的戏仿性。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大部分以小人物为主,既使出现了大人物,也注意开发这些大人物身上的小人物气息。通过小人物对大人物的戏仿,即成功地叙述了小人物的故事,获取最大限度的关注度,同时也通过戏仿式的手法,通过大人物的小人物化和小人物的逻辑,确证了大众个体的存在感,获取大众好感,形成大众文化产品商业开发的基础。第二是拼贴式的文本风格和荒诞的情节处理方式。与建构型文化产品线性的故事发展线索不同,解构型文化产品不追求故事的平稳叙述,而是追求解构过程中的陌生化手段及其所形成的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因其出人意料,这种喜剧效果构成了一次次的文化创新,迎合了大众文化产品的创新需求。第三是对经典价值观念的解构。建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目的是通过对正面或进步的歌颂或对反面和落后的讽刺,证明或建构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其人物形象的选择、线性的叙事方式等都是以这一目标为旨归的。但是,解构型文化产品则追求对经典价值观念的解构效应,以一种标新立异、卓而不群的方式彰显娱乐化时代的个人存在,“传统的喜剧是把正常的生活逻辑与人情事理作为衡量标准, 该标准的美好、崇高、善良、正义、真理等积极的一面得到肯定, 而与之对立相反的一面则以讽刺、搞笑的方式给予。而对以周星驰为代表的喜剧, 它颠覆和解构的程度比传统喜剧深, 它要尽可能拆毁一切等级制度和价值秩序, 即使对于正义、真理、崇高的东西也持保留的态度, 至少不会正面去肯定它。”*包兆会:《无厘头文化中喜剧的笑与中国式后现代》,《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通过对价值观的解构,文化产品所具有的从上而下的宣教作用被打破,大众们获得了一种“众声喧哗”的狂欢化效果。经过产业化的运作,狂欢化效果有效地推动了注意力的获取和产品的商业价值。
如果说,建构型文化产品在面对经典时,采取一种“向经典致敬”的态度,经典是模仿的对象,是一种难以超越的文化奇迹。那么,解构型文化产品面对经典的态度,则是一种平等的态度,经典只是商业化运作的手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下,解构型文化产品直接以解构经典中存在的诸多形象或观念为目标,以获取受众的无限认可。从这一角度来讲,对于经典所倡导的观念来讲,解构型文化产品天然地具有某种破坏作用。
二、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当前语境中,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这也是这类产品繁荣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及其对文化产品的不同需求,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与社会需求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影响了这一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也影响了一个文化体正常的价值建构过程。
(一)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繁荣的社会条件
一般来讲,人类文化体的建构,大体上都会经历两个阶段:建构阶段与解构阶段。目前,世界上大部分文化体都有着自己明确的传统,正常情况下,生活在这个传统中的人们都认可这个传统,遵守这个传统的约定。当然,时代的发展也会冲击这个传统中的一些即有约定。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一些约定被质疑,新的约定被认可,形成人类文化共同体不断发展的过程。大众文化产品的繁荣与衰落,只有放在文化体的建构过程中,才能得到根本的诠释。在这方面,晚年的伽达默尔曾将人类文化体的建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混沌、已在和混沌向已在的变化过程。在他看来,一个文化体的传统构成了它的已在,而一些新的时代动向促使已在重新转化为混沌并在新的定向中形成新的传统。在他看来,语言传播向图像传播转化就是一种新的时代动向并必然导致新的传统出现。当然,将一个已定的传统重新变成混沌的方式有多种,伽达默尔只是提到了一种。在我国,当我们提出要打破一个旧时代、产生一个新时代的需求时,就意味着已在有可能进入混沌并形成一种新的传统。
在上述新的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实际是一个被时代所选择的过程,生产者、传播者和读者都是处于时代中的一员,受到的是时代的支配,决定不了文化产品能否被时代所认可。从这一角度来讲,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也只有放在时代变化的趋势中,才能得以说明。从上文文化体的建构过程中可以看出,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所适应的正是旧传统被打破、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由于旧有的传统遭到质疑,那些质疑这些传统的作品,适应了新的时代,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而一旦新的传统被确认,这些以质疑而得到关注的作品,必然会因其与时代精神的不合拍而被抛弃。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与时代的关系,也变相说明了无厘头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解释了当前中西方大众文化产品面对解构的态度。当然,由于传统由许多层面组成,这些不同的层面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质疑并不相同,这就形成了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广阔的运作空间。但总体上讲,如果某个约定的传统并没有进入广泛的质疑过程,或者说社会上还坚守这一约定,强行通过大众文化产品对这一约定进行解构,其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并不会太高,反而会形成巨大的文化风险并进而影响其传播与商业价值。*参见方慧、韩云双:《论影视产业开放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威胁》,《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年第5期。
(二 )解构的破坏性与传统重构之间的矛盾
解构型文化产品以其对传统的质疑或破坏作为重要的运作方向,我们上文所提到的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面对经典的态度与生产方式,都指明了其以对特定文化传统的破坏为方向。但是,对于所有的文化体来讲,最为关键的,并不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建立一个新世界。人们不可能永远生活于混沌或虚无之中,而解构型文化产品对已在秩序的作用,正是将已在重新推倒为混沌状态。对于人类来讲,混沌状态正是一种虚无。这一状态,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特定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并不具永久性。因此,所有的解构型文化产品,都必然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解构之后何为、破坏之后如何建设的问题。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当人们将已在重新拉回到混沌,人们拉回已在的方式必然会形成一种新定向,这一定向将人们导向新的传统的形成过程。正是由于解构型文化产品中所存在的新的定向,解构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变相的建构过程。尤其在大众性文化产品中,由于要考虑到大众接受的可能性,它不可能解构所有的约定,在解构的同时也会形成新的建构方向。“周星驰电影中小人物‘幽默的笑’,所传递的就是他们的挣扎与拯救,以及他们对某种正面的人生信念和人性价值的肯定,里面有些庄严和高尚的东西。《大话西游》尽管搞笑,但《大话西游》最终没有彻底解构理想和爱情。”*包兆会:《无厘头文化中喜剧的笑与中国式后现代》,《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解构是另一种形式的建构。如何引领这个建构的方向,仍是解构型文化产品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建设中,如何在解构型文化产品中建构一个新的伦理规范,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三、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走出解构困境的对策
在当前语境下,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因其对经典的解构、对大众的关注而具有重要的商业运作空间,但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也因其质疑的态度与破坏的冲动,与一些传统的约定冲突,甚至影响了社会伦理的导向。因此,如何在符合社会伦理导向的前提下开发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是摆在文化生产者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对此问题,历史上已有许多先例,比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堂吉诃德》《洛丽塔》等,影视史上的《大话西游》《武林外传》等,这些产品甚至已经形成了解构型文化产品的经典,构成一种新的文化生产范式,这为我们走出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困境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经典的选择
解构型文化产品必然是以解构某些特定的对象为前提的,这是它们关注经典的根本动因。但是,选取什么样的经典进行解构,满足大众文化产品的文化需求,却考验了生产者的智慧。纵观那些成功的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在经典的选择上都遵循着下述两个原则:
首先,都十分关注经典的影响。如果一个作品还没有成为经典而对这个作品强行解构,不仅会影响这个作品的文化影响力,同样也不能吸引注意力而影响其产业价值。纵观近几年我国以解构经典为导向的电视小品节目,可以看出,它们所解构的,几乎都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名作,比如《新白娘子传奇》《西游记》等。只有当某个经典经历了充足传播以后,人们才有可能形成明确的期待视野,解构型文化产品才有可能通过打破这种期待视野形成创新。可以看出,对象作品经过广泛的传播形成经典,是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前提。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很少进行跨文化的经典解构,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有,也一定也要等到这个经典有了充足的传播之后才进行。周星驰的《大内密探零零发》,产生于《007》被我国观众广泛熟悉之后。只有这样,解构型文化产品才有广阔的市场运作空间。
其次,都十分注意时代的变化,关注文化产品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吻合性。如果没有骑士文学的泛滥,没有时代为人们对这种文学形式进行反思提供的社会条件,《堂吉诃德》就不会成为一个经典的解构型文化产品。同样的,《大话西游》的传播过程更是说明了解构型作品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大话西游》上映时票房的惨败与其后作品所受到的热棒,不仅出乎创作者的意料,也出乎专业评论人士的意料。它不仅是一种观念被时代所认可的标志,也暗示了一个大众文化产品对商业运作空间和时间的要求。
(二)形象的选择
大众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是故事与形象。根据故事的真伪,形象可分为真实的形象与虚构的形象。在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对形象的解构尤为重要。如何选择我们要解构的形象,上述解构型文化产品也提供了一部分经验。
首先,如果要在真实与虚构的形象中作出选择,要尽量选择那些虚构的文化形象。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解构对文化传统的破坏力,同时也论证了解构的目标不应止于破坏,而是建构。纵观解构型文化产品的历史,可以看出,大部分成功的解构型文化产品,都首选虚构的人物形象进行解构,因其虚构,观众在解构的狂欢中能意识到这是对虚构的解构,而非对现实或历史的解构。这样,解构型文化产品就能使自己的影响限于虚构的艺术天地而非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减轻解构行为对即定文化传统的破坏。这也是为什么《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之类的作品被频频解构并不断衍生为新的文化产品的原因。我们可以解构嫦娥、后羿,解构孙悟空和唐僧,解构《上海滩》和武侠经典,就在于他们本身就是虚构的(人们心目的唐僧已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但要解构真实的历史人物,由于涉及文化传统的延续,其难度比对虚构形象的解构要大得多,这也是解构行为首先在文学艺术中应用的原因之一。当前,人们对花木兰形象的解构之所以产生了诸多的争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花木兰这一形象的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分歧。而这一分歧,直接影响了人们赋予花木兰形象的象征意义。当然,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也曾解构过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形象。纵观这些形象,可以发现:这些进入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的真实历史形象,经历了严格的挑选和长时间的历史虚化。比如,人们解构一些已得到定论的负面人物形象,由于对其形象的解构本身就是建构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导向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人们也解构一些长时间被文学艺术作品所虚化的真实的人物形象,如唐伯虎,经过长时间的文学化与艺术化描述,已经生成为一个虚化的艺术形象,或者说,在大众心中已经拥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特质,这些特质为解构这一形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条件,对这些形象的解构也并不会真正地挑战文化共同体核心的价值观念。
(三)价值观的选择
解构是特殊的建构,这句话不仅体现在对经典和形象的选择上,也体现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所有的故事,都涉及两个方面:事件和对事件的讲述。前者是某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本身,而后者则是讲述这一事情。任何讲述,都是有着特定目的的讲述。现象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对事件的选择,都是在意识意向性支配下的选择,因而任何故事在讲述之前,必然都会受到讲述者意识意向性的影响。讲述者为什么会讲述这个故事?他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什么样的意义或价值?都会或多或少地体现在这个故事之中。对于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解构者的价值观和他通过解构经典所要传达的意蕴,仍然会支配着他的讲述方式。解构者的方向是解构经典,在戏仿经典的过程中解构经典所构建的核心价值。众所周知,要构建一个文化体,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而摧毁它,过程就变得非常简单。比如我们对英雄的崇拜,要构建这种崇拜,需要许多文化产品的熏陶与感染;而要破坏它,只需解构其中一个形象即可。这就要求我们在解构经典过程中,对解构的视角、解构的价值观进行谨慎的判断。
要进行这种谨慎的判断,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所要解构对象本身的价值观并判断这一价值观在当前文化体中的认可情况。如果所要解构的对象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进步的观念,那么,对这种进步观念的戏仿或解构就会破坏这一文化体本身。当然,不同人群对某种观念的认可不同,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观念之间本身就充满了对峙,而观念之间的对峙本身也是文化产品生产与传播接受的客观背景,这种客观背景本身就是区分文化产品受众的一种约束性条件。某个文化体的形成,必然有这个文化体不同于别的文化体的根本属性,没有这种根本属性,这个文化体就不可能独立于别的文化体。在这个方面,某些经典构造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对这些文化基因的解构,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破坏这些文化基因,从而激起这个文化体的共同反抗。从这一角度来讲,某些形象,对某个文化体的影响巨大,其价值观代表了这一文化体的根本倾向,而在具体的现实社会里,这一价值观仍有其自身的理性,那么,对这一价值观的解构必然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争议。因此,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必须明白解构的限度,避免解构那些根本的价值倾向。不然的话,不仅使其文化产品形成巨大的文化风险,进而使其失去商业运作的合理空间;从长远的角度讲,更容易形成历史虚无主义,从而变相地剥夺了历史的合理解释以及某一文化体的根本特征。
总之,大众文化产品要追求的目标,仍隶属于文化产业的范围之内,那就是通过内容生产形成受众的意蕴,通过形象说出真实与必然,形成读者强烈的共鸣,扩大受众的群体。这是文化产业商业进程的根本条件。而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仍需服从文化产业的这一根本追求。通过解构的方式,建构并维护一个文化共同体认可的真、善、美,仍是这一类型的文化产品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只有满足了这一根本目标,解构型大众文化产品才有获取商业利润的保证。
(责任编辑:陆晓芳)
G124
A
1003-4145[2017]10-0050-05
2016-09-20
孙丽君(1969—),女,山东宁阳人,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教授、硕导,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生产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现象学视野中生态美学的方法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BZW0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