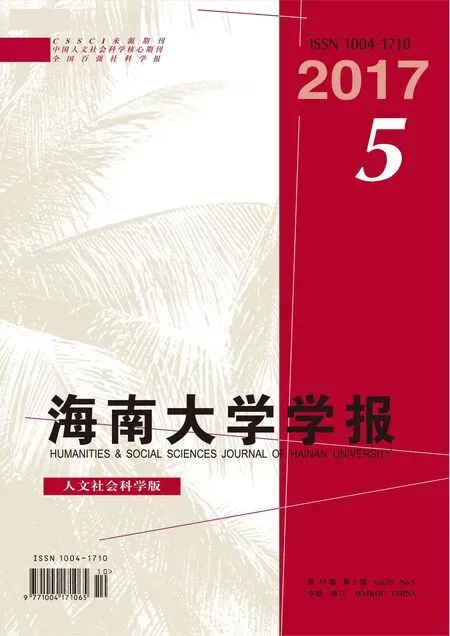现代性视域下的乌托邦图绘
2017-02-24高信奇
高信奇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9)
现代性视域下的乌托邦图绘
高信奇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9)
乌托邦作为一种怀揣着梦想、超越现实的人类精神,一直蕴含于西方文化之中,并存在着“古今”之别。与传统乌托邦相观照,现代乌托邦具有未来时间观念和进步历史意识、现世性和世俗性、可能性和可建设性等特质。在类型学上,现代乌托邦呈现出文学型、法典或理论型、共同体(社区、公社)实验型等诸多面向。现代乌托邦直面近代自由主义之弊,倡导整体主义,追求一种共同体生活。
现代乌托邦;古今之别;诸类型;共同体生活
在人类建设美好生活的诸多方案中,一直存在着乌托邦的思想谱系与实践冲动。尤其在现代性*现代性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仅从时间维度来看,如果将西方历史区分为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现代三大时期来看,现代性是指中世纪之后至今的历史时期。进程中,乌托邦呈现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质与实践特点,并对现代思想构建和现实社会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梳理和廓清现代乌托邦的得与失,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作为人类美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
一、乌托邦的“古”与“今”:乌托邦具有唯一不变的传统吗?
从词源学来看,“乌托邦”一词,最早来自于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成名之作《乌托邦》。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乌托邦往往具有一定的暧昧性:一方面,有人将乌托邦解读为一种空想的、难以实现的“乌有之乡”;另一方面,有人则赋予乌托邦以美好地方(人间福地)的想象。其实,理解乌托邦最为重要的是,其蕴含着人们不满现实、企图超越现实、建设美好新世界的人类精神。尽管这种精神直到近代才获得“乌托邦”的名号,然而这种乌托邦精神却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在古代,乌托邦精神有着两种不同的起源,分别体现出人们对现实生存社会的不满,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共同向往,然而由于民族与文化的迥异,两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乌托邦路向与模式。一种起源,可以在犹太教—基督教中找到乌托邦元素与踪影。美国乌托邦研究专家乔·奥·赫茨勒将其追踪到纪元前8世纪希伯来先知们的预言,以及后续的犹太教弥赛亚预言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思想。蕴涵于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中的乌托邦精神是一种宗教—伦理性的乌托邦。这种路向的乌托邦,从道德伦理切入,企图利用救世主等神秘力量、诉诸神权政制、重建人际关系来达到美好的理想世界。“先知们这种乌托邦思想的要点在于,它不仅要求建立正常的人类关系,而且要求建立超人类、超尘世、神权政治的关系。……变革不仅是伦理性的,而且是宗教—伦理性的。”*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另一种乌托邦精神,缘起柏拉图在《理想国》基于理想城市模式而畅想出来的美好社会,即“理想共和国”,这是一种理性理念式乌托邦。理性理念路向的乌托邦是建立在哲学理念基础上,以理性为原则,以形而上学为形式,企图设计出一切都符合正义与善的要求的理想城邦模式。
无论是宗教—伦理性的、还是理性理念式的乌托邦精神一直隐匿于西方文化之中,并在传承中不断演绎与变化。当时间穿梭过古代和中世纪来到了近代,现代乌托邦观念开始在西方文化中肇兴,并呈现高涨之势。现代乌托邦从16世纪发端,蔓延至今,形成了连绵不断的现代乌托邦潮流与思想谱系。其实,对于乌托邦的“古今”之辩*对于乌托邦的存在,不同的学者按照不同标识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英国乌托邦研究专家克里斯安·库玛的观点,乌托邦是现代性的产物,因为,乌托邦的目标是人的理想社会,其核心在于其根本的世俗性和反宗教性。与此相反,赫茨勒则认为乌托邦一般蕴含在西方自古至今的文化中,甚至于在希伯来先知们的思想中就蕴藏着乌托邦思想,并且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传承。,目前依然没有取得共识。按照英国乌托邦研究专家克里斯安·库玛的观点,前现代的乌托邦理念本身不是乌托邦,现代乌托邦才是真正的乌托邦。古代人们对黄金国、香格里拉、天堂等美好地方的想象,其实不是严格意思上的乌托邦,“我们应把社会的理想之城与基督教的千年王国看作史前史或无意识的乌托邦。它们是潜藏的元素,给乌托邦提供了许多目的与动力。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乌托邦。”*约翰·吕森:《思考乌托邦》,张文涛,甄小东,王邵励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争论仍在继续。然而现代性生活中存在着乌托邦思想与实践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现代乌托邦的生成,得益众多,其中古希腊乌托邦的理性因素与犹太教—基督教乌托邦中历史意识因素的融合,是现代乌托邦产生的智识条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是现代乌托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理性主义、科学技术和实证主义的肇兴,是现代乌托邦产生的理论助产士。现代乌托邦,与传统乌托邦元素有着勾连,但也呈现出巨大的区隔,实现了在传承中蜕变与发展,主要表现为:
(一)现代乌托邦蕴含着未来的时间观念与进步的历史意识
与古希腊理念乌托邦不同,现代乌托邦思想中渗透着未来的时间观念和进步的历史意识。对古希腊人来说,他们具有清晰的空间观念而没有明确的未来时间观念,或者说,对希腊人来说,时间主要体现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时间,即“时间是计算前后出现的运动得到的所计之数”*亚里斯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2页。,因此,古代乌托邦的实现往往是寄托于某个空间(岛国、山林,或者哲学家做王抑或王做哲学家的城邦),而很少谈及实现的时间问题。古代人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往往难以寻觅到具体实现的时间,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古代人不具有进步的历史意识,“柏拉图从未有完全实现这一理想的念头。这样一种想法不可能为当时的人所接受,因为它意味着要具有不断进步的眼光,……进步的思想是现代的而不是古代的观念。在古代,人们对古老的事物只有模糊的概念,那时还没有历史哲学。”*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第101页。另一方面,从历史观来看,古希腊人大都坚持退化历史观或循环论历史观,因此古希腊文化中对乌托邦谋划不在遥远的未来,而在于逝去的过往,如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黄金时代是赫西俄德所向往的乌托邦,因此这种乌托邦往往是“向后看的乌托邦”。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从过去向未来一维流逝的现代时间意识的形成,相应产生了进步观念*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隆克认为人类持有进步观念需要具备五个约束性条件: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变化、对过去持批判的态度、普遍相信人类理性及其驾驭变化的能力、世俗的环境、不相信失去的乐园以及周期性、循环历史观,而这五个先决条件只有在启蒙运动时期才都具备。因为,他认为在18世纪启蒙运动以前,进步的观念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也有诸如路德维格·爱德尔斯坦和E·R·杜德斯认为,在古代就存在人类进步的历史观点,但是由于古代社会将地球生命视为神的意志,以及循环历史观,因此进步观念在古代并未成为主流观念。参阅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当进步与时间意识走进历史就形成了进步历史观。进步历史观,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性、人性可以趋向完美,相信科学的进步有可能将乌托邦由理想化为现实。正是基于这种“新优于旧、今胜于昔、未来比过去更美好”的进步历史哲学,人们把现代乌托邦的实现寄托于未来、在不远的前方,因此,现代乌托邦获得一种“向前看的乌托邦”特质,“进步观念在17世纪晚期与18世纪早期的胜利,使欧洲思想释放出决定性的现世性,乌托邦也是如此。人们逐步按照时间而不是按照空间的方式来对待乌托邦。乌托邦不是在某个远处的岛上,也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山谷,而是在将来,随着利用人类社会必要发展对人类知识产生的动力而出现。”*约翰·吕森:《思考乌托邦》,第21页。
(二)现代乌托邦的现世性或世俗性
一般来说,乌托邦的设计理念不同,其实现形式也往往有别。犹太教—基督教式乌托邦诉诸神学教义对其进行理论论证与制度设计,因此,往往此类理想社会的实现通常被放置于天堂、天国之类的地方,故而这类乌托邦带有浓烈的超验与神秘的底色,如犹太教中伊甸园故事隐含着人类的乐园不可能在人间实现,而只能寄希望于来世与天堂。古希腊理念乌托邦则援用哲学玄思与逻辑推演,实质属于理念层面的东西,故而其往往只是人们形而上思辨的鹄的,美好乌托邦生活则成为哲学沉思的对象。由是观之,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式乌托邦,还是古希腊理念式乌托邦,都具有超越现实的特点。自近代开始,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理性主义占据了理论的制高点,现代性进程实质表现为理性化的规训,人类生活世界发生了如韦伯所言说的“现代世界之祛魅”或熊彼特所研判的“世界观的毁灭”,并向世俗化、现世性转变:在价值观领域,企图对世界进行统摄的一体化宗教解体了,宗教由原先无处不在退缩到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祛除宗教色彩,并出现了价值多元与诸神之争;在思想领域,传统形而上的思辨哲学遭到拒斥,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等成为思想理论的风向标;在社会领域,出现了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翻转,政治与宗教发生了分离,公共生活领域横空出世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经济生活领域,追逐财富丰腴,享受物质成为现代人诉求的重要对象。与此相适应,现代乌托邦将目光转向现实世界,关怀世俗的生活世界,开始了乌托邦的世俗化旅程,“传统的乌托邦观念随之走向消解,代之而起的是典型的现代性的世俗性社会发展理念,即追求此生此世的现实幸福,相信只要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达,社会就越来越趋于完善完满”*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这种世俗化、现实性乌托邦呈现出以下的症候:一是从实现空间来看,现代乌托邦将理想社会的实现不再寄托于上帝之城、遥远岛国,而是安置于现实的生活世界,甚至就在我们城市的一隅或乡村的一方。库玛说道:“宗教与乌托邦在原则上有基本矛盾……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的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张隆溪:《乌托邦:观念与实践》,《读书》1998年第12期,第12页。二是从蕴涵的文化精神来看,现代乌托邦具有厚重的世俗文化气质,体现为对凡人庸常生存的关照与肯定,尤其表现在肇始于19世纪的现代乌托邦共同体(community,也译为“社区”“公社”“社群”)实验区里,大多数制度规定与日常事务都是满足平凡卑微的人们庸常琐碎的寻常生活。
(三)现代乌托邦的可能性与可建设性
如果说,前现代的乌托邦是人为想象的成果,这种理想乌托邦生活的实现是寄托于人们的某次偶遇、奇遇或梦境,是完全建立在形而上的玄想或神学超验想象之上的,没有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实现条件,是可欲却不可行的,因此,往往被视为虚妄与无法实现的。现代乌托邦虽然也要借助想象力,但是这种想象力被勘定了边界。这种想象力是基于现实社会环境、科学技术条件而展开想象的,是在对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预测的基础上设想,所以不仅是可欲而且是可行的、可能的。“自一开始,在莫尔的理性而有约束的乌托邦幻境中,乌托邦就带有与当前现实步调一致的某种清醒与希望。……但它仍旧是可能性的王国——根据手边人类与社会的物质是可能的。”*约翰·吕森:《思考乌托邦》,第17页。与传统乌托邦不同,现代乌托邦不仅有着思想层面的设计,18世纪末以后,现代乌托邦告别文学式想象和思想的玄想,开始付诸大量的政制变革、社会实践,着手尝试建构美好新世界,开启了现代乌托邦的建设之旅。这些现代乌托邦政制变革或社会实践,一方面表现为声势浩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浪潮,另一方面表现为19世纪、甚至20世纪出现的大量社会改革和社会重建的方案与实验,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进行了一些乌托邦共同体实验区(移民区)建设。
二、乌托邦的类型学:现代乌托邦的诸面向
从其观念演变、涉及领域和呈现方式来看,现代乌托邦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形成了现代乌托邦亮丽多姿的图绘。鉴于乌托邦内涵的多义性、涉及主题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分类标准,现代乌托邦表现出不同的类型:从时间分期来看,主要有早期乌托邦、中期乌托邦和晚期乌托邦;从研究主题来看,有建筑乌托邦、市场乌托邦、审美乌托邦、技术乌托邦等;从国别来看,有英国乌托邦、法国乌托邦、俄国乌托邦,等等,不一而足。本文主要立足于现代乌托邦思想的呈现形式与载体的视角,梳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较为重要的乌托邦类型。
(一)文学型乌托邦
现代乌托邦首先是以小说、游记样式表现出来的“文学乌托邦”或者乌托邦小说,如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等等。这些文学型乌托邦的创作者大多是一些人文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他们偏爱运用散文、小说为载体,以故事的叙事方式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与历史性事实写作不同,文学型乌托邦偏爱于对美好生活的虚构或浪漫的想象;与写实主义小说不同,它们更侧重对看似不可能或者至少非常不可能生活的描绘与设计。从总体来看,文学型乌托邦尽管有虚构的成分,免不了一些脱离现实的想象,但其寓意在于对现实的不满,企图寻觅一种美好生活的愿景。实际上,以文学体裁表现出来的乌托邦,蕴涵着一种超越精神,一种对未来的寄托与希冀。因此,乌托邦成了“希望”的代名词,德国哲学家布洛赫就将“乌托邦哲学”称之为“希望哲学”,并认为希望不仅是人的一种意识特征,而且也是一种本体论现象。人的本质同希望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希望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人类需要,是人的本质的结构。
(二)法典或理论型乌托邦
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乌托邦似乎不再是无法实现的想象,也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即将来临的可能事件,因此,现代乌托邦在做了短暂的文学式旅行之后,便出现了以法典或理论形态呈现出来的乌托邦。法典型乌托邦,一般诉诸自然法理论,以法律条文形式对理想乌托邦制度作出详尽的设计与规定,如马布利的《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和《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德萨米的《公有法典》等;理论型乌托邦,则摒弃法典型乌托邦的刻板法律条文,援用启蒙思想,注重以理论论证形式来建构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思想体系,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路易·勃朗等乌托邦主义者的思想。究其根源,在近代理性主义、实证科学、进化论等强大现代性知识推动下,乌托邦主义者撇开了文学浪漫的想象,从改造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模式等层面来论证乌托邦的可欲性与可行性,并将其铆钉于不远的将来,这种类型乌托邦往往也被称为“大写的乌托邦” 或者“大范围的乌托邦(Utopia write big)”*如果将以莫尔、圣西门为代表的乌托邦主义者醉心于对整个现代社会做总体上改造的乌托邦称为大写乌托邦的话,那么,以欧文、傅立叶学派、伊加利亚学派的乌托邦共同体实验则在有限空间内实现的乌托邦,就是一种小写的乌托邦。。大写的乌托邦,主要以某些理性原则对现存社会弊端进行批判、改造现存政制,并对未来社会作总体性设计或建构,“改革与重建的方案取代了它的位置,它们利用新的社会科学,以严格理性的与科学的事业方式给乌托邦指出了一条道路。”*约翰·吕森:《思考乌托邦》,第21页。其实,这种大写的乌托邦在《乌托邦》中早已若隐若现。《乌托邦》虽然以虚构的文学样式来表达,但它也暗含着一些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莫尔笔下的乌托邦是一个废除了财产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往后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张隆溪:《乌托邦:观念与实践》,《读书》1998年第12期,第12页。大写的乌托邦在19世纪乌托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圣西门企图以科技、现代组织和专家治国,欧文以互助合作,傅立叶以生产与消费联合的共同体等方式来实现对现代社会的全面改造。
(三)共同体实验型乌托邦
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乌托邦从田园牧歌、思想改造开始进入实践操作层面,自19世纪起,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大量乌托邦共同体(移民区、公社)实验热潮。这些乌托邦共同体实验,从类型和形式上来看,呈现出从欧文及其追随者尝试建设新和谐村、傅立叶学派的乌托邦公社实验、卡贝门徒的伊加利亚运动,到各类宗教公社实验;从工业工厂实验到农业实验;从生产合作实验到消费合作实验。从时间上来看,从19世纪开始,一直绵延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乌托邦共同体实验运动。从规模来看,这些乌托邦实验区往往规模不大,都是在一个小型区域,企图建立一种关系亲密的、家庭般的、自足式的共同体,因此一般被称为“小写的乌托邦“(Utopia write small)。“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这一理想的追求者,在一个引领人或者预言家的指挥下,坚持不懈地进行尝试,建立了数百个小规模的社团。”*让-克里斯蒂安·珀蒂亚斯:《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梁志雯,周铁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这些实验者怀揣着梦想,告别以暴力革命和自然演进的方式建立美好家园和幸福生活,直接踏上心中理想天地的找寻之路,奔赴一个个乌托邦共同体实验区。从数量来看,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大量的乌托邦试验区(尽管有的规模不大)。按照美国学者希尔奎特的说法,“根据我们对这些著者的片段叙述的估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上世纪美国各地存在好几百个公社,并且先后参加实验的人数有几十万人。”*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朱立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页。“单是从数量来看,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十余年时间在美国共出现了1万多个乌托邦组织。其中,在加州,美国西海岸乌托邦社群的数量就达数千之中。”*谢江平:《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这些小型的乌托邦共同体实验,指导思想各异,既有主张平等、自治和集体主义原则的,也有倡导等级、崇尚权威或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有严格一夫一妻制的,也有集体婚制的;共同体成员数量多寡不一,有的几十人,有的多达几千人,而且成员可以自愿自由地进出;共同体实验区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寿命短的甚至只有几个月,长的则有几年、几十年甚至二百年的历史。
三、现代乌托邦生活:回归共同体生活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对人类群体生活模式区隔出共同体与(市民)社会两种类型。他认为,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近的;共同体自古有之,社会则产生于现代。易言之,在现代以前,人类群体性生活方式主要是共同体模式。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它是在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紧密联系起来的有机体。从特质上来看,共同体以内在的共同的情感为纽带,包括着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基本形式。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来看,共同体主义奉行整体主义原则,强调共同体优先于个人,没有共同体,就没有个人安身立命之地;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实现的保障,没有共同体利益,个人利益也就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在现代性进程中,伴随着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传统共同体遭到颠覆,共同体类型的生活方式逐渐被社会类型的生活方式所代替,现代社会开始出场。滕尼斯认为:“社会则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个人预计共同实现某一种特定的目的会于己有利,因而聚合在一起共同行动。”*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2页。也就是说,与共同体以情感友情为纽带不同,现代社会是以外在的利益关系作为纽带,是一种为了维护和满足个人私利为目的的互利合作联合体。这种社会联合体是人工制品,是一种机械的聚合。这种由个人私利主导的现代社会,在政治哲学修辞中往往赋予另一称谓,即市民社会*作为与共同体相异质的现代社会,有着不同的称谓:古典政治经济学者们称之为市场型社会,马克斯·韦伯称之为世俗社会,马克思主义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市民社会性质的认知,黑格尔给出了最为深刻的阐释:“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郭台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现代(市民)社会的肇兴得益于自由主义的降生,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群体性生活改造的结果。自近代以降,自由主义及其推崇的个人主义,无论在思想智识上还是在具体政制设计上都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设计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并促成了人类群体性生活方式的古今转换: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展开,是共同体逝去和市民社会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利益得到高扬而共同利益不断受到贬损,人际关系从休戚与共的团结与合作不断走向紧张与对抗;同时也是个体对群体高度依赖逐渐走向个体化、自主独立和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却失去了归属感和安全感,并变得越来越孤独,“经过凸显个人主义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个体逐渐被迫从‘共同体’中剥离出来而进入一种以个体为轴心的‘社会’并成为用一种契约方式重构社会规范、政治制度和组织行为的原点。”*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53页。马克思曾把这一历史过程,称之为是“一个产生孤立的个人”的时代。于是,西方现代性陷入一种悖论之中:远离共同体的现代人,在得到梦寐以求的自由和自主的同时,又要企图逃避自由,重新回归共同体生活。对于个体而言,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字眼,也是个赋予人们有着太多想象与向往的词汇。对于共同体的渴望和追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亚里士多德曾就城邦共同体生活说道:“凡隔离而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袛。”*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页。言下之意,每个公民个体都无法脱离城邦共同体而生活。之后,不同思想家或不同社会思潮为构建不同模式的共同体生活作出了智力努力,现代乌托邦共同体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种。现代乌托邦倡导的共同体(公社、社区)生活,企图消解自由主义现代性和市民社会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矫正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失衡,重建人与人之间健康的社会联系,寻找现代人可以安身立命的归属地,为现代人安置一个温暖的空间。具体理论主张体现为:
(一)重建共同体式的共同的善(common goods)
权利优先于善,还是善优先于权利,是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争论的焦点。作为现代自由主义核心的个人主义,偏爱个体权利与个人利益,贬低共同的善(公共利益),尤其是自由市场经济推崇个人私利的至上性,导致了共同的善的缺场。相反,共同体主义则奉行整体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竭力倡导共同体价值的首要性和共同的善的至上性。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关于权利与善,哪一个更为优先、更为根本的讨论,其实可以归结为自我(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自由主义以自然法为理论武器,将个人置于共同体之前、之上,倡导个人优先于共同体、个人价值高于共同体价值,主张个人权利的天赋性、绝对性、不可侵犯性以及个人权利与共同体的无涉性,维护个人权益是国家等共同体存在的理由。因此,自由主义视野中的个人就成为脱离具体历史、现实社会情境的抽象的人,即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称之为“无牵无挂的人”。也正是从个人先于共同体的立场出发,自由主义无法正确厘清和处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导致了个人与共同体、个人权利与共同的善等关系的紧张。共同体主义则认为,个人是共同体的产物,个人的价值和自我的认同是在一定具体历史文化环境中型构起来的,如桑德尔所说的那样,不是在共同体中选择了自我,而是由共同体形成了自我。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共同体主义者查尔斯·泰勒则认为,自我是在与他者的部分公开、部分隐蔽的对话和协商中形成的。共同体主义者也认为,任何个人权利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与其生于兹长于兹的共同体是无法割裂开来的。面对着自由主义的主张所带来的种种困境与危机,现代乌托邦主义者倡导共同体生活,重视集体理性,努力维护共同体共同的善。现代乌托邦追求的共同体生活,采用一种整体主义原则与策略来消解个人利益与共同的善之间的冲突,提升共同的善的重要性与价值位阶,从莫尔的乌托邦共同体、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共同体,再到傅立叶的法郎吉共同体和欧文的新和谐村共同体,都把维护共同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作为最高的追求。对此,理查德·萨基说到,“与契约主义相反,他们(即乌托邦主义者)严格摒弃近代的个人化过程。他们的模式只有一个目标:通过内在世俗的乌托邦,来终结社会精神与物质基础的个人化和分裂化。这个目标从一开始就设定,应当建立的是国家的集体理性,而不是个人理性;集体理性在制度和生活休戚相关的形式中得到发展;集体理性必须成为杠杆,现代危机通过它得以终结。”*郭台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第48页。
(二)重塑共同体式的联系网络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以个人优先于共同体的原则,倡导个人的独立与自主、自治,引发了现代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把个体自我推到至尊的位置,进而导致了个体的孤立、孤独、缺少依靠与必要的联系,个人成为一种原子化的存在状态,查尔斯·泰勒称之为“点状的自我”。这种原子化生存状态,也带来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无情流失。在此背景下,自由市场经济崇尚的无情竞争淹没了合作和互助,欺诈代替了友爱与信任,个体竞相追逐自身利益,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现代乌托邦主义者企图通过集体劳动、生产合作、结社、互助、协作、信任、友爱等共同体式生活方式将现代人重新纳入联系网络,改变原子化的自我生存窘境,“‘乌托邦主义者’最能恰当运用的普遍观念是:以退回到自足的公社来逃避工业时代的冷酷;在这个公社中,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将在自由合作的基础上,满足各自的需要,而不必依靠市场。”*克拉莫尼克,F·M·华特金斯:《意识形态的时代——近代政治思想简史》,章必功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在欧文的乌托邦共同体实验区内,是以合作取代竞争;在傅立叶学派所实验的模范共同体——法郎吉中,消除无政府竞争,鼓励带有情感的劳动竞赛;就连蒲鲁东也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各自分散的工人合作社制度,让工人合作社彼此交易,互换货物,互致服务。
(三)重温共同体式的家园
从传统共同体转变为现代(市民)社会是个社会分化过程,齐格蒙特·鲍曼等社会学家将现代社会称为 “个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打破了传统对人的束缚,现代人获得了自由与独立,但是也带来悖论式的现代性后果:现代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归属感与安全感,于是,向往一种温暖的家园之感和往昔的兄弟般情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重要追求,“这种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所说的代价就是没有保障或者说是危险。”*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2页。美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瑞克·佛洛姆也认为,自由对现代人有着双重寓意。一方面,人在现代社会中打破了中世纪的种种约束与枷锁,脱离了中世纪的传统权威,获得了自由,成为所谓“独立的个人”;但是另一方面,独立的个人获得解脱之后,“也失去了中世纪时代生活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安全感和相属感,于是他感到孤立与不安全”*E·佛洛姆:《逃避自由》,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面对现代性这一困境,一批不满现实的乌托邦主义者直面社会的分化或个体化社会的病灶,倡导个体归属于集体的整体主义观念,开出以共同体主义来对抗和矫正个体化社会之弊的药方:要么挑选如孤岛、荒芜等偏远或难以达到等地理空间作为理想乌托邦共同体生活之地,要么保持乌托邦共同体生活的封闭性和相对独立性,要么通过修筑水道或城墙、建立卫戍部队或审查制度来构筑共同体的安全屏障,要么倡导集体劳动、公共就餐、集体宿舍等集体生活,等等,从而企图为现代人营造一种有着强烈归属感的共同生活空间和安全温暖的幸福家园,重新找回传统共同体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淳朴敦厚的友情,唤起失去安定生活的人们强烈的共同体乡愁。
四、余 论
现代乌托邦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生活的一种批驳式反应,正如托尼·赖特所言,空想社会主义(现代乌托邦的一个部分)代表着对工业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个人主义的首次智力挑战。随着现代性的挺进,工具理性的肆意扩张导致了人们生活在理性的铁笼里,科技蔓延导致人们被技术所统治,20世纪极权主义国家出场与持续在场使得国家权力和整体利益成为个体权利的粉碎机,凡此种种,催生了现代乌托邦的反面——反乌托邦(Dystopia)的出现。反乌托邦也称为敌托邦或恶托邦,存在着文学类和政治哲学类两种不同类型。对于文学类反乌托邦,按照库玛的看法,早期乌托邦作品,甚至于也包括一些晚期乌托邦作品中,都混合着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原则,“自19世纪晚期始,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分开了。反乌托邦表达了对科学、技术、物质进步的担忧之情,它们似乎要给人类价值带来最大的威胁,对于乌托邦而言,恰恰正是这些东西提供了希望。”*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1984》《美丽的新世界》《我们》是20世纪文学类“反乌托邦三部曲”。政治哲学类反乌托邦,主要出自20世纪一批奋斗在政治哲学领域内的学者,诸如卡尔·波普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迈克尔·奥克肖特等,他们从政治哲学视角对乌托邦学说进行了批驳,阐述了乌托邦思想及其运动对人类现实政治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与乌托邦对现实超越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肯定性的向往不同,反乌托邦是对现代乌托邦所信奉的原则(理性、科学)和手段(科技、集权)发挥到极致而导致的、过分强调整体主义(集体主义)的乌托邦共同体生活对个体自由与自尊的戕害,以及对前苏联式集权社会导致灾难的批驳与反思,也是对现代乌托邦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美梦的警惕与警示。厘清从现代乌托邦超越现实怀揣梦想的起航、到社会实验的局部偏差,总结其中的得与失,对于推进我国现代性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ImageofUtopiainthePerspectiveofModernity
GAO Xin-q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Utopia as a kind humane spirit with dreams and beyond the reality has been embedded in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exhibit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ntient and the moder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utopia, modern utopi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pt of future time and progressive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 the secularism and worldliness,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and constructiveness. In terms of typology, modern utopia presents the features of the literary style, the code or theoretical type, and the community experiment and so on. While criticizing the drawbacks of modern liberalism, modern utopia advocates the holism and pursues a kind of community life.
modern utopia; ancient and modern distinction; other types; community life
B081
A
1004-1710(2017)05-0107-07
2017-04-05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ZZ2012)
高信奇(1972-),男,安徽全椒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0级博士生,南京市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
[责任编辑:张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