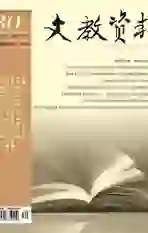从荒诞剧的话语隐喻看品特笔下的女性露丝
2017-02-23陈薇薇
陈薇薇
摘 要: 《回家》是哈罗德·品特荒诞剧中的经典之作。它一登上文学历史的舞台,其女主人公露丝就颇受评论界的争议。本文通过对荒诞剧人物对话话语中的隐喻的分析,说明露丝以开放的思想、特有的方式试图走出丈夫所代表的男权主义和“普遍真理”的桎梏,超越男性,让女性成为主体,男性降为客体,折射出男权社会下男性欲望的双重身份。
关键词: 《回家》 露丝 男权主义 自由 颠覆
长期以来,哈罗德·品特的《回家》被读者和评论家看作是对家庭神圣性的攻击,“1965年,当该剧首次登上文学历史的舞台时便震惊了伦敦的观众,人们一时还难以接受品特对家庭生活中的原始部落般本性的描述”(Albemarle of London)。当观众看到剧中唯一一位女性角色露丝在剧末并未跟随丈夫回到他们在美国的家中,而是看似满意地留在了由丈夫的父亲和兄弟组成的家庭中,当起了母亲和妓女的双重角色这一行为时,他们便不厌其烦地评价起了品特为这一家庭剧安排的离奇的结局,而同时关注的矛头直指露丝这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人们要么被动地、不假思索地接受麦克斯、列尼和乔伊的话语中描绘的露丝——妓女,因为她从母亲到妓女这一身份的急速转变使她从男性眼中的天使降为魔鬼,因此她将理所当然地不被理解;要么称她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给予其极大的同情。
然而,这位荒诞派剧作家并无意将露丝塑造成魔鬼或受害者。尽管品特研究专家、希腊学者伊丽莎白·塞克拉丽多(Elizabeth Sakellaridou)说,“品特倾向于把他的男性人物用相当人性化的笔触描写,对他们的弱点给与理解”,而“这种同情的关注却没有倾注在女性人物的身上”(Elizabeth Sakellaridou,1988:40-42),但剧作家本人却否定这样的一种倾向,他在1971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吉勒特(Jacky Gillott)的采访时说,“女性人物也各有细微的差别,可能你体察不到。但我认为女性并不都是一样的,并不都是邪恶或可怕的”(Harold Pinter,1971)。事实上,品特笔下的露丝超脱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简单刻板定义,她承载了折射出男权社会下男性欲望的双重身份——母亲和妓女,她渴望超越男性,让女性成为主体,男性降为客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露丝是一位追求自由的“新女性”。
一、露丝超脱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定义
首先看看男人们是如何评价露丝的出色之处的。麦克斯喝着她沏的咖啡,对她笑着,“这咖啡味道好极了”,“我有一种感觉,你是个一流的厨师”(Miriam Gilbert,1994:532),“你是位有魅力的女人”(Miriam Gilbert,1994:534)。泰迪非常赞同麦克斯对她的称赞,他积极地应和着,“是的,她是个非常好的厨师”(Miriam Gilbert,1994:533)。看来泰迪还是非常满意他们在美国的舒适生活的,“她在那儿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是一位很棒的妻子、很棒的母亲。她是个很受欢迎的女人。她有许多朋友。这是一种非常美满的生活,在大学里,你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我们有一幢很可爱的房子……我们拥有所有……我们拥有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环境非常令人兴奋。(停顿)我所在的系……非常成功。(停顿)我们有三个男孩,你们知道的”(Miriam Gilbert,1994:534)。从话语中得知,作为母亲,露丝为泰迪生养了孩子;作为妻子,她为泰迪提供了他所向往的母性、陪伴和舒适生活;而泰迪作为一个“上等人”,他更離不开她,要知道“在资产阶级社会,女人必须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有优雅的风度:她的美丽、魅力、智力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财富的明显外在标志”(西蒙·德·波伏娃,1998:292)。
那么,既然露丝如此让人喜爱,又生活在泰迪描述中的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她怎么会不跟随丈夫回家,而选择成为“背信弃义”的“坏女人”呢?西方的男权意识形态将女性简单地分成两类:“如果她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并遵循男权社会规范,她就是‘好女孩(good girl),即‘天使(angel);否则,她就是‘坏女孩(bad girl),即‘魔鬼(monster)。”(Lois Tyson,1999:88)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男人把顺从的女人看作天使,把叛逆的女人看作魔鬼。在普通读者眼里,露丝俨然是背叛了丈夫泰迪,她理应被打入地狱,得到魔鬼的称号,殊不知她逃离家庭是有原因的。与其说品特用了含蓄的笔调写出了露丝和泰迪婚姻生活中的细节,不如说他在这两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独到的荒诞手法为观众展示了他们交流的障碍。光“累”(“tired”)这个字就在短短的篇幅中重复出现了三次:露丝跟随泰迪回到了他老家,经过旅途奔波的她说了句“我累了”,她刚坐下泰迪又问她“累吗?”见露丝不理会他让她上楼睡觉的提议便再次问了“你累吗?”聪明的露丝显然看出了丈夫对她的“关心”实质是要她顺从地接受上楼睡觉的安排,所以她两次的回答是“只有一点点”、“不累”,简单的几个字。无足轻重的事情,却透出了她对丈夫安排的不满、反抗。而泰迪作为丈夫,他的言语却显得很陌生,“我母亲死了”,“我生在这儿,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Miriam Gilbert,1994:525)妻子早已熟知的信息他却以如此的方式重复着,一方面说明他们没有夫妻之间应有的默契,找不到比这更亲密的语言,另一方面说明丈夫没有把她当成有思想、有头脑、有智慧的平等的人。面对泰迪一连串怪诞的话语,面对他不断重复着施加要她上楼休息的压力,露丝感到窒息,她提出要去“吸点新鲜空气”(Miriam Gilbert,1994:525)。可见,这简短的序曲却映射出了她逃离家庭的动机。可以想象,当丈夫把妻子关在家中,法律、道德和宗教将她置于严格的管束之中,她的本能反抗就是挣脱枷锁,就是逃跑。泰迪代表着制定法律的男权主义和男尊女卑的“普遍真理”,而露丝的反抗、逃跑就是对男权主义和“普遍真理”的否定;她对自由的追求,就是对男性统治力量的颠覆。
二、露丝以特有的方式追求着自由
初次见到列尼,她的问候、交谈是如此地自然、大方,可列尼却反复地怀疑其与泰迪的关系,露丝对此则是沉着冷静、不卑不亢地应对,“我是他妻子”,“我们结婚了”,“我们已经结婚六年了”(Miriam Gilbert,1994:527-528),简短而坚定。列尼回避她的回答,开始以杯子为筹码向她挑衅。“列尼:把杯子给我。露丝:不。(停顿)列尼:那么我要占有它。露丝:如果你占有这只杯子,我就占有你。(停顿)列尼:要是我占有杯子而你不占有我怎么样?露丝:为什么不是仅仅我占有你呢?(停顿)列尼:你在开玩笑。”(Miriam Gilbert,1994:529)显然露丝在这场语言冲突与争斗中成了赢家,她对列尼命令式的口吻进行了挑战,从反抗到征服,她在语言上、感情上都占据了支配地位,使得列尼这个挑衅者只能以“你在开玩笑”来掩盖自己作为失败者的尴尬,然后又以无赖般的方式转换话题,编造了露丝与另一个男人私通的秘密,“无论如何,你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你和他秘密私通,他家人甚至不知道”(Miriam Gilbert,1994:529),面对如此荒谬的诬陷,露丝反其道而行之,她没有为自己的清白争得面红耳赤,也没有因为受到诬陷而委屈得流泪,而是对列尼采取进攻,“坐在我膝盖上,在我杯子里啜一大口,它凉凉的”,“躺在地上,继续,我会把水倒进你喉咙里”,“噢,我口渴”(Miriam Gilbert,1994:529),她的语言是强有力的,行为是征服性的,使列尼变得木讷,变得无所适从,而她却扔下列尼,径自上了楼。可以说,露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特有的方式挑战着、征服着、折磨着男人。
三、露丝的思想是开放的
在与大家交谈时,她毫不隐讳自己的过去,面对麦克斯的夸奖“你是位有魅力的女人”,她的回答却是“我过去是……”“我过去是……不同的……当我刚刚……遇到泰迪的时候”(Miriam Gilbert,1994:534)。她想把自己结婚前的生活状况告诉大家,却受到了丈夫的阻拦,因为丈夫害怕妻子过去的形象有悖于现在这个母亲—妻子的天使形象而遭到父亲、兄弟的嘲笑和辱骂,从而有损他维护的男性统治力量的基石。然而露丝并不害怕,她告诉列尼她曾经是身体模特,而且有时是户外的。不过当她回忆起与泰迪在美国的生活时,她的神情是黯淡的。美国,这片乐土,是泰迪当教授、受人尊敬、获得更高层次生存状态的天堂;而对露丝来说,那儿有的只是“岩石”和“沙子”,还有许许多多“昆虫”,那是一片贫瘠的荒原,她不喜欢那儿,因为在那儿她没有了感觉,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同”,甚至不能再做身体模特。
事实上,露丝需要更多的、更大意义上的自由。自古以来,女人就被当作工具而存在,她们只能通过隐蔽的婚外情来证明自己并非丈夫的奴隶,如《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红字》中的海丝特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等。然而露丝毫不回避,她在丈夫面前明目张胆地与乔伊共处,堂而皇之地走出了婚姻和家庭的大门,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而面对“天使”般的妻子顷刻间正沦为“魔鬼”,泰迪,这位代表男权主义和“普遍真理”的王子竟然被动地、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们,他似乎一点也不心痛,这或许是品特对虚伪的中产阶级男性的极大讽刺。
如果说简·爱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要求获得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独立自主的地位,从而摆脱“他者”身份,男性女性互为主体的话,那么在女性已取得选举权的品特时代,露丝则有了更高的追求,她要求超越男性,让女性成为主体,男性降为客体。摆脱了丈夫奴役的露丝机智地维护着自我的完整,她没有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成为其他男人的奴隶,而是在男人们之间周旋,尽情地施展魅力,但她理智的头脑又使她委身于多个男人却不受任何男人的支配。男人们想占她为己有,因为拥有了她,他们就能像泰迪那样得到“天使”般的呵护。听到泰迪描述了他们六年来美满的生活,露丝扮演着好母亲、好妻子的角色,“她拥有男权制要求下的女性所有的美德——女性的温柔和对家庭的摯爱:她谦逊、忍让、自我牺牲、教养督责儿女”(Lois Tyson,1999:89),这些男人们对泰迪羡慕得近乎妒忌、愤怒,对露丝的渴望也就不言而喻了。男人们想占她为己有,因为她又是“魔鬼”的化身,使他们在分享中妒忌,在欲火中受罪,使他们神魂颠倒,诱惑他们坠入地狱,在不知不觉中他们成了她的俘虏。
露丝和乔伊在楼上的房间里独处时,守在楼下的泰迪也在忍受着妒火的灼烧。他向列尼承认,是他故意吃了他的奶酪卷,“列尼,我拿了你的奶酪卷”,“好吧,对此你想怎么样?”“但是,列尼,我是故意把它拿走的”,“我看见你把它放在那儿。我饿了,所以就把它给吃了”(Miriam Gilbert,1994:538-539)。可见,此时的泰迪似乎是放弃了袖手旁观,他在妒火中开始了报复行为,他要像列尼和乔伊一样,不顾及他人的权利,不顾及“物体”的拥有者,就把他想要的东西拿走。因为他的兄弟公开地偷走了他的妻子,他也要公开地偷走他兄弟的奶酪卷,以示公平。显然在他心目中,他妻子仅仅被置于与奶酪卷相当的水平线上,作为摆放着的“物体”而随时等待被人吞噬,当然他的话语与露丝的挑战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传记作家麦克尔·比林顿(Michael Billington)认为这是一部讲述“露丝的胜利和最终获得权利”的荒诞剧,因为她是“一个精明的操纵者”(Michael Billington,1996:171)。评论家马丁·艾斯林(Martin Esslin)认为在该剧的结尾处,露丝在“管理这个家”(Martin Esslin,1973:154)。其实在女权和男权的斗争中,“露丝是最为强大的”(Steven H. Gale,1977:154),她有“能够对男人实施性操纵的能力”(Victor L. Gahn,1994:68)。
四、品特笔下的露丝留给人的思考
在该剧的帷幕落下时,阿妮塔·R·奥舍罗看到露丝“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活力”(Anita R. Osherow,1974:431)。的确,我们或许很难用“好”或“坏”两个简单的词来定义露丝,甚至无法用传统的眼光来分辨其“天使”或“魔鬼”的双重角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露丝思想开放、胆识过人,她走出了泰迪所代表的男权主义和“普遍真理”的桎梏,以特有的方式追求着自由,实现对男性统治力量的颠覆。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露丝所采取的这一特有的方式已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长此以往,将使这个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人类社会杠杆失衡,因为任何的绝对男权或绝对女权都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存在与发展。因此,《回家》的剧情在品特笔下停止了,但露丝的故事并未结束,她将继续找寻女性生存的更好方式。
参考文献:
[1]Albemarle of London. The Homecoming.http://www. The Homecoming.htm.
[2]Billington,Michael.The Life and Work of Harold Pinter.London:Faber and Faber,1996.
[3]Cahn.Victor L.Gender and Power in the Plays of Harold Pinter.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4.
[4]Esslin,Martin.Pinter:A Study of His Plays.London:Eyre Methuen,1973.
[5]Gale,Steven H. Butters Going Up:A Critical Analysis of Harold Pinters Work.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77.
[6]Gilbert,Miriam.ed.Modern and Contemporary Drama.Boston:St.Martins,1994.
[7]Irigaray,Luce.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8]Osherow.Anita R. Mother and Whore:The Role of Woman in The Homecoming, Modern Drama,1974.
[9]Pinter,Harold. Interview, Interview with Jacky Gillott,1971.
[10]Sakellaridou,Elizabeth.Pinters Female Portraits:A Study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Plays of Harold Pinter.Basingstoke:Macmillan,1988.
[11]Tyson,Lois.Critical Theory Today——A User-Friendly Guide.New York &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99.
[12]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鐵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本论文为江苏省第三批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境外研修项目成果。